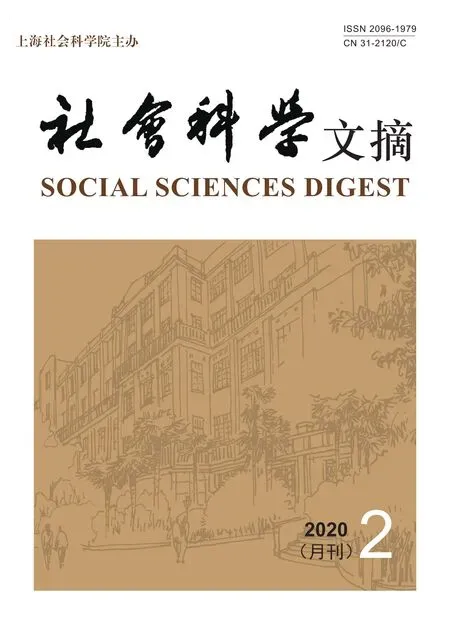集體信念的哲學分析
文/朱佳慧 王巍
在傳統的認識論中,信念的主體通常是個人。例如:畢達哥拉斯相信數是萬物的本原;王充相信人死魂滅;哥白尼相信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但在日常語言尤其是社會科學中,經常也會將信念賦予集體。例如:中國人相信自己是炎黃子孫;物理學家相信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臺(LIGO)探測到了引力波;京東公司相信自己的CEO是清白的。
這些信念往往被稱作“集體信念”。它們的共同特征是這種類型的表達式可以拆分成三個部分:主語是某個集體;謂語是一種特殊的認知類型——信念,賓語是某個具有內容的命題。這種類型的表達式被稱為“集體信念命題”。
在社會認識論中,對于集體信念主要有三種模型:奎恩頓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多數人解釋”模型;吉爾伯特在20世紀80年代末討論了共同承諾模型;塞爾提出了合作模型。這幾種模型也可以分為累積主義和非累積主義兩種進路。累積主義把集體信念看成是集體成員個人信念的累加,他們認為只要集體成員的個人信念一旦確定,就存在一個特定的“匯總程序”,能夠將集體成員的個人信念匯總成集體信念。非累積主義主張集體信念不能還原為個人信念,集體信念不是由集體成員的個人信念決定的。
然而,這三種模型也有各自的問題。本文將分門別類介紹三種模型及其問題,并嘗試給出解決方案。
多數人模型及其問題
20世紀70年代,英國哲學家奎恩頓首先提出了一個叫做“多數人解釋”的模型,開辟了對于集體信念進行專門研究的先河。多數人模型非常接近于我們的日常直覺,認為集體信念是由集體中大多數成員的個體信念匯總而成。
多數人模型可以有強版本與弱版本。強版本提出要求集體的全體成員都共同相信:集體G相信P,當且僅當G中所有成員都相信命題P。弱版本只需要集體的大多數成員相信就可以了:集體G相信P,當且僅當G中至少有m名成員相信命題P,此處的m通常要過半數,對于重大問題(如修改憲法)則要達到2/3以上。
多數人模型很符合常人的直覺,但也受到很多哲學挑戰。首先,大家共同具有的秘密信念似乎不屬于共同信念!例如,在童話《皇帝的新裝》中,大家都心知肚明皇帝沒有穿衣服,但都沒有說出來,這就不算共同信念。
對此,多數人模型可以進一步修正。我們稱P是集體G中的共同信念,當且僅當下述條件均成立:(1)G中的每個人都相信P;(2)G中的每個人都相信(1);(3)G中的每個人都相信(2);……多數人模型修改為:集體G相信 P,當且僅當G中所有成員(或大多數人員)共同相信。
但即使是這樣的修正也會遇到兩大問題:集體中很有可能包含無此信念之人,例如出生不久的嬰兒;集體中的成員通常并不相互認識,無法形成往復循環。
其次,伯德提出了不相關性反駁:隨意挑選出一些人構成一組(如工作證尾號為單數),都相信“雪是白的”這類事實命題以及“2+2=4”這類重言式命題——但這好像并不足以構成集體信念!
對此,多數人模型往往提出“因果性條件”作為修正。因果性條件要求信念P是由集體G產生的:集體G相信P,當且僅當G中所有成員(或大多數人員)共同相信P,并且P是由G產生的。
然而,吉爾伯特認為“因果性條件”也解決不了問題。她提出反例:假設K市的每個青少年都在報紙上讀到一則新聞報道——“K市的青少年都相信吸食大麻是有害健康的”,K市的每個青少年由此繼續堅持“吸食大麻有害健康”的信念。在這個例子中,K市青少年持續持有“吸食大麻有害健康”的信念乃是他們自身信念所導致的,滿足了因果性條件。但這并不足以使得K市的青少年構成一個集體。
最麻煩的是利斯特與佩蒂特指出,多數人模型會遇到“推論困境”。科學共同體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場景——三位科學家要對某個天體上是否存在外星生命作出判斷,他們面對著如下三個待判斷的命題:(1)根據理論T,只要存在還原性大氣、水蒸氣和放電現象的星球,那么該星球上就有80%的概率存在生命體;(2)星球S上存在還原性大氣、水蒸氣和放電現象;(3)星球S有80%的概率存在生命體。
如果科學家認為命題(1)和(2)是成立的,那么根據邏輯,他必然要承認命題(3)也是成立的。這是個人信念的一個基本邏輯屬性。當我們談論集體信念時,我們自然也期望它能具有這一特征。然而在多數人模型中,集體信念并不總是具備這種屬性。例如,假設三位科學家對三個命題的判斷如下表所示:

按照多數人模型,集體信念是由集體中大多數成員的信念所決定的,因此科學家組成的集體的信念就如上表最后一行所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集體信念就不具有邏輯一致性:它認為根據理論T,只要存在還原性大氣、水蒸氣和放電現象的星球,那么該星球上就有80%的概率存在生命體,并且星球S上存在還原性大氣、水蒸氣和放電現象,但是它同時認為并非星球S有80%的概率存在生命體。
利斯特與佩蒂特甚至進一步證明:不存在同時滿足普遍性、匿名性和系統性的判斷匯總函數F。
共同承諾模型及其問題
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吉爾伯特在《論社會事實》一書中大規模討論了集體信念的問題,并在此以后對于這個問題又相繼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論文。
吉爾伯特認為,集體G相信P,當且僅當G中的成員共同接受P。其中,G中的成員共同接受P,當且僅當如下這點是G中的共同知識,即G中所有成員公開表示愿意與其他成員一起共同接受。
吉爾伯特要求,集體成員在一個儀式性的時刻,通過類似于“聯名簽署公告牌”的行為,使自己處于一種負擔義務的狀態中。例如,斯坦福大學有“榮譽守則”共識:學校不安排監考,但學生有遵守學術誠信的義務。因此,“斯坦福大學師生相信老師與學生都遵守榮譽守則”使得斯坦福的師生都需要負擔義務:老師不能安排監考,否則會被投訴;學生不能作弊,否則會被處分。
吉爾伯特以化學中的化合物與混合物做類比:水是新的化合物,并非氫與氧的混合加總。因此,她認為“共同接受”或“聯合承諾”不可以化約為個人承諾的加總,復數主體也不可以化約單數主體的加總。復數主體在本體論上乃是一種新的事物。
吉爾伯特強調集體信念的客觀性與涉及集體。客觀性是指,集體信念一旦形成,它就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吉爾伯特還提出了“成員知識原則”:一個集體G不可能擁有集體信念P,除非G中的成員都知道G相信P。她設想,一所大學中有兩個委員會,分別是圖書館委員會和飲食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是同一批人。這些人都相信,這個學校里的學生在日常飲食中攝入了過多的淀粉。我們可以說“飲食委員會相信學生攝入了過多的淀粉”,但不能說“圖書館委員會相信學生攝入了過多的淀粉”。因為這個信念和圖書館委員會這個特定集體之間缺少一種關聯,這個缺失的關聯就是所謂的“涉及集體”性質。
吉爾伯特進一步區分了“涉及集體”和“創造集體”這兩個概念。例如李·斯莫林在《物理學的困惑》一書中,回顧了弦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弦理論科學家因為與相信標準粒子模型的科學家觀點不一,最終形成了自己的集體。
然而,共同承諾模型也至少面臨兩大問題。一方面,并非所有的集體信念都是“承諾”。英國日常語言學派代表、牛津大學教授奧斯汀主張“以言行事”:我們的言語都有做事的功能。例如,婚禮上新郎與新娘說“我愿意”,他們并非陳述事實,而是在給出行為承諾。但是,并非所有的言語都有做事功能,有些就只有陳述功能。例如,如果有斯坦福學生違反榮譽守則,那么斯坦福大學有權開除該學生;但如果有個別中國人基于學術原因,質疑中國人是炎帝與黃帝的后代,我們似乎無權開除他的中國國籍。
另一方面,“共同”對于集體信念可能也是過高要求。在現實中,集體成員很難百分之百地共同相信或承諾。即使是修改憲法這樣的重大決定,也只需要2/3的多數就可以了。
合作模型及其問題
塞爾以意向性概念聞名于世。他把意向性分為兩種:認知與意志。其中認知又可以分成三種:知覺、記憶、信念;意志也可以分成三種:行為中意圖、在先意圖、欲望。他進而指出人類社會中的制度性事實:諸如政府、家庭、雞尾酒會、暑假、工會、棒球和護照等東西都可以化約為集體意向性,他們在本質上都是集體意向性穿上了形形色色的外衣而表現出來的事物。
他對于集體信念提出了“合作模型”:無論如何,我們的分析都不能與如下的基本事實相矛盾——即集體是由個人組成的。由于集體只是由個人組成的復合物,因此類似于集體心智這樣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謂的意識現象只能存在于個人的大腦之中。
塞爾讓我們想象哈佛商學院的一群畢業生的兩種情形,他們在教學中信奉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相信通過每個人的自利與富有,最終可以有利于人類。第一種情形是他們每個人都此信念,并且每個人都知道其他所有人也是這么想的,因為他們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但是他們之間不存在任何合作,甚至他們的意識形態都是“不應該合作”。第二種情形是,他們臨畢業之前達成共同契約,通過自利富有但不合作的方式去改造世界。在兩種情形中,這些畢業生的行為模式完全一致。但塞爾認為,第一種情形式不構成集體信念,第二種情形才是,因為后者存在更高層次上的合作。
然而,塞爾的合作模型也可能遇到兩個問題。一是設想荒島上僅剩下魯濱遜一人,而地球上的其他人類因為重大災難而毀滅了。但魯濱遜并不知情,仍然在腦中有著與他人合作的意識,例如保留證件與貨幣。在此情形中,魯濱遜的信念滿足合作模型,但似乎無法稱為“集體信念”!
另一問題是普特南的“缸中之腦”。我們可以設想給缸中之腦以適當的腦電波刺激,使得他們誤以為在與別人合作,共同經營,一起玩耍。但我們也很難認為這些缸中之腦共同形成了集體信念。
可能的解決方案
關于集體信念的三種模型都各擅勝場,但都有缺陷。筆者以為,這可能與“集體”概念本身的含混有關,因此帶來“集體信念”的多元化。筆者建議,把“集體”進一步細分為集合、機構與社群,再對各自的信念做分門別類的研究。
集合是個人的松散組合,其特征是集合行為可以還原為個人行為的總和。例如,圍棋團體賽的結果可以由每個成員的具體比賽結果累加而成的。機構是建制化、結構化的整體,其行為無法還原為個人行為的總和。例如,足球隊的比賽結果雖然有賴于每個球員的具體表現,但優秀球員并不必然組成優秀球隊。社群則介乎集合與機構二者之間,一方面比集合更加緊密,另一方面又不像機構那么建制化。例如,如果支持超弦的物理學家不贊同,可以獨立出來形成自己的學術共同體。
本文最初提到的集體信念的三個例子,其主語“中國人”“物理學家”“京東公司”分別對應的就是集合、社群與機構。因此筆者建議,最好不要籠而統之地作為一個概念來分析,而是分為集合信念、機構信念、社群信念三個概念來處理。
對于集合信念,可以適用多數人模型。多數人模型所遇到的很多挑戰,其實是針對機構信念或社群信念,對于集合信念就不成立。例如,集合信念可以不需要共同信念。即使每個中國人不知道其他中國人是否信奉“人類的非洲起源說”,但只要中國人相信“非洲起源說”的比例占了多數,我們仍可以說“中國人相信人類起源于非洲”。
同樣的,不相關反駁也主要是針對機構信念或社群信念。我們完全可以建立任意人群拼湊的集團信念,例如“北京市汽車尾號為3或8的車主相信周三是最糟糕的日子”(因為他們的車輛限行)。
至于利斯特與佩蒂特擔心的“推論困境”,集合信念確實可能無法同時滿足普遍性、匿名性和系統性,但正如阿羅不可能定理同樣表明,不存在的選舉制度。但真正機構決策時,可以通過明確規則來克服。例如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希拉里贏得了選民的多數;但是特朗普贏得了更多選舉人票。根據美國“贏者通吃”的選舉規則,最終是特朗普當選總統。
對于機構信念是如何產生的,可能要做具體的社會學研究。例如,美國總統選舉是“贏者通吃”的選舉人票制度;中國政府決策是民主集中制,例如毛主席當年成功說服政治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大多數公司采納董事會制度,股權多數(而非人數的多數)決定公司決策;但也有少數公司(如阿里巴巴)是合伙人制度,公司創始人有更大的話語權。
機構信念需要最低程度的共同承諾。例如,即使京東公司有個別員工不相信CEO是清白的,但除非主動辭職,否則不能公開挑戰公司決定。但是,并非所有集體信念都是需要共同承諾的機構信念,例如集合信念不太需要共同承諾,社群信念需要的共同承諾程度則更低。
此外,機構信念需要最低程度的合作。如果機構成員都不合作,機構就可能解體,也就無所謂機構信念了。但是同樣的,并非所有集體信念都是需要合作的機構信念,例如集合信念不太需要合作,社群信念需要的合作程度也更低。
社群的建制化與緊密性介乎集合與機構之間,也可歸為“社會網絡”。因此社群信念的共同承諾與合作程度也是高于集合信念,但低于機構信念。在社會學中,組織社會學有對社會網絡有專門的研究。
筆者之所以建議,將集體信念進一步細分為集合信念、機構信念與社群信念:一方面符合分析哲學的傳統,分門別類地研究往往能夠避免籠而統之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哲學更好地與科學前沿緊密聯系,集合、機構、社群等概念可以分別對應于社會科學中的市場、科層制、社會網絡等研究,從而讓哲學探討積極吸納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