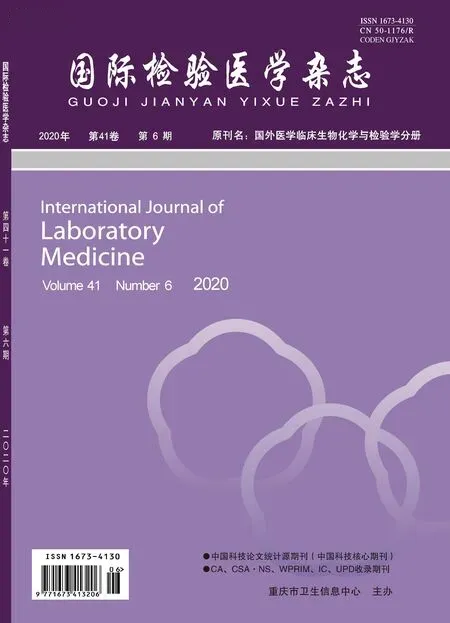呼吸系統疾病并發抑郁癥的分子機制研究進展
黃慶暉,胡銳寧 綜述,袁 良 審校
(1.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廣東廣州 510000;2.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廣東廣州 510000;3.廣東省南山醫藥創新研究院,廣東廣州 510000)
呼吸系統常見疾病如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肺癌等,此類疾病多數病程長、病情復雜,從而容易并發焦慮、抑郁。盡管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不斷加深,尚缺乏概括總結,因此,非常有必要理清楚呼吸系統疾病并發抑郁的分子機制,本文將就此作以綜述。
1 ARDS并發抑郁癥及其分子機制
ARDS是以肺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強、雙肺彌漫性炎癥浸潤為主要病理變化的一種危重疾病,其以氧合指數≤200 mm Hg和進行性低氧血癥為特征,臨床上主要表現為呼吸窘迫、肺功能嚴重下降和嚴重缺氧[1]。ARDS發病率高,且病死率隨發病時間延長而增加,在美國每年約有20萬例,病死率約為35%[2]。近年來,隨著醫學的進步,危重癥患者的生存率逐年升高,但是患者在出院后普遍存在一些預后問題,尤其是ICU幸存的ARDS患者神經、心理變化和認知、記憶能力明顯下降。一些研究表明,遭受過肺損傷(包括ARDS)與后期發生抑郁癥密切相關[3]。此外,對ARDS患者的隨訪跟蹤研究也發現其出院后1~2年內嚴重抑郁發生率為16%~23%[4],且53%ARDS患者存在腦萎縮病變及神經認知功能障礙[5]。關于ARDS抑郁發生的細胞分子機制,目前主要有3類理論。
1.1炎性反應介導學說 炎性反應介導學說已成為最為主流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系統性炎性反應與ARDS并發抑郁密切相關,且C反應蛋白和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細胞介素(IL)-6、IL-1β等炎癥介質的水平與ARDS并發抑郁的嚴重程度有關,除了系統性炎癥之外,血管炎癥可能也發揮了重大作用。ARDS的發病不僅與機體促炎和抗炎平衡被打破有關,而且與復雜炎性細胞因子的級聯活化相關,其中IL-6與 IL-8 是引發ARDS細胞因子風暴的關鍵炎性細胞因子。研究也發現在老年抑郁患者血清中的IL-1β和IL-6水平顯著高于健康人[6-7],這說明促炎因子水平的升高可能與老年ARDS并發抑郁癥的病理生理有關。近期的一項研究報道,ARDS導致的抑郁樣癥狀是通過影響嗜中性粒細胞和神經NADPH信號通路實現的[8-9]。因此,ARDS并發抑郁可能是由于刺激引起的炎性反應的級聯放大效應,導致了神經炎癥,造成神經功能損傷,最終引發了抑郁。
1.2神經內分泌功能障礙理論 神經內分泌功能異常,如膽堿能和腎上腺素能神經功能效應紊亂等,導致一些神經遞質如5′羥色胺、多巴胺的分泌異常,進而神經元損傷,引發抑郁等精神障礙性疾病。
1.3酸中毒和電解質紊亂理論 酸中毒和電解質紊亂理論認為ARDS抑郁的發生主要是由腦缺氧和CO2潴留引起的。ARDS患者多數呼吸功能障礙、肺功能不全、換氣不足,其肺泡PO2減低、PCO2增高,因而動脈血中的PCO2增高,pH降低,引起高碳酸血癥和電解質紊亂等,進而造成起呼吸性酸中毒和CO2麻醉,使腦組織處于低氧狀態,引起腦組織水腫。而腦組織水腫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嚴重影響,導致抑郁等精神障礙的發生。
綜上所述,ARDS抑郁的發生主要與系統性炎性反應、神經內分泌功能障礙、呼吸性酸中毒和電解質紊亂等的影響有關。
2 COPD并發抑郁癥及其分子機制
COPD是一種可以預防和治療的常見疾病,以持續氣流受限為特征,通常是由于患者明顯暴露于有毒顆粒或氣體環境中引起的氣道和/或肺泡的慢性炎癥[10],在臨床上常表現為呼吸困難、慢性咳嗽、咳痰、胸悶等且反復發作[11],一旦這些癥狀不能及時緩解,患者就會出現疼痛、害怕、焦慮及呼吸不暢導致的乏力等各種身體不適[12],而且長期處于這種狀態會誘發其他疾病,影響身體功能,使患者的生活質量不斷下降[13]。
COPD患者肺功能改善后仍可不同程度地出現神經系統相關疾病,如抑郁和認知記憶功能減退等[14-15],有學者報道,在75例 2級及以上COPD患者中,28%出現了抑郁(HADS量表診斷其評分≥8),而另外有研究報道,在302例COPD 患者中(包括106例1級患者和 196 例2級及以上患者),45%出現抑郁癥狀(HADS量表診斷其評分≥8)。關于COPD并發抑郁癥的發生率,不同研究的差異比較大,大致在8%~80%,但一致認為COPD患者比同齡健康人群更容易患抑郁[16-17]。而且,吸煙或煙草煙霧暴露與大腦功能退化或更嚴重的抑郁癥狀密切相關。COPD患者出現抑郁后,可以引起自我封閉、與周圍人群溝通減少、治療依從性降低等一系列后果,致使病情反復發作和住院,而這又加重了COPD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關于COPD并發抑郁癥的細胞分子機制,目前有以下3種理論。
2.1炎癥細胞因子理論 炎癥細胞因子理論認為COPD患者肺組織中的巨噬細胞產生大量IL-8、IL-6、TNF-α和花生四烯酸等炎性介質,其中TNF-α促進炎癥細胞的游走和浸潤,IL-8誘導炎癥介質的大量釋放,放大炎性反應,加重氣道炎癥,導致肺組織結構改變。此外,這些炎癥介質可以隨血液流動,并通過血腦屏障缺失的位點由特定載體蛋白主動轉運透過血腦屏障進入腦內,或被動轉運至腦實質內,然后與腦內的細胞因子或相應的受體相結合,影響了機體內分泌功能,進而引起全身炎癥和神經炎癥或神經遞質分泌失調、神經功能受損和情緒調節失常,最終導致抑郁[18]。而且COPD患者的血液及肺泡灌洗液中IL-6水平明顯升高,抑郁癥患者血液中的IL-6水平也明顯升高,研究也發現血清中IL-1β和IL-6水平均與COPD并發抑郁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也有研究認為,COPD并發抑郁癥可能與吸煙或煙草煙霧暴露有關,因為吸煙的COPD患者出現抑郁的概率更高[19],而且抑郁的個體大多有吸煙史。這可能是因為煙草中的尼古丁被吸入后激活機體內的尼古丁乙酰膽堿受體,其不僅直接引起氣道和肺部炎癥,也能夠激活神經炎癥,從而導致肺泡灌洗液和海馬區都出現IL-1β和IL-18的異常表達[20],進而引起一系列全身性炎性反應,最終導致COPD患者抑郁的發生和發展。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在COPD患者的肺組織和重度抑郁癥患者的單核細胞中均可檢測到活化的NLRP3炎性小體(轉錄后的調節因子)表達[21],其可顯著誘導IL-1β和IL-18成熟,表明COPD并發抑郁癥可能與NLRP3的激活有關。同時,海馬區的IκB降解和核轉錄因子(NF)-κB p65磷酸化,可增強IL-1β和IL-18的轉錄,表明NF-κB炎癥通路在COPD合并抑郁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22]。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研究認為炎癥通路如Toll樣受體(TLR)信號通路、NF-κB信號通路等炎癥相關通路在COPD并發抑郁中具有關鍵作用。
2.2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功能障礙理論 HPA軸是神經內分泌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控制對生理、心理壓力的反應和應激激素的合成。當刺激作用于機體時,刺激機體合成和釋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和糖皮質激素進入體循環,并通過血腦屏障進入大腦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發揮作用。健康人群的HPA軸具有明顯的晝夜節律的特征,包括醒來時皮質醇增加和對一系列刺激做出反應[23-24],一些研究發現,COPD患者的HPA軸活性降低,血清中皮質酮水平顯著升高,過高的皮質醇/酮和抑郁的發生密切相關,進一步研究發現慢性注射皮質酮會導致嚙齒類動物抑郁。成年人的抑郁和對壓力的反應失調密切相關,這反映在HPA軸活性的增加上,在重度抑郁患者中,HPA軸有多種改變,包括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水平升高、ACTH和皮質醇升高、糖皮質激素敏感性降低等。
2.3其他理論 腫瘤相關抗原黏蛋白1(MUC1)是一種跨膜黏蛋白,其在急性氣道和肺部感染中發揮重要的抗炎作用。據報道,KL-6(MUC1蛋白的一種亞型)水平在穩定的COPD患者的肺、血漿和痰中增加,并受到年齡和吸煙的影響[25],而吸煙又是抑郁癥發生的高危因素,因此,MUC1可能與COPD并發抑郁癥有關。此外,也有理論認為 COPD 抑郁是由機體的氧化應激反應和免疫應答失調等介導的。
3 肺癌并發抑郁癥及其分子機制
肺癌是臨床上最為普遍的惡性腫瘤,全球每年約有140萬人死于肺癌,隨著空氣質量的下降和吸煙人數的增多,30年來我國的肺癌病死率上升了 465%[26],癌癥病情復雜、進展迅速、轉移率高,初期癥狀輕甚至以無癥狀為主,加上大眾防癌意識淡薄,一旦確診,多數已為晚期,治愈率極低,素有“談癌色變”之說。肺癌疾病本身的嚴重性給很多患者造成了嚴重的心理負擔。此外,癌癥患者不僅要遭受軀體疼痛及放化療帶來的惡心、嘔吐、疲乏、脫發和貧血等各種不良反應,還要承受昂貴的治療費用所致的巨大經濟壓力,因此,常常會出現恐懼、無助、悲觀、絕望等負性情緒。長期處于這種情緒壓力下,會導致抑郁的發生。據國內報道,肺癌患者抑郁發生率為39%~55%。MUSTIAN等[27]研究顯示,45%~59%的肺癌患者存在疼痛和軀體癥狀,其通過神經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影響腫瘤的發展和轉歸,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存在與心理因素密切相關的軀體癥狀。
肺癌并發抑郁癥患者可表現出焦慮的心情(如絕望、偏執以及疑病性等神經癥狀)、惡劣的心境(如抑郁情緒、興趣喪失、交流溝通障礙等)以及自主神經功能紊亂(以睡眠障礙為主),這可能是器質性病變的直接影響,也可能是心理精神疾病的影響。對于肺癌抑郁的發病因素,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肺癌抑郁的發病的細胞分子機制卻沒有統一的定論,總體來說,發病的細胞分子機制可以歸為以下4類。
3.1炎性反應理論 該理論認為在肺癌抑郁的發生進展中,炎癥介質起著重大的作用。研究發現[28],肺癌并發抑郁患者血清炎性細胞因子如IL-1β、IL-6、TNF-α水平較健康人群升高,且抑郁的嚴重程度越高,這些炎癥介質的水平就越高,證實了這些炎癥介質參與了肺癌抑郁癥的發生發展,并與肺癌并發抑郁癥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
3.2免疫應答理論 該理論認為機體的抗腫瘤免疫效應主要是以細胞免疫為主,其中T細胞是機體抗腫瘤免疫的中心,且輔助性T細胞(CD4+)與抑制性T細胞(CD8+)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相對平衡以協調機體的免疫平衡,兩者的比值能夠作為抗腫瘤的免疫調節中的重要指標[29]。此外,T細胞亞群CD3+細胞、CD4+細胞、CD4+/CD8+細胞比值及自然殺傷細胞(NK細胞)與腫瘤的發生、進展、轉移和預后也是密切相關。腫瘤患者的T細胞處于受抑制狀態,表現為CD3、CD4細胞數量降低,CD8+細胞數量增多,CD4+/CD8+比值異常。由此可知,肺癌抑郁患者的機體免疫應答功能失調。有研究表明,與非抑郁、焦慮肺癌患者相比,抑郁與焦慮肺癌患者免疫力明顯低于非焦慮、抑郁肺癌患者,它能夠減輕機體對腫瘤的抵御作用還利于病情的進展,從而加重肺癌患者的抑郁情緒,形成惡性循環。
3.3神經源性因子理論 該理論認為肺癌刺激中樞神經系統,誘導一些神經源性因子如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神經元烯醇化酶(NSE)等的過量產生,導致神經元損傷,進而誘發抑郁。研究表明,肺癌患者的血清中NSE水平明顯升高,且其水平與抑郁癥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30],而且抑郁癥患者血清中 BDNF水平降低、NSE水平升高。因此,肺癌并發抑郁的機制可能與中樞神經系統中過量的BDNF和NSE等神經源性因子有關。
3.4其他理論 如自主神經調節紊亂理論,認為肺癌患者的機體調節能力降低,一些生理病理的改變超出其調節能力,給其他并發疾病創造了便利條件,如肺癌患者發生抑郁的概率遠遠高于健康人。脂類物質代謝紊亂、單胺類物質的過量分泌、各種促凝物質和血栓素的釋放、心率改變和血壓水平異常等,其結果是加重肺癌患者的軀體癥狀,從而導致其抑郁情緒加重。HPA軸和交感神經系統(SNS)功能紊亂理論認為肺癌患者血液中的炎癥因子可導致HPA軸活性增強和SNS興奮,產生過多的神經因子,從而影響不良情緒的產生,導致抑郁,而抑郁情緒能夠通過HPA軸促進肺癌發生、發展。
4 總 結
呼吸系統主要的疾病,ARDS,COPD和肺癌等,它們并發抑郁的共同機制都是呼吸系統細胞類因子風暴和炎癥級聯反應,促炎因子與抗炎因子失衡等引起的神經系統炎癥,表現為患者血液中TNF-α、IL-6、IL-1β等炎癥介質的水平顯著異常;5′羥色胺、多巴胺等神經遞質的分泌紊亂。此外,ARDS并發抑郁的分子機制還與腦缺氧損傷和酸中毒及電解質紊亂密切相關。COPD并發抑郁的機制和HPA軸功能障礙是分不開的,HPA軸功能障礙引起ACTH和糖皮質激素等通過血腦屏障損傷神經組織。肺癌并發抑郁的機制主要是肺癌患者由于癌細胞的侵蝕,機體的免疫力低下,免疫應答嚴重失調,各臟器功能障礙等導致的自主神經調節紊亂、機體新陳代謝紊亂等綜合因素。
呼吸系統疾病并發抑郁癥的分子機制錯綜復雜,不同疾病涉及的分子機制不同,除本文提到的機制以外,還有氧化應激反應理論,機體內分泌功能障礙等理論。總之,人是一個有機整體,呼吸系統的疾病會影響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消化系統等的功能,最終表現出來的是各個系統的綜合癥狀,這就提示臨床醫生在糾正ARDS患者低氧血癥、改善COPD患者呼吸和減輕肺癌患者疼痛等的同時,要關注由此誘發的抑郁等其他疾病及患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早期發現并干預神經系統功能的減退,從而幫助呼吸系統疾病患者降低并發抑郁癥的可能性,提高生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