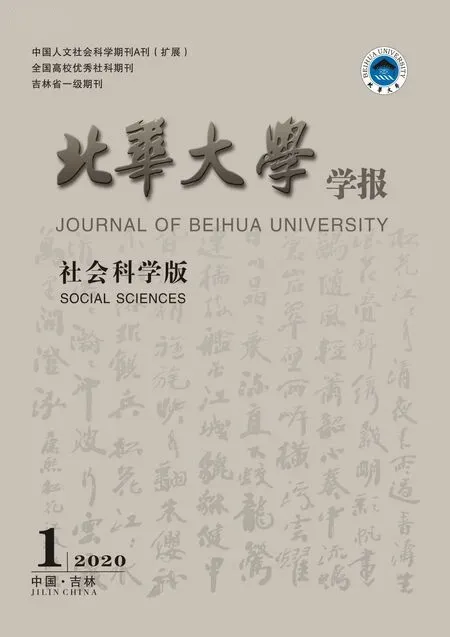上古音零札十則
孫玉文
平時讀古書,頗留心上古音問題。每有一得之愚,常常筆錄下來,寫成札記。不意竟集腋成裘,洋洋可觀。不敢藏拙,今錄出十則,敢請海內外博雅有以教正。
一、窈窕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陸德明《釋文》 “窈,烏了反。窕,徒了反。”現在已經知道“窈窕”是一個聯綿詞。“窈”,從“幼”聲,從“幼”聲的字,一般歸入幽部,“窈”影母幽部;“窕”,從“兆”聲,從“兆”聲的字,歸入宵部,“窕”定母宵部。這樣,“窈窕”只能看作是準疊韻聯綿詞。
但是聯綿詞的讀音常常有溢出常規歸部者。“窈窕”可能也是這種情況。安徽大學藏竹簡“窈窕”作“要翟”。“要”,影母宵部,跟“翟”正好可以構成嚴格的疊韻。
“翟”,一般歸入定母藥部。從“翟”得聲的字,中古分屬平聲、上聲、去聲、入聲,以歸入聲、去聲者為最多。歸入平聲和上聲的只有“嬥”字,它有“徒聊”和“徒了”二切。《廣韻》徒聊切:“嬥,《聲類》云:細腰皃。”徒了切:“嬥嬥,往來皃。《韓詩》云:嬥歌,巴人歌也。”“細腰皃”和“巴人歌”這兩個義項來自上古,《說文》女部:“嬥,直好皃。一曰:嬈也。從女,翟聲。”大徐本注音:“徒了切。”小徐本注音同。因此,這個“嬥”上古應該歸宵部,《漢語大字典》就是這樣處理的。據此以推,“要翟”原來應該都是宵部字,它們是疊韻聯綿詞。
“窈窕淑女”中的“窈窕”是否也是疊韻聯綿詞,而非準疊韻聯綿詞,這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確定,很有可能,“窈窕”的“窈”已經變入宵部。
二、“存”字的諧聲和韻部
“存”是個形聲字。大徐本《說文》子部:“存,恤問也。從子,才聲。”小徐本子部:“存,恤問也。從子,在省。臣鍇曰:在亦存也,會意。”后面的字形分析,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改為“從子,在省”:“大徐本作‘才聲’,今小徐本作‘在聲’,依《韻會》所引正。”[1]743段玉裁說小徐本作“在聲”,不確,因為“存”字里面沒有“在”這個偏旁,應該作“在省聲”。今所見小徐本是作“在省”,跟《古今韻會舉要》一致。《說文系傳考異》:“一本《系傳》作‘在聲’。按臣鍇曰:‘在亦存也,會意。’則舊本原作‘在聲’矣。然玩文義,當云:‘在省聲。’”[2]《說文系傳考異》的意見是對的,因為《說文》原文作“在省聲”,而徐鍇感覺到“存”和“在”讀音相遠,所以才有后面的“在亦存也,會意”之語,試圖糾正《說文》。無論如何,大小徐《說文》中“存”都是諧聲字。說“存”是“在省聲”,還不如說是“才聲”,“在”本來就是“才聲”。
《古今韻會舉要》卷五“存”小韻“存”:“《說文》:‘恤問也。從子,在省。’徐曰:在亦存也。會意。《廣韻》亦察也。”[3]這個說法應該是采用了小徐本的見解所致,尤其是《古今韻會舉要》特意點出“徐曰”, 表明所引《說文》之來源,進一步確證了《古今韻會舉要》是據小徐本的校改成果,非《說文》之舊說。段玉裁據此校正《說文》,恐怕有問題。
(一)“存”從“才”聲的根據
段玉裁之所以借助大小徐版本有異和《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作“在省”,改“才聲”為“在省”,是因為他看出“存”和“在”上古韻部相差甚遠。《說文》土部:“在,存也。從土,才聲。”可見“在”仍然是形聲字,從“才”聲。“在”和“才”上古都是之部字,說“在”從“才”聲很好理解。“存”是文部,如果“存”從“才”聲,就不好懂。因此,他采用《古今韻會舉要》所引,將“存”看作是會意字。
其實,將“存”解釋成從“在”省,是取“在”的“存問、問候”義。《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二三子皆使寡人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杜預注:“在,存問之。”《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存往者,在來者。”王聘珍《解詁》:“存,恤也。”“在”既然有“存問,問候”的意思,而“存”也有此義,那么將“存”字中的“才”改為一個意符,似乎有道理。
但是此說根據不足。
其一,如上所述,大小徐《說文》中“存”都是諧聲字,就這一點來說,“存”在許慎那里,應該是一個諧聲字,而不是會意字。《古今韻會舉要》說“存”是“在省”,根據不足。
其二,說“存”是從“在”省,今之所見古文字中沒有找到“存”從“子”、從“在”的這種不省形的字形。“存”的出土材料,最早見于戰國時期,如《古陶文字征》(高明、葛英會編著,中華書局,1991)“齊魯4·84”中的字形(見圖1)。因此從“在”省之說,只是一種推斷,沒有漢字材料的支撐。事實上,“才”在出土文獻中就可以用作“在”的,詳見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4]634-636
其三,如果“存”從“在”省,那么它是“在”省掉了意符,保留了聲符。漢字省形中,省掉一個字的意符,保留其聲符,讓這個聲符代表該字,在另一個會意字中作意符,這種情況應該是很罕見的。據《說文》鹿部:“麀,牝鹿也。從鹿,從牝省。”就是屬于這種情況,而“牝”是“從牛,匕聲”的形聲字,但是這類例子畢竟不太多。
其四,就詞的層面來看,“存”和“在”有很多相同的詞義,不僅僅是在“存在,生存”的意義上。例如:
(1)“存問,問候”義
“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二三子皆使寡人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杜預注:“在,存問之。”《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存往者,在來者。”
“存”,《周禮·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遍存,三歲遍覜,五歲遍省。”鄭玄注:“存、覜、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戰國策·秦策五》:“陛下嘗軔車于趙矣,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高誘注:“存,勞問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史記·魏公子列傳》:“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文選·曹操〈短歌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李周翰注:“存,問也。”
(2)“省視,鑒察”義
“在”,《書·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舊題孔傳:“在,察也。”《左傳·文公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杜預注:“又未嘗涉知軍事。”
“存”,《禮記·禮運》:“故圣人參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鄭玄注:“存,察也。”《荀子·修身》:“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王先謙集解引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漢王充《論衡·定賢》:“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黃暉校釋:“存亦察也。”
除非我們能證明“存在,生存”義、“存問,問候”義、“省視,鑒察”義之間有引申關系,“存”和“在”才有同義詞平行引申的可能性,否則,“存”與“在”有相同的假借,就很難說得過去,那只能承認“存”與“在”原來讀音相近才可以。如果讀音相近,“存”從“才”得聲也就沒有問題了。“存在,生存”義、“存問,問候”義、“省視,鑒察”義之間可能有引申關系,但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論證,至少“存問,問候”義和“省視,鑒察”義之間存在著引申關系。
即使《說文》真說“存”是“在省”,但考慮到如果“在”“存”是同源詞的話,我們仍然可以認定“存”是從“才”得聲。總之,《說文》說“存”是形聲字,這未可輕易否定。
(二)“存”的上古韻部
在“存在,生存”這個意義上,“存”和“在”應該是同源詞。“在”從“才”聲,而“才”是之部;“存”,《詩經》時代起已經是文部了。
韻文材料如:
《鄭風·出其東門》:“出其東門,有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其中“門”“云”“云”“存”“員”都押文部。
《易·系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其中“存”“門”押文部,段玉裁《群經韻分十七部表》收錄了,江有誥《群經韻讀》失收。
《漢書·王式傳》:“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服虔注:“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注:“其辭云:‘驪駒在門,仆夫具存。驪駒在路,仆夫整駕’也。”其中“存”“門”押文部。段玉裁《群經韻分十七部表》注:“《大戴禮·驪駒》詩,見《漢書》服虔注。”這個注釋不太準確。
《老子》第四章:“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其中“紛”“塵”“存”“先”押文部。
《老子》第六章:“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中“門”“根”“存“勤”押文部。
《老子》第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中“先”“存”押文部。
《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其中“勤”“存”押文部,“行”“亡”押陽部。
《荀子·議兵》:“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這里有語音技巧,“存”“神”是真文合韻,“過”“化”都是歌部。江有誥《先秦韻讀·荀子》沒有收這個韻段,有遺漏。
《賦·云》:“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愿陳。”其中“文”“神”“門”“存”“陳”真文合韻,如果“捐”入韻,則真文元合韻。江有誥《先秦韻讀》中“捐”誤作“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鈔撮江書,亦誤作“損”。
《楚辭》“存”入韻3次,《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這里“傳”“垠”“然”“存”“先”“門”元文合韻,“存在”義。
《大招》:“接徑千里,出若云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這里“云”“神”“存”“昆”真文合韻,“慰問”義。
《素問·寶命全形論》(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形”訛作“神”):“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后乃存針。眾脈不見,眾兇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于人。”其中“真”“神”“存”“聞”“先”“人”是真文合韻,江有誥《先秦韻讀》注“存針”:“當作針存。”其說是。
《八正神明論》:“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云,故曰神。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針之論,不必存也。”其中“神”“聞”“先”“言”“昏”“云”“神”“原”“存”真文元合韻。
假借材料如:
《大招》載“遽爽存只”,王逸注:“遽,趣也。爽,差也。存,前也。言乃復煎鮒魚,臛黃雀,敕趣宰人,差次眾味,持之而前也。”這里“存”之所以有“前”義,應該是假借用法,“前”從母元部,“存”從母文部。可能在某些楚方言中,“前”產生了一個新詞,讀作“存”,于是用“存”來記錄。這也說明“存”是一個[-n]收尾的音節。
諧聲材料如:
從“存”得聲的字,都是[-n]收尾的音節。例如“薦”“栫”“袸”“洊”“侟”等,“薦”“栫”見于《說文》《左傳》,“洊”見于《易》,“袸”見于《爾雅》,“侟”見于《太玄》,這都應該是“存”讀陽聲韻以后造的字,也說明“存”讀文部是很早的事。
既然“存”在《詩經》中不歸之部,而歸文部,說明《詩經》時代以前,“存”就已經變為文部了。可以假定,“存”是“在”的滋生詞,這種滋生現象在《詩經》時代之前已經出現。所以,我們研究上古音,一定要區分一個字的始相通時代和沿用相通時代的讀音。“存”從“才”聲,“存”和“才”讀音相通在《詩經》時代以前,具體的年代無法詳考,到了《詩經》時代,“存”和“才”讀音相差甚遠。
三、“二”“貳”等字的歸部

根據相關材料,我們可以推斷,“二”“貳”等字上古當歸質部長入。理由如下:
(一)上古“二”跟“次”讀音相差甚遠
從“二”得聲的字,恐怕只有一個“次”字,“弍”可以看作一個會意兼形聲字。“次”,小篆字形(采自《說文》)如圖2。《說文》欠部:“次,不前不精也。從欠,二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已經跟《說文》的說法有距離,段認為“次”從二、從欠,是個會意字;朱以為“次”是從二,二亦聲。
據考,“次”上古跟“二”讀音甚遠,段以為“次”中的“二”是意符,是很有道理的。“次”是齒音的口音字,“二”是鼻音字。
從聯綿詞來看。例如“次且”,“雙聲,猶豫不進貌。”《易·夬》:“臀無膚,其行次且。”孔穎達疏:“次且,行不前進也。”“且”是精母,則“次”精母。從“次”聲的“趑”跟“趄”雙聲,“趑趄”是“次且”的后起寫法,劉向《新序·雜事五》:“《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今本《易·夬》作“次且”。又“造次”雙聲,倉猝、匆忙的樣子。《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造”是清母,則“次”清母。
從諧聲層級來看,從“次”得聲的字,讀精母、清母、從母;從“咨”得聲的字讀精母、從母,從“資”得聲的字讀精母、清母、從母。“次”輾轉諧聲的字從不讀日母,說明“次”讀音跟日母相差甚遠,因此“次”不可能從“二”得聲。《說文》大概沒有意識到“二”可以作意符,而東漢時“二”和“次”韻母相同,就以為“次”從“二”聲。
西周金文中“次”有如圖3、圖4、圖5所示等字形。鄭妞的博士后出站報告《上古聲母特殊諧聲字研究》中關于“次”的疏證采用黃德寬之說,以為甲金文“次”本是“咨”的初文,像嘆息之狀,是一個象形字。[6]因此,“次”從“二”聲之說,不可作為定論。
“次”既不從“二”聲,則“二”的諧聲系列都不跟平聲和上聲相涉,“二”就有可能是質部,而不一定是脂部。
(二)“二”“貳”上古歸質部的內部證據
“二”“貳”跟入聲相通,上古不乏其例。
“貳”與“臲”異文。《易·困·九五》:“劓刖,困于赤紱。”漢帛書本“劓”作“貳”。《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漢帛書本“臲”作“貳”。“劓”,疑母月部;“臲”,亦為疑母月部;“貳”日母質部,聲母均為鼻音,古書中間或相通;如果“貳”為質部,則與“劓”“臲”韻部旁轉。
(三)白語漢借詞“二”所反映的上古歸部
據汪鋒《語言接觸與語音比較——以白語為例》,中古漢語的平聲對應于白語的第1調,上聲對應于白語的第2調,去聲對應于白語的第3、第4兩調,入聲對應于白語的第4調。[7]98這也就是說,漢語的去聲在白語中跟其他調類沒有混淆,只是相對白語有兩種對應情況,其中一部分跟白語的第4調相同,而白語的第4調對應的是漢語的一部分去聲,以及所有的入聲。進一步說,漢語中有一部分去聲在白語中讀成了入聲。
我們來看對應于白語第3、第4調的都是哪些中古漢語的去聲字。據《語言接觸與語音比較——以白語為例》,對應于白語第3調的是“靜”“樹”“破”“臭”“菜”“地”6字,[7]131這6字上古分別屬于耕部、侯部、歌部、幽部、之部、歌部,都是非入聲韻部。對應于白語第4調的是“吠”“二”“肺”“四”“歲”“外”6字,[7]131除了“二”,剩下的“吠”“肺”“四”“歲”“外”5字上古分別屬于月部、月部、質部、月部、月部,都是入聲韻部。只有“二”按照今天的歸部是非入聲韻部,如果將“二”處理為質部,則“二”不是例外。
(四)早期梵漢對音材料所反映的上古“貳”字的歸部
四、“黽”及相關諸字的上古歸部
(一)關于“黽”
“黽”字的上古韻部,各家歸部頗不一致。嚴可均將它歸為真部,段玉裁、朱駿聲、王力將它歸陽部,江有誥將其歸耕部。陳復華、何九盈在《古韻通曉》第四章第四節中作了詳細介紹。[8]筆者的意見是:“黽”字上古應該歸耕部和真部。
“黽”字,中古就有好幾個不同讀法。《廣韻》收了3個,《集韻》收了4個。《廣韻》的3個讀法是:(1)武盡切,軫韻:“黽,黽池縣,在河南府。”(2)彌兗切,狝韻:“黽池,縣名,在河南府。俗作澠。”(3)武幸切,耿韻:“黽,蛙屬。”《集韻》增加了眉耕切,耕韻:“地名,在秦。”在古代,這些讀音都是明母,韻母上都可以相轉,比較容易理解。這四讀的相應用法、意義上古都出現了。如果將“黽池”的“黽”歸入上古真部,“蛙屬”和“地名”的“黽”歸耕部,則很容易解釋它們的異讀關系,因為耕部、真部上古音很近,時有相通。如果將耕部改為陽部,則不好解釋它為什么有真部的異讀。
“黽”在甲金文中已經出現。如圖6、圖7、圖8、圖9所示字形(均采自《古文字詁林》):
《說文》是以武幸切(《集韻》為母耿切)一讀之義為本義。黽部:“黽,蛙黽也。從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黽,是蛙的一種,叫聲很大。因為這種蛙叫聲大,所以周代設置了一個官職,名蟈氏,負責驅除它。《周禮·秋官·蟈氏》:“蟈氏掌去鼃黽。”鄭玄注:“齊魯之間謂鼃為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耳,去之。”蟈,是蛙的另名,“蟈氏”鄭玄注:“鄭司農云:‘蟈讀為蜮,蜮,蝦蟆也。’……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蟲,國聲也。”蛙的頭部像蛇頭,所以《說文》說“黽頭與它頭同”。“黽”字描畫了蛙像蛇一樣的大頭,有的字形還畫出了其大腹,以及善于跳躍的長腿。鄭注的“耿黽”應該是個疊韻聯綿詞,這是一種色黃的小青蛙,生活在水中,叫聲很大。[9]《爾雅·釋魚》載“在水者黽”,郭璞注:“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釋文》:“黽,莫幸反。耿,耕幸反。”“耿”,耕部,則“黽”也可以歸耕部。

“黽”上古已有真部讀法。《詩經·邶風·谷風》《小雅·十月之交》等有雙聲聯綿詞“黽勉”,前者《釋文》:“黽勉,本亦作僶,莫尹反。黽勉,猶勉勉也。”這里的“黽勉”應該是準疊韻,“黽”,真部,[-n]尾。《文選》李善注引《韓詩》作“密勿”,“密勿”也是準疊韻。“黽勉”是“勉”的同源詞。
(二)“蠅”與“繩”
“蠅”和“繩”字都跟“黽”這個字形有關系。根據《說文》的解釋,一定是先有“蠅”字,然后仿照“蠅”字造了“繩”字。“蠅”和“繩”都見于上古早期文獻,“蠅”見于《詩經》,“繩”見于《周易》,光從古書上難以斷定其先后,古文字中,“蠅”和“繩”都只有較晚的字形,但是從造字理據上可以推定二字造字的先后。如果先有“繩”字,則“蠅”字的結構不可解釋;只有先有“蠅”字,才可以解釋清楚“繩”字的字形結構。
《說文》蟲部是將“蠅”看作會意字:“蠅,‘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從黽,從蟲。”黽既然是一種蛙,而蛙是一種大腹水蟲,于是借黽的大腹造了“蠅”字。這在造字方法上是允許的。《說文》黽部收了好幾個字都跟蛙沒有關系。例如:“鼈,甲蟲也。從黽,敝聲。”鼈,就是甲魚。又:“黿,大鼈也。從黽,元聲。”黿是大鼈,也就是癩頭鼈。又:“鼉,水蟲,似蜥蜴,長大。從黽,單聲。”鼉,就是揚子鱷。又:“蜘蛛”,《說文》作“鼄”。這些動物都不是蛙類,但是由于它們都具有大腹的特點,因此都以“黽”作形旁。“蠅”當然也是這樣,所以段玉裁注釋:“此蟲大腹,故其字從黽、蟲會意,謂腹大如黽之蟲也。”這說明,先民在造“蠅”字時,已經觀察到青蛙大腹的特點。我們看到,許慎對漢字結構的觀察是很細致的,他注意到有少量的漢字所指示的事物,不一定要提示其中每一個以它作形旁的字的意義類別,有個別時候是提示相關的事物類別。
《說文》糸部“繩”下說:“索也。從糸,蠅省聲。”段玉裁注釋說:“‘蠅’字入黽部者,謂其蟲大腹如黽類也,故‘蠅’以‘黽’會意,不以‘黽’形聲,‘繩’為‘蠅’省聲。”[1]657段氏在“蠅”下面的注釋與此正好可以互相補充:“‘繩’為‘蠅’省聲,非許之精詣,則必認為形聲字,遂使古音不可考矣。”由此看來,“蠅”不是從“黽”得聲,“繩”是“蠅”省聲。這兩個字上古無疑是蒸部。
五、“竄”字的上古歸部
“竄”字,今天一般歸元部。今考上古“竄”有月部讀法。顧炎武《唐韻正》卷十一《二十九換》下之“竄”字,舉出三個方面的證據證明“竄”有去聲(按:也就是王力先生的月部長入):其一,《周易》、宋玉《高唐賦》、《荀子·正論篇》、《淮南子·覽冥訓》、班固《西都賦》、魏《大享碑辭》、張協《七命》、潘岳《西征賦》、謝靈運《撰征賦》等從先秦至南北朝的韻文材料證明,“竄”跟陰聲韻相押;其二,《左傳》的《經典釋文》所引早期注音、《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索隱所注“七外反”;其三,異文及《說文》“讀若”。《說文》宀部:“,塞也。從宀,聲。讀若《虞書》曰‘三苗’之‘’。”[10]今天《尚書》作“竄三苗”。“”,《廣韻》為“麤最切”。
顧炎武的證據很充分,因此,“竄”上古有月部長入讀法當無疑;除了收入元部外,還可以收入月部。
六、《論語·微子》中周之八士取名的語音技巧
《論語·微子》:“周有八士:伯逹、伯適,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集解:“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爾。”皇侃《義疏》:“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并賢,故記錄之也。”《釋文》:“伯適,古活反。季騧,古花反。”關于一母四胎生八子的時間,邢昺《疏》:“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大家現在都知道,“逹”“適”都是月部,“突”“忽”是物部,“夜”“夏”是魚鐸部,“隨”“騧”是歌部。
其實,這里有更多的語音信息。我們先把它們的上古音構擬列在下面:
(一)韻母方面
關于等第。“逹”與“適”都是一等,“突”與“忽”為一等,“夜”與“隨”為三等,“夏”與“騧”為二等。說明當時一、二、三等有別。筆者在《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為慶祝郭錫良先生八十五華誕而作》一文中論證中古一、二、三等韻上古要各分成兩類。[11]很有可能,“逹”“適”和“突”“忽”應該歸入同一類一等韻,“夏”“騧”應該歸入同一類二等韻,“夜”“隨”應該歸同一類三等韻。說明當時一、二、三等有別。
關于開合。“逹”與“適”是一開一合。“適”,從“氒”聲,從“氒”聲的字有幾十個,全部歸合口,因此“適”是合口,跟“逹”開合不同。除此,“突”與“忽”皆合口,“夜”與“夏”皆開口,“隨”與“騧”皆合口。說明當時開合有別。
關于韻尾。這里“夏”可能取去聲讀法,是“夏天,夏季”的意思。“夜”本來是鐸部長入,有[-k]尾,它跟魚部的“夏”押韻,可能已經失去了輔音韻尾。
(二)聲調方面
“逹”“適”都是短入,“突”“忽”短入;“夜”“夏”去聲,“夜”已經由長入變成了去聲,上古應有長入、短入兩類調類,但長入很早就開始向去聲轉化,此即一例。“隨”“騧”平聲。說明當時有平聲、去聲、短入等調類。
七、《荀子·儒效》“武王之誅紂也……”句的語音技巧
《荀子·儒效》:“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
這里,“汜”字是今傳《荀子》原文,關于它到底作什么字,有兩種不同看法:
一種以為《荀子》原文作“汜”無誤。楊倞注:“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可見楊倞認為原文作“汜”。

王念孫指出,校“汜”為“氾”,是從汪中開始的,不始于盧文弨。他顯然對盧文弨沿用汪中說而不指明是汪氏的發現提出了委婉批評。氾是水名,其地在何處,還沒有考證清楚,王念孫說:“然《荀子》所謂‘至氾’者,究不知為何縣也。”[12]669又楊倞注“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盧文弨說:“案:共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指出,盧氏所注仍是沿用汪中說而未注明出處,《讀書雜志·荀子二》“至共頭而山隧”條:“此八字亦汪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12]669
汪中說“汜”為“氾”之訛,有兩方面的證據:第一,是這段文字“以音成義”;第二,“汜”和“氾”字形相近。這種校勘顯然可信。
我們現在來分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這句話“以音成義”的語音技巧。汪中、盧文弨、王念孫都注意到“氾”與“汎”和“懷”與“壞”這兩組字是“以音成義”,其實“頭”與“隧(墜)”也是如此。“氾”與“汎”、“懷”與“壞”、“頭”與“隧(墜)”各組字,讀音均有不同,但有相同的音素。
(一)“氾”和“汎”

“氾”“汎”二字中古聲母、聲調都不同,但韻母相同;上古則聲、韻、調均不同,但聲韻都相近。“氾”“汎”的語音技巧容易理解。
(二)“懷”和“壞”
“懷”,戶乖切,上古匣母微部;“壞”,胡怪切,上古匣母微部。二字聲韻都相同。按照這里的語音技巧,“懷”與“壞”只能是聲調之別,可見上古漢語平去有別,中古的去聲在上古已有相應的分別。
(三)“頭”和“隧”
《淮南子·兵略訓》中“隧”作“墜”:“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按:亦當為‘氾’)而水,至共頭而墜。”可見“隧”即“墜”。“頭”,度侯切,上古定母侯部;“隧”,《集韻》直類切,上古定母物部。二字中古聲、韻、調都不同;上古韻母和聲調都不同,但聲母相同。錢大昕說,古無舌上音,這條材料能印證其說之確。
“氾”與“汎”、“懷”與“壞”的韻母或相近,或相同;“頭”與“隧(墜)”的韻母一為侯部,一為物部(后變為微部),在荀子方言中可能也相近。
八、《荀子·解蔽》“貳則疑惑”的校勘與語音技巧
《荀子·解蔽》:“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
這里出現的幾個“貳”都是“忒”的訛字。“忒”意思是“差錯”。“其情之至也不忒”是說,其情之至極就不會出差錯;“不可以忒周行”是說,在選擇最好的途徑上不出差錯;“忒則疑惑”是說,出了差錯就會困惑不通。
王念孫《讀書雜志》卷五之八《管子》“不貳”條,[12]478-479以及卷八之五《荀子》“修道而不貳”條,[12]704-705都論證了古書中“忒”訛作“貳”的情形。在“修道而不貳”條中,他利用因聲求形的方法論證“貳則疑惑”的“貳”為“忒”字之訛。王先謙《荀子集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貳是貣之訛字,說見《天論篇》。今案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不當作貣。王說非也。”王先謙以“此貳字與上下文緊相承注”為由,否定王念孫的說法。其實,作“忒”字,與上下文也是“緊相承注”,符合上下文的韻例,是正確的。江有誥《音學十書·先秦韻讀·荀子·解蔽篇》沒有看出“枝”“知”押韻,“傾”“精”押韻,“忒”“惑”押韻,是一個疏忽。拙作《語詞札記十則》“貳則疑惑”條從語音技巧的角度論證“貳”當作“忒”。[13]130-131
此外,這里的語音技巧還有更多的語音信息,以前都沒有揭示出來,下面試作揭示。
(一)從聲母角度看
通過考察聲母,可以證明上古端組跟章組有別。“枝”跟“知”都是支部自押。據此幾個韻句,“枝”和“知”不當同音,同音則為“積韻”。兩個字韻母和聲調相同,變到中古都是支韻開口三等,其不同只能在聲母上,“枝”章母,“知”端母,似表明當時章組不能歸端組。若是,則此例為章不能歸端的佳例。
(二)從韻母角度看
開合有別。“枝”與“知”均為開口,“傾”與“精”前開后合,“忒”與“惑”前開后合。可見,每一個韻段前一個字均為開口,后一個字以使用合口音者居多。說明當時是有開合之別的。
等第不同。“枝”與“知”都是支部平聲,變到中古都是支韻開口三等字;“傾”與“精”都是耕部平聲,變到中古都是清韻三等字;“忒”與“惑”是入聲職部短入,變到中古都是德韻一等字。說明當時一等、三等有別。筆者在《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為慶祝郭錫良先生八十五華誕而作》中論證中古一、二、三等韻上古要各分成兩類。[11]很有可能,“枝”“知”應該歸入同一類三等韻,“傾”“精”應該歸入同一類三等韻,“忒”“惑”應該歸同一類一等韻。
(三)從聲調角度看
聲調上,“枝”與“知”均為平聲,“傾”與“精”也均為平聲,“忒”與“惑”短入。上古時期,平聲和短入的字要多于上去聲的字。從一個側面可見,上古漢語平聲和短入是兩類不同的調類。
九、《楚辭·卜居》“粟斯”的校勘與相關語音技巧
《楚辭·卜居》:“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
其中,“粟斯”《文選》本作“慄斯”,“儒兒”作“嚅唲”。舊注音:“哫”,音“足”;“訾”,音“貲”;“慄”,音“栗”;“喔”,音“握”;“咿”,音“伊”;“嚅”,音“儒”;“唲”,音“兒”;“突”下注“吐忽”;“滑”,音“骨”;“稽”字未見注音。

王引之《經義述聞》在論證古人隨處用韻時,就采用了“粟斯”一說。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以為當作“粟斯”。此外,游國恩《居學偶記》和譚介甫《屈賦新編》都認為“栗斯”當作“粟斯”。拙作《語詞札記十則》“栗斯”條則從語音技巧的角度論證“栗斯”當作“粟斯”。[13]127-130現在先復述拙作“栗斯”條對這幾句詩語音上揭示的大概。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這幾句詩,其音樂安排的回環美,就表現在多處使用雙聲疊韻上。“高舉”是見紐雙聲;“正”章紐,“直”定紐,古章組字跟端組字音近(有人認為章組分別歸入端組),所以“正直”是準雙聲。下面把“哫訾粟斯,喔伊儒兒,突梯滑稽,如脂如韋”4句詩各字的上古音韻地位列出(采用郭錫良師《漢字古音手冊》[14],下面擬音也采自這本書):
哫(精屋)訾(精支)粟(心屋)斯(心支)
喔(影屋)伊(影脂)儒(日侯)兒(日支)
突(透物)梯(透支)滑(見物)稽(見脂)
如(日魚)脂(章脂)如(日魚)韋(匣微)
這些詩句中各字的上古音構擬是:
哫[tsǐwǒk] 訾[tsǐe] 粟[sǐwǒk] 斯[sǐe]
(筆者按:“突梯”的“突”是透母,不是定母,上引《文選》及《楚辭補注》均云:“《文選》注云:突,吐忽切。”)
除“如脂如韋”句外,上面3句詩中的“哫訾”“粟斯”“喔伊”“儒兒”“突梯”“滑稽”都是雙聲聯綿詞,因此把“粟斯”拆開來解釋是錯誤的。
“哫訾粟斯,喔伊儒兒”中,4個聯綿詞的第一個音節四者疊韻:“哫”“粟”“喔”“儒”屋侯疊韻。屋侯音近,可以疊韻。如《離騷》中“屬”與“具”通韻,《天問》中“屬”與“數”通韻。4個聯綿詞的第二個音節四者也疊韻:“訾”“斯”“伊”“兒”支脂疊韻。《楚辭》中,支脂音近,可以疊韻。如《遠游》中“涕”“弭”合韻。支脂相配的陽聲韻耕真,《楚辭》中也有很多合韻的例子,如《離騷》中“名”“均”押韻;《哀郢》中“天”“名”押韻;《遠游》中“榮”“人”“征”押韻;《卜居》中“耕”“名”“身”“生”“真”“人”“清”“楹”押韻;《九辯》中“清”“清”“人”“新”“平”“生”“憐”“聲”“鳴”“征”“成”押韻,又“天”“名”押韻。如果將“粟”換成“栗”,那么“栗”和“慄”都是來母質部,上古擬音為[lǐět],如果將這個音類及其音值構擬代入上面的詩文中,就可以看出,其不合作者雙聲疊韻的安排技巧是顯然的,只能認為“栗”必為“粟”之訛字。
“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中,“突”與“滑”分別是聯綿詞的第一個音節,二者疊韻;兩個“如”處于非聯綿詞結構中,其所以不用聯綿詞,大概是為了不以文害意,而且“如”字使用兩次,也有一定的音樂美。“梯”“稽”“脂”“韋”是偶數音節,四者疊韻。只有“韋”是微部。《楚辭》中,脂微合韻,真文合韻的用例很多,都可以證明脂微音近疊韻。再從大的方面看,“訾”“斯”“伊”“兒”“梯”“稽”“脂”“韋”8字可視為支脂微疊韻。
但是拙作對這幾句詩中語音技巧的其他方面關注得不夠,忽略了其中還有一些語音信息,今試作進一步闡發。
(一)聲母方面

“粟斯”。從“粟”聲的字不多,但都是心母。“斯”字頗值得注意。《說文》斤部將“斯”分析為形聲字:“斯,析也。從斤,其聲。《詩》曰:‘斧以斯之。’”按:“斯”和“其”在上古聲韻都遠隔,有多方面的證據證明“斯”遠在先秦就是心母,這里“粟斯”為雙聲聯綿詞,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它們只有都讀心母才能形成雙聲。“斯須”也是一個雙聲聯綿詞,《禮記·祭義》:“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注:“斯須,猶須臾也。”從“須”聲的字,都是心母或山母,因此推定“須”上古是心母,則“斯”也必然是心母。再如聲訓:《說文》用“析”去解釋“斯”,這應該是用聲訓,“析”是心母錫部,“斯”“析”是同源詞。這個聲訓毛傳已經用了,《詩·陳風·墓門》:“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又“斯”和“皙”在“色白”的意思上同源,“皙”是心母錫部,跟“析”同音。《詩·鄘風·君子偕老》:“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毛傳:“皙,白皙。”《廣雅·釋器》:“皙,白也。”王念孫疏證:“斯與皙聲近而義同。”《詩·小雅·瓠葉》:“有兔斯首。”鄭玄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在諧聲系列中,凡是從“斯”的字,都無一例外地屬于心母,從來不跟牙喉音相通。這些字有一些先秦已經出現,應該是“斯”讀心母以后造的字。因此,“斯”上古無疑是心母。
多方面的證據證明“其”上古是喉牙音。諧聲系列,從“其”聲的字,除了“斯”及從“斯”聲的字,都無一例外地屬于見溪群三母,可以證明“其”上古是牙喉音,即見群二讀。《詩·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鄭玄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按:“己”的諧聲系列沒有讀心母的,多為見溪群母,則上古“己”和“記”都是牙喉音字,因此“其”也是牙喉音字。
鄭妞的博士論文《上古牙喉音特殊諧聲關系研究》,對于“其”和“斯”的音讀關系作了較詳細的辨析,[16]讀者可以參看。這樣,“其”和“斯”從先秦以來讀音就相差甚遠。許慎之所以說“斯”從“其”聲,是因為他沒有看出“其”如何在“斯”字中表意,而漢字諧聲字居多,只好說“斯”從“其”聲。“斯”從“其”聲的這一例說明,《說文》說某字從某得聲,并不能證明許慎時代主諧字和被諧字音同或音近,作為超一流的文字學家,許慎對某字是會意還是諧聲,有自己的推斷,這種推斷有一定主觀性。段玉裁看出“斯”并不從“其”得聲,《說文解字注》“斯”下注:“‘其’聲未聞。‘斯’字自《三百篇》及《唐韻》在支部無誤,而‘其’聲在之部,斷非聲也。”段氏之說確鑿無疑,清代有的研究《說文》的學者并沒有詳考段氏之說,以為“支之二部本相通”,輕易否定段說,沒有可靠的理由。林義光《文源》:“按:‘其’非聲。其,箕也,析竹為之,從斤治箕。”他的說法可取。因此,“斯”很難說從“其”得聲。遇到這種字形分析,我們不能將它們作為心母和牙喉音相通的鐵證,而構擬另一類聲母。
“儒兒”。“儒”從“需”聲,“需”,《說文》雨部說本義是“等待”,“從雨,而聲”。“需”,上古心母侯部;“而”,日母之部。《說文》而部說,“而”的本義是“頰毛”。在許慎看來,“而”的本義與“需”的本義相隔甚遠,“而”無法說是一個意符,“而”的其他義也很難跟“等待”義拉上關系,所以許慎說“需”字是“而聲”。
但“而”“需”音遠,所以清代學者有不同看法: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二“而”字條說:“《說文》‘需,從雨,而聲。’蓋即讀‘而’為‘如’也。”[17]但“如”是魚部,跟“需”仍然聲韻有隔,而且是否有此造字法,需要論證。

清代有學者不同意段說,仍堅持“需”從“而聲”,以為“需”“而”音近,而曲為之說,如徐灝、桂馥、王筠等人。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為“需”是會意字,但“而”是“耎”省形;“耎”指“濡濕”,林義光《文源》采此說。按“耎”無“濡濕”義,其本義指物體前面比后面稍大。
從古文字字形看,“需”上面是“雨”,下面是一個人,是會意字,如圖11、圖12所示字形等(圖11字形采自《漢語大字典》,圖12字形采自《金文編》)。甲骨文干脆就是畫一個人被沾濕的樣子,是象形字(字形如圖13所示,字形采自《漢語大字典》)。因此“需”應該是“濡”的古字,指濡濕。
從“需”聲的字,除了“耎”訛作“需”,其他分屬于中古心母、泥母、日母。
“兒”字,從“兒”聲的字中古屬泥母、日母、疑母、影母,上古就有聲母不同的讀音,詳細的討論見拙文《上古漢語特殊諧聲中聲母出現特殊變化的大致時代的一些例證》一文,[18]此不贅述。
由此可見,“儒兒”只有在讀泥母或日母時才可以雙聲。
(二)韻母方面
“哫”“粟”“喔”“儒”4字中,前3個都是屋部,只有“儒”是侯部,前人說上古音侯部和屋部是相配的陰聲韻和入聲韻,這顯然是正確的。大概屈原創作時找不到更多的前一個字入聲、后一個字平聲的雙聲聯綿詞,因此選一個有相配關系的“儒兒”來行文。
“哫”“粟”“喔”“儒”4字中,只有“喔”是二等韻,其他幾個字都是三等韻;“訾”“斯”“咿”“兒”全部是三等韻,其中7個字在介音上有回環;中古漢語三等韻在上古一定有相應的區別。筆者在《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中論證中古三等韻上古要分成兩類。[11]很有可能,“哫”“粟”“儒”“訾”“斯”“咿”“兒”應該歸入同一類三等韻。至少“哫”“粟”“儒”和“訾”“斯”“咿”“兒”這兩組分別歸為同一類三等韻。
“突”“梯”“滑”“稽”4字中,“突”“滑”都是一等韻,“梯”“稽”都是四等韻,“突梯”和“滑稽”分別形成回環。中古漢語一、四等韻在上古一定有相應的區別。筆者在《上古漢語韻重現象研究》中論證中古一等韻上古要分成兩類。[11]很有可能,“突”“滑”應該歸入同一類一等韻。
“如”“脂”“如”“韋”4字都是三等韻,形成回環,也可以證明,中古漢語三等韻在上古一定有相應的區別。很有可能,這四個字應該歸入同一類三等韻。
(三)聲調方面
考察聲調,這里的語音技巧表明,中古的平聲和入聲上古有相應的分別。“哫”“粟”“喔”“儒”“突”“滑”主要用入聲字,“儒”是平聲字,用“儒”,是因難以找到相應的入聲字,只好退而求其次,這說明當時入聲(即短入)自成一類;“訾”“斯”“咿”“兒”“梯”“稽”“如”“脂”“如”“韋”全部是平聲字,這說明當時平聲自成一類。
十、里耶秦簡所反映的異讀別義
《里耶秦簡(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2012)8-461號木方有涉及秦朝用字、用語規范的文字。這段文字經過多位古文字學者的釋讀,已經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見。
(一)秦簡8-461號木方第一欄用字用詞概況
原簡分上下兩欄,這里抄錄第一欄:
(1)囗
(2)囗
(3)[叚如故,更]假人
(4)[囗如故,]更錢囗
(5)大如故,更泰守
(6)賞如故,更償責
(7)吏如故,更事
(8)卿如故,更鄉
(9)[走]馬如故,更簪褭
(10)者如故,更諸
(11)酉如故,更酒
(12)法如故,更廢官
(13)鼠如故,更予人
(14)更詑曰謾
(15)以此為野
(16)[歸]戶,更曰囗戶
(17)諸官,為秦盡更
(20)曰產,曰族
(22)毋敢曰王父,曰泰父
(23)毋敢曰巫帝,曰巫
(24)毋敢曰豬,曰彘
(25)王馬,曰乘輿馬
這里,第(1)和第(2)條已殘,無法知道,其余23條,除了(15)、(18)、(19)條是規范異體字,其他20條都是規范分化字和用詞。這里“更”指更改,更改前和更改后的用字或用詞必不相同。例如更改用詞的:
(4)[囗] ≠錢囗
(9)[走]馬≠簪褭
(14)詑≠謾
(16)[歸]戶≠囗戶
(17)諸官≠秦盡更
(20)囗(生?)≠產,囗≠族
(22)王父≠泰父
(23)巫帝≠巫
(24)豬≠彘
(25)王馬≠乘輿馬
這11條更改用詞的,更改前和更改后的詞屬于不同的詞。
(二)秦簡中的異讀別義現象分析
我們關心的是下面這些記錄同一個詞語,而更改前和更改后用字不同的例子。這些例子反映了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原來一個字記錄不同的詞或詞素,這不同的詞或詞素讀音一定有差異。
(3)叚≠假人
(5)大≠泰守
(6)賞≠償責
(7)吏≠事
(8)卿≠鄉
(10)者≠諸
(11)酉≠酒
(12)法≠廢官
(13)鼠≠予人
這9條,更改前和更改后的用字讀音都不一樣,絕非偶然,說明秦代對異讀別義的一些字,采取了分化字形的方式,并且規范下來。這幾則材料,透露出秦代及秦代以前不少語音信息。
1.“叚”與“假人”
《說文》又部:“叚,借也。”這是指借進來;“假人”,指借出,借給別人。二者在語音上有上去之別,并伴之而意義有別,詳參拙著《漢語變調構詞考辨(上冊)》[19]548-550。這說明,秦代漢語中有去聲,當時有變調構詞。《集韻》中“叚”與“假”都有舉下切和居迓切二讀,是上去別義的。跟秦代規范用法不同的是,“叚”本來有上去二讀別義,秦代規定用“假”來記錄去聲的“叚”,讓“叚”只記錄原始詞讀音,到后來“叚”“假”用法混同了。
2.“大”與“泰”
關于“大”和“泰”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大”是定母月部長入,“泰”是透母月部長入,秦代“大”“泰”都已經是去聲了。最明顯的例子,秦代不少刻石,短入常常自押,長入常常跟去聲一起押韻。例如《泰山刻石銘》“飭”“服”“極”“德”“式”“革”是短入,“治”“誨”“志”“事”“嗣”“戒”是長入和去聲押;《瑯琊臺刻石銘》“事”“富”“志”“字”“載”“意”和“帝”“地”“懈”“辟”“易”“畫”兩個韻段都是長入和去聲押,“德”“極”“福”“殖”“革”“賊”“式”是短入。
這則材料說明,至晚秦代,定母和透母是不同的聲母,當時有變聲構詞。此例還說明,原來“大”有定、透二母讀法,至晚秦代用“泰”記錄滋生詞,讓“大”只記錄原始詞讀音。《廣韻》“大”有徒蓋切和唐佐切二讀,均來自上古定母;《集韻》“大”還有他蓋切、他佐切二讀,均來自上古透母。“泰”,《廣韻》《集韻》只讀他蓋切。《廣韻》反映“大”“泰”的用法,跟秦代規范用法一脈相承,《集韻》則跟秦代以前的用法相同。
3.“賞”與“償”
關于“賞”和“償”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賞”是書母陽部開三上聲,“償”是禪母陽部開三平聲或去聲。“償”也有跟“賞”相同的異讀,見陸德明《莊子音義》和《集韻》,但是根據《岳麓書院藏秦簡》這一段的通例,“賞”“償”必不同音。這則材料說明,秦代及秦代以前,“賞”至少有兩個讀音,至晚到秦代,人們已經開始用“償”來分擔其禪母陽部開三平聲一讀,讓“賞”只記錄書母陽部開三上聲一讀。傳世秦漢文獻中,“賞”還有作“償,酬報”講的用例,《韓非子·飾邪》:“釋法禁而聽請謁,群臣賣官于上,取賞于下,是以利私家而威在群臣。”王先慎集解:“賞讀為償。”賈誼《新書·修政語上》:“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俞樾《諸子平議·賈子二》:“賞讀為償。”
《廣韻》《集韻》“賞”只有一個讀音,《廣韻》書兩切:“賞,賜也。”“償”則多音,《廣韻》市羊切:“償,報也,還也,當也,復也。”時亮切:“償,備也,還也。”跟《岳麓書院藏秦簡》這一段文字比起來,“賞”由原來有異讀的字變成了只有一個讀音,跟秦代的規范用法是一致的。
4.“吏”與“事”
關于“吏”和“事”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上古“吏”屬來母之部去聲,“事”屬崇母之部去聲。這則材料說明,“吏”本來有來母之部去聲和崇母之部去聲的異讀,至晚到了秦代,人們用“事”記錄“吏”作“事”講的音義,讓“吏”只記錄其來母讀音。傳世文獻中,“吏”有作“事”講的用例,《管子·大匡》:“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郭沫若等集校:“吏當為事,古字通用。”《韓非子·孤憤》:“則修智之吏廢。”于省吾新證:“吏本應作事。金文吏、事同字。”
《廣韻》《集韻》“吏”只有一讀,來自上古來母,《廣韻》力置切:“吏,《說文》曰:治人者也。”“事”,《廣韻》鉏吏切:“使也,立也,由也。”《集韻》士史切:“從所務也。”仕吏切:“《說文》:職也。”可見,《廣韻》《集韻》反映“吏”“事”二字分工以后的用法,跟秦代規范通行的用法一脈相承。
5.“卿”與“鄉”
關于“卿”和“鄉”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上古“卿”屬溪母陽部平聲,“鄉”屬曉母陽部平聲。這則材料說明,“卿”本來有溪母陽部平聲和曉母陽部平聲的異讀,至晚到了秦代,人們用“鄉”記錄“卿”作“鄉”講的音義,讓“卿”只記錄其溪母讀音。古文字中,“卿”“鄉”本同一字。出土金文中,“卿”有作“鄉”的用例,作“鄉人相聚飲酒”“犒賞”“朝向”等義。[4]865-867拙作《漢語變調構詞考辨》(上冊)對“鄉”字諸條進行了考證,結論是:“鄉”屬變調構詞,有平上去三讀。[19]775-779
《廣韻》《集韻》中“卿”只有一讀,來自上古溪母,《廣韻》為去京切,《集韻》丘京切。“鄉”,《廣韻》只有一讀,許良切:“鄉黨。”《集韻》兩讀,除了虛良切,還有許亮切:“面也。”上聲讀法由“饗”或“享”字承當,《廣韻》許兩切:“饗,歆饗。”可見,《廣韻》《集韻》反映“卿”“鄉”二字分工以后繼續分工的用法,跟秦代規范通行的用法一脈相承,但不完全一致。
6.“者”與“諸”
關于“者”和“諸”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上古“者”屬章母魚部開三上聲,“諸”屬章母魚部開三平聲。這則材料說明,“者”本來有章母魚部上聲和章母魚部平聲的異讀,至晚到了秦代,人們用“諸”記錄“者”作“諸”講的音義,讓“者”只記錄其章母魚部開三上聲的讀音。傳世秦漢文獻中,“者”有作“諸”講的用例,可以指眾。《古文苑·秦惠文王<詛楚文>》:“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刬伐我社稷。”章樵注:“[者],諸。”漢桓寬《鹽鐵論·散不足》:“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徐德培集釋:“者生即諸生也。”“者(諸)”作兼詞講,有人以為相當于“之”,如《呂氏春秋·離謂》:“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許維遹集釋:“者與諸字古通。《廣雅·釋言》:‘諸,之也。’然有亡者國,猶云然有亡之國。”
《廣韻》中“者”只有一讀,章也切:“語助。”《集韻》中還有董五切:“語辭。”《集韻》二讀不別義。“諸”,《廣韻》章魚切:“之也,旃也,辯也,非一也。”可見,《廣韻》《集韻》反映“者”“諸”二字分工以后的用法,跟秦代規范通行的用法一脈相承。
7.“酉”與“酒”
關于“酉”和“酒”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上古“酉”屬余母幽部上聲,“酒”屬精母幽部上聲。“酉”和“酒”應該屬于變聲構詞。這則材料說明,上古漢語必然有變聲構詞;“酉”本來有余母幽部上聲和精母幽部上聲的異讀,至晚到了秦代,人們用“酒”記錄“酉”作“酒”講的音義,讓“酉”只記錄其余母讀音。甲金文中,“酉”有不少作“酒”字用的例子,秦漢簡牘猶然。
《廣韻》《集韻》中“酉”只有一讀,來自上古余母,《廣韻》與久切:“酉,飽也,老也,就也,首也;又辰名。”“酒”,《廣韻》《集韻》也只有一讀,《廣韻》子酉切:“酒醴。”可見,《廣韻》《集韻》反映“酉”“酒”二字分工以后的用法,跟秦代規范通行的用法一脈相承。
8.“法”與“廢”
關于“法”和“廢”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上古“法”屬幫母葉部短入,“廢”屬幫母月部長入。上古漢語中,葉部有些字變入了月部,不獨長入,短入也有,《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列了一些月部和葉部(原書稱為盍部)短入合韻的例子,但是用例極為罕見。[20]秦代以前,作“廢”用的“法”已經讀為了月部長入。“廢”字先秦更是月部:《管子·版法》押“殺”“廢”“外”,《內業》押“未”“廢”“竭”,《易·系辭下》押“大”“廢”,《大戴禮記·武王踐祚》押“廢”“世”,《靈樞·制節真邪》押“大”“害”“界”“外”“廢”,《文子·道原》押“墆”“廢”,《微明》押“敗”“廢”“患”,《呂氏春秋·孝行》押“殺”“廢”“闕”。由此可以推定,“法”作“廢”用,當時已經讀月部了。
這則材料說明,“法”本來有幫母葉部和幫母月部的異讀,至晚到了秦代,人們用“廢”記錄“法”作“廢”講的音義,讓“法”只記錄其幫母葉部的讀音。傳世文獻中,“法”有作“廢”講的用例:清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古文灋(法)、廢為一字也。”《管子·侈靡》:“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郭沫若等集校:“金文以‘法’為‘廢’字,此兩‘法’均當讀為廢。”秦漢及以前的出土文獻中,“法”用作“廢”,其例極多,可參陳初生編纂《金文常用字典》(修訂再版本)[4]896-897。
《廣韻》《集韻》“法”只有一讀,來自上古幫母葉部,《廣韻》方乏切:“法,則也,數也,常也。”“廢”,《廣韻》《集韻》也是只有一個讀音,《廣韻》方肺切:“止也,大也。”可見,《廣韻》《集韻》反映“法”“廢”二字分工以后的用法,跟秦代規范通行的用法一脈相承。
9.“鼠”與“予”
關于“鼠”和“予”的上古音韻地位,一般認為,上古“鼠”屬書母魚部上聲,“予”屬余母魚部上聲。這則材料說明,“鼠”本來有書母魚部上聲和余母魚部上聲的異讀,至晚到了秦代,人們用“予”記錄“鼠”作“予”講的音義,讓“鼠”只記錄其書母讀音。傳世文獻中沒有見到“鼠”有作“予”講的用例,但是出土文獻有,正是“予人”的“予”,即“給予”義:《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金布律》:“都官佐、吏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車牛、仆;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養一人。小官毋(無)嗇夫者,以此鼠仆、車牛。”《法律答問》:“盜出朱(珠)玉邦關及買(賣)於客者,上朱(珠)玉內史,內史鼠購。”
《廣韻》《集韻》“鼠”只有一讀,來自上古書母,《廣韻》舒呂切:“小獸名,善為盜。《說文》曰:穴蟲之總名也。”給予的“予”,《廣韻》《集韻》也只有一個讀音,《廣韻》余呂切:“郭璞云:予猶與也。”可見,《廣韻》《集韻》反映“鼠”“予”二字分工以后的用法,跟秦代以后的用法一脈相承。
(三)啟示
必須指出,拙作《從諧聲層級和聲符異讀看百年來的上古復輔音構擬》一文論證上古有些字的異讀到中古消失了,此處又有一些例子可作拙作的補充。我們看到,有一些字,秦代還有異讀,但是《廣韻》《集韻》并沒有反映出來。例如第6條的“賞”,第7條的“吏”、第8條的“卿”、第10條的“者”、第11條的“酉”、第12條的“法”、第13條的“鼠”,都是如此。這些例子又可以在我們研究上古音時給予有力的啟示:既然上古有些字的異讀到中古消失了,那么光利用《廣韻》《集韻》往上推,有一定欠缺,還必須充分注意上古的內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