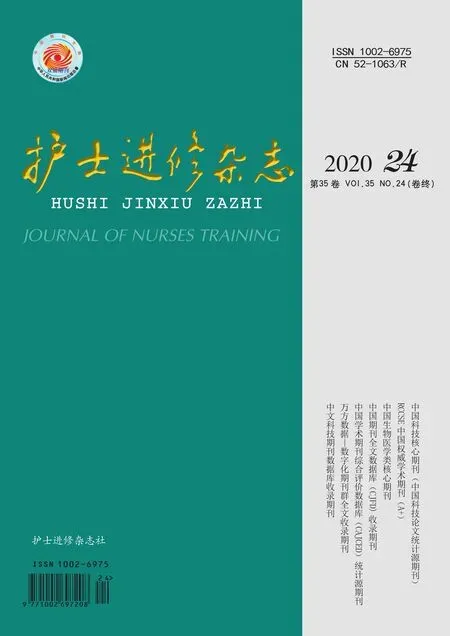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與心理韌性的相關性研究
劉晶娟
(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 國家腫瘤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天津市腫瘤防治重點實驗室天津市惡性腫瘤醫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060)
2018年全球癌癥統計[1]顯示,肝癌新發患者數高達84.1萬人次,居于第6位;死亡人數高達78.2萬人次,居于第4位。在中國,肝癌新發患者數占全球人數一半以上,成為致死第三大病因[2]。肝癌由于發病初期癥狀不明顯,臨床診斷常見分期較晚患者,生存期僅剩3~6個月[3]。晚期癌癥患者在面臨死亡時會產生緊張、絕望感、憤怒感及恐懼等身心負擔,從而引起無可規避的悲傷反應。預期性悲傷,又名“死亡前悲傷”或“失去前悲傷”,它是個體在死亡前體驗到的認知、情感、文化及社會反應[4-5]。這種悲傷從診斷期持續到生命末期,如不積極干預將發展為病態悲傷,不利于安寧療護的實施。而心理韌性是應對壓力性事件的積極特質。本研究旨在基于積極心理學,了解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及心理韌性的現狀,并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為今后制定針對性干預方案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法抽取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的200例晚期肝癌患者進行調查。納入標準:(1)病理診斷為肝癌。(2)年齡≥18歲。(3)臨床TNM分期為Ⅲ期或Ⅳ期。(4)有文字閱讀及理解能力,可完成問卷者。(5)自愿參與本研究者。排除標準:對疾病不知情;認知障礙或神志不清;合并其他重大疾病者。
1.2調查工具
1.2.1一般資料調查表 由研究者根據文獻自行設計,包括患者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婚姻狀況、醫療費用支付類型及病程等。
1.2.2晚期癌癥患者預期性悲傷量表(Preparatory grief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scale,PGAC) 該量表中文版于2017年由辛大君等[6]翻譯而成,本研究中用于評估癌癥患者感知死亡后的悲傷程度。該量表包含自我意識、疾病調整、悲傷、憤怒、宗教安慰、軀體癥狀和感知到的社會支持7個維度,共31個條目,各條目采用0~3分的Likert 4級評分法,0分表示不同意,3分表示同意,總分為各條目之和。總分越高表示患者經歷的悲傷越多。該量表總體信度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9,具有良好的信效度[7]。
1.2.3心理韌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此量表中文版于2011年由Yu等[8]翻譯而成,本研究中用于測量促進個體適應逆境的積極心理品質。該量表包含堅韌(13個條目)、自強(8個條目)及樂觀(4個條目)3個維度,共25個條目,各條目采用0~4分的Likert 5級評分法,總分為各條目之和,得分<60分為較差,60~70分為一般,70~80分為良好,>80分為優秀。該量表總體信度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內容效度為0.9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法,由研究人員進行問卷的發放及收取,調查前研究人員采用統一指導語向被調查對象闡明本項調查的目的、內容及問卷的填寫方法,獲得知情同意權后進行問卷填寫。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90份,有效回收率為95%。

2 結果
2.1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的單因素分析 見表1。

表1 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的單因素分析
2.2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及心理韌性得分狀況 見表2。
2.3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與心理韌性的相關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預期性悲傷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呈負相關(P<0.05);預期性悲傷中自我意識、疾病調整及感知到的社會支持維度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呈正相關(P<0.05);預期性悲傷中悲傷、憤怒及軀體癥狀維度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呈負相關(P<0.05);預期性悲傷中宗教安慰維度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無相關。見表3。

表2 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及心理韌性得分狀況 分

表3 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與心理韌性的相關性(r)
2.4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以預期性悲傷總分為因變量,以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及醫療費用支付類型及心理韌性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文化程度及心理韌性是預期性悲傷的主要影響因素(P<0.05),共解釋晚期肝癌預期性悲傷的54.6%。見表4。

表4 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n=190)
3 討論
3.1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現狀 本研究顯示,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得分為(38.64±8.34)分,與國內辛大君等[6]在388例晚期癌癥患者中測得結果相似。肝癌患者在生命末期,身體會出現疼痛、食欲下降及腹脹等不適癥狀,影響身體機能,同時也引發憤怒、沮喪及恐懼等負性情緒;尤其受“重生輕死”傳統觀念的影響,大多數人對死亡的恐懼及對活著的眷戀[9],使晚期肝癌患者的預期性悲傷水平比較顯著。自我意識即對自身狀態的認識,在預期性悲傷量表中用于評價其對抗疾病的信心、自我價值及生存目標等[10]。本研究各維度得分中,自我意識得分最高,也說明了晚期癌癥患者領悟到活著的意義,希望能戰勝疾病,全心全意活著,表達了對生命的眷戀;其次為疾病調整,原因可能為晚期肝癌患者知曉自己病情,意識到自己生命進入“倒計時”階段,會調整自己的人生計劃,考慮去完成自己人生中尚未完成的重要事情或心愿,以此來體現生命的意義及價值[11];得分最低為憤怒,分析原因為晚期肝癌患者面對疾病慢慢消逝,心理會經歷5個階段(即否認期、憤怒期、協議期、抑郁期及接受期)變化來達到內心自我調適的作用[12],因此憤怒得分較低。
3.2晚期肝癌患者心理韌性現狀 心理韌性是個體應對困境、挑戰及創傷等壓力性事件,能從中調適恢復過來的能力或特質。本研究中,晚期肝癌患者心理韌性得分(66.33±16.70)分,心理韌性水平較低。分析原因:(1)晚期肝癌患者的腫瘤分期較晚,失去手術的最佳治療時機,主要以姑息治療為主,無疑降低患者對抗疾病的信心[13]。(2)晚期癌癥患者的病情變化較快,存在疲乏、疼痛、發熱及認知下降等不適癥狀明顯[14],易引發焦慮及情緒低落等心理負擔,難以從中解脫,從而心理韌性水平較低。
3.3晚期肝癌患者心理韌性對預期性悲傷的影響 (1)性別因素:性別是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的主要影響因素,即女性比男性患者的預期性悲傷水平高。可能與女性天生感情細膩、抗壓能力差且情緒調節能力弱,面對離世和失去希望,更易保持悲觀的態度及采用消極的應對方式,而男性面對外界壓力時,可能較為沉穩和冷靜,具有較為積極樂觀的態度有關。提示醫護人員應更多關注女性晚期癌癥患者,及時給予其支持,減少其負性情緒。(2)文化程度因素:文化程度是晚期肝癌患者預期性悲傷的主要影響因素,即患者的文化程度越低,其預期性悲傷水平越高。但與辛大君等[6]研究結果不一致,這可能與研究對象的納入有關。分析原因:較高文化程度的晚期癌癥患者認知水平較高,可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待問題,對生命及對晚期癌癥的認識更為深刻,生活態度多數更為淡然,可能不會對疾病特別是晚期癌癥等同于絕癥的疾病抱有盲目的希望[15],但其也會主動通過各種途徑獲取更多有關疾病治療的信息和資源,積極治療,減輕病痛,提高生活質量。相反文化程度較低的晚期癌癥患者,對疾病的認知、治療方法的理解及病情變化時的自我調節能力都有所欠缺,加之大多數文化水平較低的晚期癌癥患者社會經濟地位較低,高昂的醫療費用和心理負擔讓其感到手足無措、焦慮、失眠、陷入自責與悲傷的情緒中,加重了患者預期性悲傷的水平。提示醫護人員應更多關注文化程度低的患者,針對個人情況進行正確疏導,減少其負面情緒。(3)心理韌性因素:晚期肝癌患者心理韌性與預期性悲傷呈負相關,即心理韌性水平越高,其預期性悲傷水平越低。原因在于心理韌性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心理韌性水平高的患者能正確認識自己的疾病,采取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緩解心理不適,降低預期性悲傷[16]。本研究中各維度相關性分析顯示,預期性悲傷的3個維度(自我意識、疾病調整及感知到的社會支持)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呈正相關,原因在于自我意識、疾病調整及感知到的社會支持為患者在遭受疾病過程中感知到的積極層面,而心理韌性也是積極品質,故呈正相關;預期性悲傷的3個維度(悲傷、憤怒及軀體癥狀)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呈負相關,可能原因為心理韌性能緩解并減輕負性情緒[17],而悲傷、憤怒及軀體癥狀等為晚期肝癌患者承受的生理癥狀及負性情緒;預期性悲傷的宗教安慰維度與心理韌性及其維度無相關,可能原因在于調查對象中含有宗教信仰的人數較少,兩者的關聯不顯著,今后可做進一步探索。提示臨床人員可通過協同護理模式、認知行為干預及生命回顧療法等干預形式[18],建設患者的心理韌性,幫助其正確認識疾病,領悟生命意義,緩解預期性悲傷。
綜上所述,晚期癌癥患者的預期性悲傷及心理韌性處于較低的水平,且兩者呈負相關。因此,提高晚期癌癥患者的預期性悲傷及心理韌性水平刻不容緩。臨床人員可通過建設心理韌性水平,幫助其正確認識疾病,以緩解預期性悲傷,從而提高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