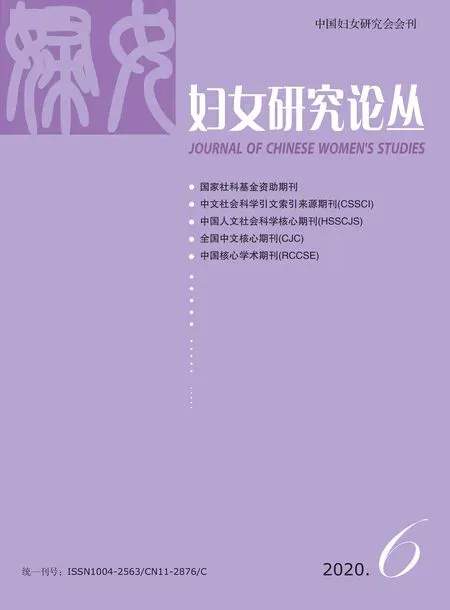身份、主體與合理性:清代閨秀家務詩詞的日常化書寫
2020-02-24 17:07:52劉陽河
婦女研究論叢
2020年6期
劉陽河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香港 999077)
有清一代出現了閨秀詩詞創作繁盛的文學景觀,“婦人之集,超軼前代,數逾三千”[1](P 5)。閨秀詩詞的興盛,不但表現為女詩人群體之大、詩詞創作之多,更表現為題材、內容等創作空間上的拓展。閨秀詩詞突破了唐宋以來女性詩詞經典傳統中閨情閨怨的狹隘內容,也因社會穩定而逐漸淡化動蕩時期的家國之思,在這兩大女性傳統詩詞主題的罅隙中,轉而從平淡世俗的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汲取靈感,增加了對日常瑣事俗務的記錄與真實生活感受的表達。詩詞日常化的創作趨勢,打破了“唐宋以還,婦才之可見者不過春閨秋怨、花草榮凋”[2](P 182)的偏見。這類詩詞創作在選材上不避凡俗,關注日常細節,涉及現實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詩題上就可見端倪:有極細微的有趣發現,如許禧身《金縷曲·獨坐無聊忽見蜘蛛一絲微吐滿屋旋轉戲作》;有閨友交往,如凌祉媛《分龍日以紅鹽一箬從陸氏聘貓雛翌日謝之以詩》;有溫馨的親情體驗,如盛氏《月夜同兒女坐話》;有繁瑣的家務整理,如俞慶曾《架上亂書手自整理口占一絕》;有家計營生的操勞煩憂,如季蘭韻《鬻衣》、楊繼端《無米》;有生活中的微小探索,如陳蘊蓮《自制豆腐偶成》;甚至還有難登大雅之堂的略顯粗鄙之作,如王慧《詠蚤虱》……主題紛繁,內容駁雜,不一而足。
日常化研究在男性詩詞領域已然甚夥,如“以俗為雅”的宋詩及清代關注自我的性靈詩派。反觀女性詩詞,雖然早在20世紀末孫康宜已提出明清女詩人“從刺繡、紡織、縫紉到烹飪,直到養花、撫育”[3](P 80)等日常化新氣象,但學界對明清女詩人的研究卻大多圍繞更為新異的“閨外敘事”展開。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