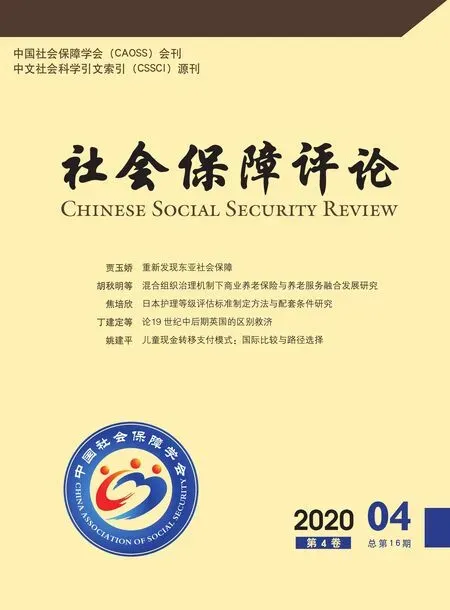重新發現東亞社會保障
——對發展主義話語中東亞國家發展能力的回應及新解
賈玉嬌
伴隨東亞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打破西方一枝獨秀的格局,以及東亞國家與學者主體意識的增強,東亞開始成為一個知識與話語體系產生的空間,其形成的標志之一是關于東亞國家與地區發展能力以及社會保障制度討論的興起。在此過程中,一套清晰表征東亞國家與地區社會保障體制的概念體系逐漸形成,并亟待實現進一步的發展,以增強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發展的解釋力和指導力,進而更加明晰東亞國家發展之路。
一、打開東亞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之門
1990年,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問世。在此書中,他繼承并發展了熊彼特對西方國家進行全景-分類式研究的路徑,運用馬克思提出的勞動力“商品化”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存在屬性進行福利國家透視,發現并討論社會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性質,及其維護一定社會階層結構的秩序意義,由此揭示出作為“去商品化”承載容器的社會權利與資本主義對立、依存的矛盾關系問題。這一矛盾的不同樣態成為決定西方國家社會權利實踐程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差異的根本所在。接著,埃斯平-安德森進一步揭示了不同矛盾樣態下所掩蓋的政治權力結構,比較分析了各國不同的政治聯盟傳統及聯合水平。由此,埃斯平-安德森解密了福利資本主義生成邏輯,提煉出三種社會保障與資本主義邏輯的互動模型,從而生動展開了“福利體制”內容。①參見[丹麥]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鄭秉文譯:《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本文認為,“福利體制”分析范式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福利制度”單維分析的研究局限,強調將福利制度視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部分,并將福利分析置于與西方國家治理邏輯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之中。
二戰以來,西方成為主控世界政治、經濟、社會話語權的知識產出空間。在這一空間中,研究者們基于西方優越的價值立場來開展研究的研究慣習與西方優越于其他國家的“領先”“中心”形象之間彼此強化。其所形成的“發展”階段論調預設了東亞等非西方國家的“落后”“邊緣”處境與必然接受現代化引導、進行現代發育,進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命運。埃斯平-安德森福利體制的三分法理論同樣蘊含這一隱喻。這也成為對其理論地域解釋力不足進行辯護的有力托詞,即因為東西方經濟、政治與社會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在全球發展體系中處于不同位置,因此用處于高發展階段的、全球發展格局中心位置的西方福利體制類型,來歸類分析仍舊處于低發展階段和邊緣地位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必然不具有現實解釋力,但對這一地區的未來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具有理論前瞻意義。以這套概念表征體系關照東亞后所形成的建構意義是提高東亞與西方的同質性,進而強化西方引領、中心論。
但是,東亞所具有的特殊性即便在其接受了強勢的現代化洗禮后,仍舊彰顯開來,它是決定東亞之所以為東亞的本質所在。用與資本主義發展訴求緊密契合的勞動力“去商品化”來度量西方社會保障發展水平是有效的,但是在解讀東亞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時顯得局促不足②武川正吾、金妮:《轉型期的日本社會保障》,《社會保障研究(京)》2005年第2 卷。。為增強“福利體制”范式的解釋彈性,埃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的再版自序中提出“去家庭化”,用以測度東亞社會保障。但是,這種以家庭與國家二元對立作為先驗性前提的理論,真的適用于東亞嗎?由此,引出了東亞是否存在社會保障的世紀疑問③鄭功成:《東亞地區社會保障模式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2 期;林義:《東亞社會保障模式初探》,《財經科學》2000年第1 期;林閩鋼、劉璐嬋:《東亞福利體制研究: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社會保障研究(京)》2012年第2 卷;席恒、田宋:《合作收益視角下的東亞社會保障模式》,《山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7 期。。20 世紀90年代,越來越多的東亞學者接觸到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體制理論,從而打開了發現東亞社會保障的研究大門,開啟了一場在東亞國家與地區的共性與差異性所生張力之中探尋社會保障體制之旅,逐步為世人展現一幅鮮活、豐富的東亞社會保障發展圖景。
二、是否存在東亞本土意義上的社會保障體制?
擺在學者們面前的一個亟待闡釋清楚的前提性問題是,根植于儒家思想的東亞價值觀與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是否沖突并難以融合,①王卓祺:《東亞國家和地區福利制度:全球化、文化與政府角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第97 頁。對該問題的探討成為20 世紀末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碰撞大討論中的子話題之一。這一時期的主流觀點認為,本土文化在經受外來強勢文化侵襲后發出何種回應,不僅能夠體現出其生命力的韌度,還能據此判斷其發展前景。因此,早期發端于文化維度的東亞社會保障討論不僅意在闡明東亞社會保障發展規律的特性問題,還對東亞傳統社會發展邏輯與現代性發展邏輯交匯前景做出預判。
對此,學者們的觀點出現了分殊。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文化抑制或不利于現代化及其產物——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主要理由是儒家文化取消了個體與外部世界的緊張感,無法生成社會發展與制度創立的動力源。據此認為應當去除儒家文化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現代社會建設的影響,進而取消東亞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發現與建構,運用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三分法,演繹出現代東亞版,如將日本視為混合自由主義型和保守及共責主義型的福利國家,自由主義對保守主義福利模型光譜,或保守主義型福利體系。
與上述觀點相左,另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文化在與外來文明的碰撞過程中表現出超強的適應性,從而強調儒家文化在東亞現代社會發展與社會保障制度發展中的積極意義。在此方面,沈潔從歷史角度考察了與東方價值觀相異的西方社會保障理念的傳入途徑及其與儒家文化的沖突與交匯過程。②沈潔:《中、日、韓社會保障發展路徑的比較研究》,《社會保障研究(京)》2013年第1 卷。儒家文化博大精深,除了需要去除的落后部分,其思想精髓對中國以及東亞影響深遠,已然成為東亞國家和地區現代化轉型與發展歷程的文脈。儒家世俗倫理之于東亞的意義,猶如基督教之于西方的意義,進而對東亞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下面,筆者從三個方面進行闡釋。
第一,儒家家庭保障觀對東亞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實踐來看,無論是施行社會保險的東北亞,還是施行強制儲蓄的東南亞,都很重視家庭的保障功能。一些學者將孔子思想中重視家庭團結和父權思想下的群體主義價值視為促成東亞國家和地區福利制度發展的重要基礎。③參見Joseph Wong, 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與西方國家將家庭作為國家瞄準保障對象的單位④例如,德國將家庭作為受益單位,而非繳費單位,維持的是傳統的家庭結構與社會分工。不同,東亞國家和地區強調家庭或家族的初級庇護作用,將家庭成員之間的分工與功能補償視為重要保障資源。這是因為,與西方“橫軸式”的家庭結構不同,東亞的家庭結構是“縱軸式”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情感與責任成為東亞家庭的核心內涵。
第二,儒家包容理念對東亞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由上文可知,雖然國家刻意讓家庭承擔較重的福利責任,但是不能由此得出東亞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此消彼長的簡單論斷。因為在東亞社會的差序格局中,家庭與個人之間的庇護-忠孝關系是可以依次向外復制的,即在國家和家庭、家族之間也同為庇護-忠孝關系,從而模糊了國家保障與家庭保障之間的邊界。換言之,東亞“國家-家族-家庭-個人”天然具有內在利益訴求的一致性。從具體的制度實踐上看,新加坡將儒家思想所主張的“藏富于民”的國家治道與個體“勤勞節儉”的生活之道演繹為強制儲蓄型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一方面強調儲蓄對個體應對未來風險的重要性,進而提高社會整體應對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形塑出勤勞自強的社會勞動者,并有助于增強個體安全感、自信心和尊嚴。因此,該制度具有同時增促個體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功能,成為新加坡“善治”體系中的重要構成。
第三,儒家和合觀對東亞社會保障發展的影響。與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不同,在儒家和合文化邏輯的支配下,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建立起了與經濟發展相包容、與經濟發展目標相協同的社會保障制度,亦即東亞社會保障制度實踐過程具有消解西方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對立困境的功能。例如,中國總體性社會時期確立起來的集政治、經濟和社會三位一體的國家-單位勞動保障體制;具有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融合屬性的新加坡組屋政策;日本現代企業管理引入家族式治理邏輯,在企業中形成如同家族般的庇護-效忠機制,從而消解勞資雙方激烈的利益沖突等。
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提煉出具有濃厚現代儒家色彩、鮮明東亞特色的社會保障模式,如“生產式福利體制”“東亞社會福利體系”“儒家福利國家”“發展型福利國家模型”。在上述理論觀點中,生產性福利體制和發展型福利體制得到更多的理論關注與實證支持。這是因為上述兩種分析范式描述并揭示出了對二戰后東亞國家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制度運行機理。其中,生產性福利體制強調社會保障政策依附于經濟政策,發展型福利國家強調社會保障政策與經濟政策相融合。
三、發展主義框架下的東亞社會保障范式探析
(一)發展主義框架下的東亞社會保障范式的形成與爭論
在20 世紀上半葉,東亞國家和地區都處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時期。二戰后,各個擺脫殖民統治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紛紛走上“發展”之路,并以實現“經濟發展”作為國家或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因此,“發展主義”成為主導東亞國家重塑的重要邏輯。所謂發展主義是指在二戰后伴隨亞非拉國家解放而由西方國家確立起來的、具有支配性的、對亞非拉國家治理系統建構與國家治理目標產生重要影響的知識-權力體系。具體說來,發展主義依據西方國家樣態而形塑出發達國家的形象,從而確立西方國家的優勢地位。以此為參照,廣大的亞非拉國家無論在政治民主、經濟發展,抑或是社會進步等方面都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因此被貼上“野蠻”“未開化”等標簽,成為亟待接受西方現代性開化的國家,而這一開化進程的廣泛鋪開即為現代性的全球化。
在此背景下,東亞國家與地區發展在國際學術研究領域始終被冷落。開啟人們廣泛關注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模式與機理的標志性事件是,20 世紀70年代左右的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即亞洲“四小龍”創造的經濟奇跡,以及亞洲經濟群①世界銀行于1993年發表了名為《東亞奇跡》的報告,把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泰國等八個國家和地區贊譽為“實現了高水準成果的亞洲經濟群”(HPAE)。參見鄭功成等:《東亞地區社會保障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2 頁。的形成。這引起西方學者們20 世紀80、90年代的熱烈討論,并大致形成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派學者持偶然論,認為東亞經濟繁榮是由于人口紅利或政府以犧牲社會發展為巨大代價而換來的,因此,東亞經濟繁榮不具有可持續性和研究的代表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持這一派理論觀點的學者更加堅信其觀點。但是,隨著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復蘇,該知識共同體內的許多人開始倒戈。與之相對,另一派學者認為東亞經濟繁榮的背后體現出的是具有東亞特色的國家發展模式。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被迫接受了以產業政策為代表的國家干預,并將擁有一套具有超凡治理稟賦的官僚體系②[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沙希德·尤素福編,王玉清、朱文暉譯:《東亞奇跡的反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 頁。視為成功的關鍵。約翰遜(Chalmers Ashby Johnson)將其稱為“發展型國家”③[美]阿圖爾·科利:《高速增長的政治經濟體從何而來?韓國“發展型國家”的日本譜系》,載禹貞恩編,曹海軍譯:《發展型國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也有學者稱之為“管治國家”。發展型國家是二戰后世界社會科學理論界對東亞國家特征所形成的共識性描述,這一結論是在對東亞與拉美和東歐等地域內的國家發展進行對比后得出的。該觀點認為東亞國家和地區采取的是國家機關技術官僚帶領的市場經濟模式,政府或官僚有意識地將經濟發展視為優先治理目標,同時利用國家力量(經濟及社會政策)提升經濟生產力及競爭力。發展型國家具有兩大相互關聯的重要特征:一是官僚體系所具有的超凡稟賦,即官僚能力或國家治理能力;二是明確的國家發展目標所依托的制度組合載體,即政府通過制定并形成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集合體,以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
在進一步解讀發展型國家何以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時,大多數研究將焦點放在了政府制定的產業、工業、金融等經濟政策所具有的國家治理功能,以及世界經濟重心轉移、技術普及等給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提供的機遇上。然而,雖然從經濟視角解讀發展型國家的治理能力看似直接有效,但卻回避了同是發展中國家并采取相似經濟發展策略的拉美國家同期的經濟增長率遠遠低于東亞的問題④20 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的平均增長率為1.7%,遠遠低于東亞地區的6.6%。。同時,還忽視了由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代價,及其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的嚴峻挑戰以及國家所作出的制度回應。如前文所述,此種二元對立的、將經濟發展“脫嵌”于社會的西方式分析路徑,難以全面準確解讀東亞國家治理能力。這是因為,一方面,發展型國家的治理能力是通過一個由政治政策、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等有序組成的執行體系來共同承載的,因此,不能僅從經濟層面進行單維度分析。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不同東亞國家的發展目標一致,但是達成目標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內部結構有所差異,亦即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不同,這將在下文中進行詳細闡述。另一方面,由于東亞各國深植于儒家文化中,“和合”“中庸”等觀念早已內化于東亞社會實踐的方方面面。那些在西方社會處于矛盾對立關系的勞動者與資本家、個人與國家、社會與經濟、公平與效率等,經由東亞國家治理后結為矛盾統一體。因此,一些東亞社會政策研究者和比較政治研究者紛紛從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互動關系中,探討社會政策在東亞現代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這方面作出開創性貢獻的是古德曼(Roger Goodman),他指出東亞各國和地區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包含了這些國家和地區中的大多數社會政策①Roger Goodman, et al.,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66-169.;權赫周發現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1997年金融危機期間,將社會保障作為促進經濟恢復的重要手段;吉爾伯特(Neil Gilbert)也通過分析這一時期的東亞社會保障指出,與20 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政策分析中的社會負擔轉向不同,東亞新興經濟體正在發展積極的社會保障。然而,在探討東亞國家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整合的內在機理時,學者們的觀點出現了分歧,可以分成以米德格雷為代表的“發展型社會福利”和以郝利德為代表的“生產性社會福利”兩種觀點,它們都是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體制可能具有的共性的探索與共識。發展型社會福利指出社會政策的思維深受經濟發展考慮的影響,認為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融合。生產性社會福利強調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成長的效用,認為社會保障政策應當高度從屬于經濟政策。然而,反駁生產性社會福利的觀點指出,從政治民主化或是全球化的角度看東亞福利體制的性質變遷,似乎逐漸轉向較為普遍式的福利供給②Yeon-Myung Kim, "Beyond East Asian Welfare Productivism in South Korea," Policy and Politics, 2008, 36(1).。當然,在此過程中,存在福利擴張的現象,以及堪虞的“肉桶政治”與相關的財政惡化后果③Yeun-wen Ku, "Is There a Way out? Global Competition and Social Reform in Taiwan,"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2004,3(3).。
(二)對發展主義框架下的東亞社會保障范式爭論的回應
生產性社會福利與發展型社會福利已經成為現階段解讀東亞社會保障的兩大基本話語體系,雖然不同話語下的學者們的觀點不同,立場有所差異,但是他們的核心意圖是基于東亞與西方不同的理論前提,在東亞社會保障制度實踐中提取區別于西方且穩定存在于東亞政治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制度特征,如重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協調、強調家庭(與婦女)的福利責任等等,發現或推動建構具有一致性的且具有東亞特色的社會保障體制。由于二者在社會保障政策與經濟政策關系上持相反觀點并不可調和,進一步加深了構建一致的東亞社會保障體制的理論解釋困境,造成東亞社會保障學術話語斷裂。結合二戰后東亞國家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提煉出來的發展型國家分析框架,以上研究為本文研究提供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奠基性內容。
第一,從國家治理體系的宏大視野中審視社會保障制度。總覽東亞社會保障制度研究,雖然自20 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成果數量不斷增多,但是研究同質性強,絕大多數研究就社會保障制度而論社會保障制度,或是對東亞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政策構成、支出總量的橫向比較研究,或是進行縱向的制度演進史梳理,還有少數研究關注東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與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情境,以及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初始條件、路徑和速度等方面。此種將社會保障制度與宏觀國家制度體系以及國家發展目標相脫嵌的做法,無法對東亞社會保障發展機理做出深入解讀,并會陷入到因各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情境不同而放大東亞社會保障異質性,進而無法把握其整體發展特征與脈絡的研究境地。而上述研究的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是引入政策體系的結構分析視角,將社會保障置于國家治理這一宏大視域下,據此就可以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一幅東亞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體制的發展進程圖。在東亞國家治理的歷史變化趨勢中,考量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結構性變遷,以順應國家治理和發展的需要。從學者們達成的研究共識來看,東亞國家和地區國家治理與發展的主導邏輯經歷了威權-經濟發展優先、威權民主化-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威權民主化-經濟社會包容性發展的轉變。在此宏大敘事中,東亞社會保障故事應運而生。
第二,在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與國家發展目標實現的聯系中展開社會保障制度分析。絕大多數東亞國家和地區是在20 世紀中期起開啟的那場自上而下的國家重建運動過程中建立起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由此可見,雖然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水平有限,但是東亞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成為東亞國家和地區提高國家建設與發展能力的應有之義,成為東亞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項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成為社會的重要組成形式。具體說來,其一,該制度滿足了國家權力獲得社會認同的需求,從而夯實國家權威的合法性,這點對于東亞新興國家而言尤其重要。這是因為新政權在建立之初亟需形成穩固的社會支持基礎和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只有如此,才能談經濟發展。由于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顯性的實現社會團結、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這點成為東亞各國在建設國家治理體系過程中考量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基本出發點。其二,它在儒家文化、殖民文化與發展主義三股文化流的交融影響下,具有推動實現東亞國家和地區自主、自強,并尋求獨特發展之路的重要功能。其三,它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都與本國、本地區的全面發展目標緊密結合起來,它們實際上的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對達到總目標所能做出的貢獻的程度。
第三,在社會保障政策與經濟政策關系中考量社會保障制度。以上述研究為代表,對東亞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往往以經濟政策為參照系,通過考察其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來進行社會保障制度及其功能定位分析。這一研究路徑的形成受20 世紀80年代以來的西方福利國家危機爭論的影響,其討論的一個核心議題就是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二者關系已經成為影響西方福利國家性質與走向的核心變量。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們發現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在金融危機期間的社會保障支出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由此引發了對東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持續、深入的關注。在對二者關系進行橫向比較研究得出生產性與發展型社會福利體制之別的同時,陳芬苓、古允文等學者指出東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所具有的階段性,亦即東亞國家和地區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從經濟優先轉為重視社會發展,而體現在社會制度方面則是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力度,以及擴大包容性或普及性的福利項目。
第四,上述研究使得構建一致的東亞社會保障分析框架成為可能。一直以來,研究者們雖然在東亞社會保障獨特性認知方面達成共識,但是就建構一致的東亞社會保障分析框架始終未能達成一致看法。王卓祺認為將東亞社會保障模式進行歸類是徒勞的①王卓祺:《東亞國家和地區福利制度——全球化、文化與政府角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第42 頁。。這主要是由于東亞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異質性較為明顯,例如社會保險型和強制儲蓄型的分立,各國和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結構的差異性顯著,因此要建構起一致的東亞社會保障模式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然而,綜合以上研究思路,可以大致勾勒出一個東亞社會保障體制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超越于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具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及產生情境,使得嘗試建構一致的東亞社會保障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四、東亞社會保障分析框架與制度模式的嘗試性建構
(一)東亞社會保障體制分析框架
1.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社會保障制度位置及其與經濟政策關系
本分析框架的主體結構采用了周雪光提出的“權威類型-支配手段-合法性基礎”的研究思路②周雪光:《國家治理邏輯與中國官僚體制:一個韋伯理論視角》,《開放時代》2013年第3 期,第5-28 頁。。與之不同之處在于,本文并非將其應用于對“官僚制”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研究方面,而是用以闡釋國家治理運行機理與變遷機制。該分析框架來源于韋伯(Max Weber)有關國家治理模式的研究。在《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中,韋伯劃分出三種理想的權威類型,即傳統權威、卡里斯瑪權威、法理權威③[德]馬克斯·韋伯著,康樂等譯:《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7-323 頁。。然而,這并非僅僅是一種類型學意義上的研究,它還具有國家治理邏輯轉換的動力學意義。具體說來,一種權威類型就是由一套“權力”“支配手段”和“合法性基礎”,按照一定的主導邏輯,結成彼此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力的有機整體。在其內部,由于“支配手段”的有效性具有“雙向檢驗”特征,即在權威運行過程中,支配手段的有效性需要接受來自國家權力和合法性基礎的雙重檢驗。由于國家權力與合法性基礎的組織載體之間存在利益分野,甚至利益沖突,使得支配手段需要在維護國家權力的前提下,吸合來自不同組織的作用力④唐睿:《體制性吸納與東亞國家政治轉型——韓國、新加坡和菲律賓的比較分析》,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13 頁。。當支配手段不能有效滿足社會利益訴求,亦即支配手段失準、失靈,則產生消極社會認同,引發國家權力合法性危機。其中,當由社會結構變遷產生新的權益訴求得不到有效滿足,引發支配手段失準、失靈,進而引起國家權力合法性危機時,表明該權威類型內的張力運動超越其包容范圍,從而生成權威轉型動力,引起權威類型更替。
在此基礎上,本部分結合前文分析范式,對其作出以下發展。首先,將“支配手段”具體化為官僚制與政策兩個方面。官僚制是支配手段的組織載體,政策是支配手段的作用形式,具體包括政策內容與政策結構兩個維度。從既有的相關研究來看,從政策內容方面討論東亞國家治理的研究較多,從政策結構方面討論國家治理能力的研究較少。由前文分析可知,政策結構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升與現代化轉型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在具體實踐中,大多數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精英基于本國社會保障的歷史傳承和具體國情,圍繞經濟發展,推動形成各具特色的社會保障與經濟政策的有序組合。為對此作出清晰描述,筆者將“發展型社會福利”和“生產性社會福利(生產主義社會福利)”所提出的社會保障與經濟政策關系問題置于東亞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在這里將國家治理體系視為由眾多制度按照一定組合邏輯形成的制度體系,從社會保障與經濟政策的關系及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兩個維度,綜合描述并詳細分析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在東亞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機理。由補償性政策模型、生產性社會福利和發展型社會福利提煉出三種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的組合形式,即“依附-托底”“依附-中心”和“融合-中心”。從亞洲“四小龍”經濟和社會政策結構的變遷來看,韓國、日本與中國臺灣地區都經歷了從“依附-托底”到“依附-中心”的政策結構轉向,并且在后來的政策實踐中出現“融合-中心”的變遷趨向,從而順應新形勢下所提出的國家治理要求,提高國家治理有效性,夯實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將合法性基礎具體化為社會結構與社會認同兩個方面。其中,社會結構是具有實體意義的社會單元的結合體,社會認同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個體對所處社會,以及在其中所獲情感和價值的主觀確認,二是由上述個體主觀確認匯聚、凝結而成的社會自我評價與對國家權力正當性的評價。第三,將該框架內的“雙向運動”分別描述為:國家權力引導與建構合法性基礎;合法性基礎推動國家權力體系調適與支配手段改革。
2.國家治理視域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外結構的雙向互動關系
上述分析框架將生產性社會福利與發展型社會福利統合起來,由這兩大范式凝練出來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之間及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與國家治理和發展目標互為因自變量,亦即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之間及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受國家治理和發展目標驅動形塑,反過來國家治理和發展目標的實現需要與之相適恰的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關系及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從而取消生產性社會福利與發展型社會福利的二元對立關系,將它們所揭示出來的社會保障政策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作為特定國家發展階段中服務特定國家治理目標的具體表現形式。需要說明的是,社會保障制度并非是一個制度,而是一系列制度構成的總和。從東亞各國和地區的制度構成來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包括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大基礎板塊。在下文所列的不同的社會保障與經濟政策的組合關系中,分別對應特定的社會保障制度內在結構。
(二)重構東亞社會保障體制
1.依附-托底型
所謂依附-托底型是指社會保障制度依附于經濟政策,服務于經濟發展這一國家治理的主導目標,且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于托底位置。與之相適恰,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部結構為社會救助制度居于主導,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制度初步發展。其存在于20 世紀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韓國、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國。在此體制中,將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工業主義思維占據主導地位,主張經濟先行,只有經濟發展上去了,才能談社會保障;將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穩定器、安全閥,化解由于經濟外部性和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弊端,形成事后補救式的社會保障理念,重視收入維持。在依附-托底型的社會保障體制中,重視收入維持式的社會保障的積極意義在于:一方面保障社會成員的生活,另一方面將其作為促進消費的手段。然而,這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提高消費能力的問題,反而助長消費社會中透支消費的問題。這種體制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之初,會形成立竿見影的治理效果,平復由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樹立國家權威,但是從長遠看,這一模式會致使社會保障陷入成為社會負擔的困境,從而加劇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致使政府陷入經濟發展優先還是社會保障發展優先的兩難選擇困境。
經濟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割裂,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兜底定位,會對經濟社會良性互動造成極其消極的影響。第一,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在于人,人力資本的提升成為推動諸多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依附-托底型社會保障體制中,社會保障無法發揮出促進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積極作用。因此,從長遠看會逐漸加劇產業升級與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失衡問題,即形成用工荒和勞動力過剩等結構性勞動力問題,從而使經濟發展速度放緩①[丹]克勞斯·彼得森:《為福利而增長還是為增長而福利?北歐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之間的動態關系》,《社會保障評論》2019年第3 期。。同時會增大社會保障資源國家供給的社會需求,從而進一步加深社會保障作為社會負擔的社會認同,加劇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對立關系。第二,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割裂,導致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資本運作、金融創新與科技進步,而這會在社會公共資源分配不公的條件下加劇社會貧富差距,導致部分社會成員脫離于主流經濟社會發展體系,由此導致底層群體越來越依賴社會保障,缺少競爭能力。由上述分析可知,依附-托底型的社會保障體制會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惡性循環。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踐上看,這一體制往往存在于新興國家治理體制初創的國家發展早期。隨著國家發展與治理水平的提高,國家發展目標發生變化,與之相適應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之間的位置關系及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也隨之發生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該如何認識這一時期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狀況,是否有如西方學者所研判的其為經濟發展的社會犧牲品呢?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水平低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其內部蘊含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動力,因此低水平是階段性的,這被后來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踐所證實。同時,與低水平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相補充的是不斷向外釋放制度紅利的傳統家庭保障制度。此外,低水平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這一事實內隱含的國家社會關系不是國家剝奪社會權益,而是在國家發展、民族獨立自強的強烈愿望下,國家動員全體人民共建國家。這意味著當國家發展水平提高的時候需要反哺社會。
2.依附-中心型
所謂依附-中心型是指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是依附型的,但是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與經濟政策同處于中心位置,即與經濟相互協調發展。與之相對應,社會保障制度內部結構為社會保險制度居于主導地位,社會救助制度兜底,社會福利制度有所發展。與上一社會保障體制類型相比,這一體制更具有促進與調節經濟發展的積極功能。按照社會政策研究者們的觀點,社會政策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但不是直接的經濟效益,而是間接效益。這是因為,更加積極的社會保障制度會對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產生重要作用,但是卻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只有勞動者從事經濟生產,才能將社會保障投入轉換為經濟效益。在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保險制度正是實現社會資源轉化為經濟效益的中介機制。在該體制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時空范圍是20 世紀60—80年代的日本,20 世紀80、90年代的韓國,20 世紀90年代的中國。
在此體制中,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前提仍舊是二元對立,但是在工業社會發展日益鼎盛時期,社會保險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和諧統一關系開始形成。這是因為隨著戰后初期國家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保險制度由體現社會名義權利向實現社會事實利益方向轉型。戰后初期制定的諸多社會保險制度開始不斷得到推廣與發展。隨著社會保險制度覆蓋面的不斷擴展,社會保險基金積累規模不斷擴大,社會保險的經濟調節與間接促進經濟生產的功能逐漸得到釋放。同時,工業社會發展也為社會保險制度發展奠定物質基礎,促進了社會保險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然而,隨著世界經濟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相繼爆發,以及東亞國家和地區壓縮式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錯配,工業社會與后工業社會的交織等復雜情境,使得這一體制面臨嚴峻挑戰。然而,與同期的一些西方國家相比,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從投入的具體方面上看,主要投資領域為更具有積極意義的教育、兒童營養、醫療。①[韓]金炳徹、[韓]都南希:《低生育率危機背景下韓國家庭福利政策變遷研究》,《社會保障評論》2020年第2 期。
3.融合-中心型
所謂融合-中心型是指從功能上看,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合二為一,亦即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顯著的經濟意義,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于中心位置。與之相適應,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部的結構為社會救助制度兜底、社會保險廣覆蓋,從二者的發展規模與程度上看,處于繼續完善階段;以婦女兒童福利、教育福利、就業服務、醫療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福利水平不斷提高。具體代表性的時空范圍為20 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新加坡、20 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日本、20 世紀末21 世紀初期以來的韓國和21 世紀初期的中國。此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融合關系及其發展趨向的得出,仍是基于勞動力商品化這一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勞動力是生產要素中的首要要素,因此用于投入到勞動力維持、發展與質量升級的社會保障資源如同用于擴大再生產的經濟投入一樣,具有經濟屬性,但是與具有私人利益屬性的用于資本擴大再生產的經濟政策不同,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使得人力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成為一項社會公共產品①[日]白瀨由美香:《日本社會福利的變遷:向以“自立”為主的生活支援轉型》,《社會保障評論》2018年第2 期。。同時,由于幫助勞動者提高應對未來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變遷風險的能力,增強了社會個體的自我發展能力和社會適應力,因此又具有社會保護的基本屬性。
4.國家發展目標與社會保障制度結構調整之間的扭曲關系
在現階段,無論是西方還是東亞,抑或是拉美,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順應國家治理與發展目標調整而做出相應調適,進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一個重要議題。隨著人類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新風險的常態化,人的存在狀態亟待需要通過完善與優化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得以重塑。然而,在此進程中,許多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觸及到了政治天花板,使這些國家陷入到所謂的福利國家悖論之中,即特定政治權威體制對國家發展目標導向下政策結構性調整起到約束作用,如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在于社會,而其所要維護的主要利益群體是資本家集團,由于資本與社會之間存在根本對立,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在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下,釋放社會保障制度改變人存在方式,重塑國家與社會、社會與個人關系的制度功能,進而通過采用一系列政治權術來掩蓋和轉移問題,扭曲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外部的雙向協同關系。與之相似,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社會保障發展中也面臨這一問題。
(三)東亞社會保障體制發展的新型“雁陣”
武川正吾認為應當建立一個區域一致的東亞社會保障模式,以應對區域性合作發展的需求。由前文分析可知,東亞社會保障體制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體制形態變遷具有內在穩定的動力機制,從而使其呈現出階段性特征。上述三種類型的演進是遞進累積式的,形成一個時間軸上的實踐序列,即由于各個國家與地區發展的初始條件與先天稟賦的不同,使得上述三種類型在不同時間段出現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中,但總體上呈現出一個比較清晰的雁型矩陣,即在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的內在邏輯的支配下,在東亞的時空場中上述三種體制層層演進。這一內在演進的支配邏輯為,在后工業社會變遷和政治民主化訴求增強的背景下,國家需要對不斷發展的社會需求與期待做出及時回應,將其融入到國家發展目標之中,以維護國家治理權威,不斷尋求新威權政府的正當性,因此,社會保障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必然得到逐步調整,使之更加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社會保障體制演進的“雁陣”不僅僅是時空間意義上的,還是社會發展意義上的。
從既有的進化過程來看,韓國、日本、臺灣地區經歷了社會保障體制從“依附-托底”型向“依附-中心”型,并趨向“融合-中心”型轉型的發展歷程。以韓國為例,以下剖析并展示國家治理體系、國家發展目標與社會保障制度內外部結構變化之間的動態圖景。從1961年到1979年為韓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初創期,韓國建立威權體制,經濟社會快速完成現代化變遷,創造出“漢江奇跡”,奠定了現代韓國發展基礎①Yamamoto Watanabe, New Challenges, New Approaches: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1, pp. 56-59.。從早期社會保障制度實踐來看,政府頒布系列社會保障法②樸正熙政權建立前期相繼出臺多個社會保障法律。1960年頒布《公務員年金法》,1961年頒布《生活保護法》《軍事救援補償法》《兒童福利法》,1962年頒布《災害救護法》,1963年頒布《有關社會保障之法律》《軍人年金法》《醫療保險法》《產業災害補償保險法》。,賦予社會成員福利權利之名。后隨著新的社會結構發育形成,不斷對既有的國家治理的支配手段形成挑戰。在這一時期中,勞工集團呈現出三大變化,勞工規模持續擴張,勞工集團的性別結構發生改變,出現青年知識分子這類特殊的勞工群體。不斷發展的勞工集團及其利益訴求難以進入國家權力體系。1972年,樸正熙政府面臨第一次的合法性危機。為此,樸正熙政府一方面加大社會壓制,另一方面逐漸落實部分社會保障政策,將其作為換取社會認同的資源。在1972年起的第三次計劃經濟時期,提出健康保險的重要性。1976年,全面修改《醫療保險法》,將參保對象由原來的大企業職工擴至全民,實行“當然參保”和“自愿參保”雙軌制③Shinyoung Kim,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elfare Policy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Nation: A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s Pension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06, 15(1).。同時,發展低收入階層的醫療保護事業。然而,有限發展的社會保障政策并未達到提升國家治理有效性的水平,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危機愈演愈烈。伴隨這一時期社會運動出現聯合趨勢,政治影響力增強,政府開始考慮保障其權益,先后制定了《老人福利法》(1981年)、《身心殘疾者福利法》(1981年),頒布《最低工資法》(1986年)。其中,《最低工資法》規定,沒有特殊技能或技能不熟練的勞動者工資達不到最低工資時,政府介入勞動力市場,保障勞動者工資高于最低工資④金鐘范:《韓國社會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23 頁。。但是,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政策仍舊延續樸正熙時代的做法,以社會救助為主⑤Huck Ju Kwon, "Advocacy Coali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in Korea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 Policy and Politics, 2003, 31(1).。由于國家治理手段的有效性不足,導致國家權力出現合法性危機。1987年,韓國工人運動出現井噴現象,最終導致威權體制瓦解。
威權體制時代結束之后,韓國進入政治多元時代。在這一期間,政府推動建立新型勞資關系,促進勞資協商文化形成;工會政黨化,允許工會涉足政治領域,從而重塑政治權力格局以及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格局,逐漸形成多元主體合作共治局面。由于韓國一直奉行輕社會保障、重經濟增長的基本國策,導致潛伏于20 世紀60、70年代的勞動力維持危機開始顯現。20 世紀80年代后半期,在新興技術產業發展所產生的勞動力需求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出現了“錯位”,即現有勞動力儲備無法與新興產業發展相適應,具體表現為“招人難”和“就業難”問題同時存在。在這一時期中,“隨產業結構調整的雇傭支援問題”和“需要強化職業培訓的問題”等被廣泛提出。與此同時,民主運動結成進步陣營,提出社會公平、正義和發展社會福利;工人運動出現大爆發,工人要求提升待遇。 在此形勢下,韓國政府在社會保障發展方面,作出劃時代的決斷。在1987年至1991年之間的第六次經濟發展計劃中,出現提高社會福利公平性的目標①蔡增家:《韓國轉型》,巨流出版社,2005年,第111-113 頁。。與1988年之前源于君王父權恩澤的社會救助②Song Ho Keun, "The Birth of a Welfare State in Korea: The Unfinished Symphony of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3, 3(3).不同,此后韓國社會保障開始進入到權利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家角色由管制者向積極介入者轉型。一系列社會保障法相繼頒布,如《青少年培育法》(1989年)、《殘疾人雇傭促進法》(1989年)、《嬰幼兒保育法》(1991年)、《雇傭保險法》(1993年)等,國家實施著力于人力資本培育的積極社會保障政策。其中,198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將低收入戶納入健康保險范圍中。同時,政府開始對全民健康保險給予財政支持,但是由于實施過程中引發財務危機的問題,使得改革之聲強烈。然而,這一時期的改革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得政府專業人士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顯性化,并造成改革信任瓦解③Huck Ju Kwon, "The Korean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genda," in Christian Aspalter (ed.), Discovering the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 Praeger, 2002.,直到2002年,全民健康保險的財務問題才達成共識。到20 世紀90年代中期,上述政策調試的效果才開始完全顯現。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政府相繼頒布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法律和制度,成立勞資委員會,建立勞資協商平臺。在經濟方面,開始超越先增長、后福利的發展模式,追求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協同成長”“同伴成長”,即二者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由傳統的“托底-依附”向“中心-依附”轉變。這表明韓國現代國家治理手段發生重大轉向,政策內容與組合形式發生里程碑式的變化。
轉型后的社會保障發展并非注重水平的提高,而是更側重于制度內涵的改善和結構調整,向與經濟發展相融合的方向轉型,集中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1999年《國民健康保險法》的頒布及其后的財政整合,表明韓國社會保障向更加積極的方向轉變,并被評價為韓國醫療保障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第二,1999年將《生活保障法》修改為《國民基礎生活保障法》,其重大意義在于生活保障政策由過去40年的“單維-施惠型”轉變為“系統-權益型”,針對低收入階層提供綜合性、系統性的自立支援服務,鼓勵個體參與勞動,防止勞動意愿減退。第三,2000年以后加大教育援助。以韓國bk21 計劃為例,從1999年到2012年,教育援助經費增長了近一倍。第四,2007年1月,韓國政府宣布實施CDAS 賬戶④王卓祺:《東亞國家和地區福利制度——全球化、文化與政府角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年,第42 頁。,適用于18 歲之前的孤兒和機構安置兒童,2008年擴及低收入家庭兒童,2009年擴至工作貧困家庭的兒童,2010年50%的韓國兒童被覆蓋。該制度目標在于縮小兒童貧富差距、培育人力資本、擴大未來勞動力儲備。
此外,單位社會時期的中國大陸、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建立起來的則是“融合-中心”型社會保障體制。需要說明的是,伴隨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升級,中國社會保障體制的變遷路徑為由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融合-中心”型逆轉為20 世紀80、90年代的“依附-托底”型、21世紀初期的“依附-中心”型,并在未來國家建設與發展中趨向新的“融合-中心”型。中國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進程中不斷完善優化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體系,不斷釋放國家治理制度效能。在改革開放初期,伴隨經濟社會體制轉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目標下,中國快速實現了市場經濟的壓縮式發展,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迅猛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與此同時,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被提上政治議程。從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內部結構來看,社會救助制度得到迅速發展,社會保險開啟了制度建設的大幕。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給社會保障制度結構優化提出新要求,社會保險制度得到快速發展。自黨的十六大起,國家開始重視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及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具體表現為以發展市場經濟為中心,同步大力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這標志著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保障制度與經濟政策的“依附-中心”階段。黨的十七大報告繼續對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做出重要表述,指出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指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對社會保障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空前地在黨的綱領性文件中將社會保障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國內外的重要場合都提到了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觀點。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發揮出了直接的經濟調節與促進功能。總的來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經歷了從被動反應到主動促進的轉變,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在結構由社會救助居大到社會保險為主導的轉變,社會保障制度功能由社會穩定器到促進消費,再到激活生產、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的轉變。從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變遷軌跡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與經濟政策之間的相對關系由“依附-托底”向“融合-中心”轉變。與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沒有給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設限的政治局限性。相反,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優勢會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在順應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下實現充分發展,最終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共在。
五、小結
本文的一個理論訴求是嘗試性建構表征東亞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體制的概念邏輯體系。這是因為,不同的社會保障話語體系具有不同的現實建構力,它作為指導人實踐的主觀意識構成,通過人與外部世界互動轉化為客觀實在,使外部世界被打上其烙印,同時該話語體系也會在此過程中不斷得到豐富與發展。具體說來,本文運用宏觀政策結構分析視角,將福利體制、發展型國家和生產性社會福利、發展型社會福利等分析框架結合起來,對東亞國家發展背景、目標、進路,以及每一時期中各個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內部增長點,外部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歷史考察,嘗試建構一個統一的用來分析和考量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框架。然而,這一研究過程是非常復雜且有難度的。未來,筆者將會持續進行東亞制度發展史、社會發展史、經濟發展史、政治發展史的深入學習與研究,進一步豐富與優化該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