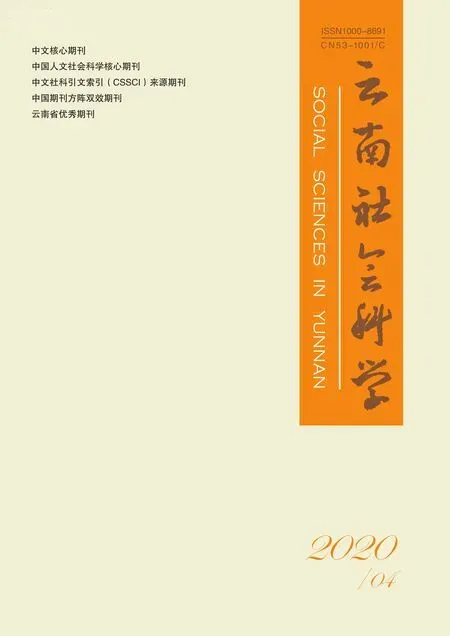論宋代橋梁記科技與文學的雙重書寫
李 佳
橋梁記,是因修建橋梁而作的記文,文章題目多為“橋梁名稱+記”形式,屬于中國古代記體文類。目前所見的最早橋梁記是后魏武定七年(549)于子健的《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自此至唐存有4篇,而有宋一代則驟增到80余篇,可見宋代橋梁記創作的繁榮景象。目前,學界已經認識到了宋代記體文的獨特價值,譚家健、曾棗莊、楊慶存、洪本健等人已有論述,尤其是以繪景抒懷為主的亭樓記、游記,因其文學性較強,為文學研究者所偏愛,研究成果較多,但對內容寫實、風格質樸的橋梁記則關注不足。實際上,橋梁記內容豐富,包含建橋方案、施工過程、山川地貌、地域風俗、哲理闡釋、人事評價等內容,具有文學、建筑學、地理學、史學等多維價值。橋梁記的繁榮與宋代的儒學復興、科技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從文學與科學并置統一的視角考察宋代橋梁記書寫,分析實現雙重書寫的文體、文士、文化因素,對探究宋代乃至古代中國文學與科技的密切關聯、中華文明的整體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一、掄材選址、纜舟架梁:宋代橋梁記中的科學記載
宋代橋梁記中包含的最為豐富的科學信息主要集中在橋梁建筑科學領域。自春秋戰國時期的《考工記》倡導“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為良”①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頁。開始,歷代百工匠人在追求優良品質的過程中,無不綜合考量天時、地理、材美、工巧四大因素,宋代橋梁建造概莫能外。宋代橋梁記中,記載了橋梁的選料用工、修造原理、造型規模、尺寸功用等科學信息。以下按照橋梁外形并參照建材主料,分別考察宋代橋梁記所載的浮橋、梁橋的建筑科技書寫。
(一)浮橋建造技術書寫
浮橋,古時稱為舟梁。它是用船只來代替橋墩,故又有“浮航”“浮桁”“舟橋”之稱。①王俊:《中國古代橋梁》,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15年,第13頁。浮橋,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橋梁,《詩經·大雅·大明》所載“造舟為梁,不顯其光”②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1頁。,便指浮橋,因其聯舟而成,營造難度小,見效快,故經漢魏至唐宋,一直是中國古代橋梁家族的重要成員。尤其是河面寬闊、水流湍急的大江大河,修建橋墩、架設橋梁非常困難,而聯舟而成的浮橋則能快速有效地解決渡水難題。宋代橋梁記中有很多修建浮橋的記載,從中可見修造技術不斷完善的過程。
鳳林橋位于今江西吉安安福縣,南宋王庭珪、周必大相繼為此橋作記。南宋紹興十年(1140)王庭珪因縣令韓幫光重修鳳林橋而作《鳳林橋記》,文中詳載橋之規模狀貌:
橋長三百尺,廣十有二尺,下為二十舟,魚貫而浮。橋心為亭,其方如橋之廣而益其三分之一,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江之南為屋于堤上,以觀浮梁之倒影,丹雘飛動,若欲凌鶩大空者,曰彩虹亭。
換算成現代長度單位后,橋長約100米,寬約4米,橋板用浮于水上魚貫而列的船只承托。鳳林橋不僅考慮到交通需求,而且考慮到審美需求,橋中間修建“跨江亭”,橋南岸修建“彩虹亭”,用以觀覽長橋臥波、水光天色的美景。浮橋相對易建,但木舟木梁隨水漲落而伸縮飄蕩,再加上風侵雨蝕很容易損壞。南宋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受縣尉陳章請托,因再修鳳林橋而作《安福縣重修鳳林橋記》,而這已經是自王庭珪撰寫《鳳林橋記》50年來的第三次修繕了。周必大在文中梳理了鳳林橋修建變遷后,指出了浮橋易壞的重要原因——材料不足、工匠不巧、維修不及時,陳章再次修造則吸取了教訓:“掄材選工,舉大舫二十而新之,冶鐵為綆,紉竹為筰,圖惟悠久之計”③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31冊),上海、合肥: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5頁。,與王氏《鳳林橋記》記載相比,這次建橋挑選了能工巧匠,將小船換為大舫,繩索換為鐵鏈,并辟專門資金用作日后修繕,以圖橋梁使用久遠。在此之后,鳳林橋經歷了多次毀修,并在明代萬歷、崇禎年間經鄉紳鄒善、知縣陳寶泰等人相繼維修加固,成為長約170米的石梁橋,更加堅固宜行。④注:鳳林橋歷代修繕使用情況,可參看劉崇坦主編,安福縣人民政府地名辦公室編印:《江西省安福縣地名志》,1986年,第319頁。
浮橋易建,也易毀。其常因水流大小漲落而被不斷拉伸,特別在夏秋季節強降雨后,水量暴漲,往往拉斷繩纜,解體船舫,瞬息之間,沖散浮橋。鑒于此,宋人不斷改進浮橋技術,唐仲友《新建中津橋碑記》中,便詳細記載了如何解決這一難題:
以寸擬丈,創木樣置水池中。節水以筒,郊潮進退……橋不及岸十五尋,為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撻。筏隨潮與橋岸低昂,續以版四。鍛鐵為四鎖,以固橋。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系筏。⑤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60冊),2006年,第353頁。
中津橋由南宋唐仲友于淳熙八年(1181)任職臨海(今浙江臺州境內)時,親自設計建造。他仔細考量河流變化,先按1:100的比例在水池中制作了橋梁木樣,使建橋工匠明確橋梁原理構造,做到胸有成竹后,方予施工。唐仲友用6個木筏連接橋與岸,使浮橋長度可隨水面寬度變化,這是中津橋最可貴的設計。“漲潮時,筏浮于水,但又靠柱和篾纜控制住位置。潮落時筏成坡道,各支點擱在兩柱之間不同高度的楗上,成為名副其實的棧橋,由于潮水漲落坡道與舟節之間距離的改變,以及浮橋平面上曲率的變化,靠續以筏間的跳板來調節,一切自動進行。這一‘活動引橋’原理,現代浮橋還在應用。”⑥唐寰澄、唐浩:《中國橋梁技術史》(第1卷),北京: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89頁。
上述以外,宋代還有很多記文寫有浮橋技術信息,如葉適《利涉橋記》中的浮橋建于今浙江黃巖:“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笝繂索,隄其兩旁,梱圖狻猊,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兩萬五千,夫公六萬余。”①葉適著:《葉適集》,劉公純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170頁。宋祁《壽州重修浮橋記》所建浮橋位于今安徽壽州,施工如是:“下令於冬,材集以春。百桴盤盤,泛溜而臻。是鋸是斤,疏為千章。密貫致聯,壓柞扶持。舟牢索堅,垣為夷涂”②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4 冊),2006年,第373頁。。范成大在乾道五年(1169)任處州(今浙江麗水)郡守時修葺浮橋,并作《平政橋記》:“凡為船七十有二,聯續架梁,為梁三十有六,筑亭溪南以涖之。”③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24 冊),2006年,第389頁。朱熹《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橋之修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視水之上下而時損益焉。”④朱熹撰:《朱子全書》(第24 冊),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3802頁。這些記文留下了江左、嶺南大小型浮橋的諸多信息,為探究宋代浮橋應用地域和建造技術留下了寶貴資料。
(二)梁橋建造技術書寫
梁橋古稱平橋,可直接架梁于河谷兩岸,也可架于木柱或橋墩上,外形平直,相對于拱橋容易建造。宋代橋梁記中出現最多的橋梁類型便是梁橋,主要有木柱木梁、木柱石梁、石墩石梁三種,建造者根據地形、財力等情況因地制宜,修建完畢作文以記。
石介《宣化軍新橋記》所記“新橋”是木柱木梁橋,建于宣化軍(今山東高青縣),施工過程嚴謹科學:“工之巧拙、材之良惡,斧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如此九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⑤石介:《石徂徠集》(2),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68頁。建造者兼顧工匠能力、材料優劣、工具效用、測量方法等因素,特別考慮到木材易腐、質地柔韌的特性,專門精選多年生長、壯大堅硬的木料,設置37座木柱來支撐78根木梁,力圖使用長久。中原和江右一帶木柱木梁橋相對較多,蓋因木材獲取方便,臺風暴雨較少,并非一定要石橋來抵抗惡劣天氣侵襲。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汴梁城中的虹橋便是木拱橋,楊億《南津橋記》所記南昌的南津橋:“以時斬木,必取楩楠之良”⑥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12 冊),第2頁。,楩木、楠木皆為大木。《戰國策》載:“荊有長松、文梓、楩、楠、豫”⑦劉向編訂:《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7頁。,說明楚地盛產這幾種木材,在南昌建木橋只需依照時令,去附近山中采伐即可,比較方便。
石橋比木橋更堅固耐用,然而大型石材的切割、運輸、架設需要巨大的財力、人力和高超的技術,并不容易實現,故而長城才被譽為世界奇跡。運石上山困難,砌石江底、架石江面亦殊為不易,然而,憑借天時地利、眾志巧思,宋代仍然修造了大型石梁橋,成為橋梁史上的奇跡。蔡襄于泉州任上,歷時7年主持修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入海口處大型石梁橋——萬安橋,也稱洛陽橋。竣工后,蔡襄作《萬安橋記》載:“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工。壘址于淵,酈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⑧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47 冊),第198頁。蔡襄記文樸素,只是記錄了橋梁地址、規模尺寸、大略外貌,并未夸耀建造之苦與功績之大,反而映襯其謙遜務實的品格。實際上,萬安橋的先進技術在同期和后期其他橋梁記中,得到重要補充。北宋方勺《萬安橋》記載:“多取蠣房散置石基上,歲久延蔓相粘,基益膠固矣”⑨程國政編注:《中國古代建筑文獻集要·宋遼金元》(上),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5頁。,利用牡蠣分泌物加固橋基,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采用“種蠣固基”的生物學原理加固維護橋梁,為蔡襄獨創。明代仇俊卿《重修洛陽橋記》詳細總結了蔡襄造橋時創造的“筏型基礎”“浮運架梁”等先進科學方法,為后世留下寶貴的資料。萬安橋建成后,閩地造橋多用其法,如晉江安平橋、連江縣潘渡石橋等,“僅《泉州府志》中就記載了一百十座”①潘洪萱:《古代橋梁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7頁。,很多石梁橋沿用至今,令人驚嘆。20世紀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曾在他《中國科技史》中道:“在宋代有一個驚人的發展,造了一系列巨大板梁橋,特別在福建省,在中國其他地方或國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它們相比的。”②[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183頁。
閩地出產花崗巖,修造石橋取材便利;海港大橋與內陸橋梁相比更要抗住海水侵蝕、風暴摧殘,故此地建造石橋既有條件又有必要。其他地區雖然知曉石墩石梁橋堅固持久,但處理較難、費用昂貴,而木柱木梁橋,材料處理雖然方便,卻不堅固,于是結合二者利弊,出現了石墩木梁橋。蔡襄修萬安橋,起到了榜樣作用,推廣到浙江沿海一帶,溫州樂清名士萬規便仿照萬安橋在瀕臨東海的赤水港修建了萬橋,《永樂樂清縣志》卷7曰:“(萬規)居海濱,有赤水港,舊以舟渡覆溺者多。規乃竭家資,率邑里,買石筑堤,仿泉之萬安建橋”③《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永樂樂清縣志》卷7。,但因為資金石材不足,萬規便造了石柱木梁橋,并作《萬橋記》記錄靠一己之力建橋的過程,他先用石材建兩岸灘地并向水中延伸以橫截江水:“筑成東西兩灘,上下一百尋,截江三十丈”④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75 冊),第134頁。本段引文,皆選于此。;繼而江中壘起4個石橋墩,橋墩碩大堅固,迎水面尖銳,以減少水流阻力。“乃累橫石為四柱,其形銳而大,一柱之廣縱二尋,橫一尋有半,其三尋有畸埋灘淤之下,出灘之上者裁二尋有半”;每個橋墩長約5米,寬約3.8米,高約14米,其中約7.6米隱埋在淤泥下。⑤注:八尺為一尋,宋代尺大約是今31.68 厘米,以此為標準計算石墩的長、寬、高。最后,在橋墩上橫木為梁“上跨木為梁,其柱疏以立,其間迂而闊,以石不能跨故也。吾嘗謀以石為梁,則曰:非剛厚極大者則不能長久,抑非綿力薄材所能致也”。可見萬規最初是想在橋墩上架設石梁,以求橋梁使用久遠,但橋墩之間距離較遠,非厚且長的巨石不能實現橋墩間跨聯,但單憑萬規個人的財力、技術無法實現,只能暫時架木為梁。萬規對此有遺憾亦有希望,他在文中講:“吾于是橋,曠歲以觀其變動,而后能盡其利疚。其梁木他日雖有壞,其址柱不壞,以其時損增之……吾之于利,不獨在于落成之日,而又存于救壞之時。”萬規在個人力量無法實現建造石柱石梁橋的情況下,橋柱全部使用石材,省卻后人截水建基之難,梁板更換相對容易,暫用木材,待他日有條件可隨時將木梁換為石梁。可見萬規建橋并非貪圖一時之功,而是傾盡全力,圖其久遠,便于后人。如萬規所望,萬橋經明清到現代的幾次修繕,已換木梁為石梁,在九百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普惠樂清百姓,至今仍是白龍江兩岸的聯通要道。
宋代橋梁記中記載的橋梁類型不唯以上幾種,按造型劃分,還有虹橋、單跨橋、多跨橋、屋橋等。如張玠《會湘橋記》所記為屋橋:“架屋其上,以庇風雨”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70 冊),第368頁。,唐仲友《重修桐山橋記》所修的山間橋梁是單跨“飛橋”:“相水勢不可與爭,架木為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尋有六尺,覆以板,甓甃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有七尺,疊石各廣九尋”⑦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60 冊),第360頁。,并于橋梁兩側設置石欄,美觀安全。
要之,宋代橋梁記中的橋梁書寫與詩、詞、賦文體中的橋梁書寫的最大不同,便是書寫方式與目的的不同。詩、詞、賦中的橋梁書寫多采用描寫的方式,通過形象描摹,傳達橋梁的美感,或以“橋”為一個意象,同其他意象共同構成意境,如王安石《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縈花草”⑧高克勤選評:《王安石詩文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3頁。,范成大《州橋》“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⑨高海夫選注:《范成大詩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頁。。而橋梁記中的橋梁書寫,多采用數字、敘述、白描等綜合方法,全面書寫橋梁的地域、選材、造型、原理、尺寸、工具等信息,精準、客觀地展現橋梁本身與建橋始末,這種客觀科學的書寫方式,不僅使橋梁記本身具有一種嚴謹、質實、精簡的美感,而且留存了大量古代建筑科技文獻史料。宋代距今約千年,彼時橋梁多已毀廢,但從橋梁記留存的諸多信息中,仍可見宋代領先世界的橋梁建筑技術,對于宋代建筑科學及文化發展研究,殊為可貴。
二、揚善貶惡、議理抒懷:宋代橋梁記中的情志表達
宋代橋梁記中除了大量橋梁信息的客觀記錄之外,另一突出內容便是抒情言志的主觀表達,而主觀表達是作品文學性的重要體現。宋代橋梁記主要通過議論敘述的方式來直接表達作者的情感態度,這與同時代的游記或者亭臺記主要以寫景敘事而升發出作者情感態度的方式有所不同。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淫雨霏霏、春和景明的描繪,蘇軾《石鐘山記》月夜絕壁、駭然聲響的描摹,這類描寫在橋梁記中極為少見。橋梁記作者不需要太多景象描繪作為自我情志表現的寄托或鋪墊,而是多本于儒家經世觀念,在文中直接闡明政治觀點、品評人物風格、抒發哲思感慨、揭露時局弊端。
(一)美刺社會現狀
橋梁記在漢魏時期初現,其功用一是記錄建橋始末,二是贊揚建者功績。記文完成,多勒石刻碑,立于橋旁。宋代記文沿襲了橋梁記文體的“稱頌”基因,很多作者借“稱頌”建橋者大發議論,歌頌篤誠勤奮、任責務實等高尚品格。
文同《眾會鎮南橋記》,記載了北宋鮮于端夫的建橋事件。文章開篇便稱贊:“中山鮮于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繼而簡述其抵御羌虜、平定邊陲的焯焯大功:“虜嘗薄城,欲肆其丑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眾乘陴,分制御具,隨迮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諸羌畏攝,不敢動創心,群疑釋然而安”;邊境安定后,鮮于端夫又乘其空閑,通溝修橋、惠利民眾:“坐累家居,杅杅然不自廢,猶視其所以當為者為之”;石橋建成后,過者歌德,文同亦贊:“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①文同:《文同全集編年校注》,胡問濤、羅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第971頁。本段引文,皆出于此。文章從建橋事件引申開來,插敘鮮于端夫抵御敵寇的事跡,意在彰顯其疆場建功的大才和為民謀利的大義,以彰顯愛國愛民、奮發有為的社會風尚。
其他橋梁記中也多有稱美建橋者的言辭。羅適《洞山石橋記》,記載洞山邑良民應宗貴組織族人修建石橋一事。文末嘉嘆其“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②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75 冊),第324頁。。郭知章《王公橋記》記載承議郎王成季建橋以解濟涉之難,盛贊其能吏品格:“(王成季)靜厚衍裕,政本于誠,介然與世吏殊好。并心一意,惻怛于吾民,培善使植,化悍使柔,獄訟不威而辨,賦役不猛而集”等。
宋代橋梁記中不僅沿襲了文體“稱美”的傳統,而且加入“諷刺”“批評”的意味,這是橋梁記在宋代的新變,文中常常批判政令、庸吏、惡俗。蘇轍于熙寧七年(1074)任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市)掌書記時,著有《齊州濼源石橋記》,記載了齊州知州李常、歷城知縣施辨等人建造石橋的事件,文末議論耐人尋味:
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于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于恤民,一切仰給于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于為政,與二君之敏于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于舊則倍,不可不記也。③蘇轍:《欒城集》(上冊),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00頁。
蘇轍認為州縣建橋本是正常政務,但現在管理制度嚴苛,官吏做事沒有自主權,一切以上級為是,導致政務處理阻力連連,民不獲益。與昔日制度對比,弊端明顯,那么昔日如何呢?從前政令靈活有度,建橋等惠民之事,可與民眾商量共同出資,共同受益,如此一來,民生工程建設效率高、效果好。如今,民眾急需橋梁解決交通困難,而政府修橋需要征得上級同意,并獲得官方撥款,此類政事因資金不足常常作罷。齊州濼源石橋若不是利用附近廢棄堤壩的石料鐵器,亦恐難成。而今昔之變化,源于熙寧變法。王安石于熙寧二年(1069)開始主持變法,到此時是第五年,蘇轍反對新法,他離任中央、任職齊州也與此有關。早在嘉祐末年(1063)王安石征求蘇轍對“青苗書”(此書已具青苗法之雛形)的意見,蘇轍云:“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①脫脫:《宋史·蘇轍傳》(第31 冊),卷339,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823頁。,便明確反對官吏嚴苛教條的執行政令,既不利于處理政務,又不方便百姓。《齊州濼源石橋記》中的觀念與之一脈相承,蘇轍先后任職河南、陳州、齊州,更能體會到新法具體施行中的弊端,便在文中借建橋之難,加以批評。
其他諸如此類在橋梁記中表達批評觀點的還有曾鞏的《歸老橋記》,記寫柳侯年老主動辭官歸鄉而建歸老橋的事件。文中借釋名“歸老橋”,贊賞知老而退的柳侯,暗諷那些年邁無力卻不舍爵祿的官員。正如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所載:“老而致仕,進退之節宜爾。柳侯歸老之樂,知止之意,所以風有位也。”②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052頁。石介《宣化軍新橋梁記》記載宣化軍使張景云建造清河橋,文中痛斥了地方惡俗。清河上屢次建橋都被15家擺渡人破壞,久而久之,形成奸孽之風,文章描摹其奸惡之狀:“爪距森森、牙齒顏顏,相與橫歧盤錯于其間,崇奸深,樹孽大”③石介:《石徂徠集》(2),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68頁。。從夸張的言辭中,可見作者嫉惡之心。
(二)抒發感悟哲思
宋代理學大盛,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真德秀等理學家輩出,即使以文稱盛的蘇軾、王安石等人,理學造詣亦頗精深。在士林濃郁的理學風氣影響下,作者時常在橋梁記闡述經義哲思,使得宋代橋梁記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學色彩。
真德秀是程朱理學傳人,于寶慶丁亥年(1227)作《上饒縣善濟橋記》,當時其為史彌遠所不容而退歸故里。文章記載了里間富人葉澤出資建橋的事件,真氏贊賞葉澤仁善的同時,兼論“富”與“仁”的關系:“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④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5,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437頁。先引《孟子·滕文公上》“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⑤王立民譯評:《孟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60頁。,引出富裕與仁善關系的話題,并作進一步闡釋,一般來講,“富”與“仁”是矛盾的,擁有財富的人,多缺乏仁心,一心追求利益,沒有心思去幫助別人。而心地仁善的人,多沒有財富,想要助人,卻沒有能力。真德秀的理學根植于儒學,他對“富”與“仁”矛盾關系的認識,與儒家“重義輕財”觀念,乃至由此進一步引出的中國封建時代“重士輕商”“重農輕商”的價值觀,一脈相承。
再如周必大《鄒公橋記》中總結封建社會中興利濟人的三種方式與各自局限:“力可興利濟人者有三:郡邑以勢,道釋以心,富家以資。然勢者或病于擾而其成也茍,心者必借于眾而其成也緩,資高者又豐入而吝出,瘠彼而肥己,能推惠者幾何人哉?”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31 冊),第221頁。他認為官府借助行政權威興利濟人,但常常為各種制度掣肘,成事勉強;佛道兩家借助影響人心而促其做事,但需借助眾人之力,成事緩慢;富人可憑其錢財興利濟人,但多不舍其私家財產,成事者少。周必大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官至丞相,能高屋建瓴、顧覽全局地總結社會問題,對待紛繁事物能擊中肯綮、抓住要理,清晰而準確地闡釋出來。橋梁記中的哲理闡發還有江公望《睦州政平橋記》感慨:“政之在事者有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疏、文而不害”⑦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21 冊),第340頁。,黃裳《坦履橋記》:“縣令知其所以為政,邑人知其所以為善,二者相遇于邂逅,則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⑧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03 冊),第326頁。凡此種種,皆為常見。
除哲理闡發之外,宋代橋梁記中也偶有興懷抒情。如葉適《利涉橋記》中回憶往昔同鄉鄰娛嬉山川的悠游場景:“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于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憾。”①葉適:《葉適集》,第171頁。這一段與《論語》曾點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②金良年譯注:《論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頁。所描述的場景極為相似,抒發了出葉適投身自然的怡然灑脫之情。但總體看來,宋代橋梁記的主觀表達中,仍以議論時政義理為主,此類抒發超然之情的極少。
橋梁記中既包含造橋原理數據的科技信息呈現,又包含作者情志的文學色彩表達,這種科技與文學的雙重書寫,其他文體鮮見。傳統文章如詩、賦重于情感渲染,策、論重于觀點闡發,即便是橋梁記之近親亭樓記也多是景象描繪和哲思抒發,文學韻味濃厚。而一些宋代科技文獻,如《營造法式》《木經》《宋史·河渠記》等多是客觀說明,幾乎沒有主觀色彩。宋代橋梁記是鮮有兼備文學與科技雙重表達的文體,它將文學的善感綺麗與科技直簡冷靜相雜糅,形成一種獨特的美學風范。那么,為何這種雙重書寫是橋梁記而不是其他文體能夠實現?為何是宋代而不是宋前能夠實現?以下試作探討。
三、文體、文士、文化的作用:雙重書寫的實現條件
關于宋代橋梁記何以能實現科技與文學的雙重書寫,應從文體、文士、文化三個層面分析。
(一)文體功用:宋代橋梁記具有“記錄”“教化”功能
橋梁記是記體文的一種,記體文誕生之初的功用為——“所以備不忘”,文中一一記錄建造橋梁的緣由、地點、經費、修建者等信息,便是以備將來查閱建橋始末的,并常將文章勒石刻碑,置于橋旁,用來彰顯主事者的品格功業。因此橋梁記除了“記事件”外,還有“頌功績”的意味,宋前的4篇橋梁記,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橋記》(后魏),崔祐甫《汾河義橋記》(唐)、喬潭《中渭橋記》(唐),劉丹《西郭橋記》(唐)皆是如此,從文體功用角度看,“記”實與“碑”“銘”文體互有交叉。至宋代,士人“破體為記”,使得橋梁記也打破了原有“記事件”“頌功績”的邊界,大大增加了主觀情志表達的成分,且多以議論的形式呈現,具有教化意義。宋人張玠《會湘橋記》說明作記目的:“既以此相勉,又將以觀于異日”③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70 冊),第368頁。,“勉”便是勉勵眾人之意。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論宋代記文“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41頁。,宋人在橋梁記中不僅頌揚建造者,還鮮明表達了對時政、歷史、風俗的褒貶態度,希望使文章發揮引領社會風尚的教化作用;甚而明經辨理,使教義傳之久遠。
宋代橋梁記繼承了橋梁記文體自身的“記錄”基因,使得文章可以客觀記錄建橋信息,這些客觀信息中,便包括橋梁材料、規模、尺寸、技藝等科學信息,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列舉的橋梁記文本中大量科技信息,皆得益于橋梁記文體的記錄功能,橋梁記的科學書寫便有賴于此。宋代橋梁記變革后文體又新增“教化”功能,如葉適《贈薛子長》講:“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⑤葉適:《葉適集》,第607頁。,當然這并非是宋人特意強化橋梁記文體的教化作用,而是在崇尚議論的時代風氣的熏陶下,文風的整體變化。關于宋文愛發議論的特點,諸多學者已有論述,郭預衡道:“文人學者中間,好發議論,也就蔚為風氣”⑥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3頁。,張壽康言:“宋代雜記則多議論、抒情乃至有考據、說明的成分”⑦張壽康:《文章學概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7頁。,這也是文體自身發展變革規律的體現。橋梁記若要具有“教化”功能,僅僅客觀記錄建橋事件是無法實現的,必須要有主觀議論和說理,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列文獻,橋梁記中常有態度鮮明的贊頌批判,或是平緩嚴謹的道理分析,相比宋前橋梁記,主觀色彩尤其鮮明,而鮮明的主觀色彩則凸顯了宋代橋梁記的文學性。總之,正是橋梁記文體到了宋代兼有“記錄”“教化”的兩種功能需求,成為科技書寫與文學書寫融合一體的前提。
(二)文士特征:宋代士人具有博學、務實品格
宋代橋梁記的創作主體是宋代士大夫,橋梁記創作者與建橋者的關系主要分為兩種:一是作記者與建橋者是同一人,如萬規建造萬橋后作了《萬橋記》,有能力造橋者多是官員或鄉賢,而無論是學而優則仕的官員,還是修養品格為人敬重的鄉賢,都是有著良好文化素質的知識階層;二是作記者與造橋者并非一人,如曾鞏《歸老橋》,乃柳侯修橋后向文豪曾鞏請求而作,宋代橋梁記大部分都是應請之作,考慮到傳播效應,所請皆是雄文碩學之士。
作為橋梁記創作主體的宋代士人,多兼官員、文人、學者于一身,與唐代及之前的士人相比,知識結構更加全面合理,且能知行并重,求真務實。曾鞏讀書涉獵廣泛,“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托遠、山镵冢刻、浮夸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于此”①曾鞏:《曾鞏集》,陳杏珍、晁繼周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285頁。,其中的歷法、星官、樂工、山農、地記便屬于科學技術領域。周必大所學 “源深流洪、九流七略,靡不究通”②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82 冊),第319頁。,朱熹則“對自然科學問題非常關心,因為他建立哲學體系需要科學”③李申:《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頁。。
州學、軍學、縣學、書院等教育機構所教科目也很全面,包括經、史、理、工諸類。如北宋初年胡瑗執教湖州州學時創立了“分齋教學法”,“設經義、治事兩齋,以敦實學。經義齋學習儒家經典理論,治事齋學習農田水利、軍事、天算等實學”④童一秋主編:《語文大辭海·語文教育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7頁。。治事齋教授的是具有實用性的水利、算數等專業技能,中國教育史上從此誕生了集傳統經義與科學技術于一體的教育機構。此后,分齋教學作為“蘇湖教法”,推廣于太學及各地學校。如此一來,科學技術教育的地位上升,并極大普及,宋代士人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士人都更具理學素養和技術能力,且務求實踐。他們擔任地方官員時大多重視修橋、建堤等水利工程,如蘇軾不但精通文學書畫,還在徐州任職時修筑了抗洪堤壩,在杭州任職時疏浚西湖;曾鞏在齊州(今濟南)任職時修建了北水門,明州(今浙江寧波)任職時疏浚廣德湖;唐仲友任職臨海(今浙江臺州)時親自改良了浮橋的結構,興建中津橋。正如學者所言:“在中國古代,那些在科學上做出貢獻的科學家首先是一般的人文學者或是朝廷官員。”⑤樂愛國:《國學與科學》,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頁。
在橋梁建造等工程完成后,他們或是記載自己的造橋經歷,或應請記錄他人建造過程,而無論主動還是被動作記,在橋梁記書寫中,宋代士人所具有的博學務實之精神,使得他們既能以文士的筆法去書寫情志,又能以工程師的思維書寫橋梁建設的數據和原理,這是實現宋代橋梁記文學與科學雙重書寫的重要條件。
(三)文化背景:宋代廣泛開展橋梁營建活動
書寫橋梁記的必要前提,是要有修建橋梁的活動。宋前橋梁記僅4篇,宋代則驟增到80余篇,不得不說宋代橋梁營繕的興盛局面,是促使宋代橋梁記繁榮的直接動因。宋代造橋何以興盛?除了建筑工藝提高之外,還跟國家倡導密不可分。
宋代官制變化頻繁,而無論怎樣變化,都設置了主管橋梁營繕的部門,用以籌劃、主持、督查橋梁建設。宋初實行“二府三司”制期間,度支司發運案掌管都城汴京河道的橋梁修建,戶部司修造案督查諸州橋梁營繕;元豐改制中,將作監、少府監、都水監都職掌橋梁建設,因橋梁與交通、農業、水利等領域均息息相關,故涉及的中央管理部門也比較駁雜。地方官員對橋梁的管理更加復雜,轉運使、知府、知州多兼堤堰橋道勸農使主持橋梁修造,如歐陽修、沈括等均曾任職。知縣、耆長等更是直接參與地方橋梁修建。橋梁建設還直接關系到官員的獎懲考課,《宋史·河渠志》記載:“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橋成……四月具圖來,上降詔褒美。”⑥脫脫:《宋史·河渠志》(第7 冊)卷9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36頁。向拱因修橋有功,便得到了皇帝褒獎。
在層層倡導督查之下,修建橋梁不僅是民之所需,而且是政之所顯,很多官員士人將修橋濟人作為重要政務。如魏了翁曰:“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則厲深濟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覘陳議鄭,固不越是。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以末務忽之也。”①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10 冊),第441頁。自古以來橋路修造便是考察官員吏能政績的重要參照,不能忽視。韓元吉云:“古者,矼石彴木而為之橋,病其涉之利也,后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為制,庀在有司,凡州縣之濱於巨川者,得用為法,然或為或否。君子常以是為觀政,非甚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怠云爾。”②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16 冊),第202頁。意在說明橋梁于交通之重要,能不能克服困難營造橋梁,可反映出官員品性與吏能。
國家倡導、士人重視,外加宋代建筑技術發達,如科技史研究者言:“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宋元時期達到最高峰”③[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總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第289、290頁。,“宋代在橋梁建造技術中利用力學的成就是非常卓著的。宋代在材料的選擇上表現出驚人的成就”④邵慶國主編:《宋代科技成就》,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第221頁。。座座橋梁在江河、山谷、海灣凌波而起,正如劉辰翁《習溪橋記》所描繪:“吳之垂虹,閩之水西,泉之洛陽,不論揚州金陵,錢塘姑蘇,又略杓小者,亦不可為數”⑤劉辰翁:《劉辰翁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4頁。。如此一來,橋梁記書寫便有了最直接的需求,那些橋梁科學技術、士人志向追求才有了進入橋梁記被書寫的可能。
結語
綜上,橋梁記到了宋代不僅出現創作數量上的繁榮,而且在書寫上與以抒情言志為主的賦、策、論、表、書等文體明顯不同,具有科技說明和文學表達的雙重特點,這就使得橋梁記文體既具有科技文章的客觀精準性,又具有文學作品的情思感染力,二者融合后,形成了橋梁記的獨特文風。且如今宋代橋梁遺跡所剩無幾,宋代橋梁記中保留的建筑科學信息,對古代建筑與文化研究,尤為寶貴。宋代橋梁記科技與文學雙重書寫的現象是多種因素促成的:文體自身的發展變化,使得宋代橋梁記要求其具有“記錄事實”與“教化世道”的功用,這是橋梁記進行雙重書寫的基本前提;文士博學的知識體系、務實的做事理念,使作者進行雙重書寫成為可能;文化大背景上,國家重視修造橋梁、科技發展達到頂峰,使得橋梁營繕活動廣泛開展,這是橋梁記創作的直接動因。宋代橋梁記是一座文化富礦,除了建筑學、文學價值外,其地理學、史學價值也很大,有待學人繼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