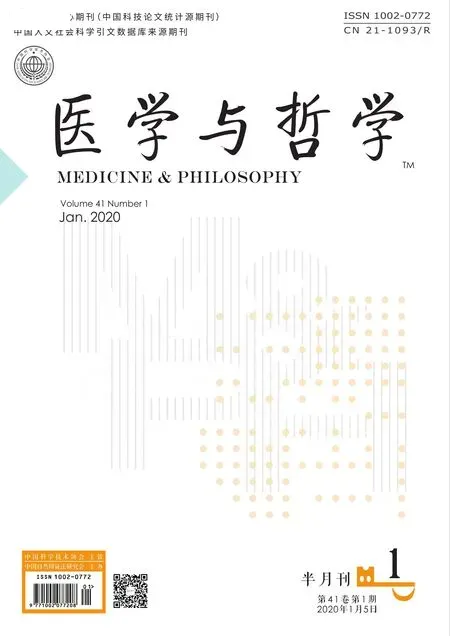出生缺陷兒的倫理決策探討*
郤冠楠 黃璐琪 田 桑 汪吉梅
1 出生缺陷流行病學和救治決策困境
出生缺陷(birth defects)或先天異常(congenital anomalies)是指胚胎或胎兒在發育過程中發生形態和功能上的異常。這些異常可由遺傳因素引起,包括染色體異常(如唐氏綜合征)、基因異常(如白化病)等;也可由環境因素所致(如沙利度胺致海豹兒畸形),以及遺傳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如唇腭裂)[1-2],嚴重危害兒童身心健康和我國人口素質。一方面,隨著醫療水平的進步,許多原本無法存活的胎兒得以幸存,卻同時也留下各種后遺癥,導致存活的出生缺陷兒不僅未減少,一定程度上還有所增加。根據衛健委2005年公布的監測數據,我國出生缺陷的發生率約為128.38/萬,且從1996年起呈逐年上升的趨勢[3]。另一方面,強制婚檢的取消、環境的污染、“二胎”政策開放導致的高齡產婦增加等,也都是出生缺陷發生率上升的原因。
國際上關于出生缺陷的分類方法有很多,如根據畸形器官進行分類[4],按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編碼分類[2]。而根據嚴重程度則分為重大和輕微缺陷兩類,前者指需要進行復雜的內外科矯正手術的缺陷,后者則不需要進行復雜處理。臨床實際中二分法過于籠統,很多時候也將出生缺陷分為四類:(1)缺陷不影響或輕度影響新生兒今后的體能或智力;(2)缺陷對新生兒今后的體能或智力有一定影響,但到達一定年齡有一定的勞動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智力可達到一定水平;(3)缺陷對新生兒的體能或智力有嚴重影響,今后生活無法自理或智力極度低下;(4)缺陷對新生兒是致命的,無法救治,必將死亡[5]。由于輕微畸形預后較好,且經濟問題有公立和民間各種救助基金協助解決[6],因而傾向于積極救治;而極重致死的患兒,放棄救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并無爭議。因此,實際真正的難題是處于中間地帶的患兒。
面對這類患兒,無論決策的天平偏向哪一方,都有可能帶來一系列問題。作為醫師,救死扶傷、延續生命本是不容猶豫的天職,但醫療資源有限,救治希望渺茫的出生缺陷兒可能會占用救助其他患兒的醫療資源。作為患兒父母,高昂的醫療費用、長期的康復訓練、所需要耗費的時間精力、沉重的心理負擔足以完全拖垮一個家庭[7]。對于社會,雖然尊重每個人的生命權本是人類的基本特征之一,但社會資源有限,嚴重出生缺陷兒不但無法為社會做出貢獻,在客觀上又需要消耗大量資源[8]。而站在新生兒自身的角度,若只是一味延長生命的長度而無法提高生命的質量,也只不過是增加痛苦。因此,對于出生缺陷兒“治療還是放棄”這個問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倫理原則和相關法律法規慎重決策。
2 處置出生缺陷兒的相關倫理學理論
生命健康權是人最基本的權利,而伴有嚴重出生缺陷的新生兒是否具有生命健康權卻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他們往往在出生后一段時間內會因自身無法矯治的疾病而死亡,無法發育為完整的個體;或者有的雖然可以靠醫療手段維持生命,但永久處于無意識狀態。在這些情況下,他們就與平常觀念中的“人”有所差別,因而人們對其生命健康權的保障也意見不一:雖然有學者認為“胎兒在體外成活時即為人”[9],但國內主流觀點認為“沒有意識的胎兒雖然是人類物種的成員,但并不享有生命權”[10](即認可墮胎的依據之一)。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時,各種觀點背后的潛在的倫理學理論基礎可分為“本體論”、“義務論”和“功利論”。
在生命倫理學的語境中,本體論意味著“人”的標準確立。按照彼得·辛格本體論的觀點,人分為“人類物種的一員”(member of the species Homosapiens)和“人格生命”(person)[11]。前者涵蓋了所有屬于人類物種的成員,包括胚胎、植物人、腦癱患者等,他們雖有生命,但不具備人類的生命權。人類不容侵犯的生命權的標志是具備自我意識、道德能力、社交能力和好奇心等。這相當于把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承認生命質量最核心的元素是智力與溝通能力。實際上,目前多數學者也傾向于這樣的觀點,即能發育出自我意識潛力(大腦相關功能完整)的患兒應得到救治,而幾乎不可能出現自我意識的患兒(如無腦兒)則建議放棄[12-13]。
義務論則強調生命的神圣可貴,高于一切。認為即便是那些注定一輩子智力低下、無自理能力的出生缺陷兒,也不能剝奪其生存的權利,主張應按照“只要有一絲希望就要盡百倍努力”的原則而采取行動,而不論最終是否實現、代價如何,是救治出生缺陷兒的理論基礎。義務論支持者認為嬰幼兒具有巨大的疾病康復潛力,許多在成年人身上預后極差的情況,發生在新生兒身上或許能發生奇跡;現在有缺陷的智力,或許將來科技發展進步了,使用新的治療方法可使其追趕上或接近同齡人的發育水平。義務論的合理之處在于體現了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人性慈愛,但救治成功的幾率有多少,代價的上限在哪里,誰來承擔代價等現實問題,義務論無法回答[14]。以義務論為主體思想衍生出的極端案例,是不顧臨床病況,甚至不顧法律規定為搶救希望渺茫的嚴重出生缺陷兒過度耗費資源。
案例:2010年天津一女嬰患有先天性肛門閉鎖、心臟卵孔未閉、腎積水等畸形,且醫生認為此女嬰病情即使進行手術,預后亦不容樂觀。女嬰家長在召集家族會議后決定放棄治療,但經媒體曝光后愛心志愿者冒著綁架兒童的指控沖入臨終關懷醫院內搶奪嬰兒連夜送至北京醫治,女嬰最終還是死亡[15]。
案例表明,在面對此類問題時,愛心常常被批評為偽善的原因——發展中國家資源有限,無差別地選擇救治是不切實際的。此外,權利和義務是需要對等的,許多嚴重出生缺陷兒自出生起一直享受父母、社會的照顧撫養的權利,但卻無法履行贍養父母、回報社會的義務,這樣的入不敷出在事實上成為了父母和社會的負擔,長遠來看是無法持續的。
功利論則從現實利益角度,按照“對多數人有利”的原則指導行為,是放棄治療缺陷患兒的理論基礎。嚴重出生缺陷兒極大概率在將來無法對社會做出貢獻,反而會消耗大量社會資源。在持功利論的學者看來,這些出生缺陷兒的死亡本就屬于被自然淘汰的“天意”,救治他們無疑對多數人不公平。于患兒的父母而言,救治出生缺陷兒會讓他們額外負擔一大筆醫療費用,而這些資源完全可用于重新孕育一個完全健康的孩子。若由政府托底出生缺陷兒長期的養育護理,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特別是許多不經救治能存活,但生活難以自理的出生缺陷兒(如唐氏綜合征)[14]。功利論的思想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皆有之,且十分常見:清朝民間的嬰兒塔——父母花點錢將新生兒置于龕內,名曰祈福,實則任其餓死;中世紀歐洲婦女常掐死自己的嬰兒,以“被子蓋得太厚”為由掩飾嬰兒的真正死因。甚至有完全健康的嬰兒,僅僅因為性別為女,或出生順序靠后就被活活溺死,更遑論肉眼可見的出生缺陷兒(如唇腭裂等)[15]。因此,雖然功利論有一定合理性,但若放任其存在也會產生不良后果——部分患兒父母可能因其他原因(如性別選擇、財產繼承等),或單純因為不愿承擔醫療費用而擴大放棄治療的范圍,導致部分本該得到救治的患兒死亡。
現實中決策者在考慮如何處置出生缺陷兒時,上述幾種理論的影子往往同時兼而有之,最后以某一種占據主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幾種理論究竟在具體案例時占據多大比重,很多時候并不僅僅取決于患兒的臨床病情,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患兒家長的受教育程度、所處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宗教信仰、當地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等。如在某些信奉傳統天主教的國家,主流思想是“醫生不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哪怕這個生命處于巨大的痛苦之中也要想盡一切方法挽救”,用安樂死來處置出生缺陷兒是約等于謀殺一樣不可被接受的行為[16]。而在這些因素中,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性的,在這方面所展現出的趨勢是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人們更傾向于義務論,經濟較落后的地區人們更傾向于功利論。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有學者對大學生群體中針對新生兒安樂死的問題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境外生認為“對缺陷新生兒實施安樂死有違倫理的”比例遠遠高于內地生[17]。
3 嚴重出生缺陷兒的決策實踐
治療與放棄到底該由誰來決定?最理想的情況是醫患雙方共同完成決策[18]。然而,患兒無法為自己做決定,作為患兒利益、生命最相關的主體和法定監護人,父母有最主要的決定權[13]。但他們的決策也有缺點:缺乏專業醫學知識,無法對客觀情況做出理性判斷。醫護作為專業人士,對患兒的治療選項和結局有清晰的認識,理論上可以為決策提供理性的力量。但由于患兒的治療費用基本由父母承擔,為了避免糾紛和矛盾,醫護人員往往只是被動順從家長的意愿[5,19]。在國外經驗中,除了父母/監護人、醫護人員以外,倫理委員會和法院也參與這一過程。倫理委員會的角色相對醫護人員和父母/監護人而言更公正和獨立,其處理類似案件的經驗和倫理準則也有助于做出最優的決策。此外,法院可作為法律代言人在決策中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從而大大減少事后糾紛,其主要適用于家長堅持要放棄“應當治療”的患兒的情況,因為一旦患兒存活卻發生醫學無法預測的不良后遺癥,家長往往會把責任推給當初建議保留的醫護一方。在美國,也曾有父母拒絕嚴重出生缺陷兒的治療而被醫生訴諸法律的案例,最后法院判決醫生強制為該患兒實施姑息性手術,理由是只要一息尚存,其就有作為人類享受生命權的基本權利[17]。但法院程序冗長、時效性差,對于正經受痛苦煎熬的危重患兒也是殘忍的。上述四種角色在決策過程中各有利弊,而它們的有機結合將能夠形成一套合理和高效的決策機制。雖然現階段我國還遠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患方知識素養的提高和法制的進步,對生命權的尊重將驅使人們逐漸產生對這一機制的需求。出生缺陷的處置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規范和指南,也需要來自外部的監管。
在面對出生缺陷的患兒時應該參照什么樣的決策原則,目前的觀點眾說紛紜,在此列舉幾種以供參考。Panicola[20]認為最主要的三條標準為“醫學治療指征”原則、“最有利”原則和“相對的生活質量”原則。符合“醫學治療指征”原則指救治患兒應根據其有無治療指征,而不是依據其缺陷的嚴重程度。“最有利”原則要求治療應考慮患兒的利益而不應考慮社會和家庭的負擔。“相對生活質量”原則要求在救治前應評估患兒將來的各方面能力是否能滿足其生活目標,如果確定他的將來沒有任何希望,那應該放棄治療。Panicola的觀點體現了對患兒生命的尊重,且相對具體,因而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最有利”原則強調的不顧代價治療在當下的中國往往難以實現。Clark[21]將缺陷新生兒按救治的優先順序分為五類,分別是:無潛力發展出人際關系;有一定發展出人際關系的潛力但一生將與病痛斗爭;有一定發展出人際關系的潛力但健康狀況可能惡化;有一定發展出人際關系的潛力但治療手段容易變得無效;有一定發展出人際關系的潛力且疾病狀態可糾正。按此分類,第五類的患兒應得到最優先救治,而第一類患兒則應放棄。他的觀點基于馬克思“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思想,優點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人的社會經濟價值和情感價值,缺點則表現為并非所有患兒都能被清晰分類,為實踐增加了困難。國內的陸于宏等[14]提出“生命尊嚴、醫學科學、社會公益、公正”四條原則,即積極救治有可能形成“自我意識”的患兒;放棄將要死亡和嚴重畸形的患兒,但為其實施減緩痛苦的姑息治療;衡量個體、家庭和社會的“受益”和“代價(風險)”比;強調醫療資源的分配公平合理,不能將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到少數患者身上。但若家屬情感上無法接受,且愿承擔開支及照顧,醫生還是應積極治療,社會也應理解,并給予關心和幫助。
一旦決定放棄對嚴重缺陷兒的治療,其具體的操作層面也有兩種選擇:停止一切生命支持手段待患兒自然死亡(即被動安樂死),或以人為手段加速患兒死亡以減輕痛苦(主動安樂死,即狹義上的安樂死)。在我國,主動安樂死仍可能被依照《刑法》界定為謀殺行為[22-23]。加之目前醫患關系緊張,哪怕患兒父母主動要求,醫護人員大多不敢實施,故我國一般默認的是被動安樂死。但被動安樂死也存在不少問題:因我國的臨終關懷和居家安寧療護還未得到推廣[24],若不可醫治、必將死亡的患兒處于巨大痛苦中,靜待其死亡反而不人道;而無法產生自我意識但生命中樞尚完整的患兒(如重度腦癱兒),停止治療后患兒不會死亡,也達不到被動安樂死的目的。
但反觀主動安樂死,因其在理論上有一定合理性,而且在其他國家也有先例,所以在我國對其討論也從未停止。但要落實到立法實施的階段,還有許多爭議。首先,我國法律認為公民自出生起就享有不容侵犯的生命權,但出生缺陷兒的情況比較特殊[23]。嬰幼兒還不具備自我意識,無法表達自身的訴求,故無論決策者是父母還是醫護人員,實際上都是作為他們的代理人替他們決定生死。父母雖是他們的骨肉至親,但在某些情況下也有可能放棄本該救治的患兒[7]。同時,醫學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確定的科學,根據一時的病情有時很難判定其最終結局,一些在醫學上被認為預后不佳的患兒,在一段時間的康復后,也可能獲得出人意料的治療效果。此外,受各地發展水平不均的影響,有的出生缺陷兒在農村地區可能確實不具備治療的條件,但在發達大城市就有救治的可能。因此主動安樂死需要非常嚴格的指征和執行機制[25]。荷蘭是世界上少數安樂死合法的國家,但在出生缺陷兒的安樂死問題上也十分慎重。荷蘭十六周歲以上的公民可以決定自己是否接受安樂死,但嬰幼兒無法表達自己的夙愿,其父母也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他們的立場。為此,荷蘭政府專門出臺《格羅寧根草案》(The Groningen Protocol)來規范嚴重疾病的新生兒安樂死問題。申請安樂死的新生兒一般可被劃分為三種:(1)沒有生還希望;(2)預后極差,無法離開重癥監護;(3)恢復希望渺茫,且被父母與醫生判定為處于難以忍受的痛苦之中。該草案規定了申請新生兒安樂死時必須滿足以下條件:診斷明確、父母雙方均同意、患兒的主治醫師和至少一名與該患兒診治無直接關聯的醫生同意。且患兒完成安樂死后,外界的法律團體會介入檢查每一步程序是否充分完整。美國并不允許對新生兒實施主動安樂死。為保護兒童權益,美國政府于1984年頒布《兒童虐待法案》,其中規定醫師應努力救治出生缺陷兒,但羅列了三種可放棄治療的情況:(1)嬰兒長期且不可逆陷入昏迷狀態;(2)所提供的治療只是延緩嬰兒的死亡,無法減輕或解除嬰兒所面臨的病情;(3)所提供的治療對嬰兒的存活無益,且在這種情況下治療本身對嬰兒而言是不人道的[26]。
4 出生缺陷防治的社會機制、法律法規和相關建議
出生缺陷的預防不容忽視。出生缺陷的一級預防是通過婚檢、增補葉酸、預防孕期感染、規范孕期用藥等方式防止缺陷胎兒的產生;二級預防是通過彩超、無創產前DNA檢測(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絨毛膜活檢、羊水穿刺、胎兒鏡等產前診斷方式防止缺陷胎兒的出生;三級預防才是對缺陷新生兒的合理處置[27]。但無論是婚前檢測還是孕檢產檢,僅靠現有手段都無法完全杜絕缺陷新生兒的產生[28]。因此,完善對已出生的缺陷患兒的處置法規同樣十分重要。目前的臨床實踐中,醫護人員雖然對患兒的處置有一定傾向,但礙于事后責任劃分和保障機制不明確,往往只能給予家屬暗示而非明確的建議。實際上孟憲武[29]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天津就曾試圖制定嚴重缺陷新生兒處置法規,其中對每個環節均有明確的處置方案:處置對象限定為新生兒;處置標準分為:(1)應當舍棄(短期內將死亡者、無法發育至成人者、可發育至成人但智力低下或自理勞動能力喪失者等);(2)選擇舍棄(對后代有不良遺傳影響者、影響一定程度智力或自理能力者);(3)不應舍棄(贅生物、小血管瘤等)。流程上,處置書須患兒主治醫師、主任/副主任醫師、助產士/護士;患兒父母;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屬缺陷兒審查組三方簽字方才有效。處置方式為除簽字人員外的三人以上行動組對缺陷兒實行主動安樂死。但由于缺陷新生兒是否具備社會屬性、處置標準等問題的爭議,當時建議的這項法規最后不了了之。雖然距今已三十余年,但這份法規草案的很多內容仍未過時,尤其是醫護人員、家長和倫理委員會三方決議的制度仍然合理且實用。同時還應重點考慮的問題是:(1)明確哪些該救助;(2)若值得救,父母遺棄的該如何處理,父母無力承擔費用的如何救助;(3)若不建議救,如何妥善對待。醫學的本質是關愛人,即使是決定放棄的嚴重出生缺陷兒,也應盡量減少其痛苦,給予其應有的臨終關懷,才更符合倫理要求。
在處置缺陷患兒的具體實踐中,因遺棄而滯留醫院的患兒同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中絕大部分情況是父母不愿意或無法承擔救治費用,主動或被動將患兒滯留醫院以期獲得免費救助[30-32]。醫院面對這樣的情況往往也束手無策,只能任其滯留或訴諸法律,但二者均會產生巨大的成本,給醫院增加不必要的負擔[33]。雖然《收養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中均有涉及這一問題的條款,但這些法律規定還不夠詳細具體,同時在執行時也困難重重,如懲罰家長會導致患兒后續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其境遇往往并不能得到改善甚至會更糟。因此,即便有法律規定,現實中家長幾乎不會承擔什么法律上的后果,頂多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另外,具有兜底功能的福利院在處置此類患兒時也并不積極,一方面是因為患兒父母尚在且仍然具有監護權和撫養義務,另一方面是因為福利院無法負擔其巨額的醫療支出。解決缺陷患兒滯留醫院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權責明晰及執行到位,例如,缺陷患兒的監護權何時應歸屬父母,何時該移交福利機構;患兒父母有支付能力和沒有支付能力時其治療費用如何劃分;醫院為患兒治療墊付的醫療成本該如何消化;社會志愿服務團體能在這一問題中發揮怎樣的作用。不過,考慮到出生缺陷對于任何一個家庭來說都是不幸,其背后都是沉重且現實的負擔,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應聚焦于“幫”而不是“罰”,救助措施應該具體且可行,例如,可借鑒成人滯留醫院的處置模式,采取政府通過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方式[34],引入醫務社會工作力量幫助解決患者出院后給家庭帶來的困難。工作流程上遵循“分析患者和家庭需求—結合介入理論—制定短、中、長期服務目標—協調社區和福利機構”的流程進行服務。在核心救治費用問題上則采取多方籌款的方式解決:區紅十字會申請補助一部分,醫院減免一部分,發動捐款再籌集一部分。
5 結語
出生缺陷患兒的處置是復雜的問題,尤其對于那些可存活至成年但智力或自理能力低下者,更是存在爭議,其決策需要結合具體問題進行。相關倫理學理論有利于我們在處理患兒時明確救治與放棄的界限。而在具體的實踐方面,需要在最大可能尊重生命的前提下,制定完善、具體、可執行的制度,從而平衡父母、醫院、社會和政府救治的權利和責任。倫理考量是形成決策的出發點,完善的法律法規和流程機制才是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落腳點。對生命的尊重,對弱者的幫助體現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希望未來某天,我們在處置每一例這樣的“殘缺的天使”時,能不疑惑、不推諉和不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