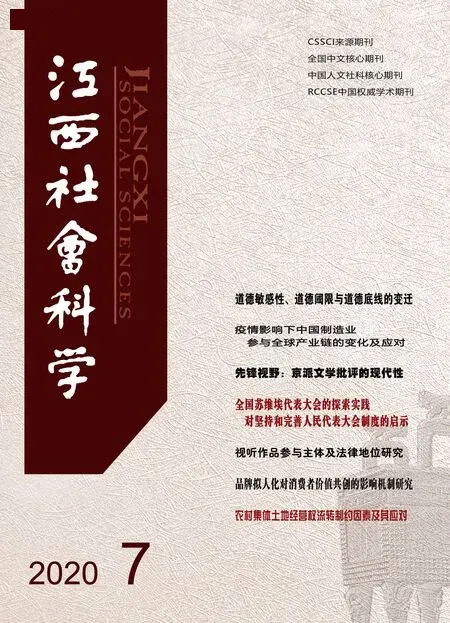人倫與規范:傳統蒙書中的道德養成
■班高杰
“蒙書”是我國傳統啟蒙教育中進行道德教化的重要載體,主要以未成年人(十五歲以下)為教化對象,進行以“明人倫”為核心道德規范教育。“明人倫”旨在教導童蒙對差序格局的認知,禮儀規范的習得是對“禮”所倡導之秩序的遵從。道德養成通過“明人倫”“知禮儀”的詳細具體的行為規范踐履,從小處、細處著手,養成童蒙的道德品質。
《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道德理念和規范,我們要大力弘揚傳承中華優秀文化,要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穿于啟蒙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各領域”。同時,“以幼兒、小學、中學教材為重點,構建中華文化課程和教材體系”,既要編寫中華文化幼兒讀物,又要創作系列繪本、童謠、兒歌、動畫等。傳統啟蒙教育無論是在教材編寫,還是在價值引導行為塑造等方面都可資借鑒的地方,尤其是以“蒙書”為載體的啟蒙道德教育,能在“明人倫”與“習禮儀”的過程中,養成童蒙良好的道德品質。
“蒙書”是我國傳統啟蒙教育中進行道德教化的重要載體,主要以未成年人(十五歲以下)為教化對象,進行以“明人倫”為核心道德規范教育。在以“蒙學”為載體的道德教化中,傳統宗法社會倡導的價值觀雖未被明確提出,但以默認的前提隱而不彰,散見于童蒙教育的各個環節。“明人倫”旨在教導童蒙對差序格局的認知,禮儀規范的習得是對“禮”倡導的秩序的遵從。傳統啟蒙教育中的道德養成,著力于通過詳細具體的行為規范,從小處、細處著手,養成童蒙的道德品質。
一、我國傳統啟蒙教育的道德指向:蒙以養正
“有人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辟則既然矣。”[1](P379)我國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擁有源遠流長的兒童啟蒙教育歷史。早在虞舜原始時期,我國就已經出現類似于現代小學的機構。《禮記》記載:“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禮記·王制》)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們的先人就提出對兒童要及早教育,引導他們走上正道,認為這是神圣的事業。《周易》明確記載:“蒙以養正,圣功也。”(《周易·蒙》)啟蒙教育作為教育的起步階段,不僅對個體的發展具有奠基性的意義,而且對整個社會和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此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啟蒙教育一直未有間斷,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啟蒙教育都占據一席之地。中下層儒者參與啟蒙教材的編寫,宋明之際更有經學大儒親自編撰童蒙書籍,以供童蒙識字、修身、養德。朱熹更明言,小學階段“知其事”,是為大學“明其理”鋪墊,小學階段是在為大學階段打下“圣賢的坯璞”。道德品性的養成與行為規范的訓練,是啟蒙教育的主要活動。通過道德教育和教化活動的實施,儒學也實現了“自上而下”的教化目的,真正體現了“切于日用而不自知”。從上層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貫徹到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這個過程也是儒學世俗化的過程。
所謂蒙學,是一個特定層次的教育,特指對兒童進行的啟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學的內容、教學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內容。這一教學舊時在書館、鄉學、村學、家塾、冬學、義學、社學等名稱不同的處所進行。[2](P2)因此,蒙學就是傳統社會人們開展的啟蒙教育,同時也包括開展啟蒙教育使用的蒙養教材,相當于我們現在的“小學”。蒙養書就是為了實施啟蒙教育而編成的教材,也稱為蒙學讀物、啟蒙教材、蒙學教材、語文教育教材、童蒙書、古代兒童讀物,盡管稱呼不同,但這些教材的實質內容大多相似,涵蓋的范圍也較為廣泛。
在啟蒙教材的編撰過程中,中下層儒者功不可沒,正是他們用世俗化和通俗化的語言編寫多種蒙學讀物。在這些啟蒙教材中,后世儒者對歷代圣賢的嘉言進行改編,力圖把蒙學讀物中的內容和知識通俗化、趣味化,滿足兒童的閱讀需要。宋明之際,上層知識分子也參與撰寫相關的童蒙讀物,如朱熹及其弟子、王陽明及呂坤父子等人,也都撰寫了以供童蒙學習的讀物,如:朱熹的《小學》《童蒙須知》,朱熹弟子真德秀的《教子齋規》,王陽明的《訓蒙大意示教劉伯頌等》,呂坤的《小兒語》,方孝孺的《幼儀雜箴》,等等。
啟蒙教材的分類,因其數目眾多,種類繁復,不同學者分類也多有不同。無論是識字教材還是歷史教育教材,抑或詩歌教育類教材,都必然滲透著倫理道德的教育,絕非不講道德的純粹識字教材,這也是傳統啟蒙教育的顯著特點。
“一陣烏鴉噪晚風,諸生齊放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三字經》完翻《鑒略》,《千家詩》畢念《神童》。其中有個聰明者,一目十行讀《大》《中》。”[3](《序》,P2)這首詩描述的讀書場景,正是儒家教化實施過程的真實寫照。啟蒙教育以儒家經典為核心,向童蒙傳授人文知識,進行倫理綱常教化。梁漱溟認為,中國人偏重于孝悌禮義的教育,而西方人則更偏重于自然科學的教育。[4](P340)在傳統啟蒙教育活動中,中國歷來注重對童蒙進行人倫道德的教化,以尚德為啟蒙教育的核心。蒙學教化和傳統文化息息相關,二者緊密相依,因此,人倫道德在我國傳統啟蒙教育中是核心內容。啟蒙教育的核心就是倫理教育,知識的傳授與培養反而在其次,所謂“有余力,則學文”,正是如此。由此可見,我國古代的童蒙教育以幫助幼童養成圣賢人格為教育宗旨,力求培養童蒙知情意行之能力。
與向往來世的宗教學說相比,儒家學說更關注經驗世界的人倫規范,強調社會生活中的倫理和道德。道德至上是我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因此,在我國傳統社會中,人們通常會以道德為標準對人對事進行評價。在傳統社會中,所學即是“學為人”,成為有德之人,正如陸象山所云:“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陸九淵集》卷三十五)啟蒙教育的任務就是讓童蒙知曉生而為人,要盡“人道”,“人道”就是人倫日常,就是切于日用的人倫規范。倫理道德教育是我國傳統社會中童蒙教育的核心,而“明人倫”則是倫理教育中的首要問題。
二、“明人倫”:道德養成的核心內容
“明人倫”是道德教化的目的,也是道德養成的核心。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我國早在夏商周時期就規定,所有學校的教育目的都是為了使學生“明人倫”:“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認為,明人倫就是造就道德的人,圣人憂慮,人如果不受教育就近于禽獸,所以教以人倫以區別之。明人倫一方面是出于人之為人的道德規定性,另一方面則是養成個體對名分的道德自覺。儒家推崇君臣上下的等級秩序,最重名分之說,個人只有做符合自己名分的事,才能顯示其在日常人倫中的地位和意義。“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中庸》)在其位盡力做好本分之事,不必外求諸多與之無關之事,即說明君子所言所行應合乎其名分,籍其名分以行事。
所謂“人倫”,即“人道”,由孟子明確提出,指的是制約和約束人與人之間基本關系的道德規范。人倫指向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孟子對此做出經典的“五倫”解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對“五倫”的內容做出規定,孟子并非第一人。若從思想淵源上考察,孟子“五倫”思想源于《尚書》的“五教”。據《尚書·舜典》記載:“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而所謂“五教”,主要內容就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左傳·文公十八年》)。孟子的“五倫”較之“五教”,其倫理關系范圍顯然是擴大了,除卻家庭關系的三倫(由于家國同構,君臣一倫可看作父子一倫的延伸),朋友一倫則指向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此外,在《禮記·祭統》里則講到十倫,即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這里所謂十倫,其實是十種關系,并非都是人倫綱常。至于對五倫中道德主體的規范要求,儒家經典的闡述稍有不同。《大學》明確指出:“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人交,止于信。”后世視孟子五倫為定論。如《禮記·喪服小紀》所說:“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道之大者也。”《中庸》里把“五倫”稱為“天下之達道”。
“倫重在分別”,別的是“父子、遠近、親疏”,“明人倫”要求人們建立一個分尊卑上下等級的社會秩序。宗法家族是傳統社會中的核心,因此,在我國古代傳統社會的五倫關系中,每一倫的關系都與宗法家族息息相關。差序格局是倫理關系的特征,“倫”即是差等次序。費孝通說:“我們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么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5](P30)“推”之一字是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作用邏輯,通過以“己”為中心,外推“己”與“群”等各種關系,就能夠推己及人、推己至家國天下,做到人同此心。
“五倫”關系的確定,奠定了傳統社會基本的人倫關系。圍繞“五倫”關系,經學大儒董仲舒進行了價值觀的理論建構,提煉出“三綱”之說。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實就是把“五倫”之中的三種倫常關系絕對化,使一方絕對服從于另一方。“三綱”逐漸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統治社會的重要工具,對后世的影響不可謂不大。賀自昭所謂“以常德為準而竭盡片面之愛或片面的義務”,道盡了三綱的本質。在“三倫”即父子關系、君臣關系、夫婦關系中,對倫理雙方都有一定的道德規范要求,在父子倫理關系中,倫理要求即是父慈而子孝;在君臣倫理關系中,道德規范表現為君禮而臣忠;在夫婦倫理關系中,道德規范表現為夫妻和睦相敬如賓。“三倫”確定為三綱之后,原來的父子、君臣和夫婦之間相對溫情的倫理關系蕩然無存,從而成為一種絕對服從的綱常,服從于權威、綱紀及名分。絕對服從強調的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絕對恭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父,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韓非子·忠孝》)“順”是絕對服從的表現,同時也直接與國家興亡息息相關。
在蒙學典籍中,對童蒙進行“明人倫”的教育是首要任務。朱熹經常教育其門人:“后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的基本精神是講明倫、重敬身。朱熹一生教書育人,尤其重視對童蒙的道德教育。在親撰的《小學》內篇中,他列立教、明倫、敬身和稽古四卷,意在明確“立教”的目的在“明倫”,“明倫”之要在“敬身”,稽古則是“摭往行,實前言,使讀者有所興起”。[6](P489)“明倫卷”以五倫為本,分列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對童蒙提出詳細甚至繁瑣的要求。在蒙學典籍中,對童蒙進行人倫教育具體有哪些規范要求,通過如下分析便可窺其一斑。
首先,“明人倫”強調五倫三綱的突出地位。蒙學教育的對象為兒童,因此,傳授知識要注意理論深度,若理論性過強,則不便兒童理解。一般的蒙學典籍只需明白告訴兒童是什么(教之以事),至于為什么(窮究那理)則是大學階段的事情。因此,人倫教育只要兒童明曉何為五倫以及倫常具有的重要意義即可。如《幼學瓊林》卷二之祖孫父子篇,提出:“何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重訂三字經》對“五倫”關系的先后次序作了規定:“五倫者,始夫婦,父子先,君臣后。”《重訂增廣賢文》中強調了五倫的重要:“農工與商賈,皆宜敦五倫。”由“五倫”觀念而生發出的“三綱五常”傳統道德標準在蒙學讀物中也有明確表述。如在《三字經》中:“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父子恩,夫婦從,兄則友,弟則恭,長幼序,友與朋,君則敬,臣則忠。此十義①,人所同。”《千字文》中有“蓋此身發,四大五常”的表述。
蒙學注重在“明人倫”方面教育童蒙,這與傳統社會宗法結構不無關系,同時也是因為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緊密相連。在科舉時代,小學教育服務于科舉考試,為當時社會培養知識精英階層。童蒙階段通過“教之以事”,使兒童“依此規矩去做”,培養出“圣賢坯模”和“圣人素質”,以便“大學去窮究那理”。在“小學”階段只有“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來”[7](P125)。
其次,“明人倫”確立詳細具體的人倫規范。蒙學讀物把人倫道德化為具體的行為規范,詳細具體規定如何孝于親、忠于君、悌于長等。五倫的先后次序,《中庸》的界定是“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婦”,夫婦一倫是人倫之始。然而,在中華傳統倫理體系中,孝無疑居首要地位,“百善孝為先”。若移孝為國家效力,則為忠,因而忠孝并提并占據正統地位。
反復強調五倫的意義,對童蒙的言行舉止做出具體的要求,最終目的在于強化君、父、夫的權威,形成絕對權威。董仲舒論證“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春秋繁露·基義》),把君、父、夫的權威訴諸天。直到宋代儒學時期,這樣的神學論證已經無法使人們信服。基于此,朱熹又提出一個更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他以“天理”來論證“人倫”的合理性。朱熹言“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以廣大高明的“天理”來論證“人倫”有其形而上的理論基礎,從而也就為“人倫”尋找到了外在力量。孟子也曾經提出“易子而教”的思想,維護父親的威嚴,這些思想都是為了強調父親在家庭中的權威性。君、父、夫一旦確定絕對權威,所有不遵從的行為都被歸為不忠不孝的行為。比如“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對臣子有著絕對的處置權力。同樣,父親對子女有著絕對的處置權力,丈夫對妻子也有著絕對的處置權力。
傳統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臣子、子女和婦人的束縛愈加嚴格,最后出現愚忠愚孝也就不足為怪。針對童蒙進行明人倫教育,可以教導童蒙以“禮”處理人際關系,養成對倫常名分的道德自覺。在差等次序的人倫關系中,“三綱”是其核心內容。在童蒙道德養成的過程中,“明人倫”是道德養成的核心與主要目標,強調“人倫”的重要性也是強調童蒙對倫理綱常“天秩天序”的遵從。童蒙時代打下坯璞,為“成人”奠定基礎。但是,過度強調綱常倫理,違背了童蒙的天性,容易扼殺童蒙的才智。
三、“知禮儀”:行為規范的日常訓練
童蒙道德品質的養成,理應從小事開始。對童蒙的基本生活行為進行規范約束,特別是對年齡較小的兒童來說,更應該從細小的事情上做出要求,規范其言行舉止。傳統社會對童蒙的教育非常細致,給出具體詳細的規范,以便落實到童蒙教育中。傳統蒙學教育服務于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對童蒙的道德教育要具備適用性與可操作性,讓童蒙在行為規范中養成對差等次序的遵從。蒙書主要通過儒家倫理道德約束規范童蒙言行,以故事典籍中的人物和行為指導兒童,具備很高的可行性,便于童蒙認識和實踐。
小學階段,童蒙重點學習的內容包括“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如朱熹在《童蒙須知》中要求,“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就提到兒童的舉止,要求童蒙必須做到:“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有缺落。”“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為塵埃雜穢所污。”對童蒙的穿衣提出細致入微的規定,可見生活中其他細節的要求也異常繁瑣。語言舉動方面,需要童蒙做到“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即使自己的兄長父親言行并不合理,也不可直接告知,在當時需要沉默,認為是兄長或者父親一時大意才如此,或者沒有考慮周全所致。灑掃涓潔的目的是培養童蒙養成清潔的行為習慣。朱熹認為,對童蒙而言,應該重點養成學習的習慣,比如讀書,要聲音洪亮,所讀要和書中內容完全一致,不可多字亦不可少字,要反復誦讀,從而朗朗上口,最終熟記在心。讀書方面需要有著良好的行為習慣,另外,還應該養成好的學習方式。朱熹強調,學習有三到,分別是心到、眼到和口到,他表示:“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朱熹還規定童蒙在飲酒、如廁、飲食、夜行等方面的細節。繁瑣的生活細節要求,目的是培養童蒙尊師敬長、愛護器件、用心學習等的良好品質。
明代屠羲英在《童子禮》中詳細列舉了兒童在家中應有的舉止,包括盥櫛、整服、叉手、肅揖、拜起、跪、立、坐等。《弟子職》則規定了學生對待老師應有的行為舉止,比如受業、應客、饌饋、灑掃、執燭、退習等,都要有規矩。各種規定非常嚴格,到了嚴苛的地步,比如塾課方面,相關的典籍包括《家塾常儀》《塾中瑣言》《變通小學義塾章程》等,規定非常繁瑣且嚴密。清代崔學古在《幼訓》一文中,單單針對童蒙的吃飯就做出詳細的要求:“毋先,毋后,毋擇,毋翻,毋鄰(謂取鄰簋食也)。”吃飯不要翻動菜肴,不要挑揀,更不可越過別人去取旁人之餐。吃飯不可把筷子含在口中,不可伸出舌頭接食物,要做到“嚼無聲,咽無疾,啜無流”,吃完要把筷子收好,才可以起身。要求童蒙嚴格按照這些規定去做,同時,師長也可以監督管理其行為。不足的是,如此繁瑣的規定,在現實中操作不易變通,不利于兒童個性的培養。另外,再詳細的要求,也會存在掛一漏萬的現象,無法包羅生活中的各種現象。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左傳·昭公十年》)通過教育能夠讓兒童逐漸了解道德規范,但是,知道并不代表能夠做到,要想在日常生活中履行這些道德規范更是難上加難。《弟子規》告誡童蒙:“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即要求童蒙要通過具體的行動和感悟學習道德規范。《重訂增廣賢文》指出:“學不尚實行,馬牛而襟裾。”認為應該將典籍中的倫理道德落實在具體的行動中,這是成為圣賢之人的必經之路。所以,蒙學教育非常重視對童蒙的禮儀教導,這有利于兒童形成良好的品德舉止。
判斷行為是否合理,需要按照一套完整的標準進行判斷,在封建社會中,這套標準便是儒家強調的“禮”。童蒙時期需要遵守的各種道德規范來自于“禮”。儒家學說中倡導的“禮”含義非常多。結合十三經進行分析,其中有《儀禮》《禮記》和《周禮》均專門對“禮”進行詳細的記載,后人將其視為《三禮》。《儀禮》對各種等級群體的行為做出具體的要求,《周禮》詳細論述政治制度,《禮記》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儀禮》的禮節。《禮記·哀公問》有云:“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在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這里就可以看出“禮”在中國古代儒學中的重要性。孔子提出的“仁”學,其實質也是以禮為實現“仁”的前提。
基于“禮”的規范系統包含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屬于倫理規范系統,目的在于調整人倫,這是宏觀角度的“禮”;第二個層面屬于道德規范系統,目的在于規范人的道德言行,這是微觀角度的“禮”。[8](P267)倫理規范系統來自于等級秩序,強調“親親”和“尊尊”,指出不同等級之間有著尊卑和親疏的關系。道德規范系統重點提升個體的修養道德,要求每個人能夠反省自己,規范自身。一般而言,“禮”具體體現為兩個方面,分別是道德規范和政治制度:一方面,“禮”強調的是個人修養品行;另一方面,“禮”成為治理國家的手段。《禮記·禮運》中的“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提到君主統治的主要手段就是禮,“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禮記·坊記》)。禮能夠被古人看重,主要根源在于,禮是維護等級制度的主要手段。
“禮”對于規范人的言行舉止以及在齊家治國上發揮著關鍵的作用,所以,儒家學者給出詳細的禮制,對人的思想言行等進行規范約束。孔子將畢生的精力都放在“克己復禮”上,希望整個社會遵守周禮,發揮周禮的作用。孔子認為禮是形式,禮的內容源自于仁,所以他強調:“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將禮和道德有機結合在一起,禮才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荀子也對“禮”進行了詳細介紹,他通過《禮論》這一篇章,全面闡述在治理國家方面“禮”的功能。“禮”的功能體現為兩種,分別是“別”和“養”。封建社會區分社會中人的地位以及貴賤等級,即是“別”。“曷為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在“別”的基礎之上,“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荀子·禮論》),又提出“養”的說法,“養”即是對人的物質欲求的滿足。
針對童蒙反復進行禮儀規范教育與訓練,不僅可以促使童蒙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通過將典籍中的道德規范內化成童蒙的言行模式,還可以讓童蒙初步了解親屬尊卑等級制度,避免日后行為僭越等現象的發生,為此后的人格養成發展做好準備。童蒙時期形成的習慣會對其一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陶行知認為:“人格教育,端賴六歲以前之培養。凡人生態度、習慣、傾向,皆可在幼稚時代立一適當基礎。”[9](P104)這也正是傳統社會對童蒙進行禮儀規范教育的意義所在。
四、結語
以蒙書為載體的傳統啟蒙教育,把社會主流的倫理觀、道德觀、歷史觀及價值觀,通過道德教化的途徑傳遞出來,把儒家思想的微言大義化為童蒙易知的揖讓言辭,密切聯系兒童的生活實際,比較通俗且易知易行。很多經典的蒙學讀本(如《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等),薈萃了前人及那個時代的經典文化,構成傳統蒙學相當完整的知識體系、思想體系、價值體系和藝術體系。通過自上而下的教化,傳統啟蒙教育完成了從上層精英文化到中下層倫理生活化的轉換,也實現了上層意識形態到民眾價值觀的傳達。傳統啟蒙教育中的道德養成,注重文道結合、因材施教、教學相長等教育思想和教學原則,教材編寫符合兒童心理特點,讀起來朗朗上口,童蒙可以反復吟誦。我們對未成年人道德品質的養成教育,在傳統啟蒙教育中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論述與表達。魯迅曾說:“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下。”[10](P255)我們對傳統文化進行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可以從中借鑒對未成年人進行道德養成教育的途徑及方法。
注釋:
①“十義”是指儒家宣揚的十種倫理道德,《禮記·禮運》說:“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