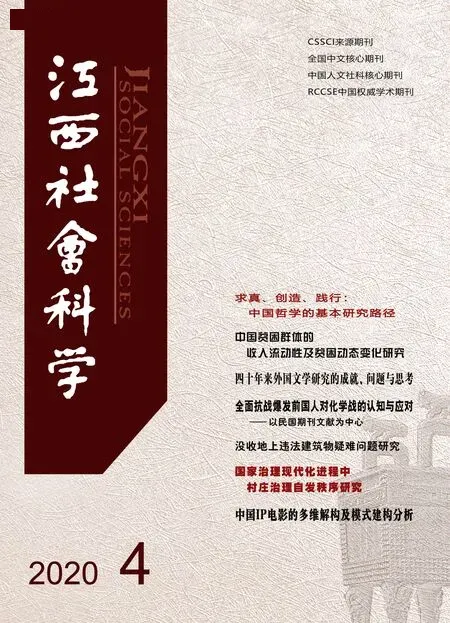商鞅、管仲軍事思想的法家淵源與異同
■方蘊翔
《商君書》與《管子》作為商鞅學派和齊法家的言論思想輯錄,反映了以商鞅與管仲為旗幟的兩種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淵源于刑兵,古有刑始于兵、兵刑一體的說法,兩種法家都有吸收兵家思想轉化為自身資源的方面,商、管之法都有其功利主義、強調軍事、以軍領政、賞罰馭民的一面,但又在戰爭觀、戰略戰術、對農工商的態度等問題上有所分歧。管法或者說齊法家重視德義,更加重視戰略戰術的研究,對戰爭取謹慎保守的態度。通過商、管軍事思想的比較可見法家、兵家的同源性,但也看出法家、兵家中因其地域文化差異展現的思想差別性,秦晉法家在吸收兵家的同時將其擴大為社會政治思想,管法則在吸收兵家思想的同時也以其他諸子思想平衡兵家思想的擴展。
管仲和商鞅是春秋戰國時期最重要的改革家和治國理政者。管仲輔佐齊桓公改革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得齊國成為春秋首霸,為齊國奠定了立于大國之林的基礎。商鞅由魏入秦,輔佐秦孝公變法,為秦國帶來六國律法,以秦律塑造秦國,為秦國從一個弱國變成強國而后統一天下做出了巨大貢獻。管仲、商鞅作為國家出色的治者和改革家,都認識到治國與治軍的同構性,認識到刑兵的一體性,法治化和軍事化的一體性,管子、商鞅作為廣義上的法家也是兵家,蒙文通就認為,法家不止于法治學說,更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但同時,發展的廣義法家又走了不同的路線,在吸收兵學、兵家的同時,在社會政治思想上又有單一化和多元化、排他性和包容性的差異與殊途。商、管法家的軍事思想展現出唯軍事主義與以軍事為中心兼重其他思想的兩種分別。
一、法家的兵家淵源
以商、管為代表的法家與兵家思想一樣,均以治國理政的實踐為旨歸,具有務實、功利、講求應用的特點。從上古職官制度、兵法兩家與諸子關系考察可以見得,兵法兩家思想上具有的源流關系。頻仍的戰爭、社會變法的運動與社會的轉型創生了法家思想。兵家與法家可以說是一個思想系統與脈絡的不同表達。
(一)刑始于兵
在諸子思想的發生與起源上,《漢書·藝文志》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王官論”。《漢書》雖然仍將《管子》一書歸為道家學說,但韓非已早有商、管之學的并稱,其后《隋書·經籍志》明確定《管子》一書為法家之首。法家學說力主進行變革、以法治國。法家二字最早出現于《孟子》,至司馬談才將法家作為主要學術流派的一家。“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1](卷三十《藝文志》,P1736)理官古稱隨時代而變,最古稱士,夏時稱大理,周稱大司寇。古代理官主管司法實踐,理官因主管司法、執掌刑律,而后下移社會,逐漸影響而形成了法家思想。從兵家來說:“兵家者流,蓋出于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1](卷三十《藝文志》,P1762)司馬戰時管理軍隊,平時則有除了軍事之外的職守。“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2](P1098)大司馬除軍事之外,還承擔著維護法治的作用。征伐是軍事手段,依據的仍是法律。《漢書·刑法志》更是大量篇幅談到軍事,這都說明古代軍事與法刑的一體兩面性,這即所謂“大刑用甲兵”。
《國語》與《漢書·刑法志》都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的說法,用兵征伐與法律制裁本為一體。《尚書·呂刑》稱:“惟始作亂,延及平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通典》則稱:“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黃帝的用兵就是用刑,軍事首領也同時作為執法官吏。王充指出:“兵與刑,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眾禁邪,其實一也。”[3](PP540)對外的軍事征伐就是刑法的最高形式,刑法則是在國內的軍事征伐,是軍事征伐的國內使用和最低形式。
從刑始于兵、王官下移角度看,兵法兩家有其親緣關系。雖然各家思想不能完全與王官一一對應,但確實不能簡單否定法家與刑獄官吏、兵家與軍事官長的關系。從古代兵刑一體出發,也可見出法家思想不脫離古代兵學。兵家、法家的親緣關系也解釋了為何法家、兵家思想會有相近的價值觀和致思趨向,兩者都指向功利實用和務實理性。
(二)功利主義致思趨向
基于春秋戰國頻仍的戰爭實踐而產生的兵家兵學思想,在思想脈絡上影響后來諸多學派。李澤厚就將孫、老、韓合說,認為兵家、道家、法家都是重視客觀、理性分析的思想流派,兵家冷靜分析戰爭,道家從客觀角度對待歷史,都是擺脫了儒家從感情角度去對待社會歷史問題。[4](P91)李澤厚認為韓非進一步發展了孫、老,即兵道兩家的客觀理性現實的態度,走向極端功利主義。從思想脈絡的繼承和發展來看,法家的思路與思維也是與兵家一脈相承的。
從兵家兼法家、軍事而論及政治的先秦典籍如《吳子》《尉繚子》等軍事著作來看,同樣兼治政治,吳起是典型的改革變法家和法家先驅,認為耕戰與法治、政治與軍事是辯證相關的。吳起、商鞅的思想都是主張改革國家、厲行法治以強國,目的就是在戰場上打敗敵國。所以,政治與軍事、法治與兵家沒有一個截然可分的界限。從《孫子》到后世兵家,兵家學說由兵學逐漸擴展到兵學以外的法治、經濟思想方面。軍事本來就是政治的延續,兵家思想擴展到單純軍事思想以外,是邏輯發展的自然規律。法家形成系統的理論也是兵家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軍事戰爭擴大化、社會結構變化與法家思想產生
長期頻仍的戰爭與社會結構和社會思潮的轉型,與法家的產生是一種互動結構。春秋戰國時期,戰爭越來越頻繁化與擴大化,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迫使國家必須進行更大規模的征兵,國野分別下的氏族貴族軍隊制度被全面的編戶齊民催民耕戰的制度所代替。戰爭迫使社會結構發生變化,貴族平民分化的社會結構滿足不了統一的軍事活動,血緣關系與世卿世祿制度被法律關系與賞功罰過制度代替。兵學的功利主義思想也被法家思想所繼承,以禮為固的舊戰爭被兵以詐立的新戰爭所取代,兵學不再將傳統價值觀奉為圭臬,反而將成敗利益視為標準,法家延伸了這種思潮。法家思想順應了時代思潮,是一種應時救弊,因應社會結構變化和軍事戰爭擴大化的新思潮,它發展了兵學思想,順應了時代從德禮轉向功利、從王道轉向霸道的時代趨勢。
二、商鞅、管仲法家思想的總體差異
商、管分別作為秦晉法家和齊法家思想的代表,體現不同地域文化的思想。任繼愈認為,三晉法家因出產于三晉,對宗周禮法變革性強。魯國產生的儒家則對宗周體系保守繼承,齊國出產的齊法家則介乎兩者之間,并不對宗周文化進行盡廢故常的變革,也不完全保守繼承宗周文化,而是既繼承又改革。不同的文化地域產生不同的法家思想,也產生不同的法家軍事思想體系。
(一)齊文化、秦晉文化的差異
齊國文化重商、重利、尚功,同時講究民本,齊國文化塑造了齊法家的品格,《管子》為代表的齊法家在思想上表現出與商、韓代表的秦晉法家的差異,都有其文化根源。首先,齊文化注重商業。在春秋戰國時期以重農為主的文化氛圍中,齊國卻將工商業放置在和農業同樣重要的地位。《管子》大量內容都與治理國家經濟有關,就可見出這點。鹽鐵資源豐富、瀕臨海河水路,給齊國提供了從事商業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齊國的統治者中如姜太公與管子都有從事商業的經歷。姜太公“屠牛于朝歌,賣飲于孟津”[5](P1360)。管仲、鮑叔牙同賈南陽,太公“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5](P1362),管仲繼續“通貨積財,富國強兵”的事業。工商之發達使得齊國法家思想較為兼容開放,而少農業國的守舊偏狹。其次,齊國治理尊賢智而賞有功,《管子》指出:“主所以為功者,富強也。”[6](P180)齊國在注重治理功績的同時,也使齊文化尚利逐利。再次,齊文化注重民本。《六韜》即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7](P15)主上應將富國與富民結合,不能獨擅財富。其后管仲、晏嬰治理齊國也以富民愛民為執政目標。
三晉與秦合稱秦晉,三晉文化為發端,成熟結果在秦,故有秦晉文化之稱。三晉之地為叔虞封地,所奉政策即“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晉國雜處戎狄之間,不斷與戎狄戰爭,也不斷通過通婚和聯盟融合。晉國將夏的習慣法與戎狄之法結合而成晉法,以治理三晉,形成三晉無親、尚利、拒斥禮義的特點。首先,不同于宗周的親親尊尊的文化,三晉吸收戎狄文化,不主張以強干弱枝模式的強大宗室治理國家,奉行“無親”治國,最終形成秦晉無親的局面。其次,秦晉文化好利尚功,受戎狄人影響,秦晉文化隨利而走,不以宗周道德為準繩,而以功勞作為用人準則,主張“無功庸者,不敢高位”。重視戰功與成績的功利思想在秦國法家商鞅、韓非的思想中更是達到頂峰。再次,晉秦皆與戎狄雜處,多奉戎狄之教,所以禮義淡薄。晉秦不守禮、不奉禮的行為很多。
齊文化與秦晉文化同樣重視功利也崇尚法度,但齊文化與秦晉文化仍有很多差異。瀕臨大海的齊國偏向海洋文化,在東夷濱海民族特點上吸收宗周的農耕特點,三晉則是內陸封閉的農耕文化,在此基礎上吸收戎狄文化,所以傾向閉塞,戎狄文化和農耕文化結合也使專制程度較高。齊文化中宗周因素較多,追求民本,秦晉文化則拒斥德禮,更具國家專制特色。齊文化和秦晉文化導致兩種法家致思路線的相通,又造成兩套法家思想的差異。
(二)齊法家和秦晉法家思想的差異
齊法家和秦晉法家思想上都以尊崇法治而對舊有制度與思想傳統進行改變作為思想中心,但同時,秦晉法家和齊法家對法治和制度思想的改造又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齊法家主張尊君愛民的同時,提出“令尊于君”,認為君主也必須在法令制度之下,對君主權力進行限制;秦晉法家則認為君主是法治的前提,只有鞏固君主權力才能保障法令推行;兩者對法律與君主的關系上表現為尊君又抑君與盲目尊君的差別。
其次,齊法家主張德法并重,《管子·牧民》提出國之四維的觀念,認為在法治之外注重禮義廉恥的教化作用,通過教訓成俗而使得刑法能夠減省,而不是專任暴力與法治;秦晉法家則認為人性好利無害不可改變,治理國家只能以法而不能以德,專任暴力刑法才能抑制人性之惡。同時,齊法家主張寬刑省法,認為誅罰過重會導致暴亂,并不主張過度提倡的刑罰的威力;秦晉法家則較為迷信暴力,認為通過以刑去刑,就能使得作惡者不敢再犯。
最后,齊法家不抑制工商,正如前述所交代,齊文化視商業為財富來源之一,并不對其做過多抑制;秦晉法家則認為從事商業之人乃奸民、六虱,主張對其進行抑制而使農業得到重視。同時,齊法家講術,認其為治國之術,即技術方面的思考,認為治國理政不可沒有一些循名責實、監察百官的技術;秦晉法家則在君權神圣角度,提出的術更多是陰謀的潛御群臣之術。齊法家在文化政策上走向包容開放,主張對各種思想進行兼收并蓄的吸收和消化,最終形成了博大多元的思想文化傳統;秦晉法家則拒斥各家學術思想,走向文化單一與專制。
三、商、管軍事思想之同
商、管法家同樣淵源于兵家,與兵家思想千絲萬縷,商鞅、管仲皆是政治家兼軍事家的代表,從學派來說也是所謂法家兼兵家的思想代表。商、管軍事思想從相通性來看,商、管皆重視軍事,認為軍事是國家興衰存亡的關鍵;同時,商、管都將法術、賞罰當作組織民眾進行戰爭的重要因素。
(一)重視軍事戰爭
《商君書》主張“以戰去戰”,戰爭是天下大爭時代各國都努力從事的,“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8](P81)。戰爭關系國家危亡,戰勝者“名尊地廣以至于王”[8](P150),戰敗者則是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要適應時代,要稱王稱霸,都必須從事戰爭,所以商君書反對取消軍事、取消戰爭的觀點和論調。《商君書》認為,只有不斷進行武備和戰爭,才能將有害的東西疏散他國,一旦放棄軍事和戰爭準備,國家就會陷入安逸的氛圍,最終國家會削弱。《商君書》以戰去戰和以戰強國是其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
《管子》也認為軍事與戰爭有其合理性。君主的尊卑、國家的安危都由軍事戰爭的成敗決定。打擊暴亂和維護國家和平也必然依賴軍事和戰爭。戰爭雖然不夠道德,但為了安國定邦、輔王成霸,戰爭與軍事準備不可或缺;而且即使道德如三皇五帝,為了正義與王道的推行也必須慎重考慮軍事與戰爭問題。如果主上不務兵而廢兵,實行所謂“寢兵之說”與“兼愛之說”,無異于施行亡國滅種的理論。
從相同性一面看,《商君書》與《管子》無疑是重視戰爭的合理性與正視軍事武備的。《商君書》主張的以戰止戰和以戰稱霸以及《管子》主張的“積務于兵”都是對廢兵、寢兵說的否定,是一種積極務實的戰爭與軍事準備學說。商管之學作為法家之學,表達共通的淵源于兵又凝聚于治的軍事家兼政治家思想特色,兩者都將軍事看作治國理政的關鍵要素,予以相當程度的重視。
(二)軍事戰爭的成功有賴于信賞必罰
《商君書》的治軍理論以嚴刑峻法和以法治軍為核心。《商君書》認為,軍事的勝利由于有嚴明的法治,“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8](P54)。同時,利用兵民欲利避害之性,《商君書》認為可以通過重刑厚賞催民耕戰。“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則民致死。”[8](P70)《商君書》指出賞罰須有具體標準,即“壹”。通過統一刑法的度量和賞賜的統一標準,可以造成民眾“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戰”的風氣。
《管子》也將信賞必罰當作治軍主要準則。《管子》指出,如果不能做到信賞必罰,國家的戰斗力就會渙散。“賞罰不信,五年而破。”賞罰如果不分明,民眾就會貪生,勇士也不會努力。因此,《管子》也將以法治軍當作唯一辦法。《管子》也和《商君書》一樣指出,因為人的情性是趨利避害,“見利莫能勿就”,所以就可以以重賞激勵;“見害莫能勿避”,所以可以嚴刑酷法使其勇敢向前。無論親疏遠近,進行按照法律度量的統一的獎懲,即:“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6](P53)這樣的一體獎懲就能讓作戰的人為之拼命戰斗,有功勞的心安、無功勞的沒有怨懟。
商、管在依法治軍、信賞必罰的思考上也是一致的,商、管法家都主張在軍隊中實現統一的功過獎懲制度,以使有功者能勸進、無功者能被屏退。只有依法治軍,以法術刑罰治理軍隊才能真正完成民眾與軍士的組織,做到強兵富民。商、管之學表達了法家之學以法治軍的思想特色。
(三)軍事戰爭的成功需注重實力
《商君書》認為,軍事戰爭要取得成功,法治修明之外還需加強國家的經濟實力。戰爭勝利常常由經濟實力更強的一方獲得,軍事勝利的關鍵在于富強:“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8](P105)富強之要在于施行農戰。只有民眾投入農業和戰爭,并將之結合,才能治理好國家。
國家只要將農業和戰爭結合,就能獲得富強。《管子》也同時指出,只有增強經濟實力才能奪取戰爭的勝利。國家富裕就能做到“富勝貧”,反之,國貧就會導致用度不足、兵士羸弱,最后就會造成戰敗國破。甲兵財貨的根本則出于田宅,所以《管子》也將糧食生產當作國家的命脈和軍事成敗的關鍵因素。
商、管法家都將國家實力當作軍事成敗的關鍵要素,國家實力的核心內容則又是農業生產。只有將農戰結合,使軍事建基于經濟,才能保證軍事戰爭的無往不利。商、管法家表現出法家之學強兵建基于富國的特色。
四、商、管軍事思想之異
商、管法家在重視戰爭、注重實力、重視法治方面表現出趨同性,也在主張慎戰還是張揚戰爭,主張德義王道規約還是徒依霸道,主張對戰略戰術進行更多研究還是更注重士氣等非戰略戰術的因素上表現出諸多差異,這也是源于兵家之外的統一性,又有文化思想特異性的展現。
(一)對戰略、戰術研究程度不同
相比于《管子》,《商君書》薄于作戰指導思想和軍事理論。《商君書》在提倡謹慎作戰、明察敵情之外,更多地強調軍士的士氣和勇敢對戰爭的作用。《商君書·立本》提出,“恃其眾者”“恃其備飾者”“恃其譽目者”都不足恃,人數眾多、精巧裝備、顯明名聲都不如勇力和士氣。《管子》書則詳盡論述其戰爭指導思想。
第一,《管子》書主張遍知天下。《管子》一書提出作戰必須“遍知天下”,遍知天下指的是必須了解敵我雙方各方面的狀況,遍知須知形、知能、知意,必須對敵我雙方具備的實力、敵我雙方將帥的指揮才能、敵我雙方的作戰意圖全面了解。遍知之中還包含早知思想,如果不能做到前瞻性和時效性,情報消息便會失去其重要意義。遍知天下便是注重信息情報收集的全面性和時效性的重要總結。
第二,《管子》主張靈活用兵、發乎不意。《管子》一書認為,作戰不應僵化守舊,而應該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進行戰爭模式的靈活選擇。主動變化、變化萬端才是用兵作戰的原則。
第三,《管子》書主張避實擊虛、釋實而攻虛。《管子》主張作戰應該避開敵人的優勢處,攻擊敵人的薄弱環節,這樣就能做到事半功倍,反之,“攻堅則瑕者堅”,攻擊敵人的堅固之處,弱小薄弱也轉化成堅不可摧。
第四,《管子》主張進行戰機的把握和計策的籌劃,計比先定,明于機數。必須對雙方實力進行籌算計劃,比較剛柔、輕重、大小、實虛、遠近、多少。《管子》書稱:“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比先定于內,然后兵出乎境。”[6](P54)籌算先定,就能把握戰機:“圣人能輔時,不能違時。”[6](P237)把握時機戰機來用兵就能做到功得而無害。
商、管法家對于戰爭指導思想方面研究的差別,是齊法家、秦晉法家在其文化地域差異基礎上形成的,秦晉法家四戰之地重勇力,齊文化機巧則更尚智謀。商管在此點上的差異體現了兩種法家在智勇之辨上的取舍。
(二)對德義王道的態度不同
《商君書》拒斥禮義,將戰爭當作克服國家產生“六虱”毒害的方法。《商君書》認為,仁義、禮樂、詩書等皆為毒害,國家之所以要堅持主動積極戰爭,一方面是爭霸必須以戰爭軍事為基礎,另一方面是國家必須長期堅持戰爭才能讓國內安逸茍且的風氣弱化。《商君書》 將德義王道視為已經過時的治理方式,只會使得國家削弱,而霸道戰爭才是《商君書》堅持的要義。
《管子》則認為,戰爭需要有德義規約,將戰爭區分為義兵與非義之兵。《管子》指出,貪于地就是所謂非義之兵,用兵打仗必須要以“案強助弱”“禁暴止貪”為旨歸,立于仁義才是所謂立于不敗之地。如果兢于兵不兢于德,軍事力量的強大反而會傷兵、殘兵。《管子》提出:“故軍之敗也,生于不義。”[6](P143)《管子》軍事戰爭思想將道德問題與積極軍事選擇相結合,是古代思想家對戰爭軍事思想上的深化和推進。
商、管法家因為對德義的態度不同,在軍事領域也有不同表現。《商君書》將軍事當作對消除德義之毒的手段,而《管子》則以德義規范軍事戰爭,認為軍事戰爭不能無限擴大,仍需以德義作為規約。
(三)慎戰與唯戰的態度不同
《商君書》把國家的強大、族群的危亡都建基于軍事戰爭,戰爭的成敗決定了能否“覆人之軍”與“凌人之城”,失敗者則面對著被屠殺和滅族的危險。《商君書》對時局與人性的估計都比較悲觀,造成其唯戰和夸大戰爭功能的傾向。在對軍事戰爭積極性主張的同時,排斥限制戰爭的其他因素,將其他一切因素歸結到戰爭的中心點之上。
《管子》則在積極面對軍事戰爭的同時,主張對戰爭持慎重對待的態度。《管子》在肯定戰爭的合理性的同時,也認為輕易地進行軍事戰爭是危險的:“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6](P145)一旦放任戰爭的破壞性作用,就會影響整個國家的利益。霸王之道以強兵為基礎,但時時與危亡相鄰,所以“至善不戰”,戰爭需積極準備卻不可經常性和隨意性發動。《管子》書有明顯的淵源于齊國兵家慎戰節兵的思想特色。
《商君書》與《管子》都認為軍事戰爭不可廢棄,應當重視,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商君書》對戰爭的態度更加求積極主動,有鼓吹戰爭將戰爭視為神物的傾向,《管子》比之則更加強調積極對待的同時也需注意戰爭的危害性,對戰爭軍事取慎重態度。
五、結語
商、管法家源于兵家,兵、法二家都有功利主義的致思趨向,軍事戰爭的擴大化,打破了國野的分界,將過去古禮主導的政治生活方式轉變為以法調控,法家思想應運而生。同時,法家因其地域化差異有齊法家、秦晉法家的分野。齊文化與秦晉文化都尚利重功,但同時,齊文化更加包容,能容納德禮體系,秦晉文化則寡禮無儒,更為封閉。齊文化與秦晉文化的差異導致齊法家和秦晉法家的分流。齊法家區別于秦晉法家:法令尊于君主,務法同時務德,務法同時主張寬省,農工商并重。齊法家比秦晉法家多元且開放。在同一思想淵源與地域文化差異基礎上,商、管法家軍事思想有同有異。商、管都認為兵不可廢需重視軍事,同時軍事戰爭需依法治軍、信賞必罰,商、管也同樣認為軍事戰爭建基于國家財富實力基礎上。
同時,商、管軍事思想也有若干差異。《商君書》有弱于研究戰爭戰略指導思想而過分強調勇力的特點,表現為勇勝于智;《管子》則強調全面研究作戰指導思想,表現為機巧和尚智。《商君書》視禮義為六虱,認為靠戰爭能去除其毒害;《管子》則認為戰爭的目的是恢復德義王道,軍事戰爭必須接受德義規約。《商君書》有夸大戰爭合理性的一面,沒有注意戰爭的危害性;《管子》則把積極準備軍事戰爭和謹慎發動戰爭相結合,既注意到戰爭的積極性、合理性,也將戰爭的危害性考慮充分。商管軍事思想的相同與相左反映了兵法同源、兵法一體的同時,因地域文化的差異齊法家的軍事思想更加多元與復合,而秦晉法家的軍事思想則更像是兵家的在治國方面的延伸,更多地表現了兵法的一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