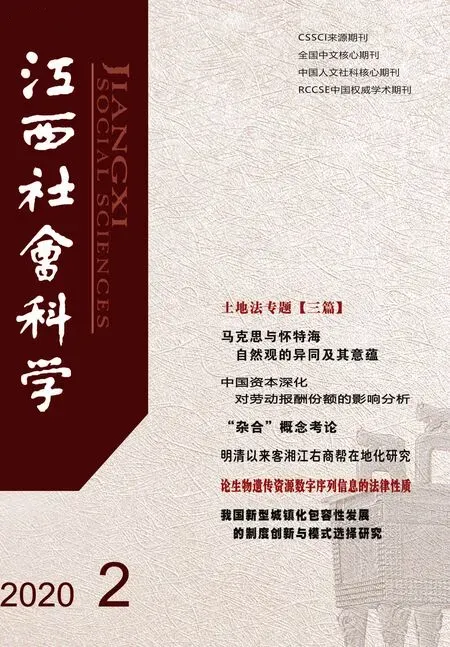見證之“我”與蘇聯成長小說的教育意義
一般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蘇聯官方文學中,全知視角占主導地位,且承擔教育功能,而內視角一向是被排擠的。高爾基《我的大學》及在其影響下哈薩克斯坦蘇聯時期作家穆坎諾夫所創作的自傳體小說《生活學堂》均采用第一人稱敘事。兩部著作中承擔教育功能的是內視角,以見證之“我”為典型,對文本教育意義的闡發產生了重要影響。見證之“我”與蘇聯成長小說教育意義關系的探索,對該時期文本第一人稱敘事乃至整個蘇聯文學的敘事研究至關重要。
一、引言
一般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蘇聯文學①中,全知視角②承擔教育功能,內視角一向是被排擠的。如:石南征指出,“五六十年代以前,全知視點在蘇聯小說中居統治地位,而內視點,多以一種片斷、輔助方式存在”[1](P31),且常超出主人公視野、認知局限,通過直接“犯規”的方式“引入全知視點”“超量采用人物話語形式”“利用敘述者的信息優勢”向全知視角傾斜,文本的教育功能引人注目,革拉特坷夫的自傳體三部曲便是典型[2](P139);王麗丹同樣認為,在“解凍”以前的蘇聯文學中,全知的敘述者“經常跳到前臺,對主人公指手畫腳”,內視角只不過是“散兵游勇”,散亂不堪,被全知視角淹沒,連本該采用第一人稱的自傳體小說《恰巴耶夫》也采用了第三人稱,服務教育旨趣便是主因之一;[3](P44-46)也有研究發現,在俄蘇傳統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中,無所不知的敘事者是視角的承擔者,其原因是蘇聯文學看重文學的教育作用;[4](P12-13)俄羅斯學者同樣指出,斯大林時期的官方文學中,全知視角占主導[5](P130),甚至馬卡連科《教育詩》中的“我”也是專斷的“作者-敘事者”的一部分,以具有鼓動性的角色參與事件,“我”毫無個性可言[5](P85)。這一情況在“解凍”之后開始有所變化,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文學中全知敘事模式退化的趨勢已十分明顯,如“小型史詩大多采用內聚焦型視角,視角的承擔者往往是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多數情況下就是作品的主人公”[6](P36),“也可以有以人物視角敘述,內心獨白,意識流動,第一人稱敘述等方式”[7](P19)。相應地,蘇聯學界則于1982—1985年集中討論了世界文學中“主觀史詩”到底是作者或是人物之“主觀”的問題,扎東斯基、赫拉普欽科、阿納斯塔西耶夫等人一致認為,全知視角的退化及人物之主觀眼光的登場才是文學發展大勢。[8](P2-9)
由上述可知,一方面,第一人稱敘事之“我”在“解凍”之前的文學中仍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文本較倚重教育功能,使得“我”被全知視角淹沒、“冷凍”,上述學者多論及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如何被“解凍”,又如何在與全知視角的博弈中獲得“解放”,頗有見地;另一方面,上述學者研究均以歐洲經典敘事學巨擘熱奈特所倡的視角分類為依據,執著于其所提的“內聚焦(內視化/內視點/內視角)”,而據申丹的敘事視角分類③,第一人稱分屬內視角和第一人稱外視角,上述研究多立足于主人公的內視角,研究點集中,挖掘深入。但問題在于,“第一人稱敘事幾乎可以容納所有的視點類型”[1](P34),那么,被“排擠”“滲透”的內視角能否代表“解凍”之前蘇聯文學第一人稱敘事的全部狀態?內視角內部又是否一成不變?與文本的教育旨歸是否有關聯?是否還存在外視角(包括回顧性的眼光及處于邊緣的見證人的眼光)?內、外視角與“我”的形象又有何關系?若忽略這五個問題,則有可能忽視內視角內部的演進及內、外視角之間的轉換,進而陷入孤立研究各個視角的境地,也極易讓人誤將蘇聯文學文本的教育意義視為全知視角的專屬功能,或誤以為蘇聯文學文本的第一人稱敘事的內視角不具備教育功能。這樣,既有礙于廓清蘇聯文學第一人稱敘事的全貌,也不利于經典文本的解讀。
有趣的是,盡管“解凍”之前貫注于教育旨歸的全知敘事大潮涌動,但以高爾基《我的大學》、馬卡連科《教育詩》等為代表的第一人稱敘事自傳體小說仍成為蘇聯文學的經典力作。其中,前者與《童年》《在人間》一道又深刻影響著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尤其是現代書面文學剛剛起步的中亞五國文學的發展,如哈薩克斯坦蘇聯時期(下文簡稱“哈蘇”④)作家穆西雷波夫是哈現代文學史上用第一人稱敘事書寫長篇小說之第一人,深受高爾基三部曲的影響,[9](P190)其同代作家穆坎諾夫也“不止一次強調,包羅萬象的自傳體作品《生活學堂》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奠基人高爾基的三部曲等自傳性作品為寫作的參照”[10](P5),“在復雜的矛盾與現實的復雜聯系之中,與人民的歷史的聯系之中”審視自己的成長歷程[11](P15),深得蘇聯官方文學主要創作手法的精髓,其蘇聯文學意義上的教育功能無可置疑。另外,據巴赫金對成長小說的分類,類似于《我的大學》《生活學堂》的自傳作品均屬于成長小說的第三類,也即“傳記(自傳)型小說”[12](P231),“成長著的人物形象”[12](P227)又賦予二者成長小說意義上的教育功能。上述雙重教育功能與第一人稱敘事在蘇聯傳記型成長小說內的交匯也讓上述“五問”之邏輯愈加清晰。
筆者比讀《我的大學》《生活學堂》二作,辨析兩者中“我”的見證眼光,旨在探討三個問題:“我”見證如何成為可能?見證之“我”如何成長?見證之“我”與教育意義何干?以期為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蘇聯成長小說第一人稱敘事乃至整個蘇聯文學的敘事研究拋磚引玉。
二、“我”見證如何成為可能?
石南征認為,全知視點文本中的行為可概括為兩類:“敘述者的敘述性意義上的行為(‘說’和‘看’)與人物在故事中的行為”,而自傳性敘事文本則有第三種行為——回憶。[1](P37)“我”既要“說”“看”,還要“回憶”,身兼多角。在此情況下,“我”“見證”如何成為可能?
要知道,當前學界談的“見證”,大多是文本內獨立“見證人”之“見證”。有的學者立足“故事”來審視“見證人”,如布魯克斯和沃倫解釋“視角”一詞時便稱:“故事可用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講述,講故事的人也許僅僅是旁觀者(observer),也許較多地參與了故事。”[13](P344-335)布斯在論及亨利·詹姆斯的敘事技巧時也認為,作者總為自己找些“觀察者(observer)”,“因為這些觀察者非常敏感,能夠把故事‘反映’給讀者。故事正是在發生‘在他們的意識之中’;隨著他們經歷這個故事,讀者也就經歷了這個故事”,“觀察者”一般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稱。[14](P351)J.希利斯·米勒的看法則印證了布斯的觀點,他指出,亨利·詹姆斯的《未成熟的少年時代》中“只有被一位敏銳的旁觀者(onlooker)看到和聽到的東西才能‘展現’出來,公開在世人面前”[15](P38),也即是說,作品實際上是一個敏銳的旁觀者看到和聽到且被“公開”的信息的一部分。在此文中,米勒還用“spectator”“observer”“witness”三詞來表示這一“旁觀者”。還有學者基于“事件”來描述“見證者”,如斯坦澤爾指出:“在《名利場》的蓬佩尼克爾片段中,我們碰到這樣的敘述者之‘我’,其從頭到尾都保持著同樣的角色,也即,敘事者作為系列事件現場的目擊者(eyewitness)、觀察者(observer),作為主人公的同輩人,作為他的傳記作者(biographer)。這種敘述者之‘我’出現于很多長篇小說和故事中。”[16](P205)但其在視角分類之時卻又根據見證者之“我”在故事內的見證位置,將弗里德曼所提的“見證人(witness)”的見證眼光細化成處于故事中心的“內視角”和處于故事邊緣的“外視角”。[17](P60)普林斯《敘述學詞典》則收錄了弗里德曼的“‘I’ as witness(作為旁觀者的‘我’)”,其界定立足于“事件”:“提供的信息限于被講述的情境與事件中作為次要人物的敘述者的感知、情感和思想。由于作為旁觀者的‘我’不是主人公PROTAGONIST,所以其行動是從外面而不是從中心被觀察。”[18](P96)顯然,不論是基于“故事”,還是立足“事件”,上述界定都強調“觀察者”“旁觀者”“見證人”(“spectator”“observer”“witness”“onlooker”“eyewitness”)單獨承擔“見證”行為。
但在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文本內,一般很難如同《黑暗中心》《吉姆老爺》《了不起的蓋茨比》《遠大前程》等作品那樣出現相對純粹、專一的見證人角色,見證之“我”只能從身兼多角的主人公之“我”中暫時脫身,雖不可能全身而退,但從某些事件或情境中局部脫離而成為該事件或情境甚至所生活時代的局部的見證者、觀照者是有可能的,這主要因為:
其一,自傳性敘事的敘事構造所致。“事件”“故事”“情節”是敘事文本的三大主要構造要素。不論是俄國形式主義的“故事”“情節”兩分,還是法國結構主義的“故事”“話語”兩分,其“故事”均“指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因果關系排列的事件”[19](P14),而“情節乃是虛擬的一連串事件構成的鏈條”[20](P164)。后來熱奈特雖然提出了“故事”“敘述話語”“敘述行為”三分,但“故事”仍是“被敘述的事件”[19](P16)。足見“事件”在敘事構造中之基礎性地位。論及情節的整一性,亞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人以為只要主人公是一個,情節就有整一性,其實不然;因為許多事件——數不清的事件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其中有一些是不能并成一樁事件的。”[21](P27)因此需要對事件進行“安排”以維護情節的統一性。對于事件系列冗長的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作品而言,這顯得尤為重要。雖說最終進入自傳性敘事文本的事件都經過精挑細選,但每個事件在情節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客觀上卻不能均一等同,外加上自傳性敘事的客觀性和藝術性考量,“我”從某些事件中脫離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二,自傳性敘事的客觀性要求使然。在自傳性敘事中,“我”雖承接了敘事和人物功能,但為保證敘事的客觀真實性,“我”會在某些事件中處于中心地位,與事件人物也有諸多交集,但卻不干預該事件的進程,有時甚至在事后才得知當事人的姓名,而“我”處于事件邊緣,通過旁聽或打聽方式確證所述事件發生的情況也不少,這都使得自傳性敘事中“我”獲得“見證”功能成為可能。
其三,自傳性敘事的藝術性和普遍性要求所致。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言:“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21](P28)歷史學家與詩人的差別在于“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描述個別的事”。[21](P29)作為文學作品的自傳性敘事,雖然以傳主之“我”的真實生平事跡為基礎,但往往會凸顯敘事的藝術性和普遍性。自傳性敘事紀事功能弱化的同時,作品中編年史意義上的小“我”往往被無限放大為社會的大“我”,進而成為所生活年代的見證者。
理論上“我”確有見證的可能,但卻又無法徹底“分身”。這是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不得不面臨的敘述困境。因此,文本如何讓“我”“分身”“有術”?怎么為“我”創造見證契機?這是很值得探究的敘事現象。值得一提的是,申丹也同樣認為,有必要根據見證人的位置來區分見證眼光,因而也贊同斯坦澤爾將第一人稱見證人眼光分為處于故事中心和故事邊緣兩類的做法,但申丹又進一步指出,第三人稱的內外視角劃分標準及其主、客觀性的對比度不適用于第一人稱見證人敘述。[22](P73)因此,應該把前者劃入內視角,而將后者歸入第一人稱外視角。[17](P60)較之于熱奈特倚重信息量大小的視角劃分,申丹更重視敘事眼光轉換,且細化了第一人稱見證視角,這便是其視角分類的主要特色。盡管如此,與熱奈特一樣,申丹的分類仍停留于“故事”這一敘事構造層面。若我們參照斯坦澤爾和普林斯的做法,將審視敘事進程的立足點從“故事”層面滑向“事件”層面,則敘事視角的考察標準則由“故事”內外轉換成“事件”內外,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發現,“我”有時能在不同事件轉換的“間隙”脫身而出,與所述事件保持一定距離,進而暫時放棄主人公的眼光,獲得了“見證”的契機。
不論是細察辭書詞義,還是反觀語言常識,我們都會發現,不管是“spectator”“observer”“witness”“onlooker”“eyewitness”,或是與之相應的“旁觀者”“見證者”“觀察者”“目擊者”等相關漢譯,均強調“我”不參與事件或情境,但又確證其發生。如其詞義那般,在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文本中,“我”是整個文本的主人公是毋庸置疑的,但又囿于認知、行動能力或其他原因,不能事無巨細盡收眼底,也并非凡事都可參與其中,因此,往往與所述的某些事件或情境保持一定距離。若細讀《我的大學》可發現,小說中與“我”交好的大半把“我”當“學生”或“后生”教導,接納“我”的多把“我”當孤兒看待,而敵視“我”的多半把“我”當反叛分子加以排斥。人物對“我”的看法也趨于標簽化,如巴什金說“我”“像個姑娘那樣羞怯怯”[23](P6),瑪利亞認為“我”“害臊”得“老不說話”[23](P29),羅馬斯在出走他鄉前擔心“又孤傲又驕傲”[23](P161)的“我”無法生存。在這一人與人關系不平等甚至異化/物化的環境中,“我”與人物對話極為簡潔、缺乏交互性,也就不難理解了。因此,大部分事件也經由出場人物之口闡述,更毋提事事都參與。與俄蘇《我的大學》中的阿廖沙一樣,哈蘇《生活學堂》中垂髫之年便落孤的穆坎諾夫也自小便在“人間”討生活,向眾多人物“拜師”,常被人物當“后生”羞辱或當“學生”訓教,也常眼睜睜地看著同伴至親被巴依欺負或相互欺辱,卻無力抗拒、勸阻,愛莫能助,如描述牧民首次觀摩割草機勞作時“我”的遭遇便極具代表性:
我什么也不懂,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這機器)割什么草?是長在地上的草嗎?”
“不是!割的是長在天上的草!”努爾塔扎粗魯地回答,“小伙子,你簡直是個蠢蛋!”[10](P127)
由上述可知,“我”本身的行為、認知能力再加上文本內其他人物的拒斥,“我”在人物面前表現得極為“拘謹”,儼然一個在“教師”面前不茍言笑的“學生”,這一方面能大體反映出飽經滄桑、求知若渴卻無法就學的“我”在“人間”這一所“大學(學堂)”內的真實身心狀態,客觀上保證了自傳體小說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又使得“我”與所述的部分事件或情境產生距離,暫時以“見證者”身份感知該事件或情境,此時,“我”顯然降級為“次要人物”,獲得了見證的契機。
需要指出的是,敘事進程審視角度由“故事”層面滑向“事件”層面后,“我”雖然獲得了見證的契機,但仍然是主人公之“我”的一部分,仍逃不出文本“故事”之外,見證之“我”的眼光仍屬于內視角,是主人公之“我”的多個敘事面相之一,但由于將研究立足點轉向“事件”,敘事眼光在事件鏈上的滑動、轉換也顯得更清晰,視角內部各種眼光相互轉換、對比、競爭的圖景也更易于捕捉。因此,“我”的成長在事件層面上的映射也更醒目。這也是一般敘事文本內獨立的見證者之“我”與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文本內見證之“我”的重要區分之一。
三、見證之“我”如何成長?
據石南征所言,若拋開“回憶”這一特性,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文本內的行為可大致分為敘事者的行為(“講”與“看”)和故事中人物的行為(“參與”事件),那么,“我”若不“參與”某些事件或情境,則只剩下敘事者的行為,因此,就要如同米勒所講的那樣,要“講”出“我”所“看到的”和“聽到的”,臨時獨立于主人公之“我”,獲得見證之“我”的眼光。那么,從成長小說的角度看,這一見證之“我”又如何成長?
就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文本而言,除了明顯的年齡和外貌變化作為“我”成長的外顯特征之外,“我”心智和認知的成長則是內在特征,這主要體現于眼光的變化。要考察敘事眼光的變化,則不得不考慮眼光的判斷標準。與第一人稱主人公經歷事件時的眼光判斷不同,見證者眼光的判斷不以時態為主要參照依據,要知道,弗里德曼、布斯、斯坦澤爾及申丹所謂的見證人貫穿了整部作品,如康拉德《黑暗中心》《吉姆老爺》中馬洛的眼光、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尼克的眼光、狄更斯《遠大前程》中匹普的眼光等便具有代表性,見證人所出現的片段時態變幻駁雜,評判標準在于見證人與事件的距離或是人物對事件的參與程度。同樣的,當將第一人稱自傳性敘事的研究落腳點從“故事”層面滑向“事件”層面后,見證眼光的判斷自然也需要考慮“我”對“事件”的參與程度:處于“事件”邊緣的“我”往往由于被空間隔絕只能以窺聽或旁聽的方式見證事件;處于“事件”中心的“我”雖在事發現場,但囿于認知、行為能力或其他原因,未能積極與在場人物互動,有時甚至只能在事后才得知當事人姓名。
據上述,在見證之“我”的眼光中,這一成長既存在于處于事件邊緣及中心的見證眼光各自的縱向演進之中,也處于眼光從事件邊緣邁向事件中心的橫向變化之間。
不論是在蘇聯文學的奠基之作《我的大學》中,還是在其仿效和踐行之作《生活學堂》中,見證之“我”都不止于見證,而是見證之余逐步反思、覺醒,因此,每一次見證都暗含著成長的契機,如:少年阿廖沙住進“馬魯索夫卡”貧民窟后,描述瘸腿的羅鍋兒和神學院數學家的爭吵前寫道“他倆緊緊關起房門”,“怪安靜地一連悶悶地坐上幾個鐘頭”,深夜十分“我”被二者爭吵聲“嚇醒”,聽到零碎的爭吵詞句,之后見到羅鍋兒離開,清晰地聽到了其關于上帝的論斷,最后聽到數學家“把房門猛力一關”,爭吵結束。[23](P12)此時,見證之“我”囿于空間,并沒有進入事件現場,事件信息零碎不堪,這是邊緣見證的典型。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面包師為了與小情人幽會,把“我”趕到了堆面粉袋的門洞里,從“關閉得不嚴密的門縫里”聽到了二人的談話,之后不堪二人聲響騷擾,躲到了院子里去,后半夜透過面包店房屋“開著的窗戶”又清晰地聽到反宗教歌曲的歌詞。[23](P59-60)
若不細讀字里行間,很難看出被空間隔絕的見證之“我”的情感反應,如:在第一處中,“我”幾乎只限于轉達事實,并沒有對所見所聞做過多反思,連對晦暗的“馬魯索夫卡”貧民窟內的生活的情感反應也較晦澀;在第二處中,隨著社會見識的增長,“我”對所見證的面包師幽會之事感到“憋悶”“可怕”,特別注意到了大學生所唱的反宗教歌曲“特別活潑地唱出了這個意味深長的低音‘喔唷!’”[23](P60),情感表達較于第一處更為明顯、清醒,但由于邊緣見證的局限性,不但情感仍隱晦,反思也遠未及處于事件中心之“我”那么深入。
相比而言,處于事件中心的“我”與人物的互動雖仍不如主人公之“我”那么積極,但其清醒程度和反思深度則比前述處于邊緣的見證之“我”要更進一層,如:在悶熱的夜晚,阿廖沙與眾人來到矮樹林,聽他們唱凄涼的歌,輕聲漫談,回憶往事,“幾乎是誰也顧不到聽誰的”,因此“我”便無法清晰記錄討論的觀點,也無法正常參與討論。但由于“我”深陷其中,對這一場面的反思則很明了:“我覺得今天夜里人們好像是已經活到了生活的盡頭,——好像一切一切的事情從前已經見過了,這以后再不會見著什么新事情了!”[23](P10)顯然,見證的“我”跳出了這一漫談之外“冥思”。又如,托爾斯泰主義者與小神父的辯論,“我”在場,雖沒有參與對話,但不僅能對現場的情形及人物的言談舉止描述得極為細致,而且還對托爾斯泰主義者的話“大吃一驚”,覺得自己“是世界上頂頂無能的人”,在心里“忽然發生了一個問題:怎么辦呢?如果說生活就是為實現人間幸福而奮斗,那么慈悲跟愛該只會妨礙斗爭的成果吧?”[23](P87)這一發問觸及了托爾斯泰主義的要害,但此時“我”仍未得知托爾斯泰主義者叫克洛波斯基,后來又打聽其住處,慕名拜訪,洞悉其思想悖謬面目,失望而歸。這一見證和之后的經歷都是“我”對愛、人道主義進行反思[23](P90)的重要契機,其思考無疑又深入一層。再如,“我”和羅馬斯下鄉后,一起聽了蘇斯洛夫、伊佐特、米貢、庫庫什金等鄉民議論商人和地主貴族誰更狠,此時作為“學生”的“我”也沒有參與會話只盼望“老師”羅馬斯能發言并揣測其發言內容,但后者卻一直沉默不語,晚間才跟“我”交代了不發言的原因。羅馬斯關于農民、沙皇、法律等的看法由“我”以自由間接引語形式轉述,羅馬斯的聲音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我”用“他們”“你”兩種人稱交替轉述[23](P113)的聲音,由于沒有直接引語的導入部分,這些轉述極易讓人產生“我”不但認同且全盤接受羅馬斯看法的印象,更何況,轉述之后,“我的心里有點灰暗憂悶起來”[23](P113),于是暗自低聲陳述了喚醒莊稼人起義奪權、選舉的見解。因此,前述轉述片段可視為“我”見證鄉民談話之后的反思,且這一反思已空前清醒、務實。
上述實例采樣嚴格遵循文本先后順序,而文本則按傳主成長的編年順序進行敘事,從中不難看出,見證之“我”逐步從事件邊緣走向中心,反思進程漸次深入,逐漸覺醒,甚至陷入矛盾的苦悶中不能自拔,與真實的傳主一樣,在內心矛盾不可調和之時,“我”試圖自殺,《我的大學》內只說因“苦悶”而自殺,而最深層的原因則是“我對社會和各種事件認識不夠”[23](P176)。之后,自殺未遂的“我”跟羅馬斯去了克拉斯諾維多沃村,不僅講學收徒,還參與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動,反思與行動由此合一,主人公之“我”的形象刻畫進一步深入。
相比之下,《生活學堂》中見證之“我”的出場方式相對單一,以處于事件中心但囿于認知、行動能力或交流需要而無法參與事件為主,也大多發生在其少年時期,致使其對所發生之事無任何改觀行動,只是圍觀,比如,1914年一戰爆發,大批成年哈薩克人被征去前線,14歲的“我”不知戰爭為何物,稍微年長的牧童凱爾克也對戰爭一知半解,卻很喜歡賣關子,這越發讓“我”好奇,為探究竟,“我”裝病不去放牧,再三掙脫看護人,才目睹了壯丁出征場面。從客觀上講,“我”囿于年齡而未參戰,卻處于戰事輿論的中心,但由于“我”缺乏認知能力,仍沒有參與這一輿論事件,又以見證之“我”的眼光經歷了此事件。又如,倆哈薩克老人老實巴交,因為他們的狗咬死了巴依老爺家的馬,之后巴依帶著所謂的眾審判官在兩位老人家大吃大喝五天,第六天的時候才提審。“我”見證了巴依審判兩位老人的過程,此處,“我”和眾人一樣都是旁觀者,但其眼光早已有所變化,如將穆斯塔法稱為“畜牲”,而并沒有提升至更抽象的政論述評層面,既符合經驗自我的眼光發展進程,也顯現了少年之“我”的真性情,雖為旁觀者,但嫉惡如仇的覺醒少年穆坎諾夫之形象已顯現。
在第二部中,“我”開始頻繁旁聽政治話題,且見證之“我”的眼光逐漸發生變化,如:在前往奧姆斯克的火車上,“我”旁聽了同行旅客聊國內戰爭話題,雖聲稱“我入神地聽著,雖然有很多聽不懂”[24](P57),沒能參與辯論,卻以直接引語形式清晰地記錄了爭論雙方褒貶高爾察克的觀點,最后“我”稀里糊涂地睡著了,不久被尖叫聲和推搡弄醒,還稀里糊涂地參加了“群毆”。往后,見證之“我”對政治話題的關注度持續加深,如:扎拜、捷列拜與俄羅斯人安德烈接頭,“我”也在場,在談及紅白兩軍形勢之前,后者把“我”當局外人提防,提示接頭人謹慎,確證“我”可信后,才談及了紅軍動向及白軍頹勢。盡管如此,安德烈在短短的談話中仍不直接回答二者的問題,作為見證者,“我已經猜到,他對我不是很放心,仍保持警覺。我后來才知道,安德烈是紅軍,在執行地下組織的任務”[24](P119)。與前幾次盲目地見證相比,此時的“我”不但離中心話題更近,且也空前覺醒。此后,“我”回鄉下當鄉村教師,在那與剛從俄羅斯回國的昔日好友拜馬加姆別特重逢,起初對“我”也甚為提防,后來在潛移默化中與“我”討論紅白軍問題,有時還提醒“我”“特羅伊茨克有布爾什維克的地下組織,還有士兵”,如此云云。顯然,見證之“我”此時離政治話題中心又近了一步,這與《我的大學》中阿廖沙接近羅馬斯的情景十分相似。要知道,此后“我”逐漸由政治話題的旁聽者轉為話題參與者,從第二部第四篇開始,“我”積極學習列寧革命思想,參加革命斗爭,入黨,革命者和蘇維埃支持者的形象更顯眼。在第三部中,“我”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社會活動家之“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需指出,見證之“我”的眼光大多集中出現于傳主少年時期,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我”的位置也逐漸由事件邊緣走向中心。若說成長小說中“主人公的變化獲得了‘情節’的意義”[12](P230),則在事件層面上首先體現為見證之“我”的變化,如阿廖沙和穆坎諾夫見證眼光的深入,思想之覺醒,行動力之增強,直至走向事件中心,成為名副其實的行動者之“我”。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具有行動力的主人公之“我”的形象也部分地體現于見證之“我”的成長中。
四、見證之“我”與教育意義的關系
巴赫金曾說:“對第五類小說⑤的理解和研究,倘若切斷它與其他四類成長小說的聯系,就無法進行了。”[12](P233)這對于本文所涉及的第三類成長小說,也即自傳體小說,也是極為合適的,畢竟,這五類小說都是成長小說,其體現成長著的主人公的形象的特性是共通的。如《我的大學》《生活學堂》中“我”的成長雖然“發生在傳記時間里”[12](P231),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如同非純年齡循環型成長小說那樣“把世界和生活描寫成每個人都要取得的經驗,都要通過的學校,并且從中達到同一種效果——人變得清醒起來”[12](P231),因此,又如同純年齡的循環型成長小說一樣“揭示人物性格及觀點隨著年齡而發生的重要的內在的變化”[12](P231),而訓諭教育小說的成分則見之于成長小說的所有變體[12](P231-232),就如同《我的大學》《生活學堂》那樣,即便“我”的“大學/學堂夢”未竟,但我已然經歷了社會這一學堂的“教育”,且在諸多事件的見證中經由反思而獲“自我教育”。那么,在上述文本中,見證之“我”的成長與教育意義有何關系?
費定曾說,蘇聯文學的創作手法“就體現在我們優秀作品所反映的新世界的人的形象里”[25](P47),留里科夫則說:“我們文學的主人公都充滿著進取精神。”[26](P65)“解凍”以前第一人稱敘事內視角內部的構造也跟進取的“我”這一“新人”形象密切相關,而其教育意義便存在于“我”的形象之中,就如同在《我的大學》《生活學堂》之中那般,見證者之“我”都經由見證、反思最終實現了由見證之“我”向覺醒及行動之“我”的演化。
其一,見證之“我”即是逐漸覺醒之“我”,教育意義源于“我”的覺醒。在反思的深度和認知的清晰度上,處于事件中心的見證眼光要優于處于邊緣的見證眼光。兩種見證眼光構成了“我”觀察、反思社會的完整視角,都是見證之“我”的一部分。《我的大學》《生活學堂》整體上按照“我”成長的編年史順序寫作,見證之“我”大體上反映了“我”在“社會大學”或“學堂”中不斷學習、覺醒的過程,如留里科夫所說的,“高爾基在二十年代初準備寫一些描寫新人物的小說,他的主要目的是表現他們如何覺醒過來而積極、自覺地生活,表現出特殊的個性是怎樣形成的”[27](P16),具有自傳性特色的《我的大學》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而《生活學堂》則深受此作影響。
其二,教育意義實現于從覺醒之“我”到行動之“我”的轉變中。從所分析的兩個自傳性敘事文本看,作為作者面具的“我”,其見證之眼光皆在為作者經歷、見證乃至反思事件。在這一前提下,自傳性敘事的“我”局部地從所述事件中脫離,而不是與主人公之“我”截然分開。因此,見證之“我”的觀察、反思也是主人公成長的一部分。這與一般性敘事中的見證者是不同的,如《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尼克只作為蓋茨比和黛西愛情悲劇的見證,他參加蓋茨比的宴會,與之認識,完成了這一見證過程,其間見證者之“我”尼克雖然因蓋茨比的遭遇而有情感波動,但未有反思,而只能沿著由蓋茨比和黛西所主導的情節發展一路見證,從未有過干預的行動。若說《了不起的蓋茨比》為一般性敘事,反思和行動不是敘事的必備任務。那么,我們可以看看以反思為主體的懺悔錄,如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第一人稱“我”懺悔、反思的聲音讓位于引自《圣經》的上帝之聲音,這一反思是內向型的,遠未涉及行動之“我”的層面。盧梭的《懺悔錄》則記錄了其出生之后到1766年被迫離開圣皮埃爾島之間50多年的生活經歷,雖然懺悔也帶有宗教意味,但自我覺醒占主導,開始反思、深挖個人不良行為背后的社會原因,展現了純凈之“我”如何被社會玷污的過程。所見證的社會不公、弱肉強食、階級紛爭等等都是其反思的對象,但囿于社會和歷史原因,這一見證之“我”在文內的“懺悔”只停留于“牢騷”,因為傳主仍不具備采取改變現實行動的可能性。
如此看來,所述的蘇聯文學自傳性敘事文本內的見證之“我”不但與一般性敘事的第一人稱見證者不一樣,且與其他時期的自傳性敘事也不一樣,畢竟其見證之“我”是從主人公之“我”局部脫身,見證則是反思進而實踐的契機。英國文論家杰克·林賽曾說:“不論作者愿意或不愿意,他在感情上和思想上都卷入了構成他的作品的內容的沖突中。他對孕育那些沖突的社會的態度,他對書中人物以及對讀者的態度,將取決于他的全部感情、理解和他對生活及其方向的洞察力。”[28](P11)就《我的大學》《生活學堂》而言,底層生活中對社會沖突的敏銳洞察讓見證之“我”產生了道德、心理矛盾,這促使“我”反思、覺醒、成長,如羅西雅諾夫所說:“道德的、精神-心理的沖突,是文學中表現公民性、人民性和黨性最為適宜的領域。”[29](P61)上述所列的見證、反思實例便是例證。“問題在于挺身而出參加斗爭,為共同目標而奮斗,這樣一方面教育自己,一方面也教育讀者。”[28](P11)這一個“我”在見證了社會現實之后,注定要邁向行動,如阿廖沙參與地下活動,宣傳革命思想,反抗富農壓迫,又如穆坎諾夫以實際行動支持蘇維埃政權建設。從見證、反思、覺醒到行動,這便是上述文本教育意義的淵源所在。畢竟,教育不僅如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所講的那樣要“喚醒人們自我覺察的能力”和“智慧”[30](P11-13),還應改變人的行為。
五、結語
研究“解凍”之前的蘇聯成長小說可知:第一,蘇聯成長小說中,第一人稱內視角與外視角并存,且被“排擠”“滲透”的內視角內部成分多樣,既有經歷事件時的主人公之“我”的眼光,也有觀察位置處于故事中心的第一人稱見證人的眼光,而外視角則以觀察位置處于邊緣的“我”的眼光最為典型;第二,“我”的各種眼光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于動態的互動、轉換之中,譬如說,同是內視角,經歷事件的主人公之“我”的眼光不僅可與故事中心的第一人稱見證人的眼光切換,在必要時,“我”還滑向“事件”之外,其觀察位置移至事件的邊緣,此時,內視角則完成了向外視角的轉換;第三,“我”的眼光與“我”的形象密切相關,在成長小說中,“我”的眼光的轉換與“我”的成長相伴相隨,服務于“我”的形象塑造。
因此,在研究蘇聯文學第一人稱敘事時,既要關注信息量大小、內外視角差異,也要從眼光的多樣性、互動甚至轉換的角度出發挖掘“我”形象的多樣性和變化。只有如此,“解凍”之前蘇聯文學第一人稱敘事的全貌才能得以揭示,蘇聯文學敘事圖景才有可能獲得較完整的呈現。本文所論及的見證之“我”只是多元敘事之“我”的一個面相,其所承載的教育意義也只是多元敘事圖景之“一角”,更僅僅是蘇聯文學多元敘事之一瞥,后者全貌則深藏于蘇聯多民族文學互動、互補的動態進程之中。
注釋:
①蘇聯文學定義頗多,本文的“蘇聯文學”指蘇聯官方所謂的多民族文學,包括受俄蘇文學深刻影響的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文學。
②敘事學術語“Point of View”“Focalization”“Viewpoint”“Angle of Vision”“Seeing Eye”“Filter”“Focus Of Narration”“Narrative Perspective”的譯法有“視點”“聚焦”“眼光”“視角”等,申丹在《對敘事視角分類的再認識》和《視角》對視角進行劃分時分別采用了后兩者,本文沿用申丹譯法和用法,引文除外。若無特殊說明,其他術語亦如是處理。
③具體分類如下:其一,零視角(即傳統的全知視角);其二,內視角(仍然包括熱奈特提及的三個分類,但固定式內視角不僅包括像亨利·詹姆斯《傳使》那樣的第三人稱“固定性人物有限視角”,而且也包括第一人稱主人公敘述中的“我”正經歷事件時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稱見證人敘述中觀察位置處于故事中心的“我”正經歷事件時的眼光);其三,第一人稱外視角(即固定式內視角涉及的兩種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我”追憶往事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稱見證人敘述中觀察位置處于邊緣的“我”的眼光);其四,第三人稱外視角(同熱奈特的“外聚焦”)。參見申丹《對敘事視角分類的再認識》(《國外文學》1994年第2期)。
④俄國學界對照俄蘇文學(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常用“казах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 ратура”(哈薩克蘇維埃文學),筆者選用“казахста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哈薩克斯坦蘇維埃文學,簡稱“哈蘇文學”),以與國內哈薩克族文學區分開。
⑤是指人與世界共同成長的小說,也是成長小說中最重要的一類。參見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