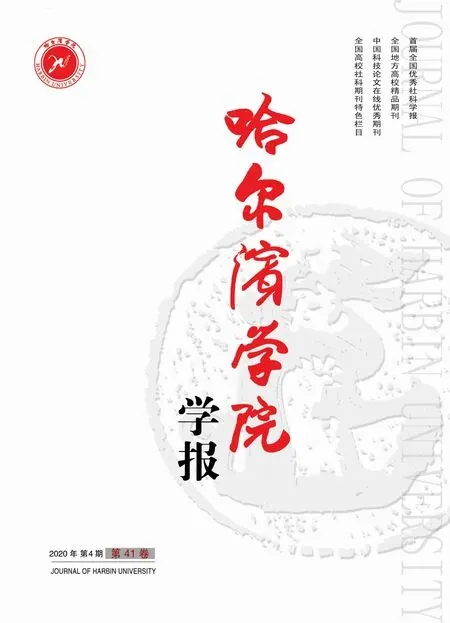論元雜劇中書生遇婚戀而棄科舉現象
王玲玲
(溫州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溫州 325035)
古人云“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科舉與婚戀是中國古人的至高追求。美好的事物往往不能同時擁有,二者不能兼得時,取舍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也有所不同。戲曲是現實生活的縮影,古人的取舍在戲曲中有所投射。南戲中,科舉是書生人生追求的最終目標,婚戀只是考取功名的輔助條件。而在元雜劇中,書生在科舉路上遇見美麗的小姐或漂亮的藝伎往往會放棄科舉,當遇到外力的干預時,書生才不得已離開小姐前去進京趕考,中舉后歸來與小姐再續前緣。從元雜劇中書生的選擇可以看出婚戀是書生的最終目的,而科舉則成了婚戀得以成功的手段。
一、遇婚戀而棄科舉
婚戀題材的元雜劇,才子佳人的故事以《西廂記》為典型代表。劇中首先交代張生是在進京趕考的途上,他的主要任務是考取功名:
小生書劍飄零。風云未遂。游于四方。即今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應。路經河中府。過蒲關上。[1](P2)
而當他遇見鶯鶯后,對待科舉的態度立馬有了轉變:
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小生不往京師去也罷。[1](P6)
與元稹《鶯鶯傳》“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2](P199)相比,王實甫《西廂記》認為“嬋娟解誤人”,這是二者主題的一大變化,同時可以看出張生遇婚戀而棄科舉之表現。但他仍以“溫習經史”[1](P8-9)為由,尋了間“靠著西廂”[1](P9)的房子,企圖早晚與鶯鶯相會。他的選房標準只有一個:離鶯鶯近,以期“過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從天降”。[1](P10)此句直接表達出張生內心所想。此后,張生再不提科舉之事。
張生與鶯鶯私自結成姻緣后,遭到老夫人以“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為由的反對,張生必須考取功名后才可以真正迎娶鶯鶯,此時他被迫進京趕考:
(生見老介老)好秀才呵。豈不聞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官司裏去來。恐辱沒了俺家譜我如今將鶯鶯與你為妻。則是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壻。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我與你養著媳婦。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1](P76)
劇中,科舉已經成為成就婚戀的條件。這樣的故事情節在元雜劇中并非個例。
王實甫另一雜劇《呂蒙正風雪破窯記》中,落魄書生呂蒙正接到劉員外家的千金劉月娥拋的繡球,劉員外不得已同意了女兒的婚事。婚后呂蒙正以街頭賣字、寺廟領齋飯為生,不愿參加科舉考試:
他(呂蒙正)空有滿腹文章,不肯進取功名,他聽的這鐘聲響便來趕齋。[3](P2138)
劉員外不忍女兒跟著呂蒙正受苦,故意讓白馬寺的長老奚落他:
你為孔子門徒,你有滿腹文章,你若應過舉呵,得一官半職,不強似在寺中趕齋?既為男子漢,不識面皮羞。[3](P2139)
呂蒙正受到羞辱這才前去科考。這里關鍵的一點是,書生對科舉的態度十分輕視,科舉考試不是他們自發的行為,而是在外界的逼迫下為之。
鄭光祖《迷青瑣倩女離魂》與王實甫《西廂記》相仿。王文舉與倩女指腹為婚,王生父母雙亡,家道中落,因此倩女之母違背婚約,讓二人以兄妹稱之,并以“三輩兒不招白衣秀士”為由,讓王生中舉后再來婚配:
(夫人云)……老身為何以兄妹相呼?俺家三輩兒不招白衣秀士。想你學成滿腹文章,未曾進取功名。你如今上京師,但得一官半職,回來成此親事,有何不可?(正末云)既然如此,索是謝了母親,便索長行去也。[4](P3831)
白樸《裴少俊墻頭馬上》也是當裴少俊與李千金私自結合被父親拆散后不得已前去參加科舉:
(裴舍云)父親,你好下的也!一時間將俺夫妻子父分離,怎生是好?張千,與我收拾琴劍書箱,我就上朝取應去。一面瞞著父親,悄悄送小姐回到家中,料也不妨。[5](P757)
裴少俊與李千金瞞著父母生兒育女,父親發現后逼迫裴李分離,裴這才前去科考,中舉后迎回李千金。客觀來講,此劇中科舉也成為婚戀得以成功的前提條件,而非書生畢生所追求的目標。
凡此種種均透露出元雜劇中書生不再執著于科舉,一旦遇見美麗的小姐就會中止科舉考試。只有當二人的結合遭到外力逼迫時,書生才進京趕考。科舉顯然成為婚戀得以成功的條件,而非如南戲中婚戀是科舉達成的手段。
南戲中的書生十分熱衷于科舉考試。早期南戲《張協狀元》,書生張協娶王貧女只是為了得到進京趕考所需的錢財,一旦目的達到就把貧女拋棄。劇中第一出就道出張協對科舉的執著:
“世上萬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今年大比之年,你兒欲待上朝應舉。覓些盤費之資,前路支用。’‘……十載學成文武藝,今年貨與帝王家。欲改換門閭,報答雙親’。”[6](P2)
張協進京趕考的途中與王貧女結合,但這與元雜劇中書生與小姐的結合有很大不同。元雜劇中書生結婚是為了得到“人”,而南戲中書生結婚是為了得到“錢”。張協與貧女結婚只是權宜之計,只因途中遭遇不測,路費被搶去,科舉之路被迫中止。如第十八出: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前程事業,豈期中路惹災迍。近日須諧貧女,未是吾儒活計,依舊困其身。爭如投上國,赴舉奪魁名。[6](P96)
以及第二十四出,張協一再表明娶貧女是迫不得已:
家住西川,回首淚暗垂。中途怎知人劫去,娶它貧女是不得已。幸然脫此處,都城在,眼下里,盡總是繁華地。[6](P122)
因此,貧女為張協謀得盤纏后,他繼續進京趕考,中狀元之后,對貧女負心也是必然的。第三十五出,貧女前來認親,遭到拒絕:
(生)唯,貧女!曾聞文中子曰:“辱莫大于不知恥辱。”貌陋身卑,家貧世薄。不曉蘋蘩之禮,豈諧箕箒之婚。吾乃貴豪,女名貧女。敢來冒瀆,稱是我妻!閉上衙門,不去打出!”[6](P161-162)
這與元雜劇中書生中舉后立馬返回與小姐團聚截然不同。南戲成熟之作《琵琶記》,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二月就進京趕考,中狀元后娶了牛府千金,雖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在客觀實際上,依然是為了功名負了婚戀。南戲反映出中國千百年來科舉制度下一直存在的問題——書生負心。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認為元雜劇中所有的書生都比較“志誠”,在他們眼中愛情大過功名利祿呢?
二、看似愛情實出“風流”
元雜劇中的書生遇婚戀而棄科舉,看似為了愛情而拋棄功名利祿,實際上追求的是風流快活而非愛情。這可從文本的具體分析中看出。
《西廂記》中,從鶯鶯、紅娘的描述和張生的自白可以看出,張生是一個風流浪子的形象。張生自言:“我是個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隋何,浪子陸賈”,[1](P56)鶯鶯看張生“(旦)外像兒風流。青春年少。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1](P21)紅娘形容他:“忒風流忒煞思。忒聰明忒浪子。”[1](P50)由此可知,《西廂記》對張生人物的設定,是一個“風流”的形象。這樣的形象,就決定了張生對鶯鶯的追求不是真情。
“風流”主要體現在張生對鶯鶯的追求是緣于美色而非真情。《西廂記》中,對鶯鶯的描寫是“顚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等可喜娘臉兒罕曾見。引的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他那裏盡人調戲亸著香肩。只將花笑捻。”[1](P4)張生之好“色”可從紅娘的話中窺見一二。崔張之事被老夫人察覺,于是拷問紅娘。紅娘一番辭令中提到“張生非慕小姐顏色。豈肯建退軍之策。”[1](P74)可見,張生對鶯鶯的感情是基于鶯鶯之美色。
張生對美色的追求還表現在他對紅娘的態度上。歷來有學者提出張生與紅娘之間超越了書生與丫鬟的關系,但多從紅娘角度來分析她對張生的愛慕,實際上,張生的“風流”本性也使得他對紅娘有了非分之想。張生對鶯鶯一見鐘情后,在僧房與紅娘見面時,調戲紅娘:
【小梁州】可喜娘的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胡伶淥老不尋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張郞。【么】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鴛帳。怎舍得他疊被鋪床。將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許放。我親自寫與從良。[1](P9-10)
張生私下里打量紅娘,垂涎其美色,并意想若與鶯鶯結良緣,也可將紅娘收入房中,不再讓她做個粗使丫鬟。此處將張生的風流本性展露無遺。
婚戀題材的元雜劇中,除了才子佳人式,還有士子妓女式。如關漢卿的《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杜蕊娘智賞金線池》《趙盼兒風月救風塵》《詐妮子調風月》,馬致遠的《江州司馬青衫淚》,石君寶的《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諸宮調風月紫云亭》,張壽卿的《謝金蓮詩酒紅梨花》,喬吉的《玉簫女兩世姻緣》《杜牧之詩酒揚州夢》,賈仲明的《荊楚臣重對玉梳記》等。劇中書生不熱心于功名,而是流連于煙花柳巷之中,對貌美的藝伎展開追求,“風流”是他們共同的特點。
關漢卿《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中,書生托名宋朝風流浪子柳永。開篇楔子中直接描述柳生之風流:
本圖平步上青云,直為紅顏滯此身。老天生我多才思,風月場中肯讓人!小生姓柳名永,字耆卿,乃錢塘郡人也。平生以花酒為念,好上花臺做子弟。不想游學到此處,與上廳行首謝天香作伴。[7](P304)
書生柳永流連風月場合,看上了貌美的上廳行首謝天香,在紅塵中放浪,游戲人間。劇中另一人物錢大尹也參與其中,為了成就柳永與謝天香的姻緣,假意將謝天香娶回府中。三年后柳永歸來,又將謝歸還。這便是“智寵”之所在。整個故事中,書生與藝伎一起,科舉只是略略提及,足以看出書生的風流本性。
再如關漢卿的《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同樣是書生與藝伎之間的故事。韓輔臣在進京趕考的途中,遇見行首杜蕊娘,從此忘記了功名,留了下來與蕊娘朝夕相伴。第二折:
一生花柳幸多緣,自有嫦娥愛少年。留得黃金等身在,終須買斷麗春園。我韓輔臣,本為進取功名,打從濟南府經過。適值哥哥石好問在此為理,送我到杜蕊娘家安歇。一住半年以上,兩意相投,不但我要娶他,喜得他也有心嫁我,爭奈這虔婆百般板障,俺想來,他只為我囊中錢鈔已盡,況見石府尹滿考朝京,料必不來復任,越越的欺負我,發言發語,只要撚我出門去。[8](P149-150)
這種現象元雜劇中并不少見,書生放浪紅塵,與藝伎飲酒作樂,是典型的風流浪子的形象。那么,這種放棄科舉而放浪紅塵的行為原因何在?元雜劇中的書生是元代文人在劇中的一個投射。因此,這與元代的科舉制度狀況、市民經濟的發展及元代文人的追求風向有關。
三、遇婚戀而棄科舉之原因
(一)時代所限:科舉之路受阻
元雜劇中,科舉讓步于婚戀。這種讓步并非是書生只羨鴛鴦不慕功名,而是元人對功名求而不得。元代下層人民躋身上層社會的唯一通路科舉被廢止。元代初年,蒙古人統治社會,游牧民族馬背上得來天下,武功了得,文治不行。上層統治者不重視讀書,他們本身大多目不識丁,并歧視知識分子。在其統治的八十一年間,元代科舉處于廢止的狀態,科舉恢復之后也不像唐宋時的盛行,錄取人數極少,且漢人參加科舉尤為受到不公平待遇。讀書人的地位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更加低下,他們失去了唐宋文人由科舉制度所帶來的優越感,進而失去了婚戀中居于支配的地位。他們的“不負心”,實則是失去了“負心”的資本。
婚戀題材的元雜劇中有一個普遍現象:書生一旦決定去參加科舉考試,必定會中狀元。如《西廂記》中的張生、《呂蒙正風雪破窯記》中的呂蒙正、《裴少俊墻頭馬上》中的裴少俊等。結合元代科舉制度,這顯然不是實際情況,就算是在唐宋兩代,通過科舉實現“鯉魚躍龍門”的愿望也極為困難,更遑論這是科舉不再盛行的元朝。因此,元雜劇中的書生在面臨科舉與婚戀時,毫不猶豫地選擇婚戀。相較于早期民間藝人創作南戲的直接、不加修飾,文人所寫的元雜劇往往具有一定的含蓄性,將自己真實的欲望層層掩蓋,故現實中的科舉無門,投射到劇中則成了無意科舉。
儒家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中國古代文人一直遵循這一古訓,因此,他們走著科舉出仕和歸隱山林兩條路。文人的首選是科舉出仕,求之不得基本會走歸隱山林的路。元代文人科舉受阻,他們卻選擇紅塵中放浪而非歸隱山林。實際上,放浪紅塵也是一種歸隱,只是與前代文人相比,他們隱于市。
(二)市民經濟的發展:書生隱于城市
中國古代文人歸隱山林基本分兩大類型:一是曲線求官,歸隱山林以博得美名進而引起統治者的注意,最終謀得官職;二是政治環境黑暗,不適合在朝為官,于是選擇隱逸山林以求獨善其身,擺脫內心的苦悶。但對元代文人來講,歸隱山林不可能達到曲線求官的目的,也無法擺脫內心的苦悶。劉彥君在《元雜劇作家心理現實中的二難情結》一文中指出元代劇作家們像歷史上那些文人一樣隱逸山林以求擺脫俗世的煩惱是行不通的。[9]但元代市民經濟的發展,勾欄瓦舍的盛行,給元代文人尋了一條出路,他們隱于市井中,不再參加科舉,更不熱衷政事,他們轉而創作了大量的劇本投入市場演出以獲取生存的資本和內心的歡愉。
隨著市民經濟的發展催生了娛樂項目,戲曲演出受到大眾的喜愛。大眾的喜愛促進了藝人的演出,而藝人演出需要有劇本的支撐,元代文人有能力也有閑情為藝人們寫劇本。這種文人創作與藝人演出相結合的商業模式唐宋時即有之。羅燁在《醉翁談錄》中描述柳永“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10](P32)元代文人與藝人的合作更為普遍。朱權在《太和正音譜》中引用趙子昂語:“雜劇出于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輩所作,娼優豈能扮乎?”又引關漢卿語曰:“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為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11](P24-25)可見,藝人演出劇本多出自文人,獲取錢財后二者分之,這就解決了元代文人的經濟問題。
同時,文人的創作除了賺錢之外,最重要的是自娛,表達自己的志趣。首先,在寫劇本的過程中,他們將自己的情感、志趣蘊含其中,對科舉求而不得的苦悶得以宣泄。其次,文人與戲曲藝人的交往,彼此欣賞對方的才藝,文藝上的精神交流也讓文人的內心有了安慰。因此,元代文人隱于市井之中,既可以解決經濟問題,又能使精神得到寄托,苦悶得以解脫。這符合元代文人的利益需求,故他們選擇隱于市而非山林。元代文人與藝人的交往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追求風流,做個浪子是元代文人共同的追求風向。
(三)元代文人的追求風向:“風流”“浪子”
正如文學自覺的時代——魏晉時期,文人如阮籍、嵇康等以放蕩不羈、飲酒作樂來麻木痛楚的神經,忘懷人生愁苦,而元代文人放浪紅塵,做個風流浪子以求將自己的窘迫潦倒、身世之嘆拋于腦后。這是落魄文人淡化人生悲劇的常用方式。元代文人形成了以風流為高尚,以風流浪子為榮的審美傾向。朱經在《青樓集序》中云:“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己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12](P15)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他們為官,只能做一個風流浪子,所以“不屑仕進”。《錄鬼簿》中對元代作家的描述多帶有濃郁的浪子色彩。王實甫“風月營,密匝匝,列旌旗。鶯花寨,明颩颩,排劍戟。翠紅鄉,雄糾糾,施謀智。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13](P173)關漢卿“風月情忒慣熟。姓名香四大神物,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13](P151)關漢卿在《【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中宣稱:“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14](P703)“占排場風月功名首,更玲瓏又剔透。我是個錦陣花營都帥頭,曾玩府游州。”[14](P704)這種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的宣稱,表現出在當時的社會中,做一個“郎君領袖”是文人都向往的事情。
綜上所述,元代科舉的廢止讓書生對功名求之不得,轉而追求風流。市民經濟的發展使他們隱于城市、放浪紅塵,故元代社會中形成了以風流為高尚,以風流浪子為榮的追求風向。因此,元雜劇中的書生遇婚戀而棄科舉,婚戀中對貌美女性的追求正是他們風流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