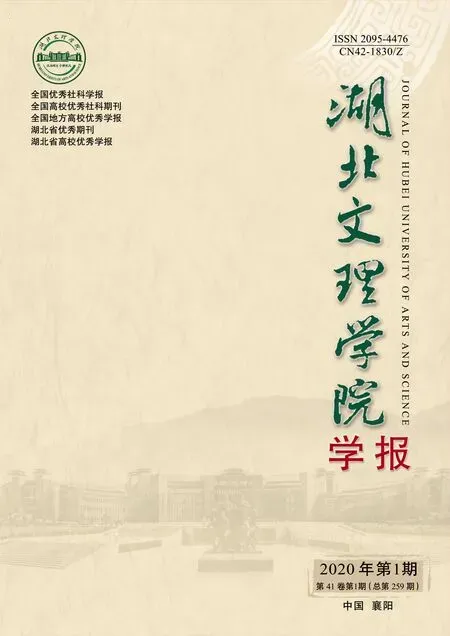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中的穩定性問題
鄧 肄,劉韞照
(1.四川輕化工大學 法學院,四川 宜賓 644000;2.貴州財經大學 信息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3.四川輕化工大學 經濟學院,四川 宜賓 644000)
穩定性問題是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的中心問題,對這一問題的重新闡釋也是羅爾斯后期哲學與前期哲學發生裂變的根本原因,因此,對《政治自由主義》的這一中心問題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羅爾斯后期哲學的思想與脈絡。同時,由于羅爾斯后期哲學本質上是憲政哲學,對《政治自由主義》的這一中心問題進行研究,也有助于我們領略羅爾斯對憲政哲學論域的深入拓展。
一、羅爾斯對穩定性問題的重新認識
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中的穩定性問題是對《正義論》中穩定性問題的重新闡釋,故這里首先簡要概述《正義論》中的穩定性問題。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認為,正義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一個城邦或一個政治社團之所以出現不穩定或內亂,是因為生活在其中的各階層認為這個城邦的政體在分配政治權利時不符合他們各自心目中的正義,因而心生不平。[2]9,234-235羅爾斯據此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就是受一個公共正義觀念有效調整因而其成員也具有通常有效的正義感的社會,而對于一個社會而言,社會合作的穩定性或持久性就取決于這個社會合作體系是否有一個得到社會各方公認的公共正義觀念,從而以公共的正義感來消除人們心理上的破壞性傾向(3)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p.4-5, p.454.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并沒有明確引述亞里士多德的上述觀點,而只明確引述了亞氏在《政治學》第一卷第二章1253a15關于人的正義感及對正義的共同理解造就一個城邦的洞見(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43),但以羅爾斯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熟悉程度,羅爾斯“秩序良好的社會理念”來自亞氏的上述理論,乃是十分明顯的。。什么樣的正義原則才是這樣一個使社會合作具有持久穩定性或內在穩定性的公共正義觀念呢?羅爾斯認為,他所矯正的自由主義性質的正義原則——兩個正義原則(公平的正義)就是一個能得到各方共同接受的公共正義觀念。因為我們一旦進入無知之幕遮蔽下的原初狀態,面對包含利己主義、功利主義、直覺主義和兩個正義原則等正義觀念的清單,理性的我們都會選擇無條件關心我們每一個人的善并體現了互惠性的兩個正義原則。同時,在羅爾斯看來,由于兩個正義原則堅定地保障了平等的自由、機會的公平平等,并在兼顧強者和弱者利益以及效率的基礎上合理解決了由于自然天賦所帶來的不平等問題,當人們生活在這種正義制度之下,便會在“以德報德”這一道德心理學法則的支配下,產生充分堅定的正義感,以此克服自利、妒忌和怨恨等破壞性的心理傾向,從而自愿按照正義原則的要求行動,而不會破壞社會合作。此外,當人們產生了充分堅定的正義感,還能自動維護正義制度,使因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再處于平衡或穩定狀態的正義制度恢復正義。這樣,在羅爾斯看來,通過一種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在社會制度中的成功貫徹,便以一種不同于霍布斯依靠絕對主權來維系社會合作的穩定性的方式,實現了社會合作的內在穩定,也實現了個人的自律。
由是可知,盡管《正義論》探討了社會合作、正義觀念和正義制度等不同對象的穩定性,但這些不同對象的穩定性在羅爾斯正義理論中的“問題”卻具有同一性,即它們涉及的都是人們“心理的穩定性問題”:社會合作的穩定性取決于這個社會合作體系是否有一個得到社會各方公認的公共正義觀念,從而以公共的正義感來消除人們心理上的破壞性傾向;正義觀念的穩定性取決于貫徹這種公共正義觀念的正義制度為他們所培育的正義感是否能在通常情況下勝過不正義的心理傾向;正義制度的穩定性也取決于人們能否產生充分堅定的正義感,以自動維護正義制度。[1]177,454-458也就是說,只要人們找到一個符合正義感產生機理的公共正義觀念,并運用它來調整社會基本制度,那么,在正義制度下生活的公民便會產生充分堅定的正義感,實現正義觀念的穩定性,而這種正義觀念穩定性的實現,也意味著社會合作的穩定性的形成,以及正義制度的穩定性問題的解決。關于這一點,澳大利亞學者庫卡塔斯也有所揭示,他在評論羅爾斯《正義論》第三部分對穩定性問題的探討時說,“一個穩定的社會,是一個接受某一穩定的正義觀念支配的社會。”[3]62顯然,羅爾斯之所以在《正義論》第三部分花費大量篇幅專門論證正義觀念的穩定性,原因就在于此。
但多年以后,羅爾斯終于意識到,自己在《正義論》中對穩定性問題的探討存在很大的問題。因為公平的正義(即兩個正義原則)“有一種憲政民主政體的要求”,[4]xlii由公平的正義所調整的秩序良好的社會顯然是一個崇尚思想自由與良心自由的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社會,那么,它也必然和現實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一樣,會形成一個多種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并存的多元化社會(羅爾斯稱之為“合理多元主義的事實”)。這樣,對公平的正義所調整的秩序良好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來說,人們盡管可以在進入原初狀態后一致接受兩個正義原則,但在這種正義制度下生活的有血有肉的公民卻并不會像在無知之幕遮蔽下的原初狀態中的假想人那樣只接受一種正義觀念,相反,他們持有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而《正義論》對穩定性問題的探究,恰恰是以在公平的正義所調整的秩序良好的社會中生活的公民都堅持體現在正義制度中的“公平的正義”這同一個正義觀念為假設前提的。由于這一假設前提并不現實,因此,羅爾斯在證明公平的正義所調整的秩序良好的社會里人們會形成充分堅定的正義感之前,在邏輯上必須先證明打開無知之幕之后的人以及在這一社會里的世代延續的公民都會“實際接受”支配其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原則,否則,他所設想的這一未來的理想社會,便會缺乏能得到社會各方共同認可的公共正義觀念,而缺乏作為良好秩序之基礎的公共正義觀念,公平的正義所調整的社會當然也并不是一個以社會的持久穩定性(內在穩定性)為特征的秩序良好的社會。正因如此,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認為,穩定性問題不僅僅是《正義論》中所探討的一個正義觀念能否產生充分堅定的正義感的問題,而是包含著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在正義制度(這種正義制度是按照政治觀念來界定的)下成長起來的人是否獲得了一種正常而充分的正義感,以使他們都能服從這些制度;第二,考慮到表現民主社會公共文化特征的普遍事實,尤其是合理多元主義的事實,該政治觀念是否能夠成為重疊共識的核心。[4]141
此外,羅爾斯還意識到,對于公平的正義所孕育的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社會來說,即使人們共同接受某一個正義觀念,但在政治領域,人們仍然會像現實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一樣,會對很多政治問題的解決存在不同的觀點,有時對這些政治問題的爭論還會形成政治沖突甚至可能導致社會的分裂。因此,存在一個共同的公共正義觀念還不能說是解決憲政民主社會持久穩定(內在穩定)的充分條件,要維系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的持久穩定性,還必須對根本政治問題提供正確的解決之道。
由此可見,羅爾斯后期對穩定性問題的闡釋較之《正義論》已有了更為全面更為深入的認識,而與此同時,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所關注的社會穩定性也不再是《正義論》普遍意義上的社會合作的持久穩定性(內在穩定性),而只著眼于以合理多元主義事實為公共政治文化特征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政體中社會合作的持久穩定性了。
二、憲政民主社會持久穩定的條件及其達成
前已指出,在羅爾斯那里,社會或社會合作的穩定性即是指其持久性,因此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一開始就這樣來表述憲政民主社會的穩定性問題:
專業技能課程在教學醫院醫學影像科進行,使“教、學、做”一體化,校內基本技能實訓與臨床崗位對接。第三、六學期的小學期,完全設置為專業技能訓練課,實訓內容與學生任職崗位技能要求緊密對接,實訓操作流程與崗位工作流程緊密對接,構建螺旋式上升的能力訓練體系[2]。
由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們因各種合理的宗教教說、哲學教說和道德教說而產生深刻分化——所組成的正義而穩定的社會如何可能長治久安?[4]4
對此,羅爾斯的回答是:
下述三個條件似乎足以使社會成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們因各種合理的宗教教說、哲學教說和道德教說而產生深刻分化——之間的一種正義而穩定的合作系統:第一,社會的基本結構是由一種正義的政治觀念所調整的;第二,這種政治觀念是各種合理的統合性教說達至重疊共識的核心;第三,當憲法問題和基本正義問題發生危機時,公共討論是按照正義的政治觀念來進行的。[4]43-44
在這里,羅爾斯將調整憲政民主社會的公共正義原則限定為一種正義的政治觀念。所謂正義的政治觀念,就是只適用于政治領域,不涉及人生觀、道德觀和世界觀等廣泛主題并在各種合理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中保持中立的正義觀念。羅爾斯認為,只要我們在構建社會基本制度時以正義的政治觀念為調整憲政民主社會的公共正義原則,生活在這種理想制度下的持合理的統合性教說的公民便都能基于各自的理由認肯這一正義觀念,即他們盡管持有各種各樣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但對調整其政治制度的正義觀念,能形成一種重疊共識。形成了重疊共識,便意味著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社會具有維護社會統一和良好秩序的基礎——公共的正義觀念,由此,當面對憲法問題和基本正義問題這些根本政治問題時,我們便能以具有重疊共識的公共正義觀念為推理前提,運用公共理性合法地行使強制性的政治權力,[4]47-48從而避免政治危機。因此,當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滿足以上三個條件時,便能世代延續,具有持久穩定性。(在1995年《答哈貝馬斯》一文中,羅爾斯將自己所追求的這種與霍布斯模式對立的社會穩定性表述為了“具有正當理由的穩定性”)
(一)正義的政治觀念的建構
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要獲得持久穩定性,調整其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原則必須是一種正義的政治觀念,在這種制度施行后的現實社會中才能為持各種合理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的公民們普遍認可,形成重疊共識,從而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才具有維護社會統一和良好秩序之基礎的公共正義觀念。那么,正義的政治觀念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它又是如何獲得的呢?
根據羅爾斯的界定,正義的政治觀念是具有以下自由主義特征的正義觀念:第一,它具體規定了某些基本權利、自由和機會;第二,它賦予了這些權利、自由和機會以一種特殊的優先性,尤其是相對于普遍善和至善主義價值的優先性;第三,它認肯了各種保證所有公民都有效利用基本自由和機會的充分適于其所有目的的措施。[4]xlvii,223而公平的正義,則是正義的政治觀念的范例。
至于正義的政治觀念或者作為其范例的公平的正義的獲得,羅爾斯說,它并不是我們運用理論理性在自然秩序中發現的客觀真理,而是我們運用實踐理性通過政治建構主義制定出來的以“合理”為評判標準的客觀性觀念。具體來說,就是從現實的憲政民主社會的公共政治文化中抽出隱含其中并為全體公民所共享的兩個基本理念——作為公平合作體系的社會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根據秩序良好的社會的基本要求,把它們結合起來,就可以制定出公平的正義之類的正義的政治觀念,然后我們再把包含正義的政治觀念在內的正義原則清單交給原初狀態中理性而合理的“公民代表”,他們就會一致選擇既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又體現了互惠性的正義的政治觀念(或公平的正義)。
(二)重疊共識的形成
重疊共識是在公平的正義等正義的政治觀念調整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制度下生活的持各種合理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的公民以各自的理由就該正義的政治觀念達成的“非強迫性”的“道德共識”[5]36-37。它意味著在假想的原初狀態中擇出的正義觀念一旦成為支配社會制度的指導原則,可以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得到公民們的普遍認同,成為實際的公共正義原則和保證社會持久穩定的內在力量。但是,人們很容易就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在假想狀態中通過理性選擇勝出的正義原則何以能成為現實社會中有血有肉的公民實際共享的正義觀念呢?在當今憲政民主社會中廣泛存在的自由主義與非自由主義學說之間,以及宗教教義與非宗教學說之間的沖突,能在正義的政治觀念(或公平的正義)調整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中得到調和嗎?或者說,持這些相互沖突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的公民能夠共同認可一種調整社會基本制度的自由主義正義觀念嗎?
羅爾斯認為,作為理性的和合理的公民,他們具有足夠的道德能力和心理力量在正義制度下就正義的政治觀念形成重疊共識,重疊共識不是烏托邦,而是可能的。對此,羅爾斯將重疊共識的形成分為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公平的正義等正義的政治觀念首先從一種純粹的臨時協定變成憲法共識;在第二階段,憲法共識演變為重疊共識。
羅爾斯描述說,在憲法共識的第一階段,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最初是作為一種臨時協定而為人們猶猶豫豫地接受下來并采納到憲法之中的,但隨著自由主義制度的成功實施,公民們就會感激納入制度中的自由主義原則給他們和他們所關心的人以及整個社會帶來的普遍好處,由于公民們的各種統合性宗教、哲學、道德教說事實上是松散的,并且許多教說只具有部分的統合性,這就為發展人們對自由主義正義觀念的獨立忠誠留下了空間,這種獨立忠誠反過來又促使人們有意識地按照憲法安排來行動,從而使他們至少能接受一種自由主義的憲法原則。而當公民們接受保障各種不同自由權利和確立民主政府政治程序的憲法原則時,他們就使自己所持有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變成了“合理的教說”,簡單多元主義就演進為合理多元主義,憲法共識便隨之達成。
那么,憲法共識又如何能趨向對公共正義觀念的重疊共識呢?羅爾斯認為,由于一種純政治的和程序性的憲法共識既不深刻,也不廣泛,無法制定與現存的憲法問題和基本正義問題有關的立法,所以一旦達成憲法共識,就會有各種政治力量推動我們發展出更深刻更廣泛的政治正義觀念。如各政治集團在公共論壇上解釋和正當化他們所偏好的社會政策時,就會系統闡釋一種更為深刻和廣泛的正義觀念;我們為解決新的和根本的憲法問題而進行憲法修改時,圍繞各種憲法修正案產生的爭論會驅使有關政治集團去制定包含正義基本理念的政治觀念;法官或其他審查官在違憲審查中為使憲法解釋具有合理的基礎,也有必要發展出一種正義的政治觀念。當這種內含于正義制度和公共文化中的正義觀念被明確闡發出來后,它便會得到各種合理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的共同支持,從而形成重疊共識。至于這種重疊共識的具體程度,羅爾斯認為它是一類在某種或多或少有些狹窄的范圍內存在變化的自由主義觀念(公平的正義是其范例)——因為憲政民主社會的政治力量和全體公民都共享著憲政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的兩個基本理念——作為公平合作體系的社會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
(三)公共理性的限制
在羅爾斯看來,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要保持持久穩定,它的政府官員、議員、法官在官方論壇上必須接受公共理性的限制。當憲法問題和基本正義問題發生危機時,它的政黨候選人和普通公民在公共論壇上也應當接受公共理性的限制。羅爾斯所謂公共理性的限制,就是在解決根本政治問題的時候,應當遵循共同的推理原則與證據規則,而不應當以自己的統合性教說或個人信念來相互行使強制性的政治權力。
為什么公共理性的限制是實現憲政民主社會穩定性的重要條件呢?這是因為羅爾斯看到了政治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對維護憲政民主社會持久穩定的重要性,特別是人們在憲法問題和基本正義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以致產生政治危機的時候,只有持有各種統合性教說的公民們合法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才能避免政治的分裂與社會的失序。(4)姚大志認為,羅爾斯混淆了合法性與穩定性(參見姚大志:《公共理性與合法性——評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這是沒有正確領悟羅爾斯關于合法性與穩定性關系的結果。那么,持各種統合性教說的公民應當怎樣行使政治權力,才具有合法性呢?對此,羅爾斯并不贊同傳統的單純以遵循多數裁決規則,服從多數人意志為基準的程序合法性觀念。羅爾斯認為,民主公民之間的政治關系具有以下兩個基本特征:第一,政治關系是公民生于其中并在此正常度過終生的社會基本結構內部的一種人際關系;第二,在民主社會中,政治權力乃是一種公共權力,即它永遠是作為集體性實體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們的權力。前者說明政治關系不應當是施密特所說的敵友關系,而應當是一種公民友誼關系。后者表明我們每一個公民對于政治權力都享有平等的份額,一個公民并不能凌駕于另一個公民之上。因此,公民們在進行選舉、投票表決重大法案和政策的時候,都應當以具有重疊共識特性的正義的政治觀念為推理原則,并遵循共同的推理方式,彼此真誠相待,才能為這些根本政治問題的解決提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正當理由。易言之,如果自由主義制度下的公民不接受公共理性的限制,而以自己的統合性教說來行使政治權力,那么投票的結果就只是各種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的糅合,而不具有道德性;同時,公民根據自己的統合性教說來行使政治權力,表面上是在堅持所謂“完整真理”,但由于判斷的負擔,在別人看來實際上只是堅持自己的“信仰”,而根據這種信仰來行使自己的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就侵犯到了其他公民的平等的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
故此,在羅爾斯看來,如果持各種統合性教說的公民在行使政治權力時不尊重公共理性的限制,即使最終在選票上形成了一個多數,但也不具有合法性;而政治權力行使的不合法,就會危害到公民之間應有的相互尊重,破壞公民友誼關系,從而危及到憲政民主政體社會合作的內在穩定性。
三、分析與評論
應當說,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對穩定性問題的重新闡釋相較于《正義論》是更有理論上的完滿性的:他的“重疊共識”理念巧妙地彌補了《正義論》忽視合理多元主義事實而存在的前提錯誤;而“公共理性”的理念,則使羅爾斯《正義論》中的另一個重大疏漏——在公平正義的秩序良好的社會中,人們通過正義感的充分發展在私人領域獲得個人自律(5)羅爾斯后來認識到,《正義論》中的這一觀點也并不成立。See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xliv-xlv.的同時,公共領域必不可少的政治權力又該如何行使——得到了必要的回應。因此,羅爾斯后期對穩定性問題進行重新闡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羅爾斯對穩定性問題的重新闡釋也帶來了諸多問題,這主要有:
第一,羅爾斯為了證明公平的正義所孕育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也存在為人們共同接受的公共正義觀念,提出了“重疊共識”的理念,為了證明在各種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相互沖突的事實下,人們仍然能夠就公共正義觀念形成重疊共識,羅爾斯將公平的正義闡釋成了一種與統合性教說不同的“正義的政治觀念”。但這一闡釋解決的只是形式問題,為了證明持不同教說的公民在現實生活中能實際接受這一政治正義觀念的內容,羅爾斯不得不從寬闡述“正義的政治觀念”,將其界定為一種承認基本自由的優先性和必要的社會保障的自由主義正義觀念,而公平的正義,只是其范例。顯然,對穩定性問題的這一重新闡釋改變了《正義論》以巨大的理論推力將“公平的正義”作為事實上的唯一選項的哲學意圖,羅爾斯已經無法將《政治自由主義》與《正義論》合乎邏輯地協調起來,直白地說,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不是“修改”了《正義論》,而是“推倒”了《正義論》。
第二,盡管羅爾斯正確指出了在憲政民主社會僅有憲法共識的不足而有必要就一種正義的政治觀念達成重疊共識,并洞察到了憲政民主社會發展政治正義觀念的政治力量,但羅爾斯并沒有成功說明持各種相互沖突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如自由主義學說與非自由主義學說、宗教教義與非宗教學說——的公民如何能夠贊成“基本自由的優先性”這一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在羅爾斯看來),盡管這些教說可以共享作為公平合作體系的社會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也可以共同接受寬容原則。
第三,由于正義的政治觀念只適用于政治領域(公共領域),在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社會中,公民的私人領域仍受各種統合性的宗教、哲學和道德教說所支配,因此,公民們對正義的政治觀念的重疊共識也只在公共領域中起作用,即為公民運用公共理性解決根本政治問題提供公共證明的基礎。這樣,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羅爾斯事實上將保持憲政民主社會持久穩定的最終力量寄托在了公民對公共理性的自覺運用上,[4]143公共理性的理念而不是重疊共識的理念才是羅爾斯解決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穩定性問題的正確答案。但是,公共理性在本質上是民主公民的一種政治美德,羅爾斯自己也承認,它可能是一種永遠也達不到的理想。[4]213既然公共理性的理念可能是一種永遠也達不到的理想,那么將公共理性作為政治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礎有何規范意義?羅爾斯以公共理性的理念作為解決憲政民主社會穩定性問題的方案又是否達到了其重新闡釋的理論目的?
在學術界,人們一般也將羅爾斯后期正義理論的不成功轉向歸咎于其對穩定性問題的重新闡釋,于是產生了一種受到廣泛關注的觀點,即認為羅爾斯將穩定性問題納入其正義理論,并沒有必要。[3]160[6-7]我不贊同這種看法。我認為,盡管羅爾斯后期對穩定性問題的重新闡釋并不成功,但羅爾斯將穩定性問題作為其正義理論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卻是完全必要的。首先,正如羅爾斯注意到的,盡管社會正義原則的作用是分配社會合作中的權利與義務,但社會合作的穩定性是一個有效用的正義理論必需予以關注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正義理論的價值追求,因此,對原初狀態中選擇的正義原則能否解決社會合作的穩定性當然是正義理論必不可少的關切與追問;其次,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兩個正義原則在第一階段的證明是通過假想的人在假想的原初狀態中對幾項正義觀念的理性選擇來“反思平衡”的,這種論證方式在范圍上和證明效力上都是有限的,而在證明的第二階段,它是通過“合理的道德心理學”來論證現實的人在人性的極限內能否接受兩個正義原則,如果證明成功,顯然就彌補了第一階段證明力疲軟的問題,對第一階段的證明起到了客觀的強化作用。
穩定性問題盡管是正義理論的應有關懷,但對于羅爾斯這樣一個成熟的哲學家來說,他當然知道在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語境下探討這一問題的艱巨性,可羅爾斯為什么不惜推翻自己精心構筑的《正義論》的理論大廈,在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社會的穩定性問題上殫精竭慮,將自己最后二十年的哲學思考都聚焦于此呢?這源于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制度長期以來的信仰危機。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擺脫宗教禁錮的世俗化基礎上的,但早在19世紀初,法國著名保守主義者梅斯特爾就斷然否認了自由主義制度能夠持久,因為他認為宗教沒落以后那些信奉個人化的價值觀的人們無法創造具有一致性的秩序。現代著名學者列奧·施特勞斯和羅伯托·昂格爾也持這樣的看法。施特勞斯認為世俗化是西方的危機,使人脫離上帝的企圖是“通向虛無之途”,是一條通往深淵的道路。昂格爾抱怨說自由主義創造了一個不安穩的社會,其主要標志就是“對一切共同價值的不穩定性和偶然性的體驗”。[9]18-19,27,200羅爾斯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堅信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宗教自由)是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的基礎和底線,盡管自由主義所導致的思想觀念的多元化與社會穩定所要求的正義觀念的公共性形成了明顯的悖論,也導致人們對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制度的信仰危機,但羅爾斯堅定地認為,對“正義而秩序良好的憲政民主是否可能?”[4]lxi這一現代性的憂思,知識界必須在理論上做出肯定的回答。羅爾斯說,如果我們不能為一種正義而穩定的憲政民主提出一種令人信服的論證,像魏瑪時期的德國傳統精英不相信自由主義議會政體那樣不相信憲政民主政體的話,憲政民主政體就必然不能形成可以構建其道德基礎的公共政治文化,而其最終的結果,就會像魏瑪政體一樣由于缺乏民眾的支持而走向崩潰[4]lxi-lxii[10]167。可見,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之所以脫離《正義論》,殫精竭慮地以合理多元主義事實為前提對穩定性問題進行重新闡釋,其根本意旨乃在于回應上述保守主義的憂慮,為西方現行的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提供辯護。[8]5[2]39而其論證的不成功,折射的則是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本身的硬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