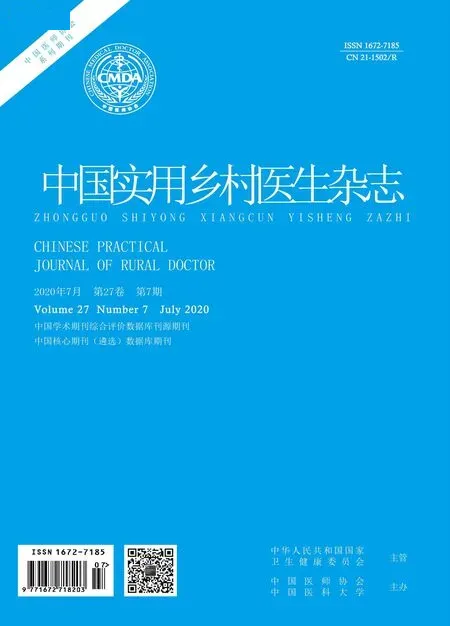艱難梭菌性腹瀉與藥物相關危險因素研究綜述
韓偉娜
作者單位:110021 沈陽,沈陽市鐵西區婦嬰醫院兒科
艱難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 CD)于1935年首次被描述,這種細菌在健康新生兒糞便標本中發現,直到1978年才首次與疾病相關。艱難梭菌是引起一系列抗生素相關性結腸炎(AAC)的主要因素之一,范圍從輕度腹瀉到中毒性巨結腸[1]。由于廣譜抗生素的普遍使用,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此類慢性病的折磨。
艱難梭菌相關疾病(CDAD)的發病率和嚴重程度在北美和歐洲正在增加。在過去的10年中,美國CDAD患者的患病率、病死率、總歸因死亡率和結腸癌切除率明顯增加[2]。
雖然艱難梭菌感染病例在中國日益引起關注,但是卻很少報告關于艱難梭菌感染的危險因素。為了對艱難梭菌性腹瀉有更好的認識,本文從艱難梭菌性腹瀉的發生機制和藥物引起的艱難梭菌性腹瀉相關危險因素進行綜述。
1 艱難梭菌性腹瀉發病機制
艱難梭菌的致病性中最重要的兩個毒素是毒素A和毒素B,兩種毒素的TcdA和TcdB基因均被編碼,并與兩個調節基因(TcdC和TcdR)相關聯。TcdE對高毒力菌株(027型)分泌TcdA、TcdB是必要的[3]。毒素A通過釋放白三烯,前列腺素2(PGE2)和腫瘤壞死因子α以及中性粒細胞遷移而產生嚴要的炎癥反應[4]。毒素B通過狹窄連接的改變,流向上皮細胞的基底外側。兩種毒素的作用都導致嚴重的上皮損傷,伴有細胞水腫和大量的腔分泌物(分泌性腹瀉)[5]。毒素在內體中被內吞并激活,然后使Rho蛋白糖基化,改變肌動蛋白連接,產生細胞毒性作用并改變腸屏障[6]。肌動蛋白解聚和細胞壞死,觸發炎癥級聯反應,破壞細胞間緊密連接,使腸道黏膜通透性增加,導致組織損傷、腹瀉以及偽膜性結腸炎[7]。
Warny M等[8]認為NAP1/027型是一種艱難梭菌的流行菌株,與嚴重疾病相關疫情有關。在N A P1/027中,毒素濃度在穩定期早期達到峰值,表明大部分毒素產生在對數階段。發現NAP1/027產生的毒素A是對照菌株的16倍,毒素B是對照菌株的23倍。如果體外毒素A和毒素B的比例在結腸腔中相似,則NAP1/027的毒力菌株可能主要源于毒素B的產生而增加。毒素A(TcdA)與毒素B(TcdB)的蛋白結構和宿主六磷酸肌醇(IP6)介導的激活機制相似,但毒素B誘導細胞凋亡的毒性至少為毒素A的100倍[9]。
包括NAPI/027型在內的約17%~23%的CD產毒株可分泌CD二元毒素(CDT)[10]。核糖體027型流行病菌株的出現,其表現通常更為嚴重,與定植相比感染率增加,復發率更高,敗血癥、中毒性巨結腸、腸穿孔的發生率和死亡率更高。腹瀉患兒中該菌株的分離率為10%~19%[11]。
2 艱難梭菌腹瀉危險因素
最常與艱難梭菌感染(CDI)相關的抗菌藥是克林霉素、青霉素和頭孢菌素[12]。也許是由于住院患者和門診患者使用氟喹諾酮類藥物的增加,這類藥物的使用最近被認為是CDI的一個危險因素。
2.1 克林霉素 克林霉素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被廣泛使用,是治療厭氧菌感染的首選藥物。然而,在1977年,一種克林霉素耐藥、產毒艱難梭菌菌株被鑒定為倉鼠克林霉素相關性結腸炎的病因[13]。首批涉及克林霉素耐藥艱難梭菌性腹瀉暴發于1989年,隨后在1990年代初暴發了3次更嚴重的情況。這些研究證實了克林霉素增加了CDI的風險。Johnson S等研究證實了在美國不同地區的四家醫院爆發的大規模腹瀉都是由一種對克林霉素高度耐藥的艱難梭菌株引起的,并且克林霉素的使用是一個特定的風險因素,其中只有15%的非流行菌株對克林霉素有高水平的耐藥性。結果表明,接觸克林霉素后艱難梭菌相關性腹瀉發生的相對較高可能性不僅是對駐留菌群的影響,也可能與機體的易感性有關。這種疾病的風險隨著克林霉素的使用和克林霉素耐藥艱難梭菌菌株的存在而增加[14]。
2.2 頭孢菌素 第一代頭孢菌素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被批準在北美使用,并迅速獲得處方認可。頭孢菌素暴露很快成為CDI暴發的一個強有力的風險因素。艱難梭菌對大多數頭孢菌素完全耐藥[15]。使用第二代和第三代頭孢菌素,如頭孢呋辛、頭孢他啶、頭孢噻肟和頭孢曲松,與CDI的特別高風險相關。Riley TV等[16]研究發現,在西澳大利亞州,一家醫院通過禁止使用第三代頭孢,導致在1999—2000年三代頭孢使用量減少,CDAD發生率降低了50%,并使用時間序列干預分析法分析了第三代頭孢使用政策對CDAD發生的影響,結果顯示,控制外源因素后,干預后的CDAD發生率在統計學上有顯著下降。因此,抗生素處方做法的變化會影響CDAD的發生率,并可能影響抗生素耐藥性病原體。
2.3 氟喹諾酮類藥物 與頭孢菌素類似,氟喹諾酮類藥物因其良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活性光譜而成為治療住院和門診患者的常用抗菌藥。自引入環丙沙星以來,氟喹諾酮類藥物的使用頻率不斷增加,應用變得廣泛[17],此類藥物還有加替沙星、吉米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和氧氟沙星等。氟喹諾酮類藥物的使用與CDI的暴發有關,報告的OR值和相對風險范圍為2.0~12.7[18-19]。Loo等[20]報告了由氟喹諾酮耐藥艱難梭菌(即BI/NAP1)的主要菌株引起的CDI發病率增加,發病率和死亡率相對較高,在超過1 700名接受評估的患者中,隨機選擇15%進行病例對照研究,以確定發生CDI的危險因素。自2001年以來,BI/NAP1菌株在北美至少8次暴發中以不同的頻率被分離出來,這些暴發中的分離株對所有測試的氟喹諾酮類藥物都具有完全的耐藥性[21]。氟喹諾酮類藥物的暴露被描述為CDI的獨立危險因素[22]。在一些研究中,艱難梭菌中氟喹諾酮耐藥性的獲得與DNA促旋酶活性位點的突變有關[23-25]。
2.4 組胺2阻滯劑(H2RAs) Tleyjeh IM等[26]在嚴格的系統綜述和薈萃分析中觀察到H2RAs和CDI之間的關聯。在接受抗生素治療的住院患者中,CDI與H2RAs相關的絕對風險最高,另一方面,證實了H2RAs在普通人群中作為非處方藥使用不會明顯增加CDI的發生風險。胃酸抑制的程度可能在增加感染風險中起重要作用。Kwok等[27]從15項研究中比較了CDI與胃酸抑制的風險,這些研究報告了獨立于參與者樣本的質子泵抑制劑(PPI)和H2RAs估計值,發現兩者都會增加風險,與H2RAs相比,PPI具有更高的感染風險。H2RAs也可能通過減少細胞增殖,抑制炎癥介導的一氧化氮濃度,通過影響結腸愈合和改變細胞因子產生來影響腸道免疫系統[28-29]。此外,維持結腸內源性細菌平衡可以防止腸道感染,胃酸減少已被證明可以改變較低的腸道菌群[30-31]。結腸細菌的改變可能增加CDI的發生風險[32]。
2.5 質子泵抑制劑 PPI和H2RAs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有效藥物。因此,它們可能與上消化道內菌群改變有關,并導致諸如吸收不良、腸感染和胃腸道外感染等并發癥[33]。Dial等[34]在兩項不同的研究中發現,PPI的使用與艱難梭菌感染的風險增加獨立相關。Turco R等[35]研究證實,PPI治療是CDAD的相關危險因素,其風險比為4.8。PPI治療是成年人和兒童CDAD的重要危險因素。盡管抗分泌藥物在預防和治療上消化道癥狀方面有明顯的好處,但醫療保健提供者應考慮抗艱難梭菌感染的風險。Nylund CM等[36]研究發現PPI和H2RA都與兒童和青少年CDI和CDI復發的風險增加有關,證實了CDI在兒科年齡組中的增加趨勢。特別是在CDI風險增加的患者中,應慎重使用胃酸抑制藥物。
3 小結
本文對艱難梭菌的發病機制以及抗生素、PPI和組胺H2RAs存在的危險因素進行了分析,盡管抗菌藥物對治療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破壞了腸道內微生物平衡,可能引起感染復發。因此,在臨床中治療腹瀉病應該注意處方藥的平衡與劑量,避免藥物帶來的風險。益生菌、盲腸造口術進行沖洗或結腸切除術治療艱難梭菌腹瀉是當前和未來的研究方向,隨著研究的深入,艱難梭菌腹瀉病的危險因素會有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