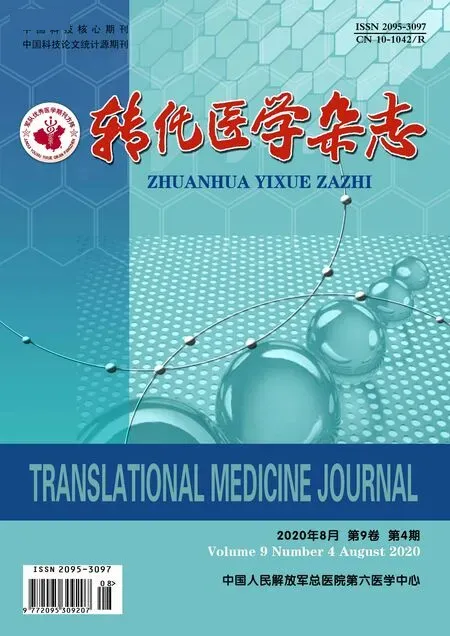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抗腫瘤療效與腸道微生物的關系
周冠舟,張曉梅,郭明洲,楊云生
近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研究獲得了較大進展,使用anti-PD-(L)1/anti-CTLA-4等藥物已逐漸成為多種惡性腫瘤(如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等)的治療中不可或缺的一種方案,惡性腫瘤患者的生存期獲得了明顯的延長。但目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有效率不高,不同患者對治療的反應也具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于anti-PD-1及anti-PD-L1治療的有效性,包括對其療效的預測以及改善其耐藥性等。一些研究指出腫瘤細胞表面PD-L1的表達數量、腫瘤突變的負荷以及腸道微生物的組成結構等都可以成為免疫治療的生物標志物[1]。人體內的細菌總數約為1013,大部分定植于腸道內[2],通過與腸腔內免疫細胞的直接作用,生成并分泌多種代謝小分子而誘導產生細胞因子并作用于局部或全身的免疫系統,起到調節機體免疫的作用。腸道微生物可能影響到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作者旨在闡述腸道微生物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研究現狀,探討提高其療效的可能性。
1 抗生素對腫瘤患者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影響
惡性腫瘤患者的免疫功能通常處于受損或低下的狀態,容易感染各類病原體,導致嚴重的臨床癥狀。一項使用anti-PD-L1的腎細胞癌及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中[3],121名腎細胞癌患者有16名患者接受了抗生素治療(其中大部分是β-內酰胺酶抑制劑),接受抗生素治療患者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為1.9個月,總生存期為17.3個月,而未接受抗生素治療的患者,其中位無進展生存期為7.4個月,總生存期為30.6個月,2組之間的差異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于239名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有48名患者在使用PD-1治療的一個月內接受了抗生素治療,其中位無進展生存期為1.9個月,總生存期為7.9個月,與未使用抗生素的患者比較(中位無進展生存期為3.8個月,總生存期為24.6個月),2組之間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考慮到抗生素影響菌群可能持續1~3個月,研究者以初次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以前60 d內是否使用抗生素對患者再次分組,結果發現腎細胞癌患者使用抗生素組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3.1個月)及中位總生存期(23.4個月)均低于未使用抗生素患者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7.4個月與中位總生存期30個月),差異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于非小細胞肺癌患者,2組中位總生存期差異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9.8個月vs 21.9個月,P<0.05)。此外,研究中提出腫瘤負荷也是影響腎細胞癌患者無進展生存期的相關因素,且與抗生素的使用獨立相關。一項納入了249例非小細胞肺癌等惡性腫瘤的研究顯示[4],有69名患者在接受腫瘤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同時使用了抗生素,其無進展生存期及總體生存期均低于未使用抗生素組。Zhao等[5]回顧了109例使用anti-PD-1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資料,有20名患者在初次使用anti-PD-1的前后30 d內使用了抗生素,主要原因為肺炎或尿路感染,而使用的抗生素種類主要為β-內酰胺類或氟喹諾酮類;抗生素組患者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為3.73個月,而無抗生素組為9.63個月;抗生素組患者的中位總生存期為6.07個月,而無抗生素組為21.87個月。此方面研究也存在不同結果,一些研究顯示抗生素使用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臨床療效呈現負相關。Sen等[6]的研究發現抗生素的使用可以造成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惡性腫瘤患者總生存期的縮短,但是對無進展生存期沒有明顯影響;Ueda等[7]研究表明抗生素可以降低腎細胞癌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而不會對總生存期造成影響。另外,抗生素的種類、劑量、使用時間的長短、用藥方式等因素是否會造成不同的臨床結局,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2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效與腸道菌群結構的關系
Frankel等[8]收集了使用anti-PD-1治療黑色素瘤患者的糞便,宏基因組測序結果提示,對于anti-PD-1反應良好的黑色素瘤患者其腸道菌群中Bacteroidescaccae菌以及Streptococcusparasanguinis菌相對豐度更高。對于使用不同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黑色素瘤患者,在療效類似的情況下,不同治療藥物所對應富集的腸道菌群種類有所不同。聯合使用ipilimumab和nivolumab反應良好患者,其Faecalibacteriumprausnitzii菌相對豐度會更高,而使用pembrolizumab的患者對應的是Doreaformicigenerans菌。一項關于中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研究表明[9],對于anti-PD-1的療效反應與其腸道菌群的α多樣性密切相關,反應良好患者的腸道菌群α多樣性高于無反應患者,差異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2者腸道菌群的β多樣性也存在差異,但差異比較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使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期間,患者的腸道菌群結構保持相對穩定,并且療效好的患者外周循環中有著更高的GZMB+CD8+Tm、Ki67+CD8+Tm和CD8+Tcm細胞,提示更豐富的腸道菌群可能誘導更強的免疫應答,產生較高水平的相關免疫細胞,加強機體的免疫效應。Chaput等[10]分析了使用ipilimumab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腸道菌群,結果表明對于ipilimumab治療反應差的患者腸道菌群中Bacteroides菌的相對豐度較高,而反應良好的患者其腸道內Faecalibacterium菌的相對豐度更高,并且其外周血中Treg細胞含量較少,α4+β7+CD4+/CD8+細胞比例更低。Treg細胞能表達CTLA-4,與ipilimumab相結合,起到抑制免疫的作用。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腸道菌群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療效也有相關性。Zheng等[11]將使用anti-PD-1治療的8名原發性肝細胞癌患者分為反應良好組(包括完全或部分緩解)及反應較差組(包括疾病進展和疾病穩定),糞便樣本的宏基因組測序結果顯示,與反應較差組比較,反應良好組的腸道菌群表現出更高的種群豐富度及基因計數;在使用anti-PD-1治療之前,2者的腸道菌群組成是類似的,擬桿菌門占據腸道菌群的主要地位,其次是厚壁菌門以及變形菌門;而比較2者在治療后的腸道菌群,擬桿菌門在反應較差患者中的豐度明顯降低,變形菌門的豐度逐漸上升并占據主要地位,且其主要組成為Escherichiacoli;而反應良好組患者的腸道菌群和治療前無明顯差別。在菌種水平,反應良好患者腸道菌群中豐度較高的菌種如4種乳酸桿菌種(L.oris,L.mucosae,L.gasseriandL.vaginalis),這些菌種常被認為是益生菌,產生乳酸,抑制病原體生長,從而有助于宿主的代謝與免疫;在反應良好組患者腸道內,一些與膳食纖維的消化利用及短鏈脂肪酸的產生密切相關的菌種含量也相對較高(Coprococcuscomes,Bacteroidescellulosilyticus)。Sivan等[12]給JAX和TAC 2種小鼠分別接種B16.SIY黑色素瘤,并使用anti-PD-L1來治療,結果發現腫瘤在TAC鼠中生長體積明顯大于JAX鼠,而將JAX鼠的糞便移植入TAC鼠后,表現出和JAX鼠同樣的抗腫瘤效應,而比較移植了JAX鼠糞便的TAC鼠和普通的TAC鼠2者腸道菌群,發現Bifidobacterium種存在著顯著差異;如果直接給TAC鼠補充Bifidobacterium菌種,也可以改善TAC鼠的抗腫瘤效應。
3 抗生素、腸道微生物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關系
人體的腸道中有大量的細菌,較其他部位更易受到抗生素的影響。抗生素的使用破壞了原有的腸道菌群,從而產生相應的臨床結果(如抗生素相關性腹瀉)。近幾年,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腸道菌群似乎在抗生素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效的關系中扮演著橋梁的角色。Vétizou等[13]將接種了MCA-205肉瘤并接受anti-CTLA-4治療的小鼠分為2組,發現使用了抗生素的小鼠組肉瘤體積明顯大于未使用抗生素組,而補充Bacteroidesfragilis等菌種可以恢復部分anti-CTLA-4的治療效果。
Gopalakrishnan等[14]將使用anti-PD-1治療的黑色素瘤患者按照臨床療效分為有效組和無效組,對2組患者的腸道菌群進行分析發現其在物種豐富度,α或β多樣性以及菌群組成方面均存在差異。其中,在反應良好患者腸道菌群中,Faecalibacterium屬含量更高,而反應差的患者腸道中含有更高的Bacteroidales目。而將2組患者的糞便分別移植到小鼠腫瘤模型中,出現了類似的結果,即移植了反應良好組患者糞便的小鼠,其腫瘤生長速度低于無效組,并且小鼠的腸道菌群中含有更高的Faecalibacterium屬。研究指出,如果患者腸道菌群中含有更高的Faecalibacterium屬,其外周循環中CD4+CD8+效應T細胞含量更高,而高含量的Bacteroidales目會伴隨高水平的Treg細胞以及髓樣抑制細胞,這些細胞發揮著免疫調控及抑制的作用。免疫組化分析結果也顯示反應良好組患者的骨髓微環境中免疫細胞的密度更高,提示其具有一個更活躍的免疫微環境。
一項關于使用anti-PD-1治療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結果顯示,反應良好患者的腸道菌群中有著更多的Bifidobacteriumlongum菌、Collinsellaaerofaciens菌、Enterococcusfaecium菌等,而這些細菌都可以造成循環中Treg細胞數量的下降,從而影響機體的免疫系統,提高其抗腫瘤作用[15]。將2組患者的腸道菌群移植到接種了B16.SIY黑色素瘤的小鼠時,發現有2/3的小鼠對于anti-PD-1的治療表現出與其供體一樣的反應,而那些與供體的療效反應有差別的受體小鼠,其腸道菌群的組成也與相應的供體有顯著差別。
Routy等[16]分別比較了抗生素的使用對于3種接受anti-PD-1治療的不同腫瘤患者療效的差別,包括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以及尿路上皮癌,結果發現,3種不同腫瘤中,使用了抗生素的患者其無進展生存期和總體生存期均低于未使用抗生素組。腸道菌群的分析結果提示,未使用抗生素的患者的腸道中Akkermansia菌的含量高于使用抗生素的患者。研究中使用這2組患者作為供體,分別將其糞便移植入預先使用廣譜抗生素處理過的小鼠腸道內,并給小鼠接種MCA-205肉瘤,發現供體對anti-PD-1反應良好的小鼠腫瘤生長速度也較緩慢,且其外周循環中CXCR3+CD4+T細胞水平較高,脾臟T淋巴細胞的PD-L1表達也上調。而移植了療效較差的供體糞便的小鼠,其腫瘤生長速度明顯快于另一組。當給應答不良的小鼠補充Akkermansia菌時,可以恢復anti-PD-1的療效,并且直接給使用了廣譜抗生素處理的小鼠補充Akkermansia菌也可以提高其應答水平,提示Akkermansia菌可能在抗腫瘤免疫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4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抗腫瘤機制的研究
在應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抗腫瘤治療以來,一些惡性腫瘤的無進展生存期獲得了明顯的延長,但一部分患者對其反應較差或顯示抗藥性,機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來源于腫瘤內部,也可能與患者自身因素相關。如某些腫瘤細胞可以直接上調自身PD-L1的表達水平,與PD-1結合,產生免疫抑制效應。某些腫瘤細胞自身可以產生能夠分解代謝色氨酸的相關酶,而色氨酸是T細胞克隆增殖的重要氨基酸,色氨酸的減少可以造成T細胞的功能障礙與凋亡。宿主的某些因素也會造成腫瘤細胞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耐藥性,如隨著患者年齡的增高,伴隨免疫功能的下降,宿主人類白細胞抗原的類型及腸道菌群的結構也會影響其藥物的應答水平[17]。
腸道菌群可以通過自身與宿主免疫系統的直接反應調節機體免疫,如Bacteroidesfragilis菌表面的多聚糖與腸道固有層的CD11b+DC結合,激活依賴于IL-12的Th1細胞免疫反應,促進腫瘤內環境中CD細胞的成熟[13]。Balachandran等[18]在腫瘤內環境及外周循環中發現了同時具有針對細菌抗原表位以及腫瘤抗原的交叉活性的T細胞,可以推測,腸道中某種細菌通過自身抗原結合并激活T細胞,這種活性狀態的T細胞同時具有抗腫瘤細胞的特性,能夠通過輔助免疫作用(如Th細胞)或直接殺傷效應(如Tc細胞)作用于腫瘤細胞。某些菌群含有的CpG寡脫氧核苷酸序列與toll樣受體9結合,激活樹突狀細胞,刺激生成一系列細胞因子如IL-12,從而增加CD8+T細胞數量,下調PD-1表達,發揮抗腫瘤效應[19]。Tanoue等[20]發現了一個包含有11種菌株的共生體,其可以定植于結腸上皮細胞,刺激細胞Ki67基因表達,使上皮細胞進入到活躍的增殖階段,并通過細菌抗原與特異性受體相結合刺激其分化,增加IFNγ+CD8+T細胞數量,從而增強anti-PD-1效果。某些腸道菌群還能通過一些小分子物質如細胞因子或者某些代謝物如短鏈脂肪酸等調控機體的免疫效應[21]。Jenkins等[22]報道,與對照組比較,使用抗生素而導致腸道菌群紊亂的黑色素瘤小鼠,無論是在腫瘤微環境或是外周循環中,腫瘤壞死因子-α水平顯著降低,從而導致腫瘤內皮粘附因子尤其是胞內粘附分子-1濃度下降,抑制了CD8效應T細胞的活化,腫瘤進展明顯增快;而對實驗組補充腫瘤壞死因子-α,可以檢測到胞內粘附分子-1水平的上升,并且腫瘤微環境中浸潤的白細胞數量也增多。短鏈脂肪酸是腸道中重要的細菌代謝產物,其可以與G蛋白偶聯受體結合,調控相應基因表達,參與調節免疫細胞的募集,減少Treg細胞的生成,從而影響機體的免疫應答[23]。乳酸桿菌利用色氨酸產生的一系列代謝物(如吲哚-3-甲醛),可以激動芳香烴受體,影響免疫細胞功能[24]。分段絲狀桿菌能通過3型先天淋巴樣細胞提高體內IL-22水平[25],進而調節細胞分化,改變機體對于anti-PD-1治療的反應。
5 展望
惡性腫瘤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已經成為當前腫瘤治療領域最具有前景的研究之一,但仍然面臨著有效率較低,相關生物標志物準確性較差等挑戰。腸道微生物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影響初步觀察到一些結果,改善惡性腫瘤患者腸道微生物的失衡狀態也逐步受到臨床醫師的重視。目前來說,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存在研究結果的不一致,還缺乏有說服力的臨床研究,腸道微生物影響抗腫瘤免疫的機制還未能完全闡釋清楚。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更大的樣本量以及更深入的菌群分析,同時考慮宿主、腫瘤以及腸道微生物三者間的相互關系,以闡明其具體機制,指導臨床決策,改善腫瘤患者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