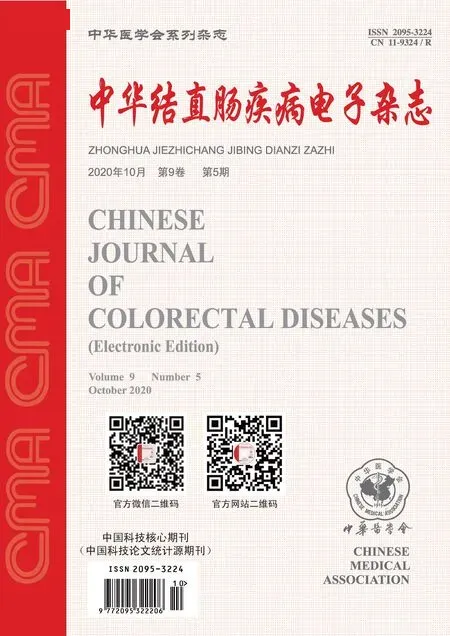直腸癌新輔助治療后病理完全緩解的預測進展
鄒雨恒 劉健博 汪曉東 李立
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報道,新輔助治療可使局部進展期直腸癌(local advanced rectal cancer,LARC)中8%~35%的患者達到病理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1]。精準預測pCR能為下一步個性化治療及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提供依據。本文就此展開對既往研究報道的回顧和總結。
一、病理特征
(一)基因/分子特征
就目前多項研究從分子/基因機制對新輔助治療后pCR進行預測來看,影響pCR的因素是多樣的,他們可能共同對pCR進行調節。有幾項研究從miRNA與pCR的關系進行了研究:Du等[2]通過基因芯片發現pCR組和非pCR組相比,手術標本中36種miRNA表達水平上調,5種miRNA表達水平下降。其中,miR-548c-5p、miR-548d-5p和miR-663a與pCR顯著相關,對于其可能的機理分析為miRNA通過調節干細胞多能性和泛素介導的蛋白酶解發揮作用,還可能調節與直腸癌相關的基因,包括白細胞介素(IL)-6信號轉導子(IL6ST)、細胞周期檢查點激酶2(CHEK 2)、Ki-67,通過調節細胞凋亡進而提高pCR率。Kheirelseid等[3]的研究認為新輔助放化療前失調的miR-16和下降的miR-153降低了pCR,聯合miR-16、miR-153和miR-590-5p對pCR進行預測中位準確度100%。現階段盡管有對于miRNA為基礎的pCR預測研究,但是都還停留在嘗試階段,樣本量小,未對機制機理提出更有價值的結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除了miRNA,還有部分研究從影響細胞增殖、衰老的表達產物,利用新輔助治療前活檢標本的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對pCR進行預測。Martinez-Useros等[4]從p38-MAPK信號通路發現DEK與磷酸化的p38表達相關(P=0.027),高表達的DEK具有預測pCR的潛在價值(P=0.023)。Peng等[5]從線粒體凋亡途徑提供了另一種預測pCR的思路,表達水平高的APAF-1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OR=5.291,95%CI:1.342~13.699;P=0.014)。還有研究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家族及配體探究其與pCR的關系,Kundel等[6]的研究納入47例患者,發現免疫組織化學標本中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增長1個百分點時,pCR增加3.9%,可作為連續性指標對pCR進行預測,但Yu等[7]的研究表明作為預測因子的應該是血管內皮生長因子(OR=1.77,95%CI:1.10~2.85;P=0.001),而不是表皮生長因子受體(OR=1.27,95%CI:0.94~1.71;P=0.11)。
在基因突變/多態性的研究上,一項研究探究了單核苷酸多樣性對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代謝的影響,5-Fu靶向的腺苷酸合酶(thymidylate synthase,TS)由2R/3R基因控制,等位基因3R的第二個重復單位可能突變為3G基因或3C基因,當至少含有一個3G基因,就更可能實現pCR[8]。KRAS基因突變分析也得到了廣泛的報道,但是否進行靶向治療及靶向治療的方案會影響pCR。在不進行靶向治療時KRAS突變意味著更難實現pCR(OR=0.34,95%CI:0.17~0.66,P=0.002),尤其是G12V和G13D突變[9];在mFOLFOX6的基礎上,KRAS野生型使用西妥昔單抗,KRAS突變型使用貝伐珠單抗的pCR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36)[10]。也有研究顯示在使用西妥昔單抗、卡培他濱和局部放療的情況下KRAS突變與pCR無關(P=1.000)[11]。基因多態性對pCR的研究還包括:Sebio等[12]納入84位患者的研究表明編碼雙調蛋白(AREG)基因中的rs11942466 C>A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OR=0.26,95%CI:0.06~0.79;P=0.0149), 而研究中選擇的表皮生長因子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的單核苷酸多樣性位點均未能預測pCR(P>0.05)。
(二)血液相關指標
1.血紅蛋白(hemoglobin,Hb)
Hb水平和血液中的含氧量有關,有一種推測為腫瘤組織含氧量充分是腫瘤組織氧合的重要因素進而可影響腫瘤對放療的反應,故有很多研究探究了Hb對pCR的預測能力,但不同研究顯示Hb對pCR的預測存在矛盾,Hb對pCR的預測能力及預測模式還需要更多探討。
在一項將Hb作為連續變量的分析表明,Hb≥ 140 g/L(P=0.03)和 150 g/L(P=0.03)均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13]。一個單中心的研究表明,術前Hb水平在pCR和非pCR中有顯著不同(13.68 g/dL vs.13.20 g/dL,P=0.04),但不具有 相 關 性(P=0.271)[14]。Krauthamer等[15]的研究中,以12 g/dL作為臨界值與pCR無關,無論是臨床Ⅱ期還是臨床III期(P>0.05)。
但一項數據量大的回顧性研究表明,手術前貧血(男性Hb<7 mmol/L,女性Hb<6.5 mmol/L)的患者更可能實現pCR(OR=1.28,95%CI:1.04~1.57;P=0.019)[16],機理尚不清楚,一個可能的推測為貧血導致瘤內缺氧和腫瘤對電離輻射的抵抗力降低,但尚無實驗證實。
2.中性粒-淋巴細胞比例(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
高NLR是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的標志,但NLR對pCR的預測價值有限,無論是在治療前還是治療后:Runau等[14]的研究表明,pCR和非pCR的患者之間NLR值有差異(4.352 vs.5.241,P=0.001),但不能作為pCR的預測因子(OR=1.067,95%CI=0.914~1.246;P=0.410)。將NLR從1.8~4.2每0.2為間隔作為臨界值的研究中,所有臨界值都不能預測pCR(P>0.05)[13]。對臨床分期為III期的局部直腸癌患者NLR<5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OR=2.54,95%CI:1.52~4.18;P=0.04),但在臨床分期為II期的患者中無預測能力(OR=1.12,95%CI:0.86~2.83;P=0.49)[15]。僅有一項研究表明NLR≤4.564可預測pCR(OR=4.564,95%CI:1.226~16.993;P=0.024)[17]。但可以確定的是,低NLR和更好的腫瘤反應有關[13-14,18]。
3.腫瘤標記物
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是與細胞黏附密切相關的糖蛋白,作為廣譜腫瘤標志物,雖然不能作為診斷某種惡行腫瘤的特異性指標,但臨床上常使用該指標進行惡性腫瘤的鑒別診斷,病情監測,并且CEA值獲取方便。
在用CEA對pCR預測的多項回顧性研究中,較低CEA水平與pCR有關。可參考新輔助治療前、后的CEA進行pCR的預測。
CEA的臨界標準尚未確定,新輔助治療前CEA<5 ng/mL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Lee等[19]的研究結果為(OR=2.921,95%CI:1.365~6.253;P=0.006),Wallin等[20]的研究結果為(OR=0.90,95%CI:0.81~1.00;P=0.04)。Li等[21]的研究認為CEA≤3.35 ng/mL可預測pCR(OR=1.427,95%CI:1.192~1.709,P < 0.001,AUC=0.785)。
另有研究表明新輔助治療后的CEA是pCR的預測因子:CEA≤2 ng/mL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OR=1.579,95%CI:1.026~2.432;P=0.038)[17]。Kalady等[22]的研究中pCR患者和非pCR患者的CEA出現統計學上顯著不同(2.1 ng/mL vs.3.0 ng/mL,P=0.03),但差異小于1 ng/mL,在臨床上預測pCR的價值有限,以2.5 ng/mL為臨界值不具有預測能力(OR=0.58,95%CI:0.25~1.35;P=0.21)。
在一組研究中,對pCR具有預測價值的是新輔助治療前后的CEA的變化值,治療開始前7天內和治療開始后每2周進行測量,將實際的CEA降低水平與理論值(認為CEA變化規律服從經典指數動力學格式)進行曲線模擬,0.9<R2≤1可預測pCR:訓練組:OR=8.30,95%CI:1.56~44.17,P= 0.013,AUC=0.73;驗證組:OR=5.22,95%CI:1.02~26.60,P=0.047,AUC=0.69[23]。
值得注意的是,在考慮到吸煙因素時,低CEA僅與不吸煙者的pCR顯著相關(不吸煙pCR組CEA=2.9 ng/mL,95%CI=2.0~3.8 ng/mL vs.不吸煙非pCR組CEA=8.3 ng/mL,95%CI=5.8~10.7 ng/mL,P=0.022;吸煙 pCR組CEA=7.0 ng/mL,95%CI=1.9~12.0 ng/mL,吸煙非pCR組CEA=14.8 ng/mL,95%CI=8.9~20.6 ng/mL,P=0.31)[15],鑒于吸煙對腫瘤放化療有負面影響,吸煙者的CEA水平較高[24],吸煙者的CEA水平與pCR無關。其他的幾項研究發現,治療前或治療后CEA不能用于預測pCR[23,25],但這些研究都未考慮患者吸煙與否。總體來說,較低的CEA水平和更好的腫瘤緩解有關,但臨界值的選擇仍存在爭議,并需要結合患者是否吸煙的背景來進行考慮。
另外Song等[26]的研究提示新輔助治療前后CA19-9之比<1.28可作為緩解的預測因子(r=0.38,OR=1.463,95%CI:1.001~2.137;P=0.049)。未見其他腫瘤標志物(CA125,CA153等)的報道。
(三)影像學特征
1.緣距(distance of tumor from the anal verge,DTAV)
多項研究表明,DTAV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但臨界值尚未確定且存在多種預測模式,不同預測模式的預測結果可能出現矛盾。一項將DTAV作為連續變量的研究認為DTAV越大,越可能實現pCR,其優勢比為DTAV每cm增加1.046倍pCR[14]。與之矛盾的是,Ren等[25]和Peng等[17]的研究以5 cm為標準來區分高位癌和低位癌,并提示低位癌雖然不能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5),但與更高的pCR相關(P=0.024;P=0.044)。另一項以5 cm為標準的研究表明DTAV與pCR之間無關(P=0.464)[27]。從4 cm開始,每2 cm進行DTAV分割的研究指出DTAV<4 cm或>8 cm,更難實現 pCR(P=0.008)[28]。
2.腫瘤長度(tumor length,TL)
TL越小越可能實現pCR,TL≤3 cm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5)[29]。另一項研究也表示TL≤5 cm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35)[30]。
(四)臨床TNM分期(clinical TNM,cTNM)
一般認為,cTNM分期更低與更好的預后相關,因此多項回顧性研究就cTNM分期對pCR的預測進行探索。部分研究由于樣本數目小,數據分析進行了組間合并,而合并方式不同可能會對研究結果帶來影響。
cT分期越高,表明原發腫瘤侵入深度更深,腫瘤的大小可能會影響其對放化療的敏感性。從邏輯上認為較低的cT分期與更高的pCR有關,但未具體到某一分期對pCR的影響為多少。按cT0-2與cT3-4分組和按cT1-3與cT4分組的研究都認為cT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43,P=0.031)[17,27]。但一項數據量大且未將cT進行合并的研究表明cT分期與pCR無關(P=0.15)[16]。
cN分期表示區域淋巴結是否轉移,通常認為較低的cN分期與更好的病理反應有關,但預測pCR價值有限。Peng等[17]的研究將新輔助后cN1-2進行合并與cN0進行比較,cN分期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03)。但按cN0,cN+分組的研究和以cN0-1與cN2分組的研究均認為cN分期不能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886;P=0.084)[27,30]。
cM對pCR的預測很少,這與大多數研究在納入研究對象時排除了遠端轉移的患者有關。根據已有的研究,出現遠端轉移,認為不容易實現pCR(P=0.00)[16]。
二、評估手段
通過MRI、腸鏡、PET-CT、直腸內超聲等評估手段和影像學特征直接對pCR進行估計或通過影像學參數預測pCR。
1.MRI
MRI對pCR的預測可通過定性與定量分析:Griethuysen等[31]在新輔助治療前通過MRI形態學評估可預測pCR。類似的,Napoletano等[32]的研究通過新輔助治療后傳統MRI的定性評估對pCR的預測結果為:敏感性為80%,特異性為50%,總體診斷能力為71.40%,結合MRI擴散加權影像的定性評估進一步提高了預測能力:敏感性為100%,特異性為67%,總體診斷能力為90.40%。
從MRI擴散加權影像中得到的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ent,ADC)的定量分析也可預測pCR。對新輔助治療后ADC的直方圖分析(將病灶各部位的ADC值統計為直方圖)顯示,獲得pCR的患者ADC更低,ADC直方圖中第25個百分數(臨界值為1.39×10-3mm2/s)對pCR的預測效果最好(AUC=0.796,P<0.001,敏感性為56.3%,特異性為91.4%),但實現pCR的患者和未實現pCR的患者在新輔助治療前ADC無顯著差別[33]。以整個病灶部位的新輔助治療前中后的ADC平均值為預測因子的預測能力有限,治療前臨界值ADC=0.81×10-3mm2/s時,敏感性為53.8%,特異性為66.7%,AUC=0.62;治療中臨界值ADC=1.05×10-3mm2/s時,敏感性為69.2%,特異性為 66.7%,AUC=0.66[34]。
2.PET-CT
有研究評估了PET-CT預測pCR的能力,最大標準化攝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及以肝臟為參照指標的SUVmax是常見的預測因子。SUVmax能夠反應腫瘤細胞的活性和腫瘤的惡性程度,其臨界值尚無標準。在新輔助治療后,獲得pCR的患者表現出更低的SUVmax和以肝臟為參照指標的SUVmax[35-36]。幾項研究都表明SUVmax是預測pCR的重要因素,Koo等[35]的研究表示在臨界值SUVmax≤2.5時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敏感性為68.3%,特異性為87.7%,AUC=0.864;Park等[36]的研究認為SUVmax具有預測價值(當臨界值SUVmax=4.36時,敏感性為100%,特異性為53.5%,準確度為52.5%,AUC=0.744),但其預測價值小于以肝臟為參照指標的SUVmax(以肝臟為參照指標的SUVmax≤1.41作為pCR的預測因子,敏感性為88.2%,特異性為64.8%,準確度為68.2%,AUC=0.826)。
3.腸鏡
van der Sande等[37]的研究中,由三位醫師獨立通過新輔助治療后8~12周的腸鏡檢查預測是否達到pCR的AUC分別是0.84(95%CI=0.77~0.90),0.80(95%CI=0.73~0.87),和 0.84(95%CI=0.78~0.91),敏感性分別為72%,90%和74%,特異性分別為83%,61%和85%。Kawai等[38]的研究中患者在新輔助治療后3~8周接受腸鏡檢查,腸鏡特征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扁平的邊緣腫脹(敏感性為69.1%,特異性為73.9%,準確度為69.7%,P=0.025,OR=3.39)和活檢標本中無腫瘤細胞殘留(敏感性為65.0%,特異性為78.3%,準確度為66.4%,P=0.004,OR=4.61)。
4.直腸內超聲
Liu等[39]的研究表明新輔助治療后6~7周的直腸內超聲預測pCR的敏感性為25.00%,特異性為93.90%,準確性為85.11%,約登指數為0.19。Li等[40]的研究認為新輔助治療6~8周后和新輔助治療開始2周在直腸內超聲獲得的腫瘤最大厚度之比與pCR相關(r=-0.347,P=0.026),預測能力還有待提高。
三、新輔助治療方案
1.化療方案
關于化療方案(基于5-Fu的化療方案)的研究很少,雖然多篇研究中均涉及多種方案,但并未探究其對新輔助治療效果的影響。根據已有研究,在都進行長程放療的情況下,化療方案的差異對pCR有影響:一項三期的隨機對照實驗比較了進行5個周期的de Gramont(亞葉酸鈣400 mg/m2靜脈滴注后氟尿嘧啶400 mg/m2靜脈滴注,氟尿嘧啶2.4 g/m2連續靜脈滴注48 h)和mFOLFOX(de Gramont基礎上每個周期第一天加入奧沙利鉑85 mg/m2靜脈滴注)pCR率的差異,前組pCR率 為14.0%, 后 組 為27.5%,OR=0.428,95%CI:0.237~0.776;P=0.005[41]。該研究中心的回顧性隊列研究表明de Gramont/卡培他濱和mFOLFOX影響了pCR率,后者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00)[25]。
2.放療劑量/時間
在都進行長程放療和同步化療的背景下,幾項研究都認為隨著放射劑量的增加,新輔助治療后的pCR率明顯提高,其中Hall等[42]、Al-Sukhni等[43]的研究均提示放療劑量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P<0.05)。在這幾項研究中,每次放射劑量為1.8 Gy~2.0 Gy,根據總的放射劑量進行分組,Hall等和Al-Sukhni等的研究均以45.0 Gy和50.4 Gy作為分界值[42-43]。但在 Wiltshire等[44]研究中三組患者接受的放射劑量分別為40 Gy、46 Gy和50 Gy,pCR率分別為15%、23%和33%,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
但長程放化療和短程放化療對pCR的影響未見明顯差異:Bujko等[45]的隨機研究將短程放療加鞏固化療(放療劑量25 Gy,5次,5 Gy/次和3周期FOLFOX4)和長程放化療(放療劑量50.4 Gy,28次,1.8 Gy/次,第一周和第五周不接受放療時靜脈滴注5-Fu 325 mg/m2/d、亞葉酸鈣20 mg/m2/d,每周第一天奧沙利鉑靜脈滴注50 mg/m2)對pCR的影響進行了比較,結果表明二者在pCR上無統計學意義(16% vs.12%,P=0.17)。Lee等[46]的研究也表明接受長程或短程放化療患者的pCR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3.3% vs.8.0%,P=0.10)。
3.單純放療與放化療的比較
將單純的放療與放化療進行對比的研究認為化療藥物的缺乏,可能導致放療敏感性降低,進而更難實現pCR:Hoendervangers等[47]將單純的短程放療和延遲手術(放療劑量25 Gy,5次,5 Gy/次,短程放療結束后與手術間隔時間超過4周)與長程放化療(放療劑量45 Gy~50 Gy,25次,1.8 Gy~2 Gy/次,5周,同時加卡培他濱,每日2次,825 mg/m2)進行了比較,后者更易實現pCR(pCR率:6.4% vs.16.2%,P<0.001)。
4.新輔助放化療后與手術間隔時間
通過對目前已有對新輔助放化療研究的回顧,新輔助放化療和手術時間間隔長短具有預測pCR的價值。在長程放化療中以時間間隙≥7周:Peng 等[17](OR=1.795,95%CI:1.151~2.801;P=0.010) 和 Choi等[48](OR=0.139,95% CI:0.022~0.877;P=0.036)和 Zeng 等[49](OR=2.588,95%CI:1.484~4.512;P=0.001)的回顧性研究表示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17,22,49],但時間過長,對pCR的提高并無幫助,12周以上并未顯著提高pCR率[22],一項隨機對照試驗顯示長程放化療下7周和11周的pCR率無差異(15.0% vs.17.4%,P=0.5983)[50]。另一項研究中,新輔助長程/短程放化療和手術時間間隔6~7周pCR率可達到峰值,但未表現出顯著的統計學意義(P=0.09)[46]。綜合已有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間隔時間7周左右可提高pCR率,可作為pCR的預測因子。
考慮到放療帶來的毒性,單純進行新輔助化療的患者新輔助化療與手術之間的間隔會縮短[28],但該研究中并未探討新輔助化療與手術之間的間隔對pCR的影響,且對此的討論很少,但新輔助放化療與手術間隔時間對pCR的預測會對新輔助化療與手術間隔時間對pCR的預測帶來一些啟示。
四、結論
對于多數可能預測pCR的因子,根據現有研究確定其預測價值或者判斷預測方向是很困難的,相比較而言,患者特征中CEA,TL及新輔助治療方案的相關參數預測價值較為穩定且更有價值,但臨界值的選擇仍存在爭議。MRI,PET/CT,腸鏡,直腸內超聲是pCR的重要預測手段。基因分子學特征方面的預測很有潛力,但仍需進一步更大的前瞻性研究,明確更有預測價值的指示物。總體來說,需要進一步的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明確目前可能的預測因子的預測價值及方向,和發現其他指標是否也有預測pCR的潛力。建立多因素的pCR的預測模型對提高pCR的預測精度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