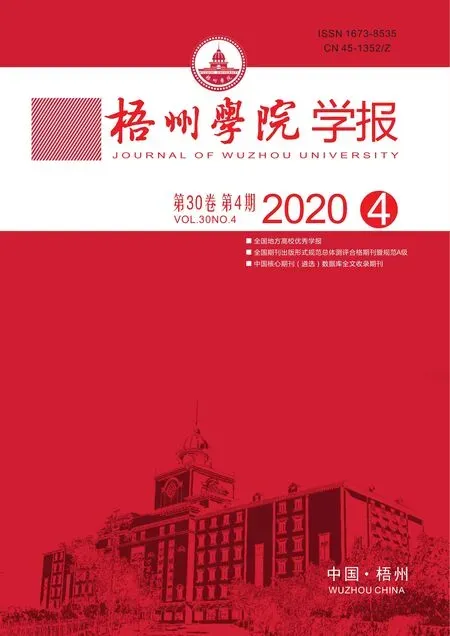回顧與反思百年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與傳播
侯 杰,王 梅
(1.2.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以文學啟蒙為重要特征的新文化運動,掀起了外國文學翻譯的高潮。不可否認,新文化運動強調“西潮”輸入來改造傳統文化,以此推動社會變革,卻忽視了本土文化及文學的輸出與傳播。2004年中國外文局設立“對外傳播研究中心”,2009年中國外文局重新出版“熊貓叢書”40本,2010年國家漢辦批準“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項目,……“新世紀的中西關系,出現了以‘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訴求中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輸出為特征的新態勢”[1]。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外譯理應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內容。
不少學者已從不同視角梳理了不同時段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的成果,如金介甫論述了1949—1999年中國文學英譯本出版情況[2],張英進同樣回顧了此時期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狀況[3],胡志揮整理的中國文學英譯本索[4],等等。多數研究聚焦1949—1999年某一時段文學作品英譯活動,對建國前及新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重視不夠,且缺乏分析不同歷史時段英譯活動的內在歷史關聯。回顧百年以來不同歷史階段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的歷史成果,反思英譯機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以利于促進中國文化、文學“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一、發軔期(1919—1948年)
建國前現代文學作品英譯活動主要是個人行為,多數由外籍人士翻譯完成,傳播的受眾也主要限于中國大陸的外籍人士,傳播媒介以英文報刊為主,有少量的小說譯文集出版。
(一)作品集及單行本翻譯
從翻譯選材上看,此時期英譯以五四啟蒙作家的現實主義經典小說為主。從翻譯主體上看,以外籍人士或海外華人譯者為主,如王際真、賽珍珠、熊式一父子、林語堂父女等;國內比較活躍的翻譯家為數不多,有蕭乾、楊憲益、司馬文森及香港的黃雯博士等。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作品集主要有由莫爾斯(E.H.F.Mills)翻譯、敬隱漁作序的《阿Q正傳和其他現代中國小說》(TheTragedyofAhQuiandOtherModernChineseStories)(1930),收集了魯迅、陳煒謨、許地山、冰心、茅盾、郁達夫等的作品;斯諾(Edgard Snow)整理了各大英文期刊魯迅短篇小說英譯本,又請蕭乾等翻譯了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從文、孫席珍、田軍、林語堂、郁達夫、張天翼等的作品,一同收錄在《活的中國》(LivingChina)(1936);王際真翻譯出版了《阿Q正傳及其他:魯迅選集》(AhQandOthers:SelectedStoriesofLusin)(1941)、《當代中國小說集》(ContemporaryChineseStories)(1944),收錄了魯迅、沈從文、老舍、茅盾、凌叔華等的短篇小說。白英(Robert Payne)與袁嘉華翻譯出版了《現代中國小說集》(ContemporaryChineseShortStories)(1946),收錄了魯迅、楊振聲、施蟄存、老舍、沈從文等的短篇小說;王際真(Chi-Chen Wang)翻譯出版了(《中國戰時小說》(StoriesofChinaatWar)(1947),收錄了包括老舍、端木蕻良、陳瘦竹、茅盾、卞之琳等的小說。白英編譯了《當代中國詩選》(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1947),收錄了徐志摩、聞一多、何其芳、馮至、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等現代詩人的代表作;白英、金隄翻譯了沈從文的小說集(《中國土地》(TheChineseEarth)(1947)。
小說獨譯本較少,梁社乾翻譯了魯迅的《阿Q正傳》(TheTrueStoryofAhQ)(1926),盛成的《我的母親》(ASonofChina)(1930)是由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譯的;老舍作品的第一個英文譯本是由伊文·金(EvanKing)翻譯的《駱駝祥子》(RickshawBoy)(1945),伊文·金還翻譯了老舍的《離婚》(Divorce)(1948),郭鏡秋女士(Helena Kuo)同年也翻譯了這部作品,定名為TheQuestforLoveofLaoLee;斯諾的力推下,肖軍的《八月鄉村》(VillageinAugust)于1942年在紐約出版。
(二)英文期刊的現代文學英譯
英美國家在華主辦的英文期刊是中國現代文學傳播的重要載體,如《亞細亞》(Asia)、《今日之生活與文學》(LifeandlettersTo-day)、《今日中國》(ChinaToday)、《密勒氏評論報》(Miller′sReview)、《中國雜志》(TheChinaJournal)、《遠東評論季刊》(TheFarEasternQuarterly)等刊載過不少經典現代作品的翻譯。海外的英文期刊,如英國的雜志《我們的時代》(OurTime)、《泰晤士報》(TheTimes)、前蘇聯共產國際主編的《國際文學》(TheInternationalLiterature)雜志多次譯介中國現代經典作品。國人主辦的英文期刊尚不多見,胡適與蔡元培支持下的幾份時政性較強的綜合性期刊,較少涉獵文學內容,如《中國評論》(TheChinaCritic)只刊載過少量由林語堂、全增嘏等創作的小品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剪報》(ChinainBrief)、《天下月刊》(T′ienHisaMonthly)及《中國文摘》(ChinaDigest)3份有不同文化身份“贊助人”資助的英文期刊,刊載的現代文學作品內容也不盡相同。《中國剪報》是美國人安瀾(Allen)聯合蕭乾創辦的,由于缺乏資金,期刊從1931年6月1日持續到7月29日共出版8期(筆者查,中國現代文學館現共存6期),便宣布夭折。《中國剪報》選譯了“魯迅、茅盾、郭沫若、聞一多、郁達夫等人作品的片段,并為沈從文出了個專集”[5]。《天下月刊》由中山文化教育文化館資助,于1935年8月創辦,1941年9月停刊,共發行12卷56期。《天下月刊》文學板塊重視古代典籍等“漢學”知識的傳播,只刊載了部分現代作家的經典作品翻譯,包括邵洵美的《蛇》、聞一多的《死水》、卞之琳的《還鄉》、戴望舒的《我的記憶》等13首詩歌,凌叔華的《無聊》、蕭紅的《手》、冰心的《第一次宴會》、魯迅的《懷舊》等21篇短篇小說,沈從文的《邊城》、巴金的《星》2篇中篇小說。《中國文摘》是中國共產黨于1946年12月在香港創辦的“紅色”英文期刊,至1950年2月停刊止,共出版7卷81期。該期刊發刊詞明確雜志的宗旨為“向世界描述中國人民的生活、藝術和活動”,通過報道解放區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輔以譯介解放區文學,力圖建構即將誕生的新政權的合法性[6]。
由上觀之,“發軔期”內的現代文學英譯主要是由外籍譯者完成,以經典作家的短篇小說合集為主,現實主義作品與左翼作家的作品占了優勢份額,這基本反映了五四運動后中國主流文學的發展脈絡。
二、緩慢發展期(1949—1978年)
二戰結束后,世界冷戰格局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英美國家與中國陷入了意識形態對立的狀態。國內文學外譯基本上由國家機構所主導,《中國文學》的英譯文學活動以建構新中國的合法性為宗旨,代表了國內文學外譯的基本機制。
建國后,《中國文摘》完成過渡時期外宣任務,于1950年停刊。新中國外宣事業已邁上新里程,全英文的《人民中國》《中國畫報》先后創刊,接過了外宣任務。1949年前后,葉君健在茅盾、周揚的委托下,開始籌備《中國文學》雜志。1951年10月1日《中國文學》創刊,葉君健先后邀請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以及沙博里(Sidney Shapiro)等外籍翻譯家入社工作。《中國文學》作為國內唯一一份中國文學外譯的期刊,50年出版590期,翻譯文學作品3 200余篇,成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文學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窗口,為建構國家形象的外宣任務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據筆者統計,從體裁上看,1951—1978年《中國文學》翻譯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戲曲、話劇、電影文學等;從篇目上看,小說和散文的數量最多,共778篇;從翻譯主體上看,共涉及小說和散文作者726位。
現代文學作品翻譯,《中國文學》主要選譯了魯迅、巴金、郭沫若、沈從文、葉圣陶、郁達夫、李廣田、許地山、蕭紅等創作的現實主義小說,其中翻譯魯迅的作品最多,高達97篇。雜志于1956年魯迅逝世20周年、1961年魯迅誕辰80周年之際,設立紀念專欄,分別翻譯魯迅作品14篇和12篇,并刊載馮雪峰、許廣平、唐弢紀念魯迅的文章。此后,雜志于1967年設“魯迅雜文選”、1971年設“紀念魯迅誕生九十周年”、1972—1973年設“魯迅作品”、1974年設“魯迅著作”、1975年設“魯迅的故事”等專欄譯介魯迅本人及其作品。可見,《中國文學》翻譯魯迅的立場立足于國家政治的需要,力圖把魯迅建構為連接五四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革命家、文學家與思想家形象,“為對外確立新生的新中國的合法地位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7]。
《中國文學》選材豐富,按照題材主題基本可以分為解放區文學、革命歷史小說、社會主義建設與民族文學題材。表現解放區人民生活與斗爭的作品,如孫犁的《荷花淀》《蘆花蕩》,劉白羽的《早晨六點鐘》《火光在前》,趙樹理的《登記》《小二黑結婚》等;表現抗日戰爭以來與中國人民英勇斗爭精神的革命歷史小說,如袁靜的《新英雄兒女傳》、柳青的《銅墻鐵壁》等;表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及社會新面貌的“十七年”小說,如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等;展現民族團結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如瑪拉沁夫的《科爾沁草原上的人們》《鄂倫春組曲》,烏蘭巴干的《第一個春天》等。
《中國文學》創刊號扉頁雖印有“致力于出版中國當代作品”的字樣,翻譯的第一篇文章是周揚的《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8],顯示出濃厚的政治色彩。1953年雜志從年刊改為半年刊,1954年出版季刊,1959年又改為月刊,文學翻譯數量與語種逐漸增多。由于時代限制,翻譯作品與翻譯質量良莠不齊,這份具有官方背景的文學外譯期刊英譯活動折射了那個時代真實的外譯體制。
三、現當代文學英譯的繁盛期(1979—1999年)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當代文學已經顯示出思想復蘇的跡象。真正引起西方關注中國新時期文學,當屬《中國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及時翻譯[2]。依托《中國文學》出版社,1981年開始推出的“熊貓叢書”,至2007年共出版英譯本149種(2000后僅出版5本)[9],涵蓋了大部分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是改革開放20年間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成果的集中體現。
從翻譯動機看,“熊貓叢書”仍然承擔了與英文版《中國文學》類似性質的政治外宣任務,但任務內容有所不同。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推出“熊貓叢書”項目,主要以英法兩種語言向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學,讓國際社會了中國文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新時期中國的嶄新面貌。
從翻譯內容看,以當代作品、短篇小說集為主。1981—1982年“熊貓叢書”前兩年出版的譯作以現代作家為主,當代作品只包括《中國當代七位女作家選》《新鳳霞回憶錄》。即使現代作家的選擇也體現了“去政治化”傾向,《中國文學》過去30年沒有翻譯過沈從文的作品,“熊貓叢書”前兩年英譯了沈從文的《邊城》《湘西散記》。1981—2007年,“熊貓叢書”英譯巴金、老舍、孫犁、李廣田、蕭紅、艾青等的作品,一直沒有翻譯魯迅的作品,這也許是受到80年代“重寫文學史”潮流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是活力四射的年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國文學創作活躍,各種文學流派紛紛登場。“熊貓叢書”先后英譯了40多位當代作家的作品,如王蒙的小說集《<蝴蝶>及其他小說》、張賢亮的《綠化樹》等“傷痕文學”,賈平凹的《天狗》《晚雨》、阿城的《空墳》、汪曾祺的《晚飯后的故事》等“尋根文學”,劉恒的《伏羲伏羲》、池莉的《不談愛情》及方方等人的“新寫實主義文學”。
從傳播渠道及效果看,20世紀80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逐步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系,文化交流增多,西方社會熱切希望了解這個“神秘”國度所發生的變化。“熊貓叢書”使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獲得國際聲譽,如古華的《芙蓉鎮》、高曉松的《退婚》極大吸引了英美讀者[2]。20世紀90年代,“熊貓叢書”銷量下滑。一方面,“熊貓叢書”選材的詩學原則有所變化;另一方面,部分西方讀者開始質疑官方贊助譯作的“可靠性”,西方讀者閱讀的政治審美也限制了文學審美。當然,“贊助”的市場因素更為重要,各國傳媒業都出現了紙媒危機,當下數字網絡社會的外國讀者了解中國渠道逐漸多元化,“熊貓叢書”于2007年最終停版。
四、新世紀以來現當代作品翻譯的趨勢及問題
(一)選材的“多元化”
改革開放以后國內興起“文學熱”,當代文學流派紛呈,在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文學》、“熊貓叢書”、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以及香港《譯叢》雜志的推動下,優秀的當代文學作品在短期內得到有效地英譯與傳播。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借助于文化產業提高國家的軟實力已成各界共識。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宣布“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005年英國企鵝圖書公司買斷《狼圖騰》的英文版權,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4年2月麥加的《解密》英譯本出版當天就創下了中國作家在英語世界銷售的最佳成績,2015年許淵沖獲得國際譯聯頒發的“北極光”翻譯獎,2016年曹文軒獲“國際安徒生獎”,……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一次次受到激勵。網絡時代參與當代文學英譯力量眾多,選材已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如果說“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是20世紀90年代英譯市場的熱點,那么新世紀以來翻譯熱點更加多元化,民族文學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與姜戎的《狼圖騰》、城市文學如衛慧的《上海寶貝》、武俠小說如金庸的《笑傲江湖》、兒童文學如曹文軒的《青銅葵花》、海外華文文學如張翎的《金山》等英譯本得到市場吹捧。中國官方助推的當代文學英譯也力圖注重多元化選材,《人民文學》英文版Pathlight的編輯總監艾瑞克曾認為該刊“按照不同的標準選擇文本”“考慮這些書譯出后的市場價值”“不做面子工程”“盡可能選取能表現中國當代藝術特色以及能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現實和精神面貌的作品來翻譯”[10]。
(二)從學術研究到平民閱讀的艱難路徑
在國家行為的助推下,“典籍外譯”“圖書推廣”“精品譯介”等項目的確提高了現當代文學翻譯的數量和規模,但相關研究表明英譯作品在海外傳播效果不容樂觀。
海外現代文學英譯主要集中于漢學研究領域。當代文學而言,據何明星統計,“大學出版社、學術研究機構、期刊社翻譯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收藏圖書館數量遠遠排在前面,在前5名中,都是大學社的作品,前10名只有2家為大眾圖書出版機構。這樣一個數據,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在歐美世界的地位仍然處在邊緣化、小眾化的格局之中,還尚未進入主流”[11]。英美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文學英譯何以能排在圖書館收藏榜的前列?這當然與學術機構一向把中國文學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傳統有關,更不可否認的是學術機構有著翻譯的語言優勢與漢學研究背景,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和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聚集了大量研究漢學研究與中國問題的專家。然而,如果中國文學的傳播僅僅局限于象牙塔內的學術研究之用,那么我們力推的文學外譯很難走向大眾,難言完成外宣任務與市場盈利。
(三)問題及對策建議
現當代文學英譯本傳播效果除了涉及翻譯本身的質量問題外,還涉及營銷策略、國家外交關系及閱讀市場傾向等問題。
首先,從翻譯本身的詩學原則出發,現當代文學面臨“譯什么”“由誰來譯”“怎么譯”的問題。翻譯的選材不僅要注重國家形象建構、彰顯“主流敘事”的現代作品,更要關注市場需求,多譯反映中國現實的、娛樂性強的當代通俗作品。英譯模式通常有中國譯者、英美人士和中西結合3種模式。馬會娟認為“文學翻譯的質量與譯者的國別、翻譯模式無關,而與譯者的文學修養以及跨文化翻譯能力有關”[12]。好在當下譯者力量多元化,海外民間翻譯力量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注入了活力。民間網絡組織Paper Republic就為熱愛中國文學的譯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臺,“致譯者”(Resources for Translators)欄目將英語國家和非英語國家從事中國文學的譯者聯系到一起,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翻譯的重要力量。“怎么譯”的問題涉及過多的語言技能、審美傾向及翻譯策略等詩學原則問題,但一定也要考慮文學藝術特色之外讀者的意識形態問題。
其次,要重視完善中國現當代作品英譯的傳播過程。朱振武認為英譯作品傳播效果不好的原因是“我國譯者對目標語讀者的接受能力不夠了解”“推廣發行沒有受到重視”[13]。因此,要重視利用權威媒體以及自媒體平臺擴大英譯本的影響力。目前,官方已經開始重視與英美權威雜志與媒體合作推廣英譯文學,如北京師范大學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共同合作創辦《今日中國文學》,重點向美國讀者介紹中國當代文學。此外,要重視國際圖書展及英美各國重要圖書館的營銷推廣機會,主動創造與商業性圖書出版社及大學圖書館合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