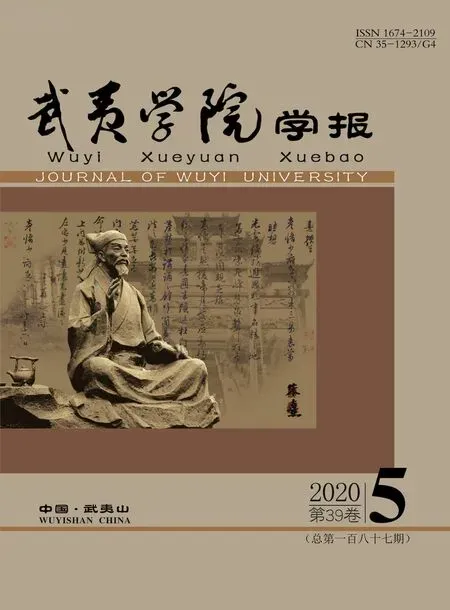評朱熹對佛教心說的批判
黎曉鈴
(武夷學院 朱子學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不同于張載與二程對佛教“心跡”是否一致的糾結,朱熹更加重視的是作為主觀能動性之主體的心如何恰當應對客觀現實之“跡”的問題。為此,朱熹將張載具有因物順應性質的“太虛”本體之虛,用在了心之本體的性質之上。朱熹說:“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1]所以,正是因為有“虛”的性質,心之本體還有明、靈、覺的特性。如此看來,朱熹十分強調心之綜合分析與判斷的功能,從而超越了二程只強調心對理之絕對服從的直線性模式。為此,朱熹又將自己所強調的心與佛教重視的心進行了辨析。
一、用虛心批判佛教的空心
朱熹十分重視將自己強調的心“虛”與佛教強調的心“空”區別開來。朱熹說:“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2]在朱熹看來,佛教將心和實理分為二,心所思考的不是理而是空,而理學家的心萬理兼備,包含和思考實實在在的現實事理。所以,理學的心虛與佛教的心空不是一回事。然而,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比較欣賞佛教喚醒此心而覺悟的修養論的。朱熹說:“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1]朱熹依然是以佛教沒有照管現實中的道理而否定了佛教的喚醒此心。
同樣,“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卻不會方外。圣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定,方能義以方外。”[2]佛教和理學也都強調心之敬,但朱熹認為,佛教沒有就外界客觀之理作為敬的對象,敬的也是空。如何判斷佛教并沒有敬重和思考現實之理呢?朱熹說:“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何在乎?”[1]朱熹認為,父子、君臣、三綱五常就是作為人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遵循的客觀之理,佛教僧人斷舍了與家庭的關系而出家,就是逃避了這種關系,從而肯定佛教實際上并不敬重客觀之理,并推斷其所強調的敬以直內也就是空理。“圣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與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于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與此都理會不得。”在朱熹看來,外在之理是不能有一絲一毫差錯的,佛教不重視禮儀就是道體上有虧欠,從而佛教心中所敬的并不是客觀之理。然而,禮儀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客觀之理呢?顯然,禮儀和理并不能完全劃上等號,不能因為佛教不重視禮儀的形式從而等同于佛教不重視客觀之理。
朱熹其實也知道,佛教所強調的空,并不是指否定一切的斷滅空。“(釋氏)說‘玄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1]佛教理論中的空是包含有的,對于這點,朱熹表示了肯定,并認為儒家也是有同樣的道理。但是,朱熹并不認同佛教的“空不真空”:“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吃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靜無為,一向恁地深藏故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1],朱熹認為,佛教沒有踐行客觀之理(儒家綱常倫理),那么其所強調的“空不真空”其實是將有也變成了空,與儒家的空包含有還是不同的。然而,佛教的“空不真空”是否真的是將有也變成了空呢,這依然還是值得商榷的。
依此邏輯,朱熹更嚴厲批評了佛教的“作用是性”。朱熹說:“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1]然而,這其實是佛教傳說中的波羅提尊者與印度異見王的談話,強調的是當下現實之心不起妄念的一種狀態。但是朱熹的理解卻不是這樣:“‘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后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后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如曰運水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1]朱熹認為,佛教的“作用是性”就是缺乏本體的把持,而只在用處的末端的為所欲為。朱熹舉儒家中的“徐行后長”與佛教中的“運水搬柴皆是妙用”進行對比。“徐行后長”其實出自孟子對告子的批評中,原話是“徐行后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意思是,慢慢地跟在長者后面走,叫作悌,快步搶在長者前面走,叫作不悌,強調的是對兄長要敬重且順從。然而,若走路時走到兄長前面就意味著不敬,這依然是將禮儀等同于理的邏輯。
其實,朱熹之所以特別強調批判佛教的“作用是性”,與這種禪法在朱熹的生活地特別流行有關。“作用是性”的禪法真正在中國被明確化而產生深遠的影響,是從洪州禪的創始人馬祖道一那里開始。慧能注重的“直指心源、頓悟見性”至馬祖道一之后為之一變,開始出現了一種向隨緣任運、無證無修方向發展的傾向。[3]而馬祖道一在建陽佛跡嶺傳法之后,其禪法在福建迅速傳播開來。百丈懷海、溈山靈祐、黃檗希運等作為其禪門開宗立派之祖師都來自福建。朱熹長期生活在此,對于這種禪法因傳播不當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了解較為深刻,從而舉起理學理論以對治之就不難理解了。在朱熹的理解中,“作用是性”就等同于其心性論中很容易被欲望牽走的“人心”:“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1]因此,朱熹提出,人心必須聽命于道心,并以此繼續批判佛教的觀心說。
二、用人心聽命于道心批判佛教的觀心
在朱熹看來,心是兼體用而存在的,而佛教的“作用是性”則是忽略了體而僅在用處的任意妄為。為此,朱熹吸收了張載的“心統性情”來解釋其理學中心的含義。其中,性為未發為體,情為已發為用。朱熹說:“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4]未發之性是靜,已發之情是動,而心則是兼體用未發已發之性情的主宰者:“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6]情的發用是否得當中節,就由心來決定。如此看來,心確實非常重要。
有人問朱熹如何看待佛教的觀心說。朱熹卻說:“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5]朱熹強調心就是主宰者。每個人的心只有一個,這個心主宰著人的一切。而這個主宰一切的心卻不需要反觀。因為朱熹認為,反觀其心則意味著有另一個心可以觀察著這個心,在朱熹看來是不符合邏輯的。朱熹說:“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吃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4]那么,又如何保證這個主宰一切的心發用得當呢?所以有人問:“若子之言,則圣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依于衡’者,皆何謂哉?”[4]可見,此心必須得到管理才能發用得當中節,而管理此心的心又被稱為道心:“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朱熹認為其哲學中,雖有道心和人心兩個概念,但是實指一個心,只是因人欲之萌和天理之奧而有不同的名字而已。然而,只有一個心,名字可以不同,但是卻又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就讓人匪夷所思了。朱熹解釋說:“‘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朱熹否認有道心和人心兩個心,然而何者居其正審何者之差?何者糾正何者之差?朱熹繼續解釋:“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4]。朱熹再次強調,心只有一個,重要的是良心的自主性是否能夠得到呈現而已。
為了更好地表達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朱熹做了一個比喻:“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5]人心聽命于道心,就象舵控制船一樣。但是舵并不是船,它只是船的一部分。船駛向哪里由舵控制,如果舵不控制,船就會無目的地亂飄。那么,舵又應當如何控制船呢?目標是必不可少的。由此,朱熹批判佛教之心是無定向之心:“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其為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圣門所謂心,則天秩、天序、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其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其有二理哉?”[4]
三、問題之所在
朱熹指出,雖然儒佛都強調喚醒此心,然而儒佛喚醒此心的目的卻不同。在儒家,喚醒此心的目的在于認識外在的作為本體的理,也就是舵手知道自己的方向。在朱熹看來,佛教始終不肯承認外在之理才是天下之大本,心就沒有需要認識的外在對象,于是便會迷失自我。這其實也是對契嵩去除天命而論心的批判。在契嵩處,沒有客觀必然的天命,只有一心向道,而道究竟是什么,沒有確定的說法,所以在朱熹看來,佛教的心就是迷失的小船。而朱熹理學強調外在的客觀道理就是認識的對象,船有了目標,心的主宰也就能得以實現。“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個心,然后得為窮理也。”[4]因此,在朱熹理學中,心雖然很重要,但是心本身卻不是需要認識的對象。因為由于心體“自明”的機制,心體是什么的問題在邏輯上已經解決。[6]關鍵在于道心(良心)的主宰能不能實現。朱熹認為,將理作為認識對象,心就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良心的主宰才有實現的可能。
所以,朱熹認為,儒佛的根本差別其實與自私與否無關,而是有沒有以現實中的理作為思考對象。朱熹說:“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在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者,只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游,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卻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見此理,無一理可違于物。佛說萬理具空,吾儒說萬理具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1]朱熹認為,正是因為沒有見理,才會產生公私、義利的差別。
然而,問題在于,客觀之理其實非常復雜,并非只有一個。朱熹也說,“物物皆有理”“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5]如何處理這些復雜的道理才是問題的關鍵。所謂“發而中節”其實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如何實現這一理想才是實際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學生問朱熹:“于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朱熹的回答是:“學者安得一一恁地!也須且逐件使之中節,方得。此所以貴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為難也。”[5]對于復雜的客觀道理,朱熹認為需要把眼前現實每一件事物的道理都一一搞清楚,“各求其中節”,這其實是一個求真和擴大見識的過程。“朱熹之心體以‘湛然’為特質,以物來能照得其真為目的”。[7]而知識是無止境的,求真其實是沒有終點的。如此,朱熹譬喻中的小船的舵手(道心)依然會因無法分辨現實中的復雜的道理而迷失方向。所以,如果僅以客觀之理為認識對象,其實并不能完全保證道心(良心)的主宰得以實現。因此當有人問朱熹:“‘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時,朱熹的回答是:“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是觀之。”[1]朱熹以謝良佐為例,指出若把求真等于圓善就不是正確的方向。而當其聽完程顥的話而汗流浹背、滿面發赤之時,才是由性體而直接導至四端七情的發用,這才是發而中節的狀態。由此,發而中節的情才是人需要達到的目標所在,也是朱熹譬喻中小船之舵(道心)把控方向的關鍵。然而,道心究竟如何主宰人心這艘小船依然是沒能解決的問題。
朱熹理學中的本體是天理,然而這個本體并不能直接去把握,而是需要通過對分殊之理的一一了解之后豁然貫通得知天理。朱熹認為“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8]。然而,由于本體的非實體性,常規的認識方法,比如分析、推理、綜合、歸納等,其實很難準確、完整對其進行認識和把握。[9]其實,雖然朱熹一再強調“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盡其心”[5],知性似乎必須在盡心之前,然而他自己其實也說:“心梏于見聞,反不弘于性耳。”[5]可見,如何使心不梏于見聞也是見性的關鍵,反觀其心使其見性其實也是必要的過程。佛教的觀心說當依然有其不可否定的價值和可資借鑒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