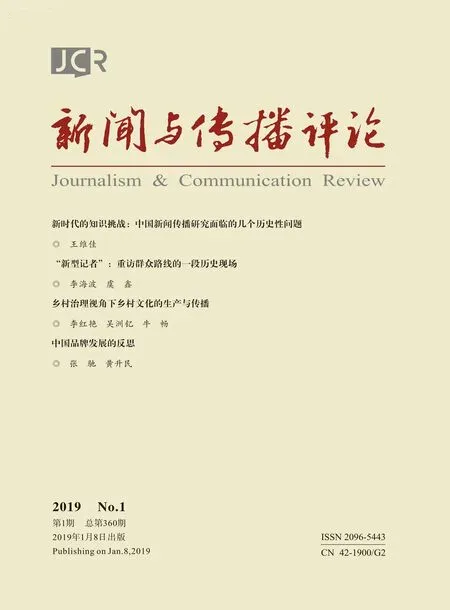廣告生產的社會過程與個體“名譽點”爭斗:基于布爾迪厄、埃利亞斯社會關系與過程論的反思
陳 凌
一、問題提出:作為社會過程的廣告生產與個體名譽點爭斗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逐漸占據壟斷地位。與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韋伯(Max Weber)、齊美爾(Georg Simmel)、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等古典社會學家把社會看作歷史的過程、社會關系不同,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把社會簡化為一種功能性結構,個人消失在結構之中。進入20世紀80年代,社會學界開始普遍反思,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Ulrich Beck)、鮑曼(Zygmunt Bauman)等學者重新梳理歐洲古典主義傳統,對社會學理論進行重建。布爾迪厄和埃利亞斯作為重要的反思者,對帕森斯提出旗幟鮮明的批評。埃利亞斯抨擊帕森斯個人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關系的理論模式,他認為應該把“封閉的個人”看作“開放的個人”,提倡“將人理解為由互相依存的人所組成的各種各樣的形態、群體和社會……超然于社會之外的個人和超然于個人之上的社會也就不存在了”。[1]布爾迪厄綜合“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建立自己的關系主義方法論,提出附著于某種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客觀歷史關系構成的“場域”,而眾所周知的“慣習”概念更是一系列歷史關系在個人身體中的“積淀”。無論從埃利亞斯的個體進程角度,還是布爾迪厄的“慣習”角度看,個人都是不能與社會分割的開放存在。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經濟學手稿》中寫道:“社會并不只由個人所組成;它還體現著個人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各種聯結和關系的總和。”[2]
布爾迪厄在《實踐理論大綱》第一章解釋了名譽的含義。該書中文版譯者高振華和李思宇認為Honneur應譯作“名譽”而非“榮譽”,因為名譽的意思有名譽與聲望、榮譽與光榮,其中還包括個人或集團的威信這一意思。布氏在分析卡比爾人社群的第一個案例時就提出,被挑戰的個人名譽是來自群體價值的。公共輿論“保護”名譽,并以輿論對個體施加“壓力”,影響個體名譽點及其行動。“名譽與名譽點是對立的,前者通過一個群體展示出來,而正因為后者的存在,人們在遭受到侮辱時會作出回應。”[3]從表面看,名譽似乎是來自群體的一系列規則和必然性的東西,但布氏從關系和實踐的角度否認了這個二元論的認識。他進一步指出:“但客觀來看,所有這些行為(關于名譽的這些事情)的必然性都是事后才存在的,其實每一個時間點都是一個抉擇的結果和一個策略的表達。”[3]在卡比爾人社群里名譽是集體價值,同時又是作為集體弱點存在的消極神圣;而名譽點才是作為反擊,并保護名譽的積極神圣。由此,整個價值體系轉變為權力結構。表面看,這一思想來源于涂爾干對澳洲原始部落“膜拜儀式”的研究,但卻有根本不同。涂爾干也把“消極膜拜”看作對“積極膜拜”具有加強作用的儀式行為,但同時他又認為,“如果某人能夠服從消極膜拜所規定的禁忌,那么他和以前就會不大一樣”[4]。因此,在涂爾干那里,集體情感是被施加于社會個體的責任和義務,個體只能服從。這與布爾迪厄認為的名譽作為結果而不是必然性的規則的觀點,是不同的。在布氏看來,人不是存在于世界結構中的封閉個體,而是在其中發現自己與世界的各種聯結和關系的總和,在這個基礎上以能動的名譽點進行爭斗,生產和再生產出屬于集體的名譽結構。但布氏也提出,“名譽上的平等感可以和事實上的不平等同時存在”[3]。這能否理解為:名譽上的獲得感,能在表象上抹平不平等,調動個體完成集體名譽的再生產;同時事實的不平等,也成為個體爭斗參與社會進程的博弈空間。
埃利亞斯的人生幾乎橫跨整個20世紀,終其一生,他始終陷于一種雙重身份的沖突與危機,這也是他思想中蘊含的張力:他既是德國人,又是猶太人。[5]他認為,20世紀的社會學觀點是,“把現在、把此時此地所存在的國家體系理想化了”[1]。這一種抽象的社會觀抹平了民族和階層的差異性,把人的社會融合想象成抽象的社會體系,和建基于抽象民族民主國家概念基礎上的同一社會化過程。然而,社會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各種社會狀態和體系,個人更不是需要融入體系的單子。在埃利亞斯看來,個人就是社會進程本身,他不是獨立于社會之外,希望進入社會之中的封閉個體。“皮膚”不是阻隔人與社會之間的分界線,更沒有一種身體外殼包裹住的真正自我,人作為“‘開放的個人’的整個一生都必須向他人看齊,都必須依靠和依賴他人……人總是以多數的形式,以形態的形式出現的”[1]。人正是在與群體之間的關系中,完成了各類社會實踐,包括生產、消費、交往、教育等,在這些實踐過程中逐漸實現能動的個體社會進程。
在華康德(Lo?c Wacquant)看來,布爾迪厄和埃利亞斯都是“有關社會現實的關系性概念的堅定倡導者”[2]。埃利亞斯強調基于開放個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的個人社會進程;布爾迪厄也認為個體正是運用“積淀”于身體中的社會關系和過程(慣習),積極投身到各類場域的實踐中,參與競爭并完成社會結構的再生產。社會個體如何積淀名譽點?回到對原始社會的考查,涂爾干提出,“膜拜并非只是能夠把信仰向外傳達出來的記號系統;而是能夠把信仰周期性地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手段的集合”[4]。“膜拜儀式”是一種真實的介質生產和鞏固的集體信仰。而布爾迪厄也認為輿論賦予個體以名譽:“對于依附于名譽的事物的忠誠”[3]。對以上理論的梳理,筆者將廣告生產過程看作個體參與社會進程的框架,社群的名譽并不簡單作為命令現身,如何使個體名譽點在廣告生產過程中忠誠于市場社會建構的名譽并參與爭斗,是廣告效果達成、廣告生產過程得以實現的重要環節。同時,廣告生產作為社會過程,調動處于不平等社會關系中的個體名譽點參與爭斗,也為再建構市場價值推進社會進程提供了博弈空間。
二、理論分析:布爾迪厄“名譽”建構思想與埃利亞斯的社會過程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開始重視布爾迪厄的文化理論,并展開大量(數百篇)研究,內容涉及布氏的文化研究、“場域”理論、“慣習”概念、符號資本理論等。筆者采用的“名譽點”理論框架,在國內的研究幾乎為零。蕭俊明評價說:“他(布爾迪厄)通過多種多樣的經驗研究對結構、實踐及文化等問題進行理論探索,因而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實踐理論和文化理論”[6]。布氏始終堅持在實踐中理解人的行為,尤其是“對他們在表現中和實踐中實施的建構行動進行分析”[7]。分析個體實踐行為與社會關系,需立足于社會進程。社會進程論是埃利亞斯社會學觀點的核心之一,其著作《文明的進程》也成為社會學必讀書目之一。國內對其思想的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共50余篇,內容涉及其歷史學研究、社會文明進程理論以及個體與社會關系的思想研究。以過程論和名譽點視角分析廣告生產過程,就需要理解社會過程論視野下的個體社會進程,以及基于社會關系的名譽點爭斗與意義再生產及其博弈過程。
(一)布爾迪厄“名譽”建構思想:名譽點爭斗與意義再生產及博弈可能
布氏曾多次表示不愿為其提出的概念下確切定義,名譽及名譽點也不例外。在對卡比爾人社群的調查中,布氏從反向角度闡釋了兩個概念:“如果說名譽被定義為可以喪失或者可以被破壞的,或者直接被看作潛在的恥辱,那么名譽點雖然無法保護名譽免受所有損害,卻可以使后者得到完全的恢復。”[3]當名譽被有意無意冒犯,甚至遭受侮辱時,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會感受到來自群體的壓力——目光,或者輿論。作為擁有名譽點的個體,會選擇回應挑戰,使名譽恢復,意義得以產生。Magdalena A Grzyb發現:“現代歐洲仍存在較為嚴重的,針對女性的所謂名譽殺害(honour killings),這些傷害行為跨越了種族、階層、宗教和年齡”[8]。作者還提到,針對女性的名譽殺害,僅只因為男權社會結構受到“損害”。而來自父親、兄長或者母親的殺害行為,被施害者表述為維護應有的秩序。名譽作為一種社會價值,廣泛存在于各類型媒介文本中,并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Solen Sanli在研究土耳其日播脫口秀節目“女人的聲音”時,發現女性被剝奪公民權利的文化特征,例如性別“名譽代碼”(honor code)的內容,已經被通過國家贊助的公共廣播從公共領域仔細審查并排除在外。[9]在歐洲社會針對女性的名譽殺害,以及土耳其電視節目中女性被排除于公共領域的案例中,可以清晰看到,直至今日,各類社會沖突中仍能觀察到個體基于社會關系的“名譽點”爭斗行為,名譽不是過去式,而是一個仍在繼續的進程。
同時,須謹記布氏的提醒:名譽上的平等并不意味著事實上的平等。名譽點是作為社會進程從個人內部生長,而不是外部強加的實踐力量存在的。隨著商業社會進程加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市場社會關系被進一步自然化,廣告生產的名譽,同時也是個體的名譽點爭斗過程選擇和行動的結果。個體通過名譽點的爭斗,參與廣告意義的再生產與博弈過程。
(二)埃利亞斯社會過程與關系視角下的溝通機制
埃利亞斯的社會過程觀在《文明的進程》序言中明確表示,“本書所要研究的正是這種長期的社會發展進程”[1]。這種長期變化埃利亞斯指的是:社會結構和個人結構的長期變化。DETLEV SCH?TTKER在研究埃利亞斯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書信往來時也指出,埃利亞斯寫作《文明的進程》一書時關注的問題是:“關鍵不在于說明社會結構如何通過家庭社會化過程嵌入到主體,并決定主體的行為……而是要分析人的心理結構,如何隨著社會進程的變遷而變化。”[10]與埃利亞斯從微觀角度觀察社會過程不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社會過程思想更宏觀,同時哈維也關注到個體內化行為,“由于哈維在德國古典哲學語境中使用‘環節’①環節:哈維的“辯證認知圖式”,由話語、全力、信仰/價值、制度、社會關系和物質實踐等六個環節構成。付清松.時空構造-不平衡發展-差異與正義——哈維基于過程辯證法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圖繪.現代哲學,2013,6:30.一詞,所以它不是要素而是關系。哈維概括說,社會過程流入、貫穿并包含所有這些環節,每一個體的行為也都同時內化這些環節”[11]。由此可見,社會之于個體不是決定性的,而是個體與周圍環節產生聯系并采取行為的過程。
個體社會進程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個體通過什么樣特定的溝通機制,主動內化社會價值,或是積累個人的名譽點。“雖然埃利亞斯的文明過程論為個人行為準則內在化的國家公共維度,與同性異能的私人性功能之間提供了隱藏的軸線,但還需要通過溝通和灌輸機制重新建立聯系,自下而上的過程,從‘生活世界’內部理解世界,個體內在化才具有現實意義”[12]。自下而上的過程如何完成?在《文明的進程》第一部分中,埃利亞斯介紹了伊拉斯謨所著的《男孩的禮貌教育》,雖然在書中他并未直接強調印刷媒介在“禮貌”向“文明”轉化過程中的重要性,但仍然可以推斷小冊子的流傳對文明進程的推動作用,“這本小冊子所涉及的題目在當時正合時宜,因為它很快就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版”[1]。事實上埃利亞斯正是對中世紀流傳盛廣的各類小冊子進行研究,才從“餐桌禮儀、睡眠與飲食習慣,談話規則以及性行為和身體規范等轉變過程中,勾勒出個體社會心理的長期變化結構和過程”[10]。從這個角度說,埃利亞斯是從社會心理變遷,尤其是對人的情感控制長期變化的過程,研究總結出個人社會結構的變化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對埃利亞斯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暗含的歐洲文明中心論視角,以及將東方社會文明進程視為東方專制主義的等。[12]盡管如此,不能否認他對個體社會進程在微觀層面所做的研究。
無論是布爾迪厄的“輿論壓力”,還是埃利亞斯的“小冊子傳播”,都不約而同將特定的符號生產和敘事放在了研究個體社會關系和進程的重要位置。在卡比爾人社群中,如果沒有輿論壓力,個體就不會采取積極態度去參與名譽點的爭斗;中世紀如果沒有諸多小冊子的流行和傳播,個體的文明進程就無法完成。可見社會關系中的個人,無時無刻不在特定社會進程中采取一種積極行動。當廣告作為一種商業社會的符號生產,成為一種潛在的“社會注視”。廣泛存在于社會空間時,就不可避免會參與個體價值內化和名譽點積累過程。由廣告生產建構的社會關聯方式和意義——名譽,與個體社會進程的完成共享同一個機制。廣告生產作為社會過程,如何與社會進程關聯?一是通過“廣告效果”;二是通過個體實踐行為。個體實踐行為——名譽點爭斗,將反作用于社會進程的方向。
三、調動的名譽點和廣告生產的“效果”:與社會進程關聯的過程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流行體系》中認為:“流行變成了一個自主的文化物……概括而言,就是經由從此以后控制它的語言,流行變成了敘事。”[13]巴特將流行體系看作一種社會結構,與布爾迪厄談及的社會結構、慣習與實踐的關系問題相關聯。Koji Kobayashi等在對耐克的跨國廣告生產過程的案例分析中提出,“將實踐和過程合法化為消費者文化研究的意義是相當重要的”[14]。Humphrey也認為,“了解消費者實踐過程的合法性建立和演變方式,可以提供消費者實踐和感知取向的文化、規范和法律結構的洞察”。[15]劉泓較早在國內提出“廣告運動”與社會關系的概念,“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廣告從單一的廣告創作、廣告發布走向整體的廣告運動,而且,廣告對于我們社會生活的影響更有其特有的文化張力全面參與了社會生活的建構”[16]。柳慶勇也認為,“廣告傳播,是一種結構為‘廣告主-廣告-消費者’的系統存在,并處于更大社會系統中”[17]。廣告生產從社會過程論和實踐關系角度看,首先需回答廣告的敘事方式如何融入社會進程;同時還要解釋廣告生產不簡單是“先期規則”的結構再生產,而是個體被賦予身份之后,通過積極實踐完成的爭斗行為及結果。
1.調動名譽點爭斗的廣告效果與社會進程的關聯
1920年左右,英美煙公司①英美煙公司:近代中國卷煙業最大的外資壟斷企業,國際性煙草托拉斯英美煙公司在華的分支機構。1902年設于上海,壟斷中國卷煙市場近半個世紀之久。互動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英美煙公司.各種牌號的煙草制品基本占領中國市場。1919年前已在中國注冊的“哈德門”香煙尤其出眾,“香煙煙牌都是彩色的……煙牌正面是人物,背面是廣告”[18]。文案為:“無人不抽哈德門,是人都抽哈德門。”[19]強勢品牌推廣使“哈德門”風靡中國,生產的各品類香煙產量高達每天50億支,銷售網絡遍布我國的大中城市。[20]同時期的主要競爭對手有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生產的“大長城香煙”,以及后來居上的民族品牌——“小囡牌”香煙。黃楚九①黃 楚九(1872—1931),又名黃承乾,號磋玖,浙江余姚人。為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的后代。是20世紀初上海實業界的著名人物。中國西藥業的先驅,中國娛樂業的先驅。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黃楚九/1140490?fr=aladdin.于1915年在上海創辦福昌煙公司,生產的“小囡牌”香煙憑借獨特廣告生產方式成功打入市場,并沖擊了英美煙公司的市場份額。“小囡牌”香煙廣告——紅蛋篇,成為中國近代廣告史上的成功案例,廣為流傳影響深遠。
作為新產品,“小囡牌”香煙需找到能調動社會大眾(消費人群)名譽點,參與其廣告生產過程的方法:一是,民族品牌崛起;二是,傳統文化的共鳴。兩個元素可以對應于當時社會受損的名譽,從而調動大眾的名譽點爭斗行為。黃楚九首先在《申報》《新聞報》等上海各報包下了第一版全幅廣告:第一天,版面上只有一個大紅蛋;第二天,又換了一根小孩的發辮;第三天,則出現了一個惹人喜愛的胖娃娃;第四天,報紙終于揭開謎底,刊出了一條“祝賀大家早生貴子”的賀詞。[20]一來慶祝“小囡牌”香煙誕生,二來與“有子萬事足”的民俗風情相契合。除在報紙上投放廣告之外,黃楚九還在馬路上張貼紅蛋廣告,同時要求“上海大世界”里節目上盡可能以說、噱、彈、唱的方式,加進一些介紹“小囡牌”香煙的話語。[21]“小囡”品牌名與“紅蛋”的形象設計,使消費者產生“得子”聯想。這與“哈德門”香煙品牌塑造的“現代形象”形成對照,喚起強烈民族自覺意識的同時,也產生傳統文化的共鳴。廣告生產成功調用目標人群的名譽點爭斗行為,促進了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品牌認同,廣告效果大獲成功,對當時的英美煙公司造成巨大沖擊。為扼殺對手,英美煙公司最后不得不以20萬元的代價收買“小囡牌”商標。[20]
關于品牌命名與消費者影響之間的關系已有研究得到證實。Keller,kl在研究廣告中的記憶因素時發現,“一個品牌的名稱被認為是建立新產品品牌資產的重要手段之一”[22]。而Kevin Lane Keller,Susan E.Heckler,Michael J.Houston在研究暗示性品牌名稱對廣告回憶度的效果時提出,“品牌名稱具有暗示性,則能提高消費者的品牌回憶度,從而達到促進廣告效果的目的”[23]。消費者將“小囡”與“紅蛋”所暗示的民族情感與社會習俗認同直接相關,積極參與到“小囡牌”香煙廣告生產過程,并推動廣告生產融入社會進程中。
2.廣告效果以消費者品牌關系的培養為目標
廣告效果養成的消費者品牌關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通過持續的廣告生產長期培養和維系。Jun Pang,Hean Tat Keh,Siqing Peng發現:“對于不同產品來說,廣告策略與產品類型之間存在互動,影響消費者的品牌喜好度”。[24]1986年江蘇鹽城無線電廠②江蘇鹽城無線電廠:江蘇燕舞電器集團有限公司的前身,位于江蘇沿海城市鹽城市,為江蘇省級企業集團和國家大型一類企業。公司始建于1968年,20世紀80年代,企業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迅速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收錄機生產基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燕舞音響曾以較高的質量暢銷全國。“燕舞,燕舞,一曲歌來一片情”的廣告詞響徹大江南北。跨入全國大型工業企業500強的行列,銷量連續8年在全國收錄機行業領先。“燕舞集團”,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燕舞集團.生產的燕舞牌收錄機廣告登上了中央電視臺。燕舞選擇情感訴求的廣告方式,啟用當時還是普通中學生的苗海忠(18歲)演繹廣告歌曲:“燕舞、燕舞,一曲歌來一片情……”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逐漸鋪開,伴隨市場開放而來的港、臺流行樂和西方搖滾文化逐漸進入中國社會,影響當時的文化潮流。陽光帥氣的苗海忠成功表達了青年追求活力與自由的價值訴求,與改革開放之前市場的“保守與僵化”形成對比,有效調動當時廣大青年和普通消費者崇尚“自由與個性”的名譽點爭斗實踐。Jun Pang,Hean Tat Keh,Siqing Peng也發現“情感廣告對基于價值的產品更為有效,更能增進消費者品牌喜好度”。[24]到1987年,“燕舞”的廣告費已達400多萬,家喻戶曉的廣告效果,幫助“燕舞”創造了2億臺的銷量。[25]“燕舞”廣告生產不僅引領文化潮流,也影響消費者與“燕舞”品牌之間的關系。
廣告生產可以促進消費者品牌關系的長期性和牢固性,Aggarwal研究發現,“大眾甲殼蟲的品牌狂熱分子已經會給他們的汽車命名,與它們談話并帶有情感地撫摸它們”[26]。而在之前Belk更提出,“這一過程的動機是消費者將他們的財產(即品牌)視為他們的自我延伸”[27]。當時的“燕舞”除了被看作流行文化的標志,在廣大農村市場還被當作財富的象征。時任鹽城無線電廠副廠長張興榮在接受網易財經記者采訪時說:“北方農村是三間房子,中間一個堂屋,進去以后有一個大的條臺,人家一進門,就看到臺上放鐘之類象征家里財富的紀念品。當時人們一般都放收音機……后來收音機過時了,就有了收錄機。”[28]獨特的產品設計和超大的喇叭外形,逐漸使消費者將“燕舞”與“家庭財富”相關聯,并采取積極的名譽點爭斗行為參與到廣告生產過程。事實上在今天看來,當時“燕舞”廣告的策略仍是非常現代的情感和價值訴求生產方式:“積極投放地方廣播廣告‘燕舞之聲’;開展體育營銷:舉辦‘燕舞杯’北京國際田徑邀請賽(1986),贊助娛樂節目:在首都體育館舉辦‘燕舞迎春晚會’(1988)。”[29]正是由于“燕舞”成功運用與建構了改革開放帶來的,“青年流行文化”和“鄉村社會追求勤勞致富的美好愿望”兩個名譽,才能調動消費者的名譽點爭斗行為參與廣告生產,實現消費者品牌的長期良性互動。
其實在當時的競爭環境下,外有三洋、松下;內有神笛、上海、春雷、紅燈、漓江等品牌,“燕舞”作為江蘇鹽城地方小廠生產的新產品,并不具備先天優勢。1986年的“一曲歌來一片情”從中央電視臺唱響全國,其情感定位的廣告生產模式與特定社會文化和進程的契合,成功調動消費者名譽點爭斗行為,積極參與廣告生產的社會過程,不失為一個補充視角。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現代廣告,開始與世界市場接軌,世界消費市場的理念和價值體系——除商品實用功能之外的情感和價值訴求——逐漸推廣開來。廣告生產的價值敘事是融入社會進程的,正如巴特所說:裙子通過修改長短來定義流行,然而裙子始終還是裙子。流行不會脫離社會而創新,廣告亦然。然而,基于特定廣告效果的消費者(社會個體)是如何運用名譽點爭斗行為,主動參與廣告生產過程,又如何反作用于社會進程等問題是下文需要回答的。
四、基于消費關系的行動社會個體:以名譽點爭斗為動力參與廣告生產
既然個人不是簡單被社會規則嵌入的封閉個體,那么廣告作為特定社會符號生產也不能命令個體形成態度并采取行動。從“廣告主—廣告—消費者”關系系統看,廣告主發出廣告的最終目的是消費者,但到達消費者需要經由社會環境。如此“廣告生產—社會結構(市場)—社會個體(消費者)”就發生了關聯。廣告效果融入社會進程調動社會個體的名譽點爭斗,才能將消費者動員到廣告生產過程中。從布爾迪厄和埃利亞斯的社會關系與過程視角看,廣告生產其實是調動積累于個體身上的名譽點——市場培育的特定意義結構、消費行為和文化態度等——通過特定的爭斗行為完成的社會過程。這就需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廣告生產過程中以消費內核的社會關系如何建立;第二,個體如何調動自身“名譽點”主動參與廣告生產的過程。
1.由社會的消費到消費的社會
基于消費關系的價值體系逐步確立。Jun Pang,Hean Tat Keh,Siqing Peng發現:“廣告是通過‘認知、情感和互動’來影響消費者與品牌之間關系的,有效的廣告會從品牌親密關系、品牌激情和品牌承諾三個方面入手培育不同的消費者品牌關系。”[24]20世紀80年代市場環境下的廣告主將品牌看作消費者的,也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廣告主與消費者,社會結構與社會個體之間的聯系是有機的。燕舞廠工友自稱為燕舞人,工人將企業看作“家”,將消費者的認可作為前進的動力,是將社會價值前置,并融入消費關系中的一種體現。這不同于今天富士康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自產品被送出流水線的那一刻起,產品與工人之間就再無半點關系。
隨著市場社會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消費者與品牌的關系逐漸發展成為獨立于社會諸多關系的獨特性存在,消費社會價值體系逐步建立,建基于此的廣告生產過程所建構的名譽與社會價值本身形成張力,消費者名譽點爭斗成為反制的能動力量,影響廣告生產進程。2013年8月20日,南方都市報刊發了一個整版“無節操”廣告,廣告內容看似“現任張太”挑釁“前任張太”。整條廣告采用了“小囡牌”香煙廣告的創意,接連幾天刊發帶有懸念的連續廣告文案。第一天文案為:前任張太,你放手吧!輸贏已定。好男人,只屬于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落款為:張太。第二天文案則以數據說明中國女性市場生活時間分配等;第三天文案,揭曉答案,向社會道歉:但抱歉!我前天沒有說清楚,其實,前任張太,現任張太都是同一個“我”。該整版廣告是某國產化妝品廣告。雖然最后一天,答案揭曉。消費者卻不買賬,廣告發布的第一天輿論嘩然,廣告主沒有等來消費者的驚喜,換來是全民憤慨。
廣告發出后幾天,“記者8月29日從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獲悉,按照總局要求,廣東省新聞出版局目前已對南方都市報社下達警示通知書,予以通報批評并責令改正。該報也已經采取整改措施,進行補救”[30]。這個案例從廣告創意的專業角度看并無問題,但將廣告生產建構的名譽與社會現實意義關聯之后,就會出現與社會價值沖突的情感問題。消費者并不是被命令的個體,而是在社會前規則建構的慣習影響下的能動個體。消費社會所調動的名譽點與社會個體本身積累的社會價值同時存在于個體內部,兩者相互協作也形成沖突,這個張力推動消費者個體在市場社會的變遷中,參與廣告生產賦予的名譽點爭斗,并反作用于廣告生產,進而影響社會進程。
2.市場社會價值體系的名譽建構與名譽點爭斗及意義再生產
布爾迪厄研究卡比爾社群時發現,社會成員正是在日常沖突中,不斷運用個人的名譽點,以爭斗方式完成社群名譽的維護和建構,以實現社會意義的再生產。廣告生產除調動社會原有的名譽結構外,還能建構服務于市場社會價值體系的名譽結構。廣告輿論通過敘述的“沖突”①“沖突”類似于布爾迪厄在名譽點爭斗具體規則分析中的“挑戰”:名譽爭斗有三條具體法則:首先,承認對方名譽上的平等;其次,當被挑戰者無能力應對挑戰時,發起挑戰者將踐踏自己的名譽;最后,只回應與自己名譽對等的人發出的挑戰。皮埃爾.布爾迪厄.實踐理論大綱.高振華,李思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23-25.——與名譽感之間的差距——來培育和調用被商業化邏輯賦予名譽點的社會個體能動性。通常所說的社會個體參與的廣告生產是指,消費者作為生產主體參與廣告文本的創作過程,“隨著傳播環境變化,媒介生產與消費在此過程中發生著深刻而多變的交織,媒介消費者同時表現出生產者的角色”[31]。關于消費者參與具體生產過程,理論界稱之為“無形勞動”②無形勞動:第一種形式主要是文化(知識或語言)上的,如問題求解、符號型的和分析型的工作、語言表達。通過這些工作,人們生產概念、符號、代碼、文本、圖像等。第二種形式是情感驅力上的,它與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有關。曹小春.論消費者生產.廣東商學院學報,2012,6:39.。蘇特.杰哈利(Sut Jhally)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當受眾在收看商業電視的時候,就是正在為媒介工作,由此生產出價值和剩余價值。”[32]針對廣告生產過程中的個體,“對于斯邁思來說,整個廣告過程的關鍵在于受眾接受了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32]然而,廣告作為個體內化社會價值的一部分,不僅指被消費者吸收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更是布爾迪厄試圖要解釋的社會進程中的個體能動部分——名譽點。
2018年6月24日,釘釘③釘釘(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團專為中國企業打造的免費溝通和協同的多端平臺,提供PC版,Web版和手機版,支持手機和電腦間文件互傳。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釘釘/16595044?fr=aladdin.在上海漕河涇地鐵站專列廣告發了一波#去他的職場規則#:數十條針對職場新人的文案句句“扎心”。比如:苦勞是你的,功勞是別人的(劃線);年輕人吃點兒虧怎么了(劃線);讓資歷老的先升職,年輕人有的是機會(劃線)……[33]。劃線的廣告創意,意味著否定,否定所謂傳統“職場規則”。然而所謂職場規則只是雇傭關系等諸多不平等社會關系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下一站:新工作方式”被釘釘廣告重新建構為市場社會獨有的名譽結構,由廣告敘事賦予的名譽點爭斗行為,則在一個既定的市場社會價值框架內展開,消費者看似在抗爭,事實上卻成為強化“職場規則”的名譽結構,并促成不平等關系再生產的一部分。同樣的例子來自“拼多多”:“拼得多,省得多”并不能解決分配不平等的現實問題,針對中下層消費人群的“拼多多”非但沒有抗爭分配不均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反而是在強化這個既定的市場社會邏輯。
調用個體名譽點爭斗的廣告生產過程,完成市場社會價值建構與再生產的同時,也從過程內部建構起價值博弈的新空間。為什么馬克思、韋伯、埃利亞斯、布爾迪厄等學者一定要強調社會的實踐性和過程性,而不是結構性,是因為過程是個體無法逃避的歷史性。廣告生產作為社會過程,同樣是個體無法回避的有意義的社會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交予的名譽點,是他們作為社會人的能動性表現之一,也是他們借由參與的廣告生產過程推動社會進程的巨大動能。
五、意義再生產與博弈的空間:廣告生產過程中的個體名譽點爭斗反思
2018年5月一篇10萬+的自媒體文章“凌晨3點不回家:成年人的世界是你想不到的心酸”刷爆朋友圈,文內配有一條視頻廣告,講述了三位職場女性(初入職場的實習生、醫院急診科護士長和廣告公司客戶經理)在深夜克服困難,加班完成工作的故事。該廣告發出后,輿論呈現兩種態度:一種以新華社公號為代表,“為了夢想,為了家人,抑或是為了成為更好的自己,職場不相信眼淚,于是你擦干眼淚,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34]。與新華社態度不同,“澎湃新聞”以“‘凌晨三點不回家’刷屏,別矯情了!”為題對該文進行回應:“‘凌晨3點不回家’背后是大都市群體對收入和工作的焦慮感,更是對現實難題的無力感……不斷鼓勵自己是必要的,但千萬不要陷入一種盲目的自我感動里。”[35]廣告生產參與建構的社會名譽,也包含市場社會進程中商業意識形態對傳統價值的“征用”。當“焦慮”和“自我感動”成為廣告生產調動的個體名譽點時,商業社會建構的意義就開始“獨立”運轉:都市人群(個體)首先是對市場社會價值及上升渠道深深不確定性產生焦慮,而這個焦慮感從市場本身是無法尋求保障的,于是個體會轉向自身的名譽點爭斗,以尋求克服不確定性的方法——自我感動,用自我勸服的方式激勵自己克服焦慮感,不斷向前奔跑。
然而,個體名譽點爭斗也是個體在社會實踐中反作用于社會進程的核心機制。因此,當廣告生產調動個體名譽點爭斗參與廣告建構的意義再生產時,個體同樣會影響廣告生產的進程,甚至反對廣告生產所建構的商業意識形態。在上文的評論區,能清晰窺見個體的名譽點爭斗能動性與反作用,“我見過廣州凌晨123456的廣州,也錯過最后一班公交車,也睡個(過)公園長椅,可是你也別想著別人會心疼你,因為沒有誰為你買單,事情總是地(得)自己做,總地(得)自己扛”。[35]此評論獲贊1.9萬次之多。由此可見,廣告并不是被廣告商生產出來投入到社會中的待解符號,而是自被生產之始,就調用各種個體名譽點爭斗行為的過程,這個進程既是社會意義再生產的過程,也是個體反抗性爭斗博弈的空間。
當效果指向的廣告生產融入社會進程中,當“凌晨三點不回家”成為時尚,當“拼得多、省得多”成為自然,當職場規則成為要去反抗的規則……那么布爾迪厄的擔憂,就有可能成為現實:“一個家庭越是易受到攻擊,就應該有越多的名譽點,以便保護它的神圣性,而輿論也會賦予它越多的功德和尊重……人們反而高看那些雖然貧窮并處于特別容易遭受羞辱的境地,但最終贏得尊重的人。”[3]因為在消費社會的邏輯里,貧窮就意味著易受傷害。但社會仍要繼續,就需要賦予貧窮以更多的名譽點,輿論也要賦予它更多“尊重”……廣告生產過程遵循這個邏輯,將市場社會隱藏的不平等關系,通過被賦予的名譽壓力轉嫁給個體的名譽點,利用社會的溝通機制(輿論)和個體能動機制(個體擁有的名譽點),在社會進程中完成了廣告生產所代表的市場社會商業意識形態建構和再生產。同時,研究也發現,廣告生產的社會過程通過調用個體名譽點爭斗行為,參與市場社會價值主導的名譽建構的同時,也抗爭性地建構社會與市場價值的博弈空間。由此,個體參與的廣告生產融入并推動社會的進程。這亦可作為布氏“名譽點”理論的延伸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