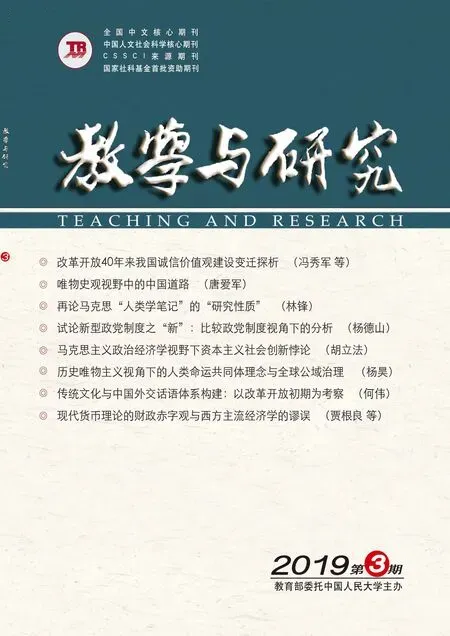試論新型政黨制度之“新”:比較政黨制度視角下的分析*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當代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既不同于歐美國家延續了近兩個世紀的政黨制度,也不同于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存續了70多年的政黨制度,更不同于它誕生之前已然存在近30多年的舊中國政黨制度,而是一種產生于中國土壤,至今已經過70余年歷史考驗、日臻完善成熟的世界范圍內的新型政黨制度。理論界對它的關注始于新時期之初,學術界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視其為特定研究對象。但從科研論文成果的數量看,關注和研究熱潮呈現于2018年3月,[注]中國知網提供的信息顯示,主題為“新型政黨制度”的論文,2018年之前僅18篇,而2018年以來已達87篇(2018年8月之前)。這主要是因為習近平在“兩會”期間對中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點所做的新闡述引發了研究者的廣泛興味。就研究現狀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學術界,大多數論者從政黨的利益表達的充分程度、功能發揮的充足程度、績效實現的計量結果等方面對“新型政黨制度”特點和優勢做了闡釋。這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以理論和實證、歷史和現實相統一為依據,從比較政黨制度角度較為全面地、深入地展示“新型政黨制度”之“新”的特征,目前這方面的闡述并不多見。[注]許多文章在論述這一問題時,一是以西方功利主義政治學理論為依據說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合理性,忽略了該制度形成之初和后來發展的根由——追求中華民族現代化,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政治追求的最低“道義”;二是有些論者關注了最低“道義”基礎,但忽略了這一制度的倡立者、主導者——中國共產黨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道義”追求,以及共產主義者的政黨觀,夸大了這一制度的歷史價值;三是對近代中國先賢尋求政黨制度合適性的史實認識過于簡單化——從“多黨制”到“一黨制”,再到“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制等,使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和實證說明力度明顯不強。本文作一嘗試。
一、與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相比之“新”
在人類政治歷史長河里,歐美國家的政黨現象已經存在了近340年之久。19世紀30年代初政黨政治步入制度化發展階段,政黨制度由此逐漸成為與選舉制度、代議制度相依存的西方民主政治三大制度支柱之一,且是其他兩種制度得以實施的政治和組織保障。迄今為止,在歐美國家和受西方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按照政黨數目、相互關系、執政方式等要素綜合考察,政黨制度可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在近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相對于選舉、議會、內閣、元首制度,政黨制度并無憲法文本的明文規定,與其說是制度,毋寧說是一種憲法慣例。如果按照政治民主原則,“多黨制”是政黨政治的常態,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是其產生的內在因素,而比例代表制是它存在的制度原因。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正式確認“多黨制”為其政黨制度。隨著議會制度在歐洲大陸的推行,德國、意大利、愛爾蘭、比利時等國也都實行了“多黨制”。二戰之后,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建立起了“多黨制”。“民意”能夠得到較為充分表達,但政局相對不穩,內閣更迭頻繁,行政效率不高,是其主要特征。“兩黨制”是“多黨制”的一種特殊形式,即在同一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內多黨合法并生并存的環境下,有兩大勢均力敵的政黨長期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狀態。它的出現與所在區域范圍內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選舉制度相對簡化等因素有關。利益表達集約化程度較高,政局的穩定性和政策的延續性較強等,是其顯著優點。按原初意義,政黨本身是同一國家或政治共同體內“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的利益代表集合,所以,“一黨制”完全是近代政黨政治的異類,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政治價值遭遇扭曲的產物。1928年底的意大利、1933年底的德國分別以法律形式宣布實行“一黨制”。二戰期間,日本和西班牙也實行過“一黨制”。在實行“一黨制”的國家,國內只允許一個政黨合法存在,其他政黨、政治團體均為非法,多被取締、解散;在統治方法方面,這些一黨專制政權主要靠謊言欺騙、暴力恐嚇來維系;在體制方面,實行黨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全面統治,而且在黨內通常制造個人迷信,推行黨魁獨裁制。“一黨制”盡管在短時間里因迅速實行國家統一(意大利法西斯蒂)或全民意志集中(德國納粹)而令人眩目,但由于它終究與近代政治文明完全背離,很快被歷史潮流拋棄。
就國際背景而論,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西方世界的“多黨制”、“兩黨制”、“一黨制”并列而存于中國人面前,且各呈其優勢。除中共之外的中國各種政黨、政團、政派組織及其代表人物,都做過自以為是的各種選擇,但中國最終還是選擇了新型政黨制度。究其根由在于中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科學理論,尤其是政黨學說運用于中國革命實踐而得出了符合中國近代政治發展規律的結論。這種科學的理論和學說內容豐富,其中最被人們熟知的是列寧的那段經典論述,“在通常情況下,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頁。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成書于1920年6月,最早中文譯本1927年出版。列寧在這里告訴人們:政黨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現代的文明”社會的產物;政黨是本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斗爭的領導者;政黨是按照一定的組織原則、由穩定的領袖集團集合起來的有紀律的團體;政黨斗爭的直接目標是掌握國家政權。
依據這些理論觀點,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認為:第一,階級性是政黨的本質屬性。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在現代中國,有多少階級就應該有多少政黨,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因此,反對階級區分和階級斗爭,號稱要進行全民性“國民”革命,一度仿效意大利法西斯蒂的中國國民黨推行極端化的“一黨制”——“一黨專政”——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那些無視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后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無視中國社會階級力量對比的政黨、政團、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公開表達或婉轉陳述要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多黨制”,只是一廂情愿的想象而已。所以,“一黨專政”制、“多黨制”均不適合中國國情。第二,歷史性是政黨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政黨是階級社會特定時代的產物和現象,所以一旦階級消失了,政黨亦隨之消滅。“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頁。中國共產黨對于政黨這一基本特征的揭示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學說,更超越了現代中國其他政黨理論,這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深刻理論依據。第三,包容性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支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是中國政治的優良傳統。“唯我獨革”“唯我獨存”“唯我獨大”的“一黨專政”制度,不“和”也不“周”;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西方式“多黨制”,又“同”又“比”,它們都不合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精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適合于超越了不同階級、階層利益訴求的更大的、共同的民族國家目標,既“和”且“周”。尤其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民主黨派賴以存在的階級基礎行將消失之際,中共依然秉持包容政治文化精神,強調“要有這么一個‘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可以安定各階層,安定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安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中共仍然強調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存在的重要價值,“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通過政協容納許多人來商量事情很需要”。[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384-385頁。更重要的是,這種包容性還體現在中國從來不將這種新型政黨制度奉為圭臬而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實行的政黨制度評頭論足,這與不少西方國家完全不同。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真正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
二、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相比之“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頁。同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社會主義政黨制度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政黨制度。因此,從比較政黨制度角度分析這一制度之“新”,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政黨制度理論的基本觀點,必須了解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的基本狀況。
馬克思、恩格斯一直認為,共產主義政黨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過程中,要努力同其他革命階級、政黨和社會力量結成聯盟,建立起一切財富生產者的政權。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強調:“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他們列舉了共產黨人支持英國憲章派、北美土地改革派、法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瑞士激進派、波蘭發動過克拉科起義的政黨等事實。不過,他們同時強調,盡管共產黨人與這些政黨、政治組織在“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是一致的,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在他們看來,共產黨人在為工人階級解放的斗爭中,于理想和目標方面,有著高于、遠于一般工人階級政黨和其他階級、階層的政治組織的追求;于組織和協調方面,“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435頁。換言之,共產黨人在斗爭中,對他們要發揮領導和引導作用。從實踐層面看,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建立的政權就是幾個革命階級、階層建立的聯合政府,“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公開地團結在工人革命旗幟下”,[注]“這證明公社完全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9、102頁。在后來的革命斗爭中,盡管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斷以新的形式展現出來,民族國家內的共產主義政黨已經建立,但是馬克思、恩格斯一直堅持認為,工業化的發展,使得社會階級、階層分化與聚合現象日趨復雜,工人運動規模也不斷擴大,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內都不可能只存在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這些政黨之間不但要善于團結斗爭,而且還要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恩格斯晚年特別重視工人階級政黨與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反對視“農民反動一幫”的謬論,認為一旦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黨需要大批的專家。
列寧繼承和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領導與多黨聯合革命的思想,并在實踐中進行了新的探索。在理論上,一方面,他強調共產主義政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在革命年代,列寧強調幾乎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緊密地靠近我們黨”。[注]《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3頁。取得政權后,列寧針對黨內出現的否認黨的領導的主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黨是直接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是領導者”,[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423頁。國家是實行黨的主張的強制領域,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另一方面,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共產主義政黨與其他政黨和政治組織、社會團體的關系。十月革命前,基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遠大目標,他要求無產階級決不應該排斥其他階級和政黨,而“應該支持進步階級和進步政黨去反對反動階級和反動政黨”。[注]《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2頁。十月革命后,基于革命形勢的嚴峻性,他強調在堅持無產階級獨立性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前提下,蘇維埃政權必須吸收代表其他勞動階級或者階層利益的政黨參加。
但是在革命過程中,蘇俄政黨制度經歷了從多黨合作制到共產黨一黨制的轉變。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俄國進入多黨并存的狀態。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作出與蘇維埃其他黨派代表組成聯合政府的決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右派拒絕與布爾什維克合作。12月底,左派社會革命黨決定參加蘇維埃政府,兩黨聯合政府成立。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雖然不愿參加政府,但在全俄蘇維埃中仍占有一定席位。1918年3月,因反對蘇俄政府與德國政府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左派社會革命黨退出政府,兩黨聯合執政結束。8月,該黨因反對布爾什維克在農村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而在莫斯科發動了武裝叛亂,但很快被鎮壓。由它分化出來的俄國民粹派共產黨和代表農民利益的俄國革命共產黨,繼續與布爾什維克合作。這年年底,民粹派共產黨全部加入布爾什維克。1920年8月,共產國際二大決定一國只允許建立一個共產黨,俄國革命共產黨并入俄共(布),蘇俄由此也成為共產黨“一黨制”國家。
蘇俄(聯)“一黨制”直接影響了后起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選擇。第一種是直接效仿蘇聯采用“一黨制”,如蒙古人民革命黨之于蒙古人民共和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之于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第二種是由“多黨制”轉變為“一黨制”。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古巴、越南、老撾、柬埔寨本來實行“多黨制”,受蘇聯影響,共產黨執政后都變為“一黨制”。如羅馬尼亞在二戰期間就存在反法西斯的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國家農民黨、國家自由黨等政黨,但1944年8月23日武裝起義之后,國家農民黨拒絕接受民族民主陣線綱領而成為國內反對派支柱,1947年被解散;國家自由黨亦于同年停止活動;1948年2月社會民主黨與羅馬尼亞共產黨合并為羅馬尼亞工人黨,羅馬尼亞人民(“人民”后改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只有羅馬尼亞工人黨(后改為“共產黨”)一黨,且由該黨長期執政。第三種表面上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制”,但共產黨外的政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其實不發揮獨特作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民主德國等國就是這樣。如保加利亞,二戰結束后,領導祖國陣線和人民起義解放軍取得勝利、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保加利亞工人黨改名為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人)并成為執政黨。1948年,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廣泛派社會主義者)并入保加利亞工人黨(共)。同年12月,保加利亞工人黨(共)恢復保加利亞共產黨名稱。曾經參加過祖國陣線的保加利亞農民人民聯盟于1947年12月宣布繼續與保加利亞工人黨(共)合作,到1971年10月,修改后的黨綱與保加利亞共產黨幾乎一致。
毫無疑義,從理論上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共產黨“一黨制”,在發揮共產黨的利益聚集和表達、干部的培養和選用、對人民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動員,以及組織高效政府等方面的作用上,是資產階級任何政黨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從實踐上看,蘇聯通過共產黨的“一黨制”,依靠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并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實,對后起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揮了榜樣和示范作用。這是這些國家采用共產黨直接的或變相的“一黨制”的重要原因。問題是,十月革命之后,列寧便發現舊時代的官僚主義現象并不因為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和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消失,相反地,“官僚主義就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注]《列寧選集》,第4卷,第510頁。以致各種官僚主義的現象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之初就泛濫起來,并逐漸蔓延到各個領域、部門,且滲透到黨內。列寧指其為“禍害”、“膿瘡”,甚至痛感蘇維埃俄國是一個“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注]《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4頁。而正是這難以克服的官僚主義弊端最終導致了1989年6月到1991年12月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劇變。從政黨制度的角度看,官僚主義成為痼疾,與忽視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忽視這一不平衡基礎上所有制的多樣性,忽視這種多樣性基礎上人們利益訴求的不一致,忽視這一訴求不一致基礎上非共產主義政黨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忽視這些政黨對執政的共產黨具有民主監督功能有著直接的聯系。
與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不同,中共從建黨之初就認識到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各政黨、政派、團體政治合作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的重要價值。統一戰線被中共視為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在后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中共始終強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意義。“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頁。
由此可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長期斗爭中形成的,黨際之間表現為“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非競爭型協商合作關系。這與十月革命前后俄國議會中存在的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合法競爭型的“多黨制”不同。也與有些社會主義國家采用的形式上的“多黨制”不同,因為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存在著實質上的“互相監督”關系。更與后來蘇聯及受其影響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共產黨“一黨制”相迥異。
三、與中國近代史上其他政黨制度選擇相比之“新”
近代中國人關注西方政黨制度始于中日甲午戰爭之后。空前的民族危機激發了一批有識之士革新政治制度的愿望。其中,以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為追求的維新保皇派人物對西方政黨制度尤為關切。自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至辛亥革命爆發,海內外立憲派人士和部分革命黨人以很大的熱情討論立憲后中國應選擇何種政黨制度的問題。從辛亥革命爆發到民國第一屆國會解散,中國進入“多黨制”時期,前后約有312個政黨、政團組織活躍在政壇上。[注]邱錢牧:《中國政黨史·緒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頁。有意思的是,熱心政黨政治的人們大多并不認同“多黨制”,而是選擇了“兩黨制”,“黨少者國安,黨多者國危,黨尤多則國可亡,若僅兩黨,則人與天合,國以富強,在朝在野,旗鼓相當”。[注]《康有為政論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723頁。有的人甚至提出了消除“多黨制”、實現“兩黨制”的行動方案,但都以失敗告終。無論這些人的“初心”如何,它們的共同點是都把政黨的本性定位于“公德”而非“私利”上。彼時中國出現“多黨制”除了政局劇變外,社會經濟關系的復雜性是其根源,“兩黨制”只是人們的主觀愿望而已。只要這一根源還存在,多黨并存的局面就會存續。
1914年年初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和地方自治會后,民初多黨并生現象暫時結束,軍閥專制和朋黨角逐局面開始出現。1914年6月至9月間經歷了“二次革命”失敗的孫中山開始否定一年前支持“多黨制”的立場,且從質疑西方政治自由主義的角度回到了辛亥革命前“一黨制”的追求,“第一次革命度量太寬,所以反對黨得從中入涉,破壞民國。第三次成功,非本黨不得干涉政權,不得有選舉權,故將來各埠選舉代表,非本黨人不可。”[注]《孫中山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104頁。幾經重大挫折之后,孫中山受十月革命成功經驗的影響,產生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允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進行國民革命的思想。不幸的是,從他因病逝世之后,中國國民黨便在政治上節節倒退,形成冥頑不化的“一黨專政”政黨制度。1928年6月,國民黨在南京開始“訓政”,宣稱“以黨治國”,“一切權力皆由黨集中,由黨發施。政府由黨負其襁母之責,固由黨指揮,由黨擁護”。[注]《胡漢民先生文集》,第1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第409頁。非但如此,國民黨還提出黨獨存的主張,“中國國民黨根據以黨治國原則,不允許其他政黨在中國境內有所活動,如發現有此種組織及反動言論與行為,應以政治的力量,立予制裁,并消滅之”,“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及共產黨、第三黨、國家主義派及一切違反三民主義之分子”。[注]《中央16次常務會議記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抗戰初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國民黨迫于形勢壓力,不得不承認共產黨和其他一些黨派的合法地位,但其“一黨專政”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以居高臨下“接納者”的姿態要求全國各黨派人士“尊重”國民黨,“服從”國民黨政府法令,“不違反”蔣介石的“三民主義”。[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511頁。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并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1943年初國際反法西斯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后,國民黨從中國封建哲學倫理和宗法制度出發,大肆宣揚其“一黨專政”的“正統”性與“合法”性,攻訐共產黨,排斥民主黨派。抗戰進入反攻階段后,國民黨竭力詆毀和反對共產黨“聯合政府”的口號,在所謂“民主建國”綱領中頑固堅持“一黨專政”制度。抗戰結束后,以國、共為首的兩大政黨陣營對峙局面逐漸形成。國民黨自恃有美國政府支持,一方面與中共和民主黨派虛與委蛇,另一方面積極部署內戰。1946年11月,國民黨自以為內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后,立即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該《憲法》以不少西方民主詞匯做包裝,將“一黨專政”合憲化、合法化。不但如此,國民黨在打擊共產黨的同時,還對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采取打壓政策,甚至宣告民盟為非法團體,迫其解散。國民黨 “一黨專政”的倒行逆施在其推向高潮的 “行憲國大”之后很快走向末路,除了民社黨和青年黨外,絕大多數中間黨派與國民黨分道揚鑣,紛紛走進了共產黨領導的推翻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人民革命隊伍。1949年12月,國民黨殘余勢力及民社黨、青年黨徒眾逃往臺灣,悖逆現代世界政治發展潮流,違背中國現代民主建設要求和人民意愿的“一黨專政”制度破產。
與國民黨不同,中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從階級性看政黨的本質,從實踐性選擇政黨制度。中共二大就主張與國民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其他各革新團體形成“聯合戰線”,使思想進步的國會議員形成“民主主義左派聯盟”,將全國各城市的群眾團體組織成“民主主義大同盟”。[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40頁。獨立領導革命初期,中共在領導武裝暴動時一直保持與國民黨左翼力量的合作關系。長征結束后,中共中央批評和糾正了黨內的關門主義錯誤,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任務。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共對國內政黨關系有了新認識,主張“把各黨派力量匯在共同政治基礎上形成民族統一戰線——首先是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注]其光:《毛澤東的談話》,《解放》第31期(1938年2月2日)。在堅持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在同國民黨的合作與斗爭中,中共形成了自己的國內黨際關系處理原則、策略和方法:其一,堅持中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1935年底中共就提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7頁。整個全面抗戰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國民黨斗爭,與共產國際爭執,與黨內動搖傾向交鋒中,堅持了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抗戰勝利后,毛澤東曾經總結道:“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8頁。其二,堅定中共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立場,這也是堅持黨的領導權的前提條件。一是無論是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還是相持階段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抑或是面對抗戰即將勝利而國民黨高喊“統一國家”,中共一直加強黨內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建設,加強軍隊內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證黨和人民軍隊性質;二是時時以大革命時期的沉痛教訓教育全黨,保持黨及人民軍隊、根據地政權的獨立性;三是從民族大義、人民利益出發,提出不同于、高明于國民黨和其他黨派令人信服的政治主張并付諸實際行動。其三,在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原則,打擊和孤立頑固派,使其反動性收斂,并以此贏得國民黨內中間派和進步派同情,使其與頑固派逐步劃清界限。其四,把爭取代表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地方實力派的黨派的支持作為“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來對待,主要方法是不斷發展進步力量,尊重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堅決地同頑固派作斗爭且取得勝利。其五,以實際作為試行新型政黨制度。一是廣泛推行了“三三制”原則。中共強調根據地政權是統一戰線政權,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別的黨派的“一黨專政”,而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和活動之權。”[注]二是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居于領導地位。中共一方面要求在民意機構和政府機關中,黨員要“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來實現黨的領導;[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0-761、741頁。另一方面強調黨“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二冊(1942—1944),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第124-125頁。
抗戰勝利后,中共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口號,以極大的誠意提出各黨派平等地位和聯合政府主張,促成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贏得了中間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解放戰爭期間,中共在軍事上歷經艱難險阻,走向節節勝利,增進了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其理想、目標及其實現途徑正義性、正當性的認同和感佩;在政治上耐心地傾聽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政治訴求,與他們坦誠溝通,積極擴大共識面;從抗戰結束后中國兩種命運尖銳斗爭的現實出發,批評了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的錯誤主張,使其鼓吹者放棄了過去的觀點,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最終,根據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五條的精神,1949年9月下旬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由中共發起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確立。這一制度延續至今近70年,雖經挫折,但日臻成熟,成為世界政黨制度中的新型種類。
中國近代之所以最終確立這種新型政黨制度完全是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之所以是歷史的選擇,是因為中國近代的歷史主題是如何使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多民族的農業文明的國度變成為現代化國家。通過政治制度的革新實現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為各方面現代化建設開辟廣闊的發展前景,是實現這一主題目標的基本前提。因此,政黨政治替代王朝政治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沒有一個起政治核心作用的政黨做統領,機械地照搬西方“多黨制”(或想象中的“兩黨制”),中國必將陷入“一片散沙”的混亂狀態,根本無法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完成歷史主題所賦予的使命。之所以是人民的選擇,是因為盡管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看到了中國施行“多黨制”的危害,但他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不允許其他政黨存在。更嚴重的是后來的中國國民黨人罔顧歷史方向的變革,固守并張揚了這一制度的缺陷,形成了反民主的“一黨專政”制度,最終被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拋棄。
如上所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新型政黨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斗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這一制度在中國確立和施行70年來,雖經挫折,但改革開放之后日益完善。歷史的賡續、理論的開放和實踐的永恒,都對這一制度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使其在創新中不斷彰顯理論魅力,實踐效率,制度威力,筆者認為:第一,必須加強對這一制度之“新”的學術探討深度,理論宣傳力度,使人們能從理性上認同它是“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偉大政治創造”,自覺地與把西方政黨政治視為普世標準的錯誤認識劃清界限,從而增強對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自信,為其不斷發展創造更加廣泛的、自覺的、群眾性的認識基礎和條件。第二,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新型政黨制度中領導地位。盡管這一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但是如前文所述,它之所以是“新型”的,最本質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不但由其形成過程中中共所秉持的理論指導科學、奮斗目標遠大、方針策略正確所決定,也由中共以對民族復興高度負責的態度敢于直面問題、糾正錯誤、不斷革新的精神所決定,更由中共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緊跟時代,不斷豐富其理論內涵、調整其運行機制、制定其規范政策而決定。換言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但是這一制度的基石,而且是其充滿活力的源泉。所以,對任何歪曲、詆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言論,我們都要及時、堅決地予以回擊;對任何削弱、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行為,我們都要認真、嚴肅地給予糾正。第三,不斷提高參政黨的參政水平和能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民主黨派的參政是構成新型政黨制度兩個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方面,一方的能力和水平削弱都會影響另一方的提高。就目前情況看,不斷提高參政黨的參政水平和能力實是當務之急。這就要求參政黨首先加強政治和理論建設,尤其是強化對現代政黨政治知識和中國政黨政治特色和政黨制度歷史的認識,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參政理論和自身建設理論。其次增強參政意識,在不斷深化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接受中共領導,以及更加明確參政黨地位、性質、任務和歷史使命認識的基礎上,參政黨不斷強化參政意識和責任意識,并在全社會繼續保持民主黨派真誠坦蕩、大公無私、敢于擔當、盡心盡責的良好形象。此外,在組織體系的完善和制度建設的落實上,參政黨建設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第四,不斷完善新型政黨制度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中,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隊伍規模、成員結構、組織網絡都將不斷發生變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自然也會隨形勢的發展而發展。因此,在堅持根本原則和基本方針的前提下,中共對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領導體制,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機制,以及民主黨派干部培養選拔使用機制等,都需要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