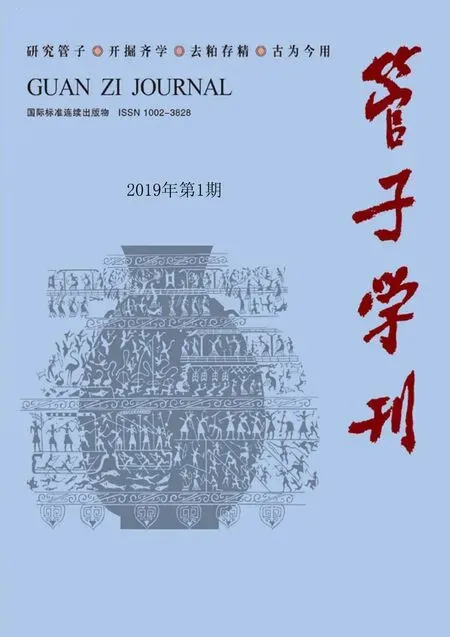上博竹書(shū)《景公瘧》再探
袁 青
(上海師范大學(xué) 哲學(xué)系,上海 200234)
據(jù)科學(xué)測(cè)定,上博竹書(shū)的年代距今時(shí)間為2257±65年[1]3,其年代約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與郭店竹書(shū)的年代大致相當(dāng)。上博竹書(shū)《景公瘧》與傳世本《晏子春秋》相關(guān)篇章大同小異,這又是《晏子春秋》早出的一個(gè)有力證據(jù)。《景公瘧》的出土具有重要意義,筆者曾著文對(duì)其作了初步的研究[2],此文我們擬在拙文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從《景公瘧》與傳世本《晏子春秋》的關(guān)系、《景公瘧》的思想特色及其所反映的戰(zhàn)國(guó)齊楚關(guān)系等方面對(duì)其進(jìn)行探究。
一、《景公瘧》與傳世本《晏子春秋》的關(guān)系
上博竹書(shū)《景公瘧》與傳世本《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景公有疾梁丘據(jù)裔款請(qǐng)誅祝史晏子諫第七》(以下簡(jiǎn)稱《景公有疾》)、《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一·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以下簡(jiǎn)稱《景公病》)類似,同時(shí)也雜糅了傳世本《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一·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以下簡(jiǎn)稱《景公信用讒佞》)相關(guān)內(nèi)容[3]。上博竹書(shū)《景公瘧》的面世,使我們可以通過(guò)將其與傳世本《景公有疾》《景公病》《景公信用讒佞》等作對(duì)比,以更深刻地認(rèn)識(shí)《晏子春秋》文本的形成。
關(guān)于《景公瘧》與《景公有疾》《景公病》的比較,梁靜已經(jīng)有所論述[4],筆者試在此基礎(chǔ)上加以申說(shuō)。據(jù)梁靜的統(tǒng)計(jì),《景公病》有370字,《景公有疾》557字,而簡(jiǎn)本《景公瘧》現(xiàn)存484字,其中重文一,合文二。根據(jù)竹簡(jiǎn)形制可以推測(cè)出,此篇?dú)埲?40字,則全文共有大概724字。《景公瘧》的字?jǐn)?shù)將近是《景公病》與《景公有疾》章的總和[5]。不過(guò)梁靜并沒(méi)有算上《景公信用讒佞》章,其實(shí)將《景公有疾》《景公病》與《景公瘧》相對(duì)照,可以發(fā)現(xiàn)《景公瘧》文句更接近于《景公有疾》,而《景公瘧》第6簡(jiǎn)和11簡(jiǎn)顯然出于《景公信用讒佞》,所以比較《景公瘧》與《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讒佞》的字?jǐn)?shù),更能說(shuō)明問(wèn)題,據(jù)筆者統(tǒng)計(jì),今本《景公信用讒佞》229字[注]據(jù)《四部叢刊》景印明活字本統(tǒng)計(jì)。,這樣與《景公有疾》557字相加,更接近于《景公瘧》的字?jǐn)?shù)。由此似乎可以推斷,《景公有疾》與《景公信用讒佞》當(dāng)是將《景公瘧》一分為二而成的。
由于《景公瘧》主題思想與《景公有疾》《景公病》是一致的,都是景公想殺祝、史來(lái)治愈疾病,晏子加以勸諫,最后景公打消了這個(gè)念頭。故而我們先來(lái)比較三者之間的差別:
其二,《景公瘧》記載了高子、國(guó)子勸諫景公殺祝、史的故事,這是《景公病》與《景公有疾》章所沒(méi)有的。
其三,《景公病》中晏子的勸諫更為直接,沒(méi)有拐彎抹角,通過(guò)揭露出“祝為有益”這個(gè)命題的荒謬性來(lái)講明殺祝、史無(wú)助于治愈景公之病的道理;而在《景公瘧》與《景公有疾》,晏子詳細(xì)論述政治與祝、史的關(guān)系,指出政治的清明與否直接影響祝、史的命運(yùn),而祝、史則影響不了政治,勸諫景公要想病痊愈,就要“修德”或“明德”,《景公有疾》說(shuō):“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后可。”《景公瘧》第9簡(jiǎn)說(shuō):“明德觀行。”這是《景公病》所沒(méi)有的內(nèi)容。
其四,《景公瘧》和《景公病》都記載在聽(tīng)了晏子的勸諫后,景公罷免了梁丘據(jù)等人的官職,然后景公之病得以痊愈;而《景公有疾》則是景公采取了“使有司寬政,毀關(guān)去禁,薄斂已責(zé)”等措施后,景公之病才痊愈。并且《景公病》在景公病愈之后,還有景公欲賜晏子以封邑,晏子辭的故事,而這是《景公瘧》與《景公有疾》所沒(méi)有的。
其五,《景公瘧》和《景公有疾》天人感應(yīng)的色彩很濃厚,《景公瘧》載“旬又五,公乃出見(jiàn)折”,《景公有疾》則記載景公采取了一些政治措施后,“公疾愈”,《昭公二十年》雖與《景公有疾》章基本相同,但惟獨(dú)沒(méi)有這三字。《景公病》的記載是“改月而君病悛”。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景公瘧》和《景公有疾》都有景公一采取措施就馬上痊愈的意味,而《景公病》像是客觀記載景公痊愈的情形。
其六,《景公瘧》糅合了今本《景公信用讒佞》的內(nèi)容,因而文意相對(duì)《景公病》和《景公有疾》而言更具復(fù)雜性。
我們?cè)賮?lái)看看《景公瘧》與《景公信用讒佞》之間的關(guān)系。《景公信用讒佞》主要講景公信用讒佞,導(dǎo)致賞罰不公,晏子加以勸諫,粗看起來(lái),這似乎與《景公瘧》《景公有疾》《景公病》三者之間的主題[注]主要都是記載晏子勸諫景公不要試圖靠殺祝史二人來(lái)取悅鬼神,說(shuō)明“詛為無(wú)傷,祝亦無(wú)益”。不一致,但《景公信用讒佞》的內(nèi)容可以作為晏子在勸諫景公時(shí)的論據(jù),說(shuō)明景公平時(shí)行為不端,用來(lái)說(shuō)明景公得病的原因不在于祭祀的物品不夠豐富,而在于自身行為不合正道,由此引出“詛為無(wú)傷,祝亦無(wú)益”的命題。
劉向《晏子敘錄》說(shuō):“所校中書(shū)《晏子》十一篇,臣向謹(jǐn)與長(zhǎng)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shū)五篇,臣向書(shū)一篇,參書(shū)十三篇,凡中外書(shū)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fù)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shū)無(wú)有三十六章,中書(shū)無(wú)有七十一章。”《景公瘧》雜糅了傳世本《景公病》《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讒佞》等章的內(nèi)容,這或許是后人將其分開(kāi)以合《漢志》之?dāng)?shù)。當(dāng)然,由于《景公有疾》與《景公信用讒佞》內(nèi)容相差較大,而且《景公有疾》在《外篇》第七章,而《景公信用讒佞》在《內(nèi)篇諫上》第十二章,兩者并非相互臨近的兩章,這與銀雀山漢簡(jiǎn)是不同的,所以最可能是劉向校書(shū)時(shí)所分。《景公瘧》雜糅了《景公病》《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讒佞》等章的內(nèi)容,這一事實(shí)或許意味著《景公瘧》可能是劉向校書(shū)時(shí)所刪去的“復(fù)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之一。不過(guò)由于材料太少,我們對(duì)于《景公瘧》與《景公病》《景公有疾》《景公信用讒佞》等章的關(guān)系還不能得出確切的結(jié)論。
二、《景公瘧》的思想特色
關(guān)于《景公瘧》的思想特色,筆者曾著文指出《景公瘧》等文獻(xiàn)否定祭祀可以求福,是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一種重人事、輕神事思想傾向的具體體現(xiàn)[2]。但當(dāng)時(shí)對(duì)《景公瘧》的思想特色認(rèn)識(shí)不夠,還必須得進(jìn)一步做出說(shuō)明。
在實(shí)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過(guò)程中,各地難免會(huì)遇到新挑戰(zhàn)和“硬骨頭”。雖說(shuō)發(fā)達(dá)地區(qū)和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差異較大,但后者更需直面困難,迎難而上,不能找理由推諉敷衍。地區(qū)差距不是“喘口氣”“歇歇腳”的借口,恰恰是奮起直追的動(dòng)力。鄉(xiāng)村振興要克服“懶政”思維,與其心動(dòng),不如行動(dòng)。
《景公瘧》否定祭祀可以求福而認(rèn)為求福的關(guān)鍵在于行德政,這種思想與孔孟荀等儒家有相通之處。帛書(shū)《要篇》載孔子之言:“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一五上】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6]243孔子認(rèn)為君子要靠德行來(lái)求福、仁義來(lái)求吉,而非祭祀、卜筮等手段。孟子更是提出“禍福自求”的觀點(diǎn),他說(shuō):“今國(guó)家閑暇,及是時(shí),般樂(lè)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wú)不自己求之者,《詩(shī)》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公孫丑上》)《孟子》的“自求多福”的觀點(diǎn)完全否定了通過(guò)祭祀、卜筮等手段來(lái)求福。而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更是直接否定了天(鬼神)有意志,故而更不可能通過(guò)祭祀、卜筮等來(lái)向天求福了。
但我們也應(yīng)該注意到,《景公瘧》等篇雖然是重人事,但也沒(méi)有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認(rèn)為靠祭祀是不能取悅鬼神的,但人事做好了自然能夠符合鬼神之意,如果人事做不好的話也會(huì)招到鬼神的制裁。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載: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wú)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wú)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益〉……”
在此,晏子提出“天道不諂,不貳其命”的命題,“天道不諂”即“天道不疑”“天道不諂,不貳其命”,也就是說(shuō)天的運(yùn)行是有規(guī)律的,不會(huì)因?yàn)槿耸禄顒?dòng)而改變。這頗有荀子“天人相分”的意味,然而《晏子春秋》并沒(méi)有將像荀子那樣將這種思想貫徹到底。《荀子·天論》提出“天行有常”的命題,認(rèn)為“天有其時(shí),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天與人各有自己的職分,天人不相干,所以說(shuō)“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荀子完全否定了天對(duì)人事的干預(yù)。《晏子春秋》雖然否定人通過(guò)祭祀等手段求福等,但并沒(méi)有完全否定天對(duì)人事的作用,《晏子春秋》認(rèn)為人事如果做得不好,天是會(huì)有所反應(yīng)的。《景公瘧》簡(jiǎn)9說(shuō):“明惪觀行。勿(物)而未(祟)者也,非為媺玉肴牲也。”物指鬼神,鬼神作祟不是為了美玉肴牲,那是為了什么呢?前一句是“明惪觀行”,雖然有闕文,但我們可以推測(cè)出,鬼神作祟是為了敦促君主“明惪”。《景公瘧》第12簡(jiǎn)說(shuō):“祭正(貞)不獲祟,以至于此,神見(jiàn)吾逕〈淫〉暴。”“以至于此”指的是景公之病不見(jiàn)好,這也就是說(shuō)神看到景公的淫暴,才導(dǎo)致景公之病不見(jiàn)好。《景公欲求福》在描述景公一系列暴政之后,也說(shuō):“是以民神俱怨。”這都體現(xiàn)出一種典型的天人感應(yīng)思想,認(rèn)為如果人事做得不好的話,天(鬼神)會(huì)懲罰君主。這種天人感應(yīng)思想與后世董仲舒的天人感應(yīng)思想相較起來(lái),也有所不同,董仲舒說(shuō):“國(guó)家將有失道之?dāng)。炷顺鰹?zāi)害以譴告之,不知自醒,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shū)·董仲舒?zhèn)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yīng)”思想夾雜著“災(zāi)害”“怪異”等“譴告”之說(shuō),具有鮮明的陰陽(yáng)家色彩,而《晏子春秋》中的天人感應(yīng)思想相對(duì)樸素得多。
由此,我們可知,《景公瘧》等篇章在思想上雖然否定通過(guò)祭祀等就可以求福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但如果君主不行德政,天也會(huì)懲罰君主,具有一種較為樸素的天人感應(yīng)色彩。
三、從《景公瘧》看戰(zhàn)國(guó)齊楚文化的關(guān)系
眾所周知,《景公瘧》是用楚文字抄寫(xiě)而成的,雖然我們不知道其具體出土地點(diǎn),但它出土于楚國(guó)卻是無(wú)疑的。楚竹書(shū)《景公瘧》的面世,顯示出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晏子春秋》的相關(guān)篇章已在楚國(guó)廣為流傳。不僅如此,上博竹書(shū)(四)中有一篇《柬大王泊旱》,主要記載了楚柬(簡(jiǎn))王的兩件軼事,其中一件就是楚簡(jiǎn)王因天氣干旱而患病,與《景公瘧》記載齊景公“疥且瘧”類似,其文曰:
簡(jiǎn)大王泊旱,命龜尹羅貞于大夏,王自臨卜。王向日而立,王汗至【1】帶。龜尹知王之庶(炙)于日而病,蓋儀愈夭。釐尹知王之病,乘龜尹速卜【2】高山深溪。王以問(wèn)釐尹高:“不穀騷,甚病,驟夢(mèng)高山深溪。吾所得【8】地于莒中者,無(wú)有名山名溪欲祭于楚邦者乎?尚言必而卜之于【3】大夏。如,將祭之。”釐尹許諾。言必而卜之,。釐尹致命于君王:“既言必【4】而卜之,。”王曰:“如,速祭之。吾騷,一病。”釐尹對(duì)曰:“楚邦有常古【5】,安敢殺祭?以君王之身殺祭未嘗有。”
王入,以告安君與陵尹子高:“向?yàn)椤?】私偏,人將笑。”君陵尹、釐尹皆辭其言以告太宰:“君圣人且良倀子,將正【19】于君。”太宰謂陵尹:“君入而語(yǔ)仆之言于君王:君王之騷從今日以瘥。”陵尹與【20】釐尹:“有故乎?愿聞之。”太宰言:“君王元君,不以其身變釐尹之常古;釐尹【21】為楚邦之鬼神主,不敢以君王之身變亂鬼神之常古。夫上帝鬼神高明【6】甚,將必知之。君王之病將從今日以已。”[7]192-197
楚柬(簡(jiǎn))王患病之后命令釐尹速祭,釐尹不肯,太宰告訴不“速祭”符合禮制,上帝鬼神會(huì)保佑,君王之病自然會(huì)好。《柬大王泊旱》這則故事與《景公瘧》情節(jié)很相似,只不過(guò)將故事中的主人公由“齊景公”換成“楚柬(簡(jiǎn))王”,“晏子”換成“太宰”,兩則故事中齊景公與楚柬(簡(jiǎn))王都相信祭祀可以醫(yī)治自己的病。只不過(guò)在《景公瘧》中晏子認(rèn)為只要為政之措施得民,自然就能符合鬼神之意,景公之病也就會(huì)好;而在《柬大王泊旱》中太宰認(rèn)為堅(jiān)持祭祀的禮制,不因君王之故而有所減省就能得到鬼神的庇護(hù),簡(jiǎn)王之病也會(huì)痊愈。《柬大王泊旱》作為楚人的作品[7]203-207,與成于齊人之手的《景公瘧》故事情節(jié)之間的相似,以及《景公瘧》在楚地的流傳,這一事實(shí)啟發(fā)我們思考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齊楚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
除《景公瘧》與《柬大王泊旱》之外,齊楚之間還存在許多內(nèi)容相似的文獻(xiàn)或故事。上博竹書(shū)(四)中還有一篇《昭王毀室》,主要記述楚昭王新宮建成后與大夫飲酒,有一位身穿喪服的人進(jìn)入宮內(nèi),告知楚王他的父親就埋葬在新宮的階下,現(xiàn)在宮室建成他就無(wú)法祭祀父母了,昭王聞此而毀室[8]181-186。這則故事與《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二·景公路寢臺(tái)成逢于何愿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景公臺(tái)成盆成適愿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情節(jié)十分相似,后二者主要記載逢于何或盆成適之母死,而其父恰恰早就葬于景公所修的路寢之臺(tái)下,逢于何或盆成適想要將其母合葬于其父所葬之地——經(jīng)景公之臺(tái),景公不許,經(jīng)過(guò)晏子的勸諫,景公同意逢于何或盆成適將其父母合葬于路寢之臺(tái)下。《昭王毀室》與《晏子春秋》二篇都涉及君主所建之宮下有其他人的墓地,結(jié)果楚昭王毀掉了宮室,而齊景公也同意別人將其父母合葬于宮室下。此外,《史記·滑稽列傳》所載齊威王“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而已,一鳴驚人”與《韓非子·喻老》所載楚莊王“雖無(wú)飛,飛必沖天;雖無(wú)鳴,鳴必驚人”,不僅故事情節(jié)一致,而且用語(yǔ)也一致。《史記·滑稽列傳》所載楚莊王欲以棺槨大夫之禮葬其愛(ài)馬,楚國(guó)優(yōu)孟諫之,這則故事與《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一·景公所愛(ài)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所載之事也有雷同之處。
齊楚之間如此之多的情節(jié)相似的故事,預(yù)示著齊楚文化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一定存在密切交流的關(guān)系,否則很難解釋這些故事之間的雷同。下面讓我們來(lái)考察一下史籍是否記載齊楚文化存在密切交流的時(shí)期呢?我們知道,楚國(guó)在歷史上屬于文化落后地區(qū),以致于楚王多次自稱“蠻夷”:據(jù)《史記·楚世家》載,周夷王時(shí),楚王熊渠說(shuō):“我蠻夷也。”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楚曰:“我蠻夷也。”楚國(guó)文化落后,自然要吸收其他國(guó)家的先進(jìn)文化。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魯國(guó)和齊國(guó)是文化最為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而齊魯與楚國(guó)在地理位置上也相距不遠(yuǎn),為楚國(guó)與齊魯兩國(guó)的文化交流創(chuàng)造了便利條件,因此文化落后的楚國(guó)理應(yīng)大量吸收了齊魯文化。從楚地出土的文獻(xiàn)看,也確實(shí)如此,近年出土的文獻(xiàn)如上博簡(jiǎn)、郭店簡(jiǎn)等大多數(shù)齊魯兩國(guó)的文獻(xiàn)。王葆玹早已指出,楚國(guó)與魯國(guó)文化關(guān)系十分密切,認(rèn)為楚國(guó)在文化上承繼了魯國(guó)文化,以致于他將其稱為楚魯儒學(xué)[9]19-27。王葆玹這一看法固然不錯(cuò),但從近年楚地出土文獻(xiàn)來(lái)看,我們也不應(yīng)忽視楚國(guó)文化與齊國(guó)文化的關(guān)系。從現(xiàn)存史料看,齊楚的交流應(yīng)始于楚成王時(shí)期,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御之,與桓公盟”。齊楚這次會(huì)盟為兩國(guó)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chǔ)。楚成王三十九年(齊孝公十年,公元前633年),“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齊桓公七子奔楚,并在楚國(guó)都做上了上大夫,而桓公七子都受到了良好教育,一定會(huì)自覺(jué)或不自覺(jué)在楚國(guó)傳播齊國(guó)的文化。楚威王七年(齊威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伐齊,敗之于徐州”,這使得齊楚兩國(guó)邊境更為接近了,有利于兩國(guó)文化的交流。而至楚懷王時(shí)期,齊楚的交往就更多了,楚懷王六年(齊威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國(guó)昭陽(yáng)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楚懷王十一年(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guó)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zhǎng)”。在這六國(guó)中,齊楚當(dāng)時(shí)是最為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這兩國(guó)的來(lái)往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致于“楚懷王十六年(齊宣王七年,公元前313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楚懷王二十年(齊宣王十一年,公元前309年),楚國(guó)“合齊以善韓”。《景公瘧》等楚簡(jiǎn)的下葬時(shí)間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剛好與楚懷王時(shí)期吻合,這都表明當(dāng)時(shí)齊楚兩國(guó)交流十分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的交流當(dāng)然也就更為密切了。現(xiàn)存史料也直接記載了齊楚文化的交流,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齊國(guó)稷下先生就有“環(huán)淵”一人,而“環(huán)淵,楚人”;齊襄王時(shí)期,荀子在齊國(guó)“作為老師”,并“三為祭酒”,后到楚國(guó),并死于楚國(guó)蘭陵。
需要指出的是,齊楚兩國(guó)的密切關(guān)系在楚懷王時(shí)期達(dá)到頂峰,也在楚懷王時(shí)期形勢(shì)發(fā)生逆轉(zhuǎn)。楚懷王二十四年(齊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05年),楚國(guó)“倍齊而合秦”,以這件事為轉(zhuǎn)折點(diǎn),齊楚從親關(guān)系開(kāi)始破裂。楚懷王二十六年(齊宣王十七年,公元前303年),“齊、韓、魏為楚負(fù)其從親而合于秦,三國(guó)共伐楚”;楚懷王二十八年(齊宣王十九年,公元前301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至齊湣王十七年[注]《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載是年為齊湣王四十年,誤,此依楊寬改,見(jiàn)氏著《戰(zhàn)國(guó)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1頁(yè)。(楚頃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4年),燕、秦、楚、三晉合攻齊國(guó),最終導(dǎo)致齊湣王出亡而后為楚使淖齒所殺,淖齒與燕國(guó)共分齊之侵地與鹵器。隨后,齊國(guó)便進(jìn)入齊襄王和齊王建時(shí)期,大概是由于齊國(guó)在齊湣王末年受到六國(guó)的攻擊已經(jīng)元?dú)獯髠灾掠诓铧c(diǎn)導(dǎo)致滅亡,齊國(guó)從此倒向秦國(guó),史載齊襄王王后、齊王建母后君王后,她在齊襄王時(shí)期以及齊王建初期對(duì)齊國(guó)政治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據(jù)《史記·田敬仲世家》載:“始,君王后賢,事秦謹(jǐn),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guó)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齊國(guó)“事秦謹(jǐn)”,以致于齊王建六年(公元前259年),秦攻趙,齊國(guó)雖然與楚國(guó)表面上去救趙,但趙國(guó)斷糧,請(qǐng)求齊國(guó)支援,齊王不給,最后導(dǎo)致“秦破趙于長(zhǎng)平四十余萬(wàn)”;齊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221年),秦攻打齊國(guó),齊國(guó)竟然不戰(zhàn)而降。而反觀楚國(guó),自從楚頃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楚懷王卒于秦,秦楚絕,之后秦楚發(fā)生了一系列的戰(zhàn)爭(zhēng),如楚頃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等,秦楚已勢(shì)同水火。齊楚的不同外交政策當(dāng)然會(huì)影響兩國(guó)的關(guān)系,從楚懷王之后,齊楚便不像以前那樣密切了,自然會(huì)影響兩國(guó)的文化交流。因此,我們可以說(shuō),齊楚文化交流至楚懷王時(shí)期達(dá)到頂峰,但也正在此時(shí)期,兩國(guó)的文化交流由盛而衰。
結(jié)語(yǔ)
以上我們比較了上博竹書(shū)《景公瘧》與傳世本《晏子春秋》相關(guān)篇章,通過(guò)《景公瘧》我們對(duì)《晏子春秋》的成書(shū)情況有了更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shí)。《景公瘧》雖然否定通過(guò)祭祀等就可以求福,認(rèn)為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但同時(shí)又認(rèn)為如果君主不行德政,天也會(huì)懲罰君主,具有一種較為樸素的天人感應(yīng)色彩。從《景公瘧》為楚簡(jiǎn)這一事實(shí)看,我們又發(fā)現(xiàn)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齊楚文化存在一個(gè)密切交流的時(shí)期,兩國(guó)文化交流在楚懷王時(shí)期達(dá)到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