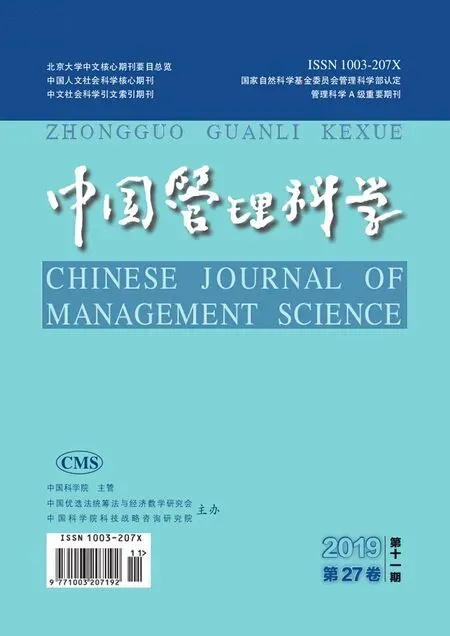考慮非期望產出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地區差異研究
——基于SBM和Tobit模型的兩階段分析
李 根,劉家國,李天琦
(1.江蘇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03;2.大連海事大學航運經濟與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3.南京農業大學金融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1 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制造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是GDP的重要貢獻者。但是,制造業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制造業在帶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長期以來,制造業每年能源消費占全國能耗的一半以上,從2000到2018年制造業能源消耗量增長超2.5倍。在呼吁低碳經濟、綠色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我國要著重提高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能源生態效率融合了能源效率和生態效率內涵,其是以最小的能源消耗和環境影響帶來最大的經濟產出,這也是“能源-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目前,針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地區差異的研究相對較少,部分學者從宏觀層面對能源生態效率地區差異展開研究。關偉和許淑婷[1]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對中國1997-2012年省際能源生態效率進行測度,從空間格局規模、格局強度與紋理等方面分析能源生態效率的空間分布特征與規律,運用計量模型驗證省際能源生態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王滕等[2]將環境非期望產出和社會福利要素納入到能源效率評價指標體系中,將能源、資本和勞動作為投入要素,從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社會福利三個維度衡量產出,構建能源生態效率理論框架。基于2000-2014年數據,對30個省市能源生態效率進行測度。趙鑫等[3]考慮非期望產出,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測算1996-2013年長江經濟帶整體及其上中下游能源生態效率,并分析省際能源生態效率收斂性。可見,學者主要從宏觀層面探究能源生態效率地區差異及影響效應,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礎。
學者針對制造業能源效率行業差異的研究相對較多。在對制造業能源效率進行測算時,按照投入要素選擇的不同,分為兩種方法。第一種是單要素生產率(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SFP)也稱為偏要素能源效率,比如能耗強度指標。李玲等[4]基于結構分解分析方法,將能源強度變動因素分解成能源消耗系數、完全需要系數、最終需求等因素,并編制了我國五個年度的實物價值型能源投入產出可比價序列表,以探索影響我國能源強度變動的主導因素。李根等[5]考慮了制造業隱含能源消耗,基于投入產出法構建了制造業完全能耗強度測度公式,并基于WSR方法論構建了制造業完全能耗強度影響因素體系,運用SVAR模型探究1980-2016年各因素對制造業完全能耗強度的影響規律。趙新剛和劉平闊[6]基于1960-2009年9國的面板數據,運用面板平滑轉換回歸(PSTR)模型及改進的算法,分析了經濟增長與能源強度的關系。徐建中和王曼曼[7]基于核密度函數模型描繪我國制造業能源強度的動態演變規律和行業異質性,從行業環境規制視角構建綠色技術創新對能源強度的非線性門檻模型,探討行業環境規制的門檻效應和時序變化,進而利用各因素多個分位數全面分析對能源強度的影響效應。這種計算方式簡單易行,但是只能衡量能源與經濟效益的比值關系,忽視了各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由于能源投入不能獨立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缺少對資本、勞動力、技術等其他因素的考慮,計算結果會夸大能源的利用效率[8]。
為了彌補單要素效率的缺陷,Jin-Li Hu和Shih-Chuan Wang提出了第二種方法,即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該方法考慮了多種投入的情形,認為是資本、勞動力、能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經濟產出,計算結果較為準確。楊愷鈞等[9]基于SBM與GML指數模型,采用2005-2014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大氣污染下中國工業全要素能源效率問題。結果顯示,工業全要素能源效率實現了41.22%的增長;東部沿海地區與東北、中部、西部地區存在較大的差距。孟慶春等[10]基于非參數前沿構建了不可分的混合測度DEA模型,將致霾污染物NOx、CO2、SO2和煙(粉)塵作為非期望產出,對各省能源效率進行測算。陳關聚[11]運用SFA測度了制造業30個行業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了能源結構對技術效率的影響。2003-2010年制造業能源效率呈先上升后停滯的階梯形變化特征,行業間能源效率差異大。王姍姍和屈小娥[12]基于2003-2008年制造業28個行業面板數據,選取行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年末從業人員數和能源消費為投入指標,行業總產值、SO2排放量為產出指標,運用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法測算了考慮環境效應的制造業行業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數;并運用To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因素。王霄和屈小娥[13]基于2001-2007年制造業28個行業數據,運用非參數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了制造業28個行業全要素能源效率。制造業全要素能源效率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行業間差異顯著。盧銳等[14]基于2003-2013年面板數據,運用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分解法,測算了制造業及其三類能耗行業全要素生產率、能源效率的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分解指數,分析了其相關影響關系。技術進步對于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負貢獻遠遠超過技術效率的正貢獻,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出現顯著的負增長;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均會提升制造業能源效率,但技術進步的貢獻顯著大于技術效率,且兩者在不同能耗行業中的效果差異明顯。趙金樓等[15]在隨機前沿分析框架下,對1980-2010年29個省市自治區的能源效率進行測算,并對能源效率地區差異、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最后運用面板單位根法對我國地區能源效率進行隨機性收斂分析。可見,較多學者分析了制造業全要素能源效率行業差異及影響因素,并提出了科學的政策建議,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基礎。
上述研究中,單要素生產率使用較為簡單,且與國家節能減排戰略目標緊密結合,實踐性較強,但它忽略了資本與勞動力對產出的貢獻及資本、勞動力與能源間的替代效應。相比而言,全要素生產率具有較大的優勢,它既可反映一個產業或地區在一定生產要素結構下的能源使用的綜合水平,也可比較客觀地衡量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效應。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來測算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目前,大多數文獻基于制造行業面板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研究成果側重于分析行業間傳統能源效率差異,而針對省域層面考慮非期望產出的制造業全要素能源效率測算的文獻相對較少,即忽視了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地區差異。
在測算全要素能源效率時,學者主要采用基于方向距離函數的前沿度量方法,包括非參數的數據包絡分析(DEA)和參數化的隨機前沿分析(SFA)。在進行效率測算時,SFA對于模型的基本假設比較復雜,不僅需建立生產函數,而且對技術無效率的分布形式也需進行具體設定,使得模型的參數估計較為困難。相比之下,DEA對生產前沿的具體形式不做嚴格要求,并對具有相同類型的多投入、多產出的決策單元是否技術有效進行評價具有較大優勢。然而,當考慮到能源消耗過程中產生的環境污染時,DEA的適用性受到質疑,部分學者則采用SBM模型測算考慮非期望產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由于能源消耗產生了較多的環境污染,學者通常依據研究需要,選取不同的環境污染指標,運用SBM模型測算產業或區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測算結果存在一定差異。較多學者將大氣污染作為能源消耗的主要污染物,選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粉)塵或工業廢氣排放量等作為測度環境污染的指標。本文認為制造業能源投入產出過程是一項復雜系統工程,除了產生大氣污染,還應包括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另外,在運用SBM模型時,可能會出現多個決策同時有效情況,不便于對這些決策單元進行區分和排序。為此,本文設定若SBM測算結果出現多個決策單元同時有效時,將運用Super-SBM模型予以解決。
較多學者關注不同因素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技術、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及規制因素。在對全要素能源效率進行測算的前提下,學者通常探究某一或較少因素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效應,結論存在顯著差異,影響因素的系統性有待提高。綜上,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改進與完善:(1)充分考慮了生產過程中的非期望產出,將制造業廢氣、廢水、固體廢物排放量納入產出變量;(2)基于2000-2016年30個省市面板數據,綜合運用SBM測算我國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充分解決可能出現多個決策單元同時有效情況:(3)構建更加系統科學的能源生態效率影響因素體系,采用Tobit模型實證分析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地區差異的成因,為提高制造業整體能源生態效率,縮小地區差異提出相應建議。
2 研究設計
2.1 SBM模型與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測算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大多采用了DEA模型。相比SFA,DEA模型的基本假設和參數估計相對簡單,而且能夠判斷多投入多產出的決策單元是否處于有效水平。DEA模型主要有CCR、BCC模型,兩者的假設前提不同,前者是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是假設規模報酬可變[16]。傳統的DEA模型,基本上都是屬于徑向和角度的考量,不能測算出松弛變量對于能源效率的影響程度,因而決策單元的效率值可能會被高估[17]。為了解決這一難題,Tone[18]提出了基于非徑向和非角度的SBM模型,規避了由于選擇徑向和角度所造成的偏差,并且克服了投入產出的松弛問題。由于在測算能源生態效率時,不但要考慮多個投入,而且還要把多個產出納入評價體系,比如期望的產出(又稱好產出)即制造業的增加值,以及不可避免的非期望產出(又稱為壞產出)即環境污染。因此,Tone[19]又改進了SBM模型,綜合衡量投入和產出(包含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二者之間的關系。本文采用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進行測算,其模型構建過程如下。
假設現有n個決策單元,每個決策單元均有3個向量即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這3個向量分別為
x∈Rq、yg∈Ru1、yb∈Ru2,可定義矩陣X、Yg、Yb如下:
X=[x1,…,xn]∈Rq×n>0
可構建包含非期望產出的生產可能性集P,
P={(x,yg,yb)|x≥Xλ,yg≤Ygλ,yb≥Ybλ,λ≥0}
依照SBM模型的處理方法,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變動規模報酬情況)的分式規劃形式為式(1):
s.tx0=Xλ+s-
(1)
式(1)中,x、yg、yb代表決策單元的投入變量,期望產出變量和非期望產出變量,s-、sg、sb分別表示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的松弛向量,λ為權重向量,模型中下標“0”為被評價單元。目標函數值ρ為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其關于s-、sg、sb嚴格單調遞減,其取值范圍在0-1之間。當ρ=1,s-、sg、sb均為0時,決策單元是有效率的;當ρ<1時,表明決策單元存在效率損失,有必要在投入產出上做出相應改進。SBM模型可以設定投入導向、產出導向和非導向三種,投入導向是指在保證產出一定時,尋找最少的投入;產出導向是指在投入量一定時,尋找最大的產出;非導向是指同時從投入和產出角度進行測算,因而也被稱作投入產出雙向,本文將根據實證結果選擇最優導向。
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可能會出現多個決策同時有效情況,從而不便于對這些決策單元進行區分和排序。若測算結果出現多個決策單元同時有效時,本文將運用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uper-SBM模型予以解決。一個排除了決策單元(x0,y0)的有限可能性集為:
考慮非期望產出的Super-SBM模型(變動規模報酬情況)的分式規劃形式為式(2):
(2)
式(2)中,ρ?為目標效率值,其它變量含義同公式(1)。
2.2 Tobit模型
當因變量為片段值或是切割值時,應采用Tobit模型,此模型屬于因變量受限模型,該模型采用極大似然法進行估計,可以較好地規避參數的估計時不一致和有偏的問題。其數學表達式如式(3)所示:
(3)
2.3 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2.3.1 投入產出變量
(1)投入變量
①資本投入。在衡量資本投入時,國內學者多選取資本存量作為資本投入的代理變量[20],結合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取各地區制造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單位:億元)作為資本存量的代理變量[21-22],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以2000年為基期,運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換算成可比價資本存量;②勞動力投入。以各省市制造業城鎮單位在崗職工的年末人數(單位:萬人)表征勞動力投入;③能源投入。本文選取各地區歷年制造業的能源消費總量(單位:萬噸標準煤)來衡量能源投入。
(2)產出變量
①期望產出。期望產出主要指制造業經濟產出,因此本文選取各省市制造業增加值(單位:億元)作為期望產出。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運用工業生產總值指數(2000年=100)將當年價增加值換算成可比價增加值;②非期望產出。由于各省市制造業的廢氣、廢水、固體廢物排放量難以獲取,本文選擇“工業三廢”(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物排放量的單位分別為億標立方米、萬噸、萬噸)衡量非期望產出,2017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統計口徑與以往年份不一致,2016年非期望產出數據采用加權平均法估算。
2.3.2 影響因素變量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物理-事理-人理系統方法,將影響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因素歸類為物理、事理與人理因素。具體而言,物理因素包含經濟、技術因素;事理因素包含能源、開放因素;人理因素包含人力、管制因素。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選擇經濟發展水平、研發投入作為經濟、技術因素變量;將能源消費結構、產權結構、對外開放度作為能源、開放因素變量;將勞動力素質、環境規制作為人力、管制因素變量,變量設定及假設如下:
(1)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水平發達的地區,資本雄厚、基礎設施便利,容易獲取到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源,一般而言,其制造業的能源生態效率也會較高。如當前經濟發達的國家,更有能力應對環境挑戰,一般生態環境較為優越。在德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制定和通過了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就有2000多項。本文選取各地區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并假定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正影響。
(2)研發投入
技術進步,一方面可提高資源利用和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先進技術比如云計算、AI、3D打印、工業智能化,有利于高端制造行業的發展,進而推動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一般而言,企業研發經費支出越多,代表技術革新越快,越能提高能源生態效率。因此,本文選取制造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與制造業增加值的比值作為研發投入的代理變量,并假定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正影響。
(3)能源消費結構
煤炭是公認的“最不清潔能源”,燃煤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和有毒物質,對大氣造成嚴重污染。由于我國富煤、貧油氣,2018年煤炭消費所占比重依然維持在60%左右,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任重道遠。因此,本文選取各地區制造業煤炭消費量與制造業能源消費總量的比值來代表能源消費結構,并假定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負影響。
(4)產權結構
產權結構的差異將導致企業激勵機制的差異,從而影響到資源配置、生產效率等因素。已有研究發現,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經營效率相對較低,產能過剩嚴重。國有資本占比越大,企業的能源生態效率可能越低。本文以各地區制造業國家資本與制造業總實收資本的比重作為產權結構的代理變量,并假定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負影響。
(5)對外開放度
對外開放與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存在密切的關系,對外開放程度越高,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壓力越大,越會激勵企業改進管理模式,提高能源生產效率。史丹[23]發現與封閉時期相比,1949-1960年以及1978年重新對外開放時期,其能源利用效率的均值明顯更高。根據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取各地區制造業出口交貨值與制造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作為對外開放度的代理變量,并假設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正影響。
(6)勞動力素質
已有文獻研究表明,高質量的勞動力素質對能源生態效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離不開高知識型人才。本文選擇平均受教育年數來衡量勞動力素質,計算方法參照彭國華[24],其式為:勞動力平均接受教育年數=文盲、半文盲的就業人口比重*1.5+接受小學教育的就業人口比重*7.5+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重*10.5+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重*13.5+接受大專及以上的就業人口比重*17,并假定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正影響。
(7)環境規制
環境規制是指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制訂實施的各項政策與措施的總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環境規制政策工具的運用略顯滯后。不同地區對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的認可程度各不相同。邁克爾·波特早在1995年提出了“波特假說”,認為恰當的環境規制可激勵技術革新,彌補環境投入所需的成本。當環境規制的費用小于它帶來的創新補償時,產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將得到提升。通過實施環境規制政策,可以籌集一定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建設。例如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實施的排污收費制度,60%以上的排污費用于污染治理,充分體現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由于環境規制政策較難用數據衡量,本文選取各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與制造業增加值的比值來代表環境規制,并假設該變量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顯著正影響。
為了減少多重共線性,一定程度上消除量綱的影響,本文對上述影響因素數據(不包含勞動力素質,因為勞動力平均接受教育年數是以年度量的變量,通常不取對數)采取對數化處理。
由于因變量能源生態效率值一般介于0-1之間,本文選擇基于極大似然估計方法的Tobit模型,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回歸方程如式(4):
ρit=β0+β1pcgdpit+β2rdit+β3enstrit+β4prostrit+β5opennessit+β6laborit+β7envirit+ε
(4)
式(4)中,it代表第t時期第i省市所對應的值,ρ為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βi為回歸系數,ε為隨機干擾項。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選取2000-2016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港、澳、臺和西藏地區)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數據來源于2001-2017年各省市的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及《中國工業統計年鑒》。

表1 影響因素變量說明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及地區差異分析
本文采用MAXDEA 7.6軟件,對2000-2016年我國30個地區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進行測算。綜合具體測算結果,模型設定為產出導向、規模報酬可變的非期望SBM模型,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2000-2016年各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值
表2顯示了2000-2016年環境約束下省際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變動情況。總體看,各省市歷年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偏低,全國歷年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均值僅0.44。可見,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在資源利用效率、質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顯,轉型升級任務緊迫而艱巨。從趨勢看,各省市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均呈現緩慢的增長趨勢。其中,北京最為引人注目,研究周期內效率均值為0.7,并在2016年效率值為1,成為有效決策單元。緊隨其后的是上海和廣東,歷年效率均值分別為0.577和0.558,位于全國前列。為了進一步深入對比分析所有決策單元的差異,本文根據歷年效率均值對各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進行梯隊劃分,劃分結果如表3所示。由于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在某種程度上集中反映了制造業發展與環境資源的協調程度[25],則四大梯隊也分別代表了制造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度。

表3 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梯隊
第一梯隊僅有一個地區即北京,其效率均值位于全國第一,因此代表了我國環境約束下制造業能源利用的先進地區,可認定為制造業發展與資源環境高度協調發展地區;第二梯隊共有5個省市,分別是上海、廣東、云南、吉林、內蒙古,涵蓋了東部與中部各2個地區、西部1個地區(按照2000年我國地區劃分標準)。第二梯隊相對第一梯隊,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表現較弱,可認定為制造業發展與資源環境中等協調度的地區;第三梯隊共有16個省市,東部、中部及西部分別有6個、6個和4個省市,該梯隊是涵蓋省市最多的梯隊,其能源生態效率均值在0.4-0.5之間,可認為該梯隊的協調度處于較低水平;第四梯隊共有8個省市,僅次于第三梯隊,其中東部、中部及西部分別有2個、1個和5個省市。該梯隊能源生態效率均值在0-0.4之間,其是制造業發展與資源環境協調程度較差的地區,也是重點發展的潛力地區。
為了更直觀地分析各地區歷年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變化趨勢,本文依據表2測算結果,分別繪制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圖,具體如圖1-3所示。

圖1 東部各省市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變化趨勢

圖2 中部各省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變化趨勢

圖3 西部各省市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變化趨勢
由圖1-3可知,2000-2016年我國所有地區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都呈現上升趨勢。分區域來說,東部地區屬于效率高值區,總體水平較高,其中北京、上海、廣東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都在0.5-1之間。但東部各省市間的差異也很明顯,這與各地區產業結構及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程度密切相關,如2001年北京就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辦法,由于政策效應日益發揮作用,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值一直都是最高的。特別是2013年《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與2014年《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的實施,將大氣污染防治同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調整、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機結合,由注重企業治理向企業、區域與行業治理并重轉變。針對違法成本普遍偏低的現實情況,加大處罰力度,提高處罰額度等,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值出現迅速上升趨勢。可見,通過實施環境政策,推行激勵與約束并舉的節能減排新機制,當制造企業行為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時,將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反之,將會受到相應的經濟處罰,從而促使制造企業主動地保護環境,提升能源生態效率。中部地區的能源生態效率收斂性最好,說明中部地區各省制造業發展水平相差不大。西部地區的收斂性介于東中部之間,這源于西部一些省份比如寧夏、青海、甘肅等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且環境污染也相對較重。
為了進一步分析我國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地區差異,本文將能源生態效率即綜合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結果如表4-6所示。從表4-6可以看出,統計期內東部地區綜合效率值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其主要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純技術效率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即東部地區制造業在管理與技術水平方面顯著優于中西部地區。但不容忽視的是,東部地區的規模效率明顯低于中西部地區,可能原因在于近年來東部地區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更加注重制造業質量的提升,不再過度追求制造業規模的擴大。中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時,更加注重制造業規模的擴大,規模優勢明顯得到提升。東部地區應在保證制造業發展質量的同時適度擴大規模,而中西部地區應在擴大制造業規模的同時注重質量的有效提升。

表4 綜合效率值(2000-2016)

表5 純技術效率值(2000-2016)

表6 規模效率值(2000-2016)
3.2 Tobit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借助EViews9.0軟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對全國、東部、中部及西部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具體影響效應如表7所示。表7顯示,各因素變量系數都異于0,各變量在相應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值為0的假設,數據擬合較好。

表7 全國及分區域的影響因素回歸結果
注:***、**表示影響系數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括號內為p值
(1)人均GDP對全國及三大地區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影響最大,影響系數分別為0.079、0.123、0.172和0.104,且呈現正相關,符合預期。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伴隨著資本投入量的增加、尖端技術的引進及產業結構的升級,這有利于提高制造業的能源生態效率。各地區要在保護環境的基礎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提升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
(2)研發投入對全國和東部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分別為0.015和0.043,與預期一致。相反地,對中西部地區來說,研發投入的影響系數為-0.04和-0.027,顯著為負。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如下:中西部地區通常屬于經濟欠發達區域,技術水平和研發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研發投入帶來的科技創新紅利暫時還不足以彌補研發所需的成本[26]。因此,國家應對中西部地區提供更多扶持政策,對欠發達地區給予更多財政撥款以用于研發活動,鼓勵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能源消費結構對全國及東部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符合預期,影響系數分別為-0.052和-0.074,對西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對中部地區則表現正相關,其影響系數為0.088。煤炭消費結構對全國及東部地區呈現負相關,這是因為煤炭的消耗存在明顯的負外部性,煤炭燃燒會產出大量的粉塵、CO2和SO2等,進而造成嚴重的大氣污染。對中部地區來說,由于煤炭資源稟賦較高,如山西、內蒙古都是煤炭大省,煤炭開采成本相對較低,雖然給生態環境帶來了破壞,但煤炭能源消費帶來的經濟產出超過了生態成本,因而其影響系數為正。盡管如此,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應降低煤炭消費比重,提升清潔能源的消費比重。
(4)產權結構對全國及東中部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分別為0.015、0.03和0.022,對西部地區的影響不顯著,這與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數量偏少密切相關。總體而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本雄厚,能帶來良好的規模經濟效應,因而國有資本占總實收資本的比重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制造業的能源生態效率。這也反映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公司治理明顯改善,交易成本顯著下降,經營績效切實提高。
(5)對外開放度對各區域的影響效應各不相同。對中西部地區來說,對外開放度的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中西部地區制造業出口相對較少。對東部地區來說,對外開放度的影響系數為0.015,顯著正相關,說明增加出口有利于東部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提高。而對全國來說,該變量的影響系數為-0.023,與預期不相符。這一現象表明,我國出口品中低附加值、高能耗產品占比相對較高。這也印證了我國尚處于全球制造業第三梯隊即中低端制造領域,成為制造強國尚需時日。因此,降低高能耗產品的出口比例,將有助于提高我國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
(6)勞動力素質對分區域的影響效應不顯著,而對我國制造業整體能源生態效率有促進作用,其影響系數為0.015,說明提高就業人員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提高節能環保意識,減少制造業能源消耗并降低污染物排放,進而提高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隨著“中國制造2025” 戰略的持續推進,需要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專業扎實,創新創業能力強的高素質人才。
(7)環境規制除了對東部地區影響不顯著之外,對全國及中西部地區的能源生態效率均有負的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0.042、-0.023和-0.071,與預期的假設相反。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如下:一方面,環境污染治理投資越多,反映環境破壞越嚴重;另一方面,我國環境治理機制還不夠完善,環境污染治理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這一成本已經超過了它帶來的環境收益。如我國已經實施近40年的排污費制度,由于存在排污費征收標準偏低、征收不能足額、開征范圍不全面、使用不規范等問題,最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取代,這有利于強化了環境執法力度,為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集中和積累財源。
4 結語
本文基于SBM模型,將制造業資本、勞動力和能源設定為投入要素,制造業增加值為期望產出,“工業三廢”排放量為非期望產出,對2000-2016年我國30個省市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進行測算,并依據物理-事理-人理系統方法論,選取經濟發展水平、研發投入、能源消費結構、產權結構等影響因素變量,采用受限因變量的面板Tobit模型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進行影響因素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各省市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差異顯著,各因素對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影響不盡相同。具體結論如下:
(1)從整體上看,統計期內我國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平均值為0.44,處于中低等發展水平,效率提升空間較大,且各地區差異顯著。能源生態效率梯隊劃分表明,第一、二梯隊東部地區占比較高,第三、四梯隊中西部地區占比較高。從綜合效率值看,東部地區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中西部綜合效率值拉低了全國整體水平。應推動區域間產業轉移,中西部地區需要向東部地區學習技術和經驗,大力引進高端人才,完善產業配套基礎設施,實施品牌建設戰略,提升公共服務能力。
(2)從綜合效率分解結果看,我國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整體上呈現上升趨勢,能源純技術效率較低是制約我國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東部地區純技術效率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但規模效率明顯低于中西部地區。因此,總體上看,大力推廣節能減排技術,優化制造企業的管理模式,加強環境保護制度建設是提升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有效措施。東部地區應在確保制造業發展質量的同時適度擴大規模,而中西部地區制造業規模效率已接近最優水平,應淡化追求制造業增長的速度與規模,重點關注制造業質量與效益的提升,在質效的大幅提升中實現規模的有效增長。
(3)從影響因素回歸結果看,經濟發展水平對全國及各地區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最為顯著,且為正相關;研發投入對全國與東部的影響效應顯著為正,而對中西部顯著為負;能源消費結構對全國與東部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而對中部顯著為正;產權結構對全國與東中部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對外開放度對全國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而對東部顯著為正;勞動力素質對全國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環境規制對全國與中西部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可見,除經濟發展水平外,其他因素對全國及各地區的制造業能源生態效率影響效應均不相同。為了提高我國制造業整體能源生態效率,縮小區域差異,總體上應采取優化升級制造業產業結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升清潔能源的消費比重、改善國企公司治理、降低高能耗產品的出口比例、培養高素質制造業人才、完善環境治理機制等。各地區應依據各因素的具體影響效應采用相適用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