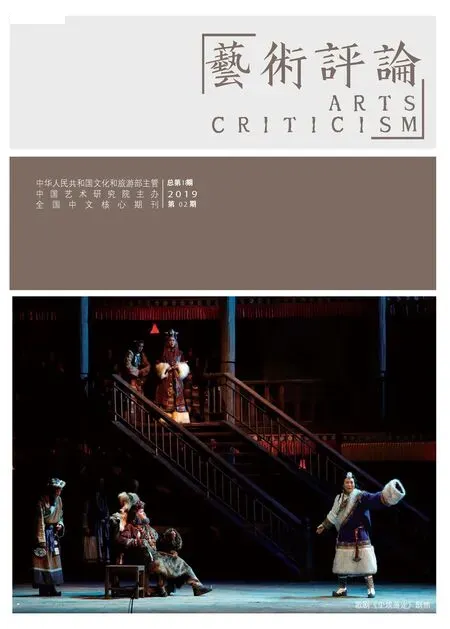當代詩詞的批評標準:從“境界”到“境外之境”
宋湘綺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文藝界把意境和境界混為一談,這是認識論思維難以說清的問題。意境和境界的關系,是足跡和歷程的關系。作者在人生實踐中創造境界,在藝術實踐中創造意境,意境保留了作者創造的人生境界的“足跡”。“有境界”指作品能從一己遭遇的境內,超越到境外,引發讀者有關歷史、人生、宇宙之思,施議對“境外之境”的提出,完善了王國維境界說這個批評模式,為當代詩詞文學批評提供了闡釋空間。
點評模式中,講一首好詩詞“有境界”,往往點到即止。這是印象式批評的含蓄、直觀。妙處難與君說?藝術批評的使命就是言說其妙。使命,是事物存在的理由,這種言說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創造。筆者認為應該在詩詞鑒賞止步的地方,向詩詞藝術批評出發,創造當詩詞藝術批評的理論話語,言說詩中“只可意會,不可言說”之處。
怎樣的作品才叫“有境界”?百年來王國維境界說被當成認識對象,難以測量,難以進一步指導文藝創作。施議對先生說,王國維所說的境界是可以測量的,這個觀點施先生1997年就提出了,二十年過去,至今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對此,筆者專門請教了施先生。施先生的解釋包含三層意思。第一,說境界是一個疆界,是可以測量的,即指可以用文學批評的標準,用科學的現代話語對作品的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作出客觀的評價;第二,說境界是意境,是時間和空間加上時空里面的人和事。以實踐存在論的生成觀看,人生境界永無止境,詩詞創作一步一步走在人生境界的攀登之路上。意境和境界的關系,是足跡和歷程的關系。第三,說境界是境外之境,王國維所說境界,在境之外,而非在境之內。
施先生的解讀擺脫了認識論思維,把詞學提升到哲學,從境內到境外,“另構新境”就是精神生產,就是人生實踐的“內環節”。
眾多學者把意境、境界當作認識對象,混為一談,爭議不休。這是詩詞認識論研究本身跨越不了的方法局限。筆者以實踐存在論分析意境,發現作品意境與作者人生境界之間的關系,是實踐與實踐者的關系,是存在與存在者的關系。
實踐存在論詩詞觀與認識論詩詞觀相比有三個轉變:一是圓融的“一體觀”。詩詞活動是人的實踐存在方式之一,從傳統詩詞觀“感性-理性”“主體-客體”二分的思路,變成“人-世界”“實踐-存在”主客一體的整體觀。二是動態的“生成觀”。“人”與“世界”在詩詞創作、接受中相互建構。不是現成的,而是生成的。三是優先的“關系觀”。傳統詩詞研究優先文與道、技法,遮蔽了人的實踐存在之維,實踐存在論詩詞研究把審美關系作為優先視角,“人”和世界在審美關系中“建構、生成”。
實踐存在論認為人生境界不是自然產生,也不是主觀臆想;境界,是在人與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建構的實踐存在活動中形成的精神形態;具有個體內在性和生成性,它是個體覺悟而生的內心靈明。“生成”指境界永遠處在“進行時”。作品“意境”保留了作者創作作品這一瞬間的“境界”。
提出具有學理深度和時代高度的當代詩詞批評標準,離不開王國維境界說這個現代詩詞美學的奠基之石。任何理論創新都不是拔地而起,創新始于“創舊”。評價一首詩詞“有境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闡釋其境界何在?需要審美價值觀、社會歷史價值觀、人性價值觀、道德價值觀、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綜合分析、判斷,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的分析,進一步打開了詩詞文學批評的闡釋空間。
簡言之,一首詩,有沒有境界,看意境中有沒有“境外之境”。施議對先生提出“意+境=意境=(人+事)+(時+空)”,以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為例。意+境=意境=(人+事)+(時+空)=(“我”+故國之思)+(昨夜+小樓)。以人為中介,通過“小樓、風月”貫通“天、地、人”之間的關系。作者從“雕欄玉砌朱顏改”之境內,通過聯想與貫通,“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從個人失國之痛這一“合乎自然”的人性出發,體察人類普遍命運,發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悲憫關懷。因精神擔荷,而被稱為“人類喉舌”。李煜創造出“春花秋月,生生不息,足以抵御春水般無盡憂愁”的“境外之境”,慰藉天下蒼生,引發讀者有關歷史、人生、宇宙之思,而成為經典。
意+境=意境=(人+事)+(時+空)。事,是人生實踐。作者述事(想象、虛構、創造)的緣起、發生、發展、完成,都涉及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我,即人與世界的相互建構,都涉及到意義、價值、夢想的求索,而后者即存在論的核心。由于“人”的介入,欲的輸入,代表著“我”的意愿,王國維以“合乎自然,鄰于理想”兩個維度,指出創造合乎自然人性,建構理想人性的藝術空間。施先生進一步挖掘出境界的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層意涵,使得王國維境界說這個批評模式得以指導實踐、成為評判作品高下的理論說明。
傳統詩詞中抒情主體“我”往往就是“藝術形象”,即人。經典之作都有“(人+事)+(時+空)”所構之意境,優秀作品都從有限的“境內之事”超越到“境外之思”。比如,記得“小蘋”的“我”(人)+初見(事),創造了“當時明月在,曾照彩云歸”的“永恒瞬間”。境內是詞人一己之遭遇,通過聯想與貫通,照亮了人們共有的懷舊情愫;“我”(人)+“夜飲醒復醉”(事),創造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豁達逍遙”。
施先生認為韻文有自己獨特的語匯系統,即布景、說情、敘事、造理。他從傳統文論中的情景交融的籠統之說、王國維境界說的“有無境界”的直覺判斷、吳世昌先生的結構分析論出發,系統梳理了“如何抒情”這個創作方法論的問題,說清了通過聯想與貫通,打通境內之事、境外之思,使作品產生宇宙、歷史、人生感懷的藝術奧秘。
試以“境外之境”比較以下兩首作品,既可以看到當代詩詞的創造潛力,也可以察覺我們與經典的差距。意境與作者人生境界的實踐存在論關系,給當代詩詞創作與批評提供了進步的臺階。天、地、人的三角結構,打開從形下到形上的藝術空間。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金縷曲·返中學母校 (李子)[2]
石徑徘徊晚。卅年來、十圍樟柳,親師俱散。惟有晴陽小河畔,依舊青春眉眼。恍似我、當年同伴。笑語書聲群山里,把繁花和夢都開遍。長想像,山外面。
萍蹤雁跡風中倦。向長車、行囊背影,燈深夢遠。百樣人生都夢過,難夢此生三變。辜負盡、鄉親酒盞。無業無家斑兩鬢,剩小名猶得多人喚。背人處,淚空潸。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與《金縷曲·返中學母校》分別以各自的遭遇和體驗,從現實人生“境內”,延伸到形上,寫出了人生的悲劇宿命。二首作品都創造了境外之境。《金縷曲·返中學母校》的筆觸從“晴陽小河畔,依舊青春眉眼”的現實畫面,延伸到“恍似我、當年同伴。長想像,山外面”的少年情懷,寫到“卅年來、向長車、行囊背影,燈深夢遠……”的世態炎涼、歲月滄桑。從天、地、人的三角結構看,作者在布景、敘事中,以“萍蹤、雁跡、風”為中介,意境已從境內飛躍到境外,升華到存在之思,觸發了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國大規模城市化進程中,向往、出走,到回歸,卻再也回不去的鄉愁。無根、無岸的漂泊中,“萍蹤雁跡風中倦”是我們共同經歷酸甜苦辣后難言的苦衷。與李煜“問君能有幾多愁”的悲憫,以及他創造的“春花秋月,生生不息,足以抵御春水般無盡憂愁”的“境外之境”相比,“背人處,淚空潸”乏力、脆弱、無助,在跨入境外之境后,一步跌倒。“無業無家斑兩鬢”是每個人的命運,人的本質是孤獨的,赤條條地來,赤條條地去,有幸擁有“笑語書聲群山里,把繁花和夢都開遍”的回憶,還有鄉親記得小名……“百樣人生都夢過,難夢此生三變”令人長嘆,蘇軾一生三起三落,亦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達觀。作為文學的詩詞,不僅“合乎自然”,慰藉心靈;還要提出“鄰于理想”的生存方式、生活提案、活法,給人以精神力量。一切文藝活動都是探尋人的自我和理想人性,是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的深化。意境的“情景交融”是自我的對象化,并且在自我(情)和自然(景)的同構中認識到人性,更深入地探索自我,建構理想人性。也只有從境外之境的角度,才能發現“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所包含的美好生機,是抵御逆境、排遣人生悲劇宿命的精神源泉。施先生說:“所謂往事,并非不堪回首之故國,亦非依然存在的雕闌玉砌;而乃春花秋月,亦即有如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事物。理解得到這一層意思,方才到達王國維所造境外之境。這是借用太史語,以打通天人界限的方法對境外之境的解讀。”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的喧囂嘈雜中,“多談現實,少談主義”是一種境界。王國維境界說,作為批評模式,在天、地、人的三足鼎立中,以境外與境內的共生互動,明確創作與批評的現實關懷和理想之維。境外之境中包含的“于事未必有,于理必可能”的文學性,為當代詩詞指明了方向。有了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的理論分析,王國維境界說將更好地應用于文藝批評。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論話語有待于進一步轉換成清晰的現代學術話語,才能對當代文藝批評產生積極有效的作用。
注釋:
[1]施議對.施議對演講集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51.
[2]金縷曲·返中學母校.搜狐.http://www.sohu.com/a/229591326_410925.
[3] 宋湘綺、施議對.疆界 意境 境外之境[J].學術研究,2018(0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