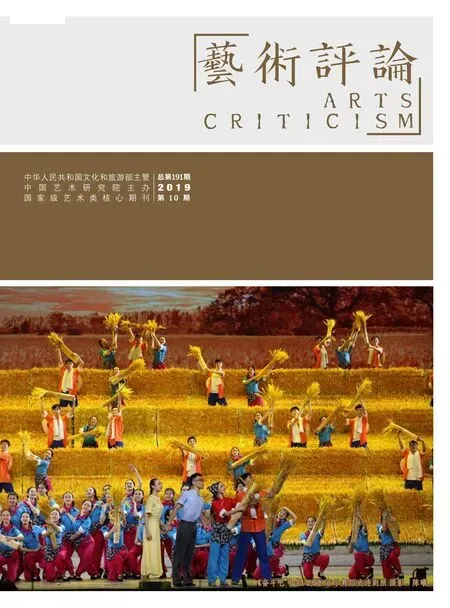美學是藝術學的動力源
——70年來三次“美學熱”回顧
[內容提要]本文依據過去70年美學發展的歷史事實,說明美學與藝術學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從1949到2019這70年中,美學經歷了三次熱潮。第一次是“美學大討論”,從1956年到1964年。這時,美學上的論爭成為施行“百家爭鳴”方針的試驗田,與“百花齊放”的方針互為表里。第二次是“美學熱”,從1978年到1985年。這一時期,美學吹響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號角,有力地促進了文藝的繁榮。第三次是“美學的復興”,從世紀之交開始,直到當下。面對市場經濟大潮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提出藝術如何出精品,以適應時代需要的問題。美學的國際學術對話,也對當下美學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當代藝術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這門學科之下,又有許多分支,實現著學科內的循環。然而,我們發現許多從事藝術學理論研究的人,原本都是美學研究者,他們曾經在美學領域中起過重要的作用,具有深厚的美學修養。這種現象是如何發生的?美學與藝術學的關系如何?對此,許多學者都在進行抽象的辨析,論證美學與藝術學的同與異。這種辨析當然是有益的,但是,對這個問題的更好的回答,還是要進入到歷史之中。當前,各行各業都在回顧過去的70年。從這種70年回顧的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看出許多學科間關系的來龍去脈。
一、“美學大討論”成為一個新起點
在過去的70年,文學藝術隊伍的整合,應該是從1949年7月在當時的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始的。這次會議史稱“第一次文代會”,是一個“會師”的大會,來自“國統區”的傾向于共產黨的文藝工作者,與來自“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在這次會議上見面。他們或是老友重逢,或是初次見面。但是,不管是新知還是舊友,這次會議意味著整編,從此以后,就開始分配工作,各就各位,為新中國的文藝事業工作了。
新中國的文學理論,是從中蘇結合開始的。季摩菲也夫的《文學原理》的翻譯,畢達可夫班的教學及后來出版的講稿《文藝學引論》,為中國文學理論提供了模板。在此后中國人編的眾多文藝理論教材中,都可看到這兩本書的影子。文學理論教材的模板,也被套用到各種藝術原理的教材之中。
當代中國美學史的寫作,都無法繞過一個重大的事件,這就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新中國的美學建設,是從這場大討論開始的。今天,對這場討論的評價各不相同。學界普遍認為,這是難得的一場具有學術性的討論,為此后的美學發展培養了隊伍,形成了論辯傳統,也留下了有價值的成果。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場討論也是蘇聯影響的結果,他們中甚至有人直接指出,蔡儀和李澤厚的美學理論,都是蘇聯理論在中國的翻版。這種表述是粗疏地遠觀歷史而沒有進入到歷史之中而造成的。
美學上的觀點分歧,早在1949年以前就有了。20世紀30年代初年,朱光潛留學歐洲回國,帶來了一本《文藝心理學》,綜合了當時在歐洲流行的美學理論,并且列舉了大量中外藝術作品的例證進行闡釋和引申。這部書使中國美學研究者耳目一新,提供了許多新知識,語言自然優美,是現代中國美學的佳作,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在此以后,蔡儀于1937年結束在日本的學習回國,帶回他從日本學到的唯物主義美學思想,相繼出版了《新美學》和《新藝術論》兩部有影響的著作。蔡儀的美學觀與朱光潛顯然不同,但那時沒有引起爭論,只是各抒己見。抗日戰爭期間,朱光潛在成都當院長、教授,蔡儀是活躍在重慶的從事抗日文藝工作的青年。他們分屬于不同的文化圈,思想相互對立卻沒有直接交鋒和論辯。50年代初年,時有美學論文出現,但那時,還是談文論的人多,而談美學的人少。
“美學大討論”是在1956年正式發動的。這一年,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中國,都注定是不尋常的一年。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舉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會議的最后一天,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對于中國人來說,這個報告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中國領導人不認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但由此意識到,全盤學蘇聯也不對。隨后,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們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是中國人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端。同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一方針經中共中央確定,成為關于科學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針,為文藝的發展和理論的探索打開了大門。蘇聯理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結束了,要通過中國古代就有的“百家爭鳴”的傳統來建立中國人自己的理論。“美學大討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不是強化蘇聯影響,而是有意識地消除或淡化蘇聯影響的結果。當然,我們仍可從當時所用的詞語和所采用的理論框架中,看到蘇聯影響的痕跡,但離開這個背景,而摘其部分詞句來發揮,就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美學大討論”是從朱光潛的自我檢討的文章《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的發表開始的。朱光潛的這篇文章發表在《文藝報》1956年6月的第12期上。這篇文章發表后,眾多重要學者撰文參加了討論,其影響席卷了整個學界。這場討論是剛剛施行的“百家爭鳴”方針的試驗田。許多重要雜志都競相開辟美學討論專欄,向專家約稿。先是朱光潛的自我批評,接著而來的是其他學者對朱光潛的批評,而作了自我切割后的“新的”朱光潛也以新的姿態加入到討論之中,與大家一道批判“舊的”朱光潛。作家出版社從1956年至1964年,先后出版了六卷《美學問題討論集》,集中收集了“大討論”的代表性文章。
朱光潛在上述自我檢討的文章中,主要講的是他原有的文藝觀中的問題,其中包括“清靜”“恬淡”“無為”“靜觀”“為藝術而藝術”等,以及重“浪漫主義”、輕“現實主義”、藝術是為“優選者”而不是人民大眾服務等。因此,重點是要在文藝思想上進行一場自我革命。蔡儀繼續堅持他在《新美學》中提出的“反映論”的觀點,提出了“美是客觀的”和“美在典型”的命題,關注藝術的形式特性和藝術形象的典型特征。李澤厚從美感出發,論及美和藝術,提出了美是“客觀性和社會性的統一”的觀點。
這場論爭原本是從藝術的問題出發的,朱光潛也是從文藝觀點上進行自我檢討。但后來,論爭變得越來越哲學化。在朱、蔡、李三大派中,朱光潛的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主客觀統一派”),蔡儀的唯物主義反映論(“客觀派”)和李澤厚的歷史唯物主義(“客觀社會派”),都努力從哲學上立論,具體的藝術指涉被逐漸被抽空。其他一些學者的論文,也都卷入到這種唯心與唯物、機械與辯證的爭論之中,用抽象的哲學標簽來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
當然,這種走向抽象的美學,后來仍回到藝術上來,出現了不少研究藝術特征論述的論文。在《美學問題討論集》的第五卷和第六卷,經過了幾年關于美的哲學的爭論,一些重要的美學家開始回到具體的審美和藝術問題上,同時,一些藝術家也加入到討論之中。例如,出版于1962年的《美學問題討論集》第五卷中,收入了張庚的《桂林山水》、李澤厚的《山水花鳥的美》和《以“形”寫“神”》、楊辛的《從新民歌看群眾對自然的美感》、李可染的《漫談山水畫》、宗白華的《美學散步》、王朝聞的《鐘馗不丑》,以及阿甲的《美于戲曲舞臺藝術的一些探索》八篇文章,這在此前的四卷中是沒有的。到了出版于1964年的《美學問題討論集》第六卷中,又收入了王朝聞的《老虎是“人”》、阿甲的《戲劇藝術的真和美》、李澤厚的《虛實隱顯之間——藝術形象的直接性與間接性》共三卷談藝術的文章。與此同時,“形象思維”討論的興起,也對“美學大討論”中的過度抽象化傾向起到了補救的作用。1961年,中央組織教材工程,《美學概論》教材委托藝術家王朝聞,而不是請美學幾大派中的主要理論家來主持編寫,這也是意味深長的。
這場從1956年起、到1964年基本結束的“美學大討論”,是從文藝問題的討論開始,又實現了對文藝問題的回歸。當我們回想這場討論時,常常只記得幾大派的抽象觀點,而實際上在這種爭論中,處處沉浸著對藝術的思考和建立藝術理論的嘗試。
二、“美學熱”與文化的新生
“文革”以后,中國藝術研究的復蘇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美學熱”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思想的禁錮仍然很嚴重。從“勝利的十月”到“三中全會”這兩年多的時間,中國人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地通過揭批“四人幫”而走向“思想解放”的。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同志的《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信中多次提到“形象思維”,講要用“比興”的手法。這封信原系在《詩刊》1978年第1期刊載,《人民日報》提前轉載,以示重視。《詩刊》在刊載這封信時,配發了一個專欄,其中有署名為“本刊記者”的文章《毛主席仍在指揮我們戰斗》,還有包括林默涵、李瑛在內的一些著名的學者和作家的文章。1978年的《人民文學》第1期,以及各地的各種報紙和刊物的第1期,都同時轉載了這封毛主席“給陳毅談詩的信”,從而成為轟動一時的重要事件。“形象思維”在當時成了揭批“四人幫”的“第三階段”的戰斗任務。
1978年,在文藝理論上,是“形象思維”年。一場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使文藝理論研究界被整體激活。一批久已沉寂的美學家,包括朱光潛、李澤厚、蔡儀,都重新拿起了筆,寫出了新作。包括錢鍾書在內的一批老翻譯家也在加緊努力,譯出一本大書——《外國作家藝術家論形象思維》。
文藝是時代的氣象哨。通過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批判“形象思維”,提出否定“十七年”文藝的“黑八論”,中國社會進入了“文革”;重提“形象思維”的討論,使人們從思想的禁錮中走了出來。在“形象思維”討論的熱潮中,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由此迎來了國家政治生活的巨變。
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的“美學大討論”的一些議題,在這一時期被重啟,但中心卻很快被轉移。這是一個美學大普及的年代。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朱光潛的《談美書簡》、宗白華的《美學散步》,被放到了所有文藝愛好者的書架上,放進了各門學科青年學子的書包里。
“美學熱”推動了文學藝術的繁榮。20世紀的80年代,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在那時,普遍的理論興趣與對有深度、有探索性的文學藝術風格的熱愛,促成了一大批優秀作品的問世。這些作品無論在內容的深刻豐富和形式的多樣方面,都是此前無可比擬的。
80年代在美學自身建設方面,成就也是突出的。與50年代美學家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建立美的哲學基礎之上相比,在80年代,美學實現了向學術本身的回歸。
經過了80年代初年的短暫的恢復時期之后,美學家們就不再繼續過去的爭論。這時的美學家,特別是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美學家,致力于做兩件事:一是引進外國的美學,二是研究中國古代美學。
在這一時期,首先出現的是翻譯大潮。過去那種憑空構想大體系的做法,已經被美學研究的主流所拋棄。這時,翻譯的浪潮開始了。在美學界,影響最大的,是李澤厚主持的《美學譯叢》。通過這套譯叢,中國美學家們意識到,美學不能僅僅圍繞著“主觀”和“客觀”進行爭論,而是要深入到藝術之中。在這套譯叢中,幾本影響最大的書,都對打開中國學者的眼界、構建中國人的藝術觀念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例如,克萊夫·貝爾的《藝術》一書,給中國學界提供了“有意味的形式”的觀念,這對藝術上克服“模仿說”,克服“形式”服從“內容”的舊有觀念,具有重要的意義。再如,魯道夫·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知覺》,引入了格式塔心理學的方法,開啟了對視知覺的深入思考。
與翻譯大潮同時,另有一批學者努力從古典中找出路。這些學者開始研究古代文論、畫論,嘗試撰寫中國美學史。當他們進入歷史的書寫的時候,就發現,那種在歷史資料中僅僅尋找主觀或客觀,或者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一類的現代詞匯來研究古代,常常就很難適用,會造成削足適履的現象。正確的做法是深入到古代的文本之中,從中整理出美學思想來。
這種向西方或古代來找出路的現象,所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使美學回歸為藝術,從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尋找理論發展的依托。
美學需要通過吸收外國的和古代的資源,以實現其學科化,完成學科體系的建設。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20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具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指向,這就是走出“文革”后的中國文藝,如何在新的理論資源的支撐下,獲得健康的發展。正是這一需求,使得一個原本是很專門的、只有少數專家從事研究的學科,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歡迎,形成空前的熱潮。
三、“美學的復興”引領藝術精品的出現
1985年,對美學來說,是一個分水嶺。這時,社會熱點開始轉移。一方面是美學本身的學科化,另一方面是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的興起,轉移了學者的注意力。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學開始降溫,到了90年代,這個學科已被人們普遍看成是一個過時的學問。盡管在大學的人文和藝術學科中,美學課還在開設,但只是依賴學科的體制而存在而已。高等院校的學科教學和研究需要,支撐著美學這個學科繼續存在。這一期間繼續有新書出版,盡管由于銷路不暢,出版變得非常艱難;也陸續有學術上的新人出現,但不受重視。這一時期,在一些有美學情懷的雜志上,仍刊登一些美學討論的文章,提出一些新的觀點,但是,這種討論已不再像80年代初年那樣能引起普遍的關注。美學逐漸變得與藝術隔離,也與社會生活隔離。
在美學與世隔絕的年代里,社會仍在向前發展著。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一個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變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從“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到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再到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社會模式發生著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有效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然而,在這一時期,文藝的發展卻失去了80年代初年的那種自由活潑的精神,受到商業大潮的沖擊。藝術上的探索精神逐漸遠去,滾滾而來的卻是商業洪流下的文化工業制成品泛濫。
對于文藝來說,市場的作用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市場提供了自由,文藝產品直接面對消費者,像普通商品一樣,要通過贏得市場來贏得生存的權利;另一方面,文藝產品的生產受價值規律制約,資本的力量在起作用。市場經濟的發展,還產生了一種被稱為“消費主義”的精神,生產不再僅僅是滿足需要,而是反過來刺激需求,造成需求的無限性,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潤。這樣,需要的滿足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取得利潤的手段。
在這一時期,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也給人文學者們帶來了新的興奮點。新技術帶來的是文學藝術在新媒介上的新嘗試。對此,人文學者所能做的工作,在一開始只是以描述為主。這種關于新技術與文藝結合的描述,常常充滿科幻的色彩。批判性的研究,要有待于這些新的文藝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有可能出現。
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翻譯運動,到了90年代仍在繼續,并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從翻譯文章到翻譯專著,直至翻譯一些國外著名學者的文集和全集;從翻譯較為經典的著作,到翻譯更為當代的理論著作。在全球化浪潮下,各行各業都在談論“與世界接軌”,這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
不過,中國與西方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無論是市場,還是新技術,都帶來一個突出的挑戰,即藝術的邊界在發生變化。但是,這種“邊界”的論題,在中國與在西方所具有的意味卻有很大的不同。許多引進的美學著作,都在談論一個話題,即杜尚的《泉》所引起的“現成物”和“工業制成品”成為藝術的問題。對于這些理論家來說,杜尚的《泉》打破了藝術的邊界。杜尚的《泉》,以致整個先鋒藝術給藝術邊界所帶來的挑戰,成為美學家們所關注的對象。然而,這個問題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具有經過移植而引入的特征。因此,中國的先鋒藝術問題,成為一個最具世界性的話題。它通過世界性的藝術交流而呈現出來,也通過美學的國際對話而得到論證,獲得理論的介入。
與此相比,中國的通俗大眾藝術,則具有實踐先行而理論滯后的特點,需要美學理論的參與來調整提高。
許多人都對一個現象感到困惑。20世紀80年代,《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四部中國古典小說相繼被拍成電視連續劇,成為經典,至今長映不衰。當時資金不足,技術條件落后,劇作的藝術成就卻很高。此后,這四大名著被多次重拍,卻無法達到當時的水平。由此,聯想到當下大量的電視劇和其他文藝產品生產中的低劣重復、胡編亂造的現象,“什么是藝術”的問題,便再一次被提了出來。
美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受到重視的。藝術在呼喚精品,要“從高原走向高峰”,這時,要通過美學研究,再一次在新的語境下反思藝術的概念,將理論思考重新植入藝術實踐之中。
結語:藝術需要美學
在藝術學學科獨立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持一種位置決定眼界的立場,用鴿籠式的思維,提出“要藝術學,不要美學”的口號。綜觀70年來美學的歷史,可以看出,美學一直都是與藝術聯系在一起的。
在不同的時代,美學對藝術的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在藝術受禁錮的時代,美學提供了解放的力量;在藝術陷入到追新的循環之中,失去意義,走向“終結”的絕望之時,美學思考“終結”后的出路,致力于意義的找回;在藝術卷入到產業化和市場洪流之中時,美學堅持藝術與娛樂產品的差異性,用原創性、對日常生活的批判性,推動藝術對現實的救贖和滋養。
美學是對藝術的哲學思考,是藝術與自然和社會之美的連續點,它本身會成為藝術學發展的動力源。沒有美學的藝術學,會失去深度,滑向知識性和技術性,從而在藝術面臨各種挑戰時失去支撐的力量。
注釋:
[1]毛澤東.論十大關系[M]//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2]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56-4-28)[M]//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3]《美學問題討論集》共6卷,前4卷由文藝報編輯部編,后2卷由新建設編,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4]新建設編輯部.美學問題討論集(第五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169-273.
[5]新建設編輯部.美學問題討論集(第六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356-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