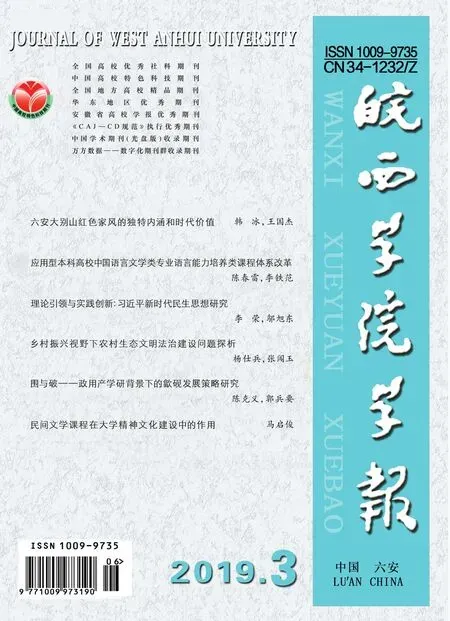略論吳子玉的家譜理論成就
楊 芳,關 欣
(安徽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徽州譜學令人稱道之處,不僅表現在浩瀚如煙的譜牒著作,還突出地表現在層出不窮的譜學家。明代徽州諸多學人嘗試去編修家譜,不斷尋求家譜內容和形式上的變革,直接促進了家譜理論的創新發展。徽州休寧人程一枝說:“諸程以譜名家者靡然鄉風。于汊口,則志堅。于率口,則師魯。……無不本之學士矣。”[1](自敘)其實,在譜學名家程敏政的影響下,程氏家族出現了像程師魯、程一枝等譜學家。吳子玉在其父吳槐的感召下,將修譜視為他一生最重要的事,因而在家譜理論上取得不小成就。
一、優良的家學傳統
吳子玉(1519—1591),名瑗,字瑞谷,號茗山,別號大鄣山人,安徽休寧人。據道光《休寧縣志》載,“(吳子玉)幼孤貧,嗜學。母機杼課之,過目成誦。童年試郡邑,輒入左氏語,主司驚異之”。及長,為求學而“負書踏雪”行數百里。晚年授應天訓導,撫按稱其“學貫天人”。他纂有《白岳志》、《郡志》、《金陵人物志》等書。都邑中的祠記、譜牒多出其手[2](P803)。他不僅參與他族家譜的編修,還積極組織編修本族家譜,如家典一卷,家譜六卷,家記十二卷①。
吳槐(1489—1527),字于庭,號竹溪,又號竹溪小隱,嘗修家譜[3](卷五茗洲吳氏登名策記)。值得注意的是,吳槐在修譜上有較強的使命感。他在《序茗洲家譜》中說:“祖元四公森甫舊編家譜一帙,積久刓缺,兄克敏出入仕途,不遑讎校,槐等以宗事之重,遂忘膚谫,謹加編訂。不足者益之,有余者損之。刓缺者,備而補之。幽隱者,闡而顯之。未系者,從而續之。……彌月,譜始成,僉曰:《茗洲吳氏續譜》。”[3](卷一譜序匯記)可見,吳槐對家族文獻的保存和整理十分重視,他在家譜編修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說:“是譜之編,協舉者睿、岳、植、賜,暨弟侄輩,至論次編續則槐也。”[3](卷一譜序匯記)應當說,吳槐為譜書的纂修付出了辛勞,他對家譜體例的醞釀、內容的記載,使之早日付梓成為現實。
吳槐的修譜精神已深入到吳子玉的精神世界,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之中。緣此,吳子玉立志要為家譜事業奉獻終身。王世貞說:“廣文(吳子玉)之父曰隱君槐,博學工古,文辭慨然,有意于先世之業,取舊譜而新之,整齊其世次,佹就緒而卒,年僅三十九。當是時,廣文猶在髫,輒抱遺書而哭曰:‘孤不執觚管,而以終先人之遺志者有如日。’未冠讀經史藝文諸篇,凡數百千萬。言其所撰述,凡十年而傾邑,又十年而傾郡,又十年而傾海內。學士大夫咸曰:‘吳子,今之太史公、班氏也。’”[3](卷一譜序匯記)不難看出,吳子玉為承繼先父遺志,通過閱讀大量載籍,來提高其史學修養。甚至,還親身參與家族文獻的搜羅和整理工作。他說:“余每因遺事尋故篋,得唐宋以來簿券若干簏,得十世祖太學元四公手錄遺文若干帖……。”[4](卷九茗洲吳氏家記序)其實,對家族文獻的采摭,為家典、家譜、家記的編修創造了條件。是后他深情地說:“非曰能論,即先人所遺而遵敘之云爾。嗟乎。先隱君負茲之命,意在斯乎。”可見,吳子玉有著優良的家學傳統。
家學傳統,在徽州譜學發展中是一個較為突出的特點。是否可以認為:譜學中的家學傳統是指父子相傳、子承父業,將編修家譜當作神圣的事業并努力去完成它[5]。元人櫟隱翁為完成先父遺愿而重修流芳集[6](櫟隱翁重修流芳集序)。范淶在其父教誨下,為編修范氏族譜,“每訪文獻故家譜例,書而藏之笥,遇耆儒績學必加咨詢,如是者幾二十年”[7](休寧范氏族譜自序)。總之,家學傳統不僅存在于史書的編撰中,在譜書的纂修過程中也有體現。

應當指出,譜書的產生,不僅與商業興衰、家族隆替等社會因素有關,還與勤奮精神、宦官權位等個人因素有緊密聯系②。但也不可忽視,“家學傳統”在譜書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實際上,家學的傳統在徽州家譜編修活動中十分突出。
二、家譜的編修思想
吳子玉“畢力史乘之業”,成為明中后期譜學大家。他在譜學上頗有造詣,在家譜理論上取得了一定成就。通過對《茗洲吳氏家記》的研究,結合他撰寫的譜序,基本上可以窺探其譜學思想。
(一)論家譜的編修
長期的家譜實踐,為吳子玉編修家譜積累了豐富經驗,并形成了獨特的家譜編修理論。他在《率口程氏續編本宗序》中提出了編修“良譜”的方法,他說:“余讀程氏譜,有三事焉:其系核、其文贍、其體整,作譜者務三而已。夫悠悠世祚尚矣,遠則不明,明者不遠,今系祖始晉太守公元譚,蓋其遠哉,而繩繩可朝徹正時日月可數,蓋其著也。深得孔安國百姓之旨,不祖帝系而胄自華焉,其考核矣。敘譜始唐將軍淘,君子以為古,由是而下無虞,數十家有譜諜以來鮮如其盛,所具論贍矣。揚榷義例,科條略意,嚴而有制,實而不隘,前譜絀者,今或收之,前譜載者,今有刪之,以明誡勸整矣。此三善也。”[4](率口程氏續編本宗序)在吳子玉看來,一部讓人滿意的譜書要做到“系核”“文贍”“體整”。具體說來,“系核”注重家族世系記載的真實性、可靠性,做到不攀附,不強援。“文贍”是對存世久遠的家族文獻做考辨和輯錄的工作。“體整”強調家譜的編修要有一定的“義例”,這樣才能取舍有法,實現家譜的“誡勸”作用。
實際上,三者間是有聯系的,不能肆意將其割裂。譜學名家朱熹說:“夫譜牒有二:一曰文獻,則詳其本傳誥表銘狀祭祀之類;一曰世系,是別其親疏尊卑嫡庶繼統之分。非世系無以承其源流,非文獻無以考其出處。”[8](P230)這里,朱熹認為家譜記載的內容無非就是世系和文獻。“系核”為編寫世系指明方向,“文贍”則對采摭文獻提出要求,“義例”是家譜在纂修中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可見,吳子玉在家譜編修上的認識是全面的,理解是深刻的。
《茗洲吳氏家記》是吳子玉編修的譜牒著作。共十二卷,卷一為譜序匯記,卷二為吳氏聞祖記,卷三為龍江茗洲吳氏先賢記、休邑吳氏文苑記,卷四為世系記,卷五為登名策記,卷六為家傳記,卷七為祠述記、家典記,卷八為里區記、物產記,卷九為墓域記,卷十為社會記,卷十一為翰札記,卷十二為雜記。在編修家記時,吳子玉并非隨意輯錄,而是有意識地對家記作剪裁。例如龍江茗洲吳氏先賢記中記載了元龍公、句容公的事跡,在茗洲吳氏家傳記中則略而不書,并寫到“見先賢記”。可以說,家記是簡明有序而內容翔實。這些,與吳子玉在家譜編修上的獨到見解有關。這種見解,在家記中表現為:譜序匯記、翰札記、雜記是對先賢文獻資料的匯集。世系記、龍江茗洲吳氏先賢記、登名策記是對可信、可考的家族世系和人物事跡進行編寫。家記前有“議例”,中有序論,即家譜在編修過程中應當遵循的原則。
(二)論家譜的體例
《茗洲吳氏家記》體例的創新之處主要表現在:龍江茗洲吳氏先賢記、登名策記、社會記。通過對其創新之處的揭示,將有助于理解吳子玉的家譜編修思想。
首先,龍江茗洲吳氏先賢記。吳子玉說:“昔人論譜有英賢譜、衣冠譜,則祖氏之先達不在所表揭哉。而晉二吳坦之隱之之賢,以吳氏譜而傳甚矣,譜之記先賢不可悠忽也。先隱君處逸高行,載入郡隱逸傳,亦得附書。”在吳子玉看來,不論是英賢譜,還是衣冠譜,都是對“祖氏先達”作“表揭”。他認為有必要編寫吳氏先賢記,不僅可以體現尊祖敬宗之意,還能形成對家族歷史的認同。他選取本族九位先賢,從宋至明,記載了他們的名字、仕宦、事跡等內容。例如隱逸公,竹溪先生,諱槐,字于庭。幼孤,家貧力學,博通經史。以母謝平寡,日夕虞侍,不肯出應制舉,號竹溪小隱。友愛弟樞,同居不分異,立家訓以教族人。居轄黟祁之間,數十里內高其學行。向慕化之客有諷先生不仕者,先生著懶散子文以自見。是時,浙許給事相卿家居以名節自高,獨與先生為方外之游,所著有《竹溪集》[3](卷三龍江茗洲吳氏先賢記)。應當說,吳子玉對先賢的記載是比較全面的。根據這些記述,基本上能對先賢們的生平事跡有個大概了解。
其次,登名策記。吳子玉在編寫登名策記時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說:“《記》曰:名者,人治之上者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以名。可無慎乎!先隱君之譜有登名策,仍舊貫而續記之。”可見,他對登名策記的編寫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強調,“登名策,書世,書行,書大事”,并對要記載的內容作了具體說明,他指出,“見諸傳者,不書。未傳者,書其概。書配氏,書女。……配之改適者,不書;女之改適者,不書。……妾之無生出者,不書,有生出,而細書。……有母之子,有繼母之子,有妾之子,必書出自某。出自某者,示有所屬也,如月山公所子謝氏,子名書,而事不書行不書,不成其為行也,不得而事也。族之犯大不韙者,削名不書,既自削,不得不之削也”[3](卷五登名策記)。不難看出,他在編寫登名策時有一套嚴格的書寫規范。
吳子玉是從世、行、從名、行實、家氏、女六方面來編寫的。例如月山公,世:十八。行:山。從名:元四。行實:字森甫,號月山老人。居雙溪,構雙溪道院,修宗譜。生淳祐乙巳,至和乙已歿于土湧莊內。葬泉源謝家后山,亥山已向,□字六伯四十八號山。生子啟老、萬老倶止。以謝秀鄉之子千□為子,以女菊配之。家氏:謝員,生歿缺,葬大嶺塢口莊后。女:無[3](卷五登名策記)。其中,“行實”記載了族人的生歿、居葬、字號、官爵、生子的情況。“家氏”記載了妻妾的名、里、生、歿、葬的情況。“女”記載了下一代女子的婚姻情況。可見,登名策所記載的內容相當全面,幾乎包含了全部家庭成員的信息。他對以往家史的撰寫作了很大調整,過去以家族男性成員為核心的書寫傳統有了新突破。
最后,社會記。吳子玉在“議例”中指出編寫社會記的初衷,他說:“及于社會者何?族人當社臘之日,則主書者載筆書族里事,亦閭史之意哉。嘉前人所次舊聞,弗敢闕。”[3](議例)這里,吳子玉將記載“族里事”當作一件神圣而嚴肅的事情,他認為這是實現“閭史之意”的一種途徑。關于社會記的記載方法,他指出,“遂于是日具簿牒,書歲候,書牧長,及時事如故,今要刪丁卯以前者不錄,采其后事載入家記云”[3](卷十社會記)。從編寫情況來看,它是從社日、歲候、牧長、時事、社渠首五方面進行記述,它的記載時間是從正統十二年至萬歷十二年。例如社日:正統十二年丁卯二月廿六日戊午。歲候:無。牧長:孫任名遇,山東福山人,有循理政。虞任名安,杭州人,以正統十年任。時事:是日,絀革吳宗成等非類者四戶,新入德烜、德安、德皓、敏文四戶。無何,宗成兄宗佑自外歸,介李存政、謝瑞懇入社,愿椎羊豕奠酒至門,賽謝社神,姑許留之社戶……。社渠首:普佑[3](卷十社會記)。文中,社日記載了社祭的日期,歲候記載了社祭的氣候,牧長是由地方官員來充當,社渠首是舉辦社祭的人員。時事是記載這一時期發生的大事,有對宗族事務的記載,也有對國家、地方的記載。如“云南寇起,檄新安衛兵同往擊之”,“以水災蠲稅之七,征其三”[3](卷十社會記)。
(三)論家譜的書法
家譜的書法是指家譜編修者在編修家譜時的態度。家譜內容是否真實、可靠,與它關系密切。吳子玉在編修家譜時,主要采取“存疑”態度和遵循“信史”原則。
首先,對先祖的記載,取“存疑”態度。吳子玉用懷疑的眼光來看待吳氏先祖,他在“議例”中指出,“姓之聞祖,聞者何?董生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若有邰梅里之傳聞,豈時十二世哉?雖百世可聞也,可聞可祖也,幸其聞乎已也。”[3](議例)文中,從見到聞再到傳聞,從三世到四世再到百世,說明了子孫對先祖的記憶會隨時間流逝而變模糊,但并不意味著這些傳聞都不可信。因而,他認為要將其記載下來使子孫知曉。他在《吳氏聞祖記》中說:“閱《周譜》,吳姓肇于有邰,出自天□遠矣。及參會近世諸吳譜,自吳王羌以下至于隋唐,皆繩繩可數,豈誠有考鏡哉?先隱君于乾符以前不之系,而首以吳姓聞祖之目,其有以晰之矣。”[3](卷二吳氏聞祖記)在吳子玉看來,吳姓由來已久,世系的演進難以盡數,而近世諸吳譜中世系卻能夠“繩繩可數”,因而他不禁提出“豈誠有考鏡”的疑問。面對這些問題,吳子玉取“存疑”態度,將其記載在譜書中,并冠以“聞祖”名,以俟后來者為之考辨。
其次,對世系的記載,遵“信史”原則。吳子玉認為世系在家譜中很重要,他說:“言譜者,先世系。……是必檢按真偽,稽參旁正,遠胄弗援,戚屬弗絀,膏粱弗右,寒畯弗左。俾考族氏者,一瞬而具,訖于掌指,繩繩總總,而不緄斯,不亦匡乎。”[3](卷四世系記)這是吳子玉為編寫世系記而作的序論,他要求對家族世系進行“檢按”,通過參考諸吳譜來辨別真偽。同時,他還強調“遠胄弗援,戚屬弗絀”。可見,他在編寫世系時是秉筆直書、據事實錄。另外,據《龍江吳氏小婆派統宗世系譜圖》載,“蓋唐左臺公由歙徙鳳山也,龍江譜系稱小婆者何?始自小婆也。何始自小婆也?逸公居守白水,小婆貞烈造基,志載吳嫗裔呼小婆祖有功也,系竟斷自小婆何也?傳信也,詳其所可征,而不侈溯其所莫考,亦猶尊祖之意也”[3](卷七祠述記)。這些,反映了吳子玉在編寫世系時,以“信史”為準則,渴望編出一部“信譜”。
值得一提的是,吳子玉有意識地對先賢記與聞祖記作區分,表明了他對先賢和聞祖的認識是不同的。另外,他對先賢的記載,反映了他對“信史”原則的遵從。在這點上,與陳櫟大為相似。陳櫟在修譜時,也在傳聞與事實之間作區別,從“前代姓陳人”到“本房先世事略”,反映了傳聞與現實是存在差異的[9](卷十五陳氏譜略)。
總之,吳子玉的“存疑”態度和“信史”原則,不僅使家譜內容記載全面,還使家譜內容更加真實、可靠。因而,《茗洲吳氏家記》的史料價值是極為豐富的。
三、余論
翰林院國史編修吳應賓說:“史,誠需才乎。孰才?如吳瑞谷先生也者,而僅僅以家史著也。”[1](卷一譜序匯記)可見,吳子玉有“良史之才”,以善修家史而著稱,他在譜學上的地位得到時人的肯定。
作為譜學大家,他編有家典、家譜,為何還要纂修家記?一方面,編修家記是為了繼承其父吳槐的遺志;另一面,家記有著家典、家譜所不具有的作用。一般而言,譜書中對世系的記載是全面的,包括名字、仕宦、生歿、婚葬等內容,但家記中的世系獨記家族成員姓名,并附言“見宗譜”。這一特征,表明了家記是區別于家譜的文獻。從整體上來看,它更青睞于記載與宗族社會相關的內容,如祠述記、社會記。根據這一現象,是否可以認為:家記是宗族社會深入發展的產物,它與家典一同維系“小范圍”的宗族社會。但也應該看到,這一時期“譜本宗”思想十分活躍,它對家記編修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明中后期,徽州家譜編修活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產生了一批數量可觀、體例創新的譜牒著作。例如程一枝的《程典》有系諜、表、世家、列傳、志、圖、錄。其實,這些是受到史學思想的指導。吳子玉說:“世本為系諜之目有四,取史諸表為年表、世表之目亦四,取鄣大記之事為志有九,諸為世家、為列傳、為圖、為錄,莫不原本于史學。”[1](程典序)不管怎樣,家譜體例的創新是可見的。
史家鄭樵說:“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10](P2)于《茗洲吳氏家記》而言,吳槐是有草創之功的,吳子玉作為“繼志之士”完成對它的編修。吳子玉對其父吳槐的論次既有因依,亦有創造,反映了徽州家譜的編修是在繼承中不斷創新的事實。總之,吳子玉的譜學思想豐富了徽州家譜理論,對后世家譜的編修有指導意義。
注釋:
① 據《程典·自敘》載,“君子謂是典也,有法式焉,有表章焉,有鑒戒焉,有顯微焉,有詳略焉,一宗之常訓,百代之憲章,罔不具矣”。不難理解,不管是“家典”,還是“程典”,它們都是譜書中的典范,起到維系宗族社會的作用。
② 徐彬指出,“一部家譜作品的好壞與其編者的水平直接相關”,主要有道德修養、勤奮精神、官宦權位、家學傳統四方面。參見徐彬的《徽州家譜的理論與方法研究》,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第57-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