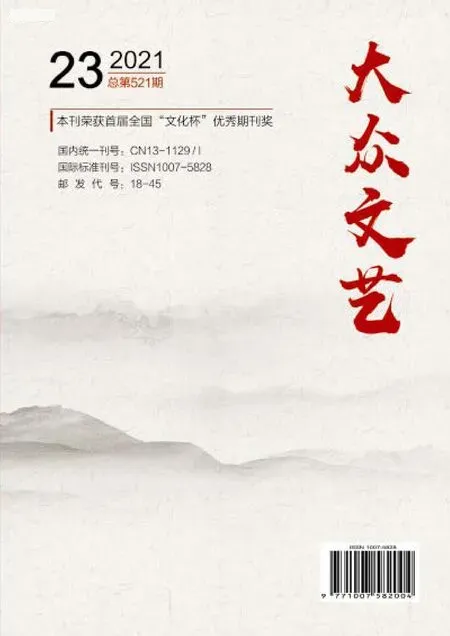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清初四僧”藝術作品成就原因及影響
(南京林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210037)
一、通過“清初四僧”作品當今貨幣價值透視其“含金量”
2004年,八大山人《山水書法合璧卷》拍賣成交價為1100萬元。
2004年,石濤《奇峰怪石圖卷》拍賣成交價為572萬元。
2005年,髡殘《溪山垂釣圖軸》拍賣成交價為408.1萬元。
2010年,八大山人《竹石鴛鴦》立軸拍賣成交價為1.1872億元。
隨著時間增長,“清初四僧”的藝術作品價值歷久彌新。2019年3月12日,中國新聞網曝出八大山人暮年作品《芙蓉蘆雁圖》估價為1400萬港元至1800萬港元。1
根據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清初四僧”作品藝術成就高,極具賞析與探究意義。
二、“清初四僧”人物、作品背景基本介紹與分析
1.“清初四僧”
“清初四僧”是指朱耷、石濤、髡殘、弘仁。四個人或表現亡國之痛,或表現不因國家破滅,向命運低頭的頑強之情,作品呈現出強烈的個性化特征,與主流地位正統派風格差異甚大。
2.八大山人朱耷
朱耷(1626-1705),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畫家,號八大山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九世孫。
八大山人以水墨畫著稱,多在自然中取材。他出身尊貴,本是皇家世孫,是朱元璋直系親屬。八大山人所動物,都不似在現實中看到那樣。這些動物的眼珠子都是翻著白眼且能轉動的。作品《鹿》,就是典型托物言志的表現,畫作中的鹿眼,桀驁不馴的向上翻著白眼,在夸張的造型中表達孤傲不群,以此表達對新王朝的不滿、不服、孤傲。朱耷畫畫,用墨極少,如《涉世》幾筆就完成了一朵荷花的描繪。他有一首詩“墨點無多淚點多”,就表現出自己雖然用墨極少,表達的情感卻是很豐厚的。
3.石濤
石濤,朱亨嘉之子,石濤構圖奇特,干濕并用,更喜濕畫,并精于破墨法。他注重創新,雖廣泛學習各家技術,卻并沒有拘泥古人的作品風格,主張“借古以開今”“我用我法”。他不盲目從眾,作品多取自于現實,也強調應從現實中去獲得感受,以此表現在畫作中。2石濤畫作以全局為重,不拘小處瑕疵,追求全局的豪放蓬勃氣勢,在追求氣勢上又善于留白,給人以豪放卻不緊促,宏博卻不繚亂,濃墨卻不悶塞的感覺。正是這種畫作虛襯實、實襯虛、淡破濃、濃破淡造就出如樂章般抑揚頓挫、交織的畫作。
4.髡殘
髡殘,清畫家,在明滅前七年已經出家,與石濤合稱“二石”。二十七歲時遁入佛門,削發為僧,三十歲時,明朝滅亡,他成了明代遺民。髡殘提倡師法自然,也是從臨仿古人入手,在四元家中特別受王蒙影響,但臨古不泥古,與石濤“借古以開今”有隱約相似,與石濤并稱為“二石”,想必也會有此方面原因。髡殘的作品充滿活力,多以真實自然風景為基礎,大膽注入個人感受。髡殘不喜積墨多遍,也不用淡墨渲染,多用渴筆禿筆,山石多皺皺蒼蒼,近看則多是點墨。不以細部雕刻為主,而在乎整體的宏偉氣勢,這方面,也與石濤有所相似。
5.弘仁
弘仁,清代著名畫家,號漸江。他與查士標、孫逸、汪之瑞等四人并稱“新安四大家”,為“新安畫派”創始人。他也是明代遺民,國家破滅后出家成為僧人。其筆法清新俊逸,尤其愛繪制黃山松石。弘仁的山水作品存在兩種不同表現形式,一種以子久、王蒙畫法為基礎的表現方法,即山石用披麻索皴,設色淡雅,采用小青綠或淺降畫法,例如《疏泉洗研圖》。另外一種則是以仿倪云林畫法特點,用墨筆勾皴,不設色,或施汁綠,景物清勁秀逸。但不論怎樣,以清為法,是其作法基調。3
三、以歷史背景為主線,分析“清初四僧”作品成就原因
“清初四僧”都擁有相同的歷史背景—都是明代遺民,都懷有對明代的愛國情懷,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對新政權抱有不甘,始終保持著本身的倔強與孤傲。其作品也是文人本心的一種表達方式,也少不了這種情懷的縈繞。
明滅亡時,朱耷年十九,本想大展宏圖的他一夜之間由皇室貴族淪為亡命之徒,這樣巨大的反差對于他來說是致命打擊。為逃脫新政權的遺民政策,他于二十三歲遁入空門,從此以書為友,以畫為伴,將國破家亡的悲痛情緒隱藏在畫中,深沉又濃烈地表現出來。朱耷的繪畫有比較典型的特點,對所畫動物進行夸張處理,大多“白眼向人”,其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則是一位王子皇孫對于國破家亡的怨恨。對于這樣情感流露大膽且新穎的的畫作,在當時清代畫作主流“清初四王”來說,是少數的,是異端的。石濤較八大山人而言,兩人雖同是皇族后裔,但是石濤對于清朝統治的仇視可以說沒那么強烈,且出家后專心研究畫作,對國事并沒花費太多心思。根據歷史記載可以看到,明滅亡時,石濤不過三歲孩童,后在四歲遁入空門。所以,他在畫中的表達的愛國情懷與八大山人有不同,與新政權的關系并不是特別緊張。相反,有記載在康熙南巡時,石濤兩次接駕,結交顯貴,但由于他當時處于異端,往往被冷眼相待。到這里,可以看出八大山人與石濤雖都為皇室后裔都懷有愛國情懷,但一個終身懷有芥蒂,一個在盡力適應現實。
髡殘、漸江與八大山人較為相似,他們都屬于明朝遺民,但不同于八大山人與石濤的是,漸江不似八大山人一樣一生難以釋懷,也不似石濤般迫切融入時代,而是儼然出家人的模樣,不問世事。漸江的風格不似八大山人一樣怪異,不似石濤一樣恢弘,他的山水畫很少用粗筆深墨,筆墨嚴謹簡約,賦有簡約不簡單,清晰明了的清新空靈風格。“清初四僧”遵循自然法則,追求實際,在實際的基礎上各有其特色。都有相似卻又有差異的歷史背景,使他們畫作都有別于當時的主流,大膽創新形成了獨特風格。其審美等價值角度,可能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主流。
四、“清初四僧”對后世的影響
“清初四僧”在畫作中,有章法地將將遺民情緒表達得淋漓盡致,情融于畫,畫中帶情。對于起草構圖、用筆用墨、著色、潤色等技法上均有講究,而在講究的基礎上大膽突破原有框架原有思維,大膽創新。他們不止沖擊著清朝,對現代人更是一種可學習的創新思維。朱耷的“白眼向人”,石濤奇特構圖,髡殘的多用渴筆禿筆,漸江的筆墨嚴謹簡約不簡單、清晰明了的清新空靈風格等等,都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人均有著獨立風格的創新意識與掌控意識,他們給我們的重要啟示就是要在時代藝術共性中古為今用、開拓創新。
五、結語
在如今高速發展的社會,創新性思維必不可少,“清初四僧”帶給我們的是崇尚自然,大膽新穎,理性與感性的深切融合,在繪畫中找到本真,在繪畫中體現思考。我們要學會理性思考,感性“描述”,創造出新時代所應擁有的真性情作品。
注釋:
1.引自中國新聞網.
2.引自《清初四僧繪畫藝術讀解與鑒賞》作者 歐陽云編 (四)京都問賞心.
3.引自《中國山水畫史略》.徐英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