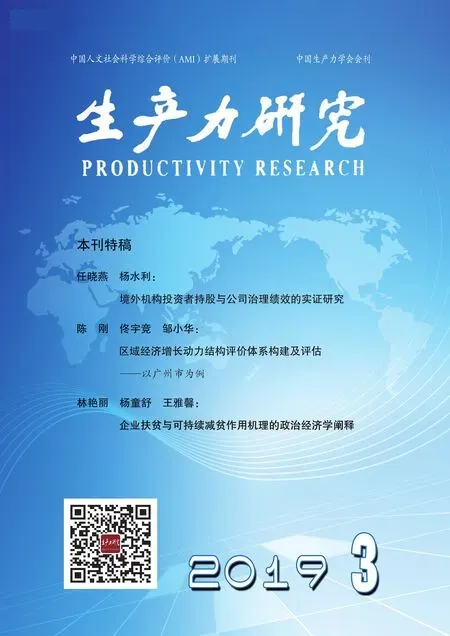影子銀行信用創造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的實證分析
——基于貨幣乘數視角
朱曉東,金嘉瑩
(1.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會計學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影子銀行體系的概念最初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執行董事麥考利提出。2011年,有關國際金融監管組織對其定義基本達成了一致。如金融穩定委員會(2011)[1]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影子銀行體系的本質是“游離在傳統銀行體系之外提供信用媒介的經濟活動或實體”。
我國除了2012年銀監會在年報中明確了幾項不屬于影子銀行業務范圍外,再無其他被廣泛引用的定義。由于國內外金融體系發展與成分結構的差異,國內學者對于影子銀行的范圍界定不盡相同。其中認可度較高的有三類:一是黃益平等(2012)[2]認為中國的影子銀行主要指國內所有金融機構在資金融通中作為信用中介向公眾出售理財產品的信托融資和委托融資;二是汪濤與胡志鵬(2012)[3]提出了三種不同統計口徑的影子銀行規模界定,即第一種是用中央銀行社會融資統計內委托貸款、未貼現票據和信托貸款余額之和表示的最窄口徑,第二種是用最窄口徑與信托資產和民間借貸之和表示的較寬口徑,第三種是用較寬口徑與非銀行持有的企業債券之和表示的最寬口徑;三是巴曙松(2013)[4]、李俊霞和劉軍(2014)[5]通過分析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的內涵后認為,現階段影子銀行應當在上述最窄口徑的基礎上加上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銀行承兌匯票以及民間金融。本文出于對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影子銀行業務的代表性以及規模考慮,將采用汪濤和胡志鵬的“最窄口徑”對我國影子銀行規模進行測算。
近年來,影子銀行體系的規模不斷擴大,依據上述影子銀行最窄統計口徑測算,截至2018年5月,我國影子銀行規模已達27.3萬億人民幣,在我國金融市場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影子銀行的出現為企業和居民提供信貸支持;但另一方面影子銀行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弱化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聯系,損害了政府貨幣政策的效力。周小川(2011)[6]指出,影子銀行體系存在著具備貨幣創造功能、參與貨幣乘數放大過程的可能性,并認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應充分考慮新環境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變化。事實上,隨著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和完善,使得影子銀行等除銀行外的金融機構具備了一定的貨幣創造能力。
關于影子銀行的貨幣創造機制,國內學者分別從影子銀行對貨幣乘數影響和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等層面做了大量研究。
(一)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乘數的影響研究
周莉萍(2011)[7]指出隨著影子銀行體系規模的不斷擴大,一方面基礎貨幣的統計將遺漏影子銀行的負債資金,另一方面,由于影子銀行不受存款準備金制度約束,圍繞存款準備金的貨幣乘數也將遺漏一個重要的市場因素。因此,無論從基礎貨幣還是貨幣乘數看,影子銀行都將大大降低當前貨幣乘數的有效性。
何平等(2018)[8]將影子銀行體系引入貨幣乘數模型時,將影子銀行“存款”分為具備流動性和不具備流動性兩部分。認為影子銀行對貨幣乘數的影響依賴于社會公眾持有現金的意愿以及影子銀行“存款”流動性的大小,并通過動態時間序列檢驗得出影子銀行體系會降低貨幣乘數的結論。
陸岷峰和楊亮(2018)[9]分別構建了將影子銀行存款納入貨幣統計和不納入貨幣統計的兩個貨幣乘數模型,對比不同模型中各因素與貨幣乘數的關系,并通過實證得出影子銀行規模的擴張與貨幣乘數具有長期的負向關系。
(二)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研究
學者們研究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角度。
1.以貨幣政策為導向,從IS-LM模型角度分析。如王振和曾輝(2014)[10]通過引入銀行信用創造和影子銀行流動性創造功能,根據修正后的IS-LM模型分析了影子銀行的發展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并通過實證分析證實,影子銀行的發展對貨幣政策的利率、信貸等傳導效果以及貨幣供應量M2產生顯著影響。
2.基于貨幣乘數角度的分析。如解鳳敏和李媛(2014)[11]以分流銀行存款的方式將影子銀行體系引入貨幣乘數模型中,進而分析影子銀行對貨幣供給補充與替代效應。并通過構建向量誤差模型和狀態空間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認為影子銀行體系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貨幣乘數,但在不同的經濟時期和貨幣政策下表現出明顯的“非對稱性”。李亙和魯靖(2015)[12]、王亞楠(2017)[13]同樣構建了引入影子銀行體系貨幣乘數模型進行分析,但他們單獨或同時使用狹義貨幣乘數(M1)和廣義貨幣乘數(M2)為應變量建立VAR實證模型、得出了影子銀行體系擴大了貨幣供應量的結論。
3.影子銀行體系能夠通過創造信用,削弱貨幣政策工具的效力。李新功(2014)[14]和常凱等(2017)[15]直接通過建立VAR實證模型、脈沖響應等分析認為,影子銀行體系能夠創造信用,在短期內擴大貨幣供應量,進而削弱貨幣政策工具的效力。
綜上所述,影子銀行體系的引入,對貨幣創造機制產生沖擊,進而對貨幣乘數產生影響,并最終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目前,從貨幣乘數角度分析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的學者較少。并且在這些學者中,大多沒有考慮社會公眾持有現金偏好的影響以及在引入影子銀行貨幣創造機制時只考慮了影子銀行出于償付保證而預留部分資金的因素,而沒有考慮影子銀行“存款”是否具備流動性,從而決定是否應納入貨幣統計。此外,現有研究中實證數據較為陳舊,時間跨度較短。對此,本文基于貨幣乘數理論,綜合考慮上述多種因素、構建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選取2005年至2018年5月的月度數據進行實證檢驗,以期更加準確地分析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為提高貨幣政策效應提出合理建議。
二、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構建
由貨幣乘數理論可知,貨幣供應量M2可以表示為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的乘積。因此,在假定基礎貨幣不變的情況下,影子銀行體系是否對貨幣供應具有放大作用等價于影子銀行體系是否對貨幣乘數具有放大作用。
為了充分考慮影子銀行“存款”流動性和預留資金比例兩者對影子銀行體系引入貨幣乘數模型的影響,本文在借鑒何平等(2018)[8]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傳統貨幣乘數模型和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
(一)傳統貨幣乘數模型分析
為了便于對引入影子銀行體系貨幣乘數模型的分析,本文對傳統貨幣乘數做如下假設:
假設1:初始資金總量為B(B>0)。
假設3:商業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r(0 圖1 傳統貨幣乘數模型 圖1所示是傳統貨幣創造的過程,即中央銀行在發行基礎貨幣(B)后,其中的進入商業銀行系統轉化為商業銀行存款,余下部分則由社會公眾出于支付等需要而以現金的形式持有,并且不再進入商業銀行體系;商業銀行在取得存款后,按照規定向中央銀行繳納一定比例的存款準備金r后,將剩余(1-r)B部分發放銀行貸款;之后這部分派生貨幣將再次以和的比例分別進入商業銀行系統和由社會公眾以現金的形式持有,不斷重復上述貨幣創造的過程。由此,可以得到: 為了更好地分析引入影子銀行體系后貨幣乘數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調整假設2為假設4: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中,比例的資金由社會公眾持有,余下部分的資金則進入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體系中。并進一步假設: 假設5:進入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的資金中,最終被商業銀行吸收為存款的比例為,則進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資金比例為。 假設6:進入影子銀行的資金可以分為具有流動性和不具有流動性兩部分。本文假設具有流動性的部分比例為,即比例進入影子銀行的資金將納入貨幣統計,則不具有流動性的部分比例為,即比例進入影子銀行的資金將不納入貨幣統計。 假設7:影子銀行出于償付保證等目的,從吸收資金中預留資金比例為,即預留扣減率為,并且將全部預留資金以存款的形式進入商業銀行。 于是,在引入影子銀行體系后傳統的貨幣創造過程演變成如圖2所示。中央銀行在發行基礎貨幣(B)后,社會公眾持有現金占比依舊為,剩余的B部分中,被商業銀行吸收為存款、則進入影子銀行體系。 圖2 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 對于商業銀行而言,進入商業銀行的資金流向與傳統貨幣創造過程類似,即在扣除向中央銀行繳納的存款準備金后,將剩余部分發放銀行貸款。 由式(4)、(5)、(6)可以求得引入影子銀行體系后的貨幣乘數k2: 為了進一步探討影子銀行體系是否對貨幣乘數具有放大作用,本文進一步將式(3)和(7)作差,可得: 因此,本文認為,影子銀行體系是否擴大了貨幣乘數最終依舊取決于影子銀行“存款”流動性與影子銀行吸收存款的比例以及預留扣減率之間的相對大小。 如上文對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分析,影子銀行吸收存款的比例以及預留扣減率是影子銀行體系影響貨幣乘數的重要因素,但這兩因素的統計數據難以獲得。現有研究認為,影子銀行體系規模的變動中隱含了這兩個因素變化。具體而言,影子銀行吸收存款的比例越高,預留扣減率越低,則代表影子銀行體系的規模越大;反之,則代表影子銀行體系的規模越小。因此,本文選取影子銀行規模作為影子銀行吸收存款比例和預留扣減比例的代理變量。考慮到影子銀行業務的代表性以及數據的可得性等,本文采用上文中影子銀行規模以中央銀行公布的委托貸款、信貸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存量之和的計量方式測算。而央行公布的數據中,2015年以前只有增量數據。為了盡可能保留多的樣本點,本文假定2002年以前三者的規模為零,再根據增量數據推出2002年以后的存量數據。 除此之外,模型還包括被解釋變量貨幣供應量(M2),以及控制變量法定存款準備金率(r)。其中,存款準備金率采用中央銀行公布的法定存款準備金。 由于貨幣供應量和影子銀行規模呈現出明顯的季節趨勢,因此,本文采用Census-X12對三者進行調整。同時,為了消除量綱差異,對影子銀行規模采用萬億為單位。 2005年至2018年5月影子銀行規模和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月度數據如圖3所示,在樣本區間內,兩者整體趨勢均表現出明顯的向上趨勢。尤其在2011—2014年,當影子銀行規模快速上升時,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時也表現出了加速上升趨勢,因此可以認為兩者表現出了明顯的正向相關性,與上述分析相吻合。 圖3 影子銀行規模和廣義貨幣供應量趨勢圖 如前所述,本文選取2005年至2018年5月的月度數據作為樣本區間,共計161組數據,按構建的實證模型進行分析。 1.平穩性檢驗。為了保證模型方法分析的可靠性和準確度,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驗證各變量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結果顯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所有變量原序列均接受原假設,即序列都是非平穩的。而影子銀行規模的一階差分序列D(SB)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貨幣供應量、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一階差分序列 D(M2)、D(R)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所有變量為一階單整序列。 表1 ADF檢驗結果 2.Johansen協整檢驗。在協整檢驗前,需確定最優滯后階數。根據信息量指標原則,在滯后階數為3時信息指標達到最小值的數最多。因此,本文選擇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 隨后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顯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變量之間存在一組協整關系,也就是說變量之間確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表2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并由檢驗結果進一步可得到協整方程為: 由此,可以認為影子銀行規模的擴大對貨幣供應量具有正向作用,而利率與貨幣供應量具有負向關系,并且由于利率與貨幣供應量具有較大量綱差異導致了其系數絕對值較大。 3.格蘭杰因果檢驗。上述協整檢驗結果顯示影子銀行規模、貨幣供應量等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為了進一步探究各變量與貨幣乘數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進一步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影子銀行規模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換而言之,影子銀行規模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貨幣供應量變動的格蘭杰原因。 表3 格蘭杰因果檢驗 4.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在得到影子銀行規模是貨幣供應量的解釋原因的結論后,為了進一步分析當影子銀行規模受到一個沖擊后,貨幣乘數的長期調整過程,本文進一步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結果如圖4所示。 圖4 貨幣供應量對影子銀行規模的脈沖響應函數 圖4表明,當影子銀行規模在0期受到一個正向沖擊時,即影子銀行的規模擴大,將引起自1期之后貨幣供應量的上升。雖然在第4期時,貨幣供應量有所下降,但不足以彌補前期的上升,其相較于影子銀行規模受到沖擊前具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在第4期之后,貨幣供應量持續受影子銀行正向沖擊的影響而上升。 通過構建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發現,影子銀行體系將對貨幣乘數產生影響,進而影響貨幣供應量。而影子銀行體系是否擴大了貨幣供應量主要取決于影子銀行“存款”和影子銀行吸收存款比例、預留扣減率的相對大小。 實證結果顯示,就我國目前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而言,影子銀行規模的擴大將擴大貨幣供應量,最終將削弱貨幣政策效力。而根據模型推導,這一結果很有可能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影子銀行和商業銀行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影子銀行“存款”流動性變化,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也將改變。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高度重視影子銀行體系信用創造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貨幣乘數的變化決定著貨幣供應量這一重要中介指標的變化。因此,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僅應充分考慮影子銀行規模變化對貨幣乘數的影響,以達到精確調控貨幣供應量,而且應當時刻關注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的變化情況,以達到科學制定貨幣政策的目標,提高貨幣政策效力。 2.重點關注影子銀行吸收存款比例、存款“流動性”及預留扣減率變化。貨幣政策的出臺是否能充分考慮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供應的影響、以及能否有效地依照影子銀行體系來制定,有賴于對影子銀行吸收存款比例、“存款流動性”以及預留扣減比例等數據的可靠性。因此,政府及監管機構應當明確影子銀行的業務范圍并加強對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督和管理,特別是加強對行業相關數據的統計與調查,才能增加貨幣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和科學性。 3.加強對影子銀行體系的統籌監管。隨著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影子銀行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勢必對金融市場的穩定以及貨幣政策效力帶來影響。因此,政府需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一方面,像銀行一樣設立法定存款準備金制度,加強政府對貨幣供應量調控效力,從而增強貨幣政策效力;另一方面,加快建設影子銀行監管體系,使其與金融市場發展相匹配,從而服務于經濟的發展。

(二)引入影子銀行體系的貨幣乘數模型




三、影子銀行體系對貨幣乘數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與數據選取
(二)數據分析

(三)實證分析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