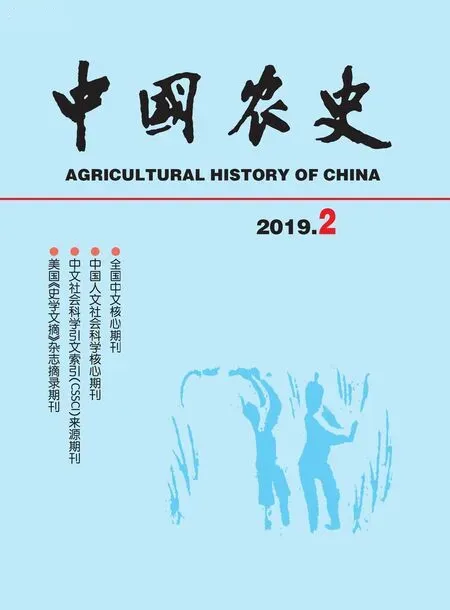張之洞籌創湖北農務學堂初期問題及原因探析
石 松 盛邦躍
(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江蘇南京210095)
晚清重臣張之洞乃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他于1889 年出任湖廣總督后,更是利用十多年的時間在荊楚大地開創了著名的區域近代化模式——湖北新政。利用湖北這個巨大的試驗場,張之洞在辦實業、興教育、練新軍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圖強之舉措。湖北農務學堂作為開辦新式實業教育的主要代表,和引進西方農業科技的重要手段,得到張之洞的高度重視,并被寄予厚望。這一點,從張之洞命人多次向西方國家催聘洋教習來華工作等諸多歷史細節中可見一斑。在張之洞親自關心下,籌建中的農務學堂從美國康奈爾大學募得首位洋教習布里爾。布氏于1897 年9 月抵鄂,開始幫助張之洞創辦農務學堂,同時考察當地農業,并提出改良建議①Shavit David. The United States in Asia:A Historical Dictionary,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0. 418.。
一、相關研究綜述
據國內相關文獻,農務學堂的興辦,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98年創辦到1900年。這一時期由一位張姓道員任總辦,由總辦推薦的監督組成學校行政主管。但此二人都是保守的官僚,既不懂農業,又缺乏辦學熱忱,既不直接接觸洋教習,又不關心學生②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4-105頁。。所以,這一時期的辦學總體而言是失敗的。直到1900年張之洞改任羅振玉為監督,并改聘四位日本教習,對農務學堂進行了整頓,學校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取得了一些進展。從時間上來看,美國教習布里爾在農務學堂僅工作了約三年的時間,于1900年羅振玉來任監督前辭職離開。布氏在華的工作時間剛好與農務學堂籌創的第一階段相重合,可以說他親身參與了農務學堂初期的籌創,并完整經歷了這一時期遇到的問題和挫敗。
湖北農務學堂乃中國歷史上較早引入西方先進科技和教育理念,并創辦起來的第一所具有近代意義的農業教育機構,因此也得到了較多學者的關注。對農史和農業教育的相關研究,已有不少涉及于此③石方杰:《晚清湖北教育發展概略》,《江漢論壇》2004 年第12 期;王迪:《清末民初我國農業教育的興起與發展》,《中國農史》1987年第1期;李玉:《晚清實業教育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徐凱希:《晚清末年湖北農業改良述略》,《中國農史》2004年第1期等。。此類研究多限于描述學堂的創辦和發展歷程,對于其興衰得失一般未做深入剖析,僅有少數研究將湖北農務學堂創辦初期的困境歸咎于管理不善、用人失察等表面原因。還有一類相關研究出于關注張之洞其人的角度,對于他的農業思想、教育思想等進行了探析④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年;趙泉民:《論張之洞的近代農業思想》,《古今農業》2005年第1期;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陳鈞:《張之洞與清末湖北農政》,《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6期等。。但是此類研究總體而言趨于宏觀,未對農務學堂的創建等具象進行專門研究。此外,以上兩類研究中有關湖北農務學堂的內容,都是以《張文襄公全集》等國內現存文獻作為史料基礎。
筆者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學期間,有幸在其特藏檔案館(Division of Rare & Manuscript Collections,Kroch Library)覓得湖北農務學堂首位洋教習布里爾生前保存的史料和檔案。這些史料在其去世后被捐至康奈爾大學并一直保存至今。康奈爾大學既是布氏的母校,也是其曾工作的地方。他結束中國之行回美后,曾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的農業試驗站從事農業推廣的相關工作。這批史料可以看出,布里爾具有良好的檔案保存意識和習慣,他收藏保存的史料內容豐富,包括其本人就在華工作經歷撰寫的文章和評論,他個人的往來書信,他在華工作的相關檔案、文書和實物,他收集保存的剪報,以及涉及其在華工作的相關報道等。這批史料形式多樣,在已有國內研究中從未被使用,因此非常珍貴。其應用價值在于,首先,補充了國內現有相關研究和史料的一些空白。例如,由于年代久遠,國內現有文獻中,對于布里爾這位中美官方在近代歷史中開展農業科技交流的代表性人物,只有“聘請康奈爾大學農學士……美國教習布里爾(Brill)①在少數研究和史料中也有的使用“白雷爾”這一中文譯名。但在檔案資料中,布里爾來華的官方護照、文書等基本均使用“布里爾”的中文名稱。”等極為簡略的陳述和幾條較為零散的信息。利用這些新發掘的史料,可以確定該洋教習全名為Gerow.D.Brill,此前有少數中文文獻將其英文全名誤作C.Brill,并可獲知其來華背景、在華參與籌創農務學堂經歷等更多的歷史細節與原貌②石松、王思明、盛邦躍:《布里爾與湖北農務學堂的籌建》,《中國農史》2017年第5期。。其次,這些新發掘的史料也為進一步開展張之洞及其洋務思想和實踐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為新鮮和獨特的視角。布里爾作為張之洞親聘的教習,在其史料中顯示出他有著較為便利的條件向張之洞直接匯報其想法和建議,張之洞也曾就改革舉措等議題在府中單獨召見布里爾,故兩人可謂“私交甚篤”③布里爾檔案中保存著一篇其本人撰寫的名為《CHANG CHI TUNG(張之洞)》的長篇評論,以個人視角和觀點詳細評述了張之洞其人以及湖北新政的諸項改革舉措。文中提及張之洞曾在府中召見并與其單獨會談,還派人多次向其征詢改革建議。另有一篇布里爾保存的剪報中的報道,題為《THE AWAKENING OF CHINA(中國的覺醒)》,出自英國報紙《The Englishman》,主要內容是記者就當時中國局勢等問題對布里爾的采訪。報道開篇,就介紹布里爾是剛剛結束了在華工作返回美國,稱之為中國問題的專家,且與張之洞“私交甚篤”。。因此,布里爾檔案中他自己撰寫的有關張之洞的評論文章、與親友通信中介紹的史實、呈書張之洞的建議等,不僅真實可信,也幫助今世學者多一個視角去看待和評述張之洞的湖北新政和功過得失。
簡言之,本研究以上述新發掘的史料為線索,從洋教習布里爾的經歷和視角出發,論述布氏在華工作期間,同時亦是湖北農務學堂籌創初期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在此基礎上,試圖從張之洞創辦農務學堂之動機、規劃、實踐等幾個方面去進一步探析和論述這些問題的具體表現和產生根源。
二、張之洞籌創農務學堂初期出現的問題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5月),湖北農務學堂正式出示招生。其示文的內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張氏對中國農業情況的評價和認識,以及學堂成立之時的一些基本情況。“照得富國之本,耕農與工業并重,近來泰西各國,農務最為興盛,由于格致、理化之學日益精深,知地力之無盡,藏于辨土。宜察物性,廣種植,厚培壅,諸事講求,不遺余力。美國尤以農致富。其制器造物,翻陳出新,務求利用。亦皆學有專門,精心考究。中國地處溫帶,原隰沃衍,甲于環球,乃因農學不講,坐使天然美利,壅閼不彰,此農學不講之故也。至于工藝,尤為西國擅長……本部堂/院前聘美國農學教習,早經到華,所購西式農具果木佳種,即日亦可運到。現暫借保安門內公所,為農務學堂,仍俟另建學堂落成遷居。一面在省城內清查官地,租用民田,興辦農學,講求相土辨種之方,炭養相資之理,兼及各項畜牧事宜……。”④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 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
由于中國傳統士人長久以來對農業的輕視等原因,初期學堂報名人數甚少。經過數月努力,學堂最終錄取了首批20 名學生,于八月開學,暫分農、桑二科⑤蔡振生:《張之洞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4-105頁。。雖然人數不多,但當時進入學堂的,大多都是有志于農業或有志于強國的士人。用今天的話說,那時的湖北農務學堂,可謂是“興農學、揚國光”的學習共同體⑥馮寧、朱殊:《湖北農務學堂創始期的三位聞人》,《武漢文史資料》2010年第12期。。

圖1 張之洞發布的農務學堂招生告示(現存美國康奈爾大學)
由于農務學堂在羅振玉任監督后的第二階段發展相對較為成功,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因此,幾乎當前所有史料和研究均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階段,而對于學堂開辦和籌創初期發展情況的關注和記錄極少。依據布里爾檔案中的相關內容可知,他在華工作的這段時間實際遇到了較多的阻力與困難,這也是他最后“心生厭惡”并辭職離開的主要原因①布里爾檔案中保存著其本人撰寫的長篇評論文章《CHANG CHI TUNG(張之洞)》,談及其個人參與創辦農務學堂的經歷及遇到的各種困難,包括無法得到被承諾的土地以開辦試驗農場,中國官員的決定和政策“朝令夕改”等,使得他最終“心生厭惡”而辭職離開。。從布里爾的敘述看,前文述及的用人失察、管理不善等現象均可視作農務學堂籌創初期遭遇困境的一些表面或直接問題,但絕非主要問題。結合布里爾的經歷和記錄,筆者認為,張之洞籌創湖北農務學堂初期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規劃之盲目性
張之洞對于西方農學的認識,始于其擔任兩廣總督期間。此時,他已知道西方有植物分類、土壤、農機等學科;知道西方農業已經達到“國無棄地,地無遺力”的境界。當時,他也曾嘗試組織引種國外桑棉,但基本未獲理想成效②苑書義:《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中華書局,1999年,第16-18頁。。光緒二十二年,他由兩江返回湖北,當地連續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次年漢口水位達歷年最高紀錄,受災地區遍及八縣,饑民百萬以上。正值甲午戰后,當時財政極端拮據,雖到處張羅告貸,亦難補救于萬一。如此困苦之局面,迫使張之洞認真考慮湖北的農業問題③蘇云峰:《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第126頁。:“富國之道,不外農工商三事,而農務尤為中國之根本”;“農政修明,以美國為最。”④劉平:《張之洞傳》,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14-215頁。于是,引進西方先進農業科學技術,從美國聘請教習的想法應運而生。但是,究竟引進什么樣的技術?以何種方式引進和推廣?所聘洋教習從何處開始著手?具體承擔什么任務?面對這一系列的具體問題,張之洞此時并未作詳細的考慮和具體的規劃。于是,農務學堂在籌創過程中,就經常表現出規劃的盲目性,也會形成規劃實施過程中“走一步,看一步”的隨意性。
對于以上的分析,或許能從以下一些史實和推斷中窺見端倪:張之洞有了從美國聘請洋員幫助發展和改良農業的想法后,首先是通過當時在武昌辦學的文華書院(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①由美國圣公會于1871年10月20日在武昌創辦,初為男童寄宿學校,中文校名為文華書院,英文名Boone Memorial School。校長貝錫鼐(Sidney C. Partridge)于美國物色合適人選。貝錫鼐乃美國在華傳教士,曾畢業于耶魯大學,但當時康奈爾大學代表了美國農業科技和教育領域的最高水平,貝錫鼐遂首先選擇向康奈爾大學求助,并于3月15 日致信康奈爾校長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②Jacob Gould Schurman(1854年5月22日-1942年8月12日),美國教育家、外交家。1892-1920年任康奈爾大學校長,1921年6月2日被任命為美國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公使,1925年離任。:“我受張之洞閣下委托給您去信,想必您對他的名字也不會陌生……請您在貴校農學院代為物色合適人選來華,工作時限為兩至三年,主要負責在武昌或附近地區建設和運營一個‘示范農場’。這個人選當然最好是教授或者教師,不僅有能力負責‘示范農場’的建設和管理,而且還能夠教習與培訓。張之洞閣下希望將來得以建成的‘示范農場’能夠配備當今美國正在使用的最先進的農業設施,并以此向前來參觀的官員展示。當然這不包括一些大型的農業機械,當前在中國還無法使用。在此農場基礎上,還將建設一所農務學堂……”貝錫鼐在信中還強調張之洞閣下希望盡快落實此事③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
從這封信的內容可以看出,張之洞聘請美國教習最初的構想的首要目標是建設一座示范農場,以此為平臺向世人展示西方農業科技和設備之先進性。而創辦農務學堂,則是依附于建設農場的一個次要目標,所以在信中也僅一句略過。基于此,對于選聘的洋教習,未來的主要工作將是農場的運作和管理,在此基礎上才兼顧一些培訓和教習任務。正是依據這封信中提出的要求,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最終選擇推薦了當時在讀的碩士生布里爾。因為從布里爾的成長經歷來看,他首先擁有運營自己家庭農場的豐富實踐經驗,此外也曾在本科學習期間利用假期參與為紐約州農民開展短期培訓和提供技術推廣服務。所以,布里爾對于貝氏信中列出的條件乃理想人選,他本人經過考慮也同意接受推薦,并通過聯絡貝錫鼐最終得到張之洞的聘任許可。以今人的視角來分析,作為早期來華且擁有良好的農學專業素養的高學歷人才,布里爾帶來的先進農學思想和科技對于當時極度落后的中國傳統農業而言可謂難能可貴。但是,他的經歷和特點或許使之更勝任農場經營者或者農業推廣者的角色,而未必是開辦農務學堂所需要的農業教育者的最佳人選。這一角色的差異,或許也為后來農務學堂籌創初期的失敗埋下了一處伏筆。從實際情況來看,自布里爾抵鄂直至辭職離開,張之洞曾多次承諾將不同地塊交予布氏創辦農場,但最終無一兌現。布里爾這期間真正從事的主要是農務學堂的教學工作。農務學堂初設學制為4年,前2 年補習預科,后兩年學習正科④華中農業大學校史編委會:《華中農業大學校史(1898-1998)》,華中農業大學,1998年,第4-5頁。。因此,布里爾在華期間主要承擔了學生的預科教學,負責教授英語和生物、化學等基礎課程,并未完全發揮其優勢和特長。
當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貝錫鼐未能準確領會或者表述張之洞的本意和真正想法。但是,布里爾于1899年10月寫給張之洞的一封信中的部分內容,則進一步佐證了創辦農務學堂并非張之洞的初衷:“我來到中國已經有兩年的時間了。在我初到之時,這里的官員就告訴我,我受聘的主要目的是改良本地農業。為此,我將得到一大塊土地,并在此之上種植谷物、果樹、棉花、桑樹、茶樹等,同時飼養馬、牛、豬等牲畜。那時,沒有人跟我提過開辦學堂一事……后來,才有人告訴我,有了地之后,需要先開辦一所學校。”⑤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至于張之洞為什么從最初創辦示范農場的規劃轉變為創辦農務學堂,依據現有史料尚不得知,或許是他后來逐漸意識到發展農業教育更有意義;亦或許是他暫時拿不出合適的土地用于建設示范農場,于是“退而求其次”,先辦學堂作為權宜之計。但不論是何原因,這里至少可以看出,張之洞籌創農務學堂之初就沒有依據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科學論證和細致規劃,在實踐中體現出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
缺乏科學細致的規劃,在張之洞與布里爾簽訂的工作契約等相關文件中也得以體現。布里爾檔案中,保存著他當時與湖北當地政府和張之洞指派的農務學堂總辦分別簽署的中英文兩個版本的工作協議,其內容一致:布里爾來鄂“充當農務教習,經管教導種植五谷桑茶棉麻,種植各種果品樹林,以及各項畜牧孳生之法,各種新式農具,各種水利理法。皆為有關農務之事,均應盡心教習試辦。擬先擇地設立田莊一所,種植各種土產果木,以新法培植,均須有益農務。遇有考察情形,應隨時稟報,如地質并各項種植情形,及應如何設法使有利益于田地,如何驅除水患,何等牲畜應自別國購來使有益于畜牧,何等果木應自別國購來使有益于種植,均當悉心研究。布里爾到鄂三月后應將所見農事呈報,在三月內當至本省各處游歷,以便考察農學。學堂俟察報后方可開辦,至隨后見聞則隨時稟報。”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張之洞最初的想法乃先“設立田莊”,即建設示范農場,之后再考慮開辦學堂。此外,對于聘請洋教習指導和改良農業的想法,當時只是一個較為粗放的概念,缺少具體和詳細的實施方案與之配套。所以,該協議基本上將主要的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內容全部予以羅列,作為洋教習之任務。在“有利”或“有益”的宏觀原則下,作物種植到動物養殖、農業機械到農田水利,農業考察到引進品種,建設農場到創辦學堂,張之洞對布里爾之期望,可謂“包羅萬象”。顯然,這樣的期望是盲目和不切實際的。
誠然,清末時期中國傳統農業之積弱,需要進行徹底的改良。從這份協議中,可以體會張之洞當時對于引進和借鑒西方農業科技之決心。但徒有迫切的心情,沒有科學和細致的規劃,不能針對最關鍵問題尋找最佳突破口,如此不分輕重緩急的設計,實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之嫌,也很難獲得預期的成效。

圖2 布里爾簽訂的中英文協議(現存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
(二)動機之搖擺性
不管是開辦農場,還是實際籌創農務學堂,張之洞雖無科學和詳盡的規劃,其基本意圖和直接目的還是確定的,那就是希望通過聘請洋教員,引進西方先進農業科技,改良極度落后的中國傳統農業①王姍萍、黎仁凱:《張之洞聘任洋員探析》,《安徽史學》2005年第4期。。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尤其是在籌創農務學堂初期,他的很多做法卻表現出其想法和動機似在“自強”與“求富”間轉換搖擺。如此帶來的影響,除了使農務學堂的籌創難有明確規劃,也使得布里爾等眾人在實踐中無所適從,困難重重。
“自強”和“求富”是晚清歷史上洋務派興辦洋務的兩項主要內容與追求,其一般規律多是先舉辦“自強”為內容的軍事工業,而后由于經費支絀,再轉而進行“求富”為內容的經濟活動。此時的張之洞,剛好面臨著洋務運動從“自強”到“求富”的轉化②劉平:《張之洞傳》,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17頁。。因此,在他的很多決策和行為中,既能看到培養人才、改良農業的“自強”抱負,也能感受到經費掣肘的窘迫和無奈“求富”的動機。布里爾在評論張之洞的文章中的一段描述,也表現出了張之洞的一些境況:“作為朝廷重臣,他忠誠、清白,無私厚愛其治下之民,為大清帝國謀求福祉,從而聲名顯赫。他不貪戀財富,這一點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難能可貴。他本應成為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因為他有太多便利的斂財之機。實際上,眾所周知,相比于像他這樣級別和地位的官員來說,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位‘窮官’。他衙門的所有收入,都被用于公共事業和慈善。”布里爾還提及自己辭職的原因,除了自身抱負難以實施等主觀因素,還有個客觀因素就是張之洞也有意改聘日本教習,因為費用更低,可以節省開支③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2。
張之洞發布的農務學堂招生示文則是更明顯的例子。從上文引用該示文的內容中,首先可以感知張之洞對西方農學的理解和進行借鑒改良的“自強”愿望。但是,在談及農務學堂入學費用時,示文亦云:“查西國無論何種學堂,均由學生自納費用,為數頗鉅。今設立農務工藝各學堂,凡一切建堂租地、購種置器、教習員司薪水,概由官給……其學生火食油燭筆墨零用等項,酌令學生每人每月納銀元四枚,稍資貼補……”④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可見,礙于經費原因,農務學堂籌創初期不得不通過收取學生費用來“求富”和維系。每月四兩銀元,絕非當時普通人家所能負擔,因此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招生人數和生源質量,制約了農務學堂籌創初期的發展。
除了在農務學堂籌創初期的招生過程中,在張之洞提出的建設農場的想法中,同樣也包含著其“自強”和“求富”的雙重動機。根據布里爾檔案中的相關史料,他嘗試建設農場過程中的一些經歷即可看出張之洞在“自強”和“求富”兩個動機間舉棋不定和左右搖擺。首先從前文提及的布里爾簽署的工作協議來看,張之洞就建設農場提出的“有利”和“有益”原則,很好地體現出他發展農業的“自強”主張。而下面的一些細節,亦可看出張之洞的“求富”意愿。據布里爾在檔案中記述,自己曾被多次追問,如果建成農場,能有多少盈利,是否足以維持農務學堂的日常運轉。為此,布里爾不得不在給張之洞的信中詳細解釋,示范試驗農場與普通農場存在很大區別,其建設目的也絕非盈利。“夫栽種之利與考究栽種之利自各不同。栽種之利只須下種收割,其中毫無鉅費;若云考究必先備地一方,視其種輿某地相宜,較之大田下種則功多費鉅矣。”⑤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
雖然布里爾直至辭職離開也沒有得到合適的土地建設農場,但他在此過程中也多次聯絡和敦促張之洞解決建設農場的土地。在其檔案中,他也將這一過程詳細記錄。我們可得知,張之洞多次承諾,也曾設法予以兌現,其中的一段經歷和波折,同樣可看出彼時張之洞“自強”和“求富”動機之間的搖擺。“雖蒙允地數區,遷延去夏,始于武備學堂之旁獲地三十畝焉。然此地于栽種頗不合宜,奈佳地難得,是以倩工人鋤高平低,去磚挖石……果樹棉花高粱并美國五色棉花均長成矣,里意欲少種大米事尚未商,忽聞還此地于武備學堂作為操場,則所種者不得不拔除凈盡,但無他地可移,前工不幾廢乎。”張之洞已批給布里爾一塊不大的田地,雖非理想之選,但聊勝于無。布里爾已經在此地開始工作,并取得一些進展。但好景不長,部分承載著張之洞“求富”愿景的這塊土地,又很快被收回用作張之洞的軍事改革和培養軍事人才,可以說被完全的“自強”之舉取而代之。如此之動搖和變化,的確也讓布里爾無所適從,幫助籌創農務學堂也自然難有作為:“里愿聞有幾何栽種之地,地在何方,何地畜養牲口,再收新生若干,否則不知從何下手矣。”①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
綜上所述,不論是單純的創辦農務學堂或者示范農場,還是和其他洋務新政放在一起權衡和比較,張之洞都表現出其行為動機的多重性。在創辦農務學堂和農場的實踐中,他也曾力圖將“自強”和“求富”的雙重動機結合起來,希望能夠實現二者兼顧和雙贏,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條件下顯然是難以實現的。由此亦可得見張之洞當時籌創農務學堂境況之艱難。

圖3 布里爾呈書張之洞的翻譯版本及原文(現存美國康奈爾大學)
(三)決策之功利性
張之洞作為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換過程中的一位過渡性人物,其“經世致用”的指導思想和觀點即體現出其價值取向的功利性。例如在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張之洞創辦農務學堂之初,礙于經費有限,不得已而出現的一些“求富”的做法和從中盈利的想法。但客觀地說,張之洞的這些功利思想和行為還是以國家為本位,以“義”作為前提,而非消極意義上的負義求利。也就是說,他的上述行為絕非單純以利益為價值取向,尤其不是以個人或集團的利益為本位②林家有:《從傳統向近代轉換過程中的價值取向——論張之洞的功利主義思想》,《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河北省社會科學院,1999年。。這可以稱得上是張之洞功利主義思想中積極的一面。但是,由于當時晚清政府的危機四伏,張之洞的改革心切,他也在其決策過程中表現出急功近利,不遵循科學規律的問題。這是張之洞功利主義思想中消極的一面,也因此導致湖北農務學堂在籌創初期出現了相應的問題。
在論述農務學堂在此方面遇到的問題之前,不妨先看看布里爾在其評論文章中談到的張之洞在實施其他洋務新政中出現的急功近利的決策和行為。“他還開辦了兩家紡織廠,一家從事紡紗和織布,另一家則主要紡紗③1890年開始設立并建設的湖北織布官局與1897年建成的湖北紡紗局。。當這些棉紡廠最初由外國人管理的時候,都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很快就覺得聘用洋人管理并無必要,于是改由中國人來負責管理。從那時開始,這些棉紡廠就陷入持續虧損……在中國人管理下,工廠產出的布匹質量很差,根本無法上市銷售……”④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由此可見,他在新辦實業剛剛取得起色和些許成績之時,就急于用中國官員取而代之,以實現“自強”的目標并以此節省開支。中國官員在現代科技和管理能力上的欠缺,再加上清末官場戾氣的侵襲,張之洞的急功近利最終使其創辦的實業接連復制失敗的結局。
張之洞在湖北實施新政,除了“辦實業”和“練新軍”,“興教育”也是主要內容之一。為此,張之洞先后嘗試開辦了工業、農務等新式學堂。關于工業學堂的創辦和興衰,布里爾也有記載和評論:“張之洞曾創辦一所化學學校,后來將其逐漸發展成一所礦業工程學校,由一位學識豐富的英國化學家來負責這所學校①1892年張之洞在湖北設立礦務局,并創辦礦業學堂和工業學堂,附設于礦務局內,英國人駱丙生為教習。。當張之洞創辦的漢陽煉鐵廠開始生產時,就陸續有學生被送到這個學校,讓他們在這里學習煤炭和鐵礦分析等技術,而且希望他們兩年,至多三年就能學成畢業。英國教習試圖解釋,學生們必須要參加預科學習,需要先儲備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然而得到的答復是,學習基礎知識沒有什么必要,給這些學生培訓技術,使之學會分析礦石成分就足矣。于是,這位英國教習對此也就難抱希望,并選擇辭職而去。”②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傳統手工業和傳統農業的發展,長期依賴經驗摸索和技藝傳承,而不深究其科學內涵和道理,這也造成了張之洞的錯誤認識和決策——創辦新式學堂,讓學生“師夷長技”,但急于求成,只求學生掌握和應用技術,而不求其甚解,不重視基礎知識的學習。這種違背科學規律的想法和教育方式,自然難以成功。因此,美國教習布里爾在農務學堂籌創中面對的問題和命運和工業學堂的英國教習如出一轍。
首批學生入學后,布里爾認識到當時存在的一些問題,在寫給張之洞的信中向其強調,不論學生將來學習什么專業,數學、歷史、地理等學科都應該作為預科階段的必修科目;而對于學習農學的學生,則必須在預科階段就修讀生理學、動物學、化學、地質學等課程。要將這些學生培養成未來的農業人才,還必須讓他們通曉英語。布里爾以日本為例,向張之洞闡明,“日本初請外國農師,學者皆已通英文,故不費教授初學之力。”③據布里爾檔案中史料顯示,在湖北農務學堂工作期間,他曾利用假期赴日本考察其農業生產和農業教育。反觀農務學堂初期招收的這批學生,只有部分有一些英語基礎,多數都是零基礎。學習過數學、歷史等預科課程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這些學生僅預科學習就需要至少三年的時間④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由此也可看出,張之洞在籌創初期給這批學生只設定了四年學制(兩年預科加兩年正科)顯然不夠,有操之過急之嫌。
三、問題原因之探析
張之洞籌創湖北農務學堂初期出現的種種問題,既有其個人思想認識的局限性的主觀因素,也有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形成的一些客觀制約與影響。當然,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后者才應該是農務學堂初期遭遇失敗根源所在。正如布里爾在給張之洞的信中最后表達的觀點:“總之,我無法將遇到的這些問題歸咎于某一個人,但我認為我們是在一個錯誤的制度和體系下在行事。”⑤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因此,在分析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時,尤其是在認識張之洞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的思想認識、性格特點等方面的局限性時,也應該從其所處的時代背景出發,更加深入地去探尋其關聯所在,并客觀地加以剖析。
(一)矛盾心態和歷史局限性
由于晚清時期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出現的內外交困,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過渡性的時代背景,張之洞于此之中也形成了一種過渡性和矛盾性的性格特點和行事風格,從其觀點和行為,處處可見“保守性與進取性交戰”之映象①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6頁。。
張之洞作為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創辦新式學堂、引進西方農業科技的做法于當時之社會而言,已有相當的先進性。但是,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認識和觀點,也表現出了極大的局限性。張之洞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分子,亦無法超越其階級的藩籬,去真正的改弦更張,追求資產階級的理想。認識不到滿清政權的腐朽沒落,則無法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也不能順應時代前進之洪流。所以,張之洞的上述改良行為只是針對“器不良”和“技不熟”的表面問題,“變器不變道”,根本目的還是保存中國封建政治和倫理傳統。這種不觸及當時中國農業發展根本問題的努力與嘗試,也無法真正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諸多問題,自然難以達其目標,難獲理想成效。
(二)西學認知的膚淺和片面性
張之洞身處長期閉關鎖國的滿清王朝,他本人得以了解和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渠道和機會是有限的。已有相關研究認為,張之洞本人“對西學并未真正掌握,不過知道些大概而已。”還有人說他“對西學可謂博而不精,甚至也談不上博,他只是努力掌握,并以之豐富自己的思想學識而已。”②皮明庥:《儒臣官品和洋務心態》,《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河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河北省社會科學院,1999年。再加上當時在中國此方面的人才奇缺,張之洞身邊自然也無人能夠就此建言獻策,提供真正科學的建議。由此也可得知和推斷,張之洞實際上對于西方農業科技的了解和認知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對于西方農業發展獲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對于西方近現代農業教育之先進性的理解,都是膚淺和片面的。正是因為只知其然,卻未必深知其所以然,當張之洞在試圖借鑒或模仿時,難免不知從何著手;在制定具體規劃時,就會出現盲目性、隨意性等問題;在實踐和決策過程中,也會因為違背科學規律而變得急功近利。這一知識的局限和認知的膚淺片面,在農務學堂初期籌創的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他曾將西方農業科技傳播簡單地理解為技藝傳承,而不懂其中的科學內涵和規律。他對于美國高等農業教育不甚了解,尤其不知其已相對成熟且頗具效果的“教育、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因此,張之洞初期未能將建設示范農場和創辦農務學堂兩個目標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統籌規劃。
四、客觀之評價
誠然,正如上文所說,張之洞的個人因素絕非湖北農務學堂籌創初期面臨問題及失敗的根本原因。而且,上述問題原因之剖析,也絕非僅現于張之洞一人的身上。張之洞其實只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一批具有類似特點的封建官員的代表,對于他的分析和評價,也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所以,滿清政權的腐朽統治,封建官場的積習弊端,不從根本上變革,僅憑某歷史人物個人的一己之力,想去開創近代農業教育和改良中國傳統農業,是難有大的作為和成效的。因此,不妨借鑒布里爾的觀點和說法并加以充實,將問題的出現歸咎于某一個人,或者將時代的前進都寄希望于某一個人,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對于張之洞在籌創農務學堂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功與過,也應該客觀和全面地看待。
我們應該看到,盡管博而不精,張之洞對西學還是有著“努力掌握”“豐富自己”的積極追求。因此,他也能夠較為認真和虛心地接受一些建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基于認識的深入和相關學識的豐富,他本人也在努力對其實踐和決策進行調試、糾正和完善。雖然農務學堂在籌創初期面臨上述種種問題和困難,而且洋教習布里爾的到來也未在實踐上有大的作為,但布里爾畢竟帶來了一些先進的教育理念和科學技術。作為親歷者,布里爾對當時農務學堂籌創期間出現的諸多問題也有著較為清醒和客觀的認識。布里爾檔案中有史料顯示,他曾通過面談、上書諫言等形式給張之洞提出了不少建議。
從現有史料來看,盡管布里爾后來辭職離開,他的一些建議依然逐步被張之洞接受和采納。例如,鑒于初設學制時間緊張,后來,農務學堂首批學生的實際學習時間由計劃的4年延長到了5年,首批學生是1903 年秋季畢業的①華中農業大學校史編委會:《華中農業大學校史(1898-1998)》,華中農業大學,1998年,第4-5頁。。除了多次力陳學堂附設農場之重要性,布里爾還曾就農場的選址向張之洞提出具體建議:“學堂與農場最好能夠相隔不遠,便于學生參與實踐勞作,免于師生徒費往返之工。以日本札幌為例,那里的農業學校和學堂之間距離不超過0.75 英里。”②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館藏檔案:Gerow D. Brill papers,1884-1924,Box 1在轉聘羅振玉為監督,并對學堂辦學進行整頓之后,張之洞也終于將學堂和農場建設進行重新布局和統一規劃。1902年農務學堂從武昌城內大東門的舊址遷至城北武勝門外多寶庵,附近.設置和建設試驗農場③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頁。。后來建成的農業試驗場,內分農場、林場、桑園、水產場等多部門,面積擴至數千畝,有耕牛數十頭,人工剝麻機、軋花機等農產加工機具和農具一應俱全④徐凱希:《晚清末年湖北農業改良述略》,《中國農史》2004年第1期。。此外,改制后的農務學堂在課程設置和實驗教學等環節上都有了顯著的改進⑤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89頁。,這些變化與布里爾之前的諫言以及張之洞逐步的采納均不無關聯。
正是張之洞虛心學習和努力充實的精神,使得農務學堂逐步擺脫了籌創初期面臨的窘境,進入一個新的較為良性的發展階段,并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和發展效益。湖北農務學堂作為全國較早出現的專門的農業教育機構,逐步培養出了一批農業人才,并在當地乃至全國帶動了講求農學的風氣。農務學堂的畢業生很多后來參與到各地農業學堂的興辦和農場實驗工作,也進一步促進了近代農業知識技術的推廣和傳播。一批近代意義的農業學堂共同為中國近代農業的發展帶來了積極的影響與推動⑥徐凱希:《晚清末年湖北農業改良述略》,《中國農史》2004年第1期。。作為近代農業教育在中國發端的早期代表,湖北農務學堂從籌創到初步發展這兩個階段的命運軌跡,也成為近代中國農業教育在艱難中發端并蹣跚前行的縮影和寫照。
但是,湖北農務學堂畢竟是在一個過渡型的時代中籌創產生的,其籌創者張之洞本人在思想和實踐中體現出的復雜性和矛盾性,也使得農務學堂不可避免地烙印著這些特征。雖然有著一段良性發展階段并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某些做法亦不無借鑒之處,但湖北農務學堂并未能徹底推動中國傳統農業向近現代農業邁進的腳步,也未能從真正意義上開創中國近代農業教育的興起和繁榮。這種由統治階級內部成員所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必然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也難言徹底。湖北農務學堂和其他張之洞的洋務新政一樣,也難當挽救國事衰微、民族危機之重任,在有限范圍產生了有限的影響力之后,難逃失敗之宿命,被歷史前進的洪流逐漸淹沒,或被更加順應歷史潮流的救亡圖存之舉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