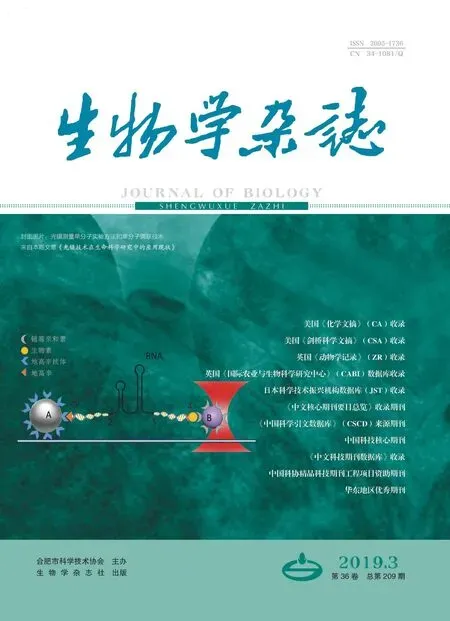北京地區人工引入東方鈴蟾種群的遺傳變異分析
朱國芬, 史 洋, 田恒久, 李 楊, 高福利, 鮑偉東
(1. 北京林業大學 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 北京 100083; 2. 北京市野生動物救護繁育中心, 北京 101399)
種群棲息地的喪失是導致全球范圍內兩棲類動物數量銳減的顯著因素,棲息地喪失導致種群數量減小,從而進一步導致種群近交增加及種群衰退[1]。種群遺傳多樣性作為評估一個種群現有狀態及生存力的指標,在物種保護遺傳學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鈴蟾科(Bombinatoridae)動物屬于易受到威脅的物種[2]。根據江建平等的研究,鈴蟾科5種動物中的3種為受威脅物種[3]。生境喪失、污染以及過度捕捉是造成兩棲類動物數量減少的最主要因素。
鈴蟾屬(Bombina)分布于歐洲的多彩鈴蟾(Bombinavariegata)和紅腹鈴蟾(Bombinabombina)已在分子生物學層面被廣泛研究[1,4],但分布于我國境內的鈴蟾屬物種,包括東方鈴蟾(Bombinaorientalis)、強婚刺鈴蟾(Bombinafortinuptialis)和大蹼鈴蟾(Bombinamaxima)等,在這方面的研究還屬空白。
東方鈴蟾(B.orientalis)為兩棲綱(Amphibian)、無尾目(Anura)、鈴蟾科物種,是我國鈴蟾屬唯一生活在北方的物種。東方鈴蟾主要分布于我國河北、黑龍江、遼寧、吉林、內蒙古、安徽、山東、北京等地,模式產地在山東煙臺,在韓國、俄羅斯、朝鮮等地也有分布[5]。北京地區的東方鈴蟾只分布于香山、臥佛寺櫻桃溝附近,系1927年劉承釗先生由山東煙臺采200余只到北京[5-6],在該地區繁衍至今。
目前,關于東方鈴蟾的研究集中在其生物學特征、繁殖生態、種群狀況及食物組成等方面[7]。東方鈴蟾還具有易在實驗室飼養繁殖及易于實驗操作的特點[8],常被用作實驗動物開展行為、生態、內分泌、組織學等方面的研究[9-10]。現有研究中,基于線粒體基因分子標記的研究均將山東、北京種群作為同一聚類枝[8,11],未對兩種群的遺傳分化做進一步探討。本研究中,我們利用線粒體及微衛星標記,對北京香山及山東煙臺東方鈴蟾種群進行了遺傳多樣性檢測及遺傳結構比較分析,探究該物種在北京地區的獨立進化軌跡。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北京地區樣品取自香山櫻桃溝,山東地區樣品取自山東煙臺昆崳山自然保護區附近,兩個取樣點共獲得樣本55只(北京26只,煙臺29只)。所采集的個體長均在40~45 mm之間,采自北京和山東的樣品分別編號為BY1-BY26、SY14-SY42。采樣時取后肢肌肉用無水乙醇固定,保存于-20℃冰箱中待測。
1.2 方法
1.2.1 DNA提取及線粒體控制區序列擴增
使用血液/細胞/組織基因組提取試劑盒(天根生物科技, 北京)提取總DNA。引物設計參照東方鈴蟾線粒體DNA全序列(GenBank登錄號為AY585338)中D-loop區段,并經由北京睿博興科生物公司進行設計合成,共使用3對引物擴增線粒體D-loop序列:DFLC-1(F:5′-TAGAGATTTGCTATGCTTGT-3′,R: 5′-GGCGTATGGGTTTTTAAAAT-3′)、DFLC-2(F: 5′-GTGTCCAGGATCACCAACTT-3′,R:5′-GGGCTCATCTCAGCATCTTC-3′)和DFLC-3(F: 5′-ATAAACGTAAAATAGAGCC-3′,R: 5′-ATAGATTCACATCCGTCA-3′)。不同引物在線粒體基因組上有不少于100 bp的重疊片段,以提高測序的準確性。
PCR擴增反應總體系為20 μL,其中ExTaq酶(Takara)10 μL,上下游引物各0.8 μL(10 μmol/L),DNA 模板2 μL,DNase/ RNase-Free去離子水補充至20 μL。反應條件如下:95℃預變性4 min;95℃變性40 s,50℃或52℃退火40 s,72℃延伸40 s,40個循環;72℃再延伸7 min。PCR產物經1%瓊脂糖凝膠電泳檢測后,交由北京睿博興科生物技術公司用ABI3730XL測序儀進行雙向測序。
測序結果在Contig Express 軟件中拼接,并輔以人工校對。利用ClustalX 2.1[12]軟件比對序列,去除非目的片段序列以及D-loop區3′端重復序列。
1.2.2 微衛星引物篩選及擴增
基于Guicking[4]、Nürnberger[13]等的研究,使用紅腹鈴蟾、多彩鈴蟾25個微衛星位點的引物對東方鈴蟾進行交叉擴增,經PCR條件優化,共篩選出6對在東方鈴蟾中擴增良好的引物:9H、B14、B13、8A、12F、BV11.7。各正向引物5′端添加熒光標記。
PCR 反應體系同線粒體控制區擴增反應。反應條件為95℃預變性4 min;95℃變性40 s,根據引物不同,48℃~52℃退火30 s,72℃延伸30 s,循環40次;72℃終延伸8 min。
PCR擴增樣品送交北京諾塞基因組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在ABI-PRISM310基因分型儀中進行基因掃描,使用GeneMarker v2.4.0軟件判讀微衛星等位基因條帶大小。
1.2.3 數據分析
在DnaSP5[14]軟件中計算單倍型多樣性h、核苷酸多樣性π、種群間的核苷酸歧異度及兩種群的單倍型數。在MEGA5.2[15]軟件中利用Kimura雙參數法[16]計算各單倍型間的遺傳距離。
在MEGA5.2軟件中基于Kimura雙參數法構建單倍型間的鄰接樹(NJ),以紅腹鈴蟾線粒體控制區序列(GenBank登錄號:EU115993)作外群。在PAUP4.0[17]軟件中基于最大似然法構建系統發生樹,最合適的DNA替代模型基于Akaike信息標準(AIC)由Modeltest3.7[18]和PAUP4.0軟件共同選出,使用Bootstrap法經1000次重復檢驗節點處的置信度。在NETWORK5.0[19]軟件中以Median-joining法構建單倍型間的網絡關系圖。
在Arlequin 3.1[20]軟件中計算種群的遺傳結構。AMOVA分析不同地理種群之間遺傳結構現狀。計算兩種群間Fst及P值,以表明種群間的分化程度。
利用GenAlEx 6.5軟件[21]和FSTAT軟件[22]計算微衛星等位基因數(Na)、有效等位基因數(Ne)、期望雜合度(He)、觀測雜合度(Ho)、基因豐富度(Ar)、Nei氏遺傳距離以及多態信息含量(PIC)。利用Arlequin3.5軟件[20]計算種群間的遺傳分化系數Fst及顯著性。利用Structure軟件[23]中的貝葉斯聚類模型分析和驗證種群間的遺傳分化。
2 結果與分析
2.1 線粒體群體遺傳多樣性
通過對55份東方鈴蟾樣本進行DNA提取、PCR擴增、測序及序列拼接,成功得到40只東方鈴蟾的線粒體D-loop片段序列,其中北京24只,山東16只。序列總長1122 bp,共檢測到堿基多態性位點22個,其中轉換18次,顛換4次,無增添、缺失,轉換顛換比為4.5。在22個多態位點中包含單態位點16個,簡約信息位點6個,這些多態位點共定義13種單倍型,其中兩種群共享單倍型(BJSD)1種,北京地區特有單倍型2種(BJ1-BJ2),山東地區特有單倍型10種(SD1-SD10)。
Dnasp 5.2軟件計算東方鈴蟾總體單倍型多樣性指數h=0.794,總體核苷酸多樣性指數π=0.0026,總體核苷酸差異數k=2.909,兩種群間的核苷酸歧異度為0.295%。北京種群的遺傳多樣性指數明顯低于山東種群(表1)。

表1 東方鈴蟾種群線粒體控制區DNA部分序列的遺傳多樣性參數
經MEGA 5.2軟件計算,13種單倍型間的遺傳距離在0.001到0.011之間,平均為0.004,表明兩地種群單倍型間遺傳差異較小。
2.2 線粒體基因標記的種群遺傳分化
AMOVA分析顯示變異有15.52%發生在種群間,84.48%發生在種群內部(P<0.01)。兩種群的Fst=0.155 (P<0.01)。
按照AIC標準得出最適合的核苷酸替代模型為HKY模型,基于線粒體D-loop區部分序列的NJ樹和ML樹均顯示北京、山東兩種群間的單倍型尚未形成顯著的譜系結構(圖1),兩種群間的單倍型交叉分布,且多個分支節點處的置信度較低。

a: Neighbor Joining Tree;b: Maximum Likelihood Tree. 節點處置信度由1000次Bootstrap計算,僅顯示大于50%的部分
圖1 基于線粒體D-loop序列片段構建的系統發生樹
Figure 1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mtDNA control region haplotypes
Network圖顯示單倍型SD2和SD7周圍存在較多的衍生單倍型,SD5和BJSD次之(圖2)。單倍型BJ1頻率最大,共享單倍型BJSD次之,且該單倍型個體主要來自北京種群。

圖中圓圈大小表示單倍型的頻率,圓圈內的不同圖案表明在不同種群中的分布,斜線表示單倍型間經歷的突變;無缺失單倍型
圖2 基于線粒體D-loop片段的單倍型網絡圖
Figure 2 Network based on mtDNA D-loop haplotypes
2.3 基于微衛星基因的種群遺傳多樣性及種群分化
篩選出的6對微衛星引物擴增特異性強、擴增效率高,基因掃描結果顯示引物多態性好,峰圖整齊,無影子峰等。54只個體在6個微衛星位點成功擴增,共檢測出64個等位基因,其中北京種群特有等位基因8個,山東種群特有等位基因33個,兩地種群共享等位基因23個。兩種群的微衛星種群遺傳多樣性差異較大,北京、山東種群平均等位基因數(Na)分別為4.833和9.667,有效等位基因數(Ne)分別為2.886和6.439(表2)。

表2 微衛星標記的兩東方鈴蟾種群遺傳多樣性
Arlequin軟件計算顯示兩種群間Fst=0.132 (P<0.01),表明基于微衛星標記,兩種群存在中等程度的遺傳分化。當k=2時,log-likelihood平均值較高(k=1時,ln likelihood=-1134.4;k=2時,ln likelihood=-984.8),因此Structure軟件支持將54只東方鈴蟾個體劃為2個亞種群(遺傳基因簇)(圖3)。

圖3 基于微衛星數據的兩地東方鈴蟾種群的Structure聚類分析
3 討論
3.1 微衛星引物的擴增
在蛙類動物研究中,微衛星標記作為線粒體控制區標記的補充,能夠彌補研究樣本量較少、線粒體標記無法揭示相應種群的遺傳結構及其變異水平的缺陷[24]。但蛙類動物的微衛星引物較難在種間通用[25],Stuckas等[26]根據紅腹鈴蟾設計了8對微衛星引物,這些引物無一在其他無尾目物種中成功擴增,僅部分在同屬物種東方鈴蟾和多彩鈴蟾中擴增成功[26],且同一引物在不同物種中的多態性也并不一致,在對目標物種進行遺傳多樣分析時,仍需進行篩選。同樣在該研究中,新設計的40對引物僅有8對能在紅腹鈴蟾中穩定擴增出單一條帶。因此,無尾目動物研究中可穩定應用的微衛星引物數量不多,導致了種群遺傳學研究存在一定困難。本實驗篩選出的6對微衛星引物在東方鈴蟾中能都穩定擴增,且多態性良好,能夠用于后續東方鈴蟾的深入研究。
3.2 北京地區東方鈴蟾群體遺傳多樣性
北京地區東方鈴蟾種群線粒體單倍型多樣性與核苷酸多樣性分別為h=0.489和π=0.001 81,相較于對德國、波蘭及烏克蘭的13個紅腹鈴蟾種群線粒體的研究[1],平均單倍型多樣性h=0.48(h為0.30~0.80),核苷酸多樣性π=0.0036(π=0.0014~0.0076),北京地區東方鈴蟾種群線粒體遺傳多樣性尚處于中等水平。基于微衛星標記的北京地區東方鈴蟾種群的觀測雜合度Ho為0.468,期望雜合度He為0.548,與紅腹鈴蟾 (Ho為0.44~0.74,He為0.59~0.78)[1]及 Guicking等[4]研究中的多彩鈴蟾(Ho為0.38~0.70,He為0.37~0.59)相比,本研究中北京地區的東方鈴蟾種群也表現出中等的遺傳多樣性。山東地區線粒體單倍型多樣性h=0.950,核苷酸多樣性π=0.0038,微衛星觀測雜合度Ho為0.631,期望雜合度He為0.701,均表現出較高水平。
綜合上述結果,北京地區東方鈴蟾種群遺傳多樣性稍低于山東種群,推測是由于奠基者效應導致,但總體處于中等水平。應警惕的是,由于種群數量較少,當種群數量減少時,遺傳漂變易導致稀有等位基因丟失,進一步引起種群近交。
3.3 種群間的系統發生關系
基于線粒體基因的13種單倍型構建的系統發生NJ樹以及ML無根樹均未顯示出明顯的譜系結構。但遺傳分化系數存在差異(Fst=0.155,P<0.01),可能是由于北京種群單倍型較少所致。與此稍顯不同的是基于微衛星標記的種群遺傳分化結果,根據Structure軟件中的貝葉斯分析,傾向于將54只東方鈴蟾個體分為兩個遺傳聚類簇,基于微衛星標記的Fst=0.1325(P<0.01),也說明兩個種群之間已經出現了遺傳分化,形成不同的遺傳聚類。
北京地區東方鈴蟾種群遺傳多樣性雖然低于山東地區,但仍處于正常水平。兩種群間已形成了不同的遺傳結構,且兩地空間距離甚遠,兩種群間不存在基因交流,我們建議將北京種群作為單獨的管理單元。目前,北京地區種群無需以提高種群遺傳多樣性為目的再次引種,因為盲目異地引種可能會對本地種群遺傳結構造成影響,不利于特有基因型的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