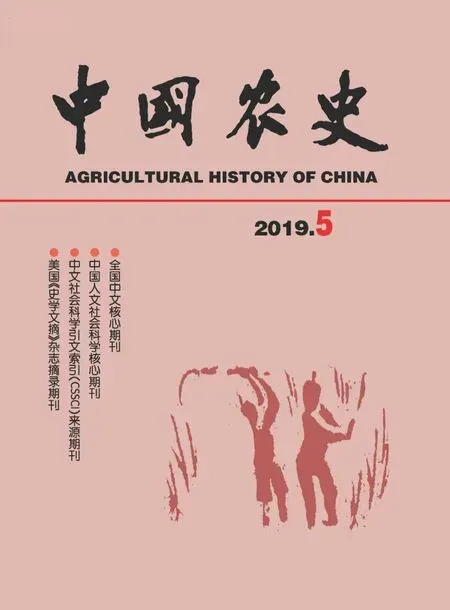氾勝之其人其書及其影響研究
王寶卿 馬 剛
(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xué)齊民書院,山東青島 266109)
西漢后期的氾勝之因其所著農(nóng)書而聞名后世,但是該書的原名究竟是什么已無從考證。《漢書·藝文志》稱之為《氾勝之十八篇》。東漢末年的經(jīng)學(xué)大師鄭玄在《周禮·地官·草人》注中解釋稱“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shù)也”,隨后賈公彥疏評:“漢時農(nóng)書有數(shù)家,氾勝為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shù)也”。隋唐時的經(jīng)學(xué)家陸德明在《爾雅釋文》中稱之為《氾勝之種植書》,李善在《文選注》中則稱其為《氾勝之田農(nóng)書》。北宋所纂類書《太平御覽》“經(jīng)史圖書綱目”中也有《氾勝之書》,但不知其時該書是否為完整原書。《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僅錄著“《氾勝之書》二卷”,唐末韓鄂撰《四時纂要》引用氾書時直接稱“氾勝書”①據(jù)清道光十一年刊刻的《敦煌縣志·人物志·鄉(xiāng)賢》記漢初有“氾騰”:“惠帝時舉孝廉,為郎中屬”;清劉藻撰《曹州府志·職官》列有“氾宮”,是三國時人;氾勝之兒子單字名輯,等等,故“之”是否為其名亦存疑,但本文按習(xí)慣仍稱其為“氾勝之”。,鄭樵《通志》農(nóng)家書目記有“范勝之書二卷,漢議郎范勝之撰”。總之,現(xiàn)在通稱的《氾勝之書》這個書名似乎也是后人給起的。
由于該書價值高,聲譽大,被當時和后世的學(xué)者不斷引用,特別是在賈思勰的《齊民要術(shù)》和宋人所輯的書中,還保留了大量的語句。原書雖然遺失,但是,從這些極不完整的材料來看,內(nèi)容的確很豐富,涉及的范圍也極為廣泛,對氣候、土壤、施肥、選種、下種、中耕、防旱、防蟲、收獲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各個方面,都提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見解,是我國古代寶貴的農(nóng)業(yè)科學(xué)名著之一②石聲漢:《氾勝之書今譯》科學(xué)出版社,1956年;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中華書局,1957年(新二版,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0年);中國科學(xué)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著:《山東古代三大農(nóng)學(xué)家》,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
因此,探索《氾勝之書》(下文簡稱“氾書”)的寫作背景以及“氾勝之術(shù)”的內(nèi)容,對于深入了解我國農(nóng)業(yè)科技的發(fā)展歷程具有重大意義,對《氾勝之書》的輯佚校證或許也有啟示。
一、氾勝之其人
關(guān)于氾勝之的生平,流傳下來的很少。按《廣韻》解釋“氾”:“國名,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于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敦煌太守,子孫因家焉”。據(jù)傳,“凡”姓為周公子凡伯之后,因躲避戰(zhàn)亂遷于氾水,故改姓氾,有燉煌和濟北兩支望族。氾水,據(jù)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濟水》載“菏水東北出于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氾水又東,合于菏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于定陶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③陳橋驛:《水經(jīng)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198-199頁。。氾水是秦漢時濟水的一個支流,在今天的山東曹縣北境,定陶縣南。因為漢代實行地方長吏任職籍貫回避制度,而其子氾輯曾任敦煌太守,所以史學(xué)家多據(jù)此認為氾勝之是山東曹縣人。
濟陰郡是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登基不久置建的。該地在周初是周武王封其弟為曹伯所建的曹國,都陶丘,南臨魯、沛,該地曾經(jīng)有“天下之中,諸侯四通”之說,是范蠡曾經(jīng)看中而移居終老之地④《史記·貨值列傳》:“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chǎn)積居。……后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yè)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后來成了秦相魏冉的封邑(《史記·穰侯列傳》),劉邦即帝位于陶,后又封多位“王”于定陶,故西漢的定陶所在地濟陰郡,雖只轄九縣,卻有人口一百三十八萬,以密度而言,居全國之首⑤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5》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552頁。。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時代,當?shù)氐霓r(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應(yīng)有突出之處,而氾勝之若早年生活于此環(huán)境,則熟悉以前先進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驗、技術(shù),并且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量化和經(jīng)濟算計,當是比較自然之事。
據(jù)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并引劉向《別錄》等記述,可知氾勝之在漢成帝(前33-前7)時曾做過“議郎”,并在三輔(今西安附近)教過農(nóng)民種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當時喜歡農(nóng)學(xué)的人尊他為師,后來轉(zhuǎn)任“御史”⑥《漢書·藝文志》:“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御史大夫位為上卿,歷任皆有名錄,并無氾勝之;還有御史中丞,掌管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nèi)領(lǐng)侍御史15 名,受公卿奏事。氾勝之或任侍御史,史書不詳載。《晉書·食貨志》亦云:“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guān)中遂穰。”因此,氾勝之生平主要活動應(yīng)該在公元前一世紀后半葉,知農(nóng)事農(nóng),在西安附近推廣種植小麥,使關(guān)中地區(qū)的糧食供給獲得保障。
二、《氾勝之書》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
(一)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工具和生產(chǎn)技術(shù)的長足發(fā)展
鐵農(nóng)具出現(xiàn)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其應(yīng)用的普及推廣在秦漢①王寶卿:《鐵農(nóng)具的產(chǎn)生、發(fā)展及其影響研究》,《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4年第9期。。在出土的戰(zhàn)國鐵器中,生產(chǎn)工具占有很大比重,而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鐵農(nóng)具又在生產(chǎn)工具中占主要部分。西漢中期實行冶鐵業(yè)官營,冶煉技術(shù)的提高和冶鐵量大增是毋庸置疑的,政府也致力于農(nóng)具的改革,并成立指導(dǎo)新農(nóng)具生產(chǎn)與推廣的機構(gòu)。漢代的《鹽鐵論》多次強調(diào)鐵器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重要性②如《鹽鐵論·禁耕》:“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nóng)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又如《鹽鐵論·水旱》:“農(nóng),天下之大業(yè)也;鐵器,民之大用也”等。。西漢中期趙過推行耦犁,鐵犁牛耕在我國傳統(tǒng)農(nóng)具與動力中的主導(dǎo)地位,就是此時確立的。鐵制農(nóng)具取代木石農(nóng)具顯然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史上的一次革命,生產(chǎn)工具的種類和形制也都更加豐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進入新階段。
另一重要技術(shù)進步是武帝時太初歷的編制并頒布實施。盡管該歷法在朔望月和回歸年日數(shù)這兩個基本數(shù)據(jù)上以現(xiàn)代標準來看存在誤差較大的缺點,但是太初歷在編制之初,匯集了官方和民間二十多位天文工作者,社會影響大;尤其是在技術(shù)上,太初歷以孟春正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解決了秦及漢初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歷法與民俗相矛盾的問題;其次修正了顓頊歷行用百余年積累的誤差,使朔望等天象與歷相符,并明確規(guī)定一回歸年由二十四節(jié)氣組成,同時規(guī)定以無中氣的月份為閏月,避免了中氣與月名不能對應(yīng)的缺點。調(diào)整了年度首月并且整合了二十四節(jié)氣的太初歷,可以直接、更好地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③崔振華、李東生:《中國古代歷法》,新華出版社,1993年。。
同時,先民在長期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實踐中,對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的基礎(chǔ)項目:土、肥、水和田間管理,都有了一定的認識和研究。土壤是地球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基礎(chǔ),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先民就對土壤學(xué)有了較系統(tǒng)的研究成果④辛樹幟:《禹貢新解》,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0年,第127-140頁。,禹貢時代,人們對土壤已有較深刻的認識。盡管與現(xiàn)代土壤分類學(xué)的細致、科學(xué)和嚴謹性不能同日而語,但是,《尚書·禹貢》中用“白、黑、赤、青、黃”等土壤顏色標識土壤類型的方法沿用至今;用“壤、墳、埴、壚、涂泥”等對土壤的質(zhì)地或地形加以區(qū)分,表明當時對土壤已經(jīng)有了認真的調(diào)查研究,掌握了較豐富的土壤學(xué)知識;對于不同地區(qū)草木特征的描述,顯示當時對土壤和植物類型、氣候之間的關(guān)系也有了一定認識。《管子·地員》和《呂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審時”等篇章,對土壤與作物的關(guān)系、耕耘的功用、六谷的審時稼穡、土壤調(diào)和問題等進行了樸素的辨析,是早期的理論探討⑤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第687-701頁。。
簡言之,先秦時期,對于土壤的質(zhì)地、構(gòu)造、顏色、燥濕等性能已有初步的研究,對于施肥、中耕、間苗等技術(shù),也有一定的認識。但是,這些知識一般零星散見于不同資料中,篇幅也有限,對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諸要素的敘述往往比較簡略,其間的聯(lián)系也說明很少,大多停留在個別問題的具體處理上,沒有一種綜合的、系統(tǒng)的農(nóng)學(xué)思想敘述。隨著時代的推進,耕作制度逐漸由古代原始方式過渡到封建農(nóng)業(yè)階段,到了西漢前期,北方的耕作制度,已經(jīng)具備了精耕細作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技術(shù)要點。
(二)糧食增產(chǎn)與關(guān)中地區(qū)種植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提高,帶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產(chǎn)量的增加。戰(zhàn)國末期的糧食畝產(chǎn)約216市斤,而秦漢時平均畝產(chǎn)則提高到264 市斤⑥王寶卿:《我國歷代糧食畝產(chǎn)量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5 年第3 期;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chǎn)研究》(增訂再版),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2016年。。《尚書·益稷》載“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堯舜時期人們開始以植物種子作為主要食物,但據(jù)說那時的主要作物是稷。到西周時期,在多樣化種植的基礎(chǔ)上,糧食作物大概一直以黍稷為主。而戰(zhàn)國至西漢初,主要糧食生產(chǎn)已由黍稷變化為粟菽。
早期麥的種植情況不明,但直到秦漢,麥的種植應(yīng)不如后世多。據(jù)《漢書·食貨志》,董仲舒上書武帝:“《春秋》它谷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今關(guān)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詔大司農(nóng),使關(guān)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后時。”或許因為《春秋》是魯國的史記,魯國地處東部平原,有大量低濕地區(qū),河流縱橫,水源便利,可以保證麥的耕作需水,種麥較多,故重點記載。而董子所述,至武帝時,關(guān)中地區(qū)很少種麥也應(yīng)是實情。在漢帝國尊儒以后,尤其是水利灌溉建設(shè)長足發(fā)展的情況下,官員如氾勝之在民間大力推廣種麥就有良好的自然和社會政治基礎(chǔ),甚至就此奠定后世北麥南稻的糧食種植格局。
(三)土地制度不斷調(diào)整解放生產(chǎn)力
先秦文獻和出土的秦簡都說明戰(zhàn)國至秦統(tǒng)一,授田制普遍實行,也是各國尤其是秦的重農(nóng)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除了對貴族和功臣的賞賜外,國家還把掌握的大量土地,按戶計口地分給農(nóng)民耕種,得地的農(nóng)民按比例繳納賦稅后,剩余歸農(nóng)民自己所有。這樣極大地提高了自由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
漢承秦制。漢文帝時(前179-前163年在位),自耕農(nóng)人均授田約為60畝左右,到了漢平帝時期(公元1-6年在位),人均授田已下降到13畝左右。國家授田數(shù)量逐漸減少,區(qū)田法這種精耕細作勞動密集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好像正是為以自耕農(nóng)為主體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設(shè)計的。
三、“氾勝之術(shù)”與《氾勝之書》的主要內(nèi)容
《氾勝之書》的全貌因原書遺失而難以確知,但是,結(jié)合該書創(chuàng)作的時代背景,并根據(jù)其書的聲譽和零星記載以及輯佚的內(nèi)容仍可做出大致的推測了解。
(一)“土化之法”與“氾勝之術(shù)”
涉及“氾書”內(nèi)容的較早評論是鄭玄對《周禮·草人》作的注:“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shù)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所謂“土化之法”,用現(xiàn)代話講,就是改良土壤以使其有利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方法。要想改良土壤,就需要首先認識土壤,了解其特性和適宜種植的作物,故緊接著用“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來解釋。這里的“物”有類別、辨物之義,是動詞;“物地”即考察分辨土地類型;“占”,估計、測算;整句對“土化之法”進行簡單解釋,就是通過考察、分辨土地類型,判斷其形態(tài)、顏色,根據(jù)土地資源情況安排合適的作物種植,比如黃白地適合種植禾之類。
這與“草人”的職責(zé)是相符的①《周禮·地官司徒·草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骍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強?用蕡,輕爂用犬。”。夏緯瑛結(jié)合《管子·地員》篇探究“草”字的用法、意義和“草人”這一名稱,指出“草”是“草木”的省文,相當于現(xiàn)代所說的“植物”;“草人”相當于現(xiàn)代所說的“植物學(xué)家”,負責(zé)考察土地的性質(zhì),因地制宜地選擇合適的作物進行栽培,并且根據(jù)實際情況和條件,采用其它措施進行土壤改良,以達到農(nóng)作物增產(chǎn)的目的,當時稱之為“土化之法”②夏緯瑛:《〈周禮〉書中有關(guān)農(nóng)業(yè)條文的解釋》,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79年,第38-42頁。。“氾勝之術(shù)”應(yīng)對此有所繼承和發(fā)展。
《周禮》中關(guān)于“土化之法”的解說非常簡略,包括“糞種”,總共幾十字,列舉了一些土壤類型和用糞種類。而“氾書”的解釋則要詳細、豐富的多,僅從《齊民要術(shù)·種谷第三》中由該書的一處引文可窺一斑:
《氾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
“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
“又取馬骨銼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飯狀。常天旱燥時溲之,立干;薄布數(shù)撓,令易干。明日復(fù)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fù)濕。至可種時,以余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①繆啟愉、繆桂龍:《齊民要術(shù)譯注》,齊魯書社,2009年,第75-76頁。
此處引文在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中,被分別放在“五、禾”和“三、溲種法”兩部分。“種禾無期,因地為時”,氾勝之首先指出種谷子的時日要根據(jù)所耕種土地的實際情況而定;三月,當一定的物候和雨水條件出現(xiàn)時,可以在高地強土上種谷子。“強土”是指耕地的質(zhì)地,據(jù)萬國鼎解釋,古人說的“強土”大體相當于現(xiàn)代土壤學(xué)上所說的重土,但意義更廣泛些,還指土壤的結(jié)構(gòu)堅實。其它引文顯示,氾勝之在講耕田時還曾指出“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的原則,就是把堅實的強土處理的松散些,使其結(jié)構(gòu)便于作物的根系發(fā)展,而對過于松散的弱土則適當?shù)匕阉幚淼木o密些,使其結(jié)構(gòu)有利于支撐作物和保持土壤水養(yǎng)。
后兩段內(nèi)容也常被人稱為早期“溲種法”的典型例證。里面不僅有詳細的“溲種”處理過程,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同時還指出,采用不同材料和方法處理種子,會產(chǎn)生不同的生產(chǎn)保收效果。對于馬骨、蠶矢之類的應(yīng)用,現(xiàn)在一般認為就是為芽苗增肥,而附子這種具有猛烈毒性和外用殺菌功能自然材料的使用,對螻蛄、蠐螬之類的地下害蟲明顯可以起到防治作用。雪汁是“五谷之精”的說法好像有點玄奧,但據(jù)現(xiàn)代研究,雪水所含重水比普通雨水少四分之三,而重水會抑制生物的生長,因此,雪水對生物的生長有促進作用。雖然古人不明其中的現(xiàn)代科學(xué)道理,但是他們已經(jīng)從經(jīng)驗中認識到雪水的特殊性,并用當時人們可理解的方式進行解釋。
“氾書”里的“溲種法”是對“糞種”方法進行發(fā)展或變通的具體措施之一,而“氾勝之術(shù)”很可能在用糞改良土壤肥力方面有較全面的總結(jié)和先進獨到之處。《周禮·草人》中對“糞種”沒有詳細解釋,只是列舉說“骍剛用牛,赤緹用羊”等等,鄭玄作注說“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這與《氾勝之書》中的“溲種”法基本一致。我們知道,對于“糞”,人類有種天然的反感情緒,甚至到近現(xiàn)代,西方仍有人抨擊種地使用人畜糞便;《吳越春秋》中也記有一例“糞種”遭人厭的故事:“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fù)生秋霜,惡之,故不食’”。筆者在幼年時也曾被教導(dǎo)不要摘食秋天路邊的生瓜果。故可以推測,我國也必然經(jīng)歷了很長時間的研究和推廣,才較普遍地在農(nóng)田耕作中使用糞肥。甚至氾勝之在推廣時也稱“神農(nóng)復(fù)加之骨汁糞汁溲種”、“伊尹作為區(qū)田,教民糞種”,找古代圣賢為自己背書。
氾勝之非常重視用糞,并且對如何使用也非常講究。“凡耕之本,在于趨時、和土,務(wù)糞、澤,早鋤、早獲”,氾勝之認為耕種的六項基本要點中,專門強調(diào)用糞。對每種作物的栽培,氾勝之都有具體的用糞指導(dǎo):“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責(zé)麥種以酢漿并蠶矢……”、“區(qū)種大豆法……取美糞一升,合坎中土攪和……一畝用種二升,用糞十二石八斗”、“春草生、布糞田”、“種麻……以蠶矢糞之,樹三升;無蠶矢,以溷中熟糞糞之亦善,樹一升”、“區(qū)種瓜……一科用一石糞,糞與土合和,令相半”、“種瓠……蠶矢一斗,與土糞合,澆之……用蠶沙與土相和,令中半,著坑中,足攝令堅……復(fù)以前糞覆之”、“種芋……取區(qū)上濕土與糞和之,內(nèi)區(qū)中萁上,令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又種芋法,宜擇肥緩?fù)两帲腿峒S之”等等。
“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氾勝之明確指出可以用糞把不好的土地改造為良田。“薄田不能糞者”,對于肥力瘠薄的土地,即使不能施肥,也可種谷:“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這與其它用糞的例子相比,數(shù)量大減。在桑蠶業(yè)極受重視且較普及的漢代,蠶糞應(yīng)是農(nóng)家易獲之物,但數(shù)量可能不足以用來大量“糞”地。接著一“又”字引出用各種材料取汁溲種的方法,明顯是對“薄田不能糞者”的各種權(quán)變措施。土地肥沃,作物生長壯實,對病蟲害的抵抗力往往會強一些。貧瘠的土地上生長的作物則一般經(jīng)不起病蟲害的折騰,而這種取各種材料汁溲種的方法,既避免了大量糞料缺乏的問題,又通過種肥保證作物的早期營養(yǎng),再輔以其它手段增加出苗率和抗病蟲害的能力以保苗,為日后的收成打好基礎(chǔ)。在主要“靠天吃飯”的“高地強土”上種禾,這樣做可以說非常劃算、實用。
按照常識,為人稱道的新書推介的方法必非大眾所熟悉或常用的方法,但往往是易于實行的好方法,古今皆然。“氾勝之術(shù)”是通過多種手段改良耕地的“土化之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應(yīng)該非常豐富,是該書的一大亮點。可惜原書失傳,否則,人們或許能從該書了解更多西漢時期有關(guān)土壤學(xué)以及用糞、制肥等方面的知識和技巧。
(二)精耕細作區(qū)田法
區(qū)田法(或稱區(qū)種法)大概是氾勝之發(fā)明的最引人注意,同時也可能是最有爭議性的內(nèi)容。如萬國鼎所分析,雖然氾勝之自稱此法起自伊尹,但是,二人生活時代相距1600余年,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無論是甲骨文還是先秦以及西漢中葉的文獻書籍均從未提到過這種方法,令人生疑;而且,很難讓人相信,早在商代初期就已經(jīng)有了區(qū)田法所代表的先進農(nóng)田豐產(chǎn)技術(shù)。因此,氾勝之很可能是假托古人之名,為了讓自己發(fā)明的方法更好地推廣。
這種精耕細作的生產(chǎn)方式所宣稱的豐產(chǎn)目標既是其最吸引人之處,也是歷來爭議的焦點。質(zhì)疑和支持其高產(chǎn)說最有代表性的研究當屬萬國鼎的“區(qū)田法的研究”①萬國鼎:《區(qū)田法的研究》,載《萬國鼎文集》,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5年。和吳慧的“區(qū)田產(chǎn)量淺議”②吳慧:《區(qū)田產(chǎn)量淺議》,載氏著《中國歷代糧食畝產(chǎn)研究》(增訂再版),第257-289頁。。萬先生勾稽史冊,遠迄北魏劉仁之,近至建國后1956 年張履鵬,根據(jù)不同時代的27 例區(qū)田實驗所得畝產(chǎn)數(shù)據(jù),并結(jié)合蘇聯(lián)小麥先進生產(chǎn)者的實驗產(chǎn)量判斷,氾勝之所說區(qū)田法畝產(chǎn)百石的高額豐產(chǎn)目標是虛高的;而吳先生則在對漢代相關(guān)史料以及度量衡單位換算研究的基礎(chǔ)上,通過細致的研究、計算,堅稱氾氏區(qū)田畝產(chǎn)百石的說法是確實可信的。但兩位學(xué)者在區(qū)田法所代表的先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和該方法畝產(chǎn)爭議產(chǎn)生的原因方面意見是一致的。簡言之,兩位先生都贊成區(qū)田法技術(shù)先進,但小規(guī)模區(qū)田試驗和大田實踐的產(chǎn)量是有差異的。因此,下面主要探討區(qū)田法所蘊含的農(nóng)業(yè)科技成分。
區(qū)田法曾長期作為北方旱作區(qū)抗旱保墑的典范耕作方式而加以研究、推廣,直至現(xiàn)代仍有學(xué)者強調(diào)區(qū)田法實驗、推廣的地域適應(yīng)性問題③楊庭碩:《中國農(nóng)史研究必須正視環(huán)境差異——對漢代關(guān)中“區(qū)田法”的再認識》,《中國農(nóng)史》2016年第1期。。盡管該法確實可能首創(chuàng)并實行于漢代的關(guān)中地區(qū),其具體操作特別適合關(guān)中地區(qū)的環(huán)境、氣候特點,但是,其整套的耕作技術(shù)所包含的農(nóng)業(yè)耕作技術(shù)原理才是其精華所在。結(jié)合前人的研究,現(xiàn)簡要概括如下:
首先,整地區(qū)種,量人力盡地力。氾勝之設(shè)計的區(qū)田法屬于精耕細作、勞動密集型生產(chǎn)方法,有非常細致的整地方式和要求,具體到作區(qū)的方法、尺寸、數(shù)量和掘土的深度等。按照布置方式可分為兩類,石聲漢簡稱之為帶狀區(qū)種法和小方形區(qū)種法,石、萬兩位先生都繪有精美的圖示,此不贅述。區(qū)田法不僅設(shè)計細致,也充分考慮了人力成本問題,“區(qū)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qū)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上農(nóng)夫區(qū)……一日作千區(qū)。……中農(nóng)夫區(qū)……一日作三百區(qū)。下農(nóng)夫區(qū)……一日作二百區(qū)”,挖土作區(qū)是繁重的體力活(現(xiàn)代專業(yè)的農(nóng)業(yè)機械則可以有效減輕人力勞動的繁重程度),土地有肥瘠,人力有強弱,而氾氏的區(qū)田法在設(shè)計之初就注意到了量人力、盡地力的原則,把荒地逐漸培育成“熟地”,思慮可謂實際、周全。
其次,糞田美地,有效施肥。“區(qū)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良田也”,上文已經(jīng)探討了“氾勝之術(shù)”以化土為美的土地改良方法見長,而“溲種”“區(qū)種”恰是精準施肥的典范,不僅根據(jù)土地、作物選擇糞肥,而且只在區(qū)中施肥,保證作物根系的吸收,做到有效施肥。
再次,合理播種,行列有距。根據(jù)區(qū)種法的田間布置方式,播種的疏密和植株的排列都有細致的安排,做到“等距、全苗”,不同作物密植情況不同,保證每株作物都有適當?shù)纳L空間。如:“凡區(qū)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行容五十二株。一畝凡九萬三千五百五十株”;“凡區(qū)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行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qū)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于禾”等。盡管沒有現(xiàn)代科學(xué)知識,但氾氏區(qū)田法與現(xiàn)代植物生理學(xué)理論是相符的。如果說在《呂氏春秋》中“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jù)之容手”是僅從勞動者耕作方便的角度來處理植物株距的話,那么,在區(qū)間的空地足以滿足勞動者田間活動需要的情況下,區(qū)田法在區(qū)內(nèi)的植株布置則顯然是為了有利于植物通風(fēng)和光照的需求。另外,考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畎畝法”、漢武帝時期趙過推行的“代田法”,再到西漢后期氾勝之發(fā)明的“區(qū)田法”,可以發(fā)現(xiàn),在作物種植行列的安排上有明顯的前后相承并發(fā)展的關(guān)系。區(qū)田法的播種安排,更好地把握了播種數(shù)量、植物日光吸收利用率和產(chǎn)量之間的關(guān)系。
第四,適當澆水,護苗保墑。后世區(qū)田法研究者一般會根據(jù)氾勝之“湯有旱災(zāi),伊尹作為區(qū)田”之說,重點挖掘其護苗保墑功能對旱作區(qū)的重要價值。熊帝兵比較了氾氏的“區(qū)田積穰”方法和現(xiàn)代中國工程院院士束懷瑞在山東多地試驗的束氏“穴貯肥水”技術(shù),指出其技術(shù)相似性,只是前者可能主要以實踐經(jīng)驗為依據(jù),而后者則以科學(xué)實驗和測量數(shù)據(jù)為依據(jù),但二者的目的都是實現(xiàn)精準供水、精準給肥,既防止水、肥不足而導(dǎo)致作物發(fā)育不良甚至枯萎致死,又避免水、養(yǎng)過量而造成的作物營養(yǎng)失調(diào)或燒苗現(xiàn)象①熊帝兵:《關(guān)于〈氾勝之書〉“積穰于溝間”的釋讀》,《中國農(nóng)史》2017年第5期。。除了蓄水保墑的設(shè)計外,氾勝之也強調(diào)旱地人為灌溉的重要性,“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qū)種,天旱常溉之”,同時講究用水的時機和技巧:“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責(zé)麥種以酢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區(qū)種瓜……以三斗瓦翁埋著科中央,令甕口上與地平。盛水甕中,令滿。種瓜,翁四面各一子。以瓦蓋甕口。水或減,輒增,常令水滿”,種芋則在區(qū)內(nèi)放置豆萁,然后用濕土和糞踩實、澆水,利用豆萁增加蓄水等等,以盡可能少的人力,有效保證作物生長所需水分。
第五,田間管理,因時制宜。氾勝之對田間管理提出了許多竅門,尤為難得的是他的田間管理措施是系統(tǒng)的,根據(jù)時令和作物的生長規(guī)律進行的,既有效去除雜草,又盡可能護苗、保苗,增強地力,促進作物生長、結(jié)實,因此他要求耕地、鋤草、收獲都要把握時機,適時耕鋤,及時收獲。荒地作區(qū),田間雜草自生,不除則必然與栽培作物分爭水養(yǎng)和陽光,影響作物生長和產(chǎn)量。如“麥生根成,鋤區(qū)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春凍解,棘柴律之,突絕去其枯葉。區(qū)間草生鋤之”;“豆生布葉,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等等。除了及時去除雜草,對作物的生長結(jié)實也給予持續(xù)的關(guān)注:“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搜去其露,日出乃止”,據(jù)說黍在沒有抽穗以前,如果被水灌入苗心,花序受傷就不能結(jié)實,因此,當適值其孕穗而又露水重時,讓兩人相向拉條長索,刮去苗心上的露水,以使每株都不會因為水傷苗心而影響結(jié)實。
由現(xiàn)存資料看,區(qū)田法是為以單戶家庭為生產(chǎn)單位所設(shè)計的精耕細作耕作方法,盡管有高產(chǎn)的前景,但是,在鐵犁、牛耕已漸普及的情況下,要求需耗費大量人力的挖土開區(qū)作業(yè),在古代大面積糧食生產(chǎn)中推廣可能有一定的難度,這點可由河南省北部內(nèi)黃縣三楊莊農(nóng)業(yè)村落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佐證,該地是兩漢之際新莽時期的黃泛區(qū)開荒地,氣候條件與關(guān)中平原類似,但多處獨立庭院周圍的大面積農(nóng)田,展現(xiàn)的都是壟作遺跡,而非區(qū)田生產(chǎn)方式②劉海旺、張履鵬:《國內(nèi)首次發(fā)現(xiàn)漢代村落遺址簡介》,《古今農(nóng)業(yè)》2008年第3期;王勇:《內(nèi)黃三楊莊漢代遺址農(nóng)耕環(huán)境論析》,《中國農(nóng)史》2014年第6期。。但是,氾氏區(qū)田法精心安排、利用人為、地生、天養(yǎng)三大因素的創(chuàng)舉仍將繼續(xù)為后世農(nóng)業(yè)工作者提供啟示。
(三)神農(nóng)之教和陶朱遺風(fēng)
“神農(nóng)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氾書”還以“神農(nóng)之教”來強調(diào)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重要性。戰(zhàn)國文獻對神農(nóng)的描述,都根植于他對農(nóng)耕技術(shù)的發(fā)明,神農(nóng)在被神化的同時,作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和農(nóng)業(yè)文明開端的象征被先民崇拜①雷欣翰:《早期神農(nóng)傳說及其文化意涵考論》,《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第4期。。許慎的《說文解字·示部》解釋“神”為“引出萬物者也,從示、申”,故“神農(nóng)”本意為“引出農(nóng)耕”或“創(chuàng)始農(nóng)業(yè)”,這與后世對“神農(nóng)”的描述和尊崇內(nèi)容正相一致,如《周易·系辭下》載:“神農(nóng)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nóng)以制作耒耜等農(nóng)具教人耕種和聚市易貨,由此肇始了早期的中國農(nóng)耕文明,這一變化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神農(nóng)不只是一個在技術(shù)上教導(dǎo)百姓的老師,也是開創(chuàng)以農(nóng)耕為基礎(chǔ)的整個傳統(tǒng)文明的標志形象。神農(nóng)氏以耒耨之利教天下,男女耕織不僅解決了人們對衣食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且為這種生產(chǎn)方式所衍生的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奠定了基礎(chǔ)。是故,《莊子·盜跖》稱贊:“神農(nóng)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呂氏春秋·愛類》則稱“神農(nóng)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這些記載和論斷都指出了農(nóng)耕技術(shù)和生產(chǎn)方式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重要作用。繼承神農(nóng)創(chuàng)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隨著生產(chǎn)技術(shù)的發(fā)展,至少到戰(zhàn)國時代,男耕女織的家庭小農(nóng)經(jīng)濟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基礎(chǔ),作為社會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基石的家國倫理思想自先秦綿延至今。
“神農(nóng)之教”不僅包含農(nóng)耕技術(shù)和生產(chǎn)方式,同時緣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所帶來的物質(zhì)豐富,自然分工下的人們開始進行“為市”、“交易”。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商貿(mào)活動相結(jié)合構(gòu)成了“神農(nóng)之教”生民之本的基本內(nèi)容。《漢書·貨殖傳》開篇即講:“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nóng)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nóng)之世。……食足貨通,然后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顯然,《漢書》的作者也深諳“神農(nóng)之教”傳統(tǒng)對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大意義和影響。
雖然氾勝之早年的學(xué)習(xí)生活是否在陶地完成,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當?shù)靥罩旃赂贿z風(fēng)的影響無法確考,但是,在現(xiàn)存的“氾書”中,其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表現(xiàn)的精明的經(jīng)濟學(xué)思想是顯而易見的:“區(qū)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qū)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又種薤十根,令周回甕,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賣之,與瓜相避。又可種小豆子瓜中,畝四五升,其藿可賣。此法宜平地,瓜收畝萬錢”;“瓠……黃色好,破以為瓢。其中白膚,以養(yǎng)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qū)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并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萬六千文。余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這些敘述中既有精確的數(shù)量計算,還有成本考量,并且表現(xiàn)出早期的農(nóng)田多種經(jīng)營思想:瓜田可同時種薤或小豆,豆葉還可賣錢;種瓠既可賣瓢,其瓤還可以喂豬,種子用來制作明燭。因為這里明確教人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并通過多種經(jīng)營“賣”得更多的“錢”,所以該書不僅在講作物的間作和栽培技術(shù),而且包含古代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思想成分。
四、《氾勝之書》的價值及影響
“氾書”在西漢以后對我國古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巨大和深遠影響是有跡可循的。成書于六世紀初我國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農(nóng)學(xué)巨著《齊民要術(shù)》分別在14個篇章引用“氾勝之書曰”19次,“氾勝之術(shù)曰”1次,“氾勝之曰”1 次,每次引用少則十幾字,多則數(shù)百字,在介紹大豆和小麥種植方法時,還專門稱“氾勝之區(qū)種法”,由此可見作者對該書的重視。
原書的體例現(xiàn)在雖不能確知,但早期稱之為“氾勝之十八篇”,應(yīng)當有其合理的編纂體例。我國古代的綜合性農(nóng)書大概主要有兩種體例,一是“月令”式,按照一年的時序講述各種農(nóng)事活動的安排,如《四民月令》《四時纂要》等;另一種為“農(nóng)學(xué)”式,按照農(nóng)林牧漁副等不同生產(chǎn)部門和動植物分類、分門別類系統(tǒng)地安排章節(jié)內(nèi)容,如《齊民要術(shù)》等。早期稱謂中的“篇”字似乎可以暗示,或許正是該書在體例上開創(chuàng)了我國古代農(nóng)書的“農(nóng)學(xué)”濫觴。后世對該書的輯佚編纂也體現(xiàn)了對這種農(nóng)學(xué)傳統(tǒng)的認識。
“氾書”中“耕之本”所述六條基本原則體現(xiàn)的邏輯性和系統(tǒng)性,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僅在眾多古代農(nóng)書中可見其運用,甚至連建國后俗稱的“農(nóng)業(yè)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也可明顯看出其發(fā)展的影子。
“氾書”作為一部古代農(nóng)科著作,其所載的多種谷物種植忌日,也影響了許多后世農(nóng)書。盡管這點在近代曾遭非議,但是,若以客觀的態(tài)度來看待其所包含的我國早期農(nóng)學(xué)理論體系,則其價值仍可作肯定性探討。首先,種植時機有宜與不宜,這是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規(guī)律的最基本認識;其次,九谷忌日是中國古代陰陽五行說理論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中的具體運用①“陰陽五行學(xué)說”是中國古代古典唯物哲學(xué)的核心思想,其影響無處不在。關(guān)于所謂氾書中的迷信思想,賀潤坤在“從云夢秦簡《日書》的良、忌日看《氾勝之書》的五谷忌日”(《文博》1995年第1期)一文中,對比分析出土文獻內(nèi)容和氾書谷物忌日相關(guān)內(nèi)容之后,指出九谷忌日是戰(zhàn)國末期至西漢中期民間的傳統(tǒng)習(xí)俗,其內(nèi)容并非純屬迷信,氾勝之只是對其客觀記載而已。金良年在“‘五種忌’研究——以云夢秦簡《日書》為中心”(《史林》1999 年第2 期)一文中,通過梳理不同《日書》的記載,考察了“五種忌”的源流及其術(shù)數(shù)原理,分析指出“五種忌”系統(tǒng)的栽種忌辰基本上是依據(jù)與該作物所屬五行沖克的支辰來排比的,并引金春峰的文章結(jié)論稱“以‘五種忌’為代表的栽種宜忌所強調(diào)的是,作物的栽種和生長、發(fā)育與時令因素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古代陰陽五行說缺乏系統(tǒng)嚴謹?shù)睦碚撽U釋,現(xiàn)代人們只能靠推測進行了解。陳瑞祥以亞里士多德和歐幾里得的公理化思想為指導(dǎo),將五行概念建立在太陽運行規(guī)律和陰陽概念基礎(chǔ)之上,并采用邏輯構(gòu)造方法給予表達,證明了只要太陽運行規(guī)律和陰陽概念成立,五行概念便可成立,五行理論可以成為基礎(chǔ)堅實、邏輯嚴謹?shù)目茖W(xué)理論;在建立了五行公理系統(tǒng)及其模型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推導(dǎo)出五行生克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作為系統(tǒng)整體的性質(zhì),其價值和地位是可以肯定的。對于五行學(xué)說,依據(jù)基本概念或本質(zhì)內(nèi)涵,經(jīng)過嚴格論證的命題,在其理論邊界和適用范圍內(nèi),具有很高的價值。關(guān)于陳瑞祥的“五行公理系統(tǒng)模型”及其應(yīng)用探討,可參看其“五行理論體系的系統(tǒng)化(一、二、三)”,分別發(fā)表在《中醫(yī)雜志》2014年第9期、2014 年第16 期和2018 年第18 期。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復(fù)雜系統(tǒng),按照金良年對秦漢以前的農(nóng)作物與五行配合情況統(tǒng)計分析,《月令》系統(tǒng)主要依據(jù)作物的形狀,《淮南子》系統(tǒng)是根據(jù)與作物相宜的水土,《淮南子》高誘注系統(tǒng)是根據(jù)作物的生長時節(jié),《內(nèi)經(jīng)》系統(tǒng)大體以作物籽實的色澤來解釋其與五行的配合,但是清代張隱庵《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集注》則以作物的成熟時節(jié)來解釋其與五行的配合。按照不同匹配方式,所導(dǎo)出的五谷宜忌內(nèi)容自然有差異。加之古代歷法精度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對歷法進行調(diào)整,支辰、歷法時日和節(jié)氣各以不同的周期匹配過程中,彼此和諧如一實非易事,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運用中,出現(xiàn)宜忌不驗現(xiàn)象而被視為迷信思想是容易理解的。,古代農(nóng)業(yè)系統(tǒng)及其運行機制應(yīng)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論加以解釋,引導(dǎo)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向精耕細作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在生態(tài)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道路上屢創(chuàng)輝煌②胡火金:《五行說對古代農(nóng)業(yè)的影響》,《自然辯證法研究》2012年第1期。。
當然,對后世影響最大、最持久的還是書中所設(shè)計的“區(qū)田法”。自漢以來,不斷有人推行或試驗區(qū)田法,直至建國后,仍不乏倡議和實驗者,學(xué)術(shù)討論更是綿延至今。后漢明帝、金、元時期都曾由政府強制推行區(qū)田法耕種。至于歷代由地方官吏主動推行或個人實踐的例子則難以完全統(tǒng)計。連著名的隱士、三國時期的嵇康都在其《養(yǎng)生論》中稱譽區(qū)田法,普通耕讀之家實踐從事區(qū)種,則恐大多沒有記錄流傳下來。據(jù)張芳、王思明主編的《中國農(nóng)業(yè)古籍目錄》統(tǒng)計,專以“區(qū)田”“區(qū)種”為題的著作有32 種之多③如《區(qū)田圖說》《區(qū)田書》《區(qū)種五種》《潘豐豫莊課農(nóng)區(qū)種法》等。參見張芳、王思明主編:《中國農(nóng)業(yè)古籍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58-64頁。。日本學(xué)者如天野元之助、大島利一等也都對氾勝之區(qū)田法進行過深入研究④[日]天野元之助:《中國古農(nóng)書考》,彭世獎、林廣信譯,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92年,第9-12頁。。
如前文所述,區(qū)田法的豐產(chǎn)優(yōu)勢源于其設(shè)計中整合的成套精耕細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法和原則,如耕田化土保持土壤肥力、注意植物間距以利通風(fēng)采光、護苗保墑適時管理等,根據(jù)作物生長特點,綜合利用人工和土地等自然環(huán)境因素。這種結(jié)合自然環(huán)境特點精心設(shè)計的精耕細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毫無疑問是我國古代為世界貢獻的最為寶貴的遺產(chǎn)之一。
由于該書在土化之法和多種作物栽培方面總結(jié)的技術(shù)經(jīng)驗具有較高價值,唐宋以前的學(xué)者多有征引,如鄭玄、韋昭、李善等在對經(jīng)、史和文學(xué)經(jīng)典涉及農(nóng)業(yè)知識內(nèi)容的注解中都有引用該書;宋代的吳淑撰《事類賦》、唐慎微撰《證類本草》、羅泌撰《路史》、羅愿撰《爾雅翼》也曾引用該書;著名的類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xué)記》《太平御覽》也都對該書部分內(nèi)容摘錄留存。眾多前代學(xué)者的推贊,使清代學(xué)者洪頤煊、宋葆淳、馬國翰等紛紛嘗試輯佚復(fù)原這部著作。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萬國鼎的《氾勝之書輯釋》和石聲漢的《氾勝之書今釋》及其英文版的成書出版,對該書的研究再次引起廣泛關(guān)注和認可。此后,針對該書內(nèi)容研究解讀的學(xué)術(shù)文獻不斷出現(xiàn),加深了人們對漢代農(nóng)業(yè)科技發(fā)展的理解。
五、結(jié)語
議郎氾勝之以輕車使者督三輔種麥,使關(guān)中地區(qū)獲得豐產(chǎn),緩解了人口稠密的西漢帝國都城地區(qū)糧食壓力;同時,在總結(jié)前人經(jīng)驗技術(shù)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性地設(shè)計了以區(qū)田法為核心的精耕細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并寫成農(nóng)學(xué)專著《氾勝之書》以利推廣,標志著我國古代農(nóng)學(xu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以現(xiàn)存材料來看,“氾書”在繼承西漢以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趣時,和土,務(wù)糞、澤,早鋤,早獲”六條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原則,建立了“耕之本”的整體觀;通過發(fā)展運用“土化之法”,詳細記載了“溲種法”等優(yōu)越的土壤改良技術(shù)措施和施肥方法,為后世的土地連作并永保土壤肥力指明了發(fā)展方向;總結(jié)了麥、粟、黍、稻、大豆、瓜、瓠、桑等13種農(nóng)作物的栽培技術(shù),其中不乏為后人提供創(chuàng)造性啟示的舉措,有些(如選種法等)甚至至今仍具實用價值;尤為值得稱道的是其“區(qū)田法”,針對干旱地區(qū)的水資源短缺問題,綜合運用各種技術(shù)護苗保墑,量人力盡地力,創(chuàng)造了至今都讓人羨慕的高額豐產(chǎn)記錄,開啟了我國精耕細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新時代,為我國利用荒田獲取高產(chǎn)設(shè)計了優(yōu)秀樣板;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氾勝之不僅精研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而且富有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思想,農(nóng)商兼顧,全面繼承“神農(nóng)之教”關(guān)于“食足貨通”“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的思想。另一古代農(nóng)業(yè)巨著《齊民要術(shù)》頻繁引用“氾書”,其作者在“序”中稱“商賈之事,闕而不錄”或有所指。
盡管書中有些說法,如“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等內(nèi)容,體現(xiàn)了兩千年前古人按照陰陽五行思想對合理安排農(nóng)事活動的認識,與現(xiàn)代農(nóng)學(xué)不屬同一體系,但正所謂瑕不掩瑜,“氾勝之術(shù)”當之無愧地可以被稱為漢代農(nóng)業(yè)技術(shù)上的一面旗幟。《氾勝之書》是我國古代農(nóng)書中的瑰寶,氾勝之則以其傳奇式的著作為我們展現(xiàn)了古代勞動人民在生產(chǎn)發(fā)展中積累的豐富智慧和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知識上的輝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