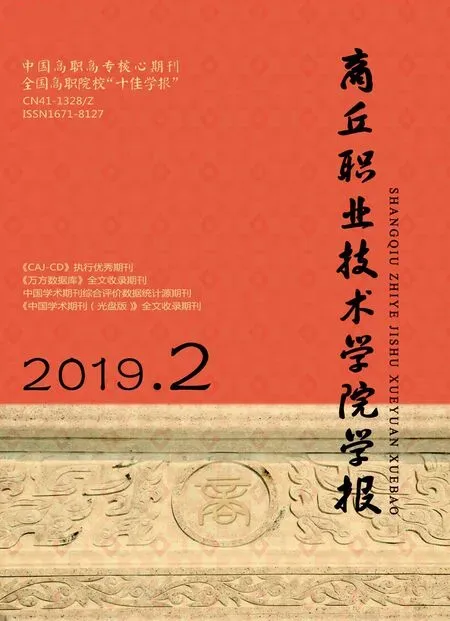西周早中期冊命禮儀演變窺探
劉青文,張德良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遼寧 大連 116000)
冊命,亦作“策命”,指封官授職,是西周至春秋時期周王或諸侯任命官員、賞賜車服的制度,包括天子任命諸侯、百官,諸侯任命卿大夫等。冊命禮儀于文獻中習見,《左傳·僖公廿八年》載:“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1]462西周冊命銘文是當時王室、公室或諸侯冊命的客觀真實記錄。冊命文字原本書于簡冊,在舉行冊命儀式時由專人當場宣讀,受命者接受冊命后鑄器銘記。現從西周典型冊命銘文①入手,對西周早中期冊命禮儀進行一番梳理。
早期冊命銘文:井侯簋 大盂鼎 宜侯夨簋
中期冊命銘文:

懿王:師詢簋 師晨鼎
其他:申簋蓋 呂服余盤
一、 冊命時間
早期:
井侯簋:唯三月
大盂鼎: 唯九月
宜侯夨簋:唯四月,辰在丁未
中期:

班簋:唯八月初吉
虎簋蓋: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
師遽簋蓋: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

師詢簋:唯元年二月既望庚寅
師晨鼎: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
申簋蓋:唯正月初吉丁卯
呂服余盤:唯正二月初吉甲寅
早期冊命銘文對時間的記錄比較簡略,只記月份而沒有明確的王年及月相干支;到西周中期,尤其是恭王時期,冊命銘文中對時間的記錄已較為詳細,王年、月份、月相、干支四項時間要素中多已具備或者至少占據兩項。可見,在西周中期已十分重視冊命時間記錄的完整性。這一現象亦是西周中期冊命禮儀完備的投影。
在上述所列的四項時間要素中,西周中期王年以元年居多。陳漢平先生曾對西周冊命銘文做過統計,冊命銘文中所見紀年以元年、二年、三年為數居多。究其原因,蓋新王即位,對先王舊臣有重新冊命之習慣[2]。月份以正月、二月、三月居多,蓋以其為年之伊始,冊命之禮為國家重要儀式,所以在年初舉行。月相中以初吉、既生霸居多,既望僅見三例,沒有關于既死霸的記錄。關于月相的四種主要計時術語,素來爭議頗多,主要有以王國維為代表的 “四分說”——將一個陰歷月大體平均分成四段,初吉代表初一到初七(八), 既生霸代表初八 (九) 到十三 (四), 既望代表望日 (十五) 到二十二(三), 既死霸代表二十三到月盡。另外,有以董作賓為代表的“定點說”,認為這四個術語各代表一個月中的某一天, 如董作賓認為初吉為初一,既生霸代表望日 (大月十六日,小月十五日) ,既望代表大月十七日,小月為十六日,既死霸也代表初一。無論采取哪一種月相的說法,上述四種術語均可與現今的天文學月相對應起來,從初吉到既生霸,是由新月到上弦月的時間,月亮從無到有,預示新生,加之初吉、既生霸的時間居于月首,古人以元為善,故而初吉、既生霸之時段為冊命儀式的首選時段。從既望到既死霸,是由滿月到下弦月的時段,此時月亮由盈到虧,暗含沒落之意,故而冊命儀式盡量避免在這一時段舉行。干支中出現最多的當為丁亥、甲戌以及庚寅,干支的選擇當與古人諏日的習俗有關,《說文》:“諏,聚謀也。”[3]52“諏日”即謀取吉日,文獻中常見諏日之習:
《禮記》:“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4]
《易·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5]23
《易·巽》:“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初,先庚三日,后庚三日。”[5]167
由上述幾例文獻可知,十天干中的丁日、甲日、庚日當為舉行各類重大事宜之吉日,冊命時間一般從這類吉日中擇取。
二、 冊命地點
早期銘文中記有冊命地點的僅有宜侯夨簋一例:
宜侯夨簋: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彳止(誕)省東或(國)圖。王立(蒞)于宜,入土(社),南鄉(嚮)。
西周中期以后,冊命地點主要分為以下幾類:
(一)廟或大廟

(二)大室
虎簋蓋:王在周新宮,格于大室。
師詢簋: 王格于大室。
師晨鼎:王在周師彔宮。旦,王格大室。
申簋蓋:王在周康宮,格大室。
(三)新宮、成宮
師遽簋蓋:王在周,格新宮

早期的宜侯夨簋中,“王立于宜宗社”之“宜”一般被認為是當時吳國境內的地域,位于今天的丹徒附近,“宜”字之后二字,曹錦炎釋為“宗土(社)”,唐蘭讀為“入土(社)”。
本文謹遵循唐蘭先生的解釋,讀作“入社”,甲骨文、金文中的土為古社字,“社”字從示從土,乃為祭祀社神之所。周王在冊命之前來到東方的領土,在宜地之社祭祀,以示對先祖的尊敬。
到西周中期,關于冊命地點的記錄格式一般是“王在某地,格于某”,其中,前者乃為周王冊命前所居或所在之地,是比較大的范圍,后者為具體的冊命地點,這與早期的宜侯夨簋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西周中期的冊命地點更為固定,以大室為主,其次為廟或大廟。大室即宗廟的一部分,《尚書·洛誥》:“王入太室裸。”[6]186孔穎達疏:“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6]186《說文·廣部》:“廟,尊先祖皃也。”[3]191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周制,天子七廟,太祖四親之外,有文武世室二祧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其制太祖廟在中,昭東穆西,皆別為宮院。凡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 。”[7]宗廟用以別尊卑之序,亦是天子與諸侯祭拜先祖亡靈之所。冊命儀式選擇在宗廟中進行,一方面顯示出儀式的莊重性;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周人對祖先的敬畏,這與早期宜侯夨簋中所反映出的敬示之禮是一脈相承的。
三、 冊命流程
西周完整的冊命儀式一般包括以下四個流程:
(一)周王即位
銘文中所記錄的即位有兩種情況,周王即位與受冊者即位。一般來說,周王即位乃為冊命儀式之首,周天子一切準備就緒后,才是受冊者即位。
早期銘文中關于周王即位的記錄僅見宜侯夨簋一例:
王立(蒞)于宜,入土(社),南鄉(嚮)。
中期銘文:
師晨鼎: 旦,王格大室,即位。
申簋蓋:王在周康宮,格大室,即位。
(二)儐者右受冊者入門
早期冊命銘文中未見對儐者的記錄,這一冊命過程可能是在穆王之后才確立下來。
中期銘文:

虎簋蓋:密叔入右虎,即位。

師晨鼎:司馬共右晨入門,立中廷。
申簋蓋:益公入右申中廷。
呂服余盤:備中內右呂服余。

備中內右呂服余。王曰:服余,令汝更乃且(祖)考事疋(胥)備中。
“疋”字本義為足,此處通“胥”,輔佐義。此銘文中,備中為呂服余之儐者,而周王下達的冊命中又命令呂服余輔佐備中,可見備中乃為呂服余的直屬長官。故儐者在引導受冊者的同時還有一層引薦的意味,儐者與受冊者的關系,大抵相當于管仲與鮑叔牙的關系。
(三)宣讀冊命
西周宣讀冊命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周王直接冊命,另一種是周王命史官宣讀冊命。
西周早期:
1.周王直接冊命:
宜侯夨簋:王令(命)虞(虎)侯夨。
大盂鼎:王在宗周令盂。
2.周王命史官宣讀冊命:
井侯簋:王令榮眔內史曰:割井候服。
西周中期:
1.周王直接冊命:
班簋:王令毛伯更虢成公服。
師詢簋:王若曰:師詢,丕顯文武,膺受天命。
呂服余盤:王曰:服余,令汝更乃祖考事胥備中。
2.周王命史官宣讀冊命:
簋:內史即命。
虎簋蓋:王呼內史曰:冊命虎。

師晨鼎: 王呼作冊尹冊令晨。
申簋蓋:王命尹冊命申。
西周早期的冊命以周王直接冊命為主,冊命辭令也更為簡單,一般為“王令某”或“王令某內史”,早期僅見“令”而未見“冊命”之辭。到西周中期,周王直接冊命的形式逐漸減少,周王命史官宣讀冊命的銘文占了較大比重,上文列舉的銘文中所見史官主要有三種:內史、作冊尹、尹氏。長期以來,學者們普遍認為內史、作冊尹、尹氏均為史官的一種。而史官之職又有細分,以文中未列舉的西周晚期器頌壺為例:“尹氏受王令(命)書,王乎史虢生冊令(命)頌②。”其中,尹氏將冊命書交給周王,周王再命史虢生宣讀冊命。頌壺中的“尹氏”當為負責書寫冊命簡冊的史官,而私名為虢生的史官,其職能當與本文中所列舉的幾位史官職能相同,在冊命過程中當庭宣讀周王冊命。書寫冊命的史官在西周早中期銘文中較少出現,這一職官很有可能是在西周中后期,隨著冊命制度的成熟而從史官中分化出來的。
(四)受命拜謝
周王完成冊命后,受冊者要對周天子行禮拜謝,以示誠心。
早期:
宜侯夨簋:宜侯夨揚王休。
井侯簋:拜稽首,魯天子受氒頻福。克奔走上下帝無終令于有周。
大盂鼎:盂用對王休。
中期:

班簋:班拜稽首曰:嗚呼!丕丕揚皇公受京宗懿釐,育文王王姒圣孫,登于大服,廣成氒工。
虎簋蓋:虎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丕魯休。
師遽簋蓋:遽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丕休。

師詢簋:詢稽首,敢對揚天子休。
師晨鼎:晨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令。
申簋蓋:申敢對揚天子休令。
呂服余盤:呂服余敢對揚天丕顯休。
西周早期,受命拜謝儀式還沒有統一的標準;到了西周中期,尤其是恭王時期,受命拜謝儀式開始呈現整齊劃一的趨勢。銘文所記錄的多為受冊命者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周人視稽首禮為最莊重的禮儀,《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兇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日肅拜,以享右、祭祀。”[8]賈公彥疏:“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作為九拜之中最為重要的稽首禮,到西周中期開始形成儀式性的規程。可見,西周中期以后,整個周王朝的禮儀制度有了比較完善的體系,由上而下的管理也更具規范性。
當時的文獻中亦有關于冊命流程的記載。《詩·大雅·韓奕》《詩·大雅·江漢》《左傳·僖公廿八年》等均有比較完整的冊命流程記載,其中,《左傳·僖公廿八年》的文字記載最具代表性: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1]462。
文獻中關于冊命流程的記載一般不見具體冊命地點,周王即位、儐者右受冊者入門兩步流程在記載中也很少見,多為周王宣讀冊命、受命拜謝兩步,具體賞賜物在文獻中也有比較清楚的羅列,可與銘文相對照。
四、 冊命內容
冊命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承襲先祖職位
虎簋蓋:更乃祖考胥師戲,司走馬馭人眔五邑走馬馭人。

申簋蓋:更乃祖考胥大祝,官司豐人眔九戲祝。
呂服余盤:令汝更乃祖考事胥備中,司六師服。
以上四例銘文體例大體一致,均為“更乃祖考,司某職”,“更”讀為“賡”,含接續之義,“更乃祖考”即為繼承先祖的職位。西周貴族在朝中擔任要職者,其年老或離世后,便由子孫來接替這一職位,成為世襲的職官。
(二) 承襲他人職位
班簋:王令毛伯更虢成公服,屏王位,作四方亟。秉緐、蜀、巢令。
從該銘文內容上來看,毛伯與虢成公并無任何親緣關系,此時毛伯承襲虢成公的職位,乃是為保衛周王室,平定東方叛亂。在世卿世祿的大背景下,這類冊命并不多見。時王的這種決策,是應時而變的明智之舉,卻并不能撼動整個世襲官制的根基。
(三)周王新命
早期:
井侯簋:割井侯服。
大盂鼎:盂,廼召夾尸司戎,敏諫罰訟。
中期:

周王新命者,多為權臣之后或戰功卓越者。上舉幾例中,井侯為周公旦長子,身世顯赫;盂為宗周重臣,在征伐鬼方時,為宗周立下大功。
(四)重申或改動原冊命
師遽簋蓋:王徙正師氏。
師詢簋:今余唯申就乃令,令汝惠雍我邦小大猷。
上述兩例均涉及對師氏的冊命,關于師氏,多數學者認為其是軍職人員。師遽簋蓋中,周王對軍事長官師氏進行了調整,周王的這一舉措,許是為適應當時的政治局勢。師詢簋中,周王重申對師詢的任命,一般來說,這種重申意味著對被冊命者之前工作的肯定,雖然職位官階未發生變化,但相應的賞賜物卻會增加,這種重申冊命是西周冊命制度中重要的獎勵機制。
早期冊命銘文一般不記錄具體的冊命職務與受冊人的職責范圍,穆王以后的中期冊命銘文中,冊命內容更為具體,記錄有具體的冊命職務與受冊人的職責范圍的銘文居多,其中,簋還記錄了具體的俸祿。
五、 具體賞賜物
早期:
宜侯夨簋:賜鬯一卣,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賜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卅,賜在宜王人十又七生,賜甸七伯,厥盧□又五十夫,賜宜庶人六百又□六夫。
井侯簋:賜臣三品:州人、人、庸人。
大盂鼎:賜汝鬯一卣,冂衣、巿、舄、車、馬,賜乃祖南公旂,用狩。賜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賜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遷自氒土。
中期:

虎簋蓋:賜汝巿幽黃、玄衣屯、鑾旂五日,用事。
師遽簋蓋:王呼師朕賜師遽貝十朋。

師詢簋:賜汝秬鬯一卣、圭瓚、夷□三百人。
師晨鼎:賜赤舄。
申簋蓋:賜汝赤巿縈黃、鑾旂,用事。
呂服余盤:賜汝赤巿幽黃、鋚勒、旂。
一般來說,冊命儀式都會伴隨著賞賜活動來進行,但也有少數僅見冊命而未見具體賞賜物的,穆王時期的班簋便是一例,蓋因其為臨時的軍事調動,平定東國之亂又迫在眉睫,賞賜活動遂被省去。
西周早期,冊命賞賜物品較為豐富,從鬯酒、玉器、兵器到車馬、臣民、奴隸、土地均有涉及,尤以臣民與土地賞賜為著,賞賜種類豐富且賞賜數量巨大。宜侯夨簋與大盂鼎中,均涉及土地的賞賜,土地是安家立命之根本,此時,與其說是對臣子的賞賜,倒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分封。到西周中期,賞賜物品由原來的臣民與土地為主轉為以冕服服飾、車馬飾、旂旗為主,賞賜物品種類單一且數量有所削減,冊命向儀式化方向轉變,賞賜物品更傾向于迎合冊命禮儀而不是如早期賞賜物品一般偏重實用性。
西周始建之時,土地廣袤,物資充盈,克商所獲奴隸與殷遺民甚眾,但西周王朝根基未穩,王室之內大小宗族亦不知其人心向背,而此時戰亂仍頻,大量的軍事活動需要強而有力的軍事指揮,土地與臣民的賞賜是穩定王室、安撫人心最有力的方式,故而早期賞賜物中多見土地與臣民。到了西周中期,周邊方國的動亂減少,社會漸趨穩定,與此相適應的禮制也確定下來,冊命活動中更具象征意義的賞賜正是中期社會平穩發展的反映。
六、結語
西周早期,冊命禮儀不甚完備,但已初具規模。冊命時間只記月份,以年初幾月居多;冊命地點雖未固定,但冊命于宗社,亦能顯示出禮儀的莊嚴性。到了西周中期,冊命銘文的記錄更為翔實,冊命時間與冊命地點也更加固定,整套冊命禮儀有了更加完備的流程,由早期偏重實用性的土地賞賜到中期偏重象征性的服飾賞賜。不難看出,到西周中期,周朝的冊命制度已經開始成熟起來,冊命禮儀趨向于系統化與規范化。這種冊命禮儀的確立與完善,顯示出周王朝禮制的成熟,亦是中期社會穩步發展的投影。同時,冊命禮儀的完善也昭示著整個西周的政治危機。對諸侯百官的每一次冊命與任職,都意味著周天子權力的下放。周王將土地與人民賜予諸侯,諸侯在其封地內享有絕對的權威,如此日積月累,把握在周天子手中的權力日漸松散;而整個周王室的經濟基礎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冊命賞賜中日漸蠹空。失去了經濟的支撐,政治上也日見式微。西周王朝后期的衰敗,與日漸成熟的冊命制度關系甚密。
注釋:

② 頌壺(《殷周金文集成》0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