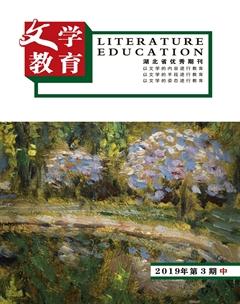論空間遷徙對艾青抗日戰爭時期詩歌創作的影響
內容摘要:抗日戰爭期間艾青流徙了大半個中國,從杭州到武漢、從北方到南方、從重慶到延安。本文通過對艾青足跡的追蹤,旨在探尋艾青的遷徙經歷對其思想觀念與抒情方式的影響。
關鍵詞:艾青 詩歌 遷徙 創作轉變
“抗日戰爭時期,是艾青創作的成熟期。”艾青從人心惶惶的杭州走到文人云集的武漢,從飽受磨難的北方轉向山明水秀的南方,從大霧彌漫的重慶奔向天朗氣清的陜北。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的三年多里,他流徙了大半個中國,在戰火與硝煙中汲取了詩情。艾青到達延安之后才得以安頓下來,解放區的文學生態與國統區有著很大的差異,此后的創作與抗戰前期的創作相比,既有內在相關性,也有新的變異。本文以艾青的空間遷徙為根據,通過對他足跡的追蹤,探尋艾青的遷徙經歷對其思想觀念與抒情方式的影響。
一.烽火里的悲哀與光明
七七事變爆發后,艾青在杭州短暫停留了兩個月之后就去了武漢。接下來是一段兵荒馬亂的生活。從武漢到臨汾、從臨汾到西安、從西安返回武漢,以至于后來回憶起這一時期的生活,艾青認為“完全是逃難性的”。然而,這段狼狽不堪的旅程,卻是艾青第二本詩集《北方》的絕好素材。張竹如回憶了艾青當時的創作狀態:“他每當靈感來了,就趕快寫,在火車上,在旅途中所見所聞,都觸動他。這些詩都是他親眼所看到的社會生活的真實表現。”《北方》集多寫詩人在隴海路沿線的見聞。詩人第一次渡過長江,來到滿目瘡痍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沖擊著這個來自南方的旅客,寫下了《補衣婦》《乞丐》《風陵渡》《驢子》《駱駝》《手推車》《北方》等詩,表現著北方的悲哀與痛苦。
艾青的詩歌有憂郁的特質。他自小就養成了憂郁的性格,成年后一直處于半流亡的境遇之中,這種始終不得安定的狀態在他的創作中醞釀出了一種哀感,《北方》集里就充滿了詩人憂郁的詩情。《北方》是悲哀的,這苦難深重的土地引起了詩人對北方與國土的深沉的愛意與崇敬,詩人并沒有沉溺于憂郁之中,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力。“我到了北方。在風沙吹刮著的地域我看見了中國的深厚的力量。”這也是為什么艾青的詩歌雖然總是憂郁的,但是依然給人以希望與力量的原因。就詩歌本身而言,《北方》集“在藝術上,繼續采用和發展了細致地描刻現實與巧妙地象征、喻比相結合的創作手法;在詩歌語言上,更加追求樸素與自然的風格;而在內容與情感上,則突出地流露出作者深深地悲愁與憂郁。”
1938年4月,艾青從西安回到武漢,以保衛武漢為背景寫成了長詩《向太陽》。如果說艾青寫土地的詩總帶有憂傷的調子,那么在他以太陽為意象的詩歌中總是能夠振奮人心,給人以光明與希望。《向太陽》開頭和第四節的開頭都引用了詩人寫于1937年春的舊作《太陽》,兩首詩雖然都以太陽為意象,但是前者通過具體而微地描繪展現了一個更廣闊的、充滿希望的時代,最后還表達了一種獻身的崇高意愿。這是時代的要求,正如艾青自己所言:“詩人能忠實于自己所生活的時代是應該的。最偉大的詩人,永遠是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艾青此時當然創作了一些迅速反應現實的詩,如《反侵略》《懺悔吧,周作人》。7月12日武漢大轟炸后不久,艾青卻寫下了耐人尋味的《黃昏》一詩,抒發著不可排遣地對故鄉田野氣息的懷念,這種親近山林田園的傾向在之后的創作中加深了。
二.山林間的安寧與躁動
由于武漢告急,1938年7月艾青從武漢來到湖南衡山,在此短暫停留之后,于11月中旬去了桂林。雖然艾青待在衡山的時間不長,但是留下了《秋日游》《斜坡》《秋晨》等幾首詩。衡山縣坐落在南岳衡山腳下,古樸優美,能夠讓漂泊多時的詩人得到片刻的安寧。這些風景詩以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飛禽走獸為意象,以鮮明的色彩、具體的描畫再現了大自然的秀美,像一幅幅立體的油畫,體現著詩人的繪畫功底。1938年11月中旬艾青去了桂林,此時寫下了《我愛這土地》,流露出比在《向太陽》中更為強烈的愿為祖國獻身的熱情。桂林時期,艾青寫下了《縱火》《死難者畫像》等反應大轟炸的詩,創作高潮應該是長篇敘事詩《吹號者》以及姊妹篇《他死在第二次》,《吹號者》“好像只是對于“詩人”的一個暗喻,一個對于“詩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而《他死在第二次》則表現了詩人由一個被迫離開土地上了戰場、英勇奮戰之后默默犧牲的傷兵所引起的憂傷。聯系此時期艾青與戴望舒對于發展中國新詩的熱切追求,不難理解艾青在努力匯入時代的聲音時仍然以自我的真情實感做基調。1939年8月下旬,艾青搬到桂林鄉間小住,創作出了《秋晨》《低洼地》等風景詩,此時的心境在散文《鄉居》中有所體現。
為了維持生計,艾青于9月下旬到衡山鄉村師范學校任教。新寧是一座寧靜優美的山城,夫夷江貼城而過,山川草木、舟船橋梁、飛禽走獸都能激發詩人創作的靈感,艾青創作了《山城》《水鳥》《船夫與船》等詩。《青色的池沼》《灌木林》《初夏》等風景詩展現了山城春夏時節的活力與明艷。但是,艾青筆下的山城并不總是清新明麗的,憂郁是他詩歌中的底色。《曠野》一詩營造了悲哀而又曠達、辛苦而又貧困的“曠野”意象。艾青在《曠野》前記中有所說明:“《曠野集》所收詩二十首,均系作者在西南山岳地帶所作,或因遠離烽火,聞不到“戰斗的氣息”,但作者久久沉于莽原的粗獷與無羈,不自禁而有所歌唱,每一草一木亦寄以真誠,只希望這些歌唱里面,多少還有一點“社會”的東西,不被理論家們指斥為“山林詩”就是我的萬幸了。”新寧雖是山野地帶,但也是運送戰士與輜重的直接后方,人員頻繁往來給詩人生動具體的感受,《兵車》一詩就與戰爭有著直接的關系。
艾青在新寧居住了八個多月,這是他創作上的豐收期,他寫下了《曠野集》中的大部分詩歌,《詩論》也完成于這一時期。鄉間的生活終究太過單調寂寞,因此當艾青受到育才學校校長陶行知的邀請函時,奔向了另一座山城重慶。在重慶,他創作了《抬》《城市人》《刈草的孩子》《篝火》《哀巴黎》《三國公約》《新的伊甸集》等詩。
三.解放區的困惑與轉變
1941年3月,艾青到達延安。獨具陜北風韻的根據地有著迥異于南方的風光,詩人放眼望去是延河、大豆、蕎麥、包谷米、騾馬隊,延安人民喜悅樂觀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于大后方。艾青創作的敘事長詩《雪里鉆》,用明快活潑的語言寫出了戰士與戰馬的英勇氣概,全詩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與英雄主義精神,一掃桂林時期創作的敘事長詩《吹號者》和《他死在第二次》中的感傷低迷的情調。艾青還寫下了《我的父親》《少年行》《希特勒》《拖住它》《古松》和《古石器吟》等詩。但是,他的創作并不一直這么順利,許多從國統區奔向延安的作家都陷入了創作上的凝滯期。《時代》這首詩就反映了艾青這種創作困境。詩人期待新時代的到來,并且有著強烈的為時代獻身的愿望,但是卻因找不到合適的語言而保持沉默。
整風運動之前的延安文藝界活躍著各種異質因素,毛澤東注意到了作家們異聲共鳴的狀態,在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曾多次與艾青通信詢問他的意見,艾青于是寫下了《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在和《講話》保持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對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等問題保留了自己的意見:“在為同一的目的而進行艱苦斗爭的時代,文藝應該(有時甚至必須)服從政治,因為后者必須具備了組織和匯集一切力量的能力,才能最后戰勝敵人。但文藝并不就是政治的附庸物,或者是政治的留聲機和播音器。”也就是說,在思想上,艾青此刻的知識分子文化觀念與區域政治文化觀念存在一定的分歧。他后來回憶道:“初到延安時,我的思想認識并不明確,帶著許多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創作于新寧的長詩《火把》細膩地描繪了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洪流中厭棄舊我、走向新生的心路歷程。經過整風運動之后,作為對講話方針的回應,艾青創作的敘事長詩《吳滿有》,以解放區的勞動模范吳滿有為主人公,以寫實的手法鋪敘農民的生活,在今昔對比中突出翻身農民的歡喜,語言簡潔明快,詩風更加樸素明朗,情緒更加飽滿昂揚。
1945年出版的詩集《獻給鄉村的詩》,表明土地/鄉村是艾青詩歌中一以貫之的主題,“對故鄉的依戀是人類的一種共同情感。”詩中深深地侵染著土地的憂郁。“我如何能使自己完全不憂郁呢?我所看見的東西真的就完全象你們所看見的那么快意么?”詩中的憂郁實屬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自我心境的真實流露。在延安創作的《村莊》與《獻給鄉村的詩》中,憂郁的色彩被稀釋了,更多的是期待鄉村崛起的愿望。
艾青在“大堰河”時期寫下的“獄中詩”,曾因技巧和語言上有著較為濃重的歐化色彩而受到非難。到了抗日戰爭時期,詩歌的風格與情感也發生了變化,進入了創作成熟期,但是處于特殊的戰時文化形態之中,其創作的合法性仍然需要被重新確認。為了適應解放區的文化方針,艾青調整了寫作策略與抒情方式,并對自己延安時期“學習性質的”創作有著清醒的認識。艾青懂得個人與時代的辯證關系,總是將自我與土地、人民、時代接通,因而他的詩能夠穿越動蕩的烽火年代,刺透濃厚的歷史迷霧,散發著歷久彌新的光彩。
參考文獻
[1]楊匡漢,楊匡滿.艾青傳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
[2]周紅興.艾青研究與訪問記[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3]艾青.艾青全集第三卷[M].石家莊:山花文藝出版社,1991.
[4]周紅興.艾青的跋涉[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
[5]艾青.艾青全集第五卷[M].石家莊:山花文藝出版社,1991.
[6]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作者介紹:紀從潔,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2017級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女性主義文學、臺灣文學)
- 文學教育·中旬版的其它文章
- 回頭
- 眼界
- 游甘孜
- 往事如麻
- “被讓座”的倫理之思
- 《飲酒·其五》閱讀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