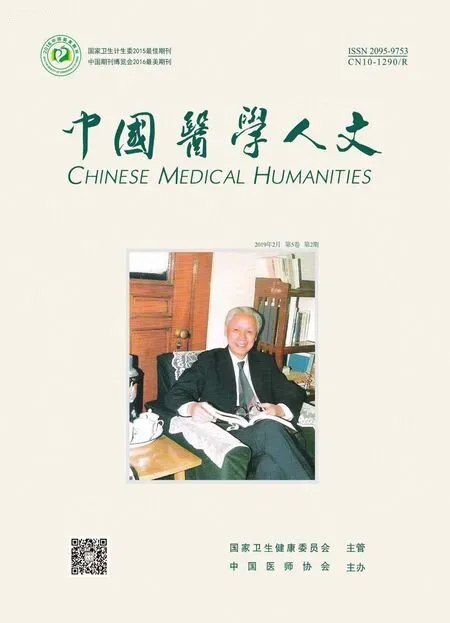生命盡頭是尊嚴
文/陳思暢

在神經內科,我輪轉的是溶栓組。也就是說,我們治療的是神經內科最兇險的疾病:腦梗死。有一位老人,他雖然不是我主管的患者,但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生命的盡頭可能是死亡,而死亡的背后還有兩個字:尊嚴。
那是一個忙碌的中午。聽說眼科有個病人術后出現腦梗,已經溶栓治療,現在正在來神內的路上。這病人會是什么情況?雖然,病人沒有分到我的頭上,但是作為神經外科來神內輪轉學習的一員,我也把這里的一切當成我的職責。危重患者,當然我要沖在最前邊。果然,是個重病號,上級醫(yī)生查看完后,讓去做CT。由于是中午,大家都在忙各種事情,我立刻自告奮勇去陪病人做CT。做之前,我們準備好了簡易呼吸器等基本的搶救設備。我看了看患者的瞳孔,一邊做了白內障手術,另一側的瞳孔已經散大固定了。患者已經陷入中度昏迷,僅有的生命體征還在維持著。
緊趕慢趕到了CT室,我們把老爺子抬到了CT床上。隨著嗡嗡的CT床移動聲,一張張片子逐層顯像。大面積腦梗,出血轉化,中線移位,環(huán)池消失……種種跡象表明,患者的時間不多了,內科治療已經幫不了他,想要救命唯一的辦法就是——手術。把腦梗一側的顱骨打開,讓壞死水腫的腦組織壓力釋放,挽救腦干的殘余功能。但是已經梗死的腦組織就沒有辦法了,患者即便活下來,很可能也是植物人,或者嚴重的偏癱和認知障礙。
在回去的路上,還沒有取得上級醫(yī)師的同意,我就給我們科室的會診醫(yī)生打了電話,并且告訴他相關的情況。“病人腦疝有多久了?”院總急切地問道。“半小時吧,做CT之前,瞳孔剛剛散大,來的時候還是好的。”我告訴院總。“八十多歲了,這么重的患者,家屬選擇手術嗎?”院總這句話把我問蒙了。是啊,我一直在想怎么樣能保住老爺子這條命。但是,這真的是他和他家人的期望嗎?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回到了病房。在請主任閱片的同時,神外的會診醫(yī)生也到場了。“保命的話,必須要做手術。”神內主任斬釘截鐵地說道。“確實是這樣。但是手術以后,患者不一定能活下來,也不一定能醒過來。而且,他一定會癱瘓在床,沒有任何生活質量。看看家屬的意見吧!”神外院總正在說著,家屬進來了。是一位老太太,年紀看著也將近80歲了。看著我們討論的情況,她眼圈紅了,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嗎,我原來也是在醫(yī)院工作的。他的情況,我非常清楚。”一句話讓我們既感到為難,又感到難過。為難的是,對面曾經的同行、前輩,這些不好的話,怎么對她說出口?難過的是,家屬是我們的同行,她本來是在醫(yī)治別人,但現在,她仍然不得不面對親人即將到來的死亡。“老爺子在退休前,是一個工程師。退休這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樂團當指揮,他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音樂家。”說著說著,老太太停了下來。眼淚從她遮掩的指縫中滲了出來。“他就是為了能看清楚樂譜,才做的白內障手術。八十多歲了,他能聽清楚每個樂器的音符和節(jié)奏”。老太太清了清鼻子,接著說道。“我想知道,如果做了手術,最好的情況,他能恢復到什么程度?他能醒過來嗎?他能生活自理嗎?”一時間,身經百戰(zhàn)的各位主任突然也陷入了沉思。真相可能是很傷人的,怎么讓老太太平靜地接受這一切呢?老太太好像讀出了我們的猶豫,她直接問神經外科會診的院總:“醫(yī)生,你說老劉如果現在做手術,他以后還有可能生活自理嗎?”“不可能了。手術創(chuàng)傷很大,除了要去掉骨瓣,很可能要把腫脹的腦組織也去除。就算能活下來,植物人的概率也非常大。右側肢體功能,是沒有恢復的希望了。”院總在猶豫之下,又說出了這些話。聽到這些,我有點不忍直視老太太的反應。但是,老太太突然間面上有一點微笑。她平靜地說道:“指揮是他六十多年來的愛好。從他參加工作,就一直在業(yè)余樂團做指揮。退休這二十年,更是一天都沒有落下。如果他做了手術,活下來卻沒有辦法活成自己希望的樣子,這樣的活法還有什么意義?老爺子以前就說過,真到了這一步就不要救了,該去的……就會去的。”說到后邊這幾句時候,老太太有些哽咽。我注意到,負責搶救的年輕醫(yī)生的眼圈也有點發(fā)紅。又和病人家屬聊了聊,老太太在放棄手術的同意書上簽了字,離開了辦公室。
其實,這個病人和我沒什么關系。但是當我陪他做CT,陪他家屬面臨著生死選擇的時候,我仿佛也融入了其中,好像內心也對他有牽掛。晚上,他的呼吸心跳還算平穩(wěn),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比平常更早來到醫(yī)院,看到值班的醫(yī)生正在滿臉倦容地寫著什么材料。我心里突然有種不詳的預感。“病人怎么樣了?”我問到。“后半夜走了。”她眼圈紅紅地告訴我。我沒有再問。我知道,當一個人面臨死亡的時候所做出的選擇,一定是窮盡了他畢生的智慧和經驗。從他的離去中我看到,真的能有人在生命的盡頭,用尊嚴來為自己書寫這最后的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