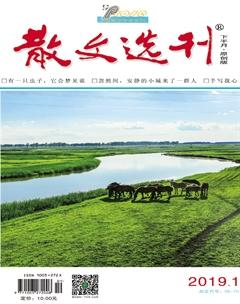有一只蟲子,它會夢見誰
蔣建偉 彩插
冬天,死亡站在地獄入口呼喚你。
暴風雪高高低低地狂吼著,迎面刮過來,爆炸,再爆炸,一股股透骨的冰刺感,緩慢地融化,浸洇,四處散開,消失了。讓你不得不感慨,這平原上暗夜潛行的姿勢,“咵咵——咵咵”,一路向北,小跑,像一列列士兵似的急行軍。
如果你打開地平線,小心哪小心,嗬,薄薄的,打開那層凍壤,下面的,全都是“呼哧,呼哧”睡著的小精靈。誰,從冰涼的土壤里調整一點點睡姿呢?誰誰誰?哦,小蚰蜒,小蜘蛛、小螞蟻,蛇、蝎子和蜈蚣,青蛙、癩蛤蟆、烏龜、土鱉、蚯蚓、蟬蟲、蠐螬、螻蛄、金針蟲、地老虎、長腿毛毛蟲和螞蚱、螳螂、蟋蟀、蛐蛐、蟈蟈們,它們都是這個世界最幸福的天使。還有,那些緊緊摟住枯枝敗葉的蚊子,半袋子碧綠色的肚子一起一伏著,那些鉆進墻縫、水泥縫、石頭縫、土坷垃縫里的小嘍啰蟲,半個綠豆粒兒大小,兩排小腿,即使撒開腿奔跑,也像移動似的,它們不論男女老幼,都怕冷,冷得直打戰兒,縮成了一粒粒土黃色的圓球。死亡隨時發生,大批的死換來了少量的生。大地夜行,許許多多的風走成了一條路,你會時不時地聽見不知誰在呻吟,驚慌失措著發出那么一聲兩聲,不過很快,風聲、草聲、樹枝碰撞聲就把它們吞沒了,星星月亮隱藏起來,影影綽綽的光亮被暗夜收了去,然后是黑暗中的最暗,逼人于死地,讓你不得不閉上眼睛。然后,然后,你聽到了驚蟄的聲音!
啊,雷聲四野,天籟初現。
太陽出來了,土壤回暖,水汽開始朝著地皮上升,暴風變小了,小風開始一陣陣朝田野里刮,土壤變得更加松軟,那么多的水汽接近地面,接近泥巴和草木,全都隱藏在細碎綿長的米線般的泥土里。地下的小天使們也跟著水汽一起往上拱,它們伸展著腰肢,它們腦袋手腳并用,使勁往上拱,像老母豬拱地,像老牙狗拱空空的食盆子。是的,它們和人類一樣有靈性,也可以直接稱呼為“他”或“她”。
最先,從腐葉爛泥里拱出頭的,是一對情侶蚯蚓,他“咝”一聲,她“咝”地回應一聲,意思在說:“這個白花花的世界,怎么沒有它們說的那么美好呢?除了冷,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一轉身,它們又原路返回。蛇、烏龜和青蛙、癩蛤蟆比蚯蚓聰明,它們拱出腦袋以后,小眼睛就開始滴溜溜了,烏龜“嘎嘎”笑了兩聲,說:“我餓死了,我餓死了,走了!你們別管我了。”說著,朝著一片池塘爬去。青蛙和癩蛤蟆也不傻呀,它們“呱呱”“嗯啊”叫著跟上。烏龜察覺了,忽然就不走了,扭頭問青蛙:“你跟著我干啥?”青蛙尷尬了半天,也回答不了什么,只好扭頭把這個問題拋給了癩蛤蟆:“你跟著我干啥?”癩蛤蟆也不好回答呀,只好惡狠狠地朝身后看去,蛇呢,正悄無聲息地尾隨它,心里頭那個氣啊!蛇的腦子活,身子更活,腦袋突然向左轉,無所謂地向一片麥田游去,吐了吐信子說:“不就是一頓大餐嗎?不請我算了,牛啥牛?”癩蛤蟆也氣呀,它感覺蛇不是在嘲笑烏龜,倒是在嘲笑自己,也拐彎去了一片泥沼地,一路氣鼓鼓著,放了七八個響屁。到了池塘邊,一看,比自己原先預想的面積大多了,烏龜也不計較后面愛跟著什么誰誰誰了,“撲通”一下,跳進池塘里,自己先美美地大吃大喝一頓,然后睡覺,等待和一位江南的美女烏龜結婚、生兒育女,這,就是他今年的目標。青蛙也是這么想的,她雖然只活了四年多,但之前的每一年,她都會遇見一個夢中的他,她“呱呱”幾聲,那對岸,便迅速回蕩起自己的聲音,看啊,多么幸福。當然,如果蛙聲落滿大地,可以像火焰一樣被點燃,“轟”,點燃起一大片一大片的蛙聲,火焰紅紅白白、黃黃藍藍,那么,她的歌聲,也一定從天上砸下來。
你聽見了大地的呼吸。像是誰誰誰剛剛醒來,還在半閉著雙眼,腦子混沌著,“啪……啪”,“啪,啪”,呼出的兩道氣流徐徐,濕濕熱熱的,響亮刺耳,龐大,氣勢恢宏的那一種。你突地想起某臺音樂會演員謝幕,觀眾用經久不息的掌聲固執地要求他們加演一曲,比方說奧地利作曲家約瑟夫·施特勞斯的《納斯瓦爾德的女孩波爾卡瑪祖卡(作品267號)》。不久,只聽見“西——西”,“拉——拉”,小提琴聲漸起,是“7、6”兩個音符發聲,逐漸放大,陽光緩緩步入室內,光線放亮,樂聲漸弱。想象還沒有止步呢,大提琴聲登場了,深沉,恢弘,各種各樣的西洋銅管樂器和弦樂器次第亮相,滿腹蒼涼的空氣,上一口,連著下一口,像極了耳鳴時的聲線持續。遼闊的田野被春天剛剛吹醒,一只蜜蜂醉倒在一束油菜花的芬芳里。呼和吸,宛如一對情竇初開的男女,突然跑到森林深處避雨,不得不窘迫地獨處,他們誰也不敢看誰,臉上飄來幾片霞光,心跳得厲害,誰也不敢打破這短促的靜寂,卻早已經滿腹蜜語了。一個人假睡的樣子就是非常滑稽的,想醒,又不想全醒。然而,世上有什么事情比戀愛課更加浪漫的呢!幾乎同時,他們都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一只手,左手碰到了右手,拉住,握住,一個旋身,整個心兒地摟住,欣喜著對視,歡笑,最后,像芭蕾舞演員那樣在巨大的圓舞曲音樂中旋轉,旋轉,全世界仿佛不存在了,只留下了我和你。如果,這時候可以在月光下,一陣陣空靈的女聲小合唱可以飄在空氣中,萬籟縹緲,他們的愛情,該是多么美妙!
天籟終究會降臨,是這樣的,更多的天籟也將降臨到我們的頭頂。天氣越來越熱了,冰雪消融了,寒冷蒸發了,雷聲下來了,雨水下來了,和風下來了,太陽和月亮星星都下來了,冬眠的小精靈們紛紛破土而出,唱起了古老的民歌。長長的地平線上,草木蔥郁,鳥類、家畜、家禽也不甘示弱,兩條腿的,四條腿的,一個個“咦咦咦”“啊啊啊”“咯咯咯”“嘎嘎嘎”地唱歌,它們站著走著跑著飛著笑著哭著尿著屙著睡著夢著,一點點積攢著火熱的理想,元氣上升,汗珠兒不斷地從額頭、腋窩、胳膊與大腿交叉的地方沁出來,熱氣裊裊蕩蕩,飄落,生命力何其旺盛。天地清明,它們潮濕的聲音,生了根,發了芽,在我們的耳孔里長成了一片片森林,葉子和葉子們飛翔歌唱。
我們坐在巨大的黃昏里。一條金毛狗在小區草地里跑來跑去,時不時找到我們,討一把狗糧,隨便叫上三五聲,也是天籟呢。它這叫聲,會穿越天空,墜落在遠處,引來了一陣陣隱隱約約的狗叫聲,我感覺,聲音距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是一幫流浪狗吧?走了,走了。”妻子急匆匆牽了狗說。狗有領地意識,相互間,經常爭地盤。我也怕它這小伙子和那幫子老家伙打起來,吃虧不說,還傷小伙子的自尊心。天色說黑就黑了,路燈“啪”一下亮了,我們嚇了一蹦,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倉促離開。路燈下,三個長長的影子移過去之后,單元樓上的燈火亮了,小區外商店的霓虹燈也亮了。
正在走路呢,就聽見頭頂上一股裹挾著大河咆哮聲、麥浪隆隆聲、農人吆喝聲、甩鞭聲、牛叫聲、婦女罵街聲、小孩叫聲、唱戲聲、鑼鼓聲、驢叫聲、豬哼哼聲,嗩吶聲、婚禮上的拜天地聲、壞笑聲、出殯途中的鞭炮聲、起起伏伏的哭聲、手扶拖拉機的馬達聲呼嘯而來,好像一路急行軍的暴風雪,從天上集體搬運到我們的耳朵里。是天籟,它們,在呼喚我們,數不盡的天籟啊!
遙遠了的,久違了的,落寞了的,重新撿回來的……這么龐大喧嚷的聲浪里,我聽見一只蟲子在呻吟,它,小小的,億億萬萬分之一,肯定睡著了,說著夢話,想著某一個人。
我的身子一震,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