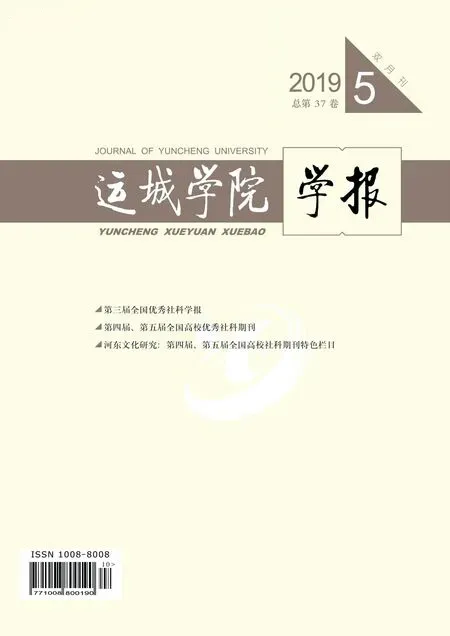從王維的畫史形象建構看文人畫的發展與演變
孫 麗 媛
(安徽大學 藝術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王維,字摩詰,以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其書畫特臻奇妙,尤其在其隱居輞川之后,體現著他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情趣的水墨畫,恬淡寧靜,清新宛麗,具有了更加鮮明的文人特色。但在以青綠山水占據主流地位的唐代并不為人所重視。宋代以后,其受到文人主體的大力追捧,直至明代一躍成為文人畫的精神領袖。王維在繪畫史上地位的升遷,究其原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伴隨著文人畫的興起而轉變的必然。其畫史地位的確立正是在時代審美趣尚的影響下逐漸發展形成的。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與文人畫的演變歷程趨于一致。正如貢布里希所指出的那樣:“整個藝術發展史不是技術熟練程度的發展史,而是觀念和要求的變化史。”[1]
一、唐:“偶被時人知”與文人畫的奠基期
在現存唐代畫史史料中,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和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分別對王維的繪畫創作做出了評價。唐朝以人物畫最為鼎盛,山水畫處于一個相對次要的地位,這在朱景玄的畫論中也有明顯的論斷:“夫畫者以人物居先,禽獸次之,山水次之,樓殿屋木次之”,[2]在朱景玄的畫品分類中位于“神品上”只以佛教人物畫最為稱頌的吳道子一人,這固然與其重視人物畫有關,但相比同時期山水畫創作的李思訓(神品下)來說,王維則被列為“妙品上”。朱景玄評價李思訓:“思訓格品高奇,山水絕妙,鳥獸草木,皆窮其態”,“通神之佳手也,國朝山水第一。”[2]其高度稱贊了李思訓的創作技藝,認為他的繪畫“皆窮其態”,可通神,也就是李思訓可以逼真地描繪自然造化的物態及神態,這里明顯是從山水畫創作的“形似”角度來談。畫論中關于王維的評述是“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復畫《輞川圖》,山谷郁盤,云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故庾右丞宅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2]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三個方面,第一,朱景玄認為王維的畫與吳道子風格相似,然而有自己獨特的風格特點,并且尤其指出其山水畫“意出塵外”,在他的畫面中意境體現出“畫外之意”;第二,朱認為王維畫作“怪”生筆端,并且評價王維‘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自負如此,明顯有不然之意;第三,指出王維畫山水并兼題記,由于王維詩人、畫家的雙重身份,在他的畫作里可能已經出現后來文人畫“詩畫一體”的影子。
與此同時,對后人影響更大的著作《歷代名畫記》中對道子、“二李”、王維等人也有評述“吳道玄者,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往往于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于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于吳,成于二李。”[3]“王維……工畫山水,體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于樸拙,復務細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壯。常自制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舍余習,偶被時人知。’誠哉是言也。余曾見破墨山水,筆跡勁爽。”[3]
與《唐朝名畫錄》一般,張彥遠對于吳道子和“二李”的山水畫成就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張彥遠同樣從“形似”角度談到王維的繪畫“復務細巧,翻更失真”,認為其在描繪自然形體的力度上還不足夠,畫面表現不盡人意以致失真;第二,張認為其繪畫筆力雄壯,這與朱對王維評價“蹤似吳生”保持一致;但與朱景玄不同的是,張肯定了王維“前身應畫師”的自稱,認為其誠哉是言也,這也是張彥遠對于王維畫作的一種肯定;最后,張指出了王維所創作的破墨山水畫,正如其所說,王維山水體涉今古,其破墨山水就指“今”,與“古”之青綠山水相較,并且對其筆跡作出評價,稱之“勁爽”。但是對于同樣使用潑墨技法的張璪,張彥遠給與的評價是“樹石之狀,妙于韋鷃,窮于張通”[3],其對于張璪的贊賞遠遠高于王維。由此,總體看來,王維在唐代山水畫的影響力較小,在唐代算不上是出色的畫家。
王維畫跡早已不存,但從當時人的評價來看,顯然王維的山水風格與當時盛唐氣象的自信與氣魄不甚契合,吳道子的天付勁毫,李思訓的金碧山水與當時唐代的主流審觀更相襯。這也是造成此時王維評價不高的一方面原因。另外,正如王維自己所稱“偶被時人知”可看出其畫作知名度于當時并不高。不過,從兩位評論家對他的評議“意出塵外”、“并兼題記”、“水墨山水”、“余習”等等可看出王維已具備與后世文人畫理想共同的思想基礎與審美情趣。為后世文人畫潮流的發展與興盛埋下了伏筆。
二、五代兩宋:“摩詰得之象外”與文人畫的發展期
至五代宋初,山水畫不斷發展已高度成熟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這時期,在不同繪畫審美觀念的主導下,王維的畫史地位一變從前,有了明顯的提高并呈現出不斷走高的趨勢。在荊浩的《筆法記》中這個跡象首當顯露出來,比起張、朱等人,荊浩更加重視水墨山水以及筆法、墨法的表現。所以對于唐人極度推崇的吳道子與李思訓,荊浩卻給予了另一番評價。其認為李思訓“理深思遠,筆跡甚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4],在荊浩的理論架構當中,“華”與“真”相對,其認為李思訓的青綠山水“華”而無“真”,且又大虧墨彩。其評價吳道子“筆盛于象,骨氣自高”,“亦恨無墨”[4],荊浩對于李、吳二人的評價在“無墨”上是趨于一致的。其畫論中評價王維則是“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4]此處,荊浩強調了王維畫作有筆有墨且特點趨于“宛麗”,并特別點出王維的作品氣韻高清,這種特點正是將文人的審美情趣融入進水墨畫的創作中所呈現出來的獨特藝術效果。此處,荊浩大贊王維,而對李、吳二人的評價則不然。這顯然與水墨山水畫逐漸取代青綠設色山水畫的趨勢分不開。與此相應,“筆”與“墨”在這里已經被賦予新的意義。陳傳席先生曾指出:“‘筆’與‘氣’相通,‘墨’與‘韻’相通”。[4]由此,荊浩認為王維的山水畫中筆墨與氣韻皆有,是一流的畫家。這一審美風格的轉變推動了山水畫“重韻”的發展。
到了宋代,士大夫階層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隆盛時代,文人畫的興起,使得王維在畫壇上備受推崇。其中關于王維最著名論述就是蘇軾的《題王維吳道子畫》中云:“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樊籠。”蘇軾認為吳道子的畫即使再妙,也只能以畫工稱之,而王維的畫則“象外有意”,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氣韻”,這是吳道子的畫中所缺失的,也就是說這是文人畫中所特有的。蘇軾在另一處說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5]蘇軾在這里明確地將士人畫與畫工畫進行了區分,“意”則是區別它們之間的關鍵點,與唐代“狀形”的審美觀不同,宋代文人更加重視“表意”的體現,文人畫不在于“形似”,而在于“象外之意”的表現與傳達。正是由于在這樣的審美風尚的籠罩之下,王維取代“畫圣”吳道子的地位也就不足為奇了。蘇軾在另一處評價王維“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5]此后,詩與畫的結合成為王維畫史上最重要的形象標簽,其中自然也沉淀著宋代文人對于繪畫的審美理想與審美情感,即“詩畫一律”的繪畫美學鑒賞觀。蘇軾的理論與觀點對后世產生了非常深厚的影響,有力地推動了文人畫潮流的發展。
《宣和畫譜》中對于王維的評價也是極盡贊賞之意,謂“至其卜筑罔川,亦在圖畫中,是其胸次所存,無適而不瀟灑,移志之于畫,過人宜矣……后來得其仿佛者,猶可以絕俗也。”[6]其認為王維的輞川圖是畫家胸內精神和人格的抒發與表現,畫中融入了畫家獨特的心境與情志,并以為這樣的畫可以絕俗。繪畫中最忌“俗氣”,與之相對應的就是“逸氣”,這更是中國文人畫魂的精髓。此后,至倪云林將這種繪畫審美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由此,王維在畫史地位上的提升與文人畫潮流的發展相輔相成,受到后世文人的極力追捧。
三、元、明:“文人之畫,自右丞始”與文人畫的鼎盛期
元代,王維尤其受到以畫壇領袖趙孟頫為代表的文人畫家的尊崇。其評價王維“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人圣而畫入神。自魏晉及唐凡三百年,惟君獨振。”[7]趙孟頫將王維已經推崇至無以復加的地步,一方面這與他主張力追“古意”的繪畫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元人對于王維的推崇從某些角度來說越過其繪畫創作本身而更多的是對于其超然世外的瀟灑態度以及人格文化內涵的標舉。元代由于異族統治,一系列的社會政治政策使得士人們失去進身之階,寒透了心的眾多士大夫放棄了對于國家民族的責任心,滋生了厭世和逃避的心理。而此時與他們具有相似人生際遇的王維,在遭遇政治劇變時寄情山水、放情林壑,其所展現出來的闊達與坦然的心境給予了元人精神上的慰藉。具有詩人、畫家雙重身份的王維成了文人畫家理想的人格范本。繪畫對于元代文人來說成為自我精神調節的一種手段,元人對于王維《輞川圖》的臨摹層出不窮,“輞川”日漸成為失意文人心目中的棲息之地。在這個圖本之上被賦予了一層強烈的象征意義,人們對它的推崇從而進入了形而上的精神層面。
湯垢在《古今畫鑒》中云:“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也。蓋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8]他在這里就重點強調了王維作為文人的“胸次”以及繪畫中所表現出來的“意境”,畫面“意境之至”正是其“胸次所存”,這是“庸史”,即職業畫工所難以達到的。其中體現出來的也正是元人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內蘊。在元代特殊的歷史語境當中,文人對于王維推崇的標準與因素與之前相比越來越趨向于復雜化。畫家的主體意識進一步被強化,其個人精神修養以及品格才情受到了更多的重視與強調。與此同時,文人士大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理想在創作中得到了更加突出的表現,賦予了文人畫發展的主要精神內涵。于此,文人畫在元代發展至成熟且引導著畫壇的主流方向,王維畫史地位的升遷也成為必然。
明代董其昌“文人畫”和“南北宗”論的出現一方面是宋元以來文人畫蓬勃發展的產物,反映了文人畫大發展以后的審美主流風尚,同時也標志著文人畫理論建構的最終確立。其在《畫旨》中云:“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一錘定音確立了王維在畫史上的地位。自宋元以來,隨著經濟中心的南移,藝術文化中心隨之也聚集于江浙一帶。南方的一批文人建立起來的繪畫審美觀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蘇東坡主張“平淡清新”、“蕭散簡遠”、“寄至味于淡泊”;黃庭堅倡導“參禪識畫”;米芾強調“平淡天真”、“意趣高古”。元四家、趙孟頫繼承的無一不是他們的審美觀。直至明代,這種審美理想在董其昌等人的論畫中也尤為明顯。陳繼儒提出:“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為宗,…所謂士夫畫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為宗,…所謂畫院畫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9]陳繼儒指出以王維為代表的南派繪畫筆墨較“文”,即使柔潤、松軟之意。而以李思訓為代表的北派繪畫筆墨則“硬”,即剛硬、勁動之意。同時期的沈顥對此的認識與其相似:“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構淳秀,出韻幽淡,為文人開山。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為行家建幢。”[10]其提出繪畫與禪宗一致分南北派,且氣運完全相對。正如南宗“頓悟”,北宗“漸修”一般,其著重強調了南派繪畫韻致悠淡,北派繪畫躁硬峭拔。南北派繪畫在藝術風格的表現上完全相異。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也提出:“南宗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勾斫之法”,[11]這種水墨渲染之法所表現出來的風格正是柔和秀潤的山水氣象,王維畫作“于山水平原尤工”、“氣韻高清”,表現出含蓄悠淡、瀟灑柔潤的藝術精神正與南宗文人繪畫的理想相一致。再者,王維好佛道,與禪宗信徒來往甚為親密,晚年更成為南宗禪信徒,在王維的畫面上自有一股空寂清凈的禪意表現。這也是董其昌等人極力所追求的精神狀態。所以,王維被選擇為南宗畫之主也就不足為奇了。董其昌等人南北宗論的提出以及王維畫史地位的確立正是歷代文人所推崇的審美觀以及文人典型審美趣尚的具體體現。其在復雜的歷史文化語境當中被賦予的精神品質正是文人所獨有的,同時也是文人潛意識里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至此,文人畫理論發展成熟得以確立形成,王維畫史形象與此相應建構完成。
四、結語
在大唐氣象以“二李”為主的青綠山水和雄壯豪放的吳道子山水占據主流,王維的水墨山水創作不受重視,但其所具備的種種審美旨趣為文人畫的發展埋下伏筆,文人畫在唐代已隱隱生根發芽。宋代隨著士大夫階層的興起,王維的水墨山水受到重視,文人畫潮流蓬勃發展,成為其畫史地位形象的轉折期。元明文人畫占據畫壇主導地位,由于王維諸多條件符合了文人畫家的最高精神追求,以至于被董其昌推舉為南宗山水畫之主。王維于唐代“偶被時人知”到明代“文人之畫,自右丞始”的畫史地位升遷,見證了不同時代背景審美觀念下文人畫潮流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