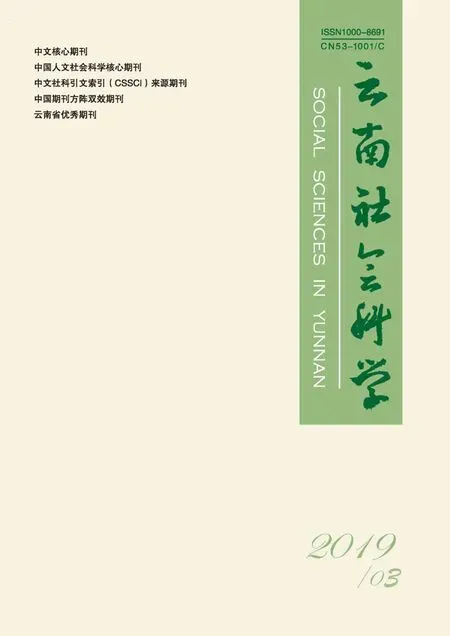陶令不知何處去
——評述斯科特的贊米亞研究
鄭 鵬
一、引 言
著名歷史學宗布羅代爾曾批評道:“長期以來,歷史學家總是對平原流連忘返,而不愿意進入附近的高山。”①[法]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龍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9-21頁。與歷史學家不同,山地是人類學家時常光顧的田野。晚年費孝通行行重行行,武夷山、南嶺、涼山、武陵山等南方山區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將族群性與空間的視角貫穿于“富民”的社會問題之中,進而提問:“什么叫山區?它同平原有什么不同?為什么山區同少數民族老是纏在一起?”他還提醒后來者,少數民族上山、下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靠一句話是解釋不通的”。②費孝通:《費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0-514頁。
令人驚奇的是,另外一位在山地的人類學家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就是斯科特。借助人類學的腳步與歷史學的目光,斯科特突破了以民族國家為“歷史研究的單位”的偏執與線性文明進化論的偏狹,站在高地追問“文明緣何不上山”?這個問題承襲于布羅代爾和恩格斯。布羅代爾啟發了山地研究的認識論。正如他的論述:“山通常是遠離文明的世界……在橫的方向,這些潮流能擴展到很遠的地方,但在縱的方向,面對一道數百米高的障礙,它們就無能為力了。”③[法]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31頁。恩格斯提供了山地研究的本體論反思。恩格斯追尋國家的起源,解構了國家的文化霸權。他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況”④[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頁。,意味著國家攫取了文明的定義權,因為“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⑤[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90頁。。因之,如果考慮與山林“等量齊觀”的江河湖泊以及更廣大的海洋,那么,斯科特問題的本質就是——“國家之外無文明”?
為了使問題被解釋得通。斯科特從馬來西亞轉戰到了一個被稱為“贊米亞”的山地。在“贊米亞”的圖繪中,“人類學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密切關系”①[美]格雷伯:《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頁。終于被斯科特推向極致。他從國家中心主義的政治學轄域中逃逸出來,對德勒茲式差異、游耕、解轄域化的后現代政治學做出了歷史學與人類學詮釋。斯科特敏銳地洞察到山地垂直效應與那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山地居民的能動性之間的親和關系。所以,如果說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中建議人們嘗試著審視國家建設中的種種極端,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弱者的武器》中展示了日常政治及反抗的日常形式,那么,《逃避統治的藝術》②該書的英文標題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斯科特賦予了它兩層意涵:一是避免被統合入國家體制;二是防止山地社會內部形成國家體制。中譯本標題表現了“逃”是免遭統治的關鍵武器,它是“不被統治的藝術”得以展開的前提。日譯本《ゾミア―― 脫國家の世界史》(2013)(直譯為《贊米亞:逃離國家的歷史》),也將“逃”作為關鍵詞。“逃”字可以追溯到費孝通的觀察。他曾指出,面對封建壓迫,少數民族只有兩條路或兩個字:走,死。要生存就要走到更偏遠的地方去,苗族、瑤族靠兩條腿一直走到了泰國、東南亞等地區。參見費孝通:《費孝通全集》(第13卷),第512頁。(Seeing Like a Refugee)一書則將反抗形式升級為逃離國家的統治,并且論證了底層依托作為非國家空間的山地而應對國家建設的正當性與可行性。
正如杜贊奇的溢美之詞,《逃避統治的藝術》“可能是迄今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將對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評并指出其中可資借鑒之處。首先,本文討論“贊米亞”的方法論意義。其次,對斯科特為贊米亞研究設定的主題——非國家空間的再生產(正當性與可行性)進行論述。最后討論贊米亞研究的學術意義與現實關懷。
二、作為方法的“贊米亞”:邊緣、鏡像與書寫單位
我要闡明,贊米亞絕對有資格成為地區。③《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明實錄藏族史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3-554頁。
通過對“歷史的地理基礎”的大篇幅論述,黑格爾歸納出山、水差異地理學的政治效應:“結合一切的,再也沒有比水更為重要的了,因為國家不過是河川流注的區域……只有山脈才是分隔的。”④[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92頁。山地的分隔性所導致的結果被古代中國政治地理學家總結為“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⑤《禮記·王制》。。贊米亞,便是一個被高山分隔的碎片區域。
贊米亞的空間,最早由荷蘭學者申德爾構建。隨后,讓·米肖追蹤了它的空間范圍。贊米亞指稱著從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東北部地區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橫括9個民族國家或地區,共計250萬平方公里居住著1億少數族群的區域。其中,山地居民約800-1000萬人,族群類型以百計,語系至少有5種。山地生態景觀表現出了多樣性,多元、多變的語言、服飾、生計、居住方式、族群認同、社會結構以及宗教活動,如馬賽克一般,讓民族學家、歷史學家陷入困惑。因此,學者們在“贊米亞”的研究進路,如同贊米亞碎裂的地理/文化景觀,往往是“分散和相互隔絕的”。雖然關于贊米亞內部各地區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但它們只是“在贊米亞做研究”而非“贊米亞研究”,未能構筑出針對整個區域的社會科學的新視角。
實際上,當谷地國家忙于構建整齊劃一的社會景觀時,“山地”則不斷生產著差異性和邊緣性,這賦予了山地居民的共通文化與歷史。鑒于此,針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贊米亞狀態,斯科特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嘗試著提煉新的空間結構。
贊米亞被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地區,不是因為政治上的聯合,這根本不存在。其相似的模式在于其多樣的山地農業、分散的居住和遷徙,以及貧困的平均主義,與此相關,這里的婦女地位比谷地婦女地位高。⑥[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21頁。
贊米亞地處低地國家中心的邊緣,從而保持著“與國家相對的位置”。這種自主性產生了顯著的空間政治效應——即“其相對的無國家性”。因此,贊米亞不僅僅是一個區域研究的對象,更具有著方法論的價值。
第一,就贊米亞區域內部的社會結構而言,贊米亞研究的主旨是摒除國家中心主義,在“中心—邊緣”模式中賦予邊緣自主性。如此,需要改變“中心”到“邊緣”這種從上至下的線性思維,找出其中的斷裂與不連續性。實際上,中國研究的變遷,疊寫著類似的學術史轉向。如果以費孝通、林耀華作為漢族社會人類學研究的起始,那么,以地域化的宗族結構為中心、依據弗里德曼模式構建起來的華南研究可以稱得上第二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后,國外學者重返中國田野。與前兩階段執著于整體中國的歸納不同,這一時期的研究立足于鄉土中國的邊緣,志于尋求中國文化中的差異性。研究者認識到類型中國僅僅是漢人的單一族群投射,非漢人族群成為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一把鑰匙。于是,少數族群聚集的中國西南成了學術的新增長點。正如華南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大衛所言:“我感覺到不能一輩子只研究華南,我的出發點是去了解中國社會。研究華南是其中必經之路,但不是終點。從理性方面來想,也知道現在是需要擴大研究范圍的時候。”①華南研究會:《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年,第29頁。相應地,從《想象的共同體》開始,東南亞研究的轉向也大體循此軌跡。何況,中國西南本身就是被劃入了贊米亞的田野空間。
贊米亞的研究旨趣在于重建邊緣的自主性與邊緣人的能動性。作為一個“逃亡帶”,贊米亞的形成“歸功于”中華帝國的超前擴張,又被東南亞碩果僅存的低地王國強化。為了逃避國家的統合,山地居民從平原遷徙到低山地,又將更早的山地居民擠上高山。上山的人們并沒有“移植”平原谷地的文明,否則山地最終不過是低地社會結構的復制品。因此,如果簡單地以低地社會結構來框限贊米亞,或者以天下觀、華夷秩序來審視贊米亞,贊米亞社會景觀的異質性與多元性便一直“躲藏”在國家歷史的陰影下。
實然,贊米亞并非“文明-野蠻”“發達-欠發達”的二元結構中被壓制與放逐的他者。在贊米亞山地所呈現的族群垂直分布模式中,每一層生態區都是山地族群精心設計以適宜山地生態與抵制國家擴張的結果。宗教、文化與族群性的認同,是自主選擇的邊界形成機制,旨在強化政治與社會差異。因此,逃亡的底層如何與山地的特殊地理環境相契合,以此生產和再生產非國家空間;它得以運行的物質與文化條件是什么;它內部的結構關系,都可以是單獨的課題。
第二,山地社會是國家的反身物,構成了平原谷地國家的反寫的“鏡中我”。討論國家建設的文獻貫穿著從中心到邊緣的平滑連續性的思維與等待歸化的國家中心主義隱喻。但它鮮有關注逆向的去國家化與非國家性歷史。所以,斯科特指出,剖析山地社會的形成史,就是在透視國家建設的內在邏輯。
同時,山地與谷地之間保持著持久的共生關系。山地與谷地構成了互補的農業生態位。更重要的是,山地擁有一些價值量極高的產品,例如礦物、胡椒、稀有木材等。事實上,“谷地的政治實體,特別是小政權都被固定在特定的區域,嚴重依賴山地貿易,對他們來說,山地貿易伙伴的背叛是一個嚴重威脅”②[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127頁。。
最激烈的空間競爭是人力資源的爭奪。山地居民在不久前還是谷地國家的臣民,卻沿著“逃亡走廊”進入山地。在新的生態環境中,他們策略性地改變了生計方式、社會結構、文化譜系,據此靈活地調整他們與國家的距離。所謂調整,實質是理性地對“進化序列”的再抉擇。進化序列由“采集漁獵/游耕-農耕/灌溉稻作”“人口與社會結構的分散與縮減-強制定居”“無文字-書寫譜系”的遞進關系組成。在國家的文明化框架里,前者構成了未開化的指標體系,后者則處于文明金字塔的頂端。然而,山地居民有針對性地解構國家文明、撤回到前者。流動、自然與社會景觀的雜亂無章、社會組織的高度彈性與去中心性,讓國家無法對山地空間“提綱挈領”。游耕或采集漁獵的生計方式極大地增加了國家征用的成本,對國家財政而言幾乎沒有價值。如此一來,山地成為了耗噬國家財政人口的黑洞。于是,在國家建設的財政邏輯之下,“只有不斷清洗其邊陲地區,不斷成長的水稻國家才能實現人口集聚的目標,從而才能統治和保衛其核心區”③[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99頁。。由此,可以確認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建立在人口控制技術的基礎之上,衡量國家能力的關鍵指標是在一個合理的統治空間內所吸引和控制的定居人口數量,領土則沒有人口同等的重要性。
第三,“沒有歷史的人”與書寫單位的重構。自19世紀開始,歷史學家致力于打造民族國家起源與成長的腳本。以民族國家為書寫單位成為歷史學家的習慣性窠臼。書寫使用了排除和納入的雙重機制。那些對民族國家的形成產生影響的個人和群體及其經歷被納入歷史,而那些處于民族國家建設邊緣的人群則被排除在歷史學家的視野之外,變成了埃里克·沃爾夫筆下“沒有歷史的人民”。對此,在吸收湯因比文明史與布羅代爾區域史的經驗基礎上,斯科特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將贊米亞視為一個超國家空間的文化有機體。
贊米亞概念是要探索一個新的“地區研究”,在這里,劃定區域的理由并非基于民族國家的邊界(比如老撾),也不是一個戰略性概念(如東南亞),而是基于特定生態規律和結構關系,這些都會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如果走運的話,“贊米亞研究”的例子將可以激勵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追隨這樣的實驗并不斷完善。①[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31頁。
贊米亞是“所剩無幾”的一個透視非國家空間的窗口。贊米亞研究的實驗意義在于,它將長期以來被國家的光環壓制在陰影之中的“非國家空間”納入書寫的主體范疇。然而,重建“非國家空間”的歷史總是困難重重。一方面,多元的歷史主體往往在制作國家連續性正統的神話過程中被削足適履。正如無國家的人很難被納入到雇傭勞動或定居農業這樣具有財政清晰性的經濟中那樣,非國家空間也不會被納入到國家歷史的書寫系統之中。另一方面,文明化的趨中性表達,將中央文明描述得充滿文化和社會吸引力,加入中心文化圈被認為是一個進化與上升的過程。這種文明敘事會極力掩蓋逃亡,或者將從中心逃亡到邊陲的人們扭曲為土著的蠻夷。他們往往被抽象為統計數據,很少作為歷史的行動者出現。
然而,所謂“無歷史的族群”并非處于時間之外。斯科特在開篇處引用了克拉斯特的論斷,認為無歷史的族群的歷史就是反抗國家的歷史,實際上,族群有多少歷史是主動選擇的結果,是為了確定自己與強大的、有文字的鄰居的位置關系,也為隨時逃離國家時能夠輕裝前行。山地居民有著多重的歷史,可以根據環境的不同任選一種或者組合使用。他們可以像阿卡人一樣創造出悠久和精細的系譜,也可以像傈僳人和克欽人一樣,只有最短的譜系和移民的歷史。
為了打破國家主義敘事框架的偏頗,考察山地歷史的變遷,斯科特倡導“深度史學”(Deep History)。通過閱讀東南亞史,斯科特“吃驚地發現自己已經差不多成為歷史學家”。漫長的東南亞史,實際上長期為無國家狀態主導,因而要用東南亞的真實歷史來代替“帝國的想象”。對于無文字的山地社會,人類學有助于重建山地居民的社會結構。當然,這必須摒除線性進化論預設的偏狹。斯科特堅信“文字的劣勢以及口述的優勢”。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口述文化,成為了贊米亞田野調查的重要內容。正是口述而來的詩、傳說、依據情勢而編造的族譜,可以讓山地居民靈活地調整族群認同與聯盟。贊米亞田野過程中,斯科特盡力給予了山地居民更多的直接出場機會。
三、非國家空間的再生產:流動性、空間阻力與結構性轉化
山地居民被污名化的那些特征正是那些逃避國家的人群所提倡和完善的特征,這些特征使他們避免放棄自主權。②[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420頁。
斯科特直言“貫穿我這本著作始終的邏輯將從根本上顛覆上述邏輯。”③[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11頁。這種邏輯即在社會進化論的話語體系下,將國家統治狀態與文明、將自我治理的人民與原始狀態相混淆。這種邏輯的展開就是將贊米亞山地居民描述為“社會進化的活化石”或者是被文明遺棄的人。為此,斯科特擔任起了為贊米亞山地居民去污名化的使命,將非國家空間的正當性與可行性設定為贊米亞的研究主題。斯科特的主要觀點是,山地居民是為了逃避國家而“有意的野蠻”(Barbarians by Design),只有在“與國家相對立的位置”,才能夠更正理解山地居民的歷史。正如他所言,“山地人的歷史最好不要理解為古老過去的殘留,而是低地國家政權建設中‘逃亡’的歷史。”①[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28頁。
為了賦予非國家空間的正當性,斯科特將論述重點放在非國家空間何以可能的問題之上。如果能夠揭示贊米亞山地社會無需國家便能夠正常運轉,那么,山地社會就并非是社會進化的低端,而是為了保持自主性而精心設計的社會景觀。在這里,斯科特將非國家空間再生產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項:
(一)流動性與“無處不在的逃亡”
古代中國流行的政治思想一直就視民為“水”。它反映了人民所具有的流動性本質屬性。“流民”的稱謂,正是人民流動性屬性的表現。流動性恰恰是人民面對國家建設時的能動性反應與構成這種反應的基礎。作為流動性的政治表達,以逃離為反抗,其實是一種理性選擇。“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早已對“逃離”做出了高度評價。逃離作為“上計”一直被底層人民施展。作為底層人最早的“口述史”,在《詩經》中,人民對君主“嗇且逼急,不務廣修德于民”②李學勤:《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60頁。深惡痛絕,以至視君為碩鼠,竟提出“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的反抗方案。最終,“境內小民紛紛逃散。不久國亦旋亡”③朱熹集傳、方玉潤評:《詩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3頁。。這種反抗行動被人民賦予了正當性,因為“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王風·兔爰》)。“詩經時代”之后仍有“士民亡竄山谷”的大量記載,到了清代依舊有人攜挈妻孥,風餐露宿而去,視瘼鄉如樂土。④江立華等:《中國流民史(古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這不正好回答了斯皮瓦克“底層人能說話嗎”的命題或如斯科特般“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嗎?
然而,若將“不流動”的結果去歷史化為“社會事實”,則難以理解“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不僅是底層的控訴,更是日常政治的實踐。在這里,斯科特筆下東南亞底層與中國古代人民的行動邏輯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東南亞的證據表明,“無論是現在(殖民時代)還是以前,農民生活的主旋律是移動而非固定”⑤[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172頁。包括水稻種植者在內的東南亞人口,遷移是他們的常態而非特例,這與原有“穩定地植根于某地的農民家庭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一旦“拾得”底層流動性的假設,逃離國家就有了發生學的機制。斯科特認為,底層逃離國家空間主要由兩種原因驅動:逃避國家空間的賦役和擁擠,這在斯科特的論著中有詳細論述,在此不贅述。
(二)空間阻力與“山地公共避難地”
何處是歸程?逃亡的歸宿是理性抉擇的結果,雖然此后他們便很難逃脫“野蠻”的標簽。正如斯科特所言:
最普遍的做法是逃避為皇家服務,轉而也成為競爭人力的某一個名人或宗教權威的附屬,這是最麻煩的方法。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另外的選擇就是轉到臨近的另外一個低地王國。此外還有一種選擇則是遷移出國家的勢力范圍,逃逸到內地和/或山地。⑥[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175頁。
為何選擇山地作為逃難之地呢?其重要原因就是山地的空間阻力。山地的崎嶇地形使國家的腳步無法進入,山地密布的叢林與籠罩的瘴氣導致國家的權力觸角無法深入其中。增加空間阻力的地形還包括濕地、沼澤、沙漠、紅樹林等。在壓縮空間的技術發明之前,權力的布局不得不繞開這類區域。即便是國家偶爾的軍事征服,最終由于補給線和交通線的斷裂而無法持久地控制這些區域。所以,“最陡峭的地區是自由的庇護所”。隱蔽的山地堡壘,對于山民而言是有利于隱藏和逃跑的地理環境,對于國家而言卻是迷宮般難以習得的地理知識。因此,空間阻力作用下的國家隔離帶,維護了山地居民的政治自主性。
贊米亞就是這樣的“公共逃難地”。每當中央帝國或低地國家擴展國家空間時,首先會激發底層短暫的反叛,最后那些被國家建設擠出的人口沿著“逃亡走廊”,撤退到贊米亞。逃亡高地的人群根據各自的族群競爭力,占據不同的生態位,形成一種齒輪效應,使山地依據海拔高度而形成多樣化的族群性垂直帶譜。
(三)結構性轉化:山地的生計、社會組織與族群認同
拉鐵摩爾曾經觀察到,人們日漸放棄農業資源的利用而專力發展牧畜資源,結果使得亞洲內地的邊疆從“半草原”發展到整個的草原化。①[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頁。在國家的進化序列中,從農耕轉入游牧,或游耕-采集漁獵,是一種文明的退化。然而,斯科特堅持強調歷史和策略選擇的作用。逃亡的人群以不被統治為目標,以將自身置于與低地國家相對立的位置為原則,在贊米亞山地生態中“自我蠻夷化”,從生計方式、社會組織、文化形態等方面進行結構性轉化。
贊米亞山地居民的結構性轉化——社會結構和日常生存策略的政治抉擇——揭示了“非國家空間”再生產或者何以可能的問題。
1.生計轉換:游耕與山地作物
重回自主的生存狀態,首先需要替代生計的支撐。斯科特詳細地考證出來山地居民的農業技術選擇過程。以往,灌溉稻作被認為是高效的農作方式,而游耕則是低效的。斯科特指出,相對效率測評需要考慮要素稟賦與農業生態條件。灌溉稻作的高效率是人多地少的農業生態條件下對單位土地面積產出標準的結論。但是,對于長期地廣人稀的東南亞山地而言,游耕能夠節約勞動力而使單位勞動力產出最大化。當然,山地居民的農業技術選擇不只是經濟邏輯,最重要的是政治邏輯。因為游耕內在地抵制國家征稅并增強山地居民的流動性。所以,斯科特稱游耕是“逃避農業”,并認為:“游耕有兩個優勢:它使人們相對自主和自由,以及允許農民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和享用勞動成果。二者的核心都是政治優勢。”②[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236頁。
一些特殊的山地作物增強了游耕的優勢,它們就成為了山地居民的“逃避作物”。逃避作物有廣泛的清單,包括山藥、馬鈴薯、紅薯、木薯、玉米等。15世紀引進的美洲作物有力地支持了底層向高地撤離。如果僅僅依靠東南亞本地的旱稻,山地居民會被限制在海拔900到1000米的地帶內;玉米則讓他們可以向上再逃300米。可見,逃避農業與逃避作物,擴展了非國家空間。
2.社會重組:裂變的結構
斯科特指出:“社會結構不應該被看作特定社區的持久社會特點,而應看作一個變量,其目的之一就是調整與周邊權力區域的關系。”③[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254頁。與農業技術的政治選擇一樣,社會結構也具有抵制監控與從屬的政治功能。國家偏好穩定、可靠、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任何一個試圖控制贊米亞地區的政權,都必須找到一個可以打交道的權威,如果找不到就要創造一個這樣的權威。為了避免被統合,贊米亞山地居民像水母一樣,裂變為更小、更分散的社會單位,直到數個家庭無首領的聚合。裂變使政權只能面對一個無組織、無結構的人群,從而失去了政權建設的支撐點。
3.族群認同:情境主義的實踐
山地的族群認同是多元的,認同的表達被特定的社會情境所誘發,像變色龍那樣隨著背景變化而改變顏色,也即群體間的界限可以相互滲透,身份認同靈活多變。斯科特質疑了關于族群認同的“原生論”與“文化論”,指出了這種情境主義的族群認同背后的邏輯“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政治手段”,用來調節與國家的關系。④[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302-348頁。贊米亞山地居民的族群認同最本質的特征被斯科特稱之為“反國家的民族主義”。它既排斥國家(使國家的統合難以進行),又防御國家(使得社會難以從內部發展出等級化的社會結構)。而山地的口述文化則為認同系譜的制作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間。在口述文化中,每一次講述都反映當時的利益、權力關系和周邊社會的親屬結構。口述為山地居民提供了靈活多變的族群認同的可能性。相反,如果通過書寫來傳承系譜,那么山地居民的適應性會大打折扣。
四、討論:山地政治學、斯科特議題與“贊米亞后傳”
我在這里試圖描繪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對于我們所有的讀者來說,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看起來距離非常遙遠。在當今世界,我們未來的自由依賴于馴化利維坦式國家,而非逃避它,這個任務讓人望而生畏。①[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404頁。
非國家空間的不被整合性,是斯科特贊米亞研究結論的核心要點。由此出發,斯科特的貢獻不僅在于把空間環境要素帶入政治與人類學的研究視域,更重要的是他將被國家史觀剝奪的底層能動性重新賦予給他們,從而得以全面地總結山地族群去國家化的策略組合。當然,高度自主性的山地居民不免讓評論人使用“高貴的野蠻人”的套路進行批判性話語分析。斯科特在書中聲明:“我經常被指責為是錯誤的,但很少被指責為含糊不清或晦澀難懂的。”②[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4頁。斯科特思想的張力與想象力,足以讓更多的“山地式”學人站在更高處繼續前行。
(一)山地政治學
研究非國家社會原本就是人類學的長項。但斯科特并沒有停留于靜態地對贊米亞進行功能論的民族志構畫。斯科特超越了人類學關于非國家社會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山地政治學的“去”國家研究范式。
山地政治是國家建設的反身物。山地社會去國家化的歷史過程包括兩個維度:排斥國家(使國家難以征服和統合,難以加以控制,難以財政征用);防御國家(使得社會難以從內部發展出一個穩定的等級結構)。山地社會的去國家過程得到了三項技術的支持:一是流動性與地點的選擇(逃得越高,空間阻力越大,國家的權力觸角就越難俘獲);二是社會結構的規模與分散程度(社會組織結構越是具有裂變與聚合的彈性,就越有調節與國家距離的能力);三是生計技術的調整(增強自身的流動性與降低國家的征用性)。
在構建了山地政治的理論框架之后,斯科特將“去國家化”的歷史過程植入具體的空間結構之中。在分析層面上,自然生態地理的政治社會效應成為發掘的重點。空間阻力、山地垂直帶譜的生計效應、山地垂直族群景觀分布、山地垂直生態位都是理論構建的基石。山地為贊米亞難民、山民提供了逃避國家統治的政治掩體;不被國家統治的技術組合是基于山地生態環境的精心發明,表現出了一種選擇性親和。正是在山地空間的政治隔離帶的作用下,山地民既有能力選擇與國家發生交換關系,又不會喪失他們更為珍惜的政治自主性。
(二)斯科特議題
斯科特對贊米亞的研究成果可謂是一串璀璨奪目的珍珠。人們可以從贊米亞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與視角中獲得啟示,除了前文已經涉及的議題,還可以從中采擷出一些可以拓展的議題。
1.山上住著野人,還是神仙?
山上是否有文明,山地居民是否是被社會進化序列所遺棄的野蠻人,是斯科特理論構建的主要關懷。該議題針對于布羅代爾關于文明不上山的論斷。斯科特指出,有關文明的想象需要一個野蠻的未經馴化的對應物,它們往往處于其勢力范圍之外,并最終被馴服和統合。可見,關于文明的議題,印證了恩格斯的論斷。所以,在全書的結尾處,斯科特尖銳地提出,“如果用‘國家臣民’來代替‘文明的’,用‘非國家臣民’來替代‘不文明的’,那就差不多對了”。③[美]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第421頁。
山地族群被污名化的根本原因不過是他們堅持身處國家空間之外而已。而這些污名實指,其實是“自我野蠻化”,是那些逃避國家的人群在山地精心設計出來的技術操作。所以,斯科特指出,山地居民并非低地國家所想象的進化之前,而應該被理解為之“后”,后灌溉水稻、后定居、后臣民。“后”的政治效應表現為山地居民擁有低地國家臣民喪失的自主性。
2.國家構建的財政邏輯④進一步討論參見拙文《財政空間的生產:“山川林澤”與國家構建的財政邏輯》,《求索》2019年第1期。
正如斯科特所言,山地社會與低地國家是一對黑暗雙生子。透過山地社會的窗口也可以看到“鏡像”中的國家。低地國家的建設核心是將人口集中治理技術可行的核心區域。人力與谷物是國家財政汲取的主要對象。如此,奴隸制與水稻生產都是技術發展的關鍵里程。斯科特發明了一個核心概念國家建設的邏輯——國家可獲得生產總值(SAP)。
3.國家景觀的制作⑤進一步討論參見拙文《國家景觀的制作》,《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8年第2期。
稻田,意味著被適當組織起來的臣民和他們的產品所形成的文明景觀。“國家景觀”的概念承襲了《國家的視角》一書中的思路。與水稻國家景觀對應的是繁雜的山地景觀。采集、游耕、山地作物所構成的景觀,不合適國家征收,因而被認為是不文明和野蠻的。所以,景觀的國家性(stateness),即適合國家征收的農業景觀,成為了判斷文明程度的坐標。
4.農作的政治性
作物構成與配置、種植方式等看似技術中性,實際上在山地與低地產生了不同的政治效應。逃避農業與灌溉稻作、山地作物與谷物相對。后者與國家及其征收相親和,而前者則增強了山地居民的流動性。除了征收性之外,灌溉稻作的農藝特性,在時節周期上促進了社會景觀一致性,增強了社會結構的整合性。而分散與多樣的山地作物,則很少需要社會合作,因而也就內在地抵制著等級化的社會結構生成。
以上只是對斯科特議題清單的簡要列舉。正如斯科特期待用海上贊米亞及江河湖泊逃難所的研究,來拓展非國家空間邊界那樣,這個清單還可以不斷地延長。
(三)“贊米亞后傳”
人類學家的田野分布在那些國家不在場而人們自治的空間。由此,人類學家或多或少做出了一種民粹主義的承諾,他們從那些正在與資本或權力相抗衡的人群中獲得某種完全不同的實踐和形式。然后,他們期待著以此在現代社會的大勢中獲得改善的可能性。贊米亞的故事鮮明地重申了人類學的承諾。即便斯科特關于贊米亞的研究內容保持了程序的價值中立,他的選題鮮明地體現了他的價值立場。然而,在描寫贊米亞地區長期以來的不被整合性的同時,他非常清楚,“在這本書中所說的一切對‘二戰’以后的時期不適用。”
從19世紀開始,在國家之外生活第一次成為不切實際。如此,國家緣何上山(國家建設的垂直維度)以及被國家整合后的山地社會變遷,作為“贊米亞后傳”的研究內容,或許可以成為學術增長點。①進一步的討論參見拙文《禁山后國家緣何上山》,《社會發展研究》 2018年第3期。面對“大勢所趨”與“避而不談”,何處安置作為非國家空間的贊米亞山地研究的現實關懷呢?曾經長期存在的國家之外的生活機會選擇與歷史便被遺忘。這對學術研究造成了慣性。例如在華南研究模式中,了解一個地區的社會模式的慣性問題就是:“第一,這個地方什么時候歸納在國家的范圍?第二,歸納到國家范疇的時候,雙方應用什么辦法?”可能,科大偉提出“告別華南研究”的原因也在于此。②華南研究會:《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創造出版社,2004年,第29頁。因此,王銘銘提出了尋找東南與西南兩大“學術區”之間紐帶的呼吁。③王銘銘:《東南與西南》,《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4期。除了學術導向之外,就現實關懷而言,贊米亞山地展示了另類的生存智慧。“群山造差異”。斯科特在文中明確地引用的德勒茲“千高原”的論述。顯然,贊米亞山地居民的“游牧政治”是差異地理學與建基于流動性之上的底層能動性的復合作用的結果。如果將贊米亞山地居民視為德勒茲筆下的游牧戰士,那就“不要將這種游牧主義設想為原初狀態,而應將它看作慣于定居的群體突然發起的一次冒險,這些定居群體為一種移動魅力、一種外向性魅力所推動。”④德勒茲:《游牧政治》,載王明安等主編:《尼采的幽靈》,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66頁。可見,逃入山地是躲避國家編碼的解轄域化冒險,所生成的逃逸線預示著山地生活的自主性。
福柯曾言,古希臘以來一直存在著生存美學,“一種努力使生活藝術化”的實踐智慧。⑤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44頁。贊米亞山地居民不被統治的藝術何嘗不是一種生存美學。山地居民不關懷普遍性的歷史主體,也不謀求對自然與社會關系的統治地位。他們的生存美學不僅是“關懷自身”,更導向族群的自主性與生活的多樣性。即彼即此。
對于身處“后贊米亞時代”的我們,仍舊存在逃避新自由主義與極端現代性霸權的張力。高山上的烏托邦固然寄托著“高貴的野蠻人”的遐思。不過,一旦山地社會呈現出一種歷史的可能性,或許它可以成為身處文明社會的我們的一副解毒劑。執此,如何謹慎地在國家與社會框架之下守護差異,增強社會的自主性與自組織能力,應該成為“山地式”學人的新使命。⑥“山地式”學人的論述借鑒了葉敬忠教授在“農政與發展”論壇上對斯科特演講的評述。(致謝: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斯科特作品的中譯者王曉毅研究員與筆者的多次交談,使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