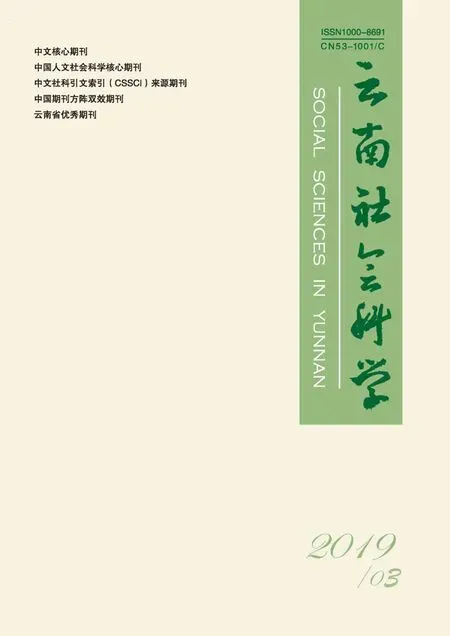中古胡姓郡望的成立與民族融合
龍成松
依托于門閥士族問題,郡望一直是中古史研究的老話題。正如毛漢光先生所指出那樣:“士族乃具有時間縱度的血緣單位,其強調郡望以別于他族,猶如一家老商店強調其金字招牌一般,故郡望與士族相始終。”①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38頁。隨著新出墓志的涌現,相關研究呈現出了新的生機,其中有兩個趨勢值得重視:一是“務實”的研究,挖掘郡望發育、生長和衰亡的譜系②這可以美國漢學家譚凱(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為代表,原著2014年由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由胡耀飛、謝宇榮翻譯,后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是“務虛”的研究,鉤沉郡望制作、偽冒和攀附的痕跡③這可以仇鹿鳴《制作郡望:中古南陽張氏的形成》一文為代表,在文中他提出一個綱領性的問題:“郡望與譜系是中古時代重要的知識資源,但這種知識如何傳播、流布,士人如何習得這種知識,進而加以利用、改造,將其作為冒入甚至制作郡望的一種手段,通過對祖先記憶的重構,謀取高貴的社會身份乃至背后的政治、經濟利益,這是本文通過對張氏諸望的檢討所欲回答的問題。”(《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二者都得益于新出墓志積累的大量郡望數據。早前的研究和最新的動向,所關注的重點都是郡望與漢人士族的關系,而較少注意到郡望與非漢人家族(胡姓家族)的關系。事實上,在中古胡、漢共同體背景下,胡姓郡望的發育、成長和衰亡,除了具有一般意義上的士族發展規律意義外,還具有族群認同和民族融合的意義,因而值得深入發掘。陳寅恪的“關隴本位政策”已將郡望問題作為宇文泰聚合胡、漢的一個關鍵要素提出來,并給予了濃墨重彩的描述,沿著他的思路,還可以進一步拓展。通過改造郡望來調整胡、漢關系,其淵源為孝文帝遷洛之后的一系列改制。胡、漢郡望整合是中古胡、漢共同體社會形成的一個重要元素,是中古民族融合宏大敘事的題中之義。
一、胡姓郡望的成立過程
胡姓郡望的成立,需要放到中古這一長時段來觀察方才有意義。范兆飛指出:“中古郡望的成立,源于兩個因素的有機結合:一是地域主義的形成,二是家族主義的確立。魏晉之際華夏帝國崩潰,國家權威的影響有所減弱,而象征社會勢力的家族主義和地方主義卻呈現出分庭抗禮之勢。郡望由此突破地域的概念,成為士族門第的名片和護身符,其形成確立乃至式微濫用的歷史過程,見證了中古士族政治社會的成立和崩潰。”①范兆飛:《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以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為中心》,《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 5 期。在郡望成立之階段,“地域”和“家族”是郡望的兩個維度,延伸至對于地方社會、文化資源的“壟斷”,而且形成了維系這一局面的各種“文本”,比如譜牒、譜志。在郡望崩潰之際,郡望與著籍發生分離,郡望僅僅成為一個符號,偽冒的現象嚴重,這一“實”一“虛”兩條線,也是理解胡姓郡望成立過程的起點。下面分為兩個時段來觀察。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
胡姓部族或家族源出華夏邊緣,原本無漢人郡望或籍貫之說,內遷之后,改漢姓,占籍各地,逐漸以郡望自高。占籍與郡望本為一義,因人口的遷徙、分支的繁衍、同姓的攀附和偽冒的出現,遂別為二②參考岑仲勉《唐史余瀋》卷四“唐史中的望與貫”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29-233頁。。郡望在各個時代并不是穩定的,有升沉流變,其地域分布也不平衡。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少數部族內遷的高潮時期,也是胡姓郡望發育時期。這一時期的郡望郡姓并沒有像唐代氏族志(郡望表)一類資料可以利用。胡阿祥先生根據相關史料和郡望、郡姓的標準,整理出《兩晉南北朝時期郡望郡姓分區對照表》,得98郡281郡姓,其中包括十六國及北朝的胡姓郡望:西平源氏,隴西乞伏氏,略陽苻氏、呂氏,南安姚氏,臨松沮渠氏,敦煌令狐氏,河東薛氏,上黨石氏,新興劉氏、赫連氏,北秀容爾朱氏,廣牧斛斯氏,神武賀拔氏,代郡穆氏、于氏、陸氏、長孫氏、尉氏、羅氏、源氏、奚氏、陸氏、侯莫陳氏、尉遲氏、宇文氏,云中斛律氏、獨孤氏,昌黎宇文氏、豆盧氏、慕容氏,河南元氏、穆氏、獨孤氏、賀若氏、劉氏、長孫氏、房氏、閻氏、竇氏,遼西宇文氏。③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歷史地理》第1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117頁。胡姓的界定和辨識存在多重的困難④按:本文對于胡姓的認定主要參考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王仲犖:《鮮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見《?華山館叢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200頁。,上面所列顯然不是全部,只是比較可靠的一些,計17郡、41郡姓,分別占整個郡姓分布的17%和15%,這并不是很高的比例,而且胡姓郡姓集中分布在代郡和河南。胡阿祥先生也指出,這一統計并不是絕對數據,而是一個大致概況,胡姓郡姓、郡望亦是如此。
魏晉北朝時期興起的胡姓郡望,多數有占籍之實,如河東薛氏,本為曹魏時從蜀中徙居河東的一支“胡”族,其族源北朝以來便屢起爭議,尤其是“蜀薛”這一身份,陳寅恪先生已辨其非華夏舊族。⑤陳寅恪:《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疏及推論》,見《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84頁。東魏興和四年(542)《薛懷俊墓志》:“公諱,字懷俊,出于河東之汾陰縣。昔黃軒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散惠葉以荴疏,樹靈根而不絕。”⑥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82頁。墓志稱薛氏出自黃帝,與拓跋氏自稱黃帝之后一樣,為胡姓家族常見的族源敘事⑦參考尚永亮、龍成松:《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敘事與民族認同》,《文史哲》2016年第4期。,從側面暴露了其出自胡姓的淵源。薛氏自魏晉之際遷徙河東汾陰之后,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河東大族,以裴氏、柳氏相頡頏。
這一時期胡姓家族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兩次重要的官方郡望調整事件。一次是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于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⑧《魏書》卷7,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8頁。第二次是北周明帝二年(558)三月:“庚申,詔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⑨《周書》卷4,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55頁。這兩次集中改望涉及的范圍較大,是北朝胡姓郡望發育的基點。這兩次調整擴大了河南、京兆兩個郡望在胡姓家族中的意義,事實上開啟了攀附和偽冒的大門,很多并未占籍于這兩地的胡姓家族也以之為姓望。
北朝時期胡姓攀附漢人譜系和郡望的情況也開始蔓延開來,而且有跡可循。如:“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于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為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為家世之基。”①《魏書》卷93,第2004、2006頁。據《魏書·官氏志》:“胡古口引氏,后改為侯氏。”②《魏書》卷113,第3008頁。侯剛即出身此族,但為了攀附漢人上谷侯氏,他不僅占籍于上谷,還為其子謀官于當地,欲培育地方基礎。《侯剛墓志》中稱:“上谷居庸人也。其先大司徒霸,出屏桐川,入厘百揆,開謀世祖,道被東漢。”③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8頁。侯剛之孫《侯義墓志》亦稱:“燕州上谷郡居庸縣人。”④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修訂本),第223頁。儼然上谷侯氏大族了。但侯剛家族占籍上谷并沒有貫徹到底,侯剛孝昌二年(526)“葬于馬鞍山之陽”,在洛陽;侯義大統十年(544)“葬于石安縣孝義鄉崇仁里”,在咸陽。相比之下,源出高麗的高肇家族的郡望改造可以說進行得更為徹底。史載: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飏,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飏女,是為文昭皇后,生宣武。……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后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⑤《北史》卷80,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684頁。
高肇一族自稱“勃海”望,在當時并沒有獲得認可,“時望輕之”,而且因為其“勃海”望為攀附,并無真正的鄉里基礎,所以高肇在朝只能結為朋黨。但高肇一系為了攀附“勃海”高氏,確實努力占籍于勃海。高肇之子高植、高湛的墓志,高肇之侄高貞的碑,都出土于德州。雖然高肇一族的占籍活動并不徹底,但高氏郡望攀附卻成功了。⑥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修訂本),第71-72頁
另外一個攀附漢人郡望但漢人社會對其認同不一的例子是鮮卑紇豆陵氏。內遷紇豆陵氏改為竇氏,遂攀附漢人扶風郡望。北魏永平四年(511)《楊阿難墓志》:“曾祖母扶風竇氏,父秦,北平太守。”⑦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第62頁。竇秦疑出鮮卑紇豆陵部而冒稱扶風望。史傳中較早攀附扶風的竇氏人物為北魏太武帝、文成帝時期的竇瑾,其本傳載:“字道瑜,頓丘衛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后。”⑧《魏書》卷46,第1035頁。攀附扶風名人竇融之后,但魏收以“自云”質疑之,而且也沒有書扶風郡望。《竇瑗傳》:“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為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⑨《魏書》卷88,第1907頁。雖稱扶風郡望,但“自云”之說也證明其攀附不被認可。又《竇泰傳》:“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⑩《北史》卷54,第1951-1952頁。這里則撇開了與扶風竇氏的關系。但相較于史傳的“權威性”,墓志中鮮卑竇氏攀附扶風望的情況顯得更為明顯。北齊天保六年(555)《竇泰墓志》云:“公諱泰,字寧世,清河灌津人。昔章武以退讓為名,司空以恂恂著稱。仍與王室,迭為甥舅,故已德隆兩漢,任重二京。雖將相無種,而公侯必復。世載有歸,名賢間起。”?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第394-395頁。雖然沒有稱扶風人,但“章武”指竇廣國,“司空”指竇融,也是攀附扶風望了。又如庾信《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志》稱夫人“扶風平陵人。魏其朝議,列侯則莫能抗禮;安豐奉圖,功臣則咸推上席”?(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35頁。。“魏其”指竇嬰,“安豐”指竇融,也是攀附扶風竇氏。
總體而言,北朝胡姓出于郡望成立的早期,更多有占籍之實。一些長久聚居于某些民族地區的胡姓家族,以占籍地為基礎形成了郡望,如天水、馮翊的氐羌胡姓雷、黨、趙等。還有一些陸續內遷而沒有經歷兩次集中改望的部族,保留了邊地作為籍貫,后來也演變為郡望。如廣牧斛斯氏、神武賀拔氏、云中斛律氏等。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胡姓占籍最后都發育成為郡望。史傳、出土墓志所書籍貫、郡望數量更多,分布也更為廣泛。如《庫狄業墓志》稱“蔭山人”①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修訂本),第181頁。,即因為高車庫狄部在孝文帝遷洛以后并未隨遷,而保留了部落組織留在北邊諸鎮。《庫狄洛墓志》稱“朔州部落人”②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第414頁。,亦是如此。這符合這一時期內遷胡姓家族的分布規律。
(二)唐代
進入唐代,門閥士族的地方基礎逐漸崩潰,一些號稱大族的郡姓“世代衰微,全無冠蓋”③(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卷7,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96頁。,但郡望作為社會地位和婚宦清望的象征意義猶存,崇尚郡望的習氣并未有所消減,隨之而來的是攀附的盛行和各種姓氏譜或郡望表的編制。以安史之亂為界,唐前后期的郡望、郡姓情況有一定差異。敦煌吐魯番地區出土多件郡姓氏譜文書,反映了唐代不同時期郡姓的分布、數量情況。胡阿祥先生根據這些資料,制作了《唐前期郡望郡姓分道對照表》和《唐后期郡望郡姓分道對照表》。④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第121-125頁。前期共85郡望、363郡姓,后期90郡望、799郡姓(缺7姓)。下面在這兩個表的基礎上,將胡姓郡望作一個整理。

表1 唐代郡望、郡姓分布表

河東道 上黨 赫連河北道 渤海 赫連、紇干廣平 啖 啖淮南道 廣陵 支同安 仆固穆、獨孤、丘、祝、元、賀蘭、慕容、古、山、莫陳、房、宇文潁川 豆盧泰山 斛斯北海 倪 倪、娥樂安 元 長孫彭城 支蘭陵 萬俟江南道 松陽 瞿曇會稽 康河南 賀蘭、丘、穆、祝、竇、獨孤河南道
表1的統計顯然也不是唐代胡姓郡望的全部,但可以作為一個大概。據表,唐前期胡姓郡望15,占18%;郡姓28,占8%。唐后期胡姓郡望25,占28%;郡姓55,占7%。結合魏晉南北朝時期胡姓郡望、郡姓的數據(郡望17,占 17%;郡姓41,占 15%),可以看到一個現象:魏晉南北朝至唐前期,胡姓郡望的數量和比例大致保持平穩,而至唐后期則有一次較大的增長。胡阿祥先生注意到了鮮卑、羌、鐵勒、天竺、昭武等族諸多姓氏在唐前、后期廣泛分布于各地的現象,但并未作解釋。王仲犖先生對此有一個更為詳細的論說:
澤州高平郡有獨孤氏,并州太原郡有尉遲氏……可見鮮卑族望不僅代居京兆、洛陽,而且分布居住在大河南北了。……此外如羌族大姓,雍州京兆郡有夫蒙氏,同州馮翊郡有黨氏、雷氏,襄州襄陽有荔非氏。又如淮南道舒州同安郡住有出自鐵勒九姓之一的仆固氏,江南道處州松陽郡住有出自五天竺的瞿曇氏,隴右道涼州武威郡住有出自昭武九姓的石氏、安氏。……這些族姓,被列為著姓郡望,那就是說他們在所住地區,還擁有一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社會地位,他們有較高深的文化修養,可以說不是很簡單的事了。⑤王仲犖:《〈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見《?華山館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46-447頁。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反映的是唐后期郡望、郡姓的資料,王仲犖先生將這個文件中新的郡望的出現視為“新興的族望在開始抬頭,門閥士族獨占的局面已經開始動搖”的表征。而包括胡姓郡望在內的新郡望出現的原因,王先生將之歸結為這些家族的地方化,這一觀點也啟發了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①王春紅:《從兩件敦煌文書看代北虜姓士族的地方化》,《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但郡望的形成其實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唐代后期的姓氏譜中所載胡姓郡望,可能萌芽、形成于唐代前期,筆者曾以唐代后期粟特族裔會稽康氏的個案為例討論過這一問題②參考筆者:《唐代粟特族裔會稽康氏家族考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版)》2017年第3期。。
對于唐后期產生的大量胡姓新望,還應該注意“虛”這一條線索,即胡姓攀附漢姓郡望的可能。這一過程當然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開始了,不過唐代更為泛濫。劉知幾對此有激烈的批評: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于平原,卑氏出于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徳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至于它篇所引,皆謂之隴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郡謝偃,并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③(唐)劉知幾撰,浦起龍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4頁。
劉知幾特別點出“西域胡人”明氏、卑氏及謝偃的例子,可見他對胡姓的郡望攀附現象是很清楚的。入唐之后,胡姓家族的郡望攀附和與世系偽冒相結合,成為他們獲得“漢人”身份的重要途徑,如前舉鮮卑竇氏,在北朝時期攀附扶風郡望,尚未完全獲得漢人社會完全的承認;但唐代鮮卑竇氏從郡望、世系、家族文化等不同層面都攀附到扶風竇氏,已完全占據了漢人扶風竇氏之名實。④參考筆者:《世系建構的傳播接受與文本層累——以中古竇氏家族為例》,《人文論叢》2017年第1期(總27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7-77頁。
二、胡姓郡望的社會認同
郡望是中古士族的“金字招牌”和“護身符”,既然如此,就存在認證、注冊和注銷的情況。而在這一點上,胡、漢郡望還存在差異。正如胡阿祥先生所指出那樣,魏晉南北朝時期胡姓郡望的出現,“并不代表這些胡人家族當時已為漢人大家族社會所認可與接納”⑤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第116頁。。在不同的書寫話語體系、接受對象中,胡姓郡望所獲得的社會認可并不相同,下面試從兩個方面做一個探索。
(一)胡姓郡望的書寫
中古文獻對于胡、漢關系的書寫,往往存在一些模式化的敘事策略⑥參考筆者:《漢唐時期胡、漢文化融合敘事模式管窺》,《云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而其中蘊含的認同關系也非常復雜。胡姓郡望在不同的文獻或者文類中所得到的認同是不同的。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官方史書中對于胡姓族屬、族源的記載有一種特殊的模式,即“籍貫+族屬+人物”的體例,這是不同于其他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如“涼州休屠胡梁元碧”“涼州名胡治無戴”⑦《三國志》卷26,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35頁。,“汾州吐京群胡薛羽”“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⑧《魏書》卷69,第1531頁。,“平原烏丸展廣、劉哆”“中山丁零翟鼠”⑨《晉書》卷104,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25頁。,相關例子不勝枚舉。但這一書寫體例在唐代及之后的文獻中逐漸減少,籍貫被郡望取代,族屬標記則被淡化或取消。在史書之外,譜牒類文獻對于胡姓郡望的記載也有不同。唐長孺先生論南北朝士籍時指出:“事實上現實中法律所承認為士族的總比姓氏書中所記載的多得多。”⑩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70頁。官方姓氏書所持之士庶標準為最嚴,但入譜郡姓依然存在偽濫。唐代前期,官方多次大修氏族志,其中《貞觀氏族志》可看作一個綱領。敦煌殘卷中提到該次氏族整理共85郡、合398姓(實收293姓),應當反映了貞觀時期氏族的基本情況。奏文殘卷末云:“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雜姓,非史籍所載,雖預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幕客商賈之類,雖有譜,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①王仲犖:《〈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華山館叢稿》,第349頁。未入錄的“二千一百雜姓”中,胡姓當占不小比例。從殘卷中也可以看到大量胡姓入譜,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唐初官方譜牒已在試圖整合胡、漢姓望結構。官修氏族志中胡姓或蕃姓所在何等、入譜之家族為誰不得而知,但官方譜牒卻有限制胡姓郡望攀附及偽冒的潛在功能。盡管從實際效果來看,卷帙浩繁的氏族志束之高閣,不便利用②參考池田溫:《唐朝氏族志研究——關于〈敦煌名族志〉殘卷》,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684-686頁。,其約束功能大打折扣,郡望偽濫的情況并未得到有效制約。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氏族志并不都指向胡、漢混一,還有一些氏族志隱含著“甄別華夷”的意圖,這主要體現在氏族志中胡、漢分別著錄的方式上。唐先天至開元初,柳沖等修《姓系錄》,“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冠帶者,析著別品”③《新唐書》卷199,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6頁。,即是在分蕃、漢。除此之外,唐人所撰譜牒還有一種也是將胡姓分列的,即裴揚休的《百氏譜》。《宋史·藝文志》著錄該書5卷④《宋史》卷204,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5150頁。;《玉海》“唐百氏譜”條引《中興館閣書目》云:“唐國子助教裴揚休撰,凡三百五十八姓,漢姓三百七,蕃姓一百二十五。”⑤《玉海》卷5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955-956頁。裴揚休原書不存,其蕃姓、漢姓分列的體例對于胡姓郡望顯然是不利的。氏族譜志文獻中區別蕃漢華夷這一情況,似乎主要出現在開元天寶年間(742-756),這與當時氏族主義復古思潮有關。當時譜學界對于胡姓郡望還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術語——“虜姓”。韋述、柳芳《氏族論》對此有經典的表述:
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并號河南洛陽人。⑥《新唐書》卷199,第5678-5679頁。
《氏族論》實際上為韋述、柳芳等人編撰的《唐書·氏族志》中內容,筆者已另撰文考證⑦參考筆者:《中古氏族理論的反思——以〈氏族論〉為中心》,待刊。。“虜姓”的出現,表明胡姓郡望的涌現引起譜學界的重視,雖然這一稱呼指向的是胡、漢區別,但客觀效果上卻奠定了胡姓郡望獲得社會認同的關鍵一步。
相比之下,有密切關系的行狀、家譜、碑志這些文類對于胡姓郡望要包容要得多。或者說,這些文類是胡姓郡望得到社會認可的最低限度。這是為什么在墓志中所見胡姓的占籍或者郡望數量遠遠大于史傳或姓氏書的原因。另外,這些文類中胡姓郡望的偽冒和攀附也是很普遍的。如前舉河東薛氏,本為魏晉以來從蜀中遷徙河東汾陰的少數部族,但在《薛孝通貽后券》中以河東名族自稱:“大魏太昌元年囗月十日,代郡刺史薛孝通,歷敘世代貽后券。河東薛氏,為世大家,漢晉以來,名才秀出,國史家乘,著顯光華者歷數百年。厥后競仕北朝,繁興未艾,今遠官代北,恐后之子孫不諳祖德,為敘其世代以志,亦當知清門顯德有所自也。”⑧陳直:《南北朝譜牒形式的發現和索隱》,《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0年第3期。陳直先生最早引用此石刻,說出土于太原,出土地點可能為薛氏之祠堂。也有學者認為該石刻系偽刻。⑨楊強:《“薛孝通貽后券”辨偽》,《文博》2002年第3期。從石刻文本書寫和傳播接受的角度而言,即便這是一方偽刻,亦是薛氏郡望改造的衍生文本。進入唐代以后,為了強化河東郡望之實,薛氏對自己的族源、譜系進行了改造,《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是一個集大成文本。這個文本應該淵源于薛氏家譜,其中將河東薛氏的譜系無縫上承漢代名人薛廣德:
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愿,為淮陽太守,因徙居焉。……衍生兗州別駕蘭,為曹操所殺。子永,字茂長,從蜀先主入蜀,為蜀郡太守。永生齊,字夷甫,巴、蜀二郡太守,蜀亡,率戶五千降魏,拜光祿大夫,徙河東汾陰,世號蜀薛。①《新唐書》卷72,第2990頁。其中不僅“制造”了薛氏占籍河東的歷史淵源,還篡改了“蜀薛”作為族名的意義。結合《氏族論》中以薛氏為關中“郡姓”之大者可知,河東薛氏已從“虛”“實”兩條線完成了漢人名族的改造。
(二)胡姓郡望的自認、他認與互認
胡姓郡望知識主要依賴漢人的古典文獻,但胡姓新望的認定則是雙向的,胡姓家族的“自認”與漢人社會的“他認”并行不悖,甚至很難區分。西安新出土天寶十三年(754)獨孤挺為其父獨孤洧所撰墓志中載其家族族源說:
獨孤氏漢皇孝景之后,中山靖王之子。北征獫狁,便寄單于,保于崇丘,因以命氏。后與魏帝并驅中原,遷居河南,時謂虜姓也。先人諱挺,字挺。五代祖信,仕魏至大司馬,輔周拜尚書令,隋封趙國,唐贈梁王。八子列侯,三女為后,功業備彰于國史,勛榮盡載于家牒。②陳財經、楊芝昉:《咸陽新出土唐獨孤大惠與獨孤挺墓志考略》,《碑林集刊》第15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37-146頁。
獨孤氏本匈奴屠各之后,其中一支很早就改姓劉氏③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第43-55頁。。獨孤挺自稱“虜姓”,應該是接受了當時漢人譜學中的概念。前面引韋述、柳芳《氏族志》中將“虜姓”作為五大姓類之一。獨孤挺這一自稱也證明,胡姓郡望在當時獲得了漢人知識精英的認同,其胡、漢區分的功能是很微弱的。
在中古時期各種郡望書寫中,可以視為“自認”的家狀和“他認”的姓氏書、史傳也存在交集。如《元和姓纂》現存的10卷中,直接標明引用家狀者就有141姓。在所引家狀中,可以確定為胡姓者如天水雙氏、河南云氏、平涼員氏、是云元、河南潘氏、箝耳氏、云南段氏、河南竇氏、拓王氏等。這些自稱的文獻,被吸納進入姓氏書,自然是胡姓郡望獲得社會認同的重要契機。
郡望書寫的另外一類重要文類——墓志,也是自稱和他稱的結合。如顏真卿作《康希銑神道碑》,詳述康氏姓源、譜系及會稽占籍之由,其內容究竟是顏真卿的手筆,還是根據康希銑家人提供的家狀,無法得知,但顏真卿這一篇文章對于粟特族裔會稽康氏被社會認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參考筆者:《唐代粟特族裔會稽康氏家族考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
胡姓郡望得到社會認可,還可以從一種特殊的“他認”方式中得到印證,就是漢人攀附胡姓郡望的情況,這可以從漢人清河房氏和高車族河南房氏兩望的攀附翻轉來觀察。清河房氏為魏晉以來漢人高門,至唐初房玄齡時代盛極一時;而河南房氏為高車貴族屋引氏所改。從北朝以來,河南房氏攀附清河房氏的例子不絕如縷,這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清河房氏攀附河南望的情況。圣歷二年(699)《房逸墓志》載:房逸,字文杰,魏郡清河人,曾祖宣,隋鄭州滎陽縣丞;祖恭,隋定州司馬;父策,不仕。房逸終官貝州清河縣尉,有子玄之、玄則、興昌⑤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6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346-347頁。。房逸自稱清河人,又在清河本籍任用,其家族出于清河房氏似乎無疑。但大歷十三年(778)《房眾墓志》稱河南洛陽人,本家代北,徙居河南;曾祖文杰,貝州清河縣令;祖興昌,長沙郡長沙縣令;父曠曜,朝州朝陽縣令⑥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6輯,第462頁。。房眾的曾祖文杰即房逸的字,二篇墓志的世系正好連在一起。但《房逸墓志》稱魏郡清河,《房眾墓志》稱代北、河南,為何同一家族前后相異如此?究其原因,在房逸之時,雖然經歷了永徽四年(653)房遺愛謀反案,但清河房氏影響猶在,所以房逸一家雖非房玄齡一支,尚稱清河望;而房逸之后,河南房氏有房融、房琯相繼入相,家族勃興,河南遂成為房氏著望,有壓過清河之勢。房逸、房眾的例子表明,郡望的認同是隨政治、文化之升沉而變遷的,胡姓郡望認同也是如此。
胡姓郡望的認同,還有一種特殊的形式是“互認”,這可以從鮮卑高氏與漢人渤海高氏之間的關系中看出。長安三年(703)高嶠為高纘撰墓志,題名中自稱“族父”⑦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0-11頁。。高纘為高德正的玄孫,而高嶠則是高士廉之孫。雖然都號稱渤海高氏,但后者為鮮卑高氏的“假冒牌”。墓志導演了一場胡、漢高氏互認“同宗”渤海郡望的好戲①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
盡管胡姓郡望通過各種方式在漢人社會獲得了認同,但也不是沒有反撥的情況。社會輿論是反映胡姓郡望認同的重要表征。還是以房氏為例,《太平廣記》引《啟顏錄》: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注:豐邑坊在上都,是兇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兒,只堪嚇鬼。”②《太平廣記》卷260,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2027頁。按此事《兩京新記》西京“豐邑坊”條較詳:“南街西通延平門。此坊多假賃方相轜車送喪之具。武德中,有一人姓房,好自矜門閥,朝廷衣冠,皆認以為近屬。有一人惡其如此,設便折之。先問周隋間房氏知名者,皆云是從祖從叔。次曰豐邑公相與公遠近,亦云是族叔。其人大笑曰:‘公是方相侄兒,只可嚇鬼,何為誑人!’自是大丑,遂無矜誑矣。”參見辛德勇:《兩京新記輯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6頁。
按照上引文字面意思,此則“笑話”頗難理解,若改“豐邑公相”為“豐邑方相”則豁然可通(“公”“方”形訛)。唐代房、方音同,用“房相”諧“方相”以折辱“姓房人”亂攀房姓宰相為親屬。《啟顏錄》的成書時間尚有爭議③參考董志翹:《啟顏錄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房姓之相可能是清河房氏的房玄齡,也可能是河南房氏的房融或房琯,這個自矜“門第”的姓房人,出自哪一支不清楚,但當時的社會輿論無疑對這種攀附行為有所回應。胡姓郡望的社會認同,也應放到這一背景下來考察。
三、“想象的共同體”——胡姓郡望成立與中古民族融合
胡姓郡望的形成和演變,是中古胡、漢融合宏大主題之下的重要課題。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的是陳寅恪。陳寅恪在討論李唐氏族時便提出賀拔岳、宇文泰改易姓望的過程:“蓋賀拔岳、宇文泰初入關之時,其徒黨姓望猶系山東舊郡之名,迨其后東西分立之局既成,內外輕重之見轉甚,遂使昔日之遠附山東舊望者,皆一變而改稱關右名家矣。此李唐所以先稱趙郡,后改隴西之故也。”④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后記》,見《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341頁。其后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對宇文泰“關隴文化本位政策”的集中論述,也將郡望問題作為一個關鍵提出:
故宇文茍欲抗衡高氏及蕭梁,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政策之進行,更可以維系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約言之,西魏宇文泰改造漢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分為二階段,其先則改山東郡望為關隴郡望,且加以假托,使之與六鎮發生關系。其后則徑賜以胡姓,使繼鮮卑部落之后。⑤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00-101頁。
陳寅恪將郡望改造視為維系胡、漢共同體的精神力量。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他進一步強調了郡望改造在“關隴本位政策”中的重要性,稱其為“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復雜民族之要道”,而且在“漢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之外補充了“改易胡人之河南郡望為京兆郡望”的政策⑥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98-199頁。。
“關隴本位政策”下胡姓郡望的改造,對于北朝隋唐之世胡、漢融合的格局影響深遠,陳氏文中多有所及。曹印雙先生也認為改易郡望民族融合的重要舉措:
地域是人們的生存空間,客觀環境對人心理的塑造也是潛移默化的。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新的共同生存空間中融合認同,這是需要引導的。改易郡望姓氏、賜姓就是具體舉措。……郡望姓氏是“關中本位政策”空間要素內涵的反映,郡望姓氏與地域結合,心理想象與客觀現實對接無礙,才能談及本位,才能收到顯著效果。⑦曹印雙:《“關中本位政策”新論——以隋唐帝國形成的基礎要素為中心》,《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2期。
通過改造郡望來整合胡、漢關系雖然集大成于宇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但其淵源則為孝文帝遷洛之后的一系列改制。正如學者指出那樣,孝文帝改制以后,胡、漢一體化,民族邊界日益模糊:“胡人已有家族的自我認同意識。孝文改制后,內遷少數民族族群歸屬感和民族意識趨于淡化,以姓氏為象征的家族歸屬感和家族自我認同意識日漸濃烈。最為主要的表現是,胡人與漢人一樣,已有強烈的郡望意識。郡望是家族地位的標識,是中古時期家族主義的極端表現。郡望所代表的家族認同可以超越時空域限。”①柏貴喜:《四—六世紀內遷胡人家族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95-296頁。
孝文帝改制,本來就包括品序胡姓郡望等級的內容,“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官,得視‘四姓’”②《新唐書》卷199,第5678頁。。胡姓郡望與漢人門閥郡望一樣,和社會地位、選舉、婚姻直接相關,所以胡姓郡望意識的增強是自然的事。更為重要的是,“河南洛陽人”這一身份對于北朝民族融合的意義,因為這一身份從空間上確立了北朝胡姓家族的“華夏性”。
繼承孝文帝之策略,宇文泰改易胡、漢郡望走了另外一條路線,就是重塑“武川”地域認同。趙翼論“周隋唐皆出自武川”云:“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余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③(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十二史札記校證》卷15,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19頁。韓昇將“武川英豪”視為一個移民群落,而武川則是他們的“第二故鄉”④韓昇:《隋文帝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頁。。陳寅恪本意是楊隋、李唐并非出自六鎮,宇文泰將西遷胡、漢集團改易郡望,“并附會其家世與六鎮有關,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鞏固其六鎮團體之情感”⑤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99頁。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第17篇也有“楊隋、李唐非出自六鎮”條,合肥:黃山書社,2000年,第288-291頁。。換言之,武川是宇文泰為其黨徒建構起來的“故鄉”,是一個“想象的”同鄉共同體。“武川幫”原本是一個胡、漢共同體,但在“同鄉意識”的維系下,他們本來的族源、籍貫甚至族系都被篡改或遺忘了,而這種家族歷史的“失憶”,對于重塑移民群體的認同具有重要意義,王明珂先生指出:
歷史失憶與認同變遷常發生在移民情境之中。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環境,除了提供結構性失憶滋長的溫床之外,也往往促成原來沒有共同“歷史”的人群以尋根來發現或創造新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新族群認同。⑥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頁。
武川集團正是一個沒有共同歷史的新族群,所以宇文泰的族群改造運動獲得了成功,以至于隋唐之世的糾正運動也未能完全恢復這一群體的真實籍貫、族源,即陳寅恪所說:“蓋公私著述敘及籍貫或僅據回復至第一階段立言,或徑依本來未改者為說,斯其所以彼此差異也。”⑦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00頁。
同樣是重建共同地域意識以凝聚新的族群認同,孝文帝選擇洛陽,宇文泰選擇武川,同途而殊效。洛陽在華夏文化中,一直以“天下之中”為稱,代表地理、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正統性⑧參考李久昌《國家、空間與社會——古代洛陽都城空間演變研究》第三章“天下之中說與列朝都洛”一節的評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63-185頁。周公“天下之中”的觀念,本來就含有整合殷商移民的族群文化意義,以及四夷道里的文化交通意義。華夏社會本有“以地理別種族”之思想,華夷之辨的另一種表述華裔之辨即地理上的族群分辨。孝文帝以洛陽為政治中心,確立了國家地理上的正統意義;同時將之作為少數部族的新的“地理中心”,使得胡姓家族占據了有利的地理認同。這其實暗合了“天下之中”思想的原始內涵。。“宅茲中國”自然就擁有了族群上的正統意義,引領了“漢化”的潮流。反觀宇文泰所據關中,當時既非華夏文化中心,亦非漢人正朔所在,故不得不采取“關隴本位”政策,其重塑“武川”認同,配合賜姓、領部族等手段,走上了鮮卑化的逆流。這種做法,后來在安祿山的“營州同鄉”還有回響。據《安祿山事跡》載: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①(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3頁。
《舊唐書·史思明傳》亦載:“史思明,本名窣干,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與安祿山同鄉里,先安祿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②《舊唐書》(卷200),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376頁。安祿山既然生于唐代羈縻邊州之“穹廬”之中,鄉里制自然不可能推及于此。史思明為“同鄉里”人,可能是安、史有意編織的“同鄉意識”,與宇文泰的“武川鄉里”一樣,意在凝聚營州各族。謝思煒先生認為安祿山稱營州人是以發跡地為籍貫:“他著籍柳城的‘本地化’行為,很可能是他在成為幽州節度使后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強化對屬下的號召力而有意為之。”③謝思煒:《“雜種”與“雜種胡人——兼論安祿山的出身問題》,《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安祿山以“同鄉”來號召營州各族,直接的原因是當地粟特胡人聚落的存在。④參考榮新江《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79-113頁;[日]森部豐:《唐前半期河北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唐代史研究》2002年第5號,第22-45頁。但另一方面,安祿山的“同鄉”集團并不限于粟特胡人,而是一個包括突厥、奚、契丹等少數部族以及胡化漢人的一個多民族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營州“同鄉”、也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是安祿山整合族群認同、重塑地域共同體的手段。
總之,中古時期胡姓郡望的發育、嬗變和消亡,應該放在當時民族融合宏大主題之下來理解。從大的方面來看,隋唐的建立,本質上就是胡、漢共同體形成的過程,正如谷川道雄先生指出那樣:
部族共同體與貴族領導的鄉黨共同體這兩個世界還肩負著一項重要課題,即克服漢代世界帝國在結構上存在的矛盾。這兩個各自有著運行軌道的世界相互影響,最終產生了一個新世界——新貴族主義國家。作為其完成形態的唐朝世界帝國同時具備了克服漢代世界帝國的最終形態,而胡漢兩個共同體則構成了從漢代到唐代這一巨大歷史運動軌跡的兩條基線。⑤[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李濟滄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2頁。
他還指出:“隋唐帝國是一個由胡漢兩族的共同體社會經相互滲透、合成,共同建設的新貴族主義國家。這是中世共同體的結晶,就其意義而言,恰恰意味著中世國家的完成。”⑥[日]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馬彪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05-106頁。在這個胡漢共同體中,以郡望整合為特征的地域共同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地域關系的融合雖然有現實的路線,但以“想象的共同體”整合胡漢民族認同的意義同樣深遠。
四、結 語
中古時期胡、漢民族大融合的進程存在多條認同路徑,包括族源神話的重塑、地域關系的整合、文化機制的凝聚等⑦參考尚永亮、龍成松:《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敘事與民族認同》,《文史哲》2016年第4期。。這些認同關系的形成,有賴于多重因子的整合,郡望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岑仲勉先生曾指出:“唐人冒宗,乃郡望統一之濫觴,五代再亂,人并郡望而忘之,由是李姓唯號隴西,王姓只知太原,同氏者便認同宗,不同氏者便如異宗,是為我國種族混亂之第二次大變。族姓之歧見,雖消滅于上層,又移植于下層,此論漢族發展史所不可以忽視之一點。”⑧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12頁。這一論斷高屋建瓴指出了郡望統一在中華民族融合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從族群互動的角度來觀察中古時期胡、漢郡望趨一的現象,一方面,大量少數民族內遷打破了漢人穩固的地理空間意識,伴隨著民族大遷徙運動,漢人需要一個“想象的”共同地域來維系“我族”意識,于是同姓聯宗、攀附郡望的現象滋生。另一方面,從朔漠到中原的少數部族,通過族源、姓氏、世系的改造,完成了譜系漢化,而攀附漢人郡望,與漢人形成“想象的”共同地域集團。上述兩股潮流的合流在形式上表現為郡望的虛化和趨一,而實質卻是胡、漢民族關系的調整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