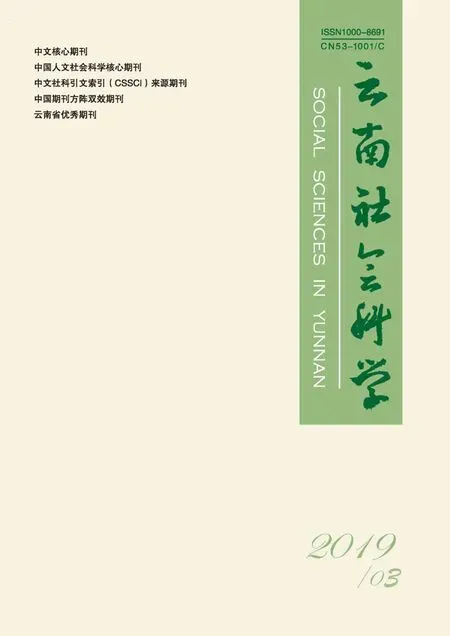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三種城市文化及其意識形態本質
——從曼紐爾·卡斯特的馬克思主義城市文化批判理論談起
溫 權
建構并維護現存不合理社會制度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決定了西方城市文化的基本政治屬性。后者作為大眾物質實踐與群際交往得以展開的符號性載體,又進一步折射出資本邏輯的人類學內涵之于城市景觀的空間性敘事。鑒于此,曼紐爾·卡斯特專門指出,“當我們談論‘城市社會’時,該議題并非囿于純粹的空間形式。與之相反,它被所有確定的文化所定位。……換言之,這是一種價值形式以及貫穿于歷史特殊性及其組織與轉換之自我邏輯當中的社會關系。”①nuel.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75.而問題的關鍵在于,該如何界定能夠表征當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城市文化形態?圍繞資本生產結構的時代性特征,卡斯特在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視域下,將其概括為以下三方面彼此呼應的板塊:
一方面,與新自由主義背景下勞動分工的精細化和價值積累的彈性化趨勢相呼應,旨在更高效調節資本部類結構及其整體生產節奏的技術性官僚體系,必然為占據市場競爭有利地位且主導城市發展走向的統治階級,營造出能夠最大限度維護自身利益的所謂“精英政治文化”。它促使“權力集中在上層階級”,并于權力網絡對普羅大眾的無情壓制中,同時完成“整個國家的非正式化以及權力結構的個人化。”藉此,再次確認資本掠奪式統治的制度合法性。②[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夏鑄九、黃慧琦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09頁。其實質不啻為傳統勞資關系已然發生形變的情境下,資本邏輯憑借市場競爭與權力主體間不對等的相互關系,對價值剝削機制的策略性鞏固。于是,在另一方面,當據此形成的等級性社群結構同資本地理性不均衡發展的空間后果彼此耦合,伴隨著社會財富的區域性集中和職能機構的選擇性分布,資本就從“權力的頂峰與其文化中心起始,組織了一系列象征性的社會-空間層級。”①[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宏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11頁。而這通常意味著原本完整的城市文明景觀,將轉化為片斷性的社區利益集合。后者進一步衍生出能夠瓦解勞動者政治聯盟的“社區隔離文化”,并以夸大群際間利益分歧的方式,維護資本不合理的社會關系。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強化統治階級空間霸權的“精英政治文化”,還是削弱被統治階級反抗運動的“社區隔離文化”,都相繼與當下正在崛起的“網絡虛擬文化”達成共謀。在“信息的發展及其壟斷成為統治階級實現社會控制的基本來源”的前提下,為社會權力、階級結構以及網絡體系共同修飾的城市文化棱鏡,無疑徹底剝離了個體空間交往和日常體驗的真實性。②[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夏鑄九、黃慧琦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09頁。如此一來,資本就在現實與虛擬的倒錯關系中,通過對信息反饋機制的操縱徹底遮蔽了已然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
應當說,與政治壓迫和價值剝削并行不悖的現代西方城市文化,可視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向社會空間彌散的結果。它試圖在居民日常生活得以展開的地理學維度,“構建一個有關真正存在的社會景觀,構建一個沒有被對抗性的分工所割裂的社會,構建一個其各部分的關系呈現有機性、互補性的社會。”③[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76頁。進而,從文化符號之于社會癥候的目的性編碼出發,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空間性再生產提供必要的條件。因此,在當前西方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城市文化形態,毋寧是資本權力能指的具象化。它們既標識出資本邏輯對其下轄人群之社會實踐方式的總體性操控,又從相反的方向表明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長時段內在危機。
一、資本靈活性積累、技術官僚主義和城市精英政治文化
資本生產與積累方式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徹底改變了西方城市景觀的社會學意義。在充斥著“彈性專業化、彈性生產體系、彈性積累以及彈性勞動管理方式與彈性技術的彈性時代,城市已然成為后福特主義工業空間的代名詞”,④Edward.W.Soja.Postmetropolis:Critique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224.并預示著嵌入其中的資本部類結構和傳統勞資關系將同時發生歷史性的重組。對于卡斯特而言,該過程“既是社會性和技術性的,又是文化性和政治性的。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是對市場利潤最大化原則的補充。”⑤Manuel Castells.“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ism”,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259.其實質不啻為資本剩余價值剝削與空間權力壟斷的精致化。反映在具體的社會治理層面,這意味著能夠高效調節資本生產節奏且鞏固統治階級政治威權的文化-制度性空間正在逐步形成。而后者又直接表現為,占據市場競爭有利地位的城市上層人群,對西方民主制度內的“精英政治文化”進行刻意渲染。藉此,構建出與普羅大眾的利益訴求完全悖離的排它性管理-決策體系。事實證明,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殘酷市場法則下,圍繞“金錢與控制權的斗爭勢必將一部分人徹底排除在平等之外,而由此引發的政治分歧,則使擁有充足金錢力量的精英對空間權力進行長期壟斷。”⑥David Harvey,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Oxfor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33.如此一來,一旦底層群眾參與城市治理并限制精英階層決策范圍的民主權利被削弱,城市自身必將陷入資本及其附帶的空間權力向少數人集中的惡性循環。
無獨有偶,在卡斯特看來,“精英政治文化”的產生,往往與西方民主制度的內在階級屬性,以及資本靈活積累模式對技術官僚體系的依賴直接相關。而它最終所要達成的目的,就是憑借“文化符碼已嵌入社會結構里的方式,使得持有這些符碼便形同開啟了通往權力結構的道路,而無需精英階層的任何有意識謀劃。”⑦[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第510頁。換言之,作為“精英政治文化”母體的西方民主制度及其內涵的技術官僚體系對社會發展模式的操縱,意味著城市空間將淪為資本財富掠奪的無意識容器。屆時,飽受摧殘且無力反抗的城市底層人群,只能被迫接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文化性強制規訓。而這主要涉及以下兩方面內容:
首先,以貨幣邏輯和競爭法則為先決條件的民主制度及其決策體系,實際上是“精英政治文化”維護資本自身合法性,并使財富向城市空間內少數人那里選擇性集中的條件性保障。一方面,從西方城市民主政治制度與決策體系得以確立的前提來看,資本毋寧是衡量城市景觀內所有政治行為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而受其裹挾的政治關系,除了向公民交往的一般領域滲透之外,還在“個人、肉體、行為舉止的層面復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①[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30頁。這就促使資本邏輯的運轉軌跡與財富分配的現行方案,能夠在單向度的市場機制推動下,毫無阻力的向精英階層大規模傾斜。一旦民主決策的可操控范圍“退回到市場自發性調節的層次,那么其后果必然是,原本用于制約財富不均衡分配的政策導向機制,喪失它對價值法則的控制能力。”②David 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141.在這樣的情形下,西方城市中所謂的民主制度不過是資產階級攫取財富,并鉗制底層群體的空間把戲。后者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即“貨幣始終是一種社會權力的形式,是規訓社會關系的工具,而非中立的”組織原則。③[美]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胡大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46頁。另一方面,從西方城市民主政治制度與決策體系得以運行的原理來說,既然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與主要任務“就是把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中盡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轉化為資本”,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6頁。那么相關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就必須與資本穩定增值的節奏彼此吻合。進而,使現存的社會關系成為資本空間性再生產的基礎與條件。以此為出發點不難看出,“如果資產階級要對自身和它對勞動的控制進行再生產,就必須使工人贏得的任何讓步都與資本積累中決定投資生產率的規則相一致。”⑤[美]大衛·哈維:《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化進程:分析框架》,《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9頁。也就是說,由勞資雙方共同參與并嘗試在其中消解政治分歧的民主決策過程,始終不能觸及資本空間積累的政治底線。對此,卡斯特專門指出,“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及其引發的沖突(即一般意義上的勞資對立——筆者注),城市中的國家干預將不斷強化;但是,作為階級社會的一種表達,依據階級和社會群體間權力關系的國家實踐行為,通常傾向于維護統治階級的霸權。”⑥Manuel.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NewYork:St.Martin’s Press,1978,p.3.而這反過來又充分證明,“精英政治文化”恰好以資本邏輯為基本運行原理。
其次,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和資本彈性積累法則同時崛起的技術官僚主義,通常構成“精英政治文化”協調資本部類生產關系,并借助具有明顯傾向性的政治程序馴服普羅大眾的操作性手段。這無疑彰顯出資本對勞動生產效率和勞動者社會屬性的雙重規訓。卡斯特認為,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資本靈活積累模式的最大負面效應,就是它在地理學維度沒有一種相對穩定的市場邏輯可以遵循,而總是由于市場被扭曲、操控和轉化等原因,時刻處于“多重文化的群眾心理,以及全球資本流動和互動越來越復雜所導致的不可預期的狂亂之下。”⑦[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第412頁。其最為典型的后果,就是在城市不同空間單位或差異性人群之間,圍繞資本某一部類同時展開的生產活動,為爭取各自的市場利益而陷入無休止的惡性競爭。從而,導致資本階段性價值獲取總量的無謂耗散。在這樣的情形下,引入用于市場管理的技術性協調機制,并將之升格為資本官僚體系的內在職能,就成為統治階級維護資本長時段有效積累的必然選擇。如此一來,能夠兼顧精英階層狹隘利益和社會總體財富訴求的全新城市治理模式就呼之欲出。它為處在市場競爭場域內的資本部類生產代言人或受益者提供了彼此媾和的政治性平臺。但在相反的方面,“拋開非常特殊的時期不談,大眾階級并沒能進入到這些不同程度上,不同社會秩序中,讓上層階級(資本家與管理者)實行‘內部民主’的機構中去。”⑧[法]熱拉爾·迪梅尼爾、多米尼克·萊維:《大分化:正在走向終結的新自由主義》,陳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0頁。這無疑顯示出以“精英政治文化”為導向的技術官僚主義,自身鮮明的意識形態特質:后者不僅克服了精英階層在瓜分社會財富時遭遇的瓶頸,而且還“在政治經濟上建構了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大眾文化,滿足分化的消費主義和個人自由至上主義。”①[美]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44頁。應當說,勞資雙方在技術官僚體系中的不同處境,恰好折射出圍繞“精英政治文化”而建構的現代資本城市決策中心,與其治下的邊緣性勞動群體彼此疏離甚至相互敵對的態勢。按照卡斯特的說法,該狀況既是現代西方城市之“剝削-異化-壓迫屬性的無意識結構性根源,又是將其境況表征為一種日常提示的特殊空間組織形式。”②Manuel Castells.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London:Edward Arnod.1983,p.326.二者相輔相成,從“文化-意識形態”與“政治-管理機制”的共軛關系中,再度確立了資本政治威權的空間合法性。
值得一提的是,“精英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架構中轉化為現實的物質操控力量,還與其內涵的“迫切感文化”(culture of urgency)因子,對被迫介入資本新自由主義場域的城市底層群體之非正常競爭意識的刻意渲染密切相關。事實證明,它用“一種沒有未來、沒有根源、只有現在的趨利性思考方式”,矮化了主體間固有的長時段穩定協作關系,并憑借資本即時性積累的單向度邏輯對勞動者日常生活每一瞬間的壓縮,促使“非常個人式的消耗和圍繞利益爭奪而展開的沖動行事成為其生活的唯一寫照。”③[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第184頁。于是,當群際交往的全面性讓位于受資本裹挾的個體自由的片面性時,“一個達爾文式的世界就以這種方式出現了。它是在科層的各個級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斗爭,每個人在充滿不安全感、遭受痛苦和壓力的條件下形成對其工作和組織的依附。這些制度和勞動后備軍的并存成功地建立起生存競爭的世界。”④[法]皮埃爾·布迪厄:《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2頁。這就與“精英政治文化”的意識形態訴求不謀而合。它需要在普羅大眾微妙的社會聯系中,以“自由”之名植入足以渙散工人階級政治凝聚力的負向干擾因子,進而以所謂“中立”的調停者身份牢牢地掌控已被資本異化的城市社會秩序。從根本上來說,這不啻為統治階級為剝離底層群眾的城市公民權,而進行的文化符號強暴。其最終目的,就是把精英階層的“特定歷史經驗和特殊需要說成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全面推廣。”⑤孫蘭英:《全球化網絡化語境下政治文化嬗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06頁。從而,在文化學的語境中,突顯出資本的政治優先性。
由此可見,寓于西方城市空間的“精英政治文化”,不能被簡單地視為孤立的社會現象。它作為統馭社會利益節點和強化資本政治壓迫的中介,毋寧是城市規劃路徑與發展節奏被統治階級事先設定好的文化主題所整合的結果。⑥Cf.Manuel.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219既然人們無法在資本靈活積累的變動不居性中獲取穩定的連結紐帶,那么為精英操控的異化交往機制就獲得了可乘之機。在這樣的前提下,與資本剝削彼此耦合的社會空間秩序,勢必“在城市政治與經濟結構中,生產出與資本發展趨勢相一致的社會意識。”⑦David Harvey.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Oxfor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266.后者自覺服從現存的資本空間規劃,并以既成事實的形式,轉化為統治城市居民的意識形態。而這在卡斯特看來,不啻為“精英政治文化”在社會關系再生產層面的自律性賡續。它意味著處于市場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將自身攜帶的霸權嵌入到四分五裂的城市空間,并在勞動群眾各行其是、地方利益爭斗不休的情形下,牢牢占據了城市政治秩序的核心地位。
二、資本選擇性集中、群際利益分歧和城市社區隔離文化
旨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精英政治文化”對資本彈性積累法則的默許與操縱,無疑強化了具有不同價值創造潛力的城市各空間單位在財富擁有量方面的巨大差異。這就導致身處其中且為市場競爭機制裹挾的社會多元群體,因資本“物”的尺度而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彼此疏離甚至相互攻訐的狀態。在這樣的情形下,“大規模的工薪階層就越來越在居住、工作、娛樂、購物等方面表現出強烈的空間分化傾向。”⑧Manuel.Castells.City,Class and Power.NewYork:St.Martin’s Press,1978,p.29.進而,在地理層面衍生出以文化-政治隔離為主要特征的群際社區關系。
作為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城市政治格局的地理性癥候,前者“既是充滿私人的和階級張力的奇特混合體,又能在社會基礎設施的再生產中,將個體的社會習俗、文化傳統以及政治過程都包含在等級化的組織形式之內。”①Davi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5,p.11.因此,在空間上彼此孤立的異質性社區,可視為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向日常生活轉嫁的產物。與資本主義的“精英政治文化”相呼應,它直接構成“社區隔離文化”由以誕生的前提。鑒于此,卡斯特不無疑慮地指出,“這種全新的城市文化形態,同(資本)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夾縫內的多模態‘意義-交互性’結構密切相關。它實際上是社會中已然發生斷裂的各組成部分,根據碎片化的孤立社群或以自我為中心的主體,彼此間的并置而實現的。”②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82.也就是說,所謂“社區隔離文化”,可視為資本彈性積累模式下城市多元利益馬賽克的一般稱謂。它揭示出財富和權力的極化效應,正在深刻影響當代城市空間格局的尖銳事實。而后者在卡斯特看來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
第一,從城市內不同社區的形成機理與資本邏輯的地理規劃二者間的關系來看,既然城市空間作為一種隱喻,同資本的“各種意識形態的確立(貨幣與商品不斷流通的‘自由’貿易)以及主體性(流動單子的個人主義)息息相關”,那么在資本主義市場的修飾下,它必然被“描寫為可牽制、可操控的空間。”③[美]本·哈默:《方法論:文化、城市和可讀性》,《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8頁。這集中反映在,原本統一的城市轄區被資本循環序列依次拆分為具有不同職能的碎片化空間單位。而后者通常構成隸屬社會各個階層的城市人群展開日常生活并參與政治實踐的地理學邊界。如此一來,“在空間的象征性、中心性和文化認同的明確界面之間,以及流動空間能被主流文化制度化的場域,社會群體的物理性-本質性分隔的臨界點就出現了。”④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84.它們在日趨多元且更加精細的資本部類生產中,使“勞動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異質,在種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樣,在人種上更加層次化,在語言上更加分裂。”⑤[美]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胡大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4頁。從而,形成彼此孤立并攜帶明顯政治分歧的社區性聚居群落。由此可見,西方城市空間中星羅棋布的社區景觀,及其對差異性群體“特定文化認同的政治意義的(再)建構,正根本地挑戰著公民權的概念。”⑥[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夏鑄九、黃麗玲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96頁。這恰好印證了大眾協作體系的瓦解和社會原子主義的興起。而社會景觀中不斷出現的堡壘式分割、封閉型社區,以及終日處于監控中的私有化的公共空間,無疑是該狀況的直接表現形式。它們在造成資本不均衡分配的同時,又于城市規劃體系內引發劇烈的空間張力。
第二,從城市內不同社區的空間定位與資本邏輯的政治預設二者間的關系來說,由于資本增值與循環系統具有鮮明的剝削屬性,它勢必將一段時間內所獲財富的總量,按非正義的分配原則不均衡地配置于城市的各個空間單位當中。因此,以之為出發點的一般政治行為“所產生的地理景觀不是平衡發展的,而是有極大差別的。通過不平衡的資本投資的簡單邏輯……‘差異’和‘他性’在空間中被生產出來。”⑦[美]大衛·哈維:《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第339頁。這就意味著,已然呈碎片化分布的城市社區景觀,將再度以財富占有量為尺度,被打上具有明顯隔離標識的“貧民窟”或“富人區”烙印。對于卡斯特而言,后者在當下又集中體現為“高收入或中高收入群體從城市當中分離出來,并且建構出更加異質性的社區。從而,促使富人聚居區的空間指標遠高于貧困人口聚居區的空間指標。”⑧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p.376-377.如此一來,在資本的財富分配序列和政治規劃格局中處于不同地位的差異性社區,就成為履行資本剝削職能或承擔被剝削后果的社會各階層人群,強化自身空間身份的地理性標簽。在這樣的情形下,“階級(資本-工資)矛盾,就延伸到社會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政治的(統治-被統治)矛盾中。人們不能從內在于資本主義的凝聚力當中看到生產關系是怎樣再生產。人們只能看到在廣大區域中不斷擴大和加劇的矛盾。”①[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63頁。而彼此疏離甚至相互敵對的社區作為矛盾的載體,則據此充分佐證了為資本邏輯催生的城市社區分化“不單是權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polarization)”②[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第91頁。。
第三,從城市內不同社區的生存樣態與資本邏輯的社會愿景二者間的關系來講,地理上持續的財富分配不均與政治上日益嚴峻的兩極分化,無疑加劇了“城市人口在關乎其日常生活能否得以維系的食物、能源,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務性資源的多元網絡體系中的沖突與爭端。”③Stephen Graham.“Urban Metabolism as Target”Cf.NikHeynenEd.In the Nature of Cities: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p.238.于是,當城市內各個階層的人群希望最大限度占有社會資源,并防止他者染指其既得利益時,以共同居住的社區為地理坐標的階級聯盟就應運而生了。它們是個體資源相對匱乏與資本價值絕對積累的消極產物。但在卡斯特看來,這種以“物”為尺度而構建的“階級聯盟”和由此推動的地方/區域的自主性,通常以加強“其領域內的精英階層的認同,并削弱此自主性的政府機制中不具地方代表性或被隔離的社會弱勢群體的認同”為代價。④[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315頁。于是,精英和大眾在城市政治格局中的不對等關系,就很容易成為統治階級維護自身特權并據此監控被統治階級社會活動的手段。它“一方面利用社區間的競爭機制,加重了對工人趨利性聯盟的壓力;另一方面又通過利益最大化原則,將全部工業生產體系整合進資本的統治地位不被動搖的投資性區域。”⑤Manuel.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London:Edward Arnod.1977,pp.214-215.從而,在實現資本價值穩定積累的同時,將其可能遭遇的反對性力量最大程度地削弱并分別置于與資本財富增值無涉的隔離性區間。由此可見,“城市空間的分化和社會關系的弱化,是資產階級努力發展自身經濟實力和社會領導權的核心。而空間重構結合高強度的監管體制,則使資產階級可以建立起新的代表文化差異的圍墻。”⑥[英]史蒂夫·派爾等:《無法統馭的城市:秩序與失序》,張赫等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4頁。后者的實質,就是在城市空間中確認資本之于個體的絕對優先性。
不難看出,作為階級沖突、政治分歧以及社會異化的空間性集合體,在地理上相互隔離的城市社區網絡,實則以取消大眾社會共識的合法性為代價,通過強化資本的地理性不平衡發展,進而鞏固了資本非正義的剝削制度。“它不僅提供了為權力斗爭而進行權力斗爭的嗜好,而且通過大規模強占和集團性奴役的手段”,使資產階級“獲得了各種勞動產品,而無須自身終日參加苦重的勞動。”⑦[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第57頁。因此,“社區隔離文化”既是資產階級對城市底層群體的地理規訓,又是資本對城市政治權力進行非法壟斷的意識形態敘事。它預示著原本統一的社會發展進程,將發生不可逆轉的自我分裂:一方面,為精英階層主導的社會文化認同“趨于涵化包容,并以其對地方制度的控制來擴充認同的社會和人口基礎”,進而實現資本生產關系的全面泛化;另一方面,與底層群體的利益旨趣休戚相關的“地方社會卻防御性地退縮,并以社會排斥的機制來建立其地方自主性”,以此消極地維護自身狹隘的政治-經濟利益。⑧[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316頁。換言之,“社區隔離文化”最終意味著資本空間生產與積累的碎片性,對城市內差異性群體之社會契約的整體性的褫奪甚至取代。對此,卡斯特專門指出,“城市契約是由隸屬不同文化背景、擁有不同資源配置的市民彼此協商的產物,這是一種部分共享的文化以及存在部分分歧的制度性平臺。但城市不斷加速的空間碎片化過程,卻從根本上破壞了我們共同生活的可能。”⑨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77.它標識著城市政治景觀的徹底失序與個體日常生活的完全異化。
顯而易見的是,在差異性群體的空間利益分歧被過分渲染的“社區隔離文化”中,一旦連結普羅大眾的“社會紐帶被定義為形式差異的變動游戲而非顯而易見的內在品質時”,有關“個體身份和地點的界定也就變成了幻滅的符號”①[澳]斯科特·麥奎爾:《媒體城市》,邵文實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1~72頁。。此時,對于由社區網絡形成的城市公共空間來說,它早已隨著大眾權力的退場而淪為資本攫取特權并加劇社區隔離的異化場所。馬克思曾尖銳地講道,“隨著城市的出現,必然要有行政機關、警察、賦稅等等,一句話,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機構(Gemeindewesen),從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頁。而所謂“一般政治”的實質,毋寧是在資本地理性不平衡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對被隔離社區內“居民極少量權利片斷的維持,進而在作為整體的城市大背景下,將其大部分利益予以擯棄。”③Don Mitchell.The Right to the City: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New York,London:The Guilford Press,2003,p.210.這就促使城市的公共空間與資本的意識形態彼此重疊,并進一步衍變為鉗制底層群眾命運的“它者”霸權。其中,居于西方城市化進程核心的,仍然是馬克思之前所指認的異化事實:即“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既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頁。。此時,城市就不再是個體得以棲居的生活空間,而更像是彼此利益爭奪的角斗場。縱然城市的經濟指數持續攀升,但因社會關系異化而導致的階級壓迫卻早已滲透到社區的各個角落。
三、資本結構性重組、數據信息空間和城市網絡虛擬文化
由資本靈活積累和選擇性集中共同催生的“精英政治文化”與“社區隔離文化”,不僅重構了現代西方城市的空間文明形態,而且還以轉變社會權力敘事的方式,促使整個資本生產體系發生結構性的變革。而它們對市場競爭機制的強化以及財富高效積累的推崇,則昭示了用于創造價值的手段和平臺將陷入愈加頻繁的更迭狀態。于是,能夠以不斷的自我更新滿足資本即時性利潤訴求的網絡信息環境就應運而生了。在卡斯特看來,這意味著一個全新的城市圖景正在形成。其中,“信息技術革命、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經濟危機及其隨后發生的再結構,連同文化上的社會運動……共同產生了一個新的支配性的社會結構,即網絡社會、信息化/全球經濟和真實虛擬的文化。而深植于這種經濟、社會和文化之內的邏輯,已經成為整個相互依賴世界里的社會行動與制度的基礎。”⑤[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第403頁。(引文略有改動)后者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資本-地理”格局,并在勞動的真實性與數據的虛擬性彼此倒錯的關系中,逐漸衍生出消解大眾直接社會體驗的“網絡虛擬文化”。作為“精英政治文化”和“社區隔離文化”在當下的最終言說載體,它憑借“個人身體網與建筑網、建筑網與社區網、社區網與全球網彼此連結的方式”,⑥W.Michell.City of Bits:Space,Place,andthe Informa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5,p.3.把資本的空間宰制力發揮至極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由資本信息網絡操縱的數據性流動空間,對地方空間內大眾日常生活經驗的蠶食。對此,卡斯特專門指出,“流動空間乃是通過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它標識出“社會的經濟、政治與象征結構中,社會行動占有者所占有的物理上分離的位置之間那些有所企圖的、重復的、可程式化的交換與互動序列。”⑦[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宏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05~506頁。其實質就是為網絡環境下資本脫域性積累提供必要的準備性條件。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既然資本邏輯的“形式化與數量化功能意欲擺脫事物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意義之網的束縛,并且還可能以暴力的方式消除它所遭遇的所有障礙與抵抗”,⑧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49.那么將資本運行的路線圖整合進去疆域化的虛擬信息符碼當中,就不失為一種祛除地緣限制的柔性舉措。這就涉及信息網絡對資本自身和城市景觀的雙重虛擬作用。對于前者而言,資本的周轉動向與財富的獲取節奏通常被抽象化為數據性的信息函數,并在網絡媒介之于個體交往的干預過程中,呈現出不受其他社會參數影響的獨立屬性。在這樣的狀況下,資本邏輯就游離于現實的社會日常情境之外,并據此獲得了自在自為的表現形式。與此同時,對于后者來說,“由于網絡虛擬空間的理念與現象正在興起,而且虛擬空間有可能給使用者脫離‘真實’世界,并真正參與到被想象和再現的世界中去的機會”,①[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與城市文化》,李東航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2頁。因此原本穩定且真實的城市文明景觀就不得不接受信息符號的編碼,進而淪為以虛擬網絡為前提的依附性存在。由此可見,正是憑借網絡信息環境對資本存在樣態和社會日常生活的不同定位,自律性的資本邏輯才在數據性的虛擬鏡像中,實現了對依附性的城市景觀的全面操控。它既意味著受資本裹挾的流動空間對個體真實社會經驗得以生成的地方空間的褫奪,又揭示出資本將“核心的經濟、象征以及政治過程從社會意義能夠被建構而政治控制能夠被執行的領域中轉移出來”的陰險狡計。②[美] 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143頁。而在“資本邏輯-網絡媒介-城市景觀”的倒錯關系中,“審慎周密的網絡虛擬文化勢必滲透我們城市的各個角落,并將其內在的多種維度縮減為一種單一連貫的視覺再現,一種主要建立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之上的再現”③[英]斯蒂芬·邁爾斯:《消費空間》,孫樂民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82頁。。以此,實現資本對城市空間的長時段政治霸權。
其二,是由資本信息網絡激化的生產力更新速度,對傳統社會中群際利益對抗張力的加劇。毋庸置疑,資本生產模式由工業主義向信息主義的歷史性轉向,標志著知識性的“文化創新在邏輯上成為決定生產力是否提高的關鍵指標,并因此作為財富的源泉而增強了資本化城市的競爭強度”④Manuel Castells.“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f.IdaSusser.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Massachusetts:Blackwell,2002,p.370.。這表明,在網絡信息時代,資本生產與積累效率在質和量上的雙重飛躍無異于數據信息體系自身的程序性更新。這同時意味著,為滿足資本的競爭需要,“任何想要將網絡中的位置凝結為特定時間及空間之文化符碼的企圖,都會造成網絡的廢棄過時,因為它會變得過于僵化,無法適應信息主義之多變幾何形勢的要求”,并與資本創造性破壞的內在文化屬性相悖離。⑤[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第245頁。然而,在卡斯特看來,資本生產的信息化趨勢在城市空間層面并非是一個均質化的過程。它通常在城市不合理的勞資關系而不平衡的區域發展結構中,增大了資本價值剝削的歷史慣性。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在此新模式下,……被信息化資本主義視為無價值且無政治利益的地區,財富和信息的流通跳過這些地區繞道而行,甚至連設施都被剝奪了。這個過程導致社會/區域所排除和接納的地理分布極度不均,并使得大部分人無法經由信息科技的全球網絡積累財富、信息及力量。”⑥[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第78頁。由此不難看出,被資本信息化潮流催化的城市兩極分化趨勢,不啻為“網絡虛擬文化”對“精英政治文化”和“社區隔離文化”之地理學旨趣的最終表達。這無形中肯定了與資本生產力提升相對應的信息即時性更新機制,對身處城市發達區域的精英階層之政治-經濟權益的接納與維護,以及對落后街區底層人群社會訴求的隔離與排除。其實質,毋寧是被信息網絡虛擬化的“城市日常節奏和活動例行地將城市空間編碼、劃分”,進而使資本的空間剝削機制“在一個鮮為人知的不平等基礎上隱秘地進行”⑦[英]多琳·馬西等:《城市世界》,楊聰婷等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7頁。。因此,信息時代的城市景觀毋寧是極度分裂的,它一方面促使“信息化生產者與可替代的無標簽一般勞工之間,也就是勞動者內部出現片斷化”,另一方面又引導“社會排斥在社會內造成明顯區段,而這些區段由被社會拋棄的個體所構成。”⑧[美]曼紐爾·卡斯特:《千年的終結》,夏鑄九、黃慧琦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15頁。二者彼此耦合,共同顯現出資本“網絡虛擬文化”內在的階級利益對抗屬性。
其三,是由資本信息網絡支配的多元化傳播媒體,對當前時代下統治階級政治意圖的修飾。從直觀上來看,日趨完善的數字化傳播媒體,在當下毋寧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向城市景觀植入的首選文化性介質。它“與現代城市主義間的相互交織,改變了地點與經驗、熟悉與陌生、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紐帶。”并通過“人類感知與技術幻想之間模糊的界限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意識的空間,進而促使主宰著現代性的自治模式和內部性模式變得越來越難以與日常經驗相協調。”①[澳]斯科特·麥奎爾:《媒體城市》,邵文實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5頁。在這樣的情形下,統治階級帶有明顯剝削屬性的政治傾向,就很容易在虛擬與現實的夾縫當中獲得特殊的偽裝。它以看似呼應城市日常生活之瑣碎、無聊甚至娛樂化特質的開放形態,充分滿足了普羅大眾之于現代資本政治結構的全部想象。然而,對于卡斯特來說,事實的本質卻是,個體及其社會關系已然成為媒體領域的俘虜,并在統治階級的個人領導權不斷強化的基礎上,通過“技術上的復雜操弄,被推向不法的金援,被丑聞政治推著走并越來越接近丑聞政治,政黨系統已失去其訴求吸引力及可信度,同時,對所有現實目的而言,它是一個不再具有公眾信心而僅剩官僚的殘余物。”②[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397頁。這恰好說明,現存的城市日常生活及其涵蓋的政治行為預期,都不過是受資本邏輯操控的網絡信息媒體,對大眾負面訴求進行刻意編織的消極產物。作為“網絡虛擬文化”的政治性投射,后者又進一步揭示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城市人群進行文化催眠的手段,將轉變為嵌入文化產品和具體日常實踐之中的“神話修辭術”。③[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與城市文化》,李東航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3頁。它使“生活本身也逐漸成為一種媒介,如同電影、電視、收音機和書刊一樣,其中的人群既是媒介中的表演者,又是這些正在表演的恢宏劇作的觀眾。”④N.Gabler.Life the Movie:How Entertainment Conquered Reality.New York:Knopt,1998,p.9.通過現實空間與文化空間的置換,原本尖銳的階層對立,就在虛擬的網絡文化層面獲得和解。加之“媒體對于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掌握,也變得更具全面性。”⑤[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第370頁。這就導致統治階級的政治意圖被掩蓋之后,資本又在“客觀上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稀薄的幻象和超現實世界”,⑥[英]喬治·拉倫:《意識形態與文化身份》,戴從容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2頁。以此來軟化社會矛盾對資本主義政治秩序的沖擊。而在被拜物教化了的虛擬文化空間當中,“人們對自己茫然無知,且思想也不會想到與這種抽象空間保持批判性的距離”⑦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94.。
毋庸置疑,圍繞“精英政治文化”“社區隔離文化”以及“網絡虛擬文化”而建構的當代西方主流城市文化敘事,不啻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空間性表達。而后者之于普羅大眾的意義性編碼及其產生的社會物質性后果,則再度凸顯出馬克思有關“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等經典論斷的正確性。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頁。鑒于此,反觀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城市文化形態,不難看出,它們依然是資本價值剝削與政治壓迫的外化。而唯有徹底變革決定現存城市社會圖景的異化生產關系,才能最終打破資本文化霸權的空間座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