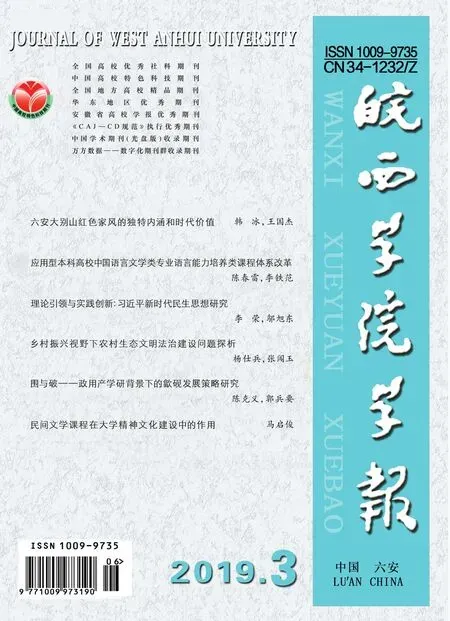東晉“依仁游藝”隱逸模式及其時代特征
——以戴逵為個案
宋明好,謝 飛
(1.皖西學院 文化與傳媒學院,安徽 六安 237012;2.六安市金安職業學校,安徽 六安 237016)
東晉之世,隱逸風尚伴隨著玄風一并進入高潮時期,隱逸內涵呈現出多元化,隱逸模式也日趨多樣化,有一種與當時以玄學為依歸的隱逸模式不同的類型,尚未引起足夠的關注。《晉書》列傳第六十四《龔玄之傳》記:“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并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1](P2459)依仁游藝,語出《論語·述而》:“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2](P67)作為一種獨特的隱逸模式,既有其悠遠而豐富的思想淵源,也有其鮮明的時代特征,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此,筆者作一點淺探,以就教于方家。
一、“依仁游藝”的形式特征
自西漢末年以來,至東晉之前,北方隱逸士人逐步形成了兩大團體,據陳君先生分析,“其中尤以青土隱逸、關隴高士為代表。這兩個地域不但隱逸士人數量眾多,而且有鮮明的群體風格。”[3]所謂“鮮明的群體風格”,實際上是指兩大團體有各自的隱逸風格,但是兩大團體同時也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儒學特征。關隴高士如法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4](P1044)又如摯恂治五經,扶風馬融等遠至求學。青土之士如氾毓,“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凈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咨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余言。”[1](P2350)《晉書》卷91《劉兆傳》:“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1](P2349)由此可見,當時很多隱士皆從事儒學研究和教授,《氾毓傳》中描述青土隱逸群體“皆務教授”,可見其一斑。與氾毓相比,劉兆的教學規模可謂相當宏大了。
不惟北方隱士多以教授為務,戴逵的業師陳留范宣也是如此,范宣當為寒門士族,所以躬耕教授以自給。《晉書》卷91《范宣傳》:“宣遂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1](P2360)而且范宣“年十歲,能誦《詩》《書》”“尤善三禮”,可見在玄風熾盛之時,被邊緣化的儒學仍在隱逸群體的師徒教授中不斷傳承,這是中國文化史上頗有意味的圖景,隱士們甘于寂寞且意志堅定。戴逵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接受了儒學的熏陶。
從戴逵的生平事跡來看,他深達儒學之精粹。《晉書》本傳記:“(戴逵)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1](P2457)所謂“以禮度自處”,尊禮守法,正是個體依仁求道的終極目標。其子戴顒亦有其父之風,“顒年十六,造父憂,幾于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5](P2276)以此可見戴氏家風,父慈子孝,頗合禮度。且子承父業,什么業呢?“父善琴書,顒并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這個業,就是音樂,也就是“游于藝”。
戴逵雖然皈依儒學,但是他沒有以儒學教授,而是投身藝術,也即“游于藝”。這個“藝”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藝術,而是指“六藝”,也即禮、樂、書、數、射、御。所以戴逵所擅之藝——“樂”正在其中也。除了“樂”之外,戴逵的擅長是繪畫和雕塑。《晉書》本傳記戴逵“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余巧藝靡不畢綜。”文章,音樂,書畫,樣樣精通,除此之外,還身懷多種才藝。其才藝之多,實屬罕見。《世說新語·識鑒》十七條:“戴安道年十余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6](P353)
就藝術成就和美術史的敘述來看,戴逵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繪畫和雕塑上,而且后來他的畫名卻為他的雕塑聲譽掩蓋了。實際上他的繪畫成就是不可低估的,南齊謝赫《古畫品錄》評論戴逵的繪畫:“情韻綿密,風趣巧拔,善圖圣賢,百工所范。荀衛之后,實為領袖。”謝赫高度評價了戴逵在人物畫創作上面所取得的成就。王伯敏先生認為,戴逵在山水畫開創時期,“還是一個先驅者”[7](P75)至于在佛像雕塑方面,更是成就輝煌。金維諾先生評價戴逵是“佛像雕塑藝術中國化過程中,做出了貢獻的代表人物”,其雕塑作品是“杰出的中國式佛像的代表”。金維諾先生還特別評價了《世說新語·巧藝》中的一段記錄“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金維諾說:“這簡短的記事也是很值得玩味的。戴逵不認為佛像的神情‘太俗’(太像現實人物)不對,正說明他是有意識地在宗教形象中賦予人的性格,是在通過宗教藝術曲折地反映他對現實的認識。”[8](P87)這段分析尤為深刻,指出了戴逵在藝術上有著自覺的創新意識和非凡的創造力。
確實,戴逵在佛像雕塑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法苑珠林》卷24記戴逵:“乃作無量挾侍菩薩,研思致妙,精銳定制。潛于帷中,密聽眾論,所聞褒貶,輒加詳改。……委心積慮,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逵又造行像五軀,積慮十年,像舊在瓦官寺。”從這些記載,再結合上述美術史家們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戴逵潛心畫藝,深研精思;廣泛聽取觀者的意見,反復修改,反映了他對于藝術的忠誠。而且每造一像,動輒數年,可以說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獻給了雕塑藝術,繪畫和雕塑是他的生命方式。
二、“依仁游藝”隱逸模式的時代特征
“依仁游藝”隱逸模式思想淵源顯然是來自儒學傳承,但東晉時代的文化環境與春秋乃至兩漢時代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依仁游藝”不是對儒家思想的單純接受,而是在現實的思想斗爭中確立起來,而且有所發展。
(一)在反玄學斗爭中顯出深厚的儒學學養
戴逵身處玄風熾盛之世,而深以元康(晉惠帝年號,公元291—公元299)以來放達的形式化為非道,乃撰《放達為非道論》,其論曰:“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1](P2457)戴逵尖銳地批判元康所謂的玄學名士的虛誕,認為他們的放蕩恣情是“捐本徇末”,“舍實逐聲”,相對于正始之放來說只是貌似而已。所以,戴逵進一步指出:“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戴逵認為,正始年間的放達是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的,而元康玄學名士(謝鯤,胡毋輔之,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世稱“八達”)的放縱是舍實求名,舍本逐末。對此,戴逵還有進一步的論析。
《世說新語》“任誕”篇:“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劉孝標注引戴逵《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后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于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樂廣也是玄學家,善清言。元康玄學名士的“放蕩越禮”連他這個玄學名家也看不下去了,忍不住譏諷說:“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于此!”樂廣的這句話并見于《晉書·樂廣傳》和《世說新語·德行篇》,《晉書·樂廣傳》:“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世說新語·德行篇》:“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比較一下,乃知戴逵引用時略作改動,“何至于此!”語氣更強烈,批評更尖銳。戴逵對樂廣的評價深為嘆服,感慨地說:“樂令之言有旨哉!”有什么“旨”呢?戴逵的這句感嘆至少有兩層含義。第一,肯定名教,而且認為只有以名教為“樂地”才是真正的依仁復禮。在此之前,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命題,調和了禮教與玄學的矛盾。戴逵借樂廣的話所闡述的命題則回到了儒學最初的命題,當初孔夫子為了使人們自覺地遵守周禮,創造性地提出“仁”的思想,并希望“仁”成為人們發自真情的自覺要求,而且以之為樂。“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子雖然泛指人們對待事物的態度,但是依仁復禮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樂’——外在的規范最終轉化為內在的心靈的愉悅和滿足,外在和內在、社會和自然在這里獲得了人的統一,這也就是‘仁’的最高境界。”[9](P3)也就是說,依仁,以仁為樂,這是戴逵稱贊樂廣之言的真正原因。第二,樂廣之言肯定禮教,批評元康玄風,戴逵對他這句話的理解應該更加深微,因為元康玄風承自正始之風,那么,正始年間阮籍、嵇康放達任誕應該怎樣認識呢,戴逵認為“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顰者也。”竹林七賢的放蕩越禮是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的,他們在內心是熱愛禮教的,他們放蕩越禮是反抗假名教,反抗利用名教謀求私利的黑暗政治,所謂放誕以書憤,弄狂以流悲是也。所以,當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準備學他父親的樣子“作達”時,阮籍立即阻止了他。因為在阮籍看來,阮渾根本沒有弄清自己父親為什么要放蕩越禮的。所以,戴逵的認識十分清晰,他說:“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第三,自元康以來,所謂名士的放縱恣肆是在“利其縱恣”,亦即矯情以干譽,邀名以徼利。以放達任誕贏得世名,再謀取高官厚祿。一面盡去禮法,行若脫俗;一面又放浪形骸,驕奢淫逸。行為極其卑劣。所以戴逵批評他們利縱恣,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然后我們來看一則《世說新語》里尤為著名的故事——“雪夜訪戴”: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1](P656)
這是一場表現暢玄主題的出色表演。主角王徽之(字子猷),玄學名士,全篇都是他的戲。而戴逵(字安道)只是被置作背景,王徽之拜訪戴逵至門前而返,有人問其緣故,他說:“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不拘禮數,何其放達!可惜,把戴逵背景化是其敘述的重大失誤,因為稍稍有些歷史常識的人都明白,這個以放達自炫的王徽之他有信心去敲那個以放達為非道的戴逵的門嗎?因此,小說中的戴逵沒有言語,并不代表他就沒有聲音。“此時無聲勝有聲”,如此,王徽之的任誕作達的表演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了。
(二)在時代發展和藝術實踐中擴展“藝”的外延
晉孝武帝司馬曜詔書所說戴逵、龔玄之“依仁游藝”的“藝”,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六藝”。從戴逵的擅長來看,更多的是指琴藝。《晉書》戴逵本傳:“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世說新語·雅量》:“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從這些記載中,我們看到戴逵的琴藝十分精湛,他在音樂上的確有很深的造詣。
但是,他的藝術成就更多的是表現在繪畫上,與他同時或稍后的藝術家、藝術評論家都充分肯定他的繪畫藝術成就,前引謝赫《古畫品錄》里的評論和《法苑珠林》的述評,都表達了這樣的認識。《世說新語·巧藝》:“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老師范宣認為戴逵的繪畫(山水畫)“無用”,不應該在這方面勞神費力,但是戴逵畫的《南都賦圖》,表現出高超的技藝,具有巨大的藝術感染力,最終改變了老師的態度。范宣因此也看重繪畫了,實際上也認同了繪畫這一“六藝”之外的技藝。
山水畫,魏晉時期是初創期,人物畫和雕塑也處于重要的發展時期,《世說新語》“巧藝”篇記錄了當時諸多技藝,其中尤以繪畫為最。戴逵跟隨時代步伐,投身繪畫和雕塑藝術之中,在“六藝”的基本范圍中,作了一定的拓展,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達到了“游”的境界。雖然今天我們不能直接看到他的作品了,但是其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三、“依仁游藝”隱逸模式的文化史意義
“依仁游藝”隱逸模式的出現,特別是以戴逵為代表的士人的實踐和拓展,使得這種隱逸模式在隱逸文化史上獲得了豐富的意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隱逸方式的新拓展
“依仁游藝”隱逸模式,從思想內涵來看,屬于儒隱,而且從語源來看,也證明了這一事實,“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儒家積極入世,同時也不廢隱逸,“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但是,對于儒家來說,隱逸只是一個手段,或者說只是權宜之計,最終目標還是入世行道。所以,從隱逸模式的源起來看,“依仁游藝”早已有之,戴逵等人的隱逸思想是以儒學為旨歸的。但是,問題沒有這么簡單,文化環境的新變和時代特征決定了戴逵們的隱逸一定有新的發展。從隱逸的目標來看,“依仁游藝”隱逸模式又屬于道隱,道家避世,以出世為隱逸的最終目標。所以,從戴逵諸人的出處來看,又具有道隱色彩。從隱逸方式來看,是隱于藝,所以是“藝隱”。從戴逵的藝術成就和影響來看,他在繪畫和雕塑的藝術世界中自由馳騁,獲得了主體精神的自由,“游”,無侍無待,既有在藝術中實現主體精神的對象化,也有在藝術活動中進入精神的自由自然的境界。同時,戴逵的隱逸不是如道家那種徹底的離世避世,而是不離塵俗生活。《世說新語·雅量》注引《晉安帝紀》記戴逵:“性甚快暢,泰于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游燕。多與高門風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隱不絕俗,潛心游藝,這是戴逵們隱逸的顯著特征。
(二)在藝術活動中實現隱逸文化精神的高揚
首先,隱逸使藝術創作主體獲得了超脫凡俗的自由感,擺脫外在功利的束縛和壓迫,擺脫群體意識對個體的遮蔽和擠壓,這是從事藝術創造活動的先決條件。戴逵面對朝廷的屢次征召,無一應命,這就擺脫了現實政治對個體身心的困擾,獲得從事藝術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同時,戴逵的藝術創作與自己的哲學思考緊密結合,譬如,他著有《竹林七賢論》,同時又以竹林人物為題材,進行人物畫的創作,他的人物畫一定體現著他對竹林人物精神特質的深刻理解。其次,在藝術創作中進一步彰顯隱逸文化精神。藝術作品是人的精神的表現,戴逵們的藝術活動就是他們隱逸文化精神的體現。所謂隱逸文化精神,就是主體精神自由,人格獨立,回歸自然;對于戴逵來說,還有一條,即依仁義,遵禮法。戴逵的作品(音樂的或美術的)應當體現著這種精神,只可惜我們今天不能對照他的作品來仔細感受了,只能通過生活細節來感受這種人格魅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晉書》戴逵本傳的這則記述,我們可以見出戴逵的人格特質,與他的兄長戴逯形成鮮明的對比。
“依仁游藝”隱逸模式,經戴逵等人的實踐,實現了人生的藝術化、審美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子戴勃、戴顒秉承父業,在思想(出入儒道釋三家)和藝術上都有所發展。劉宋時期的宗炳,也是隱逸不仕,在繪畫藝術和繪畫理論兩個方面都有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