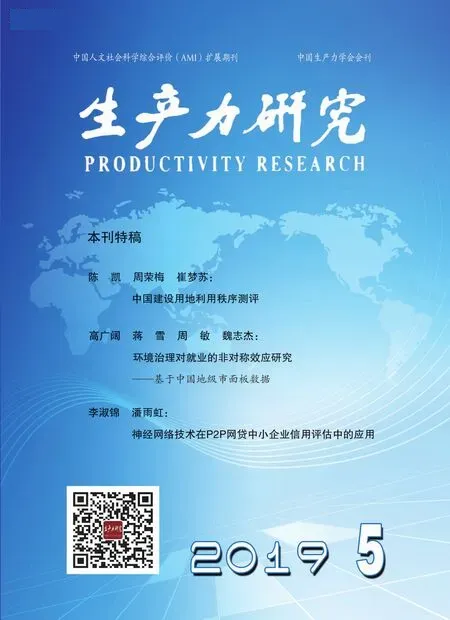煙草企業價值理性的回歸與倫理建構
張博聞 ,姜孟鵬 ,楊國慶
(1.江蘇師范大學 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2.江蘇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 徐州卷煙廠,江蘇 徐州 221000)
一、引言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作為人類理性中兩大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兩者的對立與統一始終推動著人類經濟社會在倫理軌道上的發展和變遷。伴隨著數次科學技術革命,逐漸崛起的科學技術令工具理性經常性抬頭,與價值理性之間的平衡關系也經常性地被打破。在當代經濟社會,一旦價值理性對工具理性缺乏有效制約,就會令價值理性產生背離,并對經濟社會的倫理建構提出挑戰,這就使以價值理性的回歸來完善倫理建構顯得尤為重要。
煙草產業是當代經濟社會中的特殊產業,在經濟貢獻和倫理爭議兩個維度上具有一定的矛盾屬性。自煙草這種自然植物被人類發現并利用以來,尤其在經歷地理大發現和數次工業革命的洗禮后,人類對煙草利用效率的不斷提高,以及煙草科技水平的不斷迭代,不僅導致人類在使用煙草過程中感官享受的不斷升級,更致使人類對煙草及其制品需求的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全球煙草種植和煙草制品生產的總體規模的擴張始終未出現過停滯,煙草為人類作出突出經濟貢獻的地位也始終未得以有效的撼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公眾健康意識的覺醒,“吸煙有害健康”逐漸成為人類共識,人類控煙訴求的高漲和世界各國對煙草企業所能創造的大量財政收入的依賴,也在倒逼著全球煙草企業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天平上平衡發展。
有賴于龐大的國內市場和極具潛力的國際市場,我國煙草產業以其巨大的體量,在全球煙草產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作為經濟組織,我國各大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平衡與否,將影響整個產業的經濟行為,繼而影響全球煙草產業理性天平的傾向,甚至影響倫理基礎的虛實。當代,我國在煙草農業、工業、機械以及投資領域的實力,均是全球煙草產業中不可忽略的一極。同時,全國煙草系統所直接面對的也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國內煙草消費市場,這也帶來了諸如煙草企業的發展是否道德、煙草企業的經濟作用與社會責任本身是否道德,以及我國煙草科技的發展與迭代是否道德等一系列倫理問題。但問題終究是表象,表象之下的實質還是我國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
長期以來,在來自經濟與社會的雙重壓力下,煙草企業在理性的平衡上時而出現偏頗,尤其是對價值理性的經常性疏離,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成為各種產業危機的隱患因素。因此,做好深刻的反思,協調好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關系,讓工具理性不再片面地抬頭,讓價值理性得到真正的回歸并實現良好的倫理建構,是當今我國所有煙草企業必須做好的一門功課。
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于煙草企業的哲學涵義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對社會行為的決定因素進行考察時,提出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并在其著作《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里詳細闡述了兩者的界定和差異。
(一)工具理性的涵義
馬克斯·韋伯認為,工具理性是指“行為者預期外界事物的變化和他人的行為,并利用這種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以實現自己當作成就所追求的、經過權衡的理性目的”[1]。由此可見,韋伯的工具理性強調的是目的、條件和手段,條件和手段是目的得以實現的前提。
韋伯所指的預期外界事物的變化和他人的行為,是歷史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新的目的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外界事物變化和他人的行為上,新的目的的實現也將繼續促成更新的目的的實現。就煙草企業而言,一家企業若期望能滿足消費者需求而生產出一種較之過去危害更小的卷煙產品,就必須要有卷煙產品新減害工藝的出現,或者最起碼要有對卷煙產品新減害工藝的研發行為,當這種企業所期望的危害更小的卷煙產品出現的時候,企業又可能會期待能生產出危害比之更小的卷煙產品,從而作為一種新的目的,繼而就會有更新的減害工藝的出現。因此,世界煙草科技水平之所以有如今的高度,正是因為新目的不斷地出現與實現,這是理性中的工具取向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當然,理性在現代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空前發展的現實環境下,也會作為一種純粹的方法而繼續指導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的再發展。對于我國的煙草企業來說,理性促進了企業發展,但這種發展也使理性變成了實現實用經濟目的的工具,即企業的工具理性不僅是由企業自身的發展而產生的,更是由專賣制度的強化、產銷規模的擴張、業務范圍的拓展、煙草科技水平的進步等外部環境的變化而促成的。同時,伴隨著煙草稅利的不斷增長,以及企業分工的多樣化與專業化,對諸如經濟效益與經濟地位等工具性對象的滿足,也讓工具取向悄然破壞著企業理性應有的平衡,改變了企業理性的維度[2]。
(二)價值理性的涵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上的價值范疇,是揭示外部的客觀世界對滿足人的需要的意義范疇,是指具有特定屬性的客體對于主體需要的意義。韋伯在對價值理性的界定上,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價值的基本觀點在“主體需要”的層面上是趨于一致的。韋伯認為價值理性是指“行為者自覺地和純粹地信仰某一特定行為固有的絕對價值(例如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性質的絕對價值),而不能考慮是否取得成就”[1]。韋伯的價值理性的重點在于人類對價值的自覺,“自覺”就是“主體需要”。因此,我國煙草企業的自覺就是自覺地信仰國家與消費者的利益,這是煙草企業得以倫理地存在的需要。
韋伯的工具理性沒有否定其為純粹的行為者利益的導向,它強調實在的效率與效益,更加重視目的本身而不論目的是否具有正當性,或者是否合乎理性。因此他創造性地提出了價值理性這一概念,用以與工具理性實現互約互補乃至共贏。
于煙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言,韋伯的價值理性就是企業在用煙草及其附屬產品創造社會財富時的倫理理性,其不僅要以一種肯定性價值作為基礎,更要以一種倫理應然來規范企業的經濟行為,這就等于是為企業的工具理性鋪設了一條倫理的軌道。
然而在眾多煙草企業的現實表現中,以中國煙草行業核心價值觀為代表的價值理性,常常因工具理性的抬頭而無法完全展現出它應然的作用,但卻也從未離開過時刻進行著的眾多煙草企業的發展進程。也就是說,不少企業當下雖然因對自我生存意義的困惑而更關注作為成就的經濟目的,以及達成它的條件、手段與效率,但也并未完全忘記價值理性,故而企業的行為看起來確實是工具理性行為,這種現象目前廣泛存在于我國各大煙草工業企業的品牌競爭當中。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煙草企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其取得合理的經濟利益是為社會創造更多新的財富的必要條件,企業如果只單純地作出承擔社會責任的價值理性行為,而不考慮工具理性,也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完成國家下達的經濟任務,最終造成國家財政的重大損失,這也就背離了價值理性。因此,在煙草企業追求經濟效益的背后,一定有諸如稅利貢獻、控煙履約、維護國家利益、保障消費者利益,以及公益事業投入等社會責任的同步履行,這是企業價值理性對工具理性的實在約束與補充,而當工具理性抬頭之時,社會需要的只是企業價值理性作用的及時發揮。
三、煙草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應然之態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作為人類理性之中的兩個重要維度,它們雖然相互區分,但卻又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邏輯聯系。因此,二者之間的關系絕對不是相斥相離的,而應是對立統一的。中國煙草企業的理性問題是一個很值得耐人尋味的倫理問題,它的正面是國家與消費者的切實利益,反面則是對公眾健康的現實危害。在控煙履約與國民經濟的雙重社會需求下,煙草企業始終在夾縫中尷尬求生,擴大產銷規模是對公眾健康的責任缺位,縮減產銷規模又是對國民經濟的不作為。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不能平衡,是擺在我國各大煙草企業面前的一大現實問題,這就需要明確這兩種理性在企業生存與發展中以應然之態為表征的邏輯關系。
(一)企業的價值理性要為工具理性的先導
韋伯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行為界定為:工具理性行為是“行為者以目的、手段和附帶后果為指向,并同時在手段與目的、目的與附帶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種可能的目的之間做出合乎理性的權衡,然后據此而采取的行動”。價值理性行為是“行為者可以無視、可以預見的后果,而僅僅為了實現自己對義務、尊嚴、美、宗教訓示、崇敬或者任何其他一種‘事物’重要性的信念,而采取的行動”[1]。由此可見,人的行為在工具與價值兩種理性的維度上,起碼要服從某種目的,或者能體現某種肯定性的價值。這于煙草企業而言,以“國家利益至上,消費者利益至上”為內容的中國煙草行業核心價值觀及由此所主導的行業社會責任為代表的價值理性,要為以實在的經濟效益為核心的工具理性提供行為之時的意義。也就是說,煙草企業在作為工具理性行為以實現最大化的效率時,必須承載有價值理性的切實訴求。企業經濟利益的取得,只有在企業價值理性的有效規范與約束中,才能避免企業的異化,從而使企業的正常生存與倫理發展成為可能。
(二)企業的工具理性要為價值理性的基礎
工具與價值這兩種理性的對立統一的應然,注定了二者不能獨立地實行獨裁,缺少工具理性的價值理性是難以獲得真正肯定性后果的。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體現的是企業對增強競爭實力的欲望以及對國內外煙草市場環境的整體把握,我國煙草產業的整體規模之所以能不落后于世界其他國家與國際煙草巨頭,正是因為有全體煙草企業自己的工具理性行為的保障,這是煙草企業能夠以巨額稅利等時代使命的履行而服務于國家利益的現實基礎。各大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通過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不斷拓展著我國煙草科技與市場疆域的邊界,繼而推動企業價值理性不斷地確立新的企業目標,并確定企業新的存在意義,企業工具理性如此也就使企業價值理性擁有了實在的基礎。煙草企業價值理性對工具理性的指導體現了企業的倫理建構[3]。
(三)企業的實踐要寓于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之中
人類的實踐活動只要基于某種特定的目的,才能夠使人在具體的工具上擁有一定的需求。在煙草企業的生產經營實踐活動中,各個工商企業均是以具體工具式的存在作為條件和手段,從而選擇具體的實踐對象與實踐方法。在現實實踐中,企業的價值理性解決的是“企業作出什么行為”的問題,如在精益制造、提稅順價、限產壓庫、調整種植、品牌發展以及企業文化建設等企業行為的作為;工具理性解決的是“企業怎么作為”的問題,如精益制造怎么實現、限產壓庫怎么計劃、種植規模怎么調整、企業文化怎么建設、品牌發展戰略怎么規劃、提稅順價政策怎么制定與執行等。企業工具理性通過對企業具體實踐活動進行具體的分析與計算,使得企業能夠根據國家計劃、自我產能、市場形勢、科技水平、人力資源以及政策環境等現實基礎,逐步達成由價值理性所確立的以為國為民為主流內容的企業愿景。因此,在我國煙草企業的實踐活動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這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這種統一始終推動著企業在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不斷地進行創新,并探索出新的存在意義[4]。
四、煙草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野
工具與價值這兩種理性均有屬于自己的領地,并作為獨特的因素影響著人類行為的決定。正由于這二者的對立統一關系,使其在作出我國煙草企業具體行為的時候,降低了企業脫離倫理軌道的風險。但伴隨著稅利的持續增長,以及體量的不斷膨脹,煙草企業近年來始終在工具理性的引導下,頻發諸多因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而導致的并發癥。與此同時,以功利取向為主要代表的社會負向精神暗潮,不僅給煙草企業提出了正確地與社會現實環境相處的倫理要求,更為其出了一道如何給工具理性降溫并且讓價值理性回歸的倫理難題。
(一)市場下行小冰期間的理性失衡
自我國于2015年開始施行新的卷煙產品提稅順價政策起,我國煙草行業經歷了為期兩年之久的行業小冰期,國內各個煙草工商企業在市場形勢與國家經濟重擔這兩座大山的重壓下,逐漸開始忽視自我存在的意義。在此期間,體量大的企業把贏得市場競爭作為純粹目的,體量小的企業把被動地完成任務作為純粹目的,這都是工具理性抬頭下的企業行為。雖然全國煙草行業在小冰期保證了上繳稅利任務的完成,這看起來是價值取向的勝利,但在卷煙產品產銷雙降的現實情況中,各大煙草企業依然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上出現了分歧。
我國煙草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分野的出現,與兩者平衡關系的失調有關,而這種失調不僅有工具理性行為一方壯大的外因,更有價值理性行為缺位的內因。企業工具理性有其專有的作用范圍,即描述整個企業的實然狀態。但在經歷了下行的市場形勢后,部分不堪忍受市場下行的煙草企業開始出現工具崇拜的傾向,把現實的經濟利益作為純粹的目的,把手段與目的同倫理割裂開來,將“命保下來”和“日子過好”奉為其行為中扭曲的價值取向。
畸形的價值理性行為最終使不少煙草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二者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嚴重的背離,令“國家利益至上,消費者利益至上”的中國煙草行業核心價值觀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些企業的理性不再完全是有機統一的理性,而是時常被肢解為缺乏生命力的工具與價值兩個維度的孤立存在,僅有少數價值理性尚未完全缺位的“家大業大”的煙草企業維持著岌岌可危的企業理性的平衡。
(二)市場回暖后的工具理性固化
在市場形勢上,全國煙草市場在2018年已基本走出低谷,正在穩中求進,同時,伴隨著行業稅利的再創新高,我國的煙草消費浪潮尚未褪去,消費者對各類卷煙產品的實際需求量還在持續增加,尤其是對中高檔的一類與二類卷煙產品需求量的增幅更為明顯。即使在國家煙草專賣局明確卷煙產品規格牌號只減不增的政策要求下,全國各大煙草企業仍然在以產品更新迭代的方式,加快對新產品的研發與上市速度,以滿足消費者追求感官體驗升級與健康危害降級的新型消費需求。在國內煙草品牌與產品的龐大陣容中,消費者鐘情經典與求新嘗鮮的需求都能有效地得以滿足,這也促進了煙草企業在新時代的發展。可市場形勢的向好,盡管令起初“喘不過氣”的煙草企業恢復了元氣,但這其中依然有不少企業把日漸向好的經濟利益作為企業的存在意義。在飽嘗市場回暖的甜頭后,其理性思維已經普遍讓渡于對經濟效益的物質性享受,繼而產生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不斷增長的企業財富才是企業根本價值取向”的觀念。這種純粹對經濟方面的片面強調,有違煙草企業本真的價值理性。
(三)基層一線的價值理性弱化
生產制造、倉儲物流、設備維保、煙葉收購、鄉鎮營銷等環節,是煙草企業基層一線崗位最集中的領域,同時也是企業最能夠創造價值以及最需要創新活力的“自覺”實踐環節。但在當下,眾多煙草企業在基層一線環節上出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企業的行為本身開始逐漸暴露出以基層一線中人的主體地位下降為代表的人文關懷缺位問題。近年來,煙草企業的招聘進入門檻以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應屆畢業生為主,這使得煙草企業擁有了一支人數眾多的高學歷與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其相對可觀的待遇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才加入。青年人才下基層一線始終是眾多煙草企業的慣例,其初衷是為了讓青年人才能夠從最根本處成長,進而為企業的發展遴選與儲備骨干力量。但隨著企業工具理性的抬頭,讓本是企業寶貴資源的青年人才隊伍從主導基層一線工作的主體,變成了基于純粹經濟效益目的而存在的生產經營工具,并有向淪為基層一線環節附屬品傾斜的危險。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下,人本主義明顯弱化,處在最基層的青年人才也逐漸有了“以薪水作為純粹的目的”的負面傾向,這導致了主導基層一線生產經營活動的人變成了純粹的被管理的對象,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價值訴求被工具理性掩蓋,人與人之間的先在關系開始異化為企業基層生產經營活動中人與設備、人與產品、人與經營行為之間的關系,這是對企業價值理性的反譏。
(四)企業文化價值空心的暴露
在企業文化上,工具理性在西方世界因長期獨裁了經濟領域,便對各種經濟組織的自體文化進行干預。在我國,煙草企業雖然有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成員的自體性質,但也無法孤立于國際煙草市場之外。伴隨著國外煙草巨頭對我國煙草市場的不斷覬覦,工具理性也開始對我國煙草企業的企業文化進行滲透。工具理性首先質疑中國煙草行業“國家利益至上,消費者利益至上”核心價值觀價值取向的合法性,并以純粹的工具理性的分析與計算結果,來認定這種行業核心價值觀與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合乎企業作為經濟組織而應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范式。于是企業價值理性受到了挑戰,并在企業文化中暴露了出來,如將對卷煙產品牌號的廣告化宣傳內容列入企業文化框架,亦或將沒有實際價值理性意義的口號以及純粹的經濟利益導向的內容納入企業文化體系,造成相當一部分煙草企業文化的價值空心,這是價值理性在企業文化領域上的失責性缺位。
(五)“兩個至上”為理性的平衡兜底
價值理性的缺位、工具理性的不斷做大,這種不健康的關系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遏制,將必然導致煙草企業走向工具化,令原本極富生命力的企業價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取代,并對整個煙草產業倫理的正常存在構成威脅。但我國煙草行業始終擁有以“兩個至上”為主體內容的行業核心價值觀,即“國家利益至上,消費者利益至上”,同時還有與之相匹配的核心價值體系,這是煙草企業價值理性的基點。而純粹工具理性的固步自封,最終也只能將其自囿,這也是工具理性本有的自我反作用所決定的[5]。
五、煙草企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合之途
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應然之態在前文已作論述,但現實中兩者關系的分野,使企業之現實與其應然之間確有脫離嚙合之處。面對整個煙草產業的倫理危機,煙草企業經常性越位的工具理性難辭其咎,可工具理性并未有原罪,只是一味地問責工具理性確為不妥。因此,讓企業的價值理性得到應有的回歸并實現真正的倫理建構,才是整個煙草產業能夠繼續得以生存與發展的不二法門。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煙草行業經歷了數次的體制改革,從最初的地方國營,到后來的國家煙草專賣制度以及集中管理體制的確立,整個行業在其發展過程中,公有制的性質從未發生過任何改變,無論是其農業系統、工業系統還是商業系統,任何煙草企業都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主體,而從未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牟取暴利的工具。同時,“兩個至上”的行業核心價值觀,始終是我國煙草企業的價值圭臬,這是有別于世界上其他未施行煙草專賣制度的國家的,也是我國煙草企業價值理性能得以回歸并完善企業倫理建構的基礎[6]。那么要實現這種回歸與建構,起碼需要處理好三對關系。
(一)企業與社會
中國煙草行業的行為信條是“潛心做事,低調做人”,這是行業拒絕自我中心主義的公然承諾,是把國家與消費者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意思表示,這首先避免了煙草企業與社會的倫理沖突。但僅僅避免倫理沖突并不能讓煙草企業的倫理范式得到很好地建構,企業還需要對煙草的矛盾屬性同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刻反思,自覺地將社會責任納入到企業自身的倫理責任中,且始終以對嚴格控煙履約、完成稅利任務、提升科技水平、捍衛專賣制度、升級市場服務、拓展國際市場、維護國家與消費者利益以及加大公益事業投入等眾多責任的切實履行,讓社會的利益得以先行。如此,煙草企業便突破了其原有的利益局限。
同時,滿足社會需要也是煙草企業的正當利益。由于煙草企業的正當利益也是社會整體利益的有機構成,社會不能因煙草的矛盾屬性就孤立煙草企業的存在,也不能因為煙草產業的倫理爭議與其在經濟上的義務,便對煙草企業的正當利益進行肆無忌憚地攫取。此外,社會也應讓煙草企業在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上擁有合理的自由意志,并為其倫理地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此實現企業與社會的共贏。當然,如果需要煙草企業為社會的發展,或者其他行業企業要為煙草企業的發展作出合理且必要的犧牲,受益一方則必須要對犧牲一方作出應有的補償,如此才能有效增強我國經濟社會的集體凝聚力。
(二)經濟利益與價值實現
純粹經濟利益與人文關懷的背離必然會導致純粹經濟利益的單方做大,并使經濟利益的取得缺少人文關懷的正確指引,最終背離經濟的價值理性。處理好正當的經濟利益與以人文關懷為核心的價值實現之間的關系,堅持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有機統一,如此才能真正令我國煙草產業的發展與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現正面的雙向互動。煙草企業在取得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務必把以中國煙草行業核心價值體系為代表的人文精神作為企業精神的基本導向,由此來對企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進行和合,并賦予經濟利益本身以價值實現的意義。煙草企業對經濟利益的正當取得是企業價值得以實現的基本手段,但任何煙草企業都不能本末倒置,錯把手段當目的,否則企業又將繼續陷入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二者沖突的泥淖之中。
(三)短期效益與長遠發展
人類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下,很難做到以小見大或見微知著。人類通常只關注某事物的即時影響,或者只關注事物對某個特殊群體所產生的影響,而不去探究某事物對所有群體造成的長遠影響,繼而忽視那些不是那么即時或不太明顯的后果[7]。由這種經濟短視而對人類文明造成的破壞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歷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危機的出現,人類執著于技術與經濟利益的即時反饋和對特殊群體的影響是難辭其咎的。這對我國煙草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當前國內煙草市場的回暖與煙草產業經濟效益的平穩向好,并不意味著煙草產業危機的解除。向智能化與精益化的新型煙草企業生產經營組織模式轉變,并居安思危,隨時代之進而進,不僅在我國,甚至是在全球煙草產業也已然達成了共識。但對迷戀于緊抓短期盈利與著眼當時稅利任務的經濟短視,而拖延對以高消耗與低人均產能為代表的傳統煙草企業生產經營組織模式的改造,將制約著煙草企業的長效發展。煙草企業目前真正需要的,是時刻繃緊神經來避免對即時反饋與對特定群體影響的迷戀,甘于長期深入推進對傳統模式的改造,進而防止做大的工具理性繼續挑戰企業倫理的建構。
六、結論
伴隨著我國對《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全面履行,煙草企業所面臨的倫理困境也將繼續考驗著全國50余萬煙草系統干部職工的集體智慧。根據相關數據統計顯示,目前全世界約有12億煙民,而其中我國的煙民就約有3.5億,且這個數字仍在持續增長。中國的煙草企業多年來一直艱難且尷尬地維持著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平衡,在創造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在控煙履約上不斷地進行著正面作為,并盡一切可能積極地采取各種措施降低由煙草所帶來的健康危害。
但對煙草的控制,不是能畢其功于一役的,煙草在中國與全球依然擁有異常龐大的市場才是真實的社會現實。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煙草消費市場,我國煙草企業對國家利益與消費者利益的保障是責無旁貸的。唯有勤于、勇于與善于承擔行業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態以及倫理上的責任,促進企業與社會的正向良性發展,樹立企業健康良好的社會形象,打造領跑全球的知名品牌,才能讓煙草企業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兩者關系和諧的狀態下助力整個煙草產業在新時代的飛躍,才能讓企業的價值理性在新時代實現回歸并完成有效的倫理建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