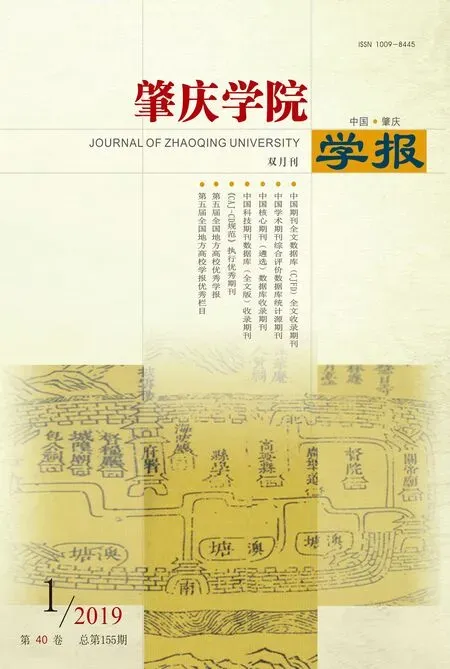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與逆全球化的關聯和應對
郭振雪
(肇慶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這是時隔26年后,我國最高級別黨代會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論述的首次重大修正①1981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用更為科學的語言表述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二大確認了這一提法,并載入黨章,黨的十三大又把這一提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這次修正將對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審視和分析有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從前者看,這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我國社會發生的歷史性劇變的理性反思;從后者看,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與20世紀90年代末興起的逆全球化“悖逆”的議題和內容有諸多關聯。因此,分析逆全球化與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之間的關聯和意蘊更能加深我們對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增強我們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一、逆全球化:意欲何“逆”?
談論逆全球化,就不得不提全球化。一般認為,全球化發軔于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迅猛發展于1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形成,深化拓展于20世紀90年代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加速推進。而逆全球化思潮和運動在上個世紀末才正式進入世人的眼簾并逐漸引起全球的關注。2016年,歐美政壇“黑天鵝事件”頻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意外勝出和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甚囂塵上,大有與全球化“徹底決裂”之勢。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地區,西亞北非地緣沖突持續、南美部分國家政局不穩,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的前行之路迷霧重重。凡此種種無不說明逆全球化已經成為當前全球化大勢中一股無法回避的思潮和力量。雖然逆全球化將完全取代全球化還為時尚早,但其議題和內容直指“美版全球化”。簡言之,“規則不公”和“發展之殤”是逆全球化“悖逆”的主要議題。
逆全球化映射的“規則之爭”主要表現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圍繞國際經貿規則改革所產生的矛盾和沖突。二戰結束后,美國構建了由其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黃金本位制”是該體系的顯著特征之一。20世紀70年代初,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解散,但憑借對關稅及貿易總協定(1994年至今改稱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的掌控,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仍然擁有無可爭議的話語權,并牢牢控制著國際經貿規則的主導權和制定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為例,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中國份額占比將從之前的3.996%升至6.394%,排名從第六位躍居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在IMF的份額占比首次進入前五名。盡管如此,IMF的組織缺陷和制度缺陷仍然廣為人所詬病。在當前的IMF架構中,組織機構仍由美國和歐盟控制,基金份額和投票權的分配仍具有濃厚的西方色彩,美國在IMF的重大決策上仍然擁有一票否決權。在此背景下,IMF竭力維護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而漠視或無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誕生的超主權貨幣的功能和作用。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當中。這就導致國際經貿規則的條款和內容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美國味道”。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縱深發展也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國際經貿規則的“偏西”色彩。這也是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貧窮落后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進入21世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不斷刷新和改變著既有世界經濟版圖,全球經濟格局的分化重組之勢愈發明顯。在此背景下,新興經濟體要求改革現行國際經貿規則,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愈來愈高。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絕不會輕言改革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其對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權和主導權的護持將不遺余力。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圍繞國際經貿規則改革的爭奪將是一個長期、曲折、復雜的過程。
逆全球化“悖逆”的“發展之殤”在全球范圍內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義理念引領的“美版全球化”①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核心就是要求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一體化,其中金融自由化又是經濟自由化的核心和“靈魂”。上述“四化”的統制性設計和安排使整個世界基本上被納入西方壟斷資本的控制體系。。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理念引領的“美版全球化”導致的“發展之殤”主要表現為貧富分化持續擴大、極化現象突出、中產階級萎縮、資本綁架民主、富豪統治、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以當今世界的頭號強國——美國為例。作為“美版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今天的美國也深陷新自由主義的泥潭難以自拔。以貧富差距為例,2014年,美國收入最低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上限為2.9萬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組年均收入下限為23萬美元,后者是前者的7.93倍。換一個角度說,占美國總人口比例僅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幾乎與占總人口高達90%的普通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相當。“金錢是政治的母乳”是對資本主義民主和政黨政治的形象概括。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組建的內閣被譽為著名的“富豪內閣”。2017年1月,特朗普及其“富豪內閣”正式入主白宮。據每日郵報報道,特朗普內閣的資產凈值超出了1/3美國人(約1億人口)的總財富。他的團隊大約有300億美元的總財富,其中包括六位億萬富翁,特別顧問卡爾·伊坎(Carl Icahn)是最富有的,有200億美元的凈資產;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和文森特·維奧拉(Vincent Viola)的財富已超過15億美元。由富豪統治和金錢政治引發的社會分裂和族群分裂已經成為當前美國社會的突出現象。打著“反建制主義”旗號入主白宮的特朗普及其“富豪內閣”能否兌現其在總統競選期間對美國中低下層民眾的承諾還存在很大的變數。
以新自由主義理念引領的“美版全球化”在侵蝕和削弱發達國家根基的同時,也給部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極為惡劣的經濟和政治影響。經濟領域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9年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出臺。這套針對拉美和東歐轉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一些國家備受推崇并大行其道,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位于南美洲的阿根廷。1989—1999年的十多年間,時任阿根廷總統的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Saúl Menem)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理念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促進阿根廷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但也為之后阿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01年,震驚世界的阿根廷經濟危機爆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阿根廷的實踐宣告破產。目前的阿根廷雖然經濟有所復蘇,貧困人口有所減少,但仍然沒能破解政策失誤、經濟低迷、腐敗橫行、經濟結構單一等發展難題。“美版全球化”在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同時,也不忘通過“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將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移植”到美國人眼里的所謂“專制國家”或“暴政前哨”。進入新世紀,美國主導并參與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并一手“導演”了當前還看不到盡頭的敘利亞內戰。遺憾的是,“美式民主”的“強行移植”留下的只有無休止的政治紛爭和乏善可陳的民生建設。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最終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阿拉伯之冬”,敘利亞內戰至今看不到結束的希望。這使得全球化進程中長期被邊緣化的一些中東國家的處境更為艱難,發展更為困難。
二、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與逆全球化的關聯和應對
黨的十九大判定的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將是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新政府著重解決的首要議題,而全球化將在和逆全球化的膠著與抗爭中“蹣跚前行”。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與逆全球化的關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
首先,我國在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安排中還處于不公平的被損害地位,變革國際經貿規則、塑造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能力亟待加強。這與逆全球化映射的“規則不公”“不謀而合”。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與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經濟體系經歷了被動隔絕(1949-1979年)、主動加入(1979-2001年)和快速融入(2001年至今)三個歷史階段。2001年11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一員,中國也從長期游離于國際經濟體系之外的反抗者、旁觀者轉變為參與者、受益者。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高,中國與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安排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這一矛盾的突出表現就是在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安排下,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還處于比較嚴重的不對等地位,以致美國動輒利用國際經貿規則的條款對中國揮舞制裁大棒。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中美雙邊貿易額雖然一直呈增長勢頭,但矛盾和沖突不斷。尤其是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為扭轉美國在對華貿易中的入超地位,不惜動用世貿規則的相關條款對出口美國的中國部分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此外,美國對中國通訊巨頭中興的制裁事件更是在一段時間內鬧得沸沸揚揚。中美貿易戰和美國對國企中興公司的制裁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這兩起事件共同證明了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霸權邏輯,即利用其在國際經貿規則和高新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徹底壓垮《中國制造2025》,迫使中國屈服,從而達到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
其次,逆全球化“悖逆”的“發展之殤”警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并積極解決當前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棘手議題。新自由主義理念引領的“美版全球化”是導致目前全球范圍內部分國家發展失衡、失序和失調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逆全球化的國內發展維度審視。就當前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而言,不平衡主要包括領域不平衡、區域不平衡和群體不平衡。具體而言,領域不平衡主要是經濟領域的一馬當先,政治社會文化領域的發展雖穩步推進,但與經濟領域相比還比較滯后。區域不平衡主要是指東中西部不平衡、城市與農村不平衡、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不平衡,甚至城市內部、發達地區內部、一些農村內部也存在不平衡現象。群體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社會群體在共享發展成果方面有差距,建立在良性橄欖型社會結構上的財富公平正義分配格局有待形成。發展的不充分主要是指整個社會的發展總量尚不豐富、發展程度尚不夠高、發展態勢尚不夠穩固。這種不充分體現在發展的方方面面,處于發展不平衡低端的那部分固然屬于發展不充分,而處于發展不平衡高端的那部分也存在著發展不充分①對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論述主要參考了中央黨校辛鳴教授的觀點。。客觀地說,我國當前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全球很多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和表現。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逆全球化折射的“發展之殤”和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關聯性。
從逆全球化折射的“規則不公”“發展之殤”及其與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關聯出發,有二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第一,以人為本,繼續加強和改善民生,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拓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深度和廣度。在當前的逆全球化思潮和運動中,民粹主義的興起是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但到目前為止,民粹主義仍然是一個沒有明確內涵的概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社會思潮,民粹主義本身并不“危險”或者說“邪惡”,但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當前風頭正勁的逆全球化),民粹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很容易結合并變成一股極具破壞性的力量。英國公投“脫歐”、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借歐洲難民問題發表反穆斯林移民的言論就是例證。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所言,上述行為是“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當前,我國正處在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弊端還比較嚴重,更需要警惕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合流。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1]同時,必須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利[1]。民生和民主猶如社會穩定的兩翼,兩者必須協調、同向、均衡發展,不可偏廢。
第二,以靈活的策略和切實的作為積極引領國際經貿規則改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為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循序漸進地最終解決構建有利的國際環境。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當前,“美版全球化”的活力和生命力都面臨重大考驗和挑戰,這為我們引領國際經貿規則改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重大機遇。但是,“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1]在機遇和挑戰并存,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兩股思潮和勢力相互交織激蕩的今天,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20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亞信峰會。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1]。這是正在崛起的中國發出的時代最強音,也是正在崛起的中國對“美版全球化”的重大修正和完善。
面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世界科技發展醞釀新突破的發展格局[2],循序漸進解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需要我們具備戰略思維、戰略定力、全球眼光和天下胸懷。當下,放眼國際局勢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循序漸進地最終解決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