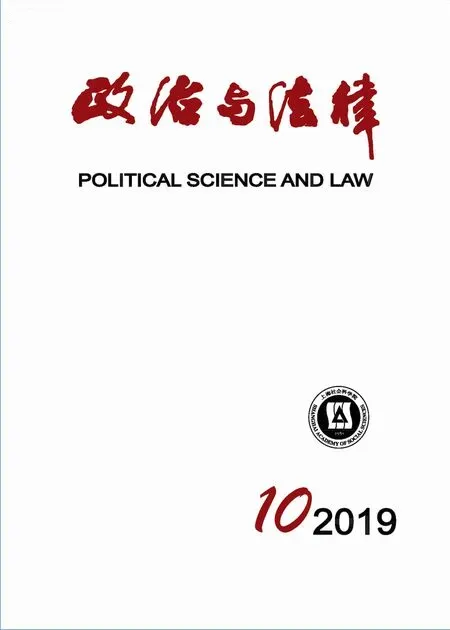論刑法中的“經營”
王飛躍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04)
我國刑法學界在“經營”是否以具有“營利目的”為必要、“經營”的含義、“經營”具有哪些特征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導致司法實踐中認定“經營”是否成立以及具體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如對利用POS機為自己刷卡套現行為和組織刷單行為的定性。①對于利用POS機為自己刷卡套現的行為,認為不構成犯罪的觀點,參見李民、趙婷婷:《POS機套現非法經營罪構成要件之實證分析》,《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認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觀點,參見李濤:《虛構交易利用POS機刷卡套現按期歸還是否構成犯罪》,《人民檢察》2016年第24期。對于組織刷單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觀點,參見劉仁文、楊學文:《用刑法規制電子商務失范行為》,《檢察日報》2015年8月26日,第03版;認為不構成犯罪的觀點,參見陳興良:《刑法階層理論:三階層與四要件的對比性考察》,《清華法學》2017年第5期。為此,本文擬對上述問題加以討論。
一、作為行為的“經營”與作為對象的“經營”
我國刑法中關于“經營”的規定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涉及“經營”的具體罪名,有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破壞生產經營罪。二是用“經營”對某些犯罪進行限定,如為親友非法牟利罪中“將本單位的盈利業務交由自己的親友進行經營的”和強迫交易罪中“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的”,用“經營”對行為方式進行限定;虛假廣告罪中的“廣告經營者”,用“經營”限定犯罪主體。從前述規定來看,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與“廣告經營者”中的“經營”均為動詞,以動詞的詞性使用“經營”一詞,意味著“經營”系行為;破壞生產經營罪與“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中的“經營”為名詞,以名詞的詞性使用“經營”一詞,意味著“經營”系對象。
(一)作為行為的“經營”
作為行為的“經營”就是具體犯罪中的實行行為,即提供服務和商品的行為。在確定“經營”客觀存在的情形下,還需要確定“經營”屬于哪一種類別,因為諸如非法經營罪的成立必須確定經營行為違反了哪一具體的國家規定。
司法實踐中,部分司法人員對于“經營”的認定不注重對于“經營”作為實行行為的考察,而是以所謂的“風險”、“嚴重破壞交易秩序”等價值評判來替代對“經營”作為實行行為的事實考察。如司法實踐中,法院、檢察院認為對于無償幫助親友利用POS機刷卡套現的行為,屬于“經營”行為。在利用POS機刷卡套現的情形下,既然用于套現的交易是虛構的,那就不存在真正的交易行為;就“幫助親友套現”而言,該行為性質的考察應當以“親友刷卡套現”為核心來進行,“親友刷卡套現”才是需要從刑法角度考察的對象,以確定是否屬于某種犯罪的實行行為。“幫助親友套現”實質上依附于“親友刷卡套現”,因為“幫助親友套現”本身既不屬于提供商品也不屬于提供服務,不具有獨立考察的基礎。尤其對于自己為自己刷卡套現,有學者認為“一人扮演交易雙重角色,但并不能改變‘非法經營’行為的性質”,②同前注①,李濤文。這種認識不僅明顯違背了常理常情,也違背了作為實行行為的“經營”必須具有提供提供服務和商品的本質屬性。認為“幫助親友套現”、“幫自己套現”、“嚴重侵犯了正常的市場交易管理秩序”,因而構成非法經營罪,③同前注①,李濤文。其錯誤就在于以片面的價值判斷取代了“經營”作為實行行為是否客觀存在的事實考察。
確定“經營”作為實行行為客觀存在的情形下,還需要準確認定“經營”屬于哪一類型。一般情形下,“經營”的類型劃分簡單明了,但某些“經營”行為的歸類有些復雜,實踐中,有些司法人員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存在隨意套用經營類型的做法,比如認為虛構交易通過銀行辦理票據貼現屬于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行為。④參見陳利、周群:《無真實交易違規辦理票據貼現非法獲利構成非法經營罪》,《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2期。行為人通過設立公司,幫助持票人完成票據在貼現銀行的貼現,銀行將資金劃轉至持票人后,行為人收取持票人一定的手續費,該行為屬于提供服務的經營行為,但并不屬于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的經營行為,因為此種情形下,資金支付結算仍然在銀行與持票人之間進行,并非在銀行與行為人或者行為人與持票人之間進行。因而考察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應當重點考察該提供幫助完成票據貼現的服務屬于哪一類型的經營、是否違反了國家法律的規定,而不能任意將其納入資金支付結算的類型。
此外,作為實行行為的“經營”既是若干同種性質行為的累計,又是若干不同類型行為功能的整合。作為若干同種性質行為的集合,特別是在行為主體為單位且發生單位人員變動的情形下,需要確定哪些人為責任者;作為若干不同類型行為功能的整合,往往涉及經營關聯行為及經營輔助行為,如為了經營而進行的場地準備、資金籌措、人員管理,雖然這些行為均不屬于直接提供服務或者商品的經營行為,但均與經營的發生、運行存在一定關聯,因而也涉及是否應當承擔責任的問題。
(二)作為對象的“經營”
作為對象的“經營”并不意味著“經營”系犯罪對象。通說認為,犯罪對象是犯罪行為直接作用的人或者物,因而,“經營”作為被侵害的對象,仍然是以作為犯罪對象的人或者物為依托的,如破壞生產經營中的殘害耕畜、毀壞機器,其犯罪對象依然為具體的“物”,“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的”,其犯罪對象是從事經營活動的“人”。“經營”是通過人與物的組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經營”是否受到侵害,不僅要考察行為直接作用的“人”和(或者)“物”,而且還需要對行為直接作用的“人”和(或者)“物”進行評價。因而認為“經營”本身為破壞生產經營罪犯罪對象的觀點,⑤參見柏浪濤:《破壞生產經營罪問題辨析》,《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3期。筆者不能贊同。
在判斷作為對象的“經營”時,直接受到犯罪行為作用的“人”和(或者)“物”必須直接承載“經營”的功能:在直接受到犯罪行為作用的對象為“物”時,“物”應當具有維系經營運轉不可或缺的特征;在直接受到犯罪行為作用的對象為“人”時,“人”應當能夠直接影響經營的發生與否、經營的規模、經營的效率等。認定作為犯罪對象的“經營”不僅要考察被侵害的“人”和(或者)“物”是否直接承載“經營”的功能,還要考察被侵害的“人”和(或者)“物”是否承載其他法律關系或者是否為其他社會關系的聯結點,如果被侵害的“人”和(或者)“物”還承載其他法律關系或者系其他社會關系的聯結點,則不能當然地將“人”和(或者)“物”受到侵害認定為單位的“經營”受到侵害。比如,債權人因為債務得不到清償,而將債務單位的部分設備和原材料拖走,造成債務單位停產,有法院認為此種行為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該判斷是錯誤的。⑥參見湖北省孝感市南區人民法院(2017)鄂0902刑初86號刑事判決書。因為部分設備和原材料被以物抵債,這些設備與原材料雖然承載了經營的功能,債務單位的經營也因此受到影響,但并不能據此當然地將該行為造成的后果評價為對“經營”的破壞,因為此時存在一個價值位階和順序問題:一般情況下,“過錯在先”可以否定“經營受侵”。例如對于欠繳電費的經營者,供電單位采取斷電措施當然會影響經營者的經營,但不能將供電單位的斷電行為評價為造成破壞經營的后果;又如原告申請法院查封被告單位財產也會影響被告單位的經營,但不能認為原告申請法院查封債務單位財產的行為造成了破壞經營的后果,即便原告敗訴,也只是需要承擔賠償損失的法律后果。
二、經營的含義
(一)經營的一般含義
“經營”一詞在經濟法、民商法以及刑法中均有涉及。在經濟法中,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產品質量法》《反壟斷法》《食品安全法》等均規定了“經營者”,而“經營”是“經營者”中的核心詞。⑦參見徐孟洲、葉姍:《經營者論:基于經濟法規范與原理的分析》,《現代法學》2007年第5期。在民商法中,《德國民法典》規定了經營者,我國也有學者提議在商法中引入經營者概念。⑧參見王建文:《我國商法引入經營者概念的理論構造》,《法學家》2014年第3期。那么,刑法中“經營”的含義是否與民商法、經濟法中“經營”的含義相同呢?
我國刑法學界不少學者在討論“經營”的含義時,往往并不考慮民商法、經濟法中“經營”的含義,如認為“經營”就是籌劃并管理之意,⑨參見羅開卷:《論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的認定及其與近似犯罪的界限》,《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5期。或者認為“經營”的核心是組織、管理和運營,⑩參見李世陽:《互聯網時代破壞生產經營罪的新解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筆者不贊同這種定義的方法及其對“經營”含義的具體界定。刑法中涉及“經營”的罪名與相應規定,如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破壞生產經營罪,都屬于法定犯,即國家法律明文禁止的行為才成立犯罪,并且刑法涉及“經營”犯罪的罪狀大多為空白罪狀,需要結合經濟法、行政法的相應規定才能確定這些犯罪行為的具體內容,因而刑法中的“經營”概念應該與經濟法等法律中“經營”的含義保持一致。我國的經濟法律中并不直接對“經營”進行定義,但對“經營者”進行了界定。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者提供服務(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我國臺灣地區的“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以設計、生產、制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服務為營業者”。參見前注⑦,徐孟洲、葉姍文。《德國民法典》第14條第1款將“經營者”界定為“在締結法律行為時,在從事營利活動或者獨立的職業活動中實施行為的自然人或者法人或者有權利能力的合伙”。陳衛佐譯注:《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經濟法學界有部分學者對“經營”進行了界定,如認為營業性經營活動,是指投資者所實施的具有反復性、不間斷性與計劃性的經營行為。參見前注⑧,王建文文。
從相關經濟法律對“經營者”的具體規定以及學者對“經營”的界定來看,盡管表述有些差別,但均包括了兩個核心內容:一是營業行為的目的在于營利;二是營業行為的內容為提供商品或者服務。因此,筆者認為,刑法中的“經營”是基于營利目的而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營業行為。經營的本質為“營業以營利”。
(二)經營含義的差異
我國刑法不同規定中“經營”的含義是否完全一致需要討論。對于生產經營活動,有學者認為,是指一切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環節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行為;參見胡康生、李福成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頁。對于“經營”一詞,有學者認為應理解為是一種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包括從事工業、商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經營活動。參見陳澤憲:《非法經營罪若干問題研究》,《人民檢察》2000年第2期。前述兩種觀點的分歧在于“經營”是否包括生產在內。在不同的罪名中,“經營”的含義確實不一定相同。一方面,破壞生產經營罪中的“經營”不包括“生產”在內,因為破壞生產經營罪中的“經營”與“生產”并列,“經營”自然不包括“生產”。非法經營罪中的“經營”不應包括“生產”在內,因為違反國家規定的生產性經營行為,應由生產偽劣產品罪、生產劣藥罪等罪名進行調整。另一方面,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中的“經營”應當包括“生產”在內,因為經營同類營業顯然不能將生產性經營行為排除在外。
當然,銷售偽劣產品、銷售劣藥等行為可能同時成立非法經營犯罪,但因為同一行為同時侵害數個刑法保護的社會關系成立想象競合而適用“從一重處斷原則”,因而銷售偽劣產品、銷售劣藥行為未定性為非法經營罪,并未限縮了“經營”的含義范圍。
三、經營與營利目的
我國刑法學界關于“經營”應否以具有“營利目的”為必要,有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營”必須以“營利”為目的,沒有“營利目的”的行為根本不是“經營”行為。參見陳興良:《非法買賣外匯行為的刑法評價——黃光裕案與劉漢案的對比分析》,《刑事法判解》2015年第1期;前注①,李民、趙婷婷文;周慶琳、湯詠梅:《采用資金對沖方式非法經營外匯構成非法經營罪》,《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4期;劉東根、王孟:《非法經營罪中“非法買賣外匯”的理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經營”不需要有“營利目的”。其主張“經營”不以具有“營利目的”為必要的理由有三種。第一種理由認為,諸如公立醫院、政府開辦的動物園等非營利機構的業務并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依然蘊含經濟利益,也屬于經營活動。參見前注⑤,柏浪濤文。第二種理由認為,互聯網時代“經營”的模式、理念與傳統經濟有著根本性差異,互聯網時代“經營”的核心是組織、管理和運營,經營不再需要營利性、經濟性。刑法應當與時俱進,把非經濟性的文化、慈善業務都解釋為“經營”。參見高艷東:《破壞生產經營罪包括妨害業務行為——批量惡意注冊賬號的處理》,《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年第2期;前注⑩,李世陽文。第三種理由認為,我國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未明確要求“經營”以具有“營利目的”為必要,因而“經營”無需“營利”目的。參見符秋:《非法經營罪的主觀故意認定》,《中國檢察官》2011年第2期。
早期,經濟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在界定“經營者”時,是強調“以營利為目的”或者“營利性”的。參見潘靜成、劉文華:《經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頁。隨著法院辦理的一些疑難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涉及諸如學校、醫院、律師事務所、行業協會等非營利性組織能否認定為“經營者”的問題,如湖南王躍文訴河北王躍文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國藥科大學訴江蘇福瑞科技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鄭雪峰、陳國青訴江蘇省人民醫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宜昌市婦幼保健院訴宜昌市工商局案,恒德信律師事務所等訴普濟律師事務所不正當競爭糾紛案,艾志工業技術集團有限公司訴中國摩擦密封材料協會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北京中匯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訴中國電器工業協會不正當競爭糾紛案等具體案件。參見李友根:《論經濟法視野中的經營者——基于不正當競爭案判例的整理與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部分學者提出“經營者”不應過于強調“營利”目的或者“營利性”。參見焦海濤:《論〈反壟斷法〉中經營者的認定標準》,《東方法學》2008年第5期。部分學者提出應當根據民法主體、商法主體、經濟法主體分別對待“營利”這一要件;參見前注,李友根文。還有學者提出用“市場主體”或者“市場參與者”取代“經營者”。參見李勝利:《論〈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競爭關系和經營者》,《法治研究》2013年第8期。
不過,經濟法學界關于從事非營利性活動、公益性活動的企業、單位能否認定為“經營者”的判斷標準是投資者對盈余是否有合法的索取權,參見陳楊忠:《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是服務業的經營者嗎?》,《中國食品藥品監管》2010年第6期。或者利潤能否分配給成員或法人的工作人員。參見謝鴻飛:《〈民法總則〉法人分類的層次與標準》,《交大法學》2016年第4期。并且營利性單位與非營利性單位區分的目的在于適用不同類型的稅費政策、財務會計制度,參見張新寶:《從〈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基于功能主義的法人分類》,《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4期。并不在于否定非營利性單位某些行為的“營利”特征,因為非營利法人的單項業務屬于“經營”活動,完全可從是否獲得利益得到解釋,參見前注,焦海濤文。因而經濟法學界對于非營利法人從事的業務可能具有“營利性”認識高度一致。參見前注,謝鴻飛文;前注,張新寶文。因此,經濟法學界雖有個別學者反對過于強調經營者的“營利”目的,其反對的主要理由是因為“過于強調營利目的”會產生“忽略和抹煞經營者作為經濟法主體理應承擔的經濟法意義上的社會責任”的后果,參見前注⑦,徐孟洲、葉姍文。并非否認非營利法人的相關行為的“營利”目的。因此,非營利單位開展的業務完全可以是“營利”業務。刑法學界基于解決公立醫院、學校、政府發行彩票等行為屬于“經營”的問題,參見前注⑤,柏浪濤文。要將“經營”的“營利”目的這一要件去除的想法大可不必。由此可見,對從事文化、慈善單位的部分業務解釋為“經營”,是不僅應當而且完全可行的。
基于互聯網經濟時代“經營”的核心是組織、管理和運營這一認識,主張要將“營利性”、“經濟性”從“經營”中剔除出去的觀點,是錯誤的。互聯網時代的經營模式、經營觀念確實明顯區別于工業時代,但其“營利”的本質并沒有改變。確實,網絡時代的“影響力”、“市場占有率”、“社會認可度”乃至“大數據——獲取消費者的信息”都能帶來利益,參見前注,高艷東文。但這些并非利益本身,并且與傳統經濟時代也沒有本質區別。因為傳統經濟時代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乃至客戶需求信息也都是能帶來經濟利益的,正因為如此,刑法為保護商業信譽、商品聲譽才設立了破壞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為保護包括客戶需求在內的經營信息等才設立了侵犯商業秘密罪。同理,網絡時代擴大影響力或者市場占有率、提升社會認可度、獲取消費者信息等行為,都是為以后開展營利業務做準備的,但并非“經營”行為本身,在這些基礎之上開展的直接獲取利益的行為才是“經營”行為。因此,如果將擴大影響力或者市場占有率、提升社會認可度、獲取消費者信息等行為均解釋為“經營”行為,不僅有悖“經營”的“營利”本質特征,而且會引發破壞生產經營罪與侵犯商業秘密罪和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之間的混亂。
至于認為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未明確要求“營利目的”而否定“經營”的“營利目的”,該理由是明顯站不住腳的。因為目的犯中的“目的”存在“明文規定”與“隱性要求”兩種類型。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頁。在非法經營罪中,雖然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未明確要求所有非法經營行為均需要有“營利目的”,但我國《刑法》第225條規定中的“買賣”當然隱含“營利”目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9月6日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明確規定:“違反國家規定,以營利為目的,通過信息網絡有償提供刪除信息服務……擾亂市場秩序……依照刑法第225條第4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由于構成要件是不法類型,并且只有侵犯法益相同且主要特征相同的具體危害行為才能歸為一個類型,參見齊文遠、蘇彩霞:《刑法中的類型思維之提倡》,《法律科學》2010年第1期。因此認為某些經營行為需具有“營利目的”而某些經營行為無需“營利目的”卻又均符合同一個犯罪的構成要件,是無法想象的。此外,如果不強調“營利目的”之于“經營”行為成立的必要性,會導致以消費為目的,從沒有取得行政許可而經營專營、專賣物品的單位或個人處購買諸如食鹽的行為,也被認定為非法經營行為的荒謬結論,因為不要求“營利目的”自然無法避免將出于消費目的的購買行為認定為“買賣”。與此類似,在認為POS機的所有權人受親友托請而刷卡套現但未收取手續費而成立非法經營犯罪的同時,同前注①,李濤文。卻并未認定信用卡持有人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共同犯罪,該錯謬除誤讀了“經營”與“營利目的”的關系外,還產生了同一邏輯無法貫穿于POS機的所有者與信用卡持有人的明顯矛盾。對于非法經營行為應具有營利目的,有學者還從非法經營罪的設立沿革、罰金刑的適用前提等角度提出了理由。參見前注①,李民、趙婷婷文。
綜上所述,經營須以營利目的為必要。
四、經營的特征
對于經營的特征,我國學界相關研究不多。有的學者認為,經營一般具有長期性、規模性、交易經常性等特點;參見羅開卷:《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疑難問題探討》,《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年第4期。有的學者認為,經營具有行為功能的經濟性、行為對象的擴充性、行為領域的廣泛性;參見前注,焦海濤文。有學者認為,經營作為經濟活動,具有計劃性、長期性的特點。鄭偉、葛立剛:《刑行交叉視野下非法經營法律責任厘定》,《法律適用》,2017年第3期。這些主張雖各有優點,但也存在不足,因為前述主張中對于“經營”特點的概括,在判斷“經營”是否成立時并不能發揮應有的指導作用。
基于“經營”的本質為“營業以營利”,筆者認為,“經營”具有兩個主要特點:交易性和營業性。
(一)經營的交易性
經營的交易性,即“經營”是經營方通過提供商品或者服務而獲得需求方的財產性對價。經營的交易性特征又可以細化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營”的合意性。經營方與需求方既有各自獨立的意志,也有認識上的一致,即經營方與需求方在自由意志支配下達成交易的一致。因此,按照單位要求完成特定勞動任務獲得報酬的行為不屬于“經營”。比方說,單位開辦食堂為職工免費提供就餐服務,完成食物加工任務的人,不屬于經營者。雖然單位內部食堂也涉及食品安全問題,但不能基于食品安全的考慮而將單位內部食堂認定為食品的經營者,參見李友根:《經營者概念的解釋與〈食品安全法(草案)〉的完善建議——基于上海愛邦鋁箔制品公司一案的研究》,《法學家》2008年第4期。因為按照單位要求完成食品加工任務,實際上是在執行單位意志,單位職工在單位就餐,也只是落實單位意志,此種情形下只有一個獨立意志。此外,共同行為中的共同故意不是合意,參見王飛躍:《論對向關系中共犯的成立》,《法學》2018年第7期。POS機的所有權人受親友托請而刷卡套現但未收取手續費的,由于POS機的所有權人與信用卡持有人只有一個共同意志,而不存在兩個獨立的意志,因而不屬于“經營”。參見前注①,李濤文。
二是“經營”的對向性。經營行為的成立以經營方與需求方兩個獨立主體的同時存在為必要,如果只有一方,是無所謂“經營”的。那種所謂“經營方”與“需求方”重合的觀點是錯誤的。參見前注①,李濤文。交易是合意行為,只有同時存在兩個獨立的主體,才具有合意產生的前提。單位開辦食堂,如果是以員工支付對價為條件而提供餐飲服務的,則此提供就餐服務的行為屬于經營行為。因為此種情形下,員工支付對價與其單位員工的身份無關,因而實際上存在兩個獨立的主體。即便單位為控制就餐人員的規模而限制非本單位人員任意就餐,也不能改變兩個獨立主體的本質。
三是“經營”的對價性。“經營”必然要求支付對價,正因為要求支付對價,才可能實現“營利目的”。基于感情或者社會道義而向公眾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行為,因為沒有取得對價,不屬于“經營”。比方說,在發生饑荒的時候免費向民眾提供食物,該行為不屬于“經營”。
四是“經營”的直接性。“經營”應當直接產生利益,即通過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直接取得對價,不能直接產生利益的行為,雖然有助于“經營”的開展,但僅屬于經營關聯行為,并非“經營”行為本身。那種將涉及“影響力”、“市場占有率”、“社會認可度”的行為也認定為“經營”的觀點,參見前注,高艷東文。是不能成立的。與此相同的是,如果不是對直接產生利益的“經營”業務本身進行破壞,而是針對公司的員工實施人身權利的侵害,或者對公司的人事管理工作進行破壞,也不宜認定為破壞生產經營犯罪。
(二)經營的營業性
經營的營業性,即“經營”是指經營方以提供商品或服務實現營利目的的業務活動、職業活動。“營業性表明行為主體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連續不間斷地從事某種同一性質的營利活動,因而是一種職業性營利行為。”范建、王建文:《商法的價值、源流及本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頁。營業性特征也可以細化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營”的業務性。“經營”需體現為一種業務,一般情形下,業務體現為掌握涉及商品處理、服務提供的專業知識以及實現交易所需的交涉能力。參見前注⑦,徐孟洲、葉姍文。“經營”以有償性為必要,但有償交易并不當然等同于營業性。業務性體現“經營”作為商事活動的特點,即“經營”屬于業務活動或者職業活動。商法學界認為,作為商行為與民事行為的分水嶺,營業是指以營利為目的而進行的連續的、有計劃的同種類的活動(行為)。參見徐喜榮:《營業:商法建構之脊梁——域外立法及學說對中國的啟示》,《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11期。因而,單純通過提供勞務取得報酬的行為,不屬于“經營”;參見前注⑨,羅開卷文。農民將自己種植的糧食、蔬菜、牲畜予以出售的行為,不屬于“經營”,這種行為屬于民事行為;如果開辦養殖場并出售牲畜的行為,則屬于“經營”,因為開辦養殖場已經屬于營業活動。
二是“經營”的持續性。“經營”需以持續發生為必要。對于經營行為持續發生,有學者表述為經營行為具有反復性、不間斷性與計劃性。參見前注⑧,王建文文。經營的持續發生是指經營的存在狀態,并不必然體現為不間斷性,由于主觀、客觀等原因暫停營業,而后又恢復的,也屬于持續發生。由于“經營”屬于業務活動或者職業活動,其必然在一定時間范圍內持續發生。如果行為不符合持續發生的特點,只是偶爾實施,就不屬于“經營”。因而在非法買賣外匯行為中,偶爾地出售外匯的行為不屬于“經營”行為。當然,持續性應當理解為經營者的意欲,如果因為客觀原因未能使經營行為持續發生的,并不影響經營行為持續性特點的成立。
三是“經營”的開放性。開放性是指經營者以一定方式、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其商品或者服務,并吸引一定的需求者發生交易的特征。因而,“經營”的開放既包括相關經營信息的公開,也包括對需求者的開放,即經營一般情形下應當為不特定的人提供商品或者服務。如果提供服務僅限于特定的少數對象,如保姆、保鏢對其雇主提供相應的服務,就不具有開放性的特征。如果家政公司、安保公司提供保姆或者保鏢服務,則具有開放性的特征。
四是“經營”判斷的中立性。“經營”判斷的中立性是指是否屬于“經營”應當從事實層面進行實質判斷,而不考慮其行為是否受法律保護,是否按照法律要求取得經營資格。因而即便是強迫兒童勞動的“黑煤窯”,不能因為此種行為涉嫌雇傭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犯罪,而否定“黑煤窯”的經營性質。因此,非出于解救兒童目的,對“黑煤窯”的生產活動實施破壞的,也應當認定為對“經營”的破壞。那種因為“黑煤窯”雇傭童工而否定“黑煤窯”的經營活動,參見王中偉、趙克:《破壞生產經營罪的認定標準》,《人民司法·案例》2014年第4期。混淆了“黑煤窯”應否保護、“黑煤窯”雇傭童工的行為應否追究責任與對“黑煤窯”的生產活動實施破壞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兩個不同的問題。實際上,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以行為人的行為為評價對象進行的判斷,而不是以行為人侵害的對象是否合法、是否受法律保護為評價對象。因而,明知他人財物系贓款,盜取贓款的行為依然成立盜竊犯罪。經濟法學界普遍認為,經營主體是否取得相應營業資格,不影響經營者的認定。參見前注,焦海濤文。
五、有關經營的其他問題
(一)經營者之判斷
在非法經營罪中,判斷涉案的自然人或者單位的行為是否為經營行為,只要對“經營”的內涵與特征進行準確適用即可。當然,在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中還涉及經營者的判斷問題。在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中,除了判斷“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中的“經營”能否成立外,還需要對“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能否成立進行認定;在為親友非法牟利罪中,除了判斷“親友”經營中的“經營”能否成立外,還需要對“親友”經營能否成立進行認定,這都屬于經營者的判斷問題。
有學者提出,判斷是否為經營者,應關注該自然人在相關單位是否屬于負責人,對于一般兼職,不能認定為經營者;參與重大決策或者公司運營進行指揮的,屬于經營者;作為公司的出資人但未參與經營管理的人,不屬于經營者。參見劉志遠、蔡雙喜:《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適用問題辨析》,《人民檢察》2002年第12期。筆者認為,經營者的判斷,應著眼利益的分配問題,而不能局限于管理、決策、運營等具體事項。在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中,只要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本人或者其利害關系人與涉案公司有利益關系,則可認定為經營者。利益關系包括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作為出資人參與公司利潤分配;另一種類型是參與具體業務的利潤分配,如對單筆業務收入提成。只要具有利益關系,即便不擔任任何管理職務、不承擔具體的管理事務,也可以成立經營者;與此同時,如果只是通過付出勞動取得報酬并且不具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不僅一般兼職不能認定為經營者,即便擔任管理職務、參與決策或者對公司運營進行組織、指揮,僅屬于違反規定兼職取酬的問題,也不能認定為經營者。此外,在適用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時,還存在“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銷售商品”的認定問題。如果親友并未設立單位,而是以自然人名義實施經營行為的,按照實質解釋方法,實質解釋應當考察刑法條文的價值指向與實質內涵。參見前注,齊文遠、蘇彩霞文。也應當解釋為向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銷售商品。
(二)破壞生產經營罪中的單個財物與“經營”之關系
發生在2002年的大學生“傷熊事件”引發了刑法學界的一定關注和討論。針對該行為是否屬于破壞生產經營罪,有學者認為,由于動物園屬于非營利單位、展示動物并收取門票不屬于生產經營活動,動物園的動物也非機器設備,因而不成立破壞生產經營罪。參見謝望原:《“黑哨”、“黑球”與“傷熊”行為的刑法學思考》,《政治與法律》2002年第6期。還有學者認為,因為行為人沒有破壞生產經營的故意,所以不成立破壞生產經營罪。參見前注⑤,柏浪濤文。
筆者也認為“傷熊”行為不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但理由并非因為動物園系非營利單位,而在于5只熊受傷的結果尚未達到影響動物園經營收益的程度——5只熊受傷的結果不會對群眾是否游玩動物園產生影響,即不會對動物園的門票收入產生影響。筆者認為,破壞生產經營的行為,必須達到直接影響生產經營收益的程度,即直接導致營業性收入減少,營業性收入減少并不等同于單位財產總量的減少或者支出增加。我國《刑法》第276條列舉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應當進行實質解釋:在毀壞機器設備的場合,“毀壞機器設備”應當達到影響生產經營收益的程度,如果雖然毀壞機器,但機器可以很快修復或者得到替換的,實際上不會直接影響生產經營收益,不宜認定為破壞生產經營;在殘害耕畜的場合,殘害耕畜是針對農業生產而言的,如果在農閑時期殘害耕畜的或者耕畜已經不再在農業生產中使用的,也不會影響農業生產經營收益,也不宜認定為破壞生產經營罪。此外,對生產經營單位的商品實施破壞,如對造紙廠生產的紙張進行銷毀并不影響其履行貨物交付義務的,或者對不屬于生產經營直接依賴的財物進行破壞,如砸爛運輸單位的辦公桌椅,均不應認定為破壞生產經營行為。當然,如果對從事經營活動單位的單個財物進行破壞,符合故意毀壞財物罪構成要件的,可以依照故意毀壞財物罪追究責任。
(三)職工參與單位經營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不屬于破壞生產經營行為
司法實踐中,對單位內部職工在實施經營行為的過程中,不正當履行職務故意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是否構罪、構成何罪有不同的認識。如劉俊為追求銷售業績而低價銷售公司電腦造成公司重大損失,法院認為不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參見崔志偉:《破壞生產經營罪的口袋化傾向與司法消解》,《法律適用》2018年第7期。又如對張某故意拖延辦理探礦權年檢手續而造成繳納80余萬元稅費的直接損失,并且因為探礦權證由此失效引發的間接損失的行為,認為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參見王耀剛:《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中國檢察官》2010年第12期。再如張某低價拋售公司股票造成公司重大損失,法院認為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參見前注,崔志偉文。
筆者認為,單位職工造成單位損失的經營行為不屬于破壞生產經營的行為,理由在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破壞生產經營應當由單位以外的個人或單位實施。單位員工實施的經營行為屬于單位經營的組成部分,單位員工在參與單位經營過程中故意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具有職務因素,屬于職務行為,均應納入背信行為的范疇,不應納入破壞生產經營的規制范疇。第二,刑法已將單位職工故意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設置相應罪名進行規制。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相應規定體現的規制邏輯,單位職工故意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不應納入破壞生產經營的規制范疇。如我國《刑法》第166條規定的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第168條規定的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第169條規定的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85條規定的挪用資金罪、第186條規定的違法發放貸款罪,第188條規定的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等等,都屬于單位員工在實施經營行為的過程中故意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因此,在現有罪名體系內,對于單位內部職工在參與單位經營行為的過程中,故意造成公司損失的,如果符合相應犯罪構成要件的,應當按照相應的罪名追究刑事責任,而不應認定為破壞生產經營罪。如果某些單位職工實施經營行為過程中故意造成單位損失的行為,尚未有相應罪名予以規制,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尚未設立背信罪之前,應認定不構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