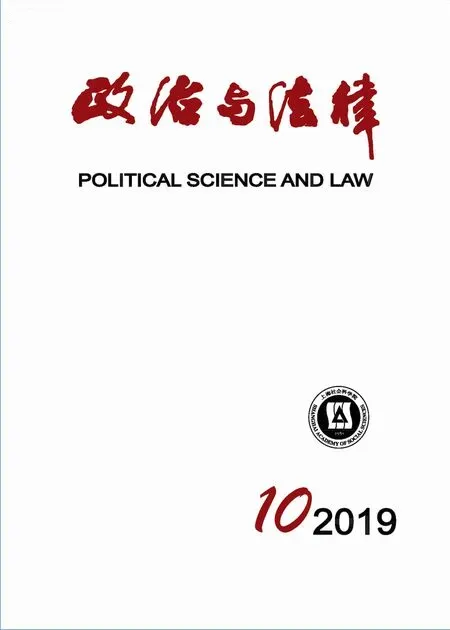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過錯判定理念的修正
——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的確立為中心
虞婷婷
(清華大學(xué)法學(xué)院,北京100084)
Web2.0時代,任何個體只要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都可以成為信息的創(chuàng)造者與傳播者,因此用戶利用網(wǎng)絡(luò)之便利侵犯他人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現(xiàn)象層出不窮,單獨追究用戶的侵權(quán)責任在經(jīng)濟上幾乎無效。基于訴訟成本的考量,權(quán)利人一般會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一并作為被告或者僅僅起訴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在判斷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要承擔侵權(quán)責任時,過錯的有無是一個核心問題。其中衡量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有過錯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其是否履行了網(wǎng)絡(luò)傳播內(nèi)容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所謂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是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當主動對用戶上傳信息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合法性進行審查,并采取合理的措施移除侵權(quán)內(nèi)容的義務(wù)。為了貫徹技術(shù)中立原則的法律精神,我國相關(guān)法律和司法解釋借鑒了美國法上的避風港規(guī)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只需在收到權(quán)利人的通知或者應(yīng)知侵權(quán)明顯的事實后采取必要措施,無需主動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合法性進行審查。①筆者于本文并無意于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和“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等概念進行區(qū)分,其指向的均是與內(nèi)容服務(wù)提供者相對的服務(wù)商,出于用語統(tǒng)一之考量,除必要引用之外,筆者于本文正文中均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之術(shù)語。即便相關(guān)規(guī)范已明確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主動審查排除于過錯的考量因素之外,司法實務(wù)中仍未形成一致意見,有的法院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不負主動審查義務(wù)”,②參見上海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7)滬73民終230號民事判決書;廣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7)粵73民終199號民事判決書。有的法院提出其有義務(wù)“采取合理、有效的技術(shù)措施防止侵權(quán)行為的發(fā)生”,③參見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津02民終2735號民事判決書。或應(yīng)設(shè)分類頻道等模式而對授權(quán)進行審查。④參見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津02民終2038號民事判決書。在學(xué)界,主流觀點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只承擔理性人的注意義務(wù),不需要對用戶上傳的信息進行合法性審查。⑤參見孔祥俊:《網(wǎng)絡(luò)著作權(quán)保護法律理念與裁判方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257頁;梅術(shù)文:《著作權(quán)法上的傳播權(quán)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27頁。不過,近年來有部分學(xué)者主張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負擔事前的內(nèi)容過濾或人工審核等義務(wù)。⑥參見崔國斌:《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版權(quán)內(nèi)容過濾義務(wù)》,《中國法學(xué)》2017年第2期;宋亞輝:《競價排名服務(wù)中的網(wǎng)絡(luò)關(guān)鍵詞審查義務(wù)研究》,《法學(xué)家》2013年第4期。司法實務(wù)、學(xué)說的混亂以及與法律規(guī)范的不一致,需要人們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不負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的基本論點進行重新審視。
一、問題之所在:避風港規(guī)則引發(fā)的利益失衡
我國在規(guī)制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知識產(chǎn)權(quán)間接侵權(quán)責任(尤其是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時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美國《數(shù)字千年版權(quán)法案》(以下簡稱:DMCA)確立的避風港規(guī)則。DMCA第512條(c)項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免責的主觀條件有如下要求:其對于用戶的侵權(quán)行為既不存在實際知情(actual knowledge),也不存在明顯知情(apparent knowledge),前者一般以權(quán)利人的通知予以證明,后者指的是意識到侵權(quán)明顯的事實或情境。為了判斷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意識到侵權(quán)明顯的事實或者情境,美國國會創(chuàng)設(shè)了“紅旗測試”(red flag test)。⑦Liliana Chang,The Red Flag Test For Apparent Knowledge Under The DMCA§512(C)Safe Harbor.28 Cardozo Arts&Ent.L.J.197(2010).然而,無論是“實際知情”還是“明顯知情”,其指向的都是具體特定的侵權(quán)事實(specific infringement),僅僅對侵權(quán)行為的存在有著概括性的知情不會妨礙其駛?cè)搿氨茱L港”。與此相應(yīng),DMCA第512條(m)項也將查找、監(jiān)控侵權(quán)行為的負擔施加給了權(quán)利人,⑧See DMCA512(m),Protection of privacy.--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condit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subsections(a)through(d)on--(1)a service provider monitoring its service or affirmatively seeking facts indicating infringing activity,except to the extent consistent with a standard technical measure complying with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i);or(2)a service provider gaining access to,removing,or disabling access to material in cases in which such conduct is prohibited by law.如果一項侵權(quán)行為還需要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進行調(diào)查才能確定,那就不屬于顯而易見的“紅旗”,因此,DMCA實際上免除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在這樣的前提下,認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存在過錯只能依靠權(quán)利人的通知以及網(wǎng)絡(luò)用戶如同“紅旗”般明顯的侵權(quán)行為,此種規(guī)制模式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引入避風港規(guī)則的中國都存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難題。
(一)理論障礙: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間接侵權(quán)的過錯形態(tài)被狹隘地解讀
美國法院在解釋“實際知情”和“明顯知情”時都將其限定于對具體侵權(quán)事實的知情,即“具體知情”(specific knowledge)。一方面,“具體知情”要求與普通法的一般理念不符。根據(jù)普通法上的輔助侵權(quán)理論,如果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對第三方侵權(quán)行為有著概括性的知情,以至于它可以“合理預(yù)期”(reason-ably anticipate)侵權(quán)行為在未來會發(fā)生,那么它應(yīng)當采取合理的預(yù)防措施。⑨David H.Bernstein,Michael R.Potenza,Why The Reasonable Anticipation Standard Is The Reasonable Way To Assess Contributory Trademark Liability In The Online Marketplace.2011 Stan.Tech.L.Rev.4(2011).另一方面,在“具體知情”理念下,實際知情或者明顯知情指向的都是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故意的過錯形態(tài),并不包含過失因素。例如,在Corbis Corp.v.Amazon.com案中,法院就指出,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一個理性人可能從既有事實中推出侵權(quán)的存在,“明顯知情”的實質(zhì)在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在其已經(jīng)意識到的公然侵權(quán)的事實面前故意繼續(xù)其行為,對明顯侵權(quán)的“紅旗”視而不見。⑩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have deduced from the circumstances.Instead,the question under§512(c)(1)(A)(ii)is“whether the service provider deliberately proceeded in the face of blatant factors of which it was aware or whether it turned a blind eye to red flags of obvious infringement”.See Corbis Corp.v.Amazon.com,Inc.,351 F.Supp.2d at 1107-1108.由此可知,“紅旗標準”適用的前提是“意識”到具體侵權(quán)行為的存在,所認定的主觀心態(tài)至少為“間接故意”。在我國,不少學(xué)者也以“紅旗標準”來解釋我國法上的“應(yīng)知”,主張其為蘊含故意內(nèi)容的“推定知道”(有理由知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年4月20日發(fā)布的《侵害著作權(quán)案件審理指南》第9.9條也指出,被告實施教唆、幫助行為應(yīng)承擔侵權(quán)責任的,主觀上應(yīng)當具有“明知”或者“應(yīng)知”的主觀過錯。“明知”指實際知道侵權(quán)行為存在;“應(yīng)知”指因存在著明顯侵權(quán)行為的事實,應(yīng)當意識到侵權(quán)行為的存在。其對“應(yīng)知”的理解亦是對紅旗標準的借鑒。與民法上的一般侵權(quán)規(guī)則相比,“應(yīng)知”的內(nèi)容被大幅限縮,降低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注意義務(wù)的要求(甚至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沒有注意義務(wù)的要求)。此種狹義的解讀將使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上的過失歸責原則在網(wǎng)絡(luò)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領(lǐng)域面臨形同虛設(shè)的窘境。
(二)實踐難題:避風港規(guī)則使權(quán)利人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之間利益失衡嚴重
由于對“實際知情”和“明顯知情”的要求如此之高,美國法院實際上確立了這樣的判定標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只有在收到符合要求的通知時才構(gòu)成“知情”。迄今為止,美國尚無一例判決認定“明顯知情”的“紅旗”成立,即便其意識到侵權(quán)普遍存在且從侵權(quán)活動中獲得利益也能駛?cè)氡茱L港。因此有學(xué)者開始提出質(zhì)疑,對于公然承載了大量侵權(quán)內(nèi)容的服務(wù),嚴格適用具體知情要求,可能不符合法律的利益平衡價值。Mary Rasenberger,Christine Pepe,Copyright Enforcement and Online File Hosting Services:Have Courts Struck the Proper Balance?59 J.Copyright Soc’y U.S.A.p669(2012).如果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過錯形態(tài)僅限于故意,那么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的著作權(quán)保護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靠權(quán)利人積極主動的監(jiān)控以及通知,對于時間敏感性較強的權(quán)利客體而言,通知后的刪除很有可能于事無補。一般來說,版權(quán)內(nèi)容在剛剛上傳的即時是最有價值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內(nèi)容的價值會逐漸降低。因此,當侵權(quán)性的內(nèi)容最終被刪除時,它可能實際上已經(jīng)毫無價值了。不僅如此,我國在引進避風港規(guī)則時還存在移植上的疏漏,并未將懲戒重復(fù)侵權(quán)用戶和容納標準技術(shù)措施作為避風港的準入門檻。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只要公開聯(lián)系信息并履行通知后的刪除義務(wù)即可免除賠償責任,客觀上促使其在打擊侵權(quán)方面完全持消極等待立場。以“紅旗原則”和“通知—刪除”義務(wù)為核心的避風港規(guī)則是對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的一種保護以及對作品傳播的鼓勵。然而,從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利益平衡的價值追求來看,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不能以犧牲其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為代價。我國在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促進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關(guān)系處理方面與美國相比有一定的目標差異,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要健康有序發(fā)展,必須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規(guī)范化為前提。
二、問題之癥結(jié):技術(shù)中立原則與最小防范成本理論
DMCA設(shè)立避風港規(guī)則旨在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和版權(quán)所有者提供更強大的激勵,使其合作監(jiān)測和處理發(fā)生在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的版權(quán)侵權(quán),在政策導(dǎo)向上偏向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利益之維護,但這種立法導(dǎo)向在今天卻導(dǎo)致了新的利益失衡,其根源在于避風港規(guī)則制定時所依賴的技術(shù)中立原則和最小防范成本理論被人為僵化了,因此也就成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用以主張其不承擔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的一把利劍。
(一)技術(shù)中立原則
中立往往意味著禁止歧視與干預(yù),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的技術(shù)中立要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扮演的“純粹傳輸者”的角色,作為一種媒介,其主要功能在于傳遞信息而不是改變信息的形式或內(nèi)容。技術(shù)中立原則在版權(quán)侵權(quán)領(lǐng)域的適用最早確立于美國的“索尼案”。在該案中,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借鑒了美國專利法中的“普通商品原則”,認為如果產(chǎn)品可能被廣泛用于合法的、不受爭議的非侵權(quán)用途(實質(zhì)性非侵權(quán)用途),那么即使制造商和銷售商知道其設(shè)備可能被用于侵權(quán),也不能推定其構(gòu)成共同侵權(quán)。Sony Crop.of America V.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464 U.S.417.(1984).按技術(shù)中立原則,網(wǎng)絡(luò)僅為一種純粹的信息傳播工具,不應(yīng)承載任何價值判斷。只要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保持“公共承運人”的中立性就享有責任豁免,無需承擔監(jiān)管網(wǎng)絡(luò)的職責和義務(wù)。參見高薇:《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公共承運人規(guī)制》,《政法論壇》2016年第4期。就技術(shù)中立與審查義務(wù)的關(guān)系而言,立法決策者需要在“完全的技術(shù)中立+豁免平臺義務(wù)”與“有限的技術(shù)中立+科以平臺更重的義務(wù)”之間作出理性的選擇。現(xiàn)實是,即便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技術(shù)不中立的運營模式越來越普遍,卻仍然憑借“技術(shù)中立”來為其服務(wù)披上圣潔的道德外衣,以求最大程度地獲得“信息中介”意義上的責任豁免。以中國最大的電商平臺阿里巴巴為例,其經(jīng)營的淘寶網(wǎng)表面上并不從雙方的交易中直接獲益而僅提供交易平臺,但其收益卻主要來源于廣告及檢索排名等增值服務(wù)。淘寶網(wǎng)站有著海量的商品和賣家,而真正得以集中曝光的商品卻集中在少數(shù)賣家手中,這往往是因為其通過在淘寶上購買廣告攤位、檢索的優(yōu)先排名等方式讓自己的產(chǎn)品能夠優(yōu)先展示在消費者面前。對于此類經(jīng)過競價排名的用戶侵犯知識產(chǎn)權(quán),淘寶網(wǎng)仍然以其中介地位為由主張不負審查義務(wù)。大數(shù)據(jù)與人工智能已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發(fā)展的潮流。在智能算法的加持下,網(wǎng)絡(luò)平臺更加積極地收集和分析用戶數(shù)據(jù),廣泛用于對用戶個人行為預(yù)測和干預(yù),逐漸偏離避風港規(guī)則下的中立被動的服務(wù)定位。參見魏露露:《網(wǎng)絡(luò)平臺責任的理論與實踐——兼議與我國電子商務(wù)平臺責任制度的對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8年第6期。因此,在新技術(shù)環(huán)境下,隨著平臺自治的主體地位得到確立和不斷深化,此種免責主張并非當然具有正當性。
(二)最小防范成本原則
DMCA之所以讓版權(quán)所有人承擔查找和監(jiān)控侵權(quán)的義務(wù),除了技術(shù)中立原則的考量,另一個原因在于其將版權(quán)所有人視為監(jiān)控義務(wù)的最小成本負擔者。在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quán)法〉修改草案送審稿》中有“單純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服務(wù)的提供者不負審查義務(wù)”之規(guī)定,國家版權(quán)局也曾召開“著作權(quán)法修改媒體互動會”作出說明:“對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來說,在技術(shù)上目前還無法實現(xiàn)對內(nèi)容是否經(jīng)過著作權(quán)授權(quán)的甄別,因此不具備可操作性,不能要求網(wǎng)站承擔這樣的義務(wù)。”楊理光:《版權(quán)局:現(xiàn)有技術(shù)不足讓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承擔審查義務(wù)》,http://tech.sina.com.cn/i/2012-04-25/17387019216.shtml,2019年7月23日訪問。質(zhì)言之,囿于技術(shù)等客觀條件,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承擔審查義務(wù)的成本過于高昂,相反,版權(quán)所有者處于一種獨特的特權(quán)地位,能夠最好地評估侵權(quán)的成本與網(wǎng)絡(luò)效應(yīng)和互補性帶來的經(jīng)濟收益。Anna Katz,Copyright In Cyberspace:Why Owners Should Bear The Burden Of Identifying Infringing Material Under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18 B.U.J.Sci.&Tech.L.372(2012).然而,問題在于,即便權(quán)利人了解自己的權(quán)屬狀況,由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不會授予權(quán)利人訪問其專有代碼的特權(quán),致使權(quán)利人難以定位和識別網(wǎng)絡(luò)上所有的侵權(quán)內(nèi)容,只能在每個站點上分別監(jiān)控。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任何一個網(wǎng)絡(luò)用戶都是潛在的“侵權(quán)人”,而識別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侵權(quán)人身份需要極高的成本。隨著侵權(quán)的泛濫,權(quán)利人進行監(jiān)控所產(chǎn)生的邊際成本是逐漸遞增的,重復(fù)執(zhí)行既浪費資源也不能有效預(yù)防侵權(quán)。從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的現(xiàn)實運作來看,權(quán)利人監(jiān)控網(wǎng)絡(luò)與防范侵權(quán)并不存在內(nèi)核的一致性。以著作權(quán)為例,一旦未經(jīng)權(quán)利人授權(quán)的作品被上傳到網(wǎng)絡(luò),侵權(quán)就已經(jīng)發(fā)生,并且,隨著傳播范圍的擴大,損害也會增加。權(quán)利人獨立于網(wǎng)絡(luò)平臺或者搜索引擎服務(wù)商,即便其對網(wǎng)絡(luò)上的信息進行了積極主動的監(jiān)控也不能阻止侵權(quán)信息的上傳,權(quán)利人發(fā)現(xiàn)侵權(quán)信息之后再向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發(fā)送通知,也不屬于預(yù)防侵權(quán)的范疇,而是僅僅一種止損手段。可見,一律將權(quán)利人視為最小防范成本的負擔人,確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三、修正的前提:注意義務(wù)與審查義務(wù)關(guān)系之厘清
(一)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注意義務(wù)之證成
只有反映行為人過失的注意義務(wù)本身得到證成,才有必要進一步探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需要承擔更為嚴格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在網(wǎng)絡(luò)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領(lǐng)域,一直以來,立法、司法以及學(xué)術(shù)界對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當承擔過錯責任這一基本理念并不存在分歧。然而,在過錯責任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具體的過錯形態(tài)如何卻未形成一致意見。我國《侵權(quán)責任法》第36條第3款在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間接侵權(quán))的過錯時經(jīng)歷了“明知”?“知道”?“知道或者應(yīng)當知道”?“知道”的變遷。籠統(tǒng)的“知道”二字應(yīng)當如何解讀,在學(xué)界也一直爭執(zhí)不休,其中不乏有學(xué)者認為“知道”規(guī)則屬于故意侵權(quán)范疇,即僅指實際知道(明知)和其證據(jù)法上的衍生類型“很可能知道”(有理由知道),不包括過失意義上的“應(yīng)知”。參見胡晶晶:《論“知道規(guī)則”之“應(yīng)知”— —以故意/過失區(qū)分為視角》,《云南大學(xué)學(xué)報(法學(xué)版)》2013第6期。具體到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條例》既采用了“不知道也沒有合理的理由應(yīng)當知道”的表述(第22條),又規(guī)定了“明知或者應(yīng)知”(第23條);《最高人民的法院關(guān)于審理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則僅規(guī)定了“明知或者應(yīng)知”(第8條)。“明知”為故意的主觀過錯形態(tài)爭議不大,但如何解釋“應(yīng)知”卻是見仁見智。有些人認為“有合理的理由應(yīng)當知道”和“應(yīng)知”應(yīng)適用推定規(guī)則,參見徐偉:《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侵權(quán)責任理論基礎(chǔ)研究》,吉林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3年,第82頁。推定規(guī)則下的“應(yīng)知”與“明知”一樣均含有故意的主觀狀態(tài)。參見王光文:《論我國視頻網(wǎng)站版權(quán)侵權(quán)案件頻發(fā)的原因與應(yīng)對》,華東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2年,第59頁。知識產(chǎn)權(quán)間接侵權(quán)的主觀判定必須以對特定侵權(quán)行為的知曉為條件,僅僅概括知曉存在侵權(quán)行為一般不宜認定構(gòu)成侵權(quán)。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間接侵權(quán)責任是一種故意而非過失責任。參見曹陽:《知識產(chǎn)權(quán)間接侵權(quán)責任的主觀要件分析——以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為主要對象》,《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2年第11期。有學(xué)者認為,無論是著作權(quán)還是商標權(quán)領(lǐng)域,在規(guī)則層面,“應(yīng)知”或“知道”都指向故意,但在實踐層面,法院卻或多或少地給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設(shè)置了注意義務(wù),“應(yīng)知”也就包含過失。參見馮術(shù)杰:《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間接侵權(quán)責任的過錯形態(tài)》,《中國法學(xué)》2016年第4期。對“知道”、“應(yīng)知”的不同認識,反映了我國研究者對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間接侵權(quán)過錯形態(tài)的認知差異。將“知道”、“應(yīng)知”限定為故意,并通過推定的法律技術(shù)予以確認,這在操作層面確實是可行的,但卻使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上的過失歸責原則在網(wǎng)絡(luò)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領(lǐng)域形同虛設(shè),而將過失納入“知道”、“應(yīng)知”的范疇則可以維系過錯內(nèi)涵的完整性。
如果像直接侵權(quán)人那樣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實行嚴格的責任,這將為權(quán)利人提供最為周密的保護,對網(wǎng)絡(luò)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則是致命的打擊。相反,如果過錯僅限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故意行為,這將明顯縮小可能成立的侵權(quán)范圍。如果過錯也涵括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疏忽行為,這將得到一個合理的中間保護范圍(intermediate scope)。David H.Bernstein,Michael R.Potenza,Why The Reasonable Anticipation Standard Is The Reasonable Way To Assess Contributory Trademark Liability In The Online Marketplace.2011 Stan.Tech.L.Rev.40-41(2011).DMCA制定時的信息技術(shù)環(huán)境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隨著Web2.0時代的到來,一方面,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越來越多地對網(wǎng)站內(nèi)容進行有意識、有控制力的引導(dǎo);另一方面,信息技術(shù)革新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的嚴重性、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履行注意義務(wù)的成本和權(quán)利人預(yù)防侵權(quán)的難度等關(guān)鍵因素發(fā)生了變化。在訴訟中要證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對用戶侵權(quán)存在故意幫助行為無疑困難重重,如果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僅為其故意行為買單,那么權(quán)利人的合法利益將毫無保障。為實現(xiàn)新的利益平衡,對“知道”和“應(yīng)知”的解讀也應(yīng)當符合當下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發(fā)展的現(xiàn)實,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為其過失行為承擔侵權(quán)責任,而過失客觀化的表現(xiàn)就是行為人對其應(yīng)履行的注意義務(wù)的違反。
(二)審查義務(wù)屬于較高層級的注意義務(wù)
DMCA出臺之前,美國法院要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對用戶上傳的內(nèi)容履行審查義務(wù),與這種審查義務(wù)對應(yīng)的是嚴格責任。如在1993年的Frena案中,網(wǎng)絡(luò)用戶未經(jīng)許可而將原告享有版權(quán)的170張照片上傳至被告運營的BBS中。法院認為,無論被告是否實施上傳行為,只要其網(wǎng)站中出現(xiàn)侵權(quán)作品的復(fù)制件,就足以認定被告未履行主動審查義務(wù)而構(gòu)成侵權(quán)。See Playboy Enterprises,Inc.v.Frena,839 F.Supp.1552(1993).由此可知,在美國早期的司法實踐中,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往往被視為電子出版者(electronic publisher),與內(nèi)容提供者一樣在運營過程中需要履行嚴格的審查義務(wù),并對此承擔嚴格責任。DMCA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審查義務(wù)免除,對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間接侵權(quán)由嚴格責任走向過錯責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上述變遷歷程來看,審查義務(wù)對應(yīng)的是嚴格責任,與其相對,注意義務(wù)則指向過錯責任,因此,審查義務(wù)與注意義務(wù)當屬并列關(guān)系。
在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學(xué)界在討論審查義務(wù)與注意義務(wù)的關(guān)系時存在并列、等同于包含三種不同的觀點。持并列論的學(xué)者以王遷為代表,其認為審查義務(wù)意味著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必須積極采取合理措施對用戶上傳的內(nèi)容主動加以逐個審視,并查驗上傳者是否有合法、完整的授權(quán)文件;注意義務(wù)則意味著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在其能夠和應(yīng)當發(fā)現(xiàn)用戶上傳的內(nèi)容侵權(quán)的情況下及時制止侵權(quán)行為,至于其是否能夠和應(yīng)當發(fā)現(xiàn)侵權(quán)事實,取決于服務(wù)性質(zhì)、職業(yè)要求、同行業(yè)中的理性人在相同情況下應(yīng)當達到的注意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參見王遷:《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的著作權(quán)保護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16頁。持等同論的學(xué)者以謝雪凱為代表,其認為注意義務(wù)和審查義務(wù)均以行為人對侵權(quán)事實盡其所能去發(fā)現(xiàn)并制止為落腳點,兩者無論內(nèi)容抑或法律效果均并無二致。參見謝雪凱:《審查義務(wù):在線服務(wù)商主觀過錯之軸心——立法與判例的啟示》,《甘肅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2013年第3期。持包含論的學(xué)者以呂炳斌為代表,其認為從法律邏輯上而言,審查義務(wù)實為一種加強版的注意義務(wù),仍可從合理人的注意義務(wù)標準推導(dǎo)而出。參見呂炳斌:《網(wǎng)絡(luò)版權(quán)避風港規(guī)則的發(fā)展趨向》,《中國出版》2015年23期。相比較而言,筆者比較贊同最后一種觀點。我國司法實踐從未經(jīng)歷過像美國法院那樣的歸責原則之變遷。一直以來,我國法院奉行的都是間接侵權(quán)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事實上,審查義務(wù)與嚴格責任并沒有直接、必然的關(guān)系,后者是一種結(jié)果責任,即無論是否具有審查義務(wù)只要存在侵權(quán)行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都要承擔侵權(quán)責任。要使審查義務(wù)發(fā)揮實質(zhì)意義的功效,就應(yīng)當使其與侵權(quán)責任的構(gòu)成聯(lián)系起來,在四個構(gòu)成要件中最佳連接點只有不法行為和過錯。不法行為往往指向積極地作為,但審查義務(wù)之違反卻是一種不作為,因此只能將審查義務(wù)與過錯聯(lián)系起來,審查義務(wù)的履行與否也是衡量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否存在過錯的客觀形態(tài)。從這個意義上講,審查義務(wù)與注意義務(wù)具有功能和效果上的一致性,但并不能因此認為兩者是完全等同的。注意義務(wù)要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在日常的經(jīng)營過程中須盡到必要的謹慎和注意,審查義務(wù)要求其還須積極地作為,事先主動審查用戶上傳信息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合法性,如事前采用過濾技術(shù)或者人工審查以排除侵權(quán)信息,這并不以侵權(quán)明顯為前提。不過,就其本質(zhì)而言,審查義務(wù)屬于注意義務(wù)涵攝的范疇,審查義務(wù)的確立,要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積極采取具有期待可能性的預(yù)防措施,彌補了既有的注意義務(wù)體系整體被動之不足,換言之,審查義務(wù)本質(zhì)上屬于較高層級的注意義務(wù)。
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廣泛存在的“較高的注意義務(wù)”,其實質(zhì)內(nèi)容就是審查用戶上傳內(nèi)容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合法性。如在中文在線訴蘋果系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蘋果公司對涉案侵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行為負有較高注意義務(wù),但其未要求涉案應(yīng)用程序開發(fā)商提供相關(guān)的權(quán)屬證明文件(未履行審查義務(wù)),因此具有主觀過錯,應(yīng)當承擔相應(yīng)的法律責任。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802號民事裁定書。在十九樓網(wǎng)絡(luò)股份有限公司與瀟湘書院(天津)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糾紛案中,一審法院認為,十九樓網(wǎng)絡(luò)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其有簽約作者提供的原創(chuàng)作品(也有用戶上傳的他人作品),對網(wǎng)絡(luò)用戶上傳的涉案作品是否獲得作者授權(quán),是否涉嫌侵權(quán),應(yīng)當負有一定的著作權(quán)審查義務(wù);二審法院指出,十九樓網(wǎng)絡(luò)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其經(jīng)營模式等負有較高注意義務(wù),應(yīng)積極與上傳者取得聯(lián)系,對相關(guān)作品是否原創(chuàng)或者是否具有合法授權(quán)進行核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侵權(quán)行為發(fā)生或持續(xù)。參見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終6209號民事判決書。質(zhì)言之,在以“較高的注意義務(wù)”認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間接侵權(quán)的過錯時,法院一方面認為義務(wù)的性質(zhì)仍然是注意義務(wù),另一方面又將審查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合法性作為該注意義務(wù)的具體內(nèi)容。
我國主流觀點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負有合理的注意義務(wù),但不承擔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參見馬一德:《視頻分享網(wǎng)站著作權(quán)間接侵權(quán)的過錯認定》,《現(xiàn)代法學(xué)》2018年第1期;姚志偉、慎凱:《關(guān)鍵詞推廣中的商標侵權(quán)問題研究——以關(guān)鍵詞推廣服務(wù)提供者的義務(wù)為中心》,《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5年第11期;李欲曉、李忠妹:《視頻分享網(wǎng)站服務(wù)提供者的注意義務(wù)》,《西部法學(xué)評論》2013年第2期。這將注意義務(wù)與審查義務(wù)進行了人為地割裂和對立。如前所述,筆者認為,從法律邏輯上而言,審查義務(wù)與注意義務(wù)的基本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注意義務(wù)的設(shè)定并非一成不變,在特定的情形下要求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主動進行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亦是其合理注意義務(wù)的應(yīng)有內(nèi)容。換言之,注意義務(wù)包含審查義務(wù),但一般注意義務(wù)并不必然引發(fā)審查義務(wù),因此,在注意義務(wù)得到證成的前提下,需要分析一般注意義務(wù)上升為審查義務(wù)的合理性。
四、修正的方向:一般注意義務(wù)上升為審查義務(wù)之合理性
(一)從技術(shù)中立原則到私權(quán)力理論
傳播學(xué)原理認為,網(wǎng)絡(luò)媒介具有雙重屬性,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一方面,網(wǎng)絡(luò)媒介作為實現(xiàn)自然界物質(zhì)、能量和信息交換的手段、方法和活動,具有自然屬性;另一方面,網(wǎng)絡(luò)媒介作為被社會的人所創(chuàng)造和應(yīng)用,服務(wù)于一定社會目的并滿足其需要的手段、方法和活動,又具有社會屬性。參見燕道成:《“網(wǎng)絡(luò)中立”:干預(yù)性的中立》,《當代傳播》2012年第4期。技術(shù)中立原則主要從網(wǎng)絡(luò)媒介的自然屬性來理解其價值,忽視其社會屬性。以競價排名為例,算法本身僅指在一個有效的輸入后,通過有限的計算步驟得出結(jié)果,從而解決某一問題或者得到結(jié)論,從這個角度看,其屬于一項自動的科學(xué)技術(shù)。然而,究其本質(zhì)而言,搜索算法僅是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人類決策而已,網(wǎng)頁排名的算法實際上被賦予了設(shè)計者或經(jīng)營者的意識因素,算法本身的自動性不等于算法運用的中立性。盡管DMCA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塑造的避風港規(guī)則也要求其僅僅作為侵權(quán)信息通過的被動渠道(passive conduits),但隨著技術(shù)變得越來越復(fù)雜,越來越多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背離了設(shè)立避風港的宗旨,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通過對內(nèi)容、訪問以及終端用戶進行控制也展示了一種新型的融合,這與網(wǎng)絡(luò)的中立性背道而馳。Georgios I.Zekos,Copyrights And Trademarks In Cyberspace: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15 Chi.-Kent J.Intell.Prop.335-336(2016).剝開技術(shù)中立的外衣,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已經(jīng)超越“單純通道”的消極角色,不僅具備了影響網(wǎng)絡(luò)行為的動機(意志),還具有影響網(wǎng)絡(luò)行為的能力,這種能力本質(zhì)上屬于網(wǎng)絡(luò)空間私權(quán)力的運行。權(quán)力的本質(zhì)在于“哪怕遇到反對也能徹底貫徹自己意志的機會”,郭道暉:《權(quán)力的特性及其要義》,《山東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6年第2期。資源優(yōu)勢的運用則是權(quán)力產(chǎn)生、作用的基礎(chǔ)。運用這種資源優(yōu)勢的主體如果是國家或社會公共組織,對應(yīng)的就是公權(quán)力,如果是普通私人主體,對應(yīng)的則是私權(quán)力(private power)。參見張小強:《互聯(lián)網(wǎng)的網(wǎng)絡(luò)化治理:用戶權(quán)利的契約化與網(wǎng)絡(luò)中介私權(quán)力依賴》,《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年第7期。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私權(quán)力建立在其具有的技術(shù)資源、平臺資源、信息資源及其支撐的市場資源優(yōu)勢基礎(chǔ)之上。在私權(quán)力作用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角色由市場規(guī)則的服從者轉(zhuǎn)變?yōu)槭袌鲆?guī)則的制定者,并漸漸成為網(wǎng)絡(luò)社會空間及其內(nèi)生秩序的主要承擔者和建構(gòu)者,憑借自身的技術(shù)優(yōu)勢成為了網(wǎng)絡(luò)世界的新型權(quán)威。參見鄒曉玫:《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之角色構(gòu)造研究》,《中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7年第3期。以淘寶網(wǎng)為例,其平臺運營者在該網(wǎng)絡(luò)空間實際上享有相應(yīng)的“準立法權(quán)”(制定大量有約束性的平臺規(guī)則)、“準行政權(quán)”(對用戶進行內(nèi)部管理)以及“準司法權(quán)”(對用戶之間的糾紛爭議進行裁決處理)。
從網(wǎng)絡(luò)空間社會治理的角度出發(fā),網(wǎng)絡(luò)社會也是國家主權(quán)所及之地。然而,由于網(wǎng)絡(luò)空間具有去中心化和信息碎片化特征,使得國家治理手段呈現(xiàn)出“去中心化”趨勢,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由此演化為國家權(quán)力的延伸。參見裴煒:《針對用戶個人信息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協(xié)助執(zhí)法義務(wù)邊界》,《網(wǎng)絡(luò)信息法學(xué)研究》2018年第1期。因此,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享有的私權(quán)力具有極強的行政執(zhí)法屬性,與私權(quán)力對應(yīng)的義務(wù)主要是行政義務(wù)(公法義務(wù)),但私權(quán)力的運作同時也可以產(chǎn)生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義務(wù)(私法義務(wù))。日益受到重視的網(wǎng)絡(luò)審查就是一個例證,目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信息過濾義務(wù)并非完全以國家和社會秩序的維護為出發(fā)點,而是同時包含私權(quán)保護的客觀要求,出現(xiàn)了公私權(quán)益同質(zhì)化的傾向。正如有學(xué)者所言,此類協(xié)助執(zhí)法義務(wù),關(guān)注對象涉及個人隱私、知識產(chǎn)權(quán)、電子商務(wù)以及色情、暴力、仇恨、危害國家安全等廣泛事項。參見張新寶、許可:《網(wǎng)絡(luò)空間主權(quán)的治理模式及其制度構(gòu)建》,《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6年第8期。知識產(chǎn)權(quán)既是一種私權(quán)利,也代表了知識經(jīng)濟時代的財產(chǎn)秩序,代表了一種客觀價值秩序。參見于波:《網(wǎng)絡(luò)中介服務(wù)商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律義務(wù)研究》,華東政法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13年,第103頁。因此,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既是對私權(quán)的保護,也是對網(wǎng)絡(luò)空間公共秩序的維護,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基于私權(quán)力的行使而主動進行知識產(chǎn)權(quán)合法性審查,著眼于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利益,此種秩序維護恰恰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私權(quán)。私權(quán)力所具有的支配優(yōu)勢、所擁有的資源,意味著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在網(wǎng)絡(luò)生態(tài)中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應(yīng)當承擔更多的責任,這也符合“有權(quán)必有責”的一般原理。換言之,私權(quán)力就是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承擔他人責任的基礎(chǔ)。在其監(jiān)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的背景下,再以技術(shù)中立原則作為豁免其審查義務(wù)的理由實在難以成立。
(二)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是最小防范成本的負擔人
根據(jù)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初始權(quán)利的分配并不影響社會的福利,即防范措施的采取與誰是最小防范成本人無關(guān)。然而,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真實世界里,這種交易無法進行,初始權(quán)利的分配就影響了經(jīng)濟效率。為實現(xiàn)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應(yīng)將權(quán)利界定給防范成本較大的一方,Daniel H.Cole,The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to Property.Indiana Legal Studies Research.32(March).267-277(2014).防范成本較小的一方則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損害的發(fā)生,因此,決策者需要在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和權(quán)利人之間確定誰是最小防范成本負擔人。最小防范成本理論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比較各方當事人負擔的防范成本,選擇成本負擔最小的一方,這是討論的前提,因為其揭示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比權(quán)利人更適合承擔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的經(jīng)濟合理性;其二,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即便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比權(quán)利人更適合作為審查義務(wù)的成本負擔人,還需進一步判斷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預(yù)防成本是否小于預(yù)防產(chǎn)生的收益。
首先,確定最小防范成本負擔人(the least-cost avoider)。隨著過濾技術(shù)的進步以及成本的降低,網(wǎng)絡(luò)經(jīng)營者可以憑借內(nèi)容識別技術(shù)和智能算法進行信息檢查,其能力大大提高。與權(quán)利人相比,讓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承擔監(jiān)控過濾義務(wù)可以產(chǎn)生規(guī)模經(jīng)濟的效果。通過運行相同的技術(shù)系統(tǒng)實現(xiàn)多個權(quán)利人的利益,過濾的邊際成本也會隨著規(guī)模的增大而降低,Lital Helman,Gideon Parchomovsky,The 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Standard.111 Colum.L.Rev.1213(2011).在上傳階段就將侵權(quán)內(nèi)容過濾掉,也是防范侵權(quán)的題中之義。平臺因承擔主動審查義務(wù)而承擔的激勵損失不僅絕對值降低了,而且在與權(quán)利人激勵損失的比較中,其相對值也下降了。除過濾技術(shù)之外,人工審查的成本也并非絕對居高不下,對于特定的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如視頻分享網(wǎng)站而言,其為了滿足行政管理部門的內(nèi)容監(jiān)管要求,必須對于網(wǎng)站內(nèi)提供在線播放的每一個視頻文件進行內(nèi)容審查,所需的相關(guān)人力成本已經(jīng)支出。雖然該審查本身不是為了防止侵犯著作權(quán)目的,但在進行內(nèi)容審查時附加進行著作權(quán)合法性的審查,對視頻分享網(wǎng)站而言不會增加不合理的負擔。即便進行監(jiān)控或?qū)彶榇_實會產(chǎn)生額外的人工成本,但其內(nèi)部的人力資源等也可以進行重新分配,“通知—刪除”環(huán)節(jié)中的人力資源很大一部分將轉(zhuǎn)移到事前的監(jiān)督環(huán)節(jié)上,因此,相對而言,其負擔的成本總量并不會明顯增加。Ashley Bumatay,A Look At TradeKey:Shifting Policing Burdens From Trademark Owners To Online Marketplaces.11 Hastings Bus.L.J.355(2015).質(zhì)言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進行人工審查的成本中,有一部分屬于其本應(yīng)承擔的行政審查義務(wù)的加強版,還有一部分則是其“通知—刪除”義務(wù)的轉(zhuǎn)嫁,這樣一來,真正增加的成本就可以控制在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承受范圍之內(nèi)。唯需注意的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客體具有非物質(zhì)性,這決定了其不能像有形財產(chǎn)一樣通過對實物的占有而彰顯權(quán)利,從而使得權(quán)利的確認和侵權(quán)的判定都格外困難。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信息不對稱更加明顯,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難以判斷哪些內(nèi)容屬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范疇,也不能確定上傳者是否經(jīng)過了授權(quán)或者屬合理使用。相反,權(quán)利人最適合處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讓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負擔審查義務(wù)的同時還需進行成本的合理分擔而不是完全轉(zhuǎn)移。
其次,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最小防范成本理論所包含的另一個含義是,被告的防范成本應(yīng)當小于預(yù)期損失,即所謂的“漢德公式”。漢德公式由美國第二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的漢德法官在United States v.Carroll Towing Co.案中創(chuàng)設(shè)。該案中被告的駁船船員離開了他的駁船長達21小時,在這段時間里駁船離開了停泊處并在隨風漂流的過程中恰巧與一艘油輪發(fā)生了碰撞。當時港口很繁忙,危險也很明顯,因此事故損失的邊際減少量很大,而船員的離開缺乏令人滿意的解釋暗示了注意的邊際成本很低,法庭據(jù)此認定了被告存在過失。參見[美]威廉·M.·蘭德斯,理查德·A·波斯納:《侵權(quán)法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王強、楊媛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頁。漢德公式鼓勵以合理的成本預(yù)防意外事故損失,因此需要就審查成本與預(yù)期損失(或因?qū)彶槎a(chǎn)生的預(yù)期收益)進行衡量。就審查成本而言,無論是人工審查還是過濾技術(shù)都意味著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需要額外負擔一定的金錢成本(包括過濾系統(tǒng)開發(fā)與維護、人力資源支出等等),但如前所述,此類成本可以隨著規(guī)模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資源重新分配而得到控制。值得關(guān)注的是,除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承擔的與審查直接相關(guān)的成本,還有整個社會可能為之負擔的成本,審查機制的運行可能會導(dǎo)致合法信息被錯誤刪除,進而威脅到用戶的言論自由與個人隱私,這是對公共利益的挑戰(zhàn)。對于此類間接成本,需要明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其本身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事實上,言論自由并非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獨有的難題,目前正在構(gòu)建的網(wǎng)絡(luò)安全審查制度也會對言論自由造成威脅,甚至威脅更大,但以網(wǎng)絡(luò)安全審查為代表的私人執(zhí)法并不能因此而廢止,參見孫禹:《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的合規(guī)規(guī)則— —以德國〈網(wǎng)絡(luò)執(zhí)行法〉為借鑒》,《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11期。如果認為網(wǎng)絡(luò)審查有其必要性,那就不能以言論自由為借口阻止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第二,技術(shù)的成熟和程序的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被錯誤刪除并為信息被錯誤刪除的用戶提供事后救濟。事前,無論是過濾技術(shù)還是人工審查都應(yīng)當將合理使用等情形考慮在內(nèi),以比例原則對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私權(quán)力進行適當限制。事后,可以設(shè)定類似于反通知的補救程序恢復(fù)用戶的合法信息。第三,即便合法信息被錯誤刪除,以經(jīng)濟分析的視角來看,同時阻止合法使用(lawful uses)和侵權(quán)使用(infringing uses)也可能會產(chǎn)生凈福利收益(net welfare gain),尤其在以下三種情形中更是如此:其一,侵權(quán)使用造成的損害高于合法使用帶來的收益;其二,侵權(quán)使用造成的損害與合法使用帶來的利益相當,但侵權(quán)使用對價格更敏感;其三,創(chuàng)作新作品帶來的激勵大于阻礙合法使用所帶來的損害。Douglas Lichtman,William Landes,Indirect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An Economic Perspective.16 Harv.J.L.&Tech.404-405(2003).
就預(yù)期損失而言,如果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不主動對用戶上傳的信息進行審查,那就只有通過設(shè)置侵權(quán)提示、投訴舉報通道等方式來預(yù)防侵權(quán)發(fā)生,但聲明、提示完全靠網(wǎng)絡(luò)用戶自覺自愿配合,并沒有強制約束力。用戶不會因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警示就放棄銷售假貨等侵權(quán)行為,由于權(quán)利人逐個維權(quán)的效率低下也使得用戶存有僥幸心理甚至有恃無恐。對于權(quán)利人而言,侵權(quán)因網(wǎng)絡(luò)傳播的擴散性造成的損失往往并非微小,網(wǎng)絡(luò)盜版盛行將導(dǎo)致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投資者不能收回其投入成本。當投資與報酬之間呈現(xiàn)顯著不相當?shù)臓顩r時就會產(chǎn)生“價值差”(Value Gap),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創(chuàng)新激勵將因此大打折扣,更有甚者會對公共利益造成威脅。例如,在商標權(quán)領(lǐng)域,網(wǎng)絡(luò)假冒產(chǎn)品的泛濫除了對商標權(quán)人利益造成損害之外,無疑會增加消費者篩選信息的搜尋成本,既扭曲正常的競爭秩序,實際上也損害了公共利益。在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以全球最大的視頻分享網(wǎng)站YouTube為例,其使用的ID Content系統(tǒng)耗費了其母公司谷歌公司5000萬美元。截至2016年,版權(quán)人就其作品通過該系統(tǒng)獲得的廣告收益分成超過10億美元。Chris Sprigman&Mark A.Lemley,Why Notice-and-Takedown Is a Bit of Copyright Law Worth Saving,Los Angeles Times,June21,2016.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sprigman-lemley-notice-and-takedown-dmca-20160621-snap-story.html.visited 20 Dec 2018.這也能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履行審查義務(wù)帶來的創(chuàng)新激勵以及產(chǎn)生的社會效益往往會超過審查的成本,從而產(chǎn)生一個有效率的結(jié)果。然而,需要明確的是,YouTube平臺上的過濾系統(tǒng)是其與權(quán)利人合作自愿應(yīng)用的,實踐中大部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并未與權(quán)利人達成這樣的協(xié)議。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如果交易成本足夠低,權(quán)利人、網(wǎng)絡(luò)用戶和平臺自然會通過談判,確定平臺應(yīng)當承擔一定主動審查義務(wù)的新秩序。不過,由于三方之間以及各方內(nèi)部的交易成本都異常高昂,如果法律不干預(yù),很難指望所有平臺都會承擔一定的主動審查義務(wù)。因此,以法律規(guī)則層面確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主動審查義務(wù)仍然十分必要。
五、余 論
從國內(nèi)外立法和司法的發(fā)展趨勢來看,確立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亦非全屬紙上談兵。盡管美國DMCA對服務(wù)商監(jiān)控義務(wù)持否定態(tài)度,但就其代表性案例觀察,似有“由嚴謹至寬松,再回歸于嚴謹”之趨勢,且相關(guān)業(yè)者于此實務(wù)發(fā)展下,亦未有因侵權(quán)責任加重,及課予監(jiān)控并采取過濾機制的責任,導(dǎo)致其創(chuàng)新受阻、發(fā)展停滯不前之情形。參見蔡碩庭:《網(wǎng)路服務(wù)提供者侵害著作權(quán)之民事責任》,《智慧財產(chǎn)評論》(臺北)2018年第1期。《歐盟電子商務(wù)指令》第15條僅規(guī)定服務(wù)商“不承擔監(jiān)督的一般性義務(wù)”,但是此規(guī)定不涉及特殊情況下的監(jiān)督義務(wù),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quán)法〉修改草案(送審稿)》完全排除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審查義務(wù)還是有所區(qū)別的。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議會于2019年3月26日通過的《歐盟數(shù)字化單一市場版權(quán)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s Market)進一步限制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責任豁免條件。該指令第17條規(guī)定的豁免條件之一是在權(quán)利人已經(jīng)提供了相關(guān)且必要信息的作品和其他內(nèi)容之后,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履行較高行業(yè)標準的專業(yè)注意義務(wù)(high industry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diligence),盡最大努力確保未經(jīng)授權(quán)內(nèi)容不被獲取。Directive(Eu)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Text with EEA relevance).OJ L 130,17.5.2019,pp.120.這樣的豁免條件將倒逼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對用戶上傳的內(nèi)容采取事先過濾的措施,盡管該規(guī)定是否完全合理還頗具爭議,See Giancarlo Frosio,To Filter,Or Not To Filter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EU Copyright Reform.36 Cardozo Arts&Ent.L.J.331-363(2018).See T.Randolph Bearda,George S.Forda,Michael Sterna:Safe Harbors and The Evolution of Online Platform Markets:An Economic Analysis.36 Cardozo Arts&Ent.L.J.317(2018).但也反映了強化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義務(wù)的趨向。在德國,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責任的《電信媒介法》(TMG)仍然以DMCA為藍本,但在司法實務(wù)中卻通過延伸適用交往安全義務(wù)而將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責任定位于“妨害人責任”,為其創(chuàng)設(shè)了“面向未來的審查義務(wù)”。德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2013年的GEMA v.Rapidshare案中就指出,身為資訊儲存服務(wù)中介者的Rapidshare應(yīng)承擔“部分主動監(jiān)控義務(wù)”,有必要采取合理措施以識別特定類型非法活動,例如通過采取詞匯過濾的方式來針對特定情況進行監(jiān)控。Urteil des BGH vom 15.August 2013(Az.I ZR 79/12).在我國司法實務(wù)中,法院對于審查義務(wù)的態(tài)度也不像立法機關(guān)或者司法解釋的起草者那樣絕對地否定,如前述樂視訴視暢以及樂視訴邁奔靈動案等案件中,法院均認為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應(yīng)當采取合理、有效的技術(shù)措施防止侵權(quán)行為的發(fā)生或因設(shè)分類頻道等模式對授權(quán)進行審查,既有判例對審查義務(wù)的適度肯定也使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在我國具有一定的生存土壤。
審查義務(wù)的正當性得以證成之后,要使其真正發(fā)揮作用,還需在制度層面確立審查義務(wù)的適用條件和履行規(guī)則,從而實現(xiàn)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在我國法律制度下的本土構(gòu)建(具體規(guī)則的完善有待筆者另行撰文研究)。一方面,網(wǎng)絡(luò)服務(wù)提供者承擔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具有正當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加區(qū)分地讓所有服務(wù)商對其網(wǎng)絡(luò)上的任何信息一一審查,即所謂的“普遍審查”。事實上,任何個案中的義務(wù)都必須結(jié)合特定的主體和具體的情形加以確定,并不存在一項先驗的義務(wù)。因此,有必要厘清適用審查義務(wù)的具體情形,即哪一類服務(wù)商在何種情況下應(yīng)當負擔積極主動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審查義務(wù),如是否需要區(qū)分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主體類型、行為類型以及權(quán)利客體類型,這有賴于以一定標準為基礎(chǔ)的類型化研究。另一方面,審查義務(wù)的履行需要充分考量成本和收益,即無論是審查方式的選擇(人工審查還是技術(shù)過濾)、審查程度的確立(形式審查還是實質(zhì)審查)、權(quán)利人和網(wǎng)絡(luò)服務(wù)商之間的成本分擔(如權(quán)利信息數(shù)據(jù)庫的建立、過濾系統(tǒng)的購買與維護),還是相關(guān)配套措施的采取(如為保障合理使用而為涉嫌侵權(quán)用戶提供的程序救濟)都應(yīng)以此為衡量標準,至于具體規(guī)則的建構(gòu),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