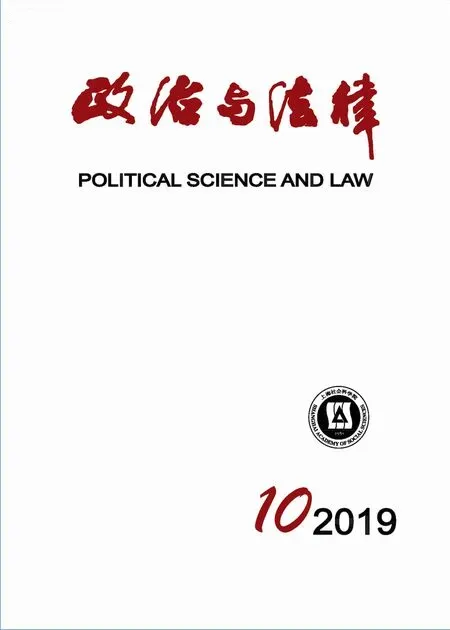論我國憲法中環境權的表達及其實施*
彭 峰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上海200020)
環境權的概念興起于十九世紀中期北美大陸盛行的保育運動。當時的這一運動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在環境權與發展權關系上,人們認為環境權需讓位于發展權,強調的是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和人類發展,所有濫用自然資源的行為均可通過正確的、有效率的行政管理體系加以制止,由此協調生產因素并獲得最大的效率。這一時期的環境權是生產取向的,以管理者為核心。①參見蘇永欽主編:《部門憲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臺北),第678~679頁。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環境保護運動取代了保育運動,這一運動以公民社會為基礎,其背景是戰后美國經濟的發展造就了史無前例的富庶,大量州際公路修建完成,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休閑活動范圍擴大,但同時,公害事件在全球范圍內頻頻發生,人們深感到環境資源的可貴。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環境權取得了非常明確的地位,甚至進入美國政府體制中,成為一種政府必須保護的天賦人權。這一階段更全面地肯定了公民環境主張和價值,甚至有凌駕于發展權的趨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環境倫理成為環境權的重要內涵,倫理的范圍被擴展至動植物,對環保主義者而言,環境倫理比人際倫理更為重要。②參見上注,蘇永欽主編書,第679~682頁。環境權概念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傳入我國學術界。③參見凌相權:《公民應當享有環境權——關于環境、法律、公民權問題探討》,《湖北環境保護》1981年第1期;蔡守秋:《環境權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此后幾十年,我國對環境權討論熱烈,觀點紛呈。從各國立憲實踐看,迄今為止,即便是已有眾多國家規定了憲法環境權,但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并沒有在憲法中規定這類權利。那些已經規定了憲法環境權的國家,并沒有在環境保護和人權保障方面積極地、富有成效地作出實施,反而是一些在環境保護和人權保障領域成效卓著的國家卻從原則上反對將這種環境權利憲法化。④參見[英]蒂姆·海沃德:《憲法環境權》,周尚軍、楊天江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這意味著,環境權入憲與否并不能等同于高水平的環境保護和人權保障能力。在2018年我國《憲法》修改以后,環境權是否入憲的問題再次引起各方關注,學界觀點不一。為此,需要反思和梳理的是,環境權的實際內容在我國是否已經入憲了,或者是否一定要以憲法列舉的模式來規定環境權,我國《憲法》現有的保護方式是否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憲法依據對其進行保護,現有模式與列舉基本權利的模式相比,是否后者更有利于環境保護這一公共目標的實現。
一、我國環境權入憲的代表性觀點
自環境權概念引入我國以來,我國環境法學者多年來積極倡導“環境權”入憲,特別是在2018年我國《憲法》修改過程中,以呂忠梅、吳衛星為代表的學者對此進行了積極的呼吁。如呂忠梅主張,將環境權作為基本權利在憲法中加以規定,是環境保護入憲的一種重要方式,它是公民享有的在清潔、健康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她認為,環境權是繼自由權、生存權之后的“第三代人權”,性質上區別于生存權、健康權,其屬于一種積極權利,“只有將‘環境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基本權利納入人權體系并在憲法中加以規定,才能為人在良好環境中生存提供最完整和最充分的權利保障,為國家承擔環境保護責任、公民享有環境權利并得到法律保護提供‘基石’或合法性依據”。她還認為,實現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確立人在自然界中的道德和法律責任的目標,并非只有賦予自然主體地位一種途徑,也可以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承認自然具有一定的主體性,肯定自然在環境法律關系形成中的價值,又不破壞“法律是人的行為準則”的基本屬性,將自然作為特殊客體加以保護,以通過“人對自然的權利”(human right to nature)實現“自然的權利”(right of nature)。⑤參見呂忠梅:《環境權入憲的理路與設想》,《法學雜志》2018年第1期。
吳衛星認為,環境權入憲在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其入憲的方式包括兩種。一種是憲法解釋路徑。我國憲法雖然沒有確立環境權條款,但是,如果采取非原旨主義的憲法解釋方法,可從“環境政策”條款(我國《憲法》第9條和第26條)推導出公民環境權。另一種是修憲路徑。通過修改憲法確認公民環境權是一種更好的路徑選擇,可以將環境權條款納入我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其條文可設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在清潔、健康、生態平衡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有依法及時獲取環境信息、參與環境決策以及通過訴訟保護環境的權利。國家有義務通過適當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他認為,該條事實上分為兩款,第一款前半句直接規定了公民的權利,即公民環境權,該款后半句表達的是知情權、參與權和訴諸司法權,以便藉由這些程序性權利來進一步保障環境權,而用“清潔、健康、生態平衡”加以修飾,則同時兼顧了人類的利益和環境本身的利益,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調和。⑥參見吳衛星:《環境權入憲的比較研究》,《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
從以上一些積極推動環境權入憲的環境法學者的觀點看,可以形成共識的是,環境權在我國是一項人的權利,即完全排除了自然可以作為法律主體的可能,最多只是將自然作為特殊客體加以保護。更趨一致的是,他們認為環境權必須在我國憲法中的基本權利部分進行條款化,而憲法中的相關國家政策條款、程序性條款、基本權利中的財產權以及通過解釋得出的生存權等,并不能推導出憲法承認了環境權。他們認為只有在基本權利中明確列舉出環境權,才意味著這一權利入憲了。他們一方面試圖推動創造一種內容獨立的環境權,另一方面卻不能指出這種環境權的主體到底是誰,作為權利主體的“人”是個人還是公民、公眾(不特定多數人),抑或是民族、由自然人組成人的組織(或集體、單位)或人類整體?⑦參見蔡守秋:《環境權實踐和理論的新發展》,《學術月刊》2018年第11期。與此同時,他們傾向于認為這種環境權是一種社會權,歸屬于積極權利范疇。然而,上述觀點存在矛盾沖突。一方面,有些社會權本身體現為一種客觀法秩序,通過國家政策條款可以作出功能替代;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希望得到的是一種主觀權利性質的環境權,那么它的內容和屬性一定是復合性的,其至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表現為消極權利,比如既有的與環境利益相關的自由權或政治權利,而他們又認為這些權利并不是其所主張的環境權。
由此可見,對作為“舶來品”的環境權概念,其不僅在東西方語境中的涵義并不一致,而且在我國其也未形成理論上的共識,相關的理論對我國實定法中的相關規范沒有全面地梳理和考察。因此,對于環境權是否應當入憲,需要厘清以下幾個前提性、基礎性問題:我們正在爭取寫入憲法中的環境權的內涵是什么,該權利主體為何;其權利屬性為何;我國現行憲法已有的國家政策條款、基本權利條款和程序性條款,是否足以保障環境權利(群)的實現。
二、西方語境下的憲法環境權及其表現形式
討論環境權入憲的基礎是要明確什么是憲法環境權。如前所述,在我國,“環境權”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性概念,Joshua C.Gellers在《憲法環境權利的全球興起》一書中指出,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世界各國在其各自的憲法中都采用了“與環境保護和治理有關的人權”這一表述,這些法律條款被統稱為“憲法環境權利”(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⑧Joshua C.Gellers,The Global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Now York,Routledge,2017,p.2.Sanja Bogojevi?與Rosemary Rayfuse則概述了三種常用于描述和促進環境權利的框架:自然權利、環境人權、環境參與權利。他們認為,雖然這些框架是流動的,可能也意味著它們相互之間有重疊,但它們各自引起了不同的討論,對環境權利的性質、內容和含義提供了不同的結論。⑨Sanja Bogojevi?&Rosemary Rayfuse,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and Beyond:Setting the Scene,in Sanja Bogojevi?&Rosemary Rayfuse(eds),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and Beyond,UK,HART PUBLISHING,2018,p.5.顯然,西方話語體系下的“環境權利”指的是一系列與環境相關的權利(群),而不是內容單一的“環境權”。此外,以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為區分標準,在各國憲法和法律中,環境權利可以分為作為“自然的權利”的環境權,以及作為“人的權利”的環境權。
作為“自然的權利”的環境權利觀建立在生態中心主義基礎上,認為環境或自然自身能夠擁有自己的合法權利。這一權利形態的邏輯假設是認為正如法律保護的對象已擴展到如少數民族、婦女和公司的權利和利益一樣,它也應擴展到自然界。⑩Sanja Bogojevi?&Rosemary Rayfuse,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and Beyond:Setting the Scene,in Sanja Bogojevi?&Rosemary Rayfuse(eds),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and Beyond,UK,HART PUBLISHING,2018,p.5.2008年,厄瓜多爾成為第一個在國家憲法中明確承認不可剝奪的自然的權利的國家,其憲法71條明確:“充分尊重自然存在的權利、充分尊重自然的生命周期、結構、功能和進化過程的維持和再生的權利。”參見《厄瓜多爾憲法》,https://m.book118.com/html/2018/1020/8057125117001127.shtm,2019年8月5日訪問。之后,一些國家也紛紛效仿,在法律中規定了自然的權利,如玻利維亞《地球母親權利法》和新西蘭《尤瑞瓦拉國家公園法》。玻利維亞《地球母親權利法》(Ley de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于2010年通過,2012年修訂為玻利維亞《世界地球母親宣言》(Proyecto de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los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新西蘭《尤瑞瓦拉國家公園法》(Te Urewera Act)于2014年通過。
玻利維亞《地球母親權利法》第2條規定了地球母親的權利:“地球母親及其組成的所有生靈具有以下固有權利:(a)生命權和存在權;(b)受尊重的權利;(c)恢復其生物能力并繼續其不受人為干擾的重要循環和過程的權利;(d)作為獨特、自我調節和相互關聯的存在保持其身份和完整性的權利;(e)獲得生命之源的水的權利;(f)享有潔凈空氣的權利;(g)整體健康權;(h)免于污染、污染物、有毒或放射性廢物侵害的權利;(i)不得以威脅其完整性或重要和健康功能的方式修改或破壞其遺傳結構的權利;(j)因人類活動造成的侵犯本宣言所承認的權利的充分和迅速恢復的權利;(2)任何生靈都有權為了地球母親的和諧運行而在其上占有一定空間、對其扮演自身角色的權利;(3)任何生靈皆有權享受福祉、并免于人類的酷刑或殘忍對待地生活的權利。”Proyecto de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los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世界地球母親宣言》,http://rio20.net/en/propuestas/universal-declaration-of-rights-of-mother-earth/,2019年8月10日訪問。新西蘭《尤瑞瓦拉國家公園法》第三部分宣稱,尤瑞瓦拉國家公園為一個法律實體,擁有作為法律實體的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其權利、權力、職責由它的董事會以其名義執行。Te Urewera Act 2014,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14/0051/latest/whole.html#DLM6183705,2019年8月10日訪問。
在司法領域,2017年,印度北阿坎德邦的高等法院授予某些河流和冰川與人類相同的合法權利。法院承認恒河和亞穆納河為法人,因為它們具有“神圣和受人尊敬”的地位,法院指定州政府為它們的監護人;此后,北阿坎德邦邦政府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稱“他們作為河流守護者的責任并不明確,因為這些河流遠遠超出了北阿坎德邦的邊界”。經審理后,印度最高法院撤銷該高等法院判決,作出否定恒河、亞穆納河“有生命實體,擁有法人地位”的決定。該國最高法院表示,將兩河視為生命實體在法律上不成立。這兩條河源自雅母諾特里(Yamunotri)和根戈德里兩條冰川,它們都是印度教中的圣河,恒河也被稱為MAA(母親),不過恒河目前是地球上污染最嚴重的河流之一,先前高等法院裁決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法律依據,讓工業廢水不能倒入“生命體”中。然而,邦政府在上訴狀中稱:“為了保護社會信仰,河流不能被宣告為法人。”2019年7月,孟加拉國最高法院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承認所有河流與人類同等法律地位,它的河流被視為生命體,這一判決旨在保護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免受污染、非法疏浚和人類入侵的進一步破壞,河流保護委員會(National River Conservation Commission)被指定為孟加拉國河流的合法監護人。《與人類平等?孟加拉國賦予河流權利有何深意?》,https://k.sina.com.cn/article_2316796262_8a17816600100k5k5.html,2019年8月10日訪問。然而,盡管有這些國家的實例,這種以生態主義為中心確認自然的權利的方法仍然具有高度爭議和有限的應用。如這種賦予自然以權利的法律遭到了工人、農民和流經社區的抵制,他們認為賦予大自然人格侵犯了他們的權利和生計,此外,判決執行的困難也是不可避免的。
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作為“人的權利”的環境權利規定得更為普遍。Joshua C.Gellers對世界各國憲法中的“憲法環境權”進行了梳理,認為其通常以下面三種表現形式出現。
第一種類型是程序性環境權利(Procedural environmental rights),具體指“促進形成環境治理基石的透明度,參與和問責制”的法律權利,這類權利內容包括結社自由、獲取信息、公眾參與決策以及在環境問題上訴諸司法。程序性環境權利可以作為實現與環境相關的目標的手段,也可以通過促進話語和民主來達到目的。Joshua C.Gellers,The Global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Now York,Routledge,2017,p.6.例如,阿爾巴尼亞憲法規定保障公民“有權了解環境狀況及其保護”。
第二種類型是實體性環境權利(Substantive environmental rights),它是指在環境問題激發人權問題時可能適用的國際人權法范疇內的權利。可能與環境問題相關的實體性權利包括“生命權,健康權,適足生活水準權和隱私權”。Joshua C.Gellers,The Global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Now York,Routledge,2017,p.6.如歐盟的法律沒有明確宣示或承認環境權,歐洲人權法院主要通過對法律明示規定的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私人生活權等的保護實現對環境權的保護。
第三種類型是社會連帶性權利(solidarity rights),它建立了與之相關的特定權利與國家可以自行確保的其他形式的權利不同的語境,要求全球共同參與執法。社會連帶性權利被認為需要廣泛的行動者、社區和普遍合作來“(實現)一個宜居的世界”。Hassan,F.,Solidarity Rights:Progressiv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New York law School human rights Annuals,I,1983,p.54.1976年,《葡萄牙憲法》規定了作為這種社會連帶權的環境權。該法第66條規定:“一、任何人均有權利享有一個適合人類、健康及生態平衡之生活環境,并有義務維護之。二、國家有責任透過本身機構以及透過呼吁與支持民間倡議,以便:(a)預防與控制污染與污染之后果以及侵蝕之危害;(b)整治及促進領土之整治,目的系為活動地點之正確性、社會與經濟發展之平衡及生物風貌之平衡;(c)建立及開發保護區、自然公園及休憩公園,劃分及保護風景與地點,以確保大自然受保護,并保存有歷史或藝術意義之文化價值;(d)促進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障其再生能力及生態穩定性。”《葡萄牙憲法》,https://bo.io.gov.mo/bo/i/cn/crpcn/crpp1t3_cn.asp#a66,2019年8月11日訪問。這種社會連帶權利也包括發展權和和平權,通常被認為是國際人權譜系中的“第三代權利”。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一些西方學者利用聯合國的機構,特別是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推動“社會連帶性權利”這一概念的使用,并且把連帶關系作為一種“人權”來提出,認為現在正在出現由“連帶關系權利”構成的“第三代人權”。其主要發起人是法國的卡雷爾·瓦薩克,他是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及和平處處長,早在1974年,他曾指出有“三類人權”,新的一類人權可以稱為“連帶關系權”,它們體現了某種共同生活的概念,它們只有由所有的社會伙伴——個人、國家、其他公私實體協同努力才能實現,這些權利是諸如健康的環境權、清潔的飲水權、新鮮空氣權以及和平權。他認為,第三代人權“源于人們明顯的兄弟情誼和他們之間必要的連帶關系;此種權利會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上把人們聯合起來”。參見李澤銳:《論連帶關系概念的重新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西方國際法學思想動向》,《法學研究》1985年第6期。
在西方國家,環境權主張的出現,始于保育運動,后來發展到環境保護運動,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現了環境正義運動,其作為社會正義運動中的一種主張,于九十年代得到發展,它是美國現代環保思想與社會正義運動的融合。美國環保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和兩次轉變: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是從保育運動到現代環保運動的發展,以人們對自然的態度轉變為標志;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則是從環境保護運動到環境正義運動的發展,以人們的關注點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回歸到人與人的關系為標志。參見趙嵐:《美國環境正義運動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頁。環境保護運動與環境正義運動雖然具有不可割舍的聯系,但也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從現代環境保護者看來,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和各物種之間的聯系是其固有特征,任何破壞此多樣性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并且物種之間的聯系使得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會最終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因此,這一運動的著眼點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里的自然仍是遠離人群的山川河流、樹林荒野以及生活在其中的野生物種,因此現代環境保護主義運動的主體是以白人、男性、中產階級為主。環境正義運動更多地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將環境問題擴展至都市生活,其在環境問題中加入了社會公平的維度,這一運動的主體則是受到有毒廢棄物影響最深重的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群體等受害者群體。參見上注,趙嵐書,第2~3頁。激進的環保主義者主張的環境權是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價值基礎的,強調的是自然的權利,而環境正義運動所主張的環境權顯然是以人的權利為基礎的,這一轉變緣自西方發展權的挑戰,以及對作為早期環境保護運動理論基礎的生態理論、反成長典范、“以人類以外的生命權”與環境倫理的批判,在美國法院,許多審理環境案件的法官肯定了環境權為人類的基本生存權利之一。參見前注①,蘇永欽主編書,第683~685頁。
雖然各國對于憲法環境權條款的設計有所不同,但從總體看,存在的重大差異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在權利的內容構成方面,是形成健康的環境還是安全的環境。第二,環境權條款是在憲法中的基本權利部分,還是在序言部分作規定。第三,該權利是可以直接訴諸法院,還是通過立法進行具體化實施。第四,將環境權設計為什么類型權利,是程序性還是社會連帶性權利。Joshua C.Gellers,The Global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Now York,Routledge,2017,p.15.
Joshua C.Gellers認為,與程序性環境權利不同,社會連帶性環境權利一般不甚清晰,其實現的途徑也非常不明確,很少包含具體的實施性指示,因此,這種特征意味著頒布憲法環境權的機關所支出的財政和政治成本可能很低,至少在跨國倡議團體迫使國家遵守之前,這種成本最小化的方式使各國更有可能在憲法中采納社會連帶性環境權,而不是程序性環境權條款。Joshua C.Gellers,The Global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Now York,Routledge,2017,p.68.相關統計顯示,將環境權作為社會連帶性權利而不是程序性權利的國家,比例遠超過三分之一。Boyd,D.R.,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Human Rights,and the Environement.Vancouver,BC:UBC Press.2012,https://www.ubcpress.ca/asset/9569/1/9780774821605.pdf,2019年8月10日訪問。
從保護目的來看,各國憲法環境權利條款主要存在兩種類型的基本環境權利(群),即以保護個人權利為目的的環境權條款和以保護與環境問題相關的群體的權利為目的的環境權條款。
三、我國憲法對作為“人的權利”的環境權的保護
筆者認為,如果我國的“環境權”的內涵與西方國家一致,皆表現為權利(群),那么我國的實體性環境權、程序性環境權、作為社會權的環境權、作為社會連帶權的環境權均已經入憲了,即都可以通過憲法解釋出來。
首先,作為參與權的程序性“環境權利(群)”的保護在我國《憲法》中可以找到充分的依據。通說認為,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被視為政治自由。參見鄭賢君:《基本權利原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結社自由、獲取信息、公眾參與決策、在環境問題上訴諸司法的程序性救濟等內容構成了作為參與權的“環境權利(群)”內容,它與我國《憲法》第35條的聯系最為緊密。該條款已經明確規定了結社自由,對于獲取信息,雖然沒有直接規定公民享有知情權,但依法理推斷,知情權被認為是包含在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之中的一項權利,通過該條規定的表達自由得以涵括。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該條款是對我國公民參政權的概括性確認,在此基礎上,我國《憲法》第41條第1款對公民監督權進行了具體表述,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該條第2款還規定:“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顯然,這些條款可以作為公眾參與決策和針對環境問題訴諸司法的憲法依據。
其次,作為自由權的實體性“環境權利(群)”的保護,可以由我國《憲法》中“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條款來涵括。一般認為,至少存在一組作為基本權利的核心人權,將其入憲是任何現代憲法都毫無例外的,這組核心人權包括生命權,免受酷刑的自由,不受任意拘留和逮捕的自由,無罪推定的權利,隱私權,活動自由,財產權,思想、良心、宗教自由,表達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政治參與的權利,等等。參見前注④,蒂姆·海沃德書,第47頁。人權既然是人之作為人應當享有的權利,它就不能只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權利,因此,在現實性上,人權主要表現為法律權利,從憲法角度看,就是憲法確認和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參見童之偉主編:《憲法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頁。對于憲法未列舉的權利,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認為可以經由憲法中的兜底性權利保障條款和“環境與生態保護”國策條款推導出“健康權”、“勞動權”、“環境權”等未列舉權利,這樣,憲法所保障之“環境權”已內涵生存權、財產權等列舉權利,“健康權”與“勞動權”之保障同理,此類憲法規定因補充功能或媒介功能所推導出之權利與已列舉權利之間產生競合關系。參見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利之保障為中心》,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臺北),第32~33頁。我國憲法文本在“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共列舉了18項權利,包括自由權和社會權,我國《憲法》第33條明文規定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概括性義務。我國憲法雖然沒有明確列舉生命權、健康權、隱私權等,但是,這類與生俱來、先于國家存在、具有固有權層次的基本權利,不會因為憲法未將之列入基本權利清單,國家即不予保障。參見上注,李震山書,第99頁。對于財產權的保護,我國《憲法》第13條第1款規定“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該條第2款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以及2004年我國《憲法修正案》用“財產權”取代了“所有權”,表明凡合法財產均受憲法保護,憲法上的財產權也可簡單界定為具有經濟利益的權利。參見謝鴻飛:《中國民法典的憲法功能——超越憲法施行法與民法帝國主義》,《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我國還存在大量關于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隱私權的民事及其他法律規范,我國對實體性環境權利可以通過對上述權利的法律保障進行間接保護。
再次,作為社會權的“環境權利”由我國《憲法》關于“自然資源保護”和“國家環境保護”的政策條款予以保障。社會權與自由權不僅存在互補性,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它們的功能完全不同,社會權不是防御和制約權力的,而是要求國家提供積極作為,從而有可能為權力的擴張,侵犯和限制個人的財產等自由權帶來便利的借口,如增加福利必然需要更多地增稅。參見夏正林:《從基本權利到憲法權利》,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頁。公民權利的形成源于政府對公民日常生活無正當理由干涉的一種限制,與此相對,社會權利則給政府強加了一種積極的職責,保證人民能夠在與一種人類尊嚴的基本水平相符的條件下生活和工作,因此,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一個是國家克制,另一個是國家參與。參見前注④,蒂姆·海沃德書,第59頁。在有些西方國家,社會權利通常被認為不是法律保護的恰當對象,因為它們需要國家采取行動,也就是它們使國家承擔積極行動的義務,這被認為將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相區分開來;公民權利僅僅是消極權利,只限制國家的行動,因此,這解釋了為什么社會權利不是由國家保障的基本權利。參見前注④,蒂姆·海沃德書,第59頁。根據傳統的解釋,國家保護公民和政治權利所必須做的全部內容就是通過法律,對政府強加特定的限制;與此相對,國家保障社會權利就必須引入包含資源配置方案的條款。因此,消極權利的實際條款可以要求國家履行積極的義務,而這些也具有行政成本,社會權利則要求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成本之外還存在實質性的成本,也隱含著如果法官就社會權利作出判決,實際上是在作超出憲法權限范圍的預算決定。參見前注④,蒂姆·海沃德書,第60~61頁。社會權規范主要有兩種類型——規則和原則;規則意義上的社會權是具有確定效力的憲法權利,是能夠主張的主觀權利;原則意義上的社會權是只具有初步效力的憲法權利,它不能夠被直接主張;與自由權規范主要體現為規則不同,規則只是社會權規范的一種例外形式,原則才是社會權規范的主要表現形式。參見前注,夏正林書,第137頁。我國學者鄭賢君認為,憲法權利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憲法權利就是基本權利,就是憲法文本中規定的權利;而狹義的憲法權利只是憲法基本權利文本中的那部分公民權與政治權利,其具體內容是人身、財產、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參見鄭賢君:《論憲法權利》,《廈門大學法律評論(第4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頁。
在我國《憲法》中,涉及作為社會權的“環境權”的條款可以分為國家目標條款和國家政策條款兩類。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對現行憲法作出了第五次修改。《憲法修正案》第32條將憲法序言中的“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憲法》第89條“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中的“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修改為“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憲法修正案》第46條)。此外,我國《憲法》第9條第2款“自然資源保護”和第26條“環境保護”即為國家環境政策條款。有學者認為,《憲法修正案》在序言部分和國務院職權部分就生態文明建設作出規定后,我國憲法上的環境法治相關規定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新的“環境憲法”規范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憲法序言第7自然段的部分根本任務,第一章總綱中第9條第2款、第10條第5款、第26條,第三章“國家機構”中第89條第6項。其中,關于“生態文明”的兩項規定和《憲法修正案》第32條的規定屬于“國家目標”條款,也就是規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應朝向什么目標、完成什么任務,是對國家生活具有基礎性調整效果的規范;《憲法修正案》第46條是國家機構條款,主要是增加了國務院的憲法上的生態文明建設等涵蓋環境保護的職權,也具備國家目標條款的性質,設定了一系列國家任務,這一國家目標的設定,主要指向的是在憲法上通過客觀法規范對國家各類權力課予不同層次或方面的義務。參見張翔:《環境憲法的新發展及其憲法闡釋》,《法學家》2018年第3期。
圖施耐特將社會權規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宣示性的、不具有司法強制性的社會權規范;第二類是具有“弱”效力的社會權規范;第三類是具有“強”效力的社會權規范。他認為沒有法律拘束義務的社會權規范可能由兩個方面的原因所確立:一是一部憲法可以直接列舉宣示性的作為國家政策目標的社會權,但可以排除它們的司法強制效力,因為這些規范沒有賦予當事人主觀上的請求權,法院也不能將其作為審判案件的依據;二是法院也會使有些本來應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條款失去法律拘束力。因此,由于這些社會權不具有司法強制性,傳統上,英美國家權利理論不認為是權利條款,因為無救濟即無權利。參見前注,夏正林書,第147頁。與自由權不同,對于以傳統自由權為理念的憲法文本要解釋出認可社會權的價值,只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憲法修改,增加對社會價值內容的敘述;二是對現有的原則規范進行擴張解釋,盡可能地“嵌入”社會權的價值。參見前注,夏正林書,第150頁。在我國,作為社會權的環境權就是通過本次修憲將生態價值“嵌入”憲法文本之中的。
再其次,作為社會連帶性權利的環境權的保護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憲法上的基本國策條款得以保障。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我國憲法上的一項基本國策,這一理念對人類社會的緊密聯系性質和互賴關系進行了深刻的闡述,對集體權利、代際權利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改變了憲法權利理論的“個體權利觀”向“共同體權利觀”進化。參見祝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憲法理論的創新和貢獻》,《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4期。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人類所面臨問題的共同性為出發點,強調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聯結。參見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289~293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到目前為止,地球是人類唯一賴以生存的家園,珍愛和呵護地球是人類的唯一選擇……我們要為當代人著想,還要為子孫后代負責。”參見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38頁。基于人類生存家園的唯一性,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將權利主體的地域范圍擴展至人類本身,把人類本身作為一個權利主體,并在時域范圍上擴展至跨世代的人;在權利的實現方式上,共同體權利觀不再簡單地限于防御、給付、制度性保障等方式,而是向協商互信、積極預防和增大供給的方向發展。參見前注,祝捷文。作為社會連帶性的環境權強調的正是這種集體人權,人人以及國際間需要相互合作來共同保護環境的理念,這一性質的環境權的價值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入憲納入了憲法所確立的多元價值中。
最后,作為個人權利的環境權存在內容和邊界模糊的缺陷。環境權無疑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即使可以確定個人擁有明確的環境權,也存在進一步細化的困難,因為權利的內容不甚清楚,并且具有不確定性。正如波義耳指出:“什么構成一個體面的環境是一種價值判斷,合理的人會在這種價值判斷上有所不同。”Colin T Reid:Pitfalls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Rights,in Sanja Bogojevi?&Rosemary Rayfuse(eds),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and Beyond,UK,HART PUBLISHING,2018,p.39.在某種程度上,環境權與憲法和類似文件中所規定的許多其他權利可能產生競合,與其他一些具有明確邊界的私法權利類型相比較,如財產權,顯然一項作為個人權利的環境權的邊界缺乏精確性,更重要的是,環境權在現階段并不存在其他已定型化的權利不能保護的內容,更多是現有權利在環境領域的適用。由于對作為個人權利的環境權利的內涵、概念、核心意義到底是什么缺乏共識,如何實現這一權利也存在固有的模糊性,很多因素對環境質量的改變造成影響,很難確定環境質量惡化到哪種程度和邊界已達到不可接受的水平,賦予一項作為個人權利的環境權,通常會增加更多層次的變量。此外,即使賦予個人環境權,它需要與其他基本權利進行競爭,在與其他實體性權利群和程序性權利群進行競爭的過程中,它不具有任何優勢,往往會被作為次要因素考量。因此,環境問題的性質使得這種獨立的個人環境權并不利于其以基于權利的方法,在參與權利競爭中確保避免持續的環境退化所需的優先權和尊重。Colin T Reid:Pitfalls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Rights,in Sanja Bogojevi?&Rosemary Rayfuse(eds),Environmental Rights in Europe and Beyond,UK,HART PUBLISHING,2018,p.27.
值得說明的是,如果我國的“環境權”是一項與西方的環境權內涵并不一致的權利,我國《憲法》也沒有必要創設一種新的作為私權的環境權,即通過擴大權利清單的方式以確立這項權利。其一,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今為止的所有國際環境公約談判中,我國一貫堅持發展中國家立場,發展權在長期來看仍是我國主張的最核心的權利,環境權在與發展權的競爭中不具有優勢,我國現階段只是在以發展權為中心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綠色轉型。其二,在我國《憲法》中確立一項新的環境權,這種直接保護模式與現行的間接保護模式相比,并不利于環境保護效果的實現,在與基本自由權如生存權的競爭中,我國《環境保護法》中規定的保護優先原則,不可能是絕對的,只能是相對的,是各種利益平衡的結果。因此,是否有必要確立一項作為個人的獨立的環境權,需考慮其與發展權的關系、與其他位階更高的基本權利之間的競爭、權利實施的成本和實際效果等因素。
四、通過立法對憲法環境權的實施
環境權利的性質本身是復合性的、含糊的,如前所述,以人的權利為基礎,各國憲法將其構造為程序性、實體性、社會連帶性的環境權利(群),我國學者則主張社會權性質的環境權。不論進行怎樣的憲制安排,作為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環境權利(群),我國《憲法》已經在主觀權利層面予以了保障;作為社會權和社會連帶性的環境權,我國憲法通過序言和國家政策條款,將其客觀價值納入其中,以客觀法秩序進行保障。在我國,憲法的實施主要通過對其條款的專門的具體立法來實現,因此,我們對環境權入憲的爭論可能更應向落實憲法環境權條款的環境立法及實施效果的關注作出轉變。
首先,對于程序性“環境權利”(群)的實現,在相關立法領域,通過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對相關權利進行保障。在結社自由方面,2016年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1條開宗明義地規定:“為了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維護社會團體的合法權益,加強對社會團體的登記管理,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制定本條例。”該條例對社會團體成立和登記管理的程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2017年1月,環境保護部和民政部共同發布的《關于加強對環保社會組織引導發展和規范管理的指導意見》指出:“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進一步促進環保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更好地發揮民間環保力量,廣泛動員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綠色發展,根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以及《慈善法》等法律法規,完善環保社會組織的管理制度,規范環保社會組織行為,加強業務指導和行業監管,注重部門協調配合,引導環保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在環境知情權和參與權方面,我國早在2007年就通過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并于2019年進行了修訂,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也規定了公眾參與制度,因此,我國有關程序性環境權利(群)的法律保障比較充分。我國生態環境部于2018年7月通過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其第1條就明確宣示:“為規范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保障公眾環境保護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制定本辦法。”該辦法是公眾參與原則在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中的具體落實,明確地承認了公眾的環境保護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其次,對于實體性環境權利群的保護,在2014年我國《環境保護法》修訂中,增加了保護優先原則。該法第5條規定:“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這樣,我國《環境保護法》可謂世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法之一。2014年我國《環境保護法》修訂中,一項重大進步就是將“健康”要素納入了該法,其第1條規定了該法的立法目的:“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其第39條規定:“國家建立、健全環境與健康監測、調查和風險評估制度;鼓勵和組織開展環境質量對公眾健康影響的研究,采取措施預防和控制與環境污染有關的疾病。”為貫徹我國《環境保護法》《“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十三五”環境與健康工作規劃》的有關精神和要求,保護環境和公眾健康,原環境保護部于2017年6月印發了國家環境保護標準《人體健康水質基準制定技術指南》和《環境與健康現場調查技術規范橫斷面調查》,這標志著環境與健康標準正式納入國家環境保護標準體系。這些規范意味著在我國實體性環境權更多地表現為健康環境權,它是與健康權相勾連的。我國《民法總則》第9條也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一條款標志著綠色原則被納入了我國民法。在傳統財產權保護方面,我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了環境侵權制度,在最新的民法典人格權編(征求意見稿)中也寫入了生存權、健康權。可見,我國現有環境立法和民事立法規范中對環境權的保護,可以通過生存權、健康權、財產權等條款進行間接保護。
再次,對于作為社會權的環境權利的保護,為了貫徹落實國家基本國策條款,我國目前已經先后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循環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礦產資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漁業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三十多部單行法律,總量已超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總量的十分之一。從環境法規層面來看,國務院先后制定了《自然保護區條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等環境保護行政法規130余部,并制定了國家環境標準近2000項。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條重申了憲法基本國策條款:“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國家采取有利于節約和循環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筆者認為,生態文明入憲后,環境法律體系仍不完善,仍處于動態發展中,相對于污染防治類的單行立法,需要在生態保護、資源利用以及海洋、極地環境保護立法領域進一步加強。可喜的是,許多跨區域的環境保護立法項目,如《長江保護法》《生物安全法》《南極與環境保護法》等已經啟動。
最后,對作為社會連帶性環境權利保護的具體化,應在我國《環境保護法》中進一步完善合作原則。從廣義上講,這一原則是指包括政府、人民、產業界在內的所有的環境使用者,都負有保護環境的責任。更進一步而言,國家與所有社會的力量,在環境保護的領域之中,必須共同合作,環境保護就是公共任務,國家、社會及產業界不容許逃脫此任務及責任的承擔,更何況國家任務就在于保障國民團體安全及福祉,所以國家有整合及達成合作原則的“獨占義務”及責任。參見陳慈陽:《環境法總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臺北),第335頁。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防止、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所造成的損害依法承擔責任。公民應當增強環境保護意識,采取低碳、節儉的生活方式,自覺履行環境保護義務。”這一條款從一定意義上強調了一切單位、個人都具有環境保護的義務,承擔共同的責任,但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環境立法中對政府、公民、產業界乃至國際社會共同合作進行全球環境治理的規范依據仍顯不足,這是今后立法需要加強的重點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