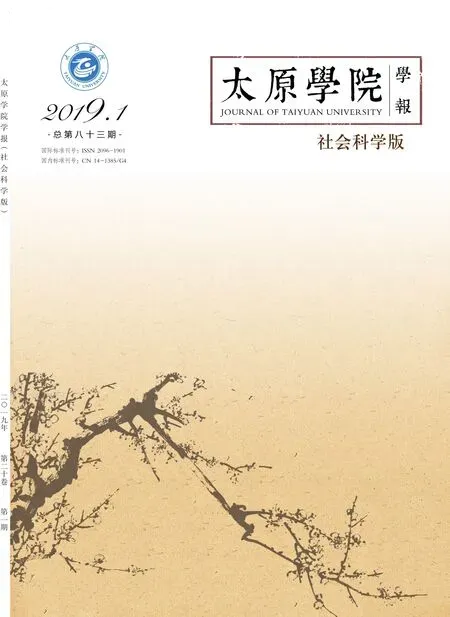論勢力范圍、租借地與國家自由
——以《民報》為考察對象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黨校 黨史黨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330003)
甲午中日戰爭不僅僅是中國這個“老大帝國”首次被一向向中國學習的日本打得如此之悲慘,而且它標志著西方列強主要由商品輸出轉向向中國進行大量的資本輸出。這雖然說明清王朝對外開放的程度更加擴大和深化了,但是這是被迫的,是清王朝被列強一次次打敗后所帶來的嚴重后果。這時,西方列強在中國強行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和強占租借地,給中國的國家自由帶來嚴重損害,引起了《民報》學人對清政府的極大不滿和憤慨。
一、勢力范圍與國家自由:吾國領土主權之存亡尤有不堪設想者
甲午中日戰爭之后,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例如英國的勢力范圍在揚子江,法國的勢力范圍在廣東、廣西、云南及海南島,日本的勢力范圍在福建,等等。這些勢力范圍既不是中國與各國之間的買賣,也不是中國的贈與,更不是中國領土的割讓,它雖然仍是中國的地盤,但是各國在其勢力范圍內有很大的自主權,中國人反而不能與其平等。
胡漢民不僅認為勢力范圍為世界以前各國所未有,以中國為先例,“其事未至于割讓,而其失敗殆有甚”,而且指出,這是“滿政府無絲毫顧惜領土之心,且于條約故為粉飾模棱以留他日之爭點,尤叵測。”[1]543-544雖然勢力范圍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都甚大,但是并不如胡氏所說它以中國為先例,因為在1885年的柏林會議上,西方列強就開始憑借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力量瓜分非洲國家。另外,胡氏將勢力范圍的劃定歸于清政府的腐敗,表明他們對勢力范圍是非常不滿的,從而把革命的矛頭指向清政府。這有他們革命需要的一面。
歐洲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對“勢力范圍”一詞有著不同的見解,胡漢民對此做了簡要的介紹和說明。大陸法系認為勢力范圍就是“Hinterland(牽他蘭)”之義,在英語中意為內陸地區、內地、窮鄉僻壤、腹地、內陸貿易區。英美法系則認為“Hinterland”與勢力范圍不同,指出“Hinterland”為海岸之實力,是先占至何種程度之解決問題,而勢力范圍則是調和假設先占之沖突而起,所以“Hinterland”是根據實力之先占,必有其先占海岸為起點,而勢力范圍則是假設先占,無是之根據。在胡漢民看來,大陸學者對勢力范圍的解說不如英美學者之密。[1]544在這一點上,胡氏還是認識比較深刻的。
胡漢民還引用荷爾的觀點解釋勢力范圍之意,指出勢力范圍并不是有確定的意義,而是一國于政治上便其擴張領地與保護國于將來,或于軍略上妨止他國占主要位置,對于其目的地有排斥他國覬覦之權利,但是在勢力范圍內各國地位曖昧不明,難以設定何種程度有排斥他國之權利,對地理范圍也不過是有道義的要求。威斯特歷亦有此意,認為勢力范圍是由數國互約不入他國之范圍而生,如1886年英德于西部太平洋劃定勢力范圍,但是勢力范圍僅生拘束力于締盟國相互之間,而不能以之對抗第三國。[1]544-545也就是說,勢力范圍主要是為了防止列強之間在爭奪某國利益時的沖突而劃定的。
高橋作衛認為評價勢力范圍有二點值得注意:一是未開無主之地(未開化人民所住,亦為無主權之地),任由萬國自由先占,設保護地;二是各國對于無主權之地欲為先占,或設保護權,而便宜上設定勢力范圍,其設定理由也有二個。一是如果實力先占,則無勢力范圍,因為先占范圍是實力所及,否則假設為將來先占保護地,不過是一種希望,而各國以通知宣言定其地域,防止各國沖突,稱此假設的范圍為勢力范圍。二是各國對于未開地皆有對等權,于同一地有數希望之累,于是由各國之間合意,甲國宣布將先占甲地,則乙國認之,乙國宣言欲先占乙地,則甲國亦認之,由此定為各自的勢力范圍。[1]545-546簡而言之,如果用實力先占某無主之地,就是其領地,不存在勢力范圍之說;如果對某地不能靠實力占領,列強只好劃定各自勢力范圍。
胡漢民綜括以上多個學者的觀點,認為勢力范圍的含義主要有七個要點:(一)其設定必在未開無主權之地(按胡氏之說,這一點對中國就不太合適,因為列強在中國劃分的勢力范圍都是中國能行使主權的地方。);(二)由數國互約避權利之沖突而生;(三)為假設之先占,而非實力之先占;(四)既設置后,對于其地得排斥他國之覬覦;(五)以其地位之不明,非決然負保護關系之責任,則仍不能妨遏他國之侵害;(六)因保護外國人之安寧,必至為嚴重之干涉;(七)勢力范圍之結果,有漸由保護地、殖民地而歸其國所有之勢。胡漢民認為這七點是學者共通之論點,可以通過1886年英德二國之于西部太平洋和1890年英德法葡四國之于阿非利加證明。[1]546-547
一些中國人想維護國家主權而不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認為勢力范圍雖壞,但此地不至于被列強所瓜分。對于有國際法思想的胡漢民來講,問題就嚴重得多。胡漢民指責說,中國雖弱,卻非野蠻無主權之地,領土先占不能行于中國的領土,況且于無主權之地假定為勢力范圍,是對于為與競爭國而設,而不是以侵進他國而設,但是中國勢力范圍之設是為競爭之國家外又有被侵進國家,因為締約一方為被侵進之中國。在胡氏看來,即使勢力范圍之目的在于妨止他國之侵進,然條約只能生拘束力于當事者之間,如英、法、日不能直接以之對抗第三國,惟間接由中國為之對抗,因此各國在中國設勢力范圍是蔑視中國的領土主權,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勢力范圍將不堪設想于國家領土主權之存亡。[1]547-548這說明胡氏把西方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的后果看得非常嚴重。
胡漢民又認為,國家自主張其權利,茍不大反于國際法,而得以條約為之,則國際之間無不容認,否則即為無效,如鎖海之約、買賣奴隸之約,但是中國任由外國設定勢力范圍,而與之合意結約,是中國人沒有國際法的觀念,自棄其權利。[1]548-549在胡漢民看來,“善外交者重實益而絀虛文,不善外交者,反之”,而“清廷每當外交有事,亦恒為不失國體計,而所挈持不舍者,惟文字而已”,如“最甚者,至于宗主國與保護國之間,條約猶有‘不礙其國家政權,不犯其皇室尊嚴’等語”。[2]825胡氏從條約實質上對清政府進行了批評,認為清政府注重文字,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胡氏舉“不礙其國家政權,不犯其皇室尊嚴”等語為證,卻不有甚合理之處,因為“不礙其國家政權”表明這些勢力范圍仍然是中國的,“不犯其皇室尊嚴”表明列強在勢力范圍內也要尊重中國的國家榮譽,這并非如胡氏所說的如此不堪。
在劃分勢力范圍等問題上,中國注重私法文書,這是因為在清政府看來,私法文書雖不依于條約形式,然其性質效力與正式文書沒有甚大差別,如此這樣還可以防止過度刺激中國人的愛國情感,導致事情難辦。但是,西方國家重視正式文書,如法國駐清公使奄西擺氏向清政府要求正式文書,慶親王奕劻力言清國無有割讓海南及他地(法國的勢力范圍)之事,請法國不要過慮,而不欲作書。但是,法國強硬要求,加上發威嚇牒書,清政府只好應之。
列強在中國劃定勢力范圍是中國的國家自由喪失的一個方面,因此《民報》學人主張廢除勢力范圍。廢除勢力范圍比收回割讓的領土要容易得多,因為勢力范圍僅生消極權利,而不生積極權利,正如胡漢民引用威斯特歷之語所說,勢力范圍非于其自體為擴張領域而設定領土主權,或保護權,不可不從于一般適用之條件。[2]826
在如何廢除勢力范圍問題上,胡漢民認為,最好的一種方式是改造政府,因為西方列強餌于利而使清政府拋棄主權,以達其“寧贈朋友”之目的。[1]549胡漢民認為,外國強鄰,鷹瞵鶚視,而滿洲于土地、財產種種權利之要求,莫敢不聽,并非度力之不敵,而是如剛毅說,“寧贈朋友,不予家奴”。[3]3915汪兆銘也指出,自滿人觀之,漢人光復與列國蠶食,其喪失囊中物相同,所以清政府才會說“與其還之家奴,不如贈之朋友”,又說“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4]1754實際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希望國家發達和人民幸福,但是美好的愿望并不能代替殘酷的現實。在內外交困之下,清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先維護好自己的統治,也就只好“寧贈朋友,不予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因為清政府經過多次交戰后認識到西方列強不像中國古代周邊那些政權一樣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做生意,所以只要滿足他們的要求,就不用擔心國家政權被西方顛覆。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統治者也只好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了。
胡氏所說的改造政府自然就是通過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但是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胡氏即使從感情上認為“決非改造政府既富既強,無是希望”,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要保證中國以后的外交不再失敗,不使列強由消極權利進為積極權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中國國力完固,絕他國覬覦之心,則此等不并等之契約亦無實際之效力,自然不難解除。[2]826-827政府改革雖然也決非一日之功,但是只要中國人上下齊心,仍然是有希望的,例如近代日本開國后也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但是在其通過明治維新強大后逐漸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從而實現了“脫亞入歐”的重大戰略。然而,革命黨人一直堅定地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所以也就不相信清政府的改革是真的。對于清政府的改革是真是假,一時難以證明是真的,因為改革的成功需要一個過程,但是改革卻很容易被證偽,因為革命黨人很容易發現改革中的不足。改革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東西,自然有其不足性。
現在鐵道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它是西方先進文化傳入中國的結果。當時鐵路的修建,在中國遇到了相當大的難度,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鐵道運輸,從中央到地方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難以忍受鐵道的鋪設。雖然他們找的理由,在我們現在看來,那是相當可笑和幼稚,例如火車轟隆隆地響,會驚動祖先神靈等等,然而在當時大家都默然認可,甚至還有人以死相逼。后來,在李鴻章等洋務派的強力支持和西方列強的強大壓力下,中國才開始進行鐵道建設。然而,從1896年到1898年間,中國鐵道“幾盡落外人之手,而鐵道所至,礦產之利隨之,為礦產運輸之便,而鐵道又許其擴充輾轉隨人”。胡漢民認為鐵道之權是勢力范圍的變相,因為由某地至某地,惟締約國有敷設鐵道之權,而他國不得侵犯,如1899年4月英俄協商簽訂協議,規定長城以北為俄國“鐵道敷設許可之范圍”,以揚子江流域為英國“鐵道敷設許可之范圍”。在胡漢民看來,這是英俄兩國避“勢力范圍”或“利益范圍”之熟語,而特造“鐵道敷設許可之范圍”之新名,這不過是外交上之善詞而已。[5]942-943西方列強獲得的鐵道權利,更強化了他們對勢力范圍的控制或對中國某地的“變相占領”。
中國近代的鐵道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中國所能自主決定的,然而這是有原因的。胡漢民認為,中國人喪失鐵道之權,一方面是由于列國之野心,一方面是由于滿政府不知如何爭權。[5]942-943胡氏之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人鐵道之權的喪失,還在于中國人現代鐵道理念的落后性,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人常常以“天朝上國”“老大帝國”自居,蔑視其他國家,從而導致中國人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能力非常低下。在兩千多年以來,中國人早就習慣了馬車等運輸方式,自然難以一下子接受鐵道運輸。1865年,英國人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外沿護城河修建一條長達一里的“展覽鐵路”德小鐵路,這是在中國出現的最早的鐵道。雖然這不能算是實質意義上的鐵道,但是很快就被清政府勒令拆除了。1876年,在英國人“連蒙帶騙”的情況下,擅自修建了中國的第一條營業鐵道,即淞滬鐵路。因為中國人特別反感修鐵道,所以英國人想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后再想辦法得到清政府的批準和支持。但是,他們太小看中國人了,這條鐵道在運行一年多時間后,就被清政府花28萬兩白銀贖回。現代中國人誰能料想清政府花大價錢收回的鐵道竟然不是自己用,而且強行拆除了。連沒有意識形態束縛的修建鐵道在中國都有如此大的壓力,那些自由、平等、博愛等新思想就更難深入中國人的人心了。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任重而道遠,特別是人的現代化更是任重而道遠。
雖然,當時的中國試圖抗拒交通運輸的現代化,但是它是擋也擋不住的。最終,鐵道事業在中國發展了起來,然而還是問題多多。在胡漢民看來,外國人經營鐵路權,本屬國際私法范圍,但是清政府與各國交涉時不是以個人名義而是以政府名義,且與公司訂立合同之外,大半定于條約,這使清政府“純然為一公司私人之性質”,如俄占滿洲線來自1896年的《清俄密約》,法占北海港線來自《廣州灣租借條約》,英國“占有直隸省諸線及揚子江流域中諸線,皆以反抗俄國之勢力而強要以得諸清政府”。[5]942-943這種以政府名義修建鐵路的行為反映了中國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它有利于清政府加強中央集權,維護中國的大一統局面,從而加強對中國經濟的控制,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把國家降到了“公司”的性質,也就無法實行市場經濟。這也正是洋務派創辦的許多企業中存在著大量腐敗、效率低下等行為的重要原因。
中國鐵道之事,不管其結果如何,在締約之時權利已許與他國,領土主權已受限制。胡漢民認為,這明顯違反了國際法,因為國際公法之原則是土地主權于國內可以絕對行使,[5]943但是,考慮到現實,也有例外,即國際地役。在胡漢民看來,國際地役來自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媾和條件,否則必有“相當之報酬”為制限。胡漢民將國際地役分為消極地役與積極地役,并指出“于版圖內使屬于自國主權之行為,因地役權之設定而不能為之者”為消極地役,“使不屬于他國主權之行為,為地役權之設定,而能行之自國版圖內者”為積極地役。胡漢民指出,在通商條約中“以保自國人于他國之權利”,或基于友誼,或出于優待,也是對待國際交際常有之事,但是“今世文明各國以鐵道為運送機關,為國家之公路,又關系于國防,故其敷設以國有事業為主,即其認可私設者,亦未嘗以與外國人”,即使本國鐵道法無否認外國人之明文,也不得以其無明文故為反對之解釋,如《清俄密約》、《膠廣租借條約》等其所許與之鐵道敷設權,在文明國際間無此類例。所以,胡漢民說:“不必問其事實之結果,而政府失敗之罪,已莫逭也。”[5]944-945
雖然西方列強通過在中國的鐵道建設加強了其對勢力范圍的控制和掠奪,便利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但是西方列強用其先進的技術在中國修筑鐵道,推動了中國鐵道事業的現代化,逐漸引起了中國人自己修筑鐵道的熱潮。然而,由于當時清政府已經非常腐敗,導致中國人自己修筑的鐵道問題很多,特別是因為清政府允許私人興建鐵道,更是問題層出不窮,根本無法與西方列強相比。
當中國人逐漸認識到鐵道建設的重要性時,也開始向西方列強施壓,希望收回路權,所以近代中國發生了許多收回路權的運動。胡漢民認為,我國可以爭回路權,如粵漢線路為我國收回,“國民主張權利之反響如是”。在胡氏看來,“各省宜要責政府,使盡公布其與各國關于鐵道條約等,而視其厚有條件期限,今已過時喪失者,則前約自可廢棄,而利權可以回復,即按于國際地役權之性質,亦有因其久不得,使為消滅之由者,故于法理亦為無迕爭國權,而講救濟之術,非兼有所研究于法律、事實之二方面而不能,凡此皆我國民之責任也”。[5]945汪東也指出,“路礦之權,日削于外國,其尤迫者,此固必爭,爭亦必力”。[6]1603
因為中國地大物博,領土廣大,一二個列強難以將中國變為他們的殖民地,所以他們只好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在勢力范圍內,列強有很大的勢力。后來,他們又為了防止列強之間的沖突,在各自勢力范圍內實行門戶開放政策(1899年由美國首先提出,先后得到列強的贊同)。雖然他們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在中國進行“分贓”,但是也有利于維持列強之間的平衡,防止一國在中國勢力獨大。
二、租借地與國家自由:清廷實已拋棄吾國此數地者予人
租借地與勢力范圍一樣,牽連到國家自由,但是比勢力范圍更能破壞國家自由。外國人憑借強力以租借名義欺騙清政府,而清政府不懂國際法,也以租借名義欺騙國民,致使中國的一些主權在不知不覺中喪失,如上海、天津、蘇州、杭州等地方租借給日本,中國惟行警察權,沒有行政、司法等之權(領事裁判權則因于國際慣例及他之條約而來,不以租借問題發生),而威海衛、旅順、膠州灣之租借,則舉高權管轄權以予他國,純然為領域主權之問題。在胡漢民看來,租借地比勢力范圍的權力更進一層,它可以積極地行使權利,“惟我國獨受其敝”,如德之于膠州灣,俄之于旅順、大連灣,英之于威海衛,法之于廣州灣,等。[2]827
有人根據條約中“帝權不得損礙”“租借地之清國主權無所妨”等條款認為清政府仍有主權。胡漢民則認為條約雖有如此條款,但是一些高權管轄權在租借國,而不在中國,所以清政府“實已拋棄吾國此數地者予人,特各國之受之,為不以割讓之名義而已”,如威、旅、膠、廣等租界內之人民不僅不受中國主權的管轄,而且中國還負有不害列國行使支配權于租界的義務。[2]830-831
租借地與租界都是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攫取的中國之地方。雖然西方列強在其范圍內享有很大的自主權,但是其主權仍然屬于中國。在這里,顯然胡氏混用了租借地與租界的概念,因為兩者還是有區別的。一是租界建立的時間較早,基本上都是位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強從經濟角度進行考慮的,而租借地都是其在中國的軍事、政治要地,有“分而治之”的企圖。二是租界的管理模式多種多樣,既有一國管理的專管租界,也有幾個國家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既有排斥中國管理的租界,又有允許中國與西方列強一起管理的租界。租借地則是某一國家強租中國的地方,都是由一國進行管理的。
國際法大家李斯德認為,歷史上往往有為傳來取得(割讓)于占領行政之引受名義下者,于此場合,從來之國權則名義上之繼續,如奧之于土耳其之波斯尼亞、希爾息哥比拿的關系(波斯尼亞及希爾息哥比拿,雖明文上猶留保主權,然此留保者,法律上無意義);英占領塞甫拉斯亦如是;德國租借膠州灣,英國租借威海衛,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皆如是。胡漢民則認為,此論有名實不符之點,奧之于波斯尼亞、希爾息哥比拿,英之于塞甫拉斯,國際法上謂行政占領,不得出于行政范圍外,與俄、德、英、法之租借占領之性質不同,因為租借者由條約定其權力,不僅僅限于行政。[2]834-835
一般而言,國家對于領土之關系有三,即領土主權、保護權及勢力范圍。羅連士又將租借權加入,形成了國家對于領土的四種關系,但是他又認為租借地之法律關系很難說明。羅連士所說,確實有一定道理,例如戰時租借地如何進行處置的問題,假使英清開戰,俄國中立,英國能否攻擊旅順港(旅順為俄國之租借地)?俄國能否禁止英國攻擊該港?胡漢民則認為日俄開戰時,日本視旅順為敵地,不生中立問題,因為俄之租借為軍港及商業保護,尤以軍事為重,不論平時還是戰時俄對其都有支配權。在胡漢民看來,在戰爭中,租借國為中立時,其租借地亦為中立。[2]836-837按胡氏之意,租借國在租借地有很大控制權,甚至租借地的命運可由租借國決定。
美濃部達吉認為,租借之名稱雖自昔日以領土為國家所有之思想而來,但其法律上之性質不得與賃貸借者相同。也就是說,租借地之區域內中國之統治權全被停止,專行租借國之統治權,純然租借國之領土,而非貸地國(清國)之領土。胡漢民受其影響,認為強國與強國相遇,所爭于國際之利害,大半以法律之關系為常,非其條約所附與或所棄失,必不生權利得喪之問題,而弱國與強國相遇,弱國恃空言為折沖,條約所定法律之性質顯豁無疑,猶且有不自保其權利之時,明明授人以柄者,用租借之名義,而以高權行使之移轉為內容,只留主權之虛名。[2]837-838這說明胡氏受日本美濃部達吉的影響,過多地強調租借國對租借地的控制,忽略了租借地的主權仍屬中國的實質,而這一點是國家自由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又有日本人認為清政府之外交是“戰國流派,而日蹙厥地,其殆師韓魏之故智”,胡漢民認為其有合理性,[2]841這有一定的道理。這也是清政府“以夷制夷”戰略的失敗。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在俄、德、法的強壓之下,被迫歸還遼東之地(中日《馬關條約》規定此地割讓給日本),被清政府認為是其“以夷制夷”戰略的最得意之手筆。清政府從此中得到好處,自以為在列強之間能游刃有余,結果拒虎引狼,喪權辱國。
雖然西方列強力圖保持對中國的均勢,但是根據利益均沾的要求,即使他們調停失敗,也會“失之桑榆,收之東隅”。清政府沒有能力維護國家主權,又弱于近代外交策略,自然被西方列強玩弄于股掌之上。例如,德國借口巨野教案中中國人殺死兩個德國傳教士為理由,先派艦隊占奪,后又提出租借要求。從國際法而言,中國此事是否理虧,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但是德國派兵,好比海賊,所以德國內部也有許多人不盡贊成這種行為。在胡漢民看來,如果當時清廷能執強硬態度,或得外交援助,不至于讓德國租借膠州,更不至于使它從此成為各國租借之濫觴。[2]841-842“東京同志”也指出,德國以山東殺二教士為藉口,奪據膠州灣,國際法學者名之曰“海賊的行動”。[7]4145也就是說,當德國二傳教士被殺后,卻派兵占領中國地方,明顯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只要清政府按照國際法原則據理力爭的辦理就是,然而,清政府并沒有這樣做。當德國與中國簽約后,非法也就變為合法了。
在德占膠州灣以前,清俄密約先許俄國以膠州灣十五年之貸借,清政府既然將膠州灣予德,俄便更有了口實,于是要求旅順和大連。清廷無奈,求援于英國,英國雖對俄有些不滿,但是并不積極制裁俄國,并且試圖也從中國得到好處,想租借威海衛。日本某氏所著的《外交史》認為英國租借威海衛,是擔心俄國租借旅順,會破壞直隸渤海灣之均勢,所以特別強調“若使俄自旅順撤回,則英于渤海灣之一港,當不敢為永借”。胡漢民則對其不以為然,認為俄國既破均勢,英國厭惡之,應力求制約俄國,但是英國復效尤租借,已是不正義之舉。[2]842-843這說明中國是塊“肥肉”,西方列強都想搶占一塊。
既然是租借,那么終究會有回收之日。然而,羅連士卻認為租借地期滿之日,當從法律和事實兩方面來看:從法律而言,條約既有期間約定解除,期間既至,自無不能回復之理,但是從事實來看,事屬將來,不得推測。日本松原一雄氏認為膠、廣之九十九年為長期租借,即使旅順、大連、威海衛為二十五年,亦以斟酌繼租,列國勢力將來會更加強大,中國想回復權利“殆近空想”。胡漢民則認為“此則不免為武斷之詞”。[2]837這說明胡漢民對于收回租借地一事是有信心的。
雖然胡漢民有信心收回租借地,但是也認為這是有條件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改造政府,并指出如果不改造政府,已喪失之外交權利鮮能回復,租借期限雖滿,即使有機可乘,亦絕對無能為力,不能僅怪別人“輕量我”,如旅順、大連租借于俄,又轉讓于日,就是如此(這是因為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勝了,俄國被迫將其在中國奪得的一些權利讓與日本)。在胡漢民看來,租借地不能隨意轉讓他國,但是日俄媾和條約卻規定旅順口、大連并其附近之領土、領水租借權及一切權利特權轉讓于日本。胡氏指出,這也不能完全怪俄國違背條約,因為《膠州灣租借條約》中有德國向中國租借之地永遠不轉租與別國的規定,但是《旅大租借條約》中沒有此語,沒有此語就不能用“永不轉租”相約束,當然俄國也不能隨意進行“交易”,而是帶有一附加條件,即惟得中國政府之承諾,此語標志著中國政府有伸縮之自由,但是日俄兩國簽訂有關中國絕大損益之條約,不許中國參與,條約既定后,以中國政府承諾為條件,只不過存其形式上以符合租借之名義。[2]839
按照國際法,條約之拘束力惟行于締約國之間,而締約國之外的第三國“不與焉”,不能因條約而使第三國負其義務。按胡漢民之意,此義務是指積極義務,而非消極義務,也就是說第三國當承認締約國之間的盟約,但是如果條約有害于第三國之權利,則可不承認。[8]111如此而論,日俄條約之拘束力本不行于中國,且條約有損害中國權利之點,則中國不得承認之,即使承認,也是有可承認之權利而非有承認之義務。
然而,我們必須重視日俄條約中所損害之中國權利已屬俄所占有之點。胡漢民也看到一點,認為中國應該在日俄構和以前反對俄國奪予中國的權利,而俄國將奪取中國的權利讓與日本,中國的權利本身沒增沒減,日本則是承繼俄國的權利,非攘奪中國的權利,所以中國運用國際法也是不能有所作為。[8]112胡氏之說,有一定的悲觀情緒,雖然當時的現實如此,但是事實上中國還是可以以國際法據理力爭的,因為只要清政府不簽字,日俄關于中國權利的條約就是非法無效的。
日本取得俄國同意后,即與清政府進行談判。在談判時,第一款就規定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允讓日本之一切概行承諾。在這種情況下,旅、大租借地雖遇可以解除條約之機,亦不能收回。按胡漢民所說,這是迫于強力,“且我之已失于俄者,爭之實難”。[2]840胡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事實也并非絕對如此。
有了日俄戰爭的先例,后來又出現了此種情況,這時候辦外交的中國人就有經驗了。一戰后,日本故技重施,在巴黎和會上想讓西方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給日本,因為在一戰中日本驅逐了德國在山東的勢力。但是,這次辦外交的中國人卻深通國際法,不再一味退讓,最終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雖然當時中國仍受列強的強大壓力,但是“弱國無外交”的理念受到了挑戰。這既說明當中國人了解國際法之后也能熟練運用好國際法,從而維護自己的國家自由,也說明中國人真的覺醒了。但是,可惜的是中國人往往睡了醒,醒了睡,并不是經常清醒的。
既然英國租借威海衛所定的期限是俄國占領旅順口之期間,那么旅順口在日俄戰爭后已不再屬俄國,威海衛是否該歸還中國呢?從理論上說,有此可能,但是在實踐上,英國仍然租借威海衛。胡漢民只好猜測說,這可能是旅順雖然不再屬俄租借,但是仍然非屬中國所有,在日本與在俄國沒什么不同,所以中國不再收回威海衛。[2]840胡氏的猜測是一方面,實際上清朝統治者抱著“寧可少一事,不可多一事”的心態,也沒有認真想過在沒到期之前就真正收回租借地的問題。
當時有消息說“德人欲歸我膠州灣”,因為德在膠州灣經營之費過巨,而議會中的一些黨員又極力反對。許多中國人“聞此說者,鮮不色喜”。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胡漢民認為,以國際法論,一國拋棄其既得權,本不生他問題,惟德與中國則不然,因為《膠州灣租借條約》第一端第五款規定“德國于租期未滿之前,自愿將膠澳歸還中國,德國所有在膠澳費項,中國應許賠償,另將較此相宜之處讓于德國”,所以,胡漢民不禁感慨說,“國力至弱,外交無援,無妄之福不易邀矣”。[2]847也就是說,即使德國有歸地之議,德必援此約以要求賠還巨款,這已非清政府所能辦,至于須將較此相宜之處為抵換,清政府更難辦。
雖然勢力范圍和租借地都是列強對中國國家自由的侵犯,但是他們在各自的勢力范圍和租借地內推行他們先進的制度和理念,不僅有利于中國進入世界大家庭之中,而且為中國一些地方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引起一系列示范效應,例如英國租借的香港和葡萄牙租借的澳門后來都成了國際化的大都市。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種發展是中國國家和中國人民付出慘痛的代價換來的。
在清王朝的末世,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國家、政府和國民可謂“百事哀”。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清政府不得不采用“以夷制夷”的方式,反而被列強所利用。它的消極作用主要是西方列強在中國占有很大的利益,中國人反而不能與之平等。它的積極作用主要是西方列強承認其勢力范圍和租借地的最高主權仍屬于中國,這一點是國家自由中非常根本的一點,因為它為中國在強大之后和平收回勢力范圍和租借地提供了合于國際性的法理依據。后來,新中國和平地收回了香港、澳門,即是由此而來,因為他們租借時間到期了。然而,我們也要看到,《民報》學人為了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自然極力批判清政府的腐敗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