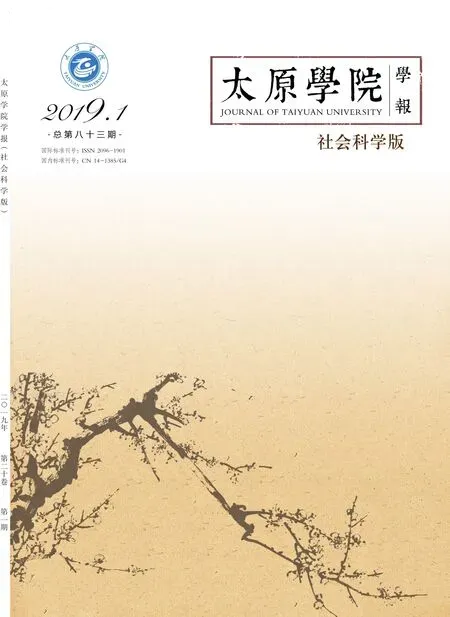論《浮世畫家》中的空間類型
李文庭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410006)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當代英國日裔作家,自1983年發表其處女作《遠山淡影》開始,便廣受好評,并與拉什迪、奈保爾一起,被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他的第二篇小說《浮世畫家》一經發表,便獲得了英國布克獎的提名。《浮世畫家》以二戰后的日本社會為背景,通過主人公小野增二的講述,“展現了普通人彬彬有禮的外表下隱藏著的真實的內心世界及震撼人心的情感之流”,“發掘了隱藏在我們與世界相聯系的幻覺之下的深淵”[1]4,描繪了小野由鼓吹軍國主義、走向人生巔峰到戰敗飽受冷遇被人遺忘的心路歷程。由于石黑一雄移民作家的身份,學界多從身份焦慮和身份認同、創傷理論、敘事學(第一人稱不可靠敘事)等角度進行研究,鮮少從空間的角度進行分析。以下筆者將從小說中的空間類型入手,對《浮世畫家》進行解讀。
一、空間解讀的必要性
《莊子》中曾談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宇指空間,宙指時間。宇宙就是在空間上無邊無際,時間上無始無終,按客觀規律運動的物質世界。這實際上點明了我們存在的時空一體性,單獨以時間維度或空間向度來描述我們的存在都會走向片面的深淵。然而,這種只側重一方的偏頗在實際的理論分析中卻難以避免。20 世紀以前的西方文藝理論大都沿襲的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開創的線性敘事傳統。《詩學》對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藝術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亞氏對線性時間、因果邏輯關系的看重奠定了日后文學作品中線性敘事的基礎。18 世紀,萊辛在《拉奧孔》中也對詩與繪畫做出了分屬于“時間藝術”和“空間藝術”的界定,提出“時間上的先后承續屬于詩人的領域”,而“空間則屬于畫家的領域”[2]1。
然而,將小說這種文學體裁簡單地歸結為一種“時間藝術”實際上是有失偏頗的。從《莊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事物既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更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20世紀以來,隨著以列斐伏爾為代表的空間理論的興起,文學理論界出現了“空間轉向”的熱潮。與此同時,現代主義文學的異軍突起更顯示了鮮明的反傳統的傾向。與傳統小說相比,現代主義小說運用時空交錯和時空倒置的方法,打破了單一的時間順序,展露了追求空間化效果的趨勢,其對象的統一性不僅存在于時間關系中,更展現在空間關系中。
由此可見,作為文學藝術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的小說實際上是具有“時空一體性”的。小說的“‘空間形式’正是在時間或時間鏈條的基礎上建構而成的”。[3]165實際上,《浮世畫家》是石黑一雄比較成熟完整的一部意識流作品。小說通過主人公小野不時偏離當前敘述的記憶回溯,展現了其顯赫一時的過往和榮光不在的當下。小說中的空間不僅僅是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事場景,更具有表現時間、推動敘事進程的重要功能。作品中所建構的開“商務會”的客廳、豪宅、左右宮等空間形式,不僅刻畫了二戰后整個日本社會傳統價值失落下的眾人虛脫迷茫的民族群像,揭示了小野個人身份歷程背后的身份認同與身份焦慮,更暗含了石黑一雄對超脫人類生存困境的探索性思考。以下筆者將通過對《浮世畫家》中空間意象的解讀,概括小說中的空間類型,分析其內涵。
二、《浮世畫家》中的空間類型
《浮世畫家》實際上是主人公小野的日記,共分為四個部分,時間跨度從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每部分的間隔大約為半年。小說主要圍繞“我”的女兒仙子的婚事,引發了“我”對于往事的種種回憶和聯想。《浮世畫家》是一部典型的意識流小說,線性時間在這里被打上了深深的“我”的主體烙印。實際上,“任何意識的流動都少不了某種空間性的物件作為其出發點”,[3]127“語言之流最終會產生某種空間”。[3]130細讀文本,我們可以發現,《浮世畫家》中營造了一些頗具意蘊的空間意象,它們各自獨立卻又互相映襯、對照,構成了戰后日本社會的“浮世”景觀,展現了廢墟與新生共存的空間格局。
(一)《浮世畫家》中的空間意象
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談到,他的小說創作在總體上受到了普魯斯特的影響,即“在作品中從A切換到B的流動敘述法”,這是一種“回顧往事,記憶模糊,填補空白,突兀轉向的寫法”。他曾說到,“在回憶時,你可以將某一個場合的片段嵌入30年之后另一個場景的片段之中,接著又回到另一場景,一個更大的場景,在回憶結束之前可能又會筆鋒一轉,轉到別的場景”。[4]137這種基于“流動敘述法”基礎之上的場景轉換,實際上跳脫了傳統小說敘事中過度重視線性時間的思維窠臼,終結了絕對時間的概念,并置了多種空間意象,任敘述者心之所至而隨意展現。
在小野的日記自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從杉村明那里購得的豪宅、左右宮與學生暢談的場景、川上夫人的酒館等不止一次出現在小說之中,這種重復出現的空間意象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作為敘事地點、場景出現,實際上卻可窺見作者靜水深流式的巧妙構思。人物的內心圖景、作者的隱含意蘊、社會語境的變遷均不動聲息地被作者網羅編織進看似理所應當的空間意象里。這些空間意象將小野、女兒仙子和節子、外孫一郎、女婿池田和大郎等人的情緒、意念嚴絲合縫式地層層包裹,使讀者難以捕捉。然而,這些空間意象是彼此參照的,約瑟夫·弗蘭克提出過“反映參照”這一概念,即在重復閱讀中通過反思記住各個意象,將這種“獨立于時間順序之外而又彼此關聯的各個參照片段在空間中熔接起來,以此重構小說的背景”。[2]4
筆者認為,石黑一雄有意識地塑造了兩種類型的空間形式——“神圣空間”和“去神圣化空間”,從主人公小野周遭的空間形式著筆,以戰敗為界,勾畫出日本社會瘡痍與新生、記憶與遺忘的復雜圖景。
(二)神圣空間
自古希臘時期,西方對空間的研究就已涉及“虛空”“處所”和“廣延”這三個基本概念。[5]35實際上,對于一般人來說,空間的意味大都包含在這三個概念之中。我們每天要經過無數的空間,卻很難有哪些空間真正被我們仔細觀察、記住。然而,對于信仰宗教的人來說,一些空間就被賦予了神圣的特性。這些空間對他們來說并非是簡單的處所,無意義的虛空和平整的廣延。在他們眼中,這些“神圣空間”具有一種中斷的特性,能夠將自身與其他空間自覺隔斷,展示出自身內在品質的不同。一個神圣空間的確立,使得一個基點成為可能,因此也使在均質性的混沌中獲得方向成為可能,并使“構建”這個世界和在真正意義上生活在這個世界成為可能。[6]17實際上,這種“神圣空間”不僅存在于教堂等宗教場所,在世俗生活中也能喚起人們對這種“非廣延“式的價值。比如,一些對個人具有特殊意義或難以磨滅的記憶的場所,如少年時的老宅、第一次去旅游的城市、戀人的家等等。這些地方也許金碧輝煌,也許很普通,但卻是他們個人生命中的“圣地”,他們從中找尋人生價值,進而確認并建構自我的主體性。
小說《浮世畫家》中,開“商務會”的客廳、從杉村明處購得的豪宅以及熱鬧喧囂的逍遙地,構成了小野生命中的“神圣空間”。首先看作者對小野父親開“商務會”的客廳的描述,“房間里沒有燈光,只在地板中央豎著一根高高的蠟燭。在那圈燭光里,父親盤腿坐在榻榻米上。……明亮的燭光使房間的其他地方都處于陰影之中”。[7]48這實質上形似邊沁所提出的“全景敞視建筑”,即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筑。[8]224盡管客廳中并無充當“瞭望塔”角色的建筑,但實際上燈光所營造出的這一中心光亮區域與四周黑暗邊緣的結構“創造和維系了一種獨立于權力行使者的權力局勢”。[8]224在這里,“我并沒有被要求說更多的話”,“父親從來就沒指望我聽懂他的話”,這種“我始終不能確定他為什么要讓我經受這樣的折磨”[7]49構成了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即父親的權威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在“我”的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即讓“我”一心一意接管家族的生意,遠離并放棄成為“骯臟而貧窮”的畫家的追求。父親的專權以及對“我”畫家夢想的打壓卻意外地點燃了“我”的雄心抱負,使“我”希望超越這樣一種生活。在這個看似有序、富有權威的地理空間——客廳中,構建了一個受限的、失去的“家”,“我”的主體價值難以從中得到確認。為了證明自己,“我”走入了“奧德賽”式的男性冒險世界,用一種更加苦澀和現實的風格演繹了“歸家”的模式。[9]43杉村明的豪宅以及逍遙地這兩個空間便是“我”歸家途中塑造英雄“自我”最重要的地理憑借。
小說開篇映入讀者眼簾的地理空間便是小野的豪宅。這棟豪宅的傳奇來歷被小野再三提及。首先,別墅之前的主人是30多年前“城里最受尊敬、最德高望重”的人之一。小野購買杉村明的房子并非僅僅是為了琉璃瓦的屋頂、美不勝收的雕梁畫棟,而是出于“和我們地位相稱”的考慮。杉樹明試圖在城市的風格中永遠留下他的印記,和“我”一樣都是“渴望超越平凡、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人。小野將自己和杉村明歸類,不僅因為兩人有著相似的成功軌跡,更是因為他們都經歷了“有尊嚴的失敗”。其次,豪宅購得的方式也頗富傳奇性。不同于常見購買中價高者得的方式,買房子的四個候選人是杉村明的家人“根據其品行和成就,嚴格挑選出來的”。[7]3在豪宅的拍賣中,作為考量的不是候選人的金錢能力,而是其道德操守和成就。這種“信譽拍賣”甚至讓“我”能夠忍受交易中杉村一家的古怪手段和專橫。盡管小野在自述中談到,購買這棟房屋不是出于虛榮,而是考慮到孩子們將來的婚配。但當杉村一家經過最為周密的調查之后,認為“我”最有資格買下房子時,“我”的滿足之情可謂是溢于言表。細致推敲小野對豪宅的描述,我們也不難發現隱藏在他得意背后的自欺。“這座房子外表壯觀、盛氣凌人……我們住在里面之后才發現,這座房子特別有助于放松心情,安享寧靜”。[7]5顯而易見,受到脅迫而得到的豪宅又怎能夠真正調節身心呢?恐怕更多撫平的是小野那顆急于證明自己、躁動不安的虛榮之心。
與小野地位相稱的地理空間除了從杉村明處購得的豪宅之外,還有戰前的逍遙地,由左右宮和川上夫人的酒館作為主要景觀加以表現。在這里,“我”是“天然的領袖”,是最受尊敬的人。在小野的回憶中,左右宮是個不斷被提起的地方。首先,左右宮的存在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勞。“我”代表左右宮的老板山形向當局提出請求,頌揚當今日本正在涌現的新的愛國精神,借以擴大左右宮的營業范圍,而當局也十分熱情地同意了“我”的這種請求。出于對“我”的感謝,山形便在左右宮的角落里專門留了一張桌子給“我”。其次,左右宮是小野和他弟子們暢談人生理想的地方。在這里,弟子們對“我”百般恭維、大唱贊歌,而我盡管表面上對他們的話不以為然,但內心里卻體驗到了一種暖融融的滿足感。除此之外,川上夫人的酒館也有著相似的空間表現意義,它們均是小野展現自身優越感的場所,象征著他所取得的成就和榮耀。
客廳、豪宅、逍遙地這三個富有深意的地點構成了小野生命中形塑自我的“神圣空間”。客廳昭示了父親的權威、小野無可奈何的順從以及深藏于心的壓抑與反叛。面對客廳這一“神圣空間”時小野感到了自身的軟弱、存在價值的被忽視,內心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為了釋放這種自卑感,個體的補償心理應運而生。[10]84于是,小野試圖通過事業上的成就感來補償自卑感。杉村明的豪宅、逍遙地便是他確立自我存在意義的“神圣空間”,小野在這些空間中得到了暫時的滿足,釋放了長久壓抑著的自卑情結。
(三)去神圣化空間
如果我們將《浮世畫家》的背景放到日本戰敗的語境來看,便會發現,自從裕仁天皇發布戰敗的宣言之后,日本社會長久以來隱藏著的深深的不安,仿佛決堤的洪水一般傾瀉而出,沖垮了民眾業已固守的心理高地。這種心理的傾頹之勢,不僅造成了普通民眾疲憊而絕望的虛脫之態,更表現在他們將所有的不安、憤怒投注在曾經竭力支持的軍國主義分子身上。小野作為小說中為軍國主義搖旗吶喊的畫家,在戰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民眾的冷落、憤恨、怒罵。為了留住自己過往的榮光,小野在講到可能使自己尷尬的事件時,常常會岔開話題,遮蔽自己不愿回首的過往。這種敘述層面上對歷史真相的背離是明顯的不可靠敘述。讀者可能會忽略其敘述中吹噓、沾沾自喜的內容。然而,不難發現,作者不僅在顯性情節中隱藏了敘事暗流,作出了對小野虛榮心的戲劇性反諷,更將豪宅、逍遙地做了橫貫時空的今昔對比,揭示了小野心中“神圣空間”的不穩定性、易逝性,以“去神圣化”的空間類型,昭示了蕓蕓眾生難以跳脫固有天地的悲劇性。
首先看戰后小野豪宅的變化。炸彈造成宅子的主體部分——長廊、東廂房受損。除了長廊和東廂房,陽臺的受損情況是最嚴重的,炸彈把地板都掀起來了,陽臺的一段仍然高低不平,滿是裂縫。陽臺的頂也未能在戰爭中幸免,一到下雨天,我們就不得不在地上擺一排容器,接上面漏下來的雨水。[7]8哪怕“我”極力向杉村小姐保證,極力修補受損的地方,恢復宅子的原樣。然而,戰后日本物資匱乏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經常要等上好幾個星期,才能等來一片木頭或一包釘子”。[7]7這實際上對應了小野的身份從一個聲名顯赫的軍國主義畫家到被遺忘在社會大潮中的老頭的轉變,契合了小說標題中的“浮世”,即流動中的社會價值觀。盡管豪宅尚在,經過修復后“時光又像回到了很久以前”。然而,物是人非,豪宅實際上成了小野自我防御的避難所。他一個人獨守老宅,舔舐傷口,回憶過往的榮光。在女兒們眼中,也由“支使得別人團團轉的暴君”而變得“脾氣溫柔隨和多了”的普通父親。小野的躲避實際上并不能使他回到過去,戰后被判定為軍國主義幫兇身份的他仍和其他人有著難以跨越的隔閡,他一家之主的地位也在戰敗的煙塵中消失殆盡。小野不止一次見到女兒們在深談,注意到她們做賊心虛地突然停住話頭,然后又裝模作樣地說些不痛不癢的閑話。除此之外,小野和外孫一郎也存在摩擦。他不理解一郎所喜愛的獨行俠、銀馬、大力水手等美國電影里的形象,試圖向外孫灌輸日本傳統中的義經大人、武士道典范的代表宮本武藏,卻遭到外孫的無視、憤怒,一郎發出的獨行俠、銀馬的嘶吼聲響徹了整個屋子,“我”頑強堅持的心理高地頓時決堤。為了找尋自己被剝奪了的權力,小野選擇把一郎”當作貶了值的、不受歡迎的‘負極’,將自己的恐懼投射到‘他者身上’”。[10]56不顧女兒的勸阻,強行帶一郎去看其并不想看的怪獸電影。在目睹一郎裹在雨衣中的小身體瑟瑟發抖的恐懼神情后,小野獲得了內心深處恐懼的宣泄。
戰后,逍遙地中川上夫人的酒館也失去了過往溫馨、親密的氣氛,只有“我”、川上夫人以及“不屬于精英團體”的坤太郎三人蜷縮在一起瑟瑟取暖。酒館仿佛是坐落在遠離文明世界的地方,周圍都是一片荒涼的廢墟。之后連過往的遺存——廢墟也難以見到,酒館外面正在建造一條寬寬的水泥馬路,兩旁已經打好了一排排大型辦公樓的地基。[7]123盡管“我”被川上夫人和坤太郎奉為“天然的領袖”,作為“將軍”的“我”會在一場戰役后將失散的人重新召集起來。然而,這只是一種傷懷過去、撫平內心創傷的方式,戰后遺民的我們如同川上夫人一般,內在的什么東西已經破碎、枯萎了,如幽靈一般,在這曾經逍遙地的“墓地”踽踽前行。
實際上,石黑一雄創設了“猶疑橋”這一重要的地理景觀來連接“去神圣化空間”中的豪宅和逍遙地這兩個重要地標。小說在開篇便提到了猶疑橋,走下這座橋就來到了逍遙地。小野經常在猶疑橋上駐足,凝望昔日逍遙地的廢墟。作者將“落日”這一意象點綴其間,刻畫出長日將盡中小野徘徊、猶疑的不安心態,表現出他極力逃避戰爭責任與責任難以避免的糾結、落寞。
三、空間類型背后的內涵
小說《浮世畫家》中,小野在選擇性回憶中著意構筑的以客廳、豪宅、逍遙地為代表的“神圣空間”象征了他超越父親權威,打破命運枷鎖,最終實現宏偉理想的光輝歷程。而作者巧妙設置的“去神圣化空間”則通過空間的去神圣化細致描繪了戰敗后小野竭力找尋避難所卻無可慰藉的復雜情感。實際上,這兩種空間類型具有一種立體豐富的“交互參照”作用。因為“在互文性的意義上,敘事文本以不具嚴密的內在時間與邏輯關聯所表現的空間敘事的意義,將可得到更為完整的理解”。[11]139通過對神圣空間、去神圣化空間這兩種空間類型的分析,我們挖掘其背后的內涵,即小野個人的身份認同與身份焦慮。
身份,狹義上指個人在團體中法定或職業的地位,廣義上指個人在他人眼中的重要性,[12]33個人的身份往往是通過他者的認同來完成的。另外,身份問題不僅包括正面的認同建構,還包括負面的焦慮掙扎,二者此起彼伏,動態地構成一個完整的身份問題。個人一旦無法完成認同的建構,就會失去自我的主體性和他人的尊重,陷入價值虛無的精神困境之中,難以擺脫身份焦慮所帶來的深刻的幻滅感。
《浮世畫家》中,掩映在表層空間變遷(即由神圣空間轉變為去神圣化空間)背后的是小野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這種認同被外力摧毀后的身份焦慮。對于畢生追求繪畫藝術的小野而言,畫家身份是他最為重要的身份。然而,這一身份從確立之日起就不時面臨著外界的質疑和打擊。首先看神圣空間(開“商務會”的客廳、豪宅、逍遙地)中小野的身份認同和身份焦慮。客廳中父親對“我”畫家理想的定義是危險、骯臟、貧窮和墮落,他甚至燒毀“我”的畫,令“我”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我”對“商務會”的情緒發生了由害怕到厭惡的轉變,而軟弱的母親更是加劇了這一轉變。父親的專制和母親話語權的缺失使小野難以通過他人的認可獲得個人身份的確證,由此產生身份問題的負面表征——身份焦慮。為了不使自己迷失個人身份的坐標、確認自我身份、緩解身份焦慮,小野瘋狂謀求事業上的成功,“用藝術相應當今世界的呼喚”[7]216,先后背叛了竹田大師、毛利君,在岡田—武田協會的松田智眾的影響下,致力于將藝術家與政治聯系在一起,頌揚當今正在涌現的新的愛國精神,接受了倡導侵略、擴張的主流意識形態,通過購買能夠彰顯個人“品行和成就”的豪宅以及回蕩著他豪言壯語的逍遙地完成了對自身軍國主義畫家身份的確認。然而,戰敗之后,整個社會發生了難以預知的變化,神圣空間喪失其神圣性的外在,從神壇跌落。小野在戰敗后受到了來自非軍事化、民主化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質疑,由德高望重的軍國主義畫家變為了遭人唾棄和不齒的帝國爪牙。原本能夠令小野“放松心情、安享寧靜”的豪宅卻成為令小野成日里悶悶不樂的空間,昔日繁華的逍遙地也成為了他回憶過往、遠離現實的避難所。小野難以從這些空間中獲得外界對其身份性的確認,在被指責、被隔絕、被遺忘的離群索居生活中,產生了深深的身份焦慮。他逃避過去的回憶性敘述實際上體現了自我苦悶難言的身份焦慮。
四、結語
以戰敗為界,小野生命中的重要空間一分為二,神圣空間昭示著他對抗父親、確證自我身份、緩解身份焦慮的內在訴求,而去神圣化空間則揭示了他在風云變化的時代中對自我身份又一次無可奈何的深深焦慮。兩種空間類型展現了小野在無法面對的悲劇人生中的個人困境,作者曾談到:“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是探討一種普通人無法超越自身環境的無力感”。[13]9由此,我們可以窺見石黑一雄對小野深切的悲憫和同情以及他對人類生存境遇的獨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