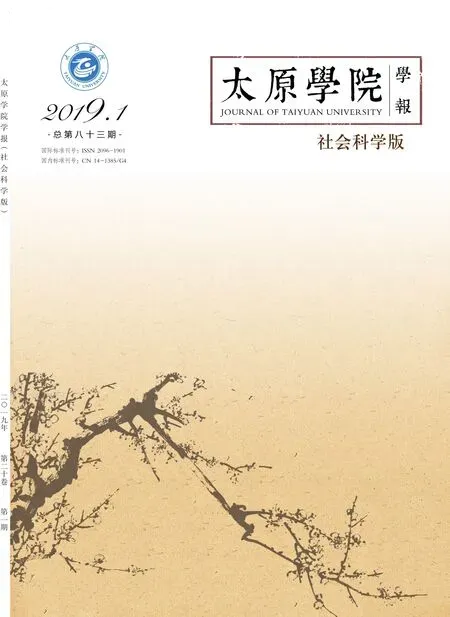問學作為一種志業和生活方式
郝慶軍
一
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卑微小公務員;因受不住基層官場的惡濁之氣,憤而考研,想過別樣的生活。盡管可能仍逃不脫另一場虛妄,但畢竟走上自己認定的問學之路。2000年,進入山東大學師從解洪祥先生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時候,我已經32歲。身邊整天活躍著一群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的師弟師妹們,我的“老成”和“沉穩”與周圍的“風景”不甚協調——我心里清楚,那其實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年齡的窘迫和對未來的不確定讓我頗感惶惑。好在,解先生并不嫌棄,常常鼓勵我說“成業有先后,問學無早晚”;適當時機,還舉一些先賢大器晚成的例子給我聽,意思是,只要一心向學,年齡不是問題。我知道自己愚鈍,甚是用功。
山東大學是以文史見長的百年學府。現代文學巨匠聞一多、沈從文、楊振聲、老舍、臧克家等前輩均在此執過教鞭,留下著述。循此淵源,我從事的現代文學學科便在這所大學留下根柢。經過歷屆學人的勉力墾殖,此學科便日益豐碩,蔚為大觀,可謂“根深葉茂,搖曳多姿”。在這樣的學術環境和學術傳統中研習,且不說常常親炙于許多著名學者,單單那氛圍和傳統便是一項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無形中的受益。此處說句題外話。前兩年“雙一流”評估,山東大學敗北,一時間閑話很多,作為校友自然心痛不已,但我認為山大學力厚重,不會因為一時一地得失而不振,只要勉力作為,勵精圖治,復興之日可待。
那時候,老師和學生都清貧,教授們尚未變成“老板”,不時興做“課題生意”;學生大抵還算“規矩”,至少還都不“忙”,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尚未嶄露頭角。于是我們便有大把的閑暇時間坐而論道。那時的師生之間,關系也算單純。老師大多“迂腐”,學生尚未學會趨時和媚世,經常圍爐夜話,敞開素心,切磋學問。苦則苦矣,可心情愉快,有一種“同你一起吃苦的幸福”。
我的導師解洪祥先生是魯迅研究的資深專家,先生的那本專著《近代理性現代孤獨科學理性——魯迅的精神歷程及其他》是我進入魯迅研究的門徑。先生的治學特點是擅長理論綜合,構建研究體系。而我等晚輩,自知不是掌控江山的推拿手,更無縱橫捭闔翻云覆雨的大手腕,只好老老實實從文本分析著手,從掌握一手材料做起。我知道,做活首先要細,日積月累,慢工出巧匠。這樣做學問,弊端是格局不夠大,氣勢欠宏闊;優點則是,吃得住細節,經得起推敲。
我第一學期的“作業”是關于蕭紅小說死亡主題的一篇論文,從蕭紅小說中關于死亡的細節分析入手,來探討作為一代才女如何應對“死亡”這個哲學大命題的。寫作之前,我細讀了蕭紅所有的小說,翻閱了關于她的大量傳記作品,這篇論文有感而發,選題還算獨到,而且有分析,有判斷,覺得挺到位的。但是,與先生“大煙大火”、摧枯拉朽式的研究方式大相徑庭,我擔心辛辛苦苦寫成的“作業”,被他一槍“斃了”,很是惶恐。
作業交上后,懷揣著二十五只小兔,百只小爪抓撓著吾心——等待著先生的判決。春節后一幫人到先生家問安,當著許多同學的面,先生很興奮地談到了我的那篇論文,大加稱贊,說了許多優點。夸我入學來很用功,學習方法正,路子對頭,做學問就應該這樣之類的話。不管怎樣,先生肯定了我,肯定了與他自己不同的研究思路,這是令我驚喜而又深思的。后來,那篇論文被先生推薦到一份雜志中發表,再后來,又被另一家著名的雜志轉載。
我喜歡個案分析。即便是談論大問題,做大題目,也不妨“法以例出”,或“理從事來”。記得攻讀碩士的第二學期,選修了孔范今先生的課。孔先生當時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業已出版,蜚聲學界,是治現代文學者的必讀書。孔先生的治學特點跟解師頗相像,亦是綜合的路子,喜歡天馬行空做大建構。人亦耿介率性,眼里不揉砂子,誰若開罪于他,必定手指哆嗦,怒目相向,頗有幾分太炎之風。且說那年課上到一半,孔先生把他著名的“小布包”往桌上一撂,用死不悔改的“曲阜普通話”突然宣布:下節課我不講了,由你們來講,題目是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天!如此“巨型”題目,我等濫竽之輩如何拿得下,吃得住?驚慌之后還得硬著頭皮去準備。我沒有花過多的時間糾纏于理論問題,而是通過對魯迅的《狂人日記》、楊沫的《青春之歌》和蘇童的《妻妾成群》三個個案的分析來辨析二十世紀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的復雜纏繞。我想,舉例說明,恐怕比空對空的邏輯推演更具說服力。于是在第二周孔先生的課上,勉力演說我心目中的“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雖然有些地方略顯生硬,竟也說得頭頭是道,一向驕傲的孔先生不由得輕輕頷首認同。后來我把講演稿略加整理,偷偷投到一家大學學報,很快被采用發表。這就是《文學中的歷史圖景》一文,現在看來,雖嫌幼稚,但畢竟是我的心血之作。
跟隨解先生讀了三年碩士,我的研究一直走的是分析的路子,而且越走越遠。到了最后寫畢業論文,竟然不可救藥地做起了考據文章:致力于探究蕭紅家庭身份,考察她的情感遭際以及造成她悲劇命運的一些性格與情感糾葛,沒有辭采飛揚的論說,也沒有上天入地的理論構架,只是一些具體的考證。比如蕭紅第一個男朋友究竟是誰?蕭紅與蕭軍之間的婚姻生活究竟怎樣?上海時期的蕭紅是一個什么情緒狀態等等,都是從一些一手材料中校讀、分析、考釋出來的,前幾年電影《黃金時代》編劇和《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在創作和報道過程中都引用了我的成果,并征求我的意見,實際是看中了論文中扎實的考證功夫。哦,不好意思,我的碩士論文題目叫《蕭紅情事考》,當時被一些同學當作笑談。在山東大學這樣的綜合類大學里,寫這樣的考據文章是注定不會得到重視的,但是先生還是給了我支持,鼓勵我按照自己的思路推動自己的研究。
二
治學的確不是“自古華山一條道”。解洪祥先生對治學思路多樣化的寬容讓我看到學術的淵深樸茂,同時,也看到學者的端誠信達與學術繁榮之間的關系。后來我到北京繼續求學,認識了許多比解先生更著名的學者,熟悉了更多學術界的“規矩”之后,反而更加懷念我的解先生。解先生在學術界固然并不多么知名,著述也不多,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遇到的給我教益多、對我影響深的老師之一。他毫無門戶之見,不死守家法,不強人所難。他也教誨你,但不跋扈;他也批評你,但不寇仇。他令你獲益,但不市恩——他不拿“老師”這個名號交換利益,包括感情。在今天這個視學術為“資源”,視學生為“家奴”,視課題為“敲門磚”,極力追求學術名利,追求所謂“成功”的風氣中,我無比懷念那種清潔的精神,懷念那種寬松而緊張的學習環境。解洪祥先生給我的最大人生啟示是:有一種教授既不知名,也不風光,著述不多,籍籍無名,但是他帶給你真實的力量,他的存在讓你覺得這個世界還有救。做教授不必名揚四海,只需誠懇,真實;千萬別做那種虛幻的,拼搶的,名不副實,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令人泛起陣陣惡心的教授。
隨著視野的開闊和學力的長進,后來我意識到,搞研究不可能永遠走“分析”的路子,沒有理論綜合的分析只是打撈碎片,是饾饤之學的腐儒作為,是魯迅先生諷刺的那種“老死南墻”死讀書的呆子所做的事,不會有大出息。但注重分析和實證研究會避免空疏,避免大而無當的理論運行與概念推演。理想的狀態是綜合的時候能進得去,分析的時候能出得來,就像民間所說的“既能下得廚房,又能上得廳堂”。
在問學之路上沒有走太多的彎路,我算是個幸運者。2003年碩士畢業后很順利地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學者楊義、李存光二位先生繼續攻讀現代文學的博士學位。在北京讀書,經常與早年非常仰慕的學界精英們打交道,自然視野開闊,也祛除了某些神秘感。但用功是必須的。在一個尊重知識,尊重學問的地方,沒有知識和學問,或缺乏吸收新知的能力,你隨時都會感到凄惶,感到窒息。
社科院的研究生院設在望京,那是個面積不大但相對安靜的院落。它的北邊是一條小河,前面是機場高速。宅書上講,背面有河,前有通衢,不順,雖然它的前面那條路叫“京順路”。我畢業不久,研究生院便搬到京西南房山的良鄉,有更大的發展,都是后話了。那時候,機場快軌還沒開通,不像現在這樣吵鬧。如果喜歡晨跑,你可以獨自享受校園的安靜,站在校操場上面向東方,可以獨自迎接一個個寧靜晨光的到來。
在這個院落里,我定下了“讀全集”的目標。我在這里一口氣閱讀了魯迅、茅盾、沈從文、老舍、胡適、周作人等六位作家的全集,同時整理他們的年表。也是在這里,《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等原始期刊悉數閱讀一遍。研究生院三樓閱覽室里有一套完整的復印本《申報》,綠色的麻布套封,散發著淡淡的油墨味道。那種味道很特別,很好聞,至今還能清晰地憶起。影印本是上海書店出的,用紙上好,裝幀也算考究。翻閱的時候,那泛著柔和光澤的紙頁,在你的指掌中磨擦出“刷拉刷拉”的聲響,令人想起白楊樹油綠的葉片在暮春的晚風中飛舞的聲音。從早晨八點半到中午十一點半,從下午的兩點到傍晚的五點,我花了整整兩個學期的時間把1910年至1936年的《申報》翻了一遍。
有一年搬家,偶然翻出我當時復印的《申報》文章和紀錄零星閱讀感受的筆記本。當年我一遇到感覺有價值的文章,都會把它們復印下來,回到宿舍,小心地把它們裝訂成卷,卷首有我寫上細字目錄,卷末附上手工索引,一本本碼好,以備后來方便查看。這些東西后來成為思考寫作的重要參考,許多有意思的題目是在細細翻閱這些手工復印卷宗不期然產生的。
那時候十三號地鐵線尚未開通,從望京到建國門社科院文學所要坐403路公交車。我和楊義先生每周二見一次面。公交車是那種加長型的大車,擠和慢是它的特點。在售票員京腔京韻的報站聲中,那車“匡當匡當”,碾著千古不變的緩慢節奏,從四元橋一路逶迤開往北京站。去一次建國門,來回花在路上的時間至少需要三個小時。那真的是一種“熬”。李存光先生在研究生院任職,每逢上課,他主動招呼我們。兩位導師都是名師,早已名揚海內外,著作等身,又擔任重要的行政職務,時間緊張。但對學生要求頗嚴,毫不含糊。閱讀書目必須在特定時間完成,布置的功課要求質量亦高。每次與導師“會晤”,須作充分準備。讀書心得,疑難問答,都須丁是丁,卯是卯,絲毫馬虎不得。與師對坐,真的是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那又是另一種“熬”。到后來,時間久了,“熬”,成了我的日課,成了一種修煉方式。正所謂“熬至滴水成珠”,三年下來,功課和學問便與時俱進,文章也越寫越有感覺。很多有分量的論文,基本上都是在這樣的情境下“熬制”而成的。
三
從研究蕭紅到研究魯迅是順理成章的事情。1934年蕭紅蕭軍夫婦去上海投奔魯迅,迅速成為魯迅文學圈子中的核心成員,本身就是很耐人尋味的。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魯迅用那么大的熱情,花費那么多的精力去扶持這對沒有任何“人脈”、不會給魯迅帶來任何“資源”、更不知道巴結逢迎趨炎附勢、在貧病愁苦中掙扎的文學青年,實在不值。到底他們身上的什么東西打動了魯迅?魯迅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帶著這些問題,我去認識魯迅,了解魯迅,研究魯迅,因此,我發現了一個不同于主流學界所認同的魯迅。
來自東北鄉野,來自苦難土地的蕭軍蕭紅們所寫出的文學作品,自然不同于上海流行的才子佳人式小資作品,也不同于“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現代派作品,更不同于“新感覺派”們描摹洋場生活的都市作品。《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表現出的清新剛健的藝術氣質,那種執著于刻寫底層中國多數人精神面貌的文學理想,以及其力透紙背,毫不矯揉造作的樸實文風,讓魯迅感到欣喜。居住在上海,遭到各色文人或咒罵,或構陷,或利用,或威懾,魯迅見了太多的嘴臉與丑態,忽然看到一對樸實而率真的鄉野青年,攜帶了東北泥土的氣味,最主要的是,他們的那支生氣淋漓的筆,還沒有被都市文學頹廢之氣所熏染,他們用真性情和苦靈魂來抒寫自己對鄉村世界的真實感受,多么好啊。
由此我開始關注魯迅的精神世界中對底層民間生命的關注,也饒有興味地探究魯迅不同于他那個時代的獨特氣質。
研究魯迅是一件吃力未必見得討好的事情。魯迅太復雜,經歷太豐富,他的一生串聯著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化史。讀懂魯迅,便能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一部魯迅精神史,便是一部中國人心史。只讀魯迅的文章遠遠不夠。即便把《魯迅全集》倒背如流,也不見得能夠理解魯迅。我的方法是讀魯迅本身,兼及魯迅的周邊,讀魯迅所處的社會這篇“大文章”,讀與魯迅過從的朋友或切近的論敵。我始終懷著這樣一個樸素的信念:要想看一個人怎樣,只需看他與哪些人交往,便知他的趣味和肺腑;再則,研究一下他的敵對者的面目如何,亦可反觀此人的思想與立場。于是我開始閱讀周作人,讀胡適,讀沈從文,也讀茅盾,讀周揚,讀瞿秋白,再后來開始讀《申報》,讀《東方雜志》,讀《良友畫報》。
從魯迅中來,回到魯迅研究中去——研究魯迅的過程,實際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深入到研究對象中,與之相契合,從中激發出熱情,進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近二十年來,魯迅研究得到很大發展,原先一些與魯迅不睦而遭到冷遇的作家,得到重新評價,恢復其歷史本來面目,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學術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的內在要求。但在具體的研究中我也發現另一個問題,就是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比如對周作人的評價,對胡適的評價,對施蟄存的評價,對梁實秋的評價,我覺得主流學界的認識有些偏差。我發現,若評價這些作家在文學史、思想史的獨特地位,并沒有多大問題,一旦涉及到他們與魯迅的論爭時,持論者往往按捺不住情緒,開始指摘魯迅,遷怒于魯迅。這嚴重妨礙了研究的深入,其本身就是一個頗可玩味的問題。我在研究中越來越覺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應該予以辨正。
于是,我把魯迅與上述幾個作家的關系作了某些方面的重新梳理,重新回到問題的原點,回到話題的中心,選擇一個關節點,在一個問題上長驅直入。比如研究魯迅與周作人關系的文章很多,精彩者不乏其例。但我覺得多數研究只停留在現成結論的論證上,或醉心于做翻案文章,或糾纏于所謂“文學性”,很少深入到歷史文化情境中做比較研究。我選擇周作人一再提及的“晚明”作為研究的重點,從周作人對晚明的重視來分析他的文學史觀,從他的“新文學的源流”論來觀察他的文學抱負,從他的提倡小品文來反觀他的文學趣味。魯迅亦重視“晚明”,他對晚明的研究也相當深入,但他發掘出的“晚明”和周作人的“晚明”頗為不同。不妨說,周作人看到的是一個風花雪月的晚明,而魯迅則發現了一個血腥虐殺的晚明,兩個“晚明”在現代中國的碰撞,反映出不同的文學史觀,也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思潮的沖突與糾葛,進而我們可以看到魯迅挺立于時代潮流中不屈時流,發出獨立聲音的姿態和形象。這篇論文《兩個“晚明”在現代中國的復活——魯迅與周作人在文學史觀上的思想分野和話語沖突》,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引起學界同仁討論,成為一時的熱點話題。
魯迅的復雜性不容許研究者偷懶,任何僥幸、討巧和自以為是都會阻礙研究的進展。如果一味引用成說,遷就權威,取悅時流,勢必造成新的遮蔽。但是,更應該警惕的是,面對魯迅的復雜性,面對研究視野的多維性,我們有可能無所適從,左支右絀,陷入新的不可知論。魯迅的形象是鮮明的,正如他鮮明的愛憎。研究魯迅固然應該占有豐富的材料,但不能成為材料的奴隸,不能迷失在叢碎的材料中,應該有明確的結論,有清晰的判斷。關于探討魯迅晚年參與的幾場著名的論爭,我并沒有簡單地說誰對誰錯,而是通過一個問題竭力去揭示論爭的社會起因、思想背景以及此問題的歷史回聲。自然我也毫不回避是非判斷,更不隱瞞自己的價值取向,我只是用材料分析和史實梳理來努力破障除弊,盡一個學者的本分而已。博士論文《詩學與政治:魯迅晚期雜文研究(1933-1936)》于2007年出版后,魯迅研究“重返政治領域”的話題開始引起學界關注,因為這部書呼應了“新左派”與“自由派”論爭,尤其是對“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興起的力量回響做出了歷史梳理,也被視為當代魯迅研究重新出發的一種艱難探討。
四
做學問回避不了質疑和問難——對別人的或對自己的。讀書多了,思考自然加深,對一些成說或流行的東西保持著一份警惕,心頭不時縈繞著一些問題,然后把這些問題與自己掌握的知識和經驗加以比照,梳理,論證,疑問就會產生。為了解決自己的疑惑,必須去掌握更多的知識,尋求便捷有效的論述方式,生成新的理論框架。于是,解答這些疑問的過程便成了不斷追求新知,進而催生新的問題、推動知識再生產的循環過程。
當然,存疑和質疑,亦有風險。上世紀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界對本學科的研究邊界有新的劃分,并進行熱烈的討論。就現代文學的起點而言,許多學者意欲推翻“五四”文學革命起點說,而把起點放在“晚清”。代表學者是海外的王德威。其“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觀點,成為學科邊界上延的動員口號,其“被壓抑的現代性”之說,也幾成學界圭臬。許多學者對此說非常認同,眼看著研究晚清成為一種時尚,而我對學界這種一窩蜂盲目跟隨海外學者一己之見的做法頗不以為然。
從學理來講,這一說法并非沒有道理。任何革命性的思潮都不是沒有歷史因由的。五四文學革命免不了受梁啟超、黃遵憲諸人在晚清時期倡導的文學革新運動影響,這是不容忽視的文學史實;但如果據此來把現代文學的源頭歸結為晚清,我認為還是有些牽強。且不說五四文學精神與晚清文學精神有質的區別,魯迅一代作家同梁啟超們又有更大的不同,單單就文學形式——白話文寫作這一道坎,你就很難超越。晚清作家也用白話,但他們是為了開啟民智,平時還是用文言;五四作家認為白話就是“我們”的語言,白話有天然的優越性,是“活”的語言,是有生命力的、與大眾生活水乳交融的思想載體。另外,我認為王德威把五四文學當做壓抑晚清文學的存在也是不符合事實的。而事實上,五四文學是從各種文化勢力的包圍和壓抑中掙脫出來的,從山林文學、廟堂文學、貴族文學,從鴛鴦蝴蝶、才子佳人、游戲人生的文學中解放出來。五四時期的人們標榜文學不是游戲,不是消遣,而是為人生,為社會的一種工作。在那時候,五四文學才是真正被壓抑的對象,而不是壓抑別人的力量。
那時候,我剛讀博士不久,還沒學會權衡,并不“考量”太多,就把自己的質疑寫成了文章,發表在《海南師院學報》上。李建軍讀后覺得文章寫得好,就推薦介紹并擇要轉載在《文藝報》上,后來此文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論文年選《2004文學評論》一書。當時也沒想太多,更沒想到會為自己找工作帶來麻煩,只是覺得抒發自己的見解,有助于自己向學術研究的深處走。今天回過頭來再讀這篇文章,雖然語氣上感覺有些生硬,但總體覺得立論站得住,敘述也可靠。當然,如果現在讓我再來寫這樣的文章,可能不會這樣直率,這樣“張嘴見喉嚨”。我會掂量對方的想法,考慮周圍的反應,措辭上會講究,語言上也選擇晦澀一點,彎曲一點。也許這叫成熟,或曰世故,但這是用自己真實的疼痛和教訓、換來的“圓滑”。魯迅先生常說,毒草之所以成為毒草,后人見到它遠遠避開,是很多前人付出生命代價之后才被認識的。這篇“惹事文章”叫《昧于歷史與過度詮釋——近十年海外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種傾向》,盡管它給我帶來許多不便,但在去年,我的專著《民國初年的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出版時,還是毫不猶豫地將此文作為附錄放在了書后。真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搞學術研究日久,寫下的文字多了,往往會對自己的文章放松警惕。但文字是有靈性的,如果不是應對考核或評職稱生湊出來的垃圾文字,就會有你的思想在里面;只要尚有一點點價值,那就會對社會產生作用——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作者都必須承擔——你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
宋代張知甫《可書》中記錄金人入侵中原時,狼牙棒作為一種武器十分了得,專門敲擊人腦而斃。于是唱戲的伶人編排說:“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魯迅在《華蓋集》中用此典故,戲謔中國對抗外敵時的無能為力。我倒覺得,此典如果用在現實生活中,也無不可。遇到問題,你必須擔當。如果你無力抗爭,躲閃不開,只有硬挺,忍著。狼牙棒來了,你又躲不過去,與其當縮頭烏龜,不如用天靈蓋相迎。寫文章的人多會遇到文字上的糾纏。文責自負,大概也沒什么可說。我想,如果你的文章惹了什么麻煩,你就必須直面,就像你的文章得到好評,也不必掩飾自己的喜悅一樣。
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之后,雖然沒有間斷學術研究,但由于一直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難以痛快淋漓地讀書寫作。無論是到《傳記文學》任主編,還是一度做過短暫的《炎黃春秋》總編輯,直到在文化藝術出版社做總編輯,一路忙忙碌碌總是脫不開身,直到2017年才有一個機會讓我全身回到科研崗位,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我對此視為人生的一大轉身,意義重大。近年來我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魯迅晚期思想的形成,魯迅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研究,以及民國初年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等方面。研究之余,從2008年開始寫小說,發表在《小說界》《小說月報》(原創版)《鴨綠江》等期刊,有幾篇曾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轉載過,后來出版了小說集《我從海德堡來》,已有三部長篇刊發。我寫小說,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調劑,說到底是對理論研究的一種補充。李陀說,小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思想,我認為是知言。如今時間充裕,自由自在,論文和小說可以并肩而行,互為補充,倒真是令人快活的一件事。從前年開始,我在研究生院給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了一門“創意寫作課”,既教學生理論,又指導他們的文學創作,試行之后,效果蠻好。教學、科研、創作三種工作方式其實歸根結底是一種生活。把問學作為一種志業,沉浸其中,以抵御惡俗侵襲,保持生命活力,尋求一種健康優質的生命方式和生命體驗,在自由創造中達致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