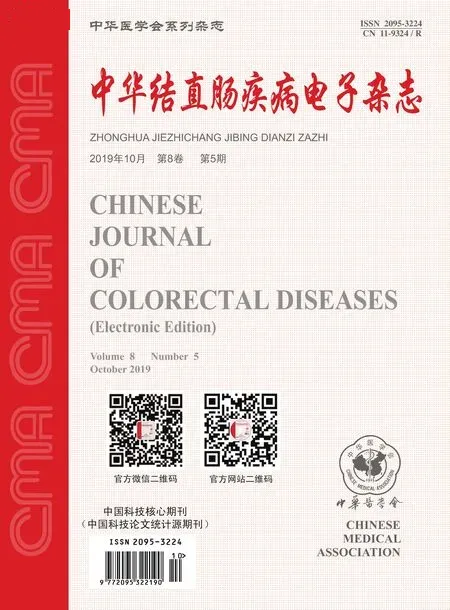循環腫瘤細胞檢測方式及臨床應用
方超 周總光
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是指從實體腫瘤原發病灶或轉移病灶脫落,進入循環系統并參與腫瘤疾病進展、轉移、復發的腫瘤細胞亞群[1]。循環腫瘤細胞理論的提出為腫瘤的復發、轉移、治療療效監測及預后評估等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2-3],而包括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及結直腸癌等的前期研究結果均在一定程度對此予以了驗證[4-7]。現階段研究對于不同腫瘤類型、不同分期患者外周循環中存在的CTC的種類及數量,CTC的分子生物學特征以及其在腫瘤疾病進展中的作用機制均存在一定爭議。同時受限于外周循環中腫瘤細胞數量稀少,且與血液細胞成分混雜,其檢測與分離極為困難,因而如何有效的檢測循環腫瘤細胞并檢獲高純度的循環腫瘤細胞成分對進一步的預后分析及機制研究顯得尤為重要[8-10];本文就循環腫瘤細胞的檢測及檢獲方式、循環腫瘤細胞現階段的臨床應用等方面進行綜述。
一、基于核酸表達的CTC檢測方式
該方法基于CTC具有區別于血液成分細胞的DNA或RNA表達而進行腫瘤患者血清中游離核酸的檢測。Gormally等[11]于2007年報道了腫瘤患者外周血循環中游離核酸的存在,而Schwarzenbach等[12]則通過擴大樣本的臨床分析,進一步發現晚期前列腺癌患者具有更高的血清游離核酸水平,證實了CTC相關游離核酸與腫瘤疾病病程的相關性。但血清CTC相關核酸檢測方法的弊端很明顯,腫瘤原發病灶或轉移病灶的微環境中的凋亡細胞、腫瘤外泌體以及循環中其他有核成分細胞所攜帶的核酸均會對檢測結果帶來顯著影響[11-13]。即便后續相關報道提出先行利用各種方法排除凋亡細胞及細胞碎片等核酸的影響,對純化后的有核細胞進行CTC相關核酸檢測的方法,但操作繁瑣且環境、操作等因素仍會明顯影響檢測結果[14]。總體而言,無論檢測樣本純化與否,利用血清特異核酸水平間接進行CTC檢測敏感度較低;同時該方法無法進一步分析CTC的分子生物學特性,而檢測血液樣本需求量較大,PCR及RT-PCR等檢測方法難于控制結果偏倚等一系列問題均制約了該方法的推廣應用。
二、基于細胞物理特性的CTC檢測方式
通常認為CTC相較于血液成分細胞具有更大的體積、更高的密度且表面電荷分布區別于其他細胞,同時部分CTC還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細胞活性以及特殊色素沉著等特性,這些差異特性逐步被認識并用于進行相應細胞的檢測及篩選[15-18]。前期相關研究有報道利用細胞密度的差異通過梯度離心的方式實現包括CTC在內的單核細胞與紅細胞的分離鑒別,但通過該方法分離后的CTC細胞中仍會混雜小部分的單核細胞[15]。Vona等[16]的研究利用CTC直徑通常大于粒細胞的特點通過過濾平臺分離循環上皮腫瘤細胞;Marrinucci等[17]后續的研究也證實了該方法的可行性;但循環上皮CTC細胞之間直徑差異較大,會導致部分CTC的遺漏;同時過濾平臺對CTC的剪切作用等對細胞活性的影響也限制了檢測后的細胞用于進一步的研究分析[18]。各種利用CTC物理特性進行檢測的方法因受各類內在及外界因素的干擾,均難以實現CTC的準確檢測;但這類方法的優勢在于分選成本低,時間短,無熒光抗體等的干擾,所分選后的細胞可進一步用于后續分子生物學分析和細胞功能驗證。
三、基于細胞表面抗體的CTC檢測方式
相關細胞膜蛋白、胞漿蛋白及胞核蛋白的發現、功能驗證及應用推廣為CTC的檢測和分選提供了新的選擇,也讓檢測和分選方法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得以明顯的改善。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CTC分離技術主要依賴于CTC細胞表面特異表達的抗體,即CTC所表達的某些上皮細胞表面標志,通常而言這些表面標志并不表達于普通粒細胞。這其中,上皮細胞黏附分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因其表達于幾乎所有上皮來源的細胞而不表達于血液成分細胞故其應用最為廣泛;上皮類細胞通過與特異的EpCAM磁珠結合,再經過特定磁場的篩選,已經被用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及結腸癌CTC的檢測分離[7,19-20]。其中CellSearch體系(Veridex)是FDA批準的基于EpCAM抗體的CTC檢測系統,主要通過某些特定的抗體組合與細胞質角蛋白結合后的顯色來進行結果的判讀;檢測中將粒細胞特異的抗體CD45則作為檢測的陰性篩選條件,具體而言CTC定義為EpCAM陽性而CD45陰性表達的細胞亞群,但該方法計數時會遺漏數量不小的EpCAM及CD45共陽性的細胞亞群[20-21]。CellSearch體系為現有檢測技術方法中較為標準且已開始應用于部分臨床試驗的CTC檢測方法,但該體系的弊端主要在于其敏感度較低(大約每毫升血液僅檢測出1個CTC細胞),單次檢測通常需要較大的血樣本,且僅在腫瘤遠處轉移患者外周血中可實現CTC的有效檢測。
Nagrath及Stott等人均報道了CTC-chip的CTC檢測方法,該方法使用一約78 000個涂有抗EpCAM的抗體暗槽的硅盒,利用2~4 mL全血即能實現CTC的有效檢測;具體工作原理為血液流經硅盒體系時相應微粒在流體動力學的作用下與對應的抗體相結合,所檢獲的細胞可進一步成像檢測以及用于進一步的DNA、RNA或分子相關的檢測[22-23]。改進后的CTC-chip相較于CellSearch體系可在一定程度提高檢測的敏感度(平均每毫升血液可檢測出50個CTC細胞)及檢獲的CTC細胞純度(0.1%~50.0%),更適用于一些稀少細胞及某些特殊標本的處理;同時CTC-chip檢獲的細胞仍具有一定的細胞活性,在短時間內將檢獲的細胞予以固定及相關處理,或可實現動物活體實驗及相關研究。CTC-chip技術操作具有一定難度并未成為應用推廣的標準方法,但其較小標本即可實現較大細胞檢獲量的特點或可實現患者治療期間療效評價的監測。
越來越多基于細胞表面標記的CTC檢測方法進行試驗并加以臨床運用,其中多通量流式細胞技術因其高通量的特點可進行一些極其稀少細胞的檢測,而多熒光通道的運用可實現多表面抗體細胞的特異性篩選及檢獲[24]。同時,近年來,部分研究提出腫瘤細胞在脫落進入循環系統時會經歷一定程度的上皮間質化轉化(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即CTC會在一定程度弱化上皮類標志的表達而強化間質類細胞表面標志的表達;單純使用EpCAM作為檢測篩選標志會存在一定的偏差并遺漏部分在腫瘤進展及遠處轉移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CTC細胞[25-26];CD133,CD44,CD26,CD24,CD166等多種分子標記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及結直腸癌等實體腫瘤的CTC及循環腫瘤起始細胞等的有效檢測中得到了一定驗證[27-30]。進一步探究并驗證更加敏感及特異的表面標記,探究并推廣可操作性更強的檢測篩選方式則將是后期研究的重點及難點。
四、其他CTC檢測方式
為檢測相對稀少的CTC,部分研究者利用上皮細胞的物理及生物學特性提出了一些較為新穎的方式,比如高通量顯微成像掃面系統,即利用光纖掃描技術對上皮成分或腫瘤特異抗原進行掃描顯像分析[31];激光掃描細胞計量術(laser-scanning cytometry)則結合熒光成像及前向散射進行細胞鑒定[17];多光子活體流式細胞技術(multiphoton intravital flow cytometry)則通過注入活體動物體內的熒光標記以進行顯像檢測[32];此外CTC的電負荷差異,細胞膜壁,微絨毛等均曾被不同的研究報道用于CTC的分離[9-10]。
五、CTC作為腫瘤患者預后標記物
盡管各種CTC的檢測方法存在各種局限性,但一些大樣本的隊列研究已經開始評估CTC計數的臨床意義;多數研究都傾向于選擇更方便且操作性更強的免疫磁珠檢測的方式,并發現乳腺癌、前列腺癌及結腸癌患者外周循環中CTC均為獨立的預后相關因子[22-33]。Botteri等[34]對乳腺癌晚期患者的評估發現每7.5 mL外周循環中CTC計數大于5的患者,其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及總體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更短;同樣在結直腸癌及前列腺癌患者中也發現治療前CTC計數同預后呈負相關[34-36]。目前預后相關研究主要通過免疫磁珠法進行CTC檢測計數,但也有通過RT-PCR方法檢測患者外周循環中上皮相關標記的表達來分析CTC同預后的相關性;但RT-PCR方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因其并未純化CTC表達,所以其中包括了粒細胞等血細胞的成分表達[37]。同時部分研究將CTC基線水平同患者臨床病理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CTC表達水平同腫瘤直徑大小無明顯相關性,而同包括腫瘤浸潤程度,腫瘤血供等生物學特征相關[38]。
六、CTC作為腫瘤患者治療療效評估
通常預后研究更關心基線CTC計數高于或低于某一特定值時其同預后的相關性,而CTC計數對治療療效的評估則需要CTC檢測方式敏感度足夠高以實現整個治療期間CTC計數變化的有效監測。Nagrath及Stott等人通過CTC-chip對CTC進行檢測及監測發現肺癌、前列腺癌等患者化療、內分泌治療前后CTC計數會明顯下降;雖然治療導致的CTC計數值變化受患者個體之間差異的影響,但仍可作為評估腫瘤治療療效的參考[22,33,38]。此外 CellSearch 體系及免疫磁珠等方法亦在乳腺癌及前列腺癌轉移患者治療療效評估中得到了一定的驗證及應用[21,39]。后期研究需進一步關注治療后CTC計數的變化是否可作為監測治療療效反應的早期指標,以及其是否可作為全周期治療獲益的評判指標。
總體而言,現存的各種CTC檢測技術主要依賴于CTC的各種物理及生物學特性,各種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優勢與弊端;且在治療療效監測、預后評估方法得到了一定的驗證及應用。隨著技術的改進,特異標記物的研發及二代測序技術等的推廣;希望未來的CTC檢測技術能夠既實現外周循環中各類腫瘤細胞的完整有效檢測與高純度分離又可避免檢測方法所帶來的細胞損傷,更便于后期CTC分子特征及功能特異研究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