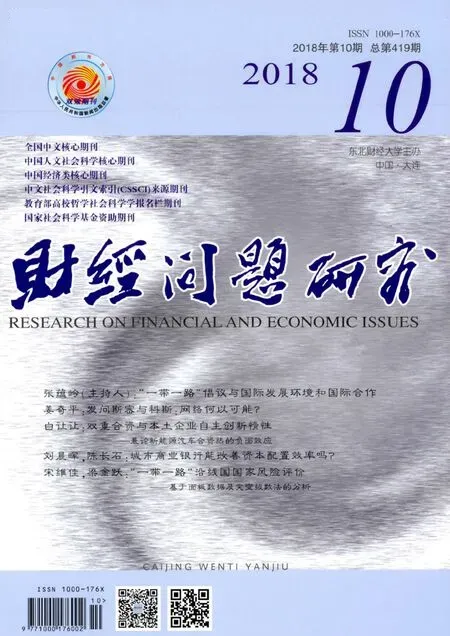組織間沖突回避動機與行為:網絡嵌入性的調節作用
蔡雙立,馬 鵬
(1.天津財經大學 商學院企業管理系,天津 300222;2.天津財經大學 商學院旅游系,天津 300222)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成長理論認為企業的成長主要依賴于內生式增長和外生式并購,然而在復雜的全球化商業環境下,通過建立企業間正式和非正式的網絡關系實現網絡化成長成為企業成長的重要途徑,其成長模式由原來的“資源—能力—成長”轉變為“網絡—資源—成長”。雖然網絡化組織有助于企業實現資源整合、能力互補、生產協同、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但這種處于“科層結構”與“市場結構”之間的過渡組織形態具有天然的不穩定性[1],并非按照預設軌跡呈現出良性關系運轉的線性演化過程。網絡關系嵌入過程存在著關系松散、低效演化、關系不穩定等問題[2],表現為復雜網絡關系下平衡、協調、解決內外各種沖突,在重復試錯中不斷優化合作關系[3]。
既然沖突是企業網絡化成長中的常態,那么如何主動規避沖突、有效管理沖突、化被動為主動、趨利避害,以達到協作的目的,借以分享網絡超額收益,享受網絡累計福利成為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問題。就沖突管理策略選擇而言,學者們從不同的理論角度給出了答案,然而沖突誘發的異質性、場域的多樣性以及沖突解決目標的錯位使得沖突解決頗具復雜性。多數學者認為直面式或整合式策略有助于化解沖突,把回避策略視為一種消極被動的不作為行為,認為回避只掩蓋了沖突的事實、緩解了沖突的程度、縮小了沖突的范圍,并非有效地解決沖突,容易引起濺溢效應。在這種拖延策略下,暫時的表面和諧孕育著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的沖突隱患。如果回避并非實質性的沖突解決方式而只是權宜之計,那么為何東方人把不顧情面的沖突視為一種不成熟、不理智行為;在沖突處理上奉行“退一步海闊天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給人留面子,給自己留回旋余地”等規避哲學。這種沖突規避的哲學邏輯和內在動機是什么?
以往研究認為沖突回避的動機和行為來源于東方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和中庸思維[4-5],這種基于文化價值觀從個體二元關系視角下的解釋剖析了中國人在沖突面前“為什么要忍”的邏輯,但是“和為貴”一定要“忍為上”嗎?這一論斷在網絡組織情境中是否存在變異,又如何變異尚不清楚。沖突策略的選擇并非只是依賴管理者決策的偏好,更體現出與組織目標和環境的匹配關系。網絡關系中關系交往程度、信任、權力、依賴方式、結構特征、第三方關系壓力等因素都影響沖突管理決策[6-7-8]。因此,有必要進行范式轉換,脫離傳統僵化的沖突最優策略范式和權變范式,考察復雜網絡關系中的結構嵌入與關系嵌入對沖突回避動機的影響[9]。
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有助于界定沖突回避的概念與形式,厘清東方文化價值觀下沖突回避的動機,探究網絡情境下的嵌入性在沖突回避策略選擇上的應用邊界。這不僅豐富了沖突管理的內容,拓展了組織間沖突研究的視角,而且有助于網絡化成長中的中小企業在沖突面前做出理性判斷與決策。
二、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一)沖突回避的內涵與形式
現有關于沖突策略的研究多基于Thomas五種沖突策略,強調合作式和整合式解決方式的正效應,而回避被視作從沖突中抽身而去,拒絕承認沖突的逃避行為,通常伴隨著不作為等行為特征。這種僵化的視角忽視了文化價值觀層面的作用。西方文化中的公平主義價值觀強調個體自由、避免社會比較,接受沖突中個人目標的追求。而崇尚集體主義的國度在沖突管理中則需要考慮身份認同、社會比較、等級差等要素,強調人情、面子的作用,講究“大事化小”,傾向采取包容、回避、利用第三方等方式來化解沖突。因此,在競爭性和合作性二元形態的沖突策略下應該增加一種適宜中國文化情境的回避性解決[10]。
沖突回避策略具有前瞻性和目的性,并非是消極不作為的單一維度。Kilmann和 Thomas[11]認為,沖突退出、延遲反應、拒絕承認沖突發生、順從都是避免沖突對抗時可能采取的方式。回避的其他表現形式還包括委婉、包容、安慰等形式,是目標導向下通過犧牲個體利益來滿足他人需求、避免對抗的前瞻性行為。因此,回避體現著暫時妥協退讓、避免直面沖突、采用迂回手段、通過第三方或群體關系來影響對方從而獲得自身利益的邏輯,包含了“被動回避—順從”和“主動回避—迂回”兩層含義[12]。順從是通過接受他人決定,抑制不滿的表達避免直面沖突,屬于被動的策略方式;迂回則是一種前瞻性的以目標為導向的積極策略,通過第三方或群體壓力或借助其他關系渠道來實現自身利益的間接策略。
根據自我控制理論,沖突回避策略受情境認知、策略選擇和結果預期的影響。在個體層面,當情境模糊、認知不清、不確定性較強時,個體會表現出防御性的順從以求降低風險追求成本最小化。在網絡關系中企業則由于權力和依賴方式的不對等導致了弱勢方往往在沖突面前敢怒而不敢言。Drory和Ritov[6]認為,在權力不對等的雙方發生沖突時,弱勢方更傾向于示弱,表現出對強勢方的服從。在文化層面,順從源于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權力距離等級差,“官大一級壓死人”就是對這種權利距離最生動的描述。在矛盾沖突中出于尊重和面子維護,地位較低的企業不會直接批評和指責地位較高的合作伙伴,而對這種“自然的”權力等級采取接受態度。
西方心理控制理論認為回避是自利行為,是在本我驅動和超我壓力以及外在現實需求下的心理舉措和防衛手段,這種自我防衛機制缺乏對他人、公眾等利益相關者的考慮。而中國式沖突回避具有社會取向。首先,回避的根本目的是維系關系和他人的面子,遵守的是人情面子的交往原則,己方暫時的退讓有助于對方強化對自己的信任,在未來交往中對方會禮尚往來,考慮到滿足己方的需求[13]。其次,關系嵌入下沖突方會具有“自滿”心理,基于信任和受關系規范的約束,他們認為可以通過人情往來、互惠信任、第三方關系壓力等方式最終說服他人、獲得他人的理解與認可,化解沖突與矛盾。“欲擒故縱”和“以退為進”就是迂回這種主動回避策略最好的詮釋。
(二)表面和諧與沖突回避
中國儒家文化重視長期導向,將對過去傳統的重視與對未來的考量同時歸到長期導向層面。這一觀念使得中國人在處理沖突中不止關注短期的利益得失,更看重未來的計劃性,希望通過營造和諧的合作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集體主義傾向的儒家社會建構的是“非對立關系”,強調個體對集體的歸屬、服從與協調,體現出了個體對集體利益和目標的傾向與妥協的“和諧觀”。
Leung[14]認為,中國人的和諧具備兩種動機:“分裂回避”和“和諧提升”。Huang[15]進一步將兩者定義為表面和諧和真誠和諧。前者指的是避免惡化關系的行為,緩解其強度和程度使之弱化直至消亡。人們將維持和諧當做一種手段,目的是自我利益保護。后者旨在建立一種長遠互惠的關系,希望通過激辯鼓勵人們積極參與互動,通過各抒己見碰撞出創新的火花,進而促進深度交流,增進感情。雖然都表現為和諧,但是第一種屬于“小人同而不和”,第二種屬于“君子和而不同”。
“和諧提升”本質上具有情感性,體現出對和諧目標的關注和追求,希望通過將心比心維護提升人際關系,表現出真誠、信任和支持等行為。而“分裂回避”則具有工具性本質,認為維系和諧是實現其他目的的途徑和方法,是出于緊張關系負面后果擔憂下的自利行為。具有真誠和諧動機的個體會發自肺腑地關心他人利益與彼此關系,投入時間精力和資源來提升關系,通過開誠布公的討論尋求最大化雙邊利益的方案。在沖突面前,他們更傾向于采用整合或合作策略來處理沖突。相反,尋求表面和諧的個體在爭議中會盡可能防止那些損害自身利益的行為發生,表現出刻意規避矛盾,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Leung等[16]發現,表面和諧與回避傾向呈正相關,表面和諧的個體會公開地向對方屈服忍讓,這并不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服從,而是希望通過示弱給對方留面子,私下迂回獲取自身利益。中國人習慣于系統性地看待時間的文化價值觀、重視過去和未來,特別是關系的遠期價值。同時,中國人又具有較低程度的不確定性容忍,導致了主觀臆想會夸大沖突的負面預期,懼怕沖突處理不得當導致關系價值的損失。兩者的合力使得中國人更愿意接受主流意見、放棄眼前利益,表現為不確定性情境下維持表面一致和團結的讓步式沖突處理方式[17]。基于以上論述,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表面和諧動機正向影響沖突回避行為。
(三)網絡嵌入性的調節作用
現有研究從個體偏好、組織規模性質和沖突類型等內生變量方面探討了回避策略產生的動機,然而,這些研究只關注了沖突主體的關系內容與屬性,忽視了網絡外部性的作用。社會網絡理論關注點正在從行為主體的屬性轉向行動者之間的關系,行動者的行為不僅受到二元關系內容和性質的影響,而且也受到其所在更大規模范圍的網絡結構、位置和關系互動方式的影響[18]。Granovetter提出了嵌入性觀點,認為社會關系影響經濟行為的機制源于網絡結構(結構嵌入)與關系的內容和性質(關系嵌入)。結構嵌入從整體網絡視角探討網絡結構中的中心度、規模和密度的影響與作用;而關系嵌入則是在人格化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關注信任、承諾、規范等要素對關系互動行為與過程的影響。
1.網絡密度的調節作用
網絡密度指的是網絡中所有行動者之間實際聯結的數目與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最大聯結數目的比值,反映了網絡中關系的平均強度[18]。高網絡密度的網絡中,成員之間的溝通效率和信息共享水平較高,更容易形成共同的期望、目標和認知一致性,促進關系規范形成、推廣和執行。
首先,高密度網絡中成員聯系緊密頻繁產生了高水平的信息共享與傳播,這使得雙方對沖突策略的反應會在網絡中迅速傳播并影響其他成員對此的態度。高密度網絡中采用強制性手段處理沖突的一方會讓其他成員感知到其真實的目的并非是為了化解沖突、維持合作關系,而是顯示其地位與權力。這種權力濫用容易產生不公平感,影響其在其他成員中的聲譽與信任[19]。這種負面評價在高密度網絡中更容易傳遞與交流,導致其在后續合作中的協調成本增加、協調能力下降。相反,在低密度網絡中沖突中的弱勢方與其他成員不存在緊密關系,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持和一致性行動,這些成員往往站在旁觀者的視角看待問題。受中立態度的支配,他們會認為沖突主體違反了關系規范,破壞了網絡關系穩定性。為了維護心理平衡抑或是達到公平的目的,其他成員希望挑起沖突的主體受到懲罰。
其次,密度較高的網絡中成員更容易了解到對方的意圖、動機和期望,形成對沖突性質、影響和沖突化解方式較為一致的感知與期望,并約束成員間的共同遵守[20]。高水平信息互動與共享削弱了合作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性和失真,使得他們對合作中的角色、信任關系有了趨同性認知,并且在沖突反應上更具一致性,展現出回避擱置爭議、維護和諧的動機與行為。高密度網絡中采取對抗式沖突策略的一方往往被視作關系規范的破壞者,其表現出的強勢與不公平對待等非道德行為容易導致集體抵制,在沖突中所獲得的收益也會被其他成員的負面反饋和回應所抵消。反之,那些采用非對抗式沖突策略,表現出維護和諧關系、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利他行為的個體更容易積累良性口碑,往往被視作潛在的合作對象,有利于關系的拓展和深化。而在低密度網絡中,集體懲罰與抵制中的一致性行動的協調成本較高、周期較長。因此,企業采取對抗式沖突策略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傳遞的范圍和速度有限,使得其不懼怕負面聲譽和群體壓力。基于以上論述,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網絡密度正向調節表面和諧與沖突回避行為之間的關系。
2.網絡中心性的調節作用
網絡中心性反映單個行動者在網絡中的地位和身份以及對網絡中其他成員資源與信息流動的控制能力[21]。中心性既給成員帶來了信息和資源獲取的便捷性,又提高其對這些資源和信息的控制能力。
網絡中心性往往與權力正相關,中心性越高的企業掌握的社會資本越豐富,動用社會資本施加影響和控制的能力越強。根據談判理論,具有高中心性的企業其網絡權力占優,較少采用讓步或妥協的沖突解決方式。受制于資源能力的約束,權力弱勢方在沖突中往往不會主動挑起爭端或者引爆沖突,而是采取息事寧人的策略。這種妥協退讓或回避策略更加強化了權力優勢方在沖突中的競爭性傾向,Wray-Bliss[8]將此界定為沖突權力優勢方的道德忽視。莊貴軍和周筱蓮[10]認為,較高中心性的成員為了體現其在網絡關系中的存在感和優越感,傾向于采用強制性手段來證明其身份和權力的合法化,因此他們不太可能在沖突中回避矛盾。基于以上論述,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網絡中心性負向調節表面和諧與沖突回避行為之間的關系。
3.人情的調節作用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基于人倫的高凝聚網絡,人情作為一種關系規范有助于判斷合作伙伴間的長期導向性。通曉人情的成員通過投入和付出展現出合作的誠意和耐心,不太計較短期得失并且在索取的同時注意對關系的投入。雖然表面和諧下企業更傾向于采取折中和間接方式處理問題和挑戰,但是當對方展現出長期合作的意圖時,這種隱晦和模糊的處理方式會增強對方的不確定性感受,會被視作對合作關系不負責抑或是關系退出的信號,影響雙方的互信與承諾。張闖等[22]的研究表明,通曉人情的企業間具有長期合作導向,會采取公開呼吁的方式來積極解決問題。
另外,同情心作為人情的另外一個重要維度體現的是相互理解和換位思考。具有同情心的合作伙伴能夠體恤他人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緒和困難,這種換位思考方式源于共享心智。共享心智模式用來描述在復雜、動態和不確定情境下團隊頻繁的隱性認知協調機制,有助于合作伙伴以共同方式來解讀信息、產生共同的未來預期,對情境形成相似的心理賬戶與判斷[23]。共享心智促使合作伙伴對合作目的和關系依存形成一致性看法,不再將關系“和諧”視作單方面獲利或規避風險的途徑,促進了和諧動機從“表面和諧”向“真誠和諧”轉換。具有換位思考的合作伙伴能夠了解和預測己方在矛盾沖突中想法、態度和難處,這不僅克服了沖突中的信息不對稱性和失真,更容易形成開誠布公的沖突規范,而不需要防備對方而隱藏己方的想法。基于以上論述,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合作伙伴的人情負向調節表面和諧與沖突回避行為之間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數據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組織間的沖突關系,因此,選取了天津濱海新區的制造業企業為樣本,涉及了醫療制藥、機械制造、電子等產業鏈相對完備的優勢行業。調研分為兩個過程:首先與MBA培訓班和天津各高校在職MBA學生面談,篩選與本文相契合的樣本企業。其次通過對這些企業的管理者做問卷內容和注意事項的培訓工作,并由他們向相關的上下游企業和同行講解、發放和填寫問卷。為了提高問卷回收率、保證調研數據真實可靠,本文為問卷填寫者提供了相關的小禮品和紅包。調研共發放211份問卷,有效問卷176份。樣本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如表1所示。
(二)測量工具
本文采用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由于研究背景和語言表述上的差異,對量表內容進行了相應的修正,并通過與部分調研企業管理者訪談溝通對量表的內容和措辭進行進一步修訂。
表面和諧(SH)參考了Leung[14]的研究,共8個題項;沖突回避行為借鑒了Sun和Tjosvold[12]的量表,共6個題項;網絡中心性和網絡密度結合了Antia和Frazier[24]的研究,分別由6個題項和4個題項構成。人情量表參考了尹洪娟等[25]的量表,由8個題項構成。所有量表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由受訪者根據實際情況真實打分填寫。
(三)量表的信度與效度
由于問卷所有變量都由管理者自我報告方式填寫,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依據Harman單因素分析法進行檢驗。主成分法提取了未旋轉的5個共同因子,解釋總變異的64.08%,其中最大特征根因子解釋了總體變異量的14.43%,表明不存在顯著的同源誤差。如表2所示,各變量的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0.700, 組合信度(CR)均大于0.70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驗證性因子分析(CFA)結果表明各題項的因子標準載荷大于0.500(P<0.001), 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值均大于0.500,說明量表題項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
表3顯示了各變量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對角線顯示各變量AVE平方根。各變量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他因子相關系數的絕對值,表明變量之間具有良好的判別效度。

表3 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結果
注:**表示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四、模型與分析結果
采用層次回歸分析法對表面和諧(SH)、沖突回避行為(CA)、網絡結構嵌入(DEN、CEN)與人情嵌入(RQ)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模型(1)—模型(2)考察表面和諧作為解釋變量對沖突回避行為的影響作用;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分別考察了網絡密度、網絡中心性和人情在表面和諧和沖突回避行為關系中調節作用。
模型(1)—模型(2):CA=β0+β1SH+β2CTRL+ε
模型(3)—模型(4):CA=β0+β1SH+β2DEN+β3SH×DEN+β4CTRL+ε模型(5)—模型(6): CA=β0+β1SH+β2CEN+β3SH×CEN+β4CTRL+ε
模型(7)—模型(8): CA=β0+β1SH+β2RQ+β3SH×RQ+β4CTRL+ε
各變量的層次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層次回歸分析結果
注:***表示P<0.05時顯著。
表4中模型(1)和模型(2)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表面和諧對沖突回避行為的正向影響顯著(β=0.328,P<0.050),假設1得到支持。模型(3)和模型(4)對比表明,R2值只從0.204增大到0.214,無顯著變化。表面和諧(β=0.322,P<0.050)、網絡密度(β=0.308,P<0.050)對沖突回避行為均存在顯著的影響,但兩者交互項(β=-0.099,P<0.050)在表面和諧動機和沖突回避行為之間存在不顯著的負向調節,與假設2相反。模型(5)和模型(6)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表面和諧(β=0.312,P<0.050)和網絡中心度(β=0.308,P<0.050)對沖突回避行為均存在顯著的影響,兩者交互項(β=-0.135,P<0.050)的負向調節作用顯著,假設3得到驗證。由模型(7)和模型(8)可知,表面和諧(β=0.252,P<0.050)和人情(β=0.406,P<0.050)顯著正向影響沖突回避行為,兩者交互項的負向調節效應顯著(β=-0.170,P<0.050),R2值增加了0.023,假設4得到驗證。
為了進一步清晰表明調節效應形態是否如假設預期,筆者選取網絡密度和人情兩個變量的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的數據繪制了調節效應圖,如圖1和圖2所示。圖1和圖2均顯示兩條線有明顯的交叉趨勢,表明在網絡中心越高和合作伙伴越重視人情時,表面和諧對沖突回避行為產生的正向影響被削弱;在低水平網絡中心性和人情時,這種影響不顯著。由此可見,高中心性和高人情關系負向調節表面和諧與沖突回避行為之間的關系。

圖1 網絡中心性的調節作用 圖2 人情的調節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本文探究了中國情境下沖突回避行為的內涵與形式,并從文化價值觀和網絡嵌入性雙重視角探究了組織間沖突回避動機的多樣性與交互性。
1.中國本土情境下沖突回避策略反映出個體對認知失調做出的自我調節與環境適應性匹配
西方心理控制理論認為,沖突回避是在本我驅動和超我的壓力以及外在現實的需要下心理舉措和防衛手段。區別于這種本體視角下的理解,東方文化價值觀下沖突回避是一種前瞻性的、以目標為導向、具有社會取向性的關系沖突處理方式。
2.沖突回避行為具有多重動機的交互性
集體主義的“和諧”價值觀決定了企業在沖突中的回避行為,即“為什么要回避”的問題;個體的負面預期從心理狀態視角回答了“怎么回避”的問題;網絡嵌入性則解釋了位置空間與互動規則對企業沖突回避行為的作用邊界。
3. 沖突回避實質上是華人企業基于理性計算和文化價值觀考量下的行為反應
無論是遠端的價值觀、中端的網絡嵌入性還是近端的個體心理狀態,沖突回避的動機歸根到底都源于中國文化與價值觀。表面和諧反映出個體在不確定性下基于負面預期的理性算計;網絡結構嵌入體現出企業在網絡組織中權力、地位、話語權等方面的等級差,是中國差序格局在網絡組織中的微觀再現;人情法則則體現關系互動中的社會取向,是儒家文化“克己復禮”思想下“情”優先于“理”的制度安排。
(二)理論貢獻與管理啟示
本文的主要理論貢獻在于:首先,本研究從中國文化價值觀視角闡述了沖突回避策略的內涵、形式與動機,展現出其在本土化應用中的權變性。其次,本研究基于沖突的復雜觀視角探討了宏觀層面的文化價值觀、中觀層面的網絡嵌入性這些沖突回避混合動機的交互性。這既是對基于個體心理特征二元主體視角下的傳統沖突理論的拓展與補充,也是沖突管理研究范式轉換的嘗試。
本文結論對管理實踐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首先,企業在沖突中不應該一味地“委曲求全”和“忍辱負重”,可以根據合作中的情境線索審時度勢地選擇積極的回避策略。其次,復雜網絡關系中企業沖突策略的選擇并不只依賴自身個體心理特征和偏好,需要轉變思維充分考慮到網絡結構和關系特征的影響,通過認清和明確自身在網絡關系中的位置,重視網絡權力結構與應用邊界以及關系互動與溝通規范的作用,靈活多樣化地選擇沖突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