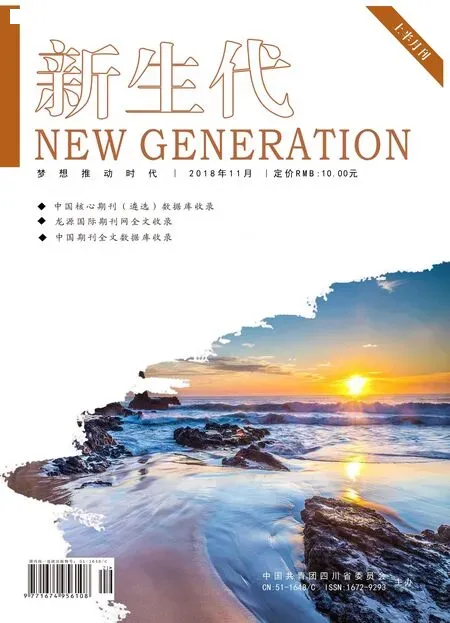民族符號學未來向度
--簡評《民族符號學論文集》
賈欣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早在1971年,匈牙利符號學家米哈伊.霍帕爾就與維爾默斯.沃伊特(Vilmos Voigt)幾乎同時提出了“民族符號學(ethnosemiotics)”的概念,開啟了民族符號學研究的大幕。民族符號學作為微觀社會與文化研究的一個常用視角而廣為人知,由于民族方法論關注日常社會活動的秩序和結構是如何被建構和隱匿存在于個人的生活之中,并強調行動者的日常生活實踐具有可說明性(accountability),反身性(reflexicality),和指示性(indexicality),它和符號學研究的聯結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在彭佳的《民族符號學探究綜述》之前,國內并沒有明確的“民族符號學”的提法,也沒有系統的民族符號學譯作或著作問世。
所以本論文集就是引介國外民族符號學的理論,匯總國內民族符號學研究的理論探討和個案研究,為該研究領域的未來發展進行知識和方法上的準備。首先,本論文集為了參照國外民族符號學的發展脈絡,編者先后翻譯了米哈伊.霍帕爾《民族符號學方法》和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的《民族符號學:一些人和理論上的反思》兩篇文章。其次就是本論文集的精華部分所在,本論文集所收錄的16篇論文的作者均為多年進行符號學,文藝學,人類學,民俗學,文學人類學,民族音樂學,民族民間文化研究學者,他們的文章或體現出對作為符號學體系的民族文化的理論思考,或者是對民族口頭傳統,身體儀式的符號化解讀。本論文集可以把論文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偏重理論和方法論探究的論文體現了符號學理論與各研究領域的融合。如徐新建的《口語詩學:聲音和語言的符號關聯》和朝戈金的《“回到聲音”的口頭詩學:以口傳史詩的文本研究為起點》兩篇論文,不約而同地從聲音符號的層次來討論口頭傳統文本,與西方民族符號學理論的發展趨勢相呼應,逐漸由結構主義對單個符號及符號體系結構的研究走向了后結構主義對文本和意義的探究,走向更廣闊,更開放的體系。納日碧力戈的《以言事與符號“仿真”》則是具體使用奧斯汀的“施為句”理論和波德里亞的“仿真”理論來分析中國民族與族群的狀況,并指出了兩種理論各自的缺陷和適用范圍。葉舒憲,烏丙安的論文分別涉及文學人類學和民俗學兩門學科的符號論,等等。
另一類則是實現理論與實踐,作者把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現象與符號學具體結合,牽涉出文化符號分析的不同側面。何星亮的《象征的類型》,討論了人們根據實證經驗的符號分類用以做裝飾,圖案的幾種編碼類型。劉俐俐的《人類學大視野中的故事問題》,梳理了故事學研究的幾種已有的理論角度,其中包括敘事符號分析。尹虎彬的《民間敘事的神話范例》,楊利慧的《語境,過程,表演與朝向當下的民俗學-表演理論與中國民俗學的當代轉型》,巴莫曲布嫫《敘事語境與演述場域-以諾蘇彝族的口頭論辯和史詩傳統為例》三篇文章,都強調了對民間敘事和口頭傳統的解讀要從文化整體和展演現場著手。李菲的《族群遺產的現代變遷:基于嘉絨跳鍋莊的田野考察》,梁昭的《漢,壯文化的交融與疏離-“歌圩”命名在思考》,楊曉的《親緣與地緣:侗族大歌與南侗傳統社會結構研究》,分別研究了藏族、壯族、侗族的民間歌舞表達符碼背后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社會結構。本文集還特地收入一篇看似與民族符號學無關系的匡宇的《論多民族文學研究的公共性-及其邊界與可能》一文,其目的是提出民族符號學研究之于中國現代性問題意義。最后以彭佳的《民族符號學研究綜述》一文結束本論文集。
符號系統的意義生產是由其深層結構決定的,而意義的具體生成,表現在民族文化中每一個象征、每一個日常生活符號的傳播中,表現在細微的符號形式與內容之變異上。符號學乃是使我們見微知著、管窺系統之整體結構的工具,尤其是,在宏大的整體結構之下,個體的意義解釋如何逆向行之,順應和改變著符號的意義和使用——而民族符號學,正是研究這些互動和變化的絕佳領域。
綜上所述,民族符號學不僅僅是符號學理論在民族學研究中的沿用,更重要的是,理論與研究對象的高度融合將對兩個學科產生反哺作用。此論文集不僅不晦澀難懂,而是把我們身邊常見的文化現象用更加科學系統的方式給我們娓娓道來,對我們研究民族符號學,把我們本民族的文化現象與西方的民族符號學理論結合,具有旗幟作用。相信不久將來,會有更多的民族符號學研究破土而出,形成蔚然大觀。